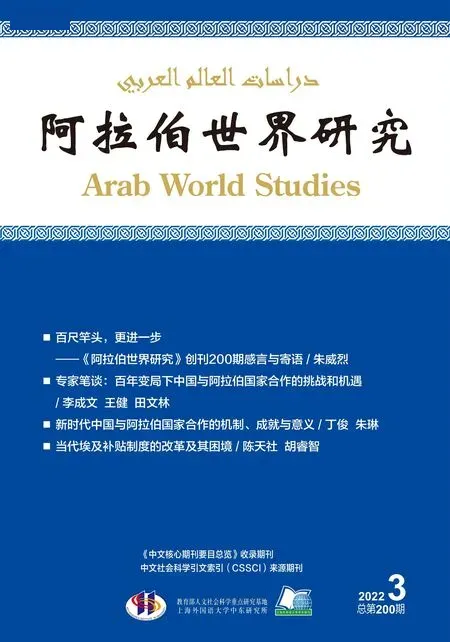埃及“隐性联盟”战略转型及其动因*
李典典 孙德刚
联盟是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是影响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促进国家间关系调整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从古代到现当代,联盟贯穿国际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结盟动机千差万别,联盟类型不胜枚举,其中“不结盟”国家的事实结盟实践赋予了联盟研究更加丰富的实例。埃及奉行不结盟政策,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浪潮兴起,埃及总统纳赛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倡导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国家自决,力图创造一条新的道路,避免在越来越两极化的地理政治环境中被吸引进美国或苏联的重力场。①[美]詹森·汤普森:《埃及史 从原初时代至当下》,郭子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8页。纵观当代埃及对外关系史,埃及作为第三世界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不结盟”是其外交政策的底色。在不结盟原则与安全需求之间,埃及选择了中间道路——“隐性联盟”。埃及隐性联盟是一种非正式弱联盟,其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先后经历了四次转型,结盟对象包括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伊斯兰力量等。为什么埃及不断调整结盟对象?其选择结盟对象的偏好是什么?
国内学界关于联盟理论以及埃及联盟实践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首先,现有成果主要聚焦正式制度化联盟研究,忽视了基于具体任务的非制度化联盟研究;②参见李海龙:《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 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郑维伟、漆海霞:《联盟制度化、自主性与北约的存续》,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87-125页;刘丰:《联盟、制度与后冷战时代的北约》,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2期,第13-17页;PatriciaA. Weitsman, Wartime Alliances versus Coalition Warfare-How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Matters inthe Multilateral Prosecution of Wars, Montgomery: ASPJ Africa & Francophonie, 2011,pp. 29-50。其次,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联盟是如何形成,并从权力、威胁、利益、身份认同等视角考察联盟的形成动因,很少有学者探讨联盟是如何调整的,即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转换结盟对象,形成新的结盟偏好;③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22页;[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1-2页;[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前言,第21页;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6、121-134页;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pp. 106-107; Dan Reiter, Crucible of Beliefs: Learning, Alliances, and World War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5。最后,现有成果大多考察结盟国家的联盟实践(如美国、欧洲国家、日本、俄罗斯等),忽视了亚、非、拉等政策宣示上奉行“不结盟”原则国家的事实结盟实践。①参见凌胜利、王彦飞:《“五眼联盟”转型:内容、原因与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4期,第27-38页;刘丰:《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6期,第23-44页;杨原:《大国政治的喜剧——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彼此结盟之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38-68页;May Darwich, Threats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Saudi and Syrian Policies in a Turbulent Re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86-120。关于埃及联盟实践的现有成果既没有解释为什么埃及在实际外交中存在类似于联盟的安全合作行为,却不愿意正式结盟,也未能回答埃及政府如何权衡“不结盟”原则与“事实结盟”实践之间的关系。②参见李典典、孙德刚:《论埃及塞西政府的“议题联盟”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1期,第145-146页;Don Peretz, “Nonalignment in the Arab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62, 1965, pp. 36-43;Robert McNamara,Britain, Nasse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1952-1967, London: Frank Cass, 2003。本文基于历史分析法,通过对埃及隐性联盟的考察,分析不结盟国家选择非正式联盟、调整结盟对象背后的具体原因。
一、埃及“隐性联盟”的概念与内涵
联盟形态千差万别,大体上可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联盟。显性联盟(tangible alliance)是可预期的制度化联盟,隐性联盟是难以预期的非制度化联盟。前者以国际安全合作制度为导向,形成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后者以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形成松散的安全合作关系。
与显性联盟不同,当代埃及隐性联盟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将当代埃及的非正式弱联盟界定为“隐性联盟”(intangible alliance),即主权国家在不结盟原则下,为维护国家战略自主性,基于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根据所要解决的安全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开展有限度的、任务导向型的非正式安全合作。第一,埃及构建隐性联盟是基于经济安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领土安全(收回西奈半岛),政权安全(打击政治伊斯兰势力、制衡以色列、土耳其)和资源安全(尼罗河水资源、东地中海天然气等)等综合安全,安全诉求具有多元性。第二,当代埃及隐性联盟是一种任务导向型的动态联盟,而不是制度导向型的静态联盟。在埃及的外交实践中,国家利益、政治体制、领导人、地缘以及宗教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因而制度化联盟不能满足埃及不同时期的战略诉求。而埃及的隐性联盟赋予了埃及在不同时期因不同战略诉求与不同行为体结盟的可能。第三,当代埃及隐性联盟战略与埃及政治领导人的性格和认知息息相关。埃及没有选择西方的分权政体,宪法赋予总统极大权限,埃及总统和主要领导人的喜好往往能决定结盟对象的选择。第四,历史经验的习得对埃及隐性联盟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埃及主要关注结盟、与谁结盟或者中立如何影响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埃及往往在战争中总结经验,建立盟友之间的信任,并且这种信任并不具备持久性,信任缺失就会立刻转向其他盟友。
隐性联盟与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者提出的“功能性联盟”“弱链式联盟”“志愿者联盟”“议题联盟”“准联盟”等都属于非制度化联盟,但划分标准不同。隐性联盟选择的参照指标是安全合作形式的外现与暗藏,而“功能性联盟”“弱链式联盟”“志愿者同盟”“议题联盟”“准联盟”选择的参照指标是合作程度的深与浅。①参见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期,第46-75页;李典典、孙德刚:《论埃及塞西政府的“议题联盟”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1期,第144-172页。显性联盟与隐性联盟都是安全合作范畴,都针对外部安全威胁,并具有对抗性,但二者属于不同类型的联盟,其背后的逻辑不同,二者在合作载体、结盟主体、合作依据、盟友关系、违约成本和主权让渡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见表1)。

表1 隐性联盟与显性联盟对比分析
由表1可见,联盟由“外衣”(体)与“内核”(用)两部分组成,显性联盟更强调“外衣”,隐性联盟更强调“内核”。显性联盟属于“一元”,隐性联盟属于“多元”。前者基于国际法,结盟本质上是国际法律问题,是主权国家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的法律承诺;后者基于实际需要,本质上是外交策略问题,是根据需要解决的安全问题而选择安全合作伙伴。显性联盟是军事一体化组织,通过结盟形成“战争共同体”,对内形成军事整合,在军事指挥、控制、通讯、情报、装备等方面形成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在对外安全上步调一致,形成合力。隐性联盟并未形成军事一体化组织——战争共同体。通过结成有限的联盟,主权国家在对外战略上保持一定的政策协调,在具体议题上形成合力,但不存在核心主权让渡(如军事指挥权和领导权),未形成统一的整体。显性联盟成本较高,包括谈判和组建联盟的初始成本以及持续的和潜在的成本等。①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 1119.隐性联盟可以节约成本,如联盟的日常管理运作等。具体来说,隐性联盟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包容性。显性联盟往往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建立,有共同的长远目标,排斥异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国家加入其中。隐性联盟基于共同任务建立,各方出于对眼前重大利益的关切,应对共同威胁而抱团取暖,不排斥与异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国家的安全合作。结盟主体往往是跨越地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②王存刚:《议题联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式》,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1日,第B03版。结盟国家与不结盟国家、不结盟国家之间都可能结成隐性联盟,即便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冲突的国家也可以结成隐性联盟。
第二,动态性。显性联盟具有稳定性,合作对象是固定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的可预期性,如冷战时期形成的北约和华约,不仅形成了对垒的军事集团,而且形成了严密的军事指挥、情报系统和财政保障系统。再比如二战后,由英美建立的多国监听组织③1946年3月5日,英美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签署“英美防卫协定”(UKUSA Agreement),建立多国监听组织“UKUSA”。演化而来的“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集军事、政治、侦察、情报于一体。显性联盟的结盟对象是相对固定的。施行隐性联盟的国际实体从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具体任务确定安全合作的对象,结盟对象是不固定的。一旦任务改变,结盟对象也会随之改变。隐性联盟各方可以在这一刻为了共同关切而抱团,也可以在任务结束后解散联盟,呈现亦敌亦友、忽敌忽友的状态。
第三,灵活性。缔结军事联盟条约或构建其他制度化的显性联盟,缔约方从国际法出发,从主权让渡、任务分担、联合行动的宏观层面审视安全合作,自上而下,分步实施。隐性联盟的国际实体不需要订立盟约,而是通过经济合作与开发项目、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在国际舞台共同发声以增强安全共同体意识,且联盟各方在其他方面存在龃龉时可以通过议题联系与共同利益加以消解。隐性联盟在任务、机制与目标,外交实践方面更具可操作性,合作形式也更加灵活,联盟各方虽未签约,却可以在规避外部压力的同时共同行动。例如,埃及加入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与苏丹等非洲国家构建隐性联盟孤立埃塞俄比亚等,均没有明确的法律文本作为合作载体,更多是基于共同议题的联合声明,并采取心照不宣的行动。
第四,有限性。显性联盟盟友多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文件,如美苏冷战时期相继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双方都是为了防范对方对己方造成的意识形态及军事安全等威胁,分别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和《友好互助合作条约》。此类官方文件是具有中长期约束性的行为规范。①孙德刚、张帅:《功能性联盟:“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联盟政治新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2期,第5页。而隐性联盟未签订正式安全合作协议,对隐性联盟行为体的约束力有限。各方多采取口头约定、承诺等,组织结构较为松散,缺乏强制约束性,大大降低了合作效力。
第五,任务导向性。显性联盟的成员国订立契约,并按照契约展开共同任务。如冷战时期美苏构建两大联盟体系,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针锋相对,阵营内部共同行动。而隐性联盟的各方基于临时任务找盟友。如为了遏制伊朗和开展反恐合作等,美国在2017年推动建立“中东战略联盟”;以色列一方面寻求与海合会六国、约旦、埃及构建“反伊朗联盟”,另一方面又与埃及、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约旦等国设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以制衡土耳其等。埃及作为以上隐性联盟成员之一,皆因本国无力完成当前的战略任务,政权安全和资源安全等没有保障,选择加入联盟以取得权力的倍增效应。埃及通过寻求与相关国家的共同诉求,塑造共同利益,以在更大范围内拥有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
在上述五个特点中,埃及隐性联盟的最大优势是动态性,突出表现为结盟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终止与旧盟友安全合作、转向与新盟友安全合作受到的法律羁绊较少、违约成本低,在利益与安全诉求变化时,政治领导人常常会通过改变结盟对象来获取更多国际资源,隐性联盟战略转型背后的动因值得深入研究。
二、埃及“隐性联盟”战略的动因考察
二战结束后,美国发起的北约军事联盟,以及在东亚建立的美日、美韩、美澳新军事联盟等双边和多边联盟具有长效性和恒定性,属于制度化的显性联盟。相比之下,埃及在不结盟原则的基础上,对外安全合作也形成了类似于联盟的行为。这种联盟不是基于规范和制度,而是基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故结成了隐性联盟。显性联盟的结盟对象是既定的,其主要任务是找敌人;隐性联盟的结盟对象是未定的,其主要任务是找资源。埃及频繁调整结盟对象,主要有三个原因:国家战略任务、历史经验习得与领导人个性特征。
首先,国家战略任务影响了隐性联盟的合作对象。隐性联盟基于任务导向而构建。对于埃及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面临的战略任务并不相同,国家战略任务是埃及政府面临的全局性重大任务。战略任务决定战略资源的索取,而战略资源的索取决定了隐性联盟的合作对象。新形势下国家根据优先考虑的战略任务、战略议题与战略目标决定隐性联盟的对象国。埃及优先选择与之建立隐性联盟关系可以促进国家战略任务、议题、目标完成的国家。
由表2可见,埃及国家面临的全局性重大任务共经过了四次转变,并且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不同的盟友选择。二战结束后,阿以问题成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埃及作为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首先将战略重点放到了“阿拉伯兄弟”上。当泛阿拉伯团结难以抵抗西方阵营侵略时,纳赛尔和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持者认为,苏联提供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不以干涉埃及为前提,接受苏联援助可以消除其外交政策的西方取向。但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的战略任务发生改变,收回失地,发展经济成为主要诉求。美国在埃以之间强大的调节能力以及优越的经济促使埃及从苏联转向美国。埃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在穆尔西上台后发生转折,穆尔西是穆兄会成员,打着“伊斯兰道路”以及“去穆巴拉克”的口号上台,外交上旨在促进亲穆兄会联盟的团结与统一,因而亲近土耳其、卡塔尔和哈马斯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但“伊斯兰道路”未能挽救埃及,埃及旧疾难医,军方代表塞西综合考量国际国内状况,出台“2030年愿景”,旨在促进埃及全方位发展,结盟对象遂从政治伊斯兰阵营扩大到更广范围,实行更加灵活多变的隐性联盟。

表2 国家战略任务的变化与埃及隐性联盟的四次转型
其次,历史经验的习得影响了隐性联盟的合作对象。不同于制度约束型联盟框架下的主权国家,埃及领导人对结盟失败的归因具有外部性,更加重视历史经验,强调意愿、决心、信任等软权力因素。①梁军:《联盟的建立与维持:历史经验视角下的理论建构与思考》,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0页。纳赛尔曾在《革命哲学》中称:“命运要我们处于世界地理的十字路口。我们常常被利用为侵略者的通道和冒险家窥伺的目标!我们经历了许多事件,如果我们不给这些事件以适当的考虑,我们就不可能理解那些潜藏在我国人民心中的各种因素。”②[埃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哲学》,张一民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8页。当结盟取得成功并维护了国家利益时,埃及就会坚持与原来的伙伴维持联盟;当遭遇战败或者未能维护国家利益时,埃及就会更换结盟对象。
埃及独立后基于历史上的联系最先与阿拉伯国家结盟,旨在推动泛阿拉伯团结以增强自身影响力。但早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溃败即使埃及认识到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分歧很大,利益分化,协调困难。历经苏伊士运河战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的埃及不愿意重新为西方国家掌控,苏联适时伸出援手,为埃及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以及技术援助,埃及遂与苏联结盟。但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苏联要么向埃及提供错误信息,要么不作为,逐渐消耗了埃及的信任。埃及认识到只有美国可以帮助埃及收复失地。此外,苏联计划经济也未能拯救埃及经济,因而埃及开始引入西方的“开放经济”,埃及的结盟对象遂由苏联转向美国。但埃及的根本性问题仍未解决,经济疲软,国家负债,西方也未能拯救埃及,“伊斯兰道路”或可一试,政治伊斯兰势力顺势上台。然而,穆尔西总统任期内埃及仍饱受就业、教育、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的困扰。“伊斯兰道路”未能成功,因而新上任的塞西政府重回世俗道路,重视民生诉求,积极发展经济,结盟对象也不再拘泥于某一国家或某一类国家,而是多面开弓,寻求多方利益。
最后,领导人个性特征影响了隐性联盟的合作对象。政治领导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行为体,对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作用。①尹继武:《试析希拉里的政治心理及对华政策偏好》,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9期,第20页。领导人个性特征包括个体所具有的独特思想、情绪、价值观、信念、感知等,这与领导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宗教背景、受教育背景等息息相关。领导人个性特征影响外交决策,是因为包括平衡威胁、选择宏大战略或走向战争等国际行为基本都是由个人做出的决定,对个人如何影响军事和外交行为进行更全面的评估是必须且有重大意义的。②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145-146.中东地区盛行威权政治,埃及是中东现代权威主义③美国学者帕尔马特将权威主义分为早期权威主义和现代权威主义,早期权威主义是少数人以少数人的名义实行的统治,而现代权威主义是少数人以多数人的名义实行的统治。的代表,埃及领导人的认知对外交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埃及政治结构中总统独大,议会弱小,个人权威主义特征突出,且总统权限由宪法明确授予。因而,埃及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温和主义与激进主义领导人在结盟对象选择上的不同偏好,导致埃及隐性联盟对象的选择不同。
领导人扩大外交决策权限、与其他机构争夺决策权是其影响隐性联盟的重要原因。从纳赛尔到萨达特乃至穆巴拉克,三位领导人都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始终坚持宗教与政治分离。纳赛尔在泛阿拉伯主义的指导下展开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萨达特上台后,拒绝泛阿拉伯主义主导政策制定,为埃以和平打开大门,启动埃美之间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合作。穆巴拉克上台后,沿袭了萨达特“埃及利益为先”的政策原则,但民生等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埃及民众对政府严重不满,对国家的不信任和不认同累积到爆发的前夕。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2008年价值观调查显示,首访埃及民众中对领导人持不满意态度的比率高达84%④郭依峰:《价值观认同视角下的埃及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争》,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6期,第101页。。与此同时,传统价值观开始回归。受访者中赞同由宗教权威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比率高达92.7%⑤同上,第103-104页。。埃及教俗矛盾达到顶峰,军方势力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穆兄会等宗教势力走向政治舞台。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担任埃及总统后,偏好与政治伊斯兰势力结盟。然而,穆尔西和穆兄会高估了埃及人民对伊斯兰教的认同。穆尔西政权很快垮台,世俗军方代表塞西上台,外交政策的伊斯兰取向被取代。可以说,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政治格局是伊斯兰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军队三方的权力斗争塑造的。①国家战略任务的确定与历史经验的习得,打上了国内政治的烙印。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相互影响,政党、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立法者、甚至公众舆论和选举不仅影响行政官员和体制安排,也影响对外政策。就埃及而言,其外交政策不仅是由领导人塑造的,而且统治阶层的利益也起到主导作用。如“一·二五革命”以来政权更迭,从穆巴拉克政府到军人临时政府、穆尔西政府、军人临时政府、及至塞西政府,军人政权作为临时过渡政府反复出现,军方的权限显露无疑。
三、冷战时期埃及“隐性联盟”战略的实例分析
埃及外交政策的抉择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历史文化记忆与现实的互动塑造了埃及隐性联盟战略的取向与行为方式的选择。在与“阿拉伯”“非洲”“伊斯兰”“西方”的日益交往中,在世界权力格局演变的影响下,埃及外交逐渐走向“隐性联盟”。冷战时期,从纳赛尔的积极中立开始,埃及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既拓展国际安全合作,又坚守不结盟原则、维护战略自主性,以任务为驱动而不是以制度为导向,在外交领域开展隐性联盟战略,并且根据不同战略任务做了两次转型。
(一)第一次转型:结盟对象从共和制阿拉伯国家转向苏联
埃及是中东地区最早倡导“泛阿拉伯团结”的国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阿拉伯世界将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埃及视为救世主。埃及则在建构民族身份的过程中注重对泛阿拉伯主义的倡导及实践。埃及共产党在1931年计划中曾言:“呼吁埃及代表所有阿拉伯人民与帝国主义战斗,并争取实现阿拉伯统一。”②Ralph M. Coury, “Who Invented Egyptian Arab Nationalism? Part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4, No. 4, 1982, p. 464.不过此时泛阿拉伯主义在埃及关于民族属性的争论中并不占据绝对优势,提倡保持法老时代民族特性的“法老主义”,主张全盘西化的“地中海主义”,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泛伊斯兰主义”等,埃及政界和知识界莫衷一是。
转机出现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兴起了大规模反犹主义浪潮,以色列建国次日,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埃及在战争中扛起大旗,自此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旗手存在。阿拉伯国家最初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等都占据优势。但以色列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联合国获得了第一次停火期,得以短暂休整。后以色列又从美国获得大量武器装备,自此,以色列扭转战局,阿拉伯国家节节败退。除了外部力量的介入,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是导致阿拉伯国家溃败的重要原因。埃及在战争中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为内部所累,埃及开始反思阿拉伯联盟内部的问题。不过,即使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重重,无论是西方还是埃及都深刻意识到了阿拉伯世界在地缘政治中的潜力。埃及独立后,面临政治、经济、安全能力薄弱的问题,英国对埃及长达72年①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954年英国与埃及就苏伊士运河达成协议,结束对埃军事占领。的占领历史以及巴勒斯坦战争中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使当时埃及的实际掌权人纳赛尔意识到绝不能加入美国构建的西方同盟以及苏联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盟。万隆会议之前,纳赛尔开始在公开声明中提出许多想法和主张,后来被称为中立或不结盟。他认为,小国必须摆脱大国统治和结盟,当今世界政治受到美苏两大阵营斗争的影响,但两大阵营力量的大致平衡可能对阿拉伯世界有利,因为它们都不允许其对手占领如此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②DanReiter, Crucible of Beliefs: Learning, Alliances, and World Wars,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71-72.随着《革命哲学》的出版,纳赛尔将阿拉伯、非洲和伊斯兰定义为埃及外交政策的“三个圈子”。阿拉伯圈子因历史、宗教、地缘等各种因素与埃及关系最为密切。纳赛尔还创办了广播节目“阿拉伯之声”,宣传其泛阿拉伯团结和抵抗西方的思想。纳赛尔政权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其最高纲领。③赵军:《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第99页。埃及特色的隐性联盟理念初步形成。自此,纳赛尔在思想上,推动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在具体行动上,推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并带领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1958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泛阿拉伯主义达到顶峰。然而,合体的埃及和叙利亚在首都所在地、政治架构、人员任命等各方面分歧日益加剧,最终导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于1961年解体,泛阿拉伯团结的尝试遭遇重大打击,泛阿拉伯主义开始退潮。
与此同时,埃苏关系稳步发展。纳赛尔执政后,为改变埃及积贫积弱的景象,在国内进行土地改革,在尼罗河修建阿斯旺大坝,并决心收回苏伊士运河。然而,由于当时正处于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企图将阿拉伯世界拉入西方阵营,将俄罗斯排斥在尼罗河之外。④[英]安东尼·纳丁:《纳赛尔》,范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3页。美国以财政援助埃及兴建阿斯旺大坝来拉拢埃及,但美国妄图以此干预埃及内政外交。埃及不愿意以牺牲主权、重新被西方大国控制的代价来换取援助,遂向苏联求援。1960年7月9日,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全国联合大会开幕式上致词说:“我们向今天的两个最大的强权美国和苏联发出了呼吁,向它们表达了我们的合作愿望。苏联做出了热情的反应,使我们能够在阿拉伯和苏联人民之间根据平等的原则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这种友谊的特点是紧密的经济合作,苏联参与阿斯旺大坝建设以及苏联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使这种友谊和合作达到了高潮。”①[英]罗伯特·斯蒂文思:《纳赛尔传》,王威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1961年7月,纳赛尔宣布选择“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埃及逐渐将结盟对象转向苏联。1962年9月,亲苏联的阿里·萨布里(Ali Sabri)被任命为部长执行会议主席,成为仅次于纳赛尔的埃及二号人物。②陈天社:《当代埃及与大国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同年,也门内战爆发,埃及将其视为在阿拉伯地区获得主动权的机遇,企图扶持亲埃及的也门共和政权。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英国、以色列和约旦等将埃及对也门的干预视为纳赛尔泛阿拉伯野心的复兴,并认为这会对他们的政权和利益构成威胁。③RobertMcNamara, Britain, Nasse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1952-1967, London:Frank Cass, 2003, p. 177.埃及在也门驻军威胁到了沙特阿拉伯和英国在亚丁的阵地,埃及与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重要盟友之间的冲突更使美埃关系紧张到破裂的地步。④Jesse Ferris, Nasser's Gamble: How Intervention in Yemen Caused the Six-Day War and the Decline of Egyptian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囿于实力不足与外部威胁,埃及愈加向苏联倾斜。值得注意的是,埃苏关系在1967年经历了一场严峻考验。1967年“六五战争”期间,苏联向埃及透露“以色列将大规模入侵叙利亚”的假情报,将埃及推到战争边缘。战争爆发后,为避免与美国和以色列空军对阵,苏联却又袖手旁观。⑤彭树智:《二十世纪中东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埃苏产生信任危机。苏联意识到埃及的不满及时弥补,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天里,派遣军舰抵达亚历山大和塞得港,莫洛绍夫海军少将宣称:“我们准备与你们的武装部队合作,以击退任何侵略者。”⑥KarenDawisha,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gyp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1979, p. 45.埃及与美英断交导致其在阿拉伯国家的威望下降,此时埃及仍呈现向苏联靠拢的趋势。此后几年间,埃苏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更为紧密。
(二)第二次转型:结盟对象从苏联转向美国
埃苏关系曾在1967年“六五战争”遭遇挫折,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平稳发展。直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苏联对阿拉伯国家表示支持,但却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战争前夕撤走了在埃及的非军事顾问及家属。埃苏之间的信任度降到最低,埃及彻底意识到只有通过美国才能拿回西奈半岛。迈出阿以和谈第一步的萨达特在自传中说道:“这里我必须说明,除了美国人,没有一个人能担负这一工作:在被可怕的仇恨、流血、憎恶、暴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持续进行的大屠杀所激怒了的双方之间进行干预。”①[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李占经、施光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7页。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萨达特个人权威主义极盛。战争后,当极度贫困和国家经济危难再次摆到眼前时,萨达特认识到,国家的资源不能再用于战争,而必须用于疲软的经济。②[美]雷蒙德·卡罗尔:《安瓦尔·萨达特》,沙仁译,北京:时事出版1985年版,第74页。埃及自此引入西方开放经济,代替苏联集中式计划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采取了国务卿基辛格改善美国、阿拉伯产油国、以色列与埃及关系的政策,且成效显著。1973年11月基辛格完成中东之行后,埃美关系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埃及和西方国家就四个主要战略目标达成了一致,包括实现中东和平,保障海湾地区的安全,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以及促进埃及发展,其中,促进埃及发展是所有目标的基石。③Abdel Moneim Said Aly and Robert H. Pelletreau, “Sadat Forum on U.S.-Egyptian Rel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8, No. 2, 2001, p. 45.1974年1月18日,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第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即《西奈半岛脱离接触协议》。2月28日,埃及与美国重新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④Mohrez Mahmoud El Hussini, Soviet-Egyptian Relations, 1945-8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p. 205.之后萨达特向美国请求援助以清理苏伊士运河,这被苏联视为埃及转向美国的信号。5月24日,莫斯科广播电台称:“美国人试图向埃及施加压力,限制苏联在运河的航行自由。”⑤Ibid., p. 205.1974年6月12日至14日,尼克松总统对埃及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其间萨达特高度赞扬了尼克松总统对中东和平的贡献。萨达特称,“美国在你(尼克松)的领导下,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推动了安理会关于叙利亚和埃及前线的停火决议。尽管这只是一个开始,但它是正确的一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没有它,就不可能在通往和平的漫长道路上取得任何进展”⑥Richard M. Nixon, Richard Nixon: 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 January 1 to August 9, 1974,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 487.。1978年9月17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经过两周的谈判,在白宫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是阿拉伯国家首次与以色列达成和解。根据协议,西奈半岛将归还埃及,以换取埃及承认以色列,埃以开放外交和经济往来。1979年3月26日,埃以双方正式签署埃以和平条约。除埃以关系正常化,埃及还在1979年之后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受援国。美国援助计划有助于埃及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如将美援用于建造开罗的下水道系统,构建电话网络以及建设数千所学校和医疗设施。①Jeremy M. Sharp, Egypt: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y 12, 2009, p. 6.
及至穆巴拉克时期,为发展经济和获得美国支持,穆巴拉克政府承袭萨达特时期的外交政策,埃美盟友关系全面发展。1982年3月,穆巴拉克发表谈话说:“我们同美国有着特殊关系,我们希望维持这种关系。”②时延春:《尼罗河之子穆巴拉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埃及在外交上表现出了对于美国一定程度上的跟随。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政府担心伊拉克也会把目光投向沙特,从而扰乱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并影响油价。布什总统遂发起“沙漠盾牌行动”,并极力争取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埃及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等于驳斥了有关这场战争是美国殖民干预的指责,并使美国得以将这场冲突描述为文明国家与违反国际法的伊拉克的对抗。③Bruce K. Rutherford and Jeannie L. Sowers, Modern Egypt: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50.作为埃及参加联军的回报,美国免除了埃及70亿美元债务。④Susan Muaddi Darraj, Modern World Leaders Hosni Mubarak, Broomall: Chelser House publishers, 2007, p. 69.在海湾危机开始后的六个月内,埃及从美国的盟友沙特、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等国家获得了47.26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和阿联酋还另外援助埃及136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要求埃及与巴黎俱乐部签订协议(豁免50%的其他债务),并要求埃及在1992年和1994年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改革计划”。通过这些安排,埃及的外债从1990年6月的476亿美元减少到1991年2月的340亿美元,1994年年中再次降至240亿美元。⑤Galal Amin, Egypt in the Era of Hosni Mubarak 1981-2011,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Press, 2011, p. 58.虽然在某些方面,埃美双方关系不对称,埃及需要做出一定让步,但显而易见,美国的援助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是无可取代的。正是由于美国的援助,穆巴拉克时期外债不再是埃及紧迫性问题之一。
(三)冷战时期埃及“隐性联盟”战略的动因分析
在埃及结盟对象从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到苏联的第一次转型中,历史经验的习得和国家战略任务的变化是其隐性联盟战略调整的主要因素。第一,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在巴勒斯坦战争中饱尝溃败之苦,又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和迅速解体中受尽打击。第二,埃及建国之初,国家亟需清除英国殖民留下的痕迹,重塑埃及大国地位。两次战争中西方国家与以色列统一战线,埃及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难以维持与以色列的对抗。埃及遂一改“泛阿拉伯团结”的大旗,转而寻求苏联的援助。虽然纳赛尔是“泛阿拉伯团结”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重要推手,但历史经验教训是推动纳赛尔转变的重要因素。
在埃及结盟对象从苏联转移到美国的第二次转型中,历史经验的习得以及国家战略任务的变化是主要动因。第一,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深感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苏联未尽盟友义务,难以信任。苏联在战争中作壁上观、置身事外,埃苏之间的信任降至最低。与此同时,埃及引入苏联集中式计划经济失败,衰败的经济形势迫使埃及转变。第二,埃及在战争中失去西奈半岛,国家领土的丧失深刻打击了国家自信。美国是唯一可以在收回失地以及发展经济两方面帮助埃及的国家。至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两位总统“以埃及利益为先”更多是基于与苏联结盟失败,与美国结盟相对成功的考量。在上述两次隐性联盟战略转型过程中,政治领导人都没有更替,但结盟对象发生了重要变化,表明领导人个性特征并非关键性因素。
四、中东变局以来埃及“隐性联盟”战略的实例分析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2011年1月,埃及爆发“一·二五革命”,总统穆巴拉克在内外部压力下宣布引咎辞职。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对埃及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变局下,埃及对结盟对象再次做出了两次重要调整:第一次是穆尔西上台后埃及从与美国结盟转向与政治伊斯兰势力结盟;第二次是塞西上台后埃及从与政治伊斯兰势力结盟转向与多元伙伴结盟。
(一)第一次转型:结盟对象从美国转向政治伊斯兰势力
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是美国在中东最忠实的盟友之一,然而穆巴拉克在“一·二五革命”中面对民众的大规模抗议而被迫下台时,美国却袖手旁观。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埃及军方施压,要求不得对抗议者使用武力。随后,埃及军方接管政权并举行总统竞选,以自由与正义党(穆兄会下属政党)以及光明党(萨拉菲派政党)为主的伊斯兰联盟成立,穆兄会成员穆罕默德·穆尔西在总统竞选中取胜。2012年,穆尔西解雇了一些军方高级领导人,包括国防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Mohamed Hussein Tantawi)和陆军参谋长萨米·阿南(Sami Anan),并在相当一部分国家职务中任用穆兄会成员。①庄北宁:《穆尔西辩护换将 否认意在边缘化军方》,参考消息网,2012年8月15日,https://world.cankaoxiaoxi.com/2012/0815/78380.s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5日。穆尔西还撤销了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条款,并发布新的宪法声明。2011年3月30日公布的《宪法宣言》第25条第2款由以下条款取代:“总统将履行本宣言第56条规定的所有职责(第56条概述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权力,包括行政和立法权力,现在由穆尔西掌握)。”①“English Text of President Morsi's New Egypt Constitutional Declaration,” Ahram Online,August 12, 2012,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50248.aspx,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5日。埃及内政外交呈现伊斯兰主义取向。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格吉斯(Fawaz Gerges)曾对穆尔西做出以下评价:“与其履行诺言,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包容性政府……穆尔西竭尽全力垄断权力,并将穆兄会置于国家机构中。”②Ruth Pollard, “After Morsi, Political Islam Losing Ground in Egypt,” SMH, August 2,2013,https://www.smh.com.au/world/after-mursi-political-islam-losing-ground--in-egypt-20130802-2r3kz.html,上网时间:2021年12月5日。
穆尔西就职埃及总统期间,埃及的战略任务是促进亲穆兄会阵营的团结与统一。埃及刚刚经历变局,国内政治斗争激烈,而穆尔西的主要支持力量来自穆兄会,这也就决定了穆尔西有必要保持穆兄会的支持。因而,穆尔西上台之初发表大量演讲,与穆巴拉克划清界限,并树立这样一种形象:他将放弃穆巴拉克对美国的屈从,终止埃及与以色列的“可耻”合作,重塑埃及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他出席阿盟峰会、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试图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埃及将不再允许任何人对其外交伙伴的选择发号施令。③Jannis Grimm and Stephan Roll, Egypt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Mohamed Morsi, Berlin:SWP Comments, November 2012, p. 1.埃及政府遂改变长期亲美的外交政策,重回伊斯兰体系。
穆尔西上台后的首访国家没有选择美国,而是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以及伊朗。作为穆兄会领导人,穆尔西也把土耳其、卡塔尔、哈马斯等作为战略合作重点。埃及与土耳其和卡塔尔结成亲穆兄会联盟的“铁三角”,以此对抗沙特等海湾国家组建的反穆兄会联盟。首先,穆尔西上台后,埃及加强了与哈马斯的接触,并考虑了哈马斯将其总部从大马士革迁往开罗的请求。其次,埃及与土耳其、卡塔尔稳步发展关系。于土耳其而言,正发党与埃及穆兄会政权修好有助于其得到土国内广大穆斯林的支持,巩固政治根基,进而扩大地区影响力。④严天钦:《土耳其正义发展党的伊斯兰民粹主义》,载《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4期,第39页。2012年9月30日,穆尔西首次访问土耳其。穆尔西在土耳其正发党年会上发表讲话称:“我们的历史、希望和目标将我们团结在一起,以实现所有国家都在为之奋斗的自由和正义。”⑤“Egypt's Morsi in Turkey: ‘Arab Spring Needs Your Support’,” Ahram Online, September 30, 2012,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54324.aspx,上网时间:2021年12月5日。同年11月,埃尔多安访问埃及期间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对穆尔西政权表示支持,称“埃及的革命向全世界表明,专制不会永远存在……独裁和封闭的政权已经结束”①Bilge Nesibe Kotan, “An Overview of Turkish-Egyptian Relations Since the Arab Uprising,”TRT World,November 27, 2017, https://www.trtworld.com/mea/an-overview-of-turkish-egyptianrelati ons-since-the-arab-uprising-12658,上网时间:2021年12月5日。。于卡塔尔而言,支持埃及穆兄会政权可以加强政治伊斯兰力量,提高话语权。这是其实施“小国大外交”的重要抓手。②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90页。卡塔尔不仅为穆尔西政府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包括数百亿的美元投资、贷款、以及免费的液化天然气油轮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还建立了名为“直播埃及”的新闻频道,对穆尔西政府进行大量报道。当然,这不仅是为了宣传革命,也是为了巩固卡塔尔以及半岛电视台在革命中的地位。③David B. Roberts, Reflecting on Qatar's “Islamist” Soft Power, Washington D.C.: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 April 2019, p. 3.埃及穆尔西政权希望借助土耳其、卡塔尔等亲穆兄会力量稳固政权,土耳其和卡塔尔也希望通过支持穆尔西政权扩大影响力,三方存在重大利益契合点,并以此开展合作。
2013年7月,在大规模反对派示威游行后,穆尔西被埃及军方推下台。土耳其和卡塔尔极力为穆尔西政权发声。11月,埃尔多安再次呼吁立即释放前总统穆尔西时,埃及决定降低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驱逐土耳其驻埃及大使侯赛因·阿维尼·博特塞利(Huseyin Avni Botsali),并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土耳其则对已经离开的埃及驻土耳其大使做出了同样的回应。④Bilge Nesibe Kotan, “An Overview of Turkish-Egyptian Relations since the Arab Uprising”.2015年5月16日,在穆尔西被判死刑当天的一次集会上,埃尔多安公开宣称:“对我来说,埃及的总统仍然是穆尔西。我一直在国际舞台上表示,我不接受塞西。”⑤Stefano M. Torelli, The Return of Egypt: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Game, ISPI,2015, p.72.卡塔尔则在穆尔西下台后就停止了对埃及的经济援助。卡塔尔发表声明称,它对民选总统穆尔西继续被拘留感到惊讶,这威胁到迫使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一·二五革命”所取得的成就。⑥“Qatar Joins Calls for Release of Egypt's Mohamed Morsi,” NDTV, July 24, 2013,https://www.ndtv.com/world-news/qatar-joins-calls-for-release-of-egypts-mohamed-morsi-529331,上网时间:2021年12月7日。随着穆尔西的下台,埃及与政治伊斯兰势力的隐性联盟寿终正寝。
(二)第二次转型:结盟对象从政治伊斯兰势力转向多元伙伴
穆尔西政府执政经验不足,政治伊斯兰未能挽救埃及,其任内最后几个月埃及饱受燃油短缺、电力中断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困扰,物价、失业和公共债务增加,货币却在贬值,信用评级降至前所未有的水平,难以获得外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和贷款。①Salem Y. Lakhal, “Morsi's Failure in Egypt: The Impact of Energy-Supply Chai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1, No. 3, 2014, p. 135.埃及军方再次接手国家政权,但穆巴拉克和穆尔西执政时期包含民主、民生和民权等的多重诉求仍然存在。这表明,埃及民众并不在乎政府是“伊斯兰”“威权”抑或“民主”,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切实保障埃及人民切身利益的政府,埃及“伊斯兰倾向”昙花一现。
塞西政府不满足于埃及在中东地区扮演配角,寻求在其议程内拥有更大发言权。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构建了非正式性的隐性联盟。
在东部,埃及基于政权安全加入美国主导建立的“中东战略联盟”。塞西上台后宣布穆兄会为非法组织,穆兄会许多成员逃到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寻求政治避难。卡塔尔和土耳其、哈马斯构筑的“亲穆兄会联盟”不仅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还利用媒体宣传其政治思想。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面对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担心其对政权统治带来威胁,遂与埃及结成统一战线。美国政治学者高斯(F. Gregory Gause III)直接指出“沙特对埃及穆尔西政府所代表的民选伊斯兰政府感到紧张。沙特一直声称为逊尼派伊斯兰说话,当一个民选的伊斯兰政府出现时,沙特民众可能会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民选政府?’”②Stefano M. Torelli, The Return of Egypt: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Game, p. 66.可见,穆兄会建立在广泛民众支持基础上的伊斯兰政治观念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传统君主制格格不入。③Bruce K. Rutherford and Jeannie L. Sowers, Modern Egypt: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p. 165.因而,沙特及其盟友不仅向塞西政府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援助和燃料捐赠等,还在政治上予以援手,如2017年,埃及、沙特、阿联酋、巴林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并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组织。
在西部,埃及基于政权安全卷入利比亚冲突。埃及在利比亚问题上与利比亚国民军、沙特、阿联酋等取得战略共识,并积极寻求俄罗斯、法国等支持,以此对抗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第一,土耳其通过支持利比亚穆兄会势力输出“土耳其模式”④董漫远:《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跨地区影响及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第98、101页。,对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反穆兄会联盟产生威胁。第二,土耳其通过与利比亚划定新海洋边界与希腊和欧盟对抗,并为其在地中海南岸的地理和政治利益延伸助力。⑤伊马德·卡杜拉、侯宇翔:《新海洋政策下土耳其出兵利比亚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4期,第154页。这触动了埃及在东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威胁到了埃及的区域大国地位。因此埃及坚决要求土耳其退出利比亚,但土耳其声称为利比亚所邀而来。2021年3月,新一届民族团结政府上台,并宣布将在12月举行总统选举。但由于各方没有达成默契,官方也没有发表一致声明,原定于12月24日举行的利比亚总统选举被推迟。土耳其以此为由,拒绝答应任何要求它在举行大选之前离开利比亚的要求。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顾问斯蒂芬妮·威廉姆斯(Stephanie Williams)强调有必要“在适当的情况下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份五年一度的声明,称必须尽快为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设定一个新的日期,但过渡时期相关的文本和协议尚不明确,政治和宪法障碍不易解决和绕过,因而利比亚总统选举仍不确定。①“Turkey and Libya: The Post-Election Era,” Teller Report, January 8, 2022, https://www.tellerreport.com/life/2022-01-08-turkey-and-libya——the-post-election-era.rJWmTjXv3Y.html,上网时间:2022年1月26日。埃及与土耳其在利比亚的对抗仍然存在。
在南部,埃及基于资源安全,围绕尼罗河水资源争端争取美国和苏丹的支持,反制埃塞俄比亚。尼罗河水资源对埃及而言不仅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1929年签订的《尼罗河水资源分配协议》以及1959年签订的《全面利用尼罗河水协议》赋予了埃及和苏丹历史性水权,奠定了埃及在尼罗河流域的主导地位。埃及的主要对手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但囿于以上两份法律文件,水权受到限制。为发展经济,埃塞俄比亚宣布建造复兴大坝,并于2021年7月完成了第二次蓄水。其间,埃及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暗示埃及将会炸毁复兴大坝。埃及也寄希望于联合国和非盟,但二者都未给出一个协调方案。11月,塞西发表声明称,“埃及期待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国际法就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②Mohamed Saied, “Ethiopia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from GERD Amid Negotiations Deadlock,”Al-Monitor, January 7, 2022,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2/01/ethiopia-generate-electrici ty-gerd-amid-negotiations-deadlock#ixzz7HwaWQ0CZ,”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5日。。目前,除了求助于国际协调,埃及竭力加强与苏丹、乍得、索马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军事和经贸往来,力图孤立埃塞俄比亚,构建以埃及为中心的联盟网络以增强外交话语权。
在北部,埃及基于资源安全,加入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反制土耳其和利比亚在东地中海地区划界。过去十年,塞浦路斯、埃及和以色列沿海大量的天然气被发现,这使地区国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地中海东部。这个地理空间正越来越多地被称为东地中海,并成为了一个有参与者、利害关系和竞争对手的次区域。③Mona Sukkarieh, The East Mediterranean Gas Forum: Regional Cooperation Amid Conflicting Interests, New York: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stitute, February 2021, p. 2.为了更好协调东地中海地区国家间利益,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于2019年在开罗成立。2020年,它转变为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成员包括塞浦路斯、埃及、希腊、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和巴勒斯坦。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土耳其。土耳其与北塞浦路斯、利比亚签署海上划界协议,在东地中海地区谋求利益。埃及通过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将土耳其排除于东地中海天然气联盟之外,土耳其的能源扩张政策受到严重遏制。2021年12月,土耳其事务专家阿萨·奥菲尔(Assa Ofir)接受采访时称,“土耳其日益孤立,经济萎缩,这让它不得不重新思考地区外交政策。”①Ksenia Svetlove, “Will Turkey Ditch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o Mend Ties with Egypt,UAE and Saudi Arabia?,” The Media Line, September 12, 2021, https://themedialine.org/top-stories/will-turk ey-ditch-the-muslim-brotherhood-to-mend-ties-with-egypt-uae-and-saudi-arabia/,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5日。埃及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隐性联盟取得初步成果。
(三)中东变局以来埃及“隐性联盟”战略的动因
中东变局以来,穆尔西和塞西先后在埃及执政,穆尔西执政期间,埃及结盟对象从美国到政治伊斯兰势力的转型中,历史经验的习得,领导人因素以及国家战略任务的变化是这一转型的主要因素。其中,领导人个性特征发挥了关键作用,历史经验的习得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②尽管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对美国在“一·二五革命”后袖手旁观不满,但是穆尔西从与美国结盟转向与政治伊斯兰结盟,并非因为埃及与美国的“隐性联盟”出现重大危机。第一,穆巴拉克时期,埃及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革”,却使得埃及陷入动荡乱,政治伊斯兰成为替代性方案。穆尔西的隐性联盟选择政治伊斯兰势力,体现出其本人政治伊斯兰的倾向。第二,穆兄会成员穆尔西上台后为维护政权合法性,维持支持其上位的宗教势力,国家政策出现伊斯兰化的转变。埃及对外战略的变化,尤其是结盟对象的选择,打上了穆尔西及其宗教政党的烙印。第三,沙特、阿联酋等反对穆兄会阵营成员对穆尔西政府持敌视态度,但土耳其、卡塔尔等亲穆兄会阵营极力欢迎穆尔西的执政,穆尔西政府在外交上面临促进亲穆兄会阵营的团结和统一的重大战略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穆尔西本人的个性特征对埃及隐性联盟战略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的联盟政治经历了一次“去意识形态化”的调整,结盟对象从政治伊斯兰转向多元伙伴主要是基于历史经验的习得以及国家战略任务变化的考量,而不是塞西的个人偏好。第一,穆尔西“伊斯兰道路”未能挽救埃及,塞西认识到,只有真正符合国家、人民利益的政策才会受到拥护。第二,塞西政府上台后,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成为其战略任务。新形势下,埃及多方受困,全方位、多手段是其必要选择。虽然塞西作为政治强人对埃及外交战略施加影响,但塞西是军人政变后上台,其背后支柱“军方力量”不容忽视。国家战略任务和埃及与政治伊斯兰势力结盟的失败经验是塞西新政府奉行“东西南北”多向结盟的关键原因。
综合分析当代埃及“隐性联盟”战略转型的四个实例可以发现,国家战略任务的变化、历史经验的习得基本影响了埃及隐性联盟战略调整的全过程。埃及领导人结盟对象选择的偏好主要还是基于国家任务与历史经验习得,而非其个性特征(见表3)。只有在穆巴拉克到穆尔西执政交替过程这一个实例中,领导人个性特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纳赛尔时期,埃及实现了从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到苏联的跨越,埃及基于对国家战略任务的变化与历史经验的总结,实现了从泛阿拉伯主义到阿拉伯社会主义再到埃及民族主义的转变;萨达特时期,埃及实现了从与苏联结盟到与美国结盟的转变,表明领导人个性特征只发挥次要作用。因此,国家战略任务的变化、历史经验的习得和政治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三个因素共同影响了隐性联盟战略转型过程中埃及结盟对象的选择,其中国家战略任务的变化和历史经验的习得是主要因素,领导人个性特征因素是次要因素。

表3 当代埃及“隐性联盟”战略转型的动因分析
五、结语
埃及是中东地区传统大国之一。1952年之前,埃及作为殖民国家存在。“7·23革命”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成立,而后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自此赢得事实上的独立。在国际上面临美苏两大阵营抉择的纳赛尔开拓出“积极中立”第三种道路,与铁托、尼赫鲁发起不结盟运动。克洛维斯·马克苏德(Clovis Maksoud)指出,不结盟是对孤立主义或古典中立主义的明确拒绝,是对人类处境的逐渐动态参与。①DonPeretz, “Nonalignment in the Arab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62, 1965, p.43.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一些不结盟成员国逐渐化被动为主动。例如,印度转向“多向结盟”后在强调战略自主的同时,做出有别于制衡、追随或中立的对冲性政策选择。②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95页。中国的不结盟政策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结伴不结盟战略明确规定“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③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31页。
相对于印度、中国而言,埃及的“隐性联盟”特征更加鲜明,它是不结盟原则与事实结盟实践之间的折中,是结盟与中立之间的“灰色地带”。第一,埃及的隐性联盟与其说是一种静态的结盟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动态的结盟过程。埃及的“不结盟原则”为埃及施行非正式联盟、转换结盟对象、调整国际合作者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埃及既依附于盟友,又对联盟不信任,试图在维护战略自主的基础上结成有限联盟。以安全任务为导向,而不是以制度化建设和联盟规范建构为导向,导致埃及的隐性联盟中战略自主与战略依附之间形成张力。第三,埃及的隐性联盟降低了结盟的门槛,却增加了双方违约的风险,使双方不得不就具体的任务不断进行磋商与协调。埃及过去结盟成败的历史经验对其选择盟友的偏好起到重要启示意义;领导人通过对历史经验的习得,调整结盟对象,从而形成了在结盟对象之间的“钟摆效应”。
以埃及为代表的广大不结盟国家,在缺乏足够的国力做到安全上自给自足、又珍视民族独立和战略自主性时,在外交实践中可以通过实施有限的“隐性联盟”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不结盟国家需要审慎地看待地区权力格局和安全态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不结盟国家更需积极提高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摆脱束缚,由被动跟随转而主动塑造,寻求适宜的自主选择空间,运筹帷幄,增强地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