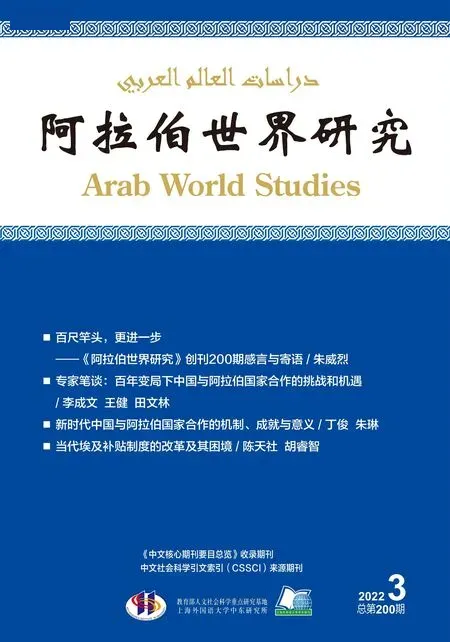塞西执政以来埃及与以色列准联盟关系的发展
潘基宏 王 昕
1979年是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分水岭,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埃以和约》,正式结束两国持续近30年的战争状态。此后30余年间,埃以再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但双边关系也未能实现全面正常化,两国在政治、安全、经贸与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始终处于低水平。对于埃以这种特殊的关系,学界多位学者将其称为“冷和平”①陈天社:《国内外学界对埃及外交关系(1970—2000年)》的研究,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第117页。(Cold Peace)。2011年,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埃及政局陷入动荡,埃以关系虽然一度遭遇冲击,但始终维持在冷和平的范畴,只是相较以往“冷”的成分进一步凸显。2013年“7·3”事件后,②“7·3”事件系指2013年7月3日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队废黜,在军队的安排下,埃及组建过渡政府,并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前国防部长塞西开始执掌埃及最高权力并当选为国家总统,此后埃以关系升温,对地区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及和以色列是中东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在中东变局背景下的新发展值得关注。目前,国内学界对塞西执政后埃以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大多只是将其嵌入在其他议题之中进行探讨,缺乏深入分析。③参见王晋:《塞西执政两周年—埃及的变化与挑战》,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7期,第56-59页;唐恬波:《埃及和以色列走向“暖和平”》,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17期,第48-49页;姚惠娜:《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6期,第50-62页;谢立忱、崔晓娟:《“阿拉伯之春”后以色列外交的新动向》,载《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18-124页;李意:《埃及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述评》,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5期,第93-113页;王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与以色列的应对》,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第27-33页;高尚涛:《阿以建交:中东局势前景展望》,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7期,第122-125页;齐淑杰:《埃以关系的嬗变(1980—2019年)》,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22-28页;唐志超:《中东剧变以来环地中海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影响》,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35期,第102-105页;周锡生:《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地区合作还是苦涩争夺?》,载《国际展望》2020年第6期,第45-64页;杨永平、杨佳琪:《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动因、问题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3期,第90-112页。鉴于此,本文旨在对塞西执政以来的埃以关系进行定义,着重对两国关系变化的动因进行研究,以期准确认识埃以关系的新发展和地区格局的新变化。
一、塞西执政后埃以关系向准联盟发展
塞西执政后埃及国内局势逐渐重回正轨,埃以关系在历经“阿拉伯之春”初期的波折后也实现顺利过渡。相较于穆巴拉克时期和穆尔西时期,这一阶段的埃以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塞西执政以来埃以关系的特点
塞西执政后,埃及和以色列的安全互信增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自1979年埃以媾和以来,埃及武装力量的部署一直保持“东强西弱”的态势,尤其在苏伊士省、伊斯梅利亚省和塞得港省一线有大量军队驻防,塞西执政后这一态势出现变化。2017年埃及西北部哈马姆地区、该国最大的军事基地穆罕默德·纳吉布军事基地正式启用。此后,埃及中央军区和北部军区的部分部队向西移防,其中包括原驻扎于吉萨省达舒尔地区的装甲第9师。装甲第9师是埃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之一,移防前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第三野战集团军应对来自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威胁。此次调整后,埃及在其西部领土的军事存在显著扩大。一些军事人员认为,“目前西部军区在埃军中具有数量最多的步兵、炮兵及其他兵种,这是通过削弱其他军区和野战集团军的实力来实现的”①[埃及]马哈茂德·贾迈勒:《埃及军队:构成与部署》(阿拉伯文),载《埃及研究所杂志》2018年总第9期,第132页,https://eipss-eg.org/wp-content/uploads/2018/01/009_。此外,塞西执政以来,埃及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武器进口国排行榜前列。在2015~2020年的全球军火采购中,埃及以5.8%的份额排名第三。②“SIPRIYearbook 2021:Armaments,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ary),”埃及在“全球火力网”(Global Firepower)的军力排名,也由2015年的第18位跃居到2020年的第9位。③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埃及成为以色列邻国中唯一有能力对以本土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国家,但是以色列对埃及军力的提升并没有表现出过多担忧,反而为埃及采购美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向美国国会积极游说,这是“历史上以色列首次为了保证阿拉伯国家的武器供给进行的游说”④。埃及军力部署的调整以及以色列对埃及采购军火的态度表明,塞西执政以来埃以安全互信得到较大提升,而两国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凸显了双方日益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
根据1978年埃以签署的《戴维营协议》,西奈半岛区域实施非军事化降级管理,从西向东分为A、B、C、D四个区。其中,A、B、C区位于西奈半岛,属于埃及领土,其中A区东西跨度58公里,埃及的军事部署不能超过1个机械师,军人数量不超过2.2万人;B区东西跨度109公里,只能部署边防部队,数量不超过4,000人且只配备轻武器;C区东西跨度33公里,不能部署任何军事力量,只允
.pdf,上网时间:2021年4月15日。
StockholmInternationalPeaceResearchInstitute, June, 2021, p. 15, https://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6/sipri_yb21_summary_en_v2_0.pdf, 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5日。
③ “GlobalFirepower.com Ranks: Military Powers Ranked Since 2005 According to Global Firepower,”GlobalFire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global-ranks-previous.php,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5日。
④[巴勒斯坦]萨利赫·纳阿米:《“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许边防警察进入,数量不得超过750人且只携带轻步枪;D区位于与西奈半岛交接的以色列境内,东西跨度4公里,以色列的军事部署不能超过4个步兵营,军人不超过4,000人;埃以的军机分别只能在A区和D区活动。①参见[巴勒斯坦]易卜拉欣·哈吉布:《埃及和以色列战略视野中的西奈半岛》(阿拉伯文),载《埃及研究所杂志》2019年总第14期,第24-26页,https://eipss-eg.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0014.pdf,上网时间:2021年4月22日。穆尔西时期,埃及为打击极端组织曾试图向西奈半岛增兵,但以色列坚持要求埃及遵守协议。塞西执政后,这一情况出现变化,以色列对埃及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大开绿灯。“在以色列的授权下,埃军派出F-16战机对北西奈省靠近加沙地带的极端组织发动攻击”②“For the First Time in 34 Years Egyptian Air Force Fighter Jets Flew over Gaza-Israel Border,”The Aviationist, October 19, 2013, https://theaviationist.com/2013/10/19/egypt-f-16-sinai/#.UmJupS6RHwOct, 上网时间:2021年5月15日。,这是两国签署协议以来埃及战机首次进入B区和C区执行作战任务。在“西奈2018”反恐行动中,埃及向西奈半岛投入了4万余兵力,兵力规模及部署区域以及武器配置均突破协议“红线”。除此之外,以色列还积极配合埃及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一方面,以色列为埃及的军事行动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撑。“8200部队”是以色列情报系统中最负盛名的电子侦察部队。“8200部队”长期跟踪、截获西奈半岛极端分子之间的通信,并将相关信息传送给埃及情报部门,为埃军实施精准打击极端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③《以色列分析人士:塞西下台是以色列的重大损失》(阿拉伯文),“阿拉比21”网,2016年8月20日,https://arabi21.com/story/935489/,上网时间:2021年5月25日。另一方面,以色列派无人机协助埃军作战。2014年至2016年,以色列多次使用无人机进入西奈半岛空域执行军事任务,除帮助埃方搜集战场信息外,还包括对极端分子直接发动空袭。④[巴勒斯坦]萨利赫·纳阿米:《“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阿拉伯文),第115页。
面对持续多年的巴以和谈僵局,以色列对巴以问题的态度已经由“解决冲突”转变为“管理冲突”。在此背景下,应对伊斯兰抵抗运动(以下简称“哈马斯”)的军事挑衅和安全威胁成为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优先事项。穆巴拉克时期,埃及虽然多次向以色列承诺会配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但实际执行较少。塞西执政后,埃及的承诺得到切实履行。为帮助以色列实现围困哈马斯的战略企图,埃及严格管控拉法口岸,在西奈—加沙边境修建“隔离墙”,尤其是重创具有哈马斯“肺部”之称的地道网络,极大削弱了哈马斯通过地道走私获取武器的能力。①参见潘基宏、王昕:《从“消极合作”到“积极合作”——中东变局下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新发展》,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5期,第127-128页。此外,埃及还同以色列分享加沙地带的情报,为以色列安全机构对哈马斯成员实施监视与抓捕提供便利。埃及安全部门有时甚至会“亲自逮捕哈马斯成员或者与哈马斯有工作关系的人员,并将他们直接交给以色列安全部门”②[巴勒斯坦]萨利赫·纳阿米:《“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阿拉伯文),第122页。。塞西政府对哈马斯的政策得到以色列方面的高度赞赏,以色列军队前发言人阿维·本亚胡(Avi Benyahu)评论道:“塞西对伊斯兰分子(哈马斯)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以至于哈马斯领导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政权”③[以色列]阿维·本纳亚胡:《应对抵制的唯一方法是在塞西的帮助下与巴勒斯坦人对话》(希伯来文),《晚报》官网,2015年9月27日,https://www.maariv.co.il/journalists/Article-499564,上网时间:2021年7月10日。。此外,为维护两国能源安全与发展利益,2017年埃及和以色列首次共同派出军队参加在东地中海举行的多国军事演习,积极倡导召开“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合力推进东地中海能源—安全合作机制建设。④参见潘基宏、王昕:《从“消极合作”到“积极合作”——中东变局下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新发展》,第128-129页。
由上可知,塞西执政后埃以在安全领域的双边关系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以色列能源部长尤瓦·斯坦尼兹(Yuval Steinitz)曾表示,目前埃以安全合作好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协调与信息交换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两国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几乎每天都在交流”⑤Ehud Yaari, “The New Triangle of Egypt, Israel, and Hama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anuary 17, 2014,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new-triangle-egypt-israel-and-hamas, 上网时间:2021年3月27日。。在政治领域,埃以关系踩住了穆尔西时期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刹车,开始逐步改善。2015年9月,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重新开放。2016年1月,埃及在时隔三年后重新向以色列派遣大使,标志着埃以政治关系已经回暖。但在其他领域,埃以关系基本延续了冷和平时期的低水平状态,两国在工业、农业、太阳能、海水淡化、绿色能源、医疗、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合作没有出现重要变化,⑥[巴勒斯坦]阿德南·阿布·阿梅尔:《埃及作用的衰落和加强它的方法:以色列的解读》(阿拉伯文),埃及研究所,2020年10月16日,第9页,https://eipss-eg.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pdf,上网时间:2021年4月10日。在人文领域的交流更是举步维艰。
总体而言,塞西执政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在构建一种新型合作关系,它具有“安全合作火热、政治互动回暖、其他领域继续冷漠”的特点。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的埃以关系称为“暖和平”①唐恬波:《埃及和以色列走向“暖和平”》,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17期,第48-49页。,这种定义虽然反映了埃以关系升温的客观现实,但因其内涵比较宽泛、缺乏针对性,无法准确体现埃以关系在塞西执政后的延续与变化。例如,埃以的文化关系依然处于“冷和平”的状态,而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度也不能简单用“暖和平”来形容。
(二)弱准联盟——塞西执政以来埃以关系的定位
准联盟(Quasi-alliance)也被称为“特殊关系”“未签订盟约的联盟”“非正式联盟”“临时联盟”“意愿联盟”等,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合作关系”。②孙德刚:《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根据这一定义,准联盟具有以下三个明确特征。
第一,以安全领域为主导的合作关系。准联盟涉及安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领域,但安全合作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安全关系是成员间最重要的关系。根据国际安全合作程度的高低,国家间关系从低到高可划分为六个等级,依次是军事冲突与敌对关系、潜在对抗关系、普通国家间关系、政治伙伴关系、准联盟关系和联盟关系。③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62页。其中,建立政治伙伴关系的国家之间可能会开展密切的安全合作,但准联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是在政治合作框架下进行的,政治关系要优于安全关系。从安全范畴来看,国家间关系由五个等级构成(见图1)。

图1 安全范畴视角下的国家间关系
第二,针对外部敌人的合作指向。在国际体系中,安全是一种稀缺品。当遭遇外界威胁时,国际实体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会倾向于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来获取外部资源以应对危机,准联盟思想的形成正是源于这一隐形逻辑。而集体安全是“国际社会设想的、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制止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维护每一个国家之安全的国际安全保障机制”④门洪华:《集体安全辨析》,载《欧洲》2001年第5期,第10页。,它的逻辑是通过国际安全实现国家安全。因此,准联盟与集体安全不同,准联盟合作指向外部敌人,而集体安全针对的是成员国内部的相互侵略行为。
第三,以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为载体。国家间缔结联盟需要签署盟约,即正式安全合作协定,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否则将视为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一是形式正式,经由国内立法机构而非行政部门批准;二是内容明确,必须具有缔约国联合对敌作战的条款。①孙德刚:《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第38页。准联盟则以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为载体,可以包含国家关系法案、合作备忘录、共同宣言、甚至口头承诺等。例如,美国和韩国根据正式安全合作协定《美韩共同防御条约》(MutualDefenceTreaty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theRepublicofKorea)开展的安全合作关系属于联盟,条约规定当其中一方在亚太地区遭受攻击时另一方必须要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和以色列有很多强调双边特殊关系的法案,如《2014年美国—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法案》(UnitedStates-IsraelStrategicPartnershipActof2014)等,但它们都没有联合对敌作战的条款。虽然以往当以色列遭遇攻击时,美国会向以色列提供有力的军事援助,但这种援助不是出于法理的强制性。因此,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属于准联盟。总体而言,准联盟的实质是联而不盟,是偏重合作“功能性”而非“制度性”的一种灵活的关系,成员致力于强化安全合作但又不愿意受盟约制约而失去外交独立性。此外,准联盟的成员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这也是准联盟与联盟不同的特征,但由于埃以关系不涉及此问题,本文不对此进行论述。
塞西执政以来,埃以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以安全合作为主导。埃以展开了一系列密切的战略协作,甚至向对方让渡了部分主权,如埃及允许以色列多次实施越境打击,两国的合作程度等级已经超越了普通国家间关系。在这一阶段,埃以安全合作的指向不是防止内部的军事冲突和侵略行为,而是针对外部敌人的共同威胁,如极端组织、哈马斯、土耳其等。埃以之间没有签署正式的安全合作协定,在目前形势下两国也不可能达成具有集体防御功能的联合对敌作战条款。至于两国的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两国均未对外界公开协定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但鉴于埃以在西奈半岛和东地中海的高度合作默契,可以推定两国之间存在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协定。此外,由于埃以关系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敏感性,两国对双边安全合作采取低调处理方式,尤其埃及官方和新闻媒体对两国在安全领域的频繁“热络”采取回避态度,具有准联盟成员间“多做少说”的特点,即“不宣扬、甚至不承认双边业已存在的密切安全合作关系”。②孙德刚:《国际关系中“准联盟”现象初探》,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第29页。综上,塞西在埃及执政可以视为埃以关系继《埃以和约》签订后的另一个分水岭,埃以关系已超越冷和平,具有准联盟的基本特征,属于准联盟的范畴(见图2)。

图2 塞西执政前后埃以关系变化示意图
准联盟是普通国家间关系和联盟关系的中间地带,从安全合作程度来看,部分准联盟会倾向于普通国家间关系,而另外一部分准联盟会倾向于联盟关系。据此,准联盟可以划分为两种,前者为“弱准联盟”,后者为“强准联盟”,两者之间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割线,但是可以根据安全合作的内容进行初步界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涉及诸多领域,其中高层面的内容包括“联合部署军队,共享军事基地、训练设施、油料库以及弹药库,军品贸易和军事技术合作(主要侧重进攻性武器、敏感性军事技术以及尖端军事科技),设立三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与控制协调或决策机制”①武琼:《国家间推进军事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以日印军事安全合作为例》,载《日本文论》2020年第2辑,第117页。等。准联盟成员的安全合作如果涉及以上一项内容,成员间的关系可视为强准联盟。例如,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机F-35等进攻性武器,与以色列共同研制“箭式”导弹防御系统等具有尖端军事科技,它们的准联盟关系涉及高层面的安全合作,应当视为强准联盟。而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尚处于低层面,未来也很难涉及高层面的内容,它们的准联盟关系属于弱准联盟。
二、埃以关系向准联盟发展的体系层面因素
塞西上台是埃以关系向准联盟发展的时间起点,塞西个人的决策对埃以关系加速升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者之间并非“充要条件”。肯尼斯·华尔兹提出,“战争源于人的本性和行为、国家内部结构问题、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①[美]肯尼斯·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应基于“三个层次”的分析,即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
其中,“体系”是指“诸多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单位(民族国家)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而组合起的一个整体”②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作为体系的成员,一般情况下,民族国家会依据自身在体系中的身份和体系的秩序进行互动。当体系结构出现变化时,体系会释放出一种“张力”,导致秩序束缚力的削弱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国家”,即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在体系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国家会对自我身份进行再定位,重新审视国家利益的诉求,进而调整对外政策,以便在体系中塑造有利于己的权力关系。“个人”,即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者,包括国家的领导人或实权者,也可以指对国家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集团或阶层。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过程,它不仅是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理性权衡的结果,也受到决策者的个性、偏好、经验和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在威权体制国家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更加突出。国家间关系的变化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埃及和以色列在塞西执政后能够跨越冷和平、向准联盟发展,正是源于这三个层次的“变量聚合”(见图3)。据此,下文将从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对埃以关系向准联盟发展的动因进行分析。

图3 体系、国家和个人层面对埃以构建准联盟关系的影响
中东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世界主要大国对中东事务一直保持深度参与,极大地影响了地区格局的发展。域外大国与中东国家以国家实力为基础进行互动,共同推动了中东体系的形成。由于国家实力的差异,各国在中东事务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权力的排列组合产生了体系结构。体系结构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国家会遵循结构的规则进行交往。但当权力在国家间的分配尤其是大国间出现较大变化时,体系结构会随之调整,进而影响国家间的互动。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成为中东唯一的霸权国。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东体系的结构没有出现质的变化,美国始终是中东事务的主导国,中东域内国家在美国“霸权稳定”的格局下也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塞西执政时,中东正处于“十年变局”的大动荡期,同时又受到“百年变局”下国际格局加速转型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域外大国的中东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出现变化。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在中东事务上实施战略收缩。“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对中东乱局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克制,引发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地区盟友的不满和担忧。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加速了战略重心东移步伐,在中东则继续保持总体收缩的态势。虽然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整合地区盟友、采取离岸平衡的政策来维系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力,但由于盟友之间的分歧以及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特朗普政府并不愿意为中东事务投入过多政治外交资源,其所主导的中东传统治理路径面临失效风险。
长期以来,欧盟和美国的中东战略高度互补。小布什时期,美国在中东偏好以武力为后盾的“民主改造”,欧盟则以“规范性力量”和“民事力量”自居,在中东采取一条渐进式、偏好政府合作的民主治理路径,旨在加强与中东地区的经贸合作与安全互利。①钮松:《中东乱局持久化背景下欧盟中东战略的调整及困境》,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3期,第19页。中东变局中,美国在中东极力避免军事介入,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则加大在中东的军事投入,率先对利比亚发起“奥德赛黎明”行动(Operation Odyssey Dawn)、卷入叙利亚战场一线。但是,这些中东国家不仅没有走向欧盟期待的“民主化”,反而陷入转型困境,甚至沦为“失败国家”,中东作为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已经演变为一条“动荡弧”,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持续溢出至欧洲地区。与此同时,欧盟本土尚未从债务危机中完全复苏,却又遭遇英国脱欧的冲击,它参与中东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都出现明显下降。
普京执政后,随着国力的提升,俄罗斯开始谋求恢复全球大国的地位,它将中东视为扩大全球影响力、突破西方制裁封锁、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场。中东变局中,俄罗斯以建设性姿态介入中东事务,充分利用出兵叙利亚获得决定性军事胜利的外溢效应,构建“阿斯塔纳进程”和“索契进程”,谋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议题设置能力。俄罗斯还积极推动恢复与苏联时期的合作伙伴埃及、苏丹、利比亚(东部“国民军”)等国的军事合作,扩大俄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同时,俄罗斯不断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协调,深化双边关系,稳步推进“欧佩克+”的能源合作新模式。近年来,俄罗斯重返中东势头强劲,但“囿于俄有限经济实力以及俄与中东国家曲折关系史,加之俄与西方的对立,当前俄重返中东只是起步,地位尚未牢固”①唐志超:《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及其战略影响》,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3期,第25页。。
总体而言,“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秩序不断遭遇挑战,域外大国在中东呈现“美退、俄进、欧徘徊”的动态权力变化格局,地区的体系结构面临重塑。中东一直缺乏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域内国家间缺乏安全互信,而中东体系结构的调整所释放的“张力”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地区风险管控出现赤字危机,地区国家普遍深陷安全困境。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多国战略自主性增强,引下各种力量不断分化重组,形成多个相互交叉的对抗性政治集团,地区体系呈现“霍布斯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抗性政治集团的形成与冷战期间通过亲苏还是亲美、冷战后亲美还是反美的划分方式不同,它更多反映的是地区国家的影响力,而不是取决于其与世界大国的关系。②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68页。例如,伊朗、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以什叶派属性为纽带形成政治集团,与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等以反伊朗为核心形成政治集团之间呈现对抗性;土耳其、卡塔尔、利比亚(西部“民族团结政府”)等以亲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为主要特征形成政治集团,与埃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以反穆兄会、遏制土耳其为共同目标形成政治集团之间也呈现对抗性。
在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下,埃以享受着丰厚的安全红利,即使两国处于冷和平的状态,依然能在地区的博弈中保持地缘优势。但是,随着体系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失序和中东国家对抗性政治集团的出现,埃以的国家安全和地缘竞争所面临的形势不断恶化,尤其是以色列对美国在中东权力的削弱充满战略焦虑。为在地区体系转型过程中获取足够的安全产品,埃以都需要借助他国的力量来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这为埃以关系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囿于阿拉伯民族作为国家主体民族以及“不结盟运动”主要旗手等身份政治问题,埃及既有寻求深化与以色列合作满足自身安全需要的向心力,也有担心两国合作可能带来政治风险的离心力,这决定了两国不可能签署正式的安全合作协定缔结联盟,而推动双边关系向富有弹性的准联盟发展则成为两国的优选项。
三、埃以关系向准联盟发展的国家层面因素
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①Hans J. Morgenthau, Dilemmas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p. 54.。埃及和以色列是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行为体,两国能够突破阿以关系的桎梏、率先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跨越,表明埃以在制定对外政策中奉行的核心原则正是国家利益至上。“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及其影响在中东的持续发酵,导致埃及和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诉求出现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塞西执政后两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扩大,这为两国关系向准联盟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
(一)安全合作职能由“合作安全”向“联盟安全”拓展
《埃以和约》签署后,埃及和以色列在安全领域建立起对话与合作机制。但中东变局发生前,两国开展安全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增信释疑,推动双边去安全化进程,属于“合作安全”的范畴。中东变局发生后,两国的安全利益出现重大变化,双边安全合作主要应对伊斯兰力量的崛起,具有“联盟安全”的特点。
1.埃及国家安全战略重心的调整
中东变局发生后,受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埃及政府对西奈半岛的管控能力下降。以“耶路撒冷支持者”(AnsarBaital-Maqdis)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力量异军突起,在西奈半岛频繁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并向盘踞伊拉克、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效忠,更名为“伊斯兰国西奈省”。埃及的邻国利比亚曾是重要的武器进口国。2011年后,利比亚深陷内战泥潭,卡扎菲时期建设的军火库被部落民兵武装劫掠,大量先进重型武器流入黑市并通过走私网络辗转至西奈半岛。2012年11月,埃及安全部队在梅莎·马特鲁港(Mersa Matruh)查获一艘由利比亚前往西奈半岛的走私船,船上装有108枚火箭弹和2万发子弹。②Eran Zohar, “The Arming of Non-State Actors in the Gaza Strip and Sinai Peninsula,”Australia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4, 2015, p. 452.“7·3”事件后,部分穆兄会成员采取暴力手段回应埃及军队的政变,促使塞西政府正式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此后,不满与愤怒情绪在穆兄会中普遍蔓延,穆兄会不少青年成员不惜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合流,选择激进极端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
正是有了利比亚走私武器的加持和穆兄会“有生力量”的加盟,西奈半岛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实力大增,甚至敢于与埃及安全部队发生正面高烈度交火,发动恐怖袭击的地点以西奈半岛为中心向全国蔓延。从2013年7月到2017年11月,埃及本土共遭受了1,165次袭击,大部分发生在西奈半岛。③《埃及2017:危机中的一年》(阿拉伯文),埃及研究所埃及战略报告,2018年7月,第47页,https://en.eipss-eg.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2-.pdf,上网时间:2020年6月8日。2017年,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市一清真寺制造了“11·24”惨案,造成30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是埃及建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最严重的恐袭事件。与此同时,埃及军警也深受伊斯兰极端组织重创。2015年至2017年间,公开消息来源显示,至少有1名少将、7名准将、7名上校、16名中校被极端分子杀害。①[埃及]艾哈迈德·莫拉纳:《埃及“圣战”局势的发展和变化(1966~2018)》(阿拉伯文),载《埃及研究所杂志》2019年总第13期,第277页,https://eipss-eg.org/wp-content/uploads/2019/01/‘0013.pdf,上网时间:2021年3月15日。2017年7月,埃军最为精锐的闪电部队103营的一支特种作战分队在拉法地区几乎全军覆没。同年12月,埃及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在北西奈省视察时遭制导导弹袭击险些遇难,1名随行中校军官身亡。据统计,2017年埃及军方共有63辆M60坦克、32辆悍马战车、199辆装甲车在与伊斯兰极端力量交战中被毁。②《埃及2017:危机中的一年》(阿拉伯文),第116页。
在此背景下,自1948年以来埃及首次不再将以色列视为“战略威胁”,国家安全重心由“防御以色列进攻”转移至“打击政治伊斯兰(穆兄会)和极端伊斯兰”,而哈马斯因为与穆兄会关系密切、又与西奈半岛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暧昧不清也遭致埃及的打压(见表1)。

表1 埃及对“战略威胁”的界定、对以色列身份的认定及采取的政策
2.以色列国家安全威胁的伊斯兰因素增加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不管是阿拉伯国家投身民族解放事业,还是伊斯兰极端组织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抑或伊斯兰国家以泛伊斯兰主义为纽带参与地区事务,以色列都是“被治理”的对象。时至今日,即使是远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文莱,出于宗教情感仍对以色列持敌视态度,体现了伊斯兰因素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因此,一直以来,以色列对中东伊斯兰势力的发展保持高度警惕,而中东变局以来后者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更趋复杂与多元。
首先,西奈半岛兴起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威胁以色列南线安全。2013年,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高级官员表示西奈半岛有15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辛贝特认为这些组织的有数百名成员,而军方情报机构估计成员数量达数千人,①Barak Ravid, “Shin Bet Forms New Unit to Thwart Attacks on Israel by Sinai Jihadists,”Haaretz, August 20, 2013,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ce/.premium-1.5424-17, 上网时间:2021年2月25日。极端分子普遍对以色列持敌对态度。一方面,极端组织直接从西奈半岛的据点向以色列发动远程袭击。例如,2012年11月底,西奈半岛的极端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99枚火箭弹。②王晋:《“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演进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2期,第53页。另一方面,极端分子以西奈半岛为“跳板”,潜入以色列境内发动恐怖袭击。2011年8月18日,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遭遇多起“相互配合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伤亡,袭击者正是经西奈半岛潜入以色列境内。鉴于此,“以色列将埃及在西奈半岛打击极端分子的战争视为以色列的战争”③[巴勒斯坦]萨利赫·纳阿米:《“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阿拉伯文),第118页。,埃军的胜利有助于保护以色列边境居民、设施乃至其领土纵深的安全。“以色列为埃及提供情报、行动支持,并愿意积极考虑埃及在西奈半岛扩大军事存在的要求,均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④Yoram Schweitzer, “Egypt's War in the Sinai Peninsula: A Struggle That Goes Beyond Egypt,” INSS, February 3, 2015,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egypts-war-in-the-sinai-peninsula-a-struggle-that-goes-beyond-egypt/, 上网时间:2021年7月30日。
其次,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埃及上台执政。“一·二五革命”⑤“一·二五革命”是指自2011年1月25日开始,埃及境内爆发的一系列反政府民众抗议示威游行活动,18天后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武装部队最高军事委员会接管政府并组织民主选举。后,埃及穆兄会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参加国家议会选举并成为第一大党,党主席穆尔西成功当选埃及第五任总统,标志着政治伊斯兰力量首次执掌埃及政权。穆尔西执政后,埃及不顾及以色列的核心关切,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态度强硬,与具有强烈反以色彩的哈马斯日益走进,与伊朗关系不断升温。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要求重新审视《埃以和约》的呼声不绝于耳,被以色列视为国家安全重要支点的埃及面临坍塌和倒戈的危险。此外,在中东变局之初,受埃及穆兄会顺利夺权的鼓舞,中东诸国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被政治伊斯兰力量“劫持”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导致以色列周边安全环境严重恶化。
最后,“国家伊斯兰”兴起,不断逼近以色列边界。伊朗奉行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它是以什叶派为人口主体且由什叶派执政的中东国家,对以色列一直秉持敌视政策,多次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东西两翼的逊尼派强敌消失,伊拉克更是从伊朗的“战略威胁”转变为“战略资产”。中东变局后,伊朗通过整合叙利亚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组建“抵抗轴心”,在地区实现强势崛起并对以色列构成战略夹击。通过深度参与叙利亚战争,伊朗在叙利亚实现驻兵,其支持的什叶派武装渗透到戈兰高地,对以色列形成强大的前沿威慑。
总体而言,塞西执政时,埃及和以色列在应对伊斯兰力量兴起所带来的挑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其中,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政治伊斯兰对两国构成共同的安全威胁,对推动两国安全合作职能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伊朗与埃及在安全领域不存在直接冲突,但长期争夺中东事务的话语权,以色列希望在与伊朗进行激烈交锋时埃及能成为其稳定的大后方,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埃以安全合作的升级。
(二)政治合作需求由“非对称”向“对称”转变
1948年建国后,以色列犹如一座“孤岛”被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包围。直至中东变局前,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埃及和约旦。1980年与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建交是以色列重大的外交胜利,但以色列并没有在阿拉伯国家产生积极的多米诺效应,埃以关系也因巴以和平进程受挫止步于冷和平,而小国体量的约旦未能帮助以色列实现新的外交突破。
为改善地缘政治环境,以色列通过大力推进“外围战略”扩大朋友圈,①这种“外围战略”表现为以色列政府试图通过与阿拉伯国家接壤的非阿拉伯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内的非阿拉伯民族建立密切联系、同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威胁的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联系,打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围困,抵消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参见汪波、历晶晶:《“外围战略”视域下的以色列库尔德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2期,第24页。从形式上突破了阿拉伯国家的围困。但是,“外围战略”塑造的朋友很多是基于“权宜之计”,以色列很少成功将这些短暂的合作关系转变为可持续的伙伴关系。①Rob Geist Pinfold and Joel Peters, “The Limits of Israel's Periphery Doctrine: Lessons from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Mediterranean Politics, No. 4, 2019, p. 2.一定程度上看,“外围战略”只具有帮助以色列实现短期目标的战术价值,尚不具备指导以色列长久解决国家安全困境的战略意义,中东变局之初以色列如履薄冰的窘境便是明证。当时,以色列为避免“阿拉伯之春”冲击国内稳定,对阿伯世界的动荡采取慎言慎行的政策,尤其是面对埃及大规模抗议活动,“以色列总理要求所有部长及官员保持高度沉默,不允许发表公开评论,以色列官方把任何轻易表态的言论都视为对政府与国家的不负责任”②张倩红、刘丽娟:《埃及变局后的以色列与埃及关系》,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24-25页。。因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一直对埃及具有较大依赖,尤其在阿拉伯国家涉以问题上,以色列希望埃及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埃及虽然充分利用与以色列保持官方沟通渠道的优势,通过在阿以问题、巴以问题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来提升自身政治地位,但在冷和平时期,两国的政治合作整体呈现“非对称”的特点,即以色列对埃及的需求远多于埃及对以色列的需求。
“7·3”事件后,西方国家指责埃及军队发动军事政变、侵犯人权、限制媒体自由等一系列举措有违“民主精神”,埃及军队及塞西政府遭到西方国家的冷落。而以色列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中东地区的“民主灯塔”,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关系密切,以色列的政治游说为塞西政府突破外交困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后不久,以色列便向美国、欧洲国家发起支持埃及军队的外交攻势。2013年8月,以色列驻欧美外交官纷纷与所驻国外长进行会谈就此议题交换意见,同时以色列政府对各国驻以大使施压,向他们强调“埃及军队是避免开罗(埃及)发生动乱的唯一希望”③《〈纽约时报〉:支持埃及当局的以色列的媒体和外交运动》(阿拉伯文),“埃及实时新闻”网,2013年8月19日,https://www.masress.com/moheet/700790,上网时间:2021年4月3日。。同年10月,美国宣布准备冻结对埃及的部分军事援助和价值2.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色列高官随即表态“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失望和担忧”,认为“美国是在玩火,这将削弱埃及军队、影响地区稳定”,同时以色列向埃及承诺,它将动员美国犹太院外集团游说美国政府继续向埃及提供援助。④《以色列担心美国冻结对埃及的援助》(阿拉伯文),“阿拉伯48”网,2013年10月10日,https://www.arab48.com/,上网时间:2021年4月2日。因此,“7·3”事件后,以色列成为埃及修复与欧美大国关系的重要桥梁,以色列的外交支持有利于塞西政府缓解国际压力、增加执政合法性。在此背景下,埃以的政治合作需求已经由“非对称”向“对称”转变,而中东变局发生后,土耳其在中东的强势回归也为埃以加强政治合作创造了新的着力点。
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布局“外围战略”的重要对象国,两国开展过密切合作,并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起双边准联盟关系。但是,土耳其和以色列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议题上出现战略分歧,两国的准联盟开始出现信任赤字并逐渐走向终结。此后,随着具有浓厚政治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执政,土以两国围绕巴勒斯坦问题龃龉不断,土耳其与哈马斯关系的升温更是引起以色列的高度警觉。2010年5月,“马尔马拉号救援船遇袭”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两国陷入长达六年的“口水战”。“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出于国内政党政治和谋取地区霸权的需要,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以色列的激烈交锋有增无减。2018年5月,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打死近60名巴勒斯坦示威者,土耳其驱逐了以色列驻土大使,两国爆发严重的外交危机。有学者指出,“以牺牲和以色列的关系为代价,土耳其似乎获利颇丰,尤其是对于埃尔多安而言,这些行动使得他以伊斯兰和巴勒斯坦的英雄自居”①李秉忠:《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2期,第30页。。
与此同时,在“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下,土耳其放弃了长期坚持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转而深度介入地区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首当其冲的就是埃及。2013年埃及军队罢黜穆尔西,破坏了土耳其试图在埃及推广“土耳其模式”和政治伊斯兰的战略构想,土耳其政府公开对埃及军队进行强烈谴责,并成为穆兄会的坚定支持者,土埃关系急转直下。此后,土耳其和埃及又因利比亚问题在外交上多次剑拔弩张。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埃及和以色列起初与土耳其并没有直接冲突,但随着东地中海海上边界的划定和海底管道建设项目的推进,埃及和以色列共同走向了土耳其的对立面。
(三)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由“强因素”向“弱因素”退化
“阿拉伯民族主义”又称“泛阿拉伯主义”,系指近代阿拉伯民族在民族觉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旨在争取生存、平等、独立、发展等一系列民族权益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②王铁铮:《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萌芽于19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逐步形成指导思想与理论架构,并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成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思潮。此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日渐式微,但仍然与国家民族主义相互交错共存于阿拉伯国家。前者根据民族差异对“我们”和“他者”进行划分、具有跨国界的特点,后者以国家边境为界、将国境内各民族视为统一的共同体,因此阿拉伯国家会出现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律背反”现象。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线阵营从“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扩大至整个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斗争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埃及对以色列政策深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的影响。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和纳赛尔的病逝,令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受重挫,萨达特在埃及执政后舍弃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中的激进成分,使其从属于国家(埃及)民族主义,直接推动了《埃以和约》的签署。虽然国家民族主义取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埃及对以色列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但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依然作为一个“强因素”制约着埃以关系的发展。穆巴拉克执政伊始便提出“埃及离不开阿拉伯,阿拉伯也离不开埃及”的主张,并表示埃及军队随时准备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履行自己的民族义务。①陈德成:《全球化时代的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2期,第23页。2006年7月,约100名埃及议员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突袭黎巴嫩南部村庄加纳、造成至少54名黎平民死亡的罪行,并要求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断交、埃及立即驱逐以色列大使。②同上,第28页。
正是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埃及在践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时始终受到“维护民族利益”的道义羁绊,这也是埃以关系始终难以突破冷和平的重要原因。但是,中东变局以来,“威胁复杂化、利益多元化和身份多重化,迫使阿拉伯国家在对外战略上寻求在‘再平衡’,包括缓和与以色列的矛盾”③孙德刚、韩睿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1期,第55页。。面对动荡的地区局势,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再定义,“政治正确”不再被“敌对以色列”的政策所捆绑。在这种背景下,埃及与以色列发展双边关系所面临的民族道义压力大大减小,与以色列单独媾和时遭致阿拉伯国家群体性孤立的场景不复存在。2020年8月至12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4个阿拉伯国家先后宣布同以色列建交,足以证明中东变局以来“先巴以、后阿以”的和谈顺序不再是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未来将更多由“巴勒斯坦人”、而非“阿拉伯人”去承担。
基于历史的视角可以发现,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相较于国家民族主义处于一个不断式微的过程。二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目标由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共同体”逐渐向多个阿拉伯主权国家实现“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转变,此后可能只局限于“文化共同体”。对此,当代埃及著名思想家宰克·纳克布·马哈茂德(Zaik Naqb Mahmoud)曾指出,“泛阿拉伯主义是文化格式,而不是政治格式”①王铁铮:《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第61页。。总体而言,至塞西执政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埃以关系的影响已经由“强因素”退化为“弱因素”,极大减少了埃以构建新型合作关系的阻力。此外,中东变局前埃以两国虽然维持了近30年的和平,但从未实现和解,埃及民众对以色列普遍“情感有余、友善不足”。中东变局后,埃及民众对以色列的关注度被国内政治、安全、民生等一系列问题稀释,为塞西政府深化与以色列的关系创造了客观条件。
四、埃以关系向准联盟发展的个人层面因素
准联盟关系的构建不是机械的“趋利避害”过程,而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互动过程。②孙德刚:《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第76页。因此,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虽然是以体系层面、国家层面的客观因素为出发点,但也会受到个人层面主观因素的影响。埃以建交后,以色列对外政策的决策者都希望能尽快和埃及发展更深层次的双边关系。从个人层面来讲,埃以关系由冷和平向准联盟发展的变量发生在埃及决策者一方,主要涉及国家领导人塞西和作为特权阶层的高级军官。
(一)国家领导人塞西
塞西15岁开始参加埃及军队,先后在野战部队、驻外使馆、军事情报局等机构任职,至2012年担任国防部长时已在军队服役43年,丰富的军事履历塑造了他果敢的个性。塞西是穆尔西为制衡前埃及国防部长坦塔维等“军中元老”所提拔的“少壮派军官”,中东变局之前他在埃及军中只属于二线人物。2013年7月,担任国防部长还不到一年的塞西在谏言穆尔西被拒后果断实行“兵变”,废黜了埃及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而当时中东地区还处于“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民主旋风”之中,埃及的民主化进程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塞西从政后,由军队统帅转身为政治强人,果敢的个性在其对内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塞西大规模压制政坛反对势力。政变后的一年内,埃及有4.1万人被拘禁,其中大部分为穆兄会成员。③JoeStork, “Egypt's Political Prisoners,” Human Rights Watch, March 6, 2015, https://www.hrw.org/news/2015/03/06/egypts-political-prisoners, 上网时间:2021年3月15日。2014年3月,在埃及法院的一次庭审中就有529名穆兄会成员同时被判处死刑。④“Egypt: UN Rights Experts Denounce Mass Death Sentences as ‘Mockery of Justice’,” UN News, March31, 2014,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4/03/465042-egypt-un-rights-experts-denounce-mass-death-sentences-mockery-justice, 上网时间:2021年4月1日。另一方面,塞西对武装力量内部的“异见者”进行大规模岗位调整。2014年至2017年间,埃及军队最高决策机构中有18名核心成员①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共25名成员。被撤换,2017年国家情报总局有19位主要负责人被迫提前退休。②《埃及2017:危机中的一年》(阿拉伯文),第19、94页。
在保持军人果敢个性的同时,塞西作为政治家又具有务实的一面。塞西是一位虔诚又相对保守的穆斯林。塞西上台后对国内最大的基督教群体科普特人实行怀柔政策,以破解中东变局以来埃及国内盛行的“文明冲突”。在两次总统就职典礼中,塞西均邀请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埃及科普特人领袖)与爱资哈尔大教长(埃及穆斯林领袖)同台出席,并高度称赞科普特人对埃及发展的历史贡献。塞西执政后,埃及议会还通过放松建设教堂限制的方案,多次讨论从埃及公民身份证中删除宗教身份一栏的草案。在对外政策方面,塞西积极推进埃及外交多元化,在美、俄、中等大国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这种平衡外交政策的核心正是实用主义。③李意:《埃及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述评》,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5期,第93页。正是在实用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塞西执政后对以色列一直持积极态度,在公开场合从未发表过批评以色列的言论。塞西因此获得以色列决策层的一致肯定,“私下以色列的高级官员将塞西称为‘我们的塞西’”④Anshel Pfeffer, “Why Israeli Fighter Jets Aren't Enough to Solve Egypt's ISIS Problem,”Haaretz, February 6, 2018,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why-israeli-fighter-jets-aren-t-enough-to-solve-egypt-s-isis-problem-1.5788574, 上网时间:2021年4月6日。,以色列国防部政策与军事事务局前局长阿摩司·吉拉德(Amos Gilad)少将将塞西描述为“历史将铭记的英雄和领袖,以色列和埃及的纽带”⑤[埃及]马哈茂德·贾迈勒:《埃及军队与以色列:思想的转变》(阿拉伯文),第110页。。除此之外,塞西和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交甚密,内塔尼亚胡称塞西为“我的好朋友”,而塞西评价内塔尼亚胡“是一位能力超强、可以带领以色列崛起的领导人”⑥[以色列]兹维卡·克莱因:《阿拉伯国家视以色列为盟友》(希伯来文),NRG网,2016年2月14日,https://www.makorrishon.co.il/nrg/online/1/ART2/754/717.html?hp=1&cat=404&loc=13,上网时间:2021年7月25日。。在以色列人看来,内塔尼亚胡和塞西具有的一些共同点将两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都感受到生存威胁、都要应对极端武装的挑战、都属于政坛中的保守派、都遭受媒体负面报道的困扰。⑦[巴勒斯坦]阿德南·阿布·阿梅尔:《当以色列称赞塞西时》(阿拉伯文),埃及研究所网站,2019年7月30日,第1页,https://eipss-eg.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pdf,上网时间:2021年3月27日。值得指出的是,与前总统穆巴拉克不同,塞西在整个军旅生涯中没有参与过对以色列的作战行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发生时,塞西还在埃及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归部队不久埃以便达成《戴维营协议》,此后埃以之间再无战事。2016年12月,塞西将前防空军司令阿卜杜·莫尼姆中将(Abdel Moneim)调离最高军事委员会,至此,以塞西为核心的埃及军队最高决策机构历史上首次所有的成员都没有对以色列作战的经历。
正是得益于果敢、务实的个性特点,加之与内塔尼亚胡的私交和没有同以军厮杀的历史恩怨,塞西在执掌埃及权力之牛耳后才能卸下埃以沉重的历史包袱,为两国深度合作搭建起信任之桥,在新形势面前再次以从上至下的方式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二)特权阶层高级军官
埃及的政治权力格局以总统为中心、由技术官僚和军人共享政治权力。其中,埃及总统常被称为“脱下军装的将军总统”,历届总统中除穆尔西外都是高级军官。埃及军队在反帝、反殖、反侵略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军人在埃及国内受到全社会的尊崇,很多军官退役后会在政府部门任职履新,尤其是高级军官一般身处政治核心,所以埃及也被称为“军官共和国”。纳赛尔担任埃及总统期间,先后有7个副总统是军官出身,17个副总理中有10个是军官出身。①詹晋洁:《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干政与政治稳定》,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59页。穆巴拉克执政后有意削弱军人的政治影响,提升技术官僚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但是退役的高级军官依然位居多个要职。以地方行政长官为例,穆巴拉克执政期间一共任命了156位省长,其中有63名是退役高级军官。塞西执政后,军队的影响几乎渗透到政府各个核心部门,高级军官从政的趋势得以延续并加强。目前,埃及27位省长中有17位是退役将军、2位来自于警察部门、8位由地方人士担任,这8位省长需要与24位退役少将共享权力,后者在省政府中担任副省长、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等职务。②Tom Stevenson, “Egypt: Land of the Generals,” Middle East Eye, November 7, 2014,www.middleeasteye.net/in-depth/features/land-generals-1661973598. 上网时间:2021年3月25日。此外,为扩大对外交、司法部门的影响,埃及军方要求这两个部门的新入职人员在正式上岗前到纳赛尔军事学院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封闭式培训,来自国防部、情报机构、安全机构的高官负责授课,以确保他们“政治正确”、服从军队高层的领导。③[埃及]阿穆尔·萨米尔·哈拉夫:《埃及外交:现状和未来》(阿拉伯文),载《埃及研究所杂志》2020年总第17期,第162页,https://eipss-eg.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0017_.pdf,上网时间:2021年3月20日。总体而言,现役与退役的高级军官组成的群体已然成为埃及的特权阶层,对埃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力。
埃及高级军官阶层在与以色列交往中通过“学习机制”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累积认知,它以埃以媾和为分界点由两个阶段构成。在第一阶段,军官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埃及军队难以战胜有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军队,而且埃及军队在战争中会受到重创”。在阿以冲突中,“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等国直接或潜在的军事挑战均给予强硬武力打击,持续的战败使埃及、叙利亚等国明确认识到以色列的实力优势和威慑决心,进而迫使这些国家对以色列采取克制策略”①刘华清:《“累积威慑”与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演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4期,第143页。。学界将其称为以色列的“累积威慑”。在第二阶段,军官从和平共处中认识到,埃及军队不同以色列作战也能保持在国内的地位,且埃及军队还能享受丰厚的和平红利。一方面,作为埃及同以色列媾和的直接福利,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另一方面,埃及军队开始大规模“下海经商”,构建起由军队控制的商业帝国。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军队也涉足经贸领域,但主要集中于军工产品。埃以媾和后,埃及国家重心由“备战打仗”转移到“经济建设”,在穆巴拉克时期大量军队控制的企业也随着兴起,经营范围已经拓展到民用商品、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能源工业等多个领域。至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军队经济’已经和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在埃及国民经济结构中呈三足鼎立之势”。②王建:《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6期,第93页。一些专家表示,埃及军队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已经高达40%,③Eric Knecht and Asma Alsharif, “Sisi Walks Fine Line Between Egypt's Tycoons and Generals,”Reuters, October16, 201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gypt-sisi-business-idUSKCN0SA1-FZ20151016, 上网时间:2021年3月28日。而军队的经济财富又主要集中于占比15%的高级军官群体中。④MarwaAwad, “Special Report: In Egypt's Military, a March for Change,” Reuters, April 10, 201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gypt-army-idUSBRE8390IV20120410, 上网时间:2021年3月30日。
穆尔西执政伊始基本履行了保护军队经济利益的承诺,尤其是继续给予军队不受国家预算监督的豁免权,政府和军队就经济领域事宜达成协议。但是,2013年在苏伊士运河发展计划和托斯卡(Toshka)土地复垦项目等大型工程上,穆尔西试图让军队“靠边站”,此举遭到了以塞西为代表的高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有消息披露,在争执期间,穆尔西曾想用一个更容易控制的人取代塞西担任国防部长,最终因为军方反对而被迫放弃。⑤Shana Marshall, “The Egyptian Armed Forces and the Remaking of an Economic Empir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15, 2015, p. 1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egyptian_armed_forces.pdf, 上网时间:2021年4月3日。穆尔西触犯军队经济利益的举动,成为高级军官阶层与穆兄会决裂的重要导火索,而以色列在推翻穆尔西政府、打击穆兄会势力问题上与埃及高级军官阶层具有高度的战略一致性,这进一步强化了后者把以色列视为利益共同体的认知,为埃以关系深入发展提供了政治支持和力量保障。
五、结语
塞西在埃及执政拉开了埃以关系向纵深发展的序幕,两国在一系列密切的安全合作中逐步形成一种新型双边关系,它具有准联盟的基本特征,属于其中的弱准联盟。这种双边关系的构建与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变量有关,其中地区体系的结构变化为埃以关系的新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政策决策者的人事调整和累积认知为埃以关系的调整提供了稳定的政策保证。而推动两国关系突破冷和平、向准联盟发展的最主要动因则源于埃以国家利益诉求的变化,尤其是两国的安全利益遭遇共同的威胁。塞西执政后,面对内外乱局的严峻形势,埃及和以色列在双边事务、地区问题上的增量共识超越了存量分歧,即使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反而成为了两国携手合作的新平台。埃以是“安全—政治—利益”共同体的共同认知成为两国关系向准联盟发展的根本动力。2021年6月,贝内特接替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新一任总理,可以预期以色列新政府将延续内塔尼亚胡时期的对埃政策,埃以的准联盟关系将得以维系和发展,但它难以达到强准联盟的程度。
埃及和以色列作为中东地缘博弈的重要参与方,两国关系的新发展是中东格局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步入大调整时期的例证,同时它也将进一步加速“新中东”的形成。二战以来,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范式兴盛于中东地区,其中有针对临时性任务、持续时间非常短暂的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苏伊士河战争期间的准联盟,有持续过较长时间但后来反目的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准联盟,也有历经考验、持续至今的美国和沙特的准联盟以及伊朗和叙利亚的准联盟等,这充分体现了准联盟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中东变局与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双重影响下,中东国家的地缘政治呈现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准联盟成为中东多国的重要选项,未来的中东将呈现多个准联盟体系相互交叉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