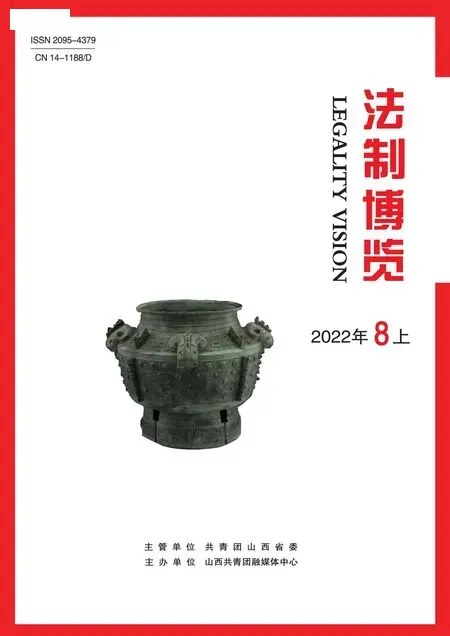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比较研究
张 娜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 100025
202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决定开展历时三年的专项行动以打击治理全国的洗钱违法犯罪活动。一直以来,《刑法》分则设置的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都作为我国反洗钱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机关惩治洗钱犯罪、查没犯罪所得,进而实现打击上游犯罪、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等目标的重要法律依据。然而,从现有立法规制来看,二者并非泾渭分明、相互独立的两个罪名,而是存在竞合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1]。在最高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该二罪的司法解释中有明确规定,即:掩饰、隐瞒明知是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的,如果既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又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2]。可见,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常被作为关联罪名予以适用。本文旨在结合该二罪名的立法演进、现有法律规制及相关司法案例,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厘清该二罪名的异同之处,以期为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正确适用罪名提供参考。
一、立法演进
(一)洗钱罪的立法演进
我国关于洗钱罪的立法最早可追溯到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该决定将掩饰、隐瞒贩毒所获财物非法性质和来源的行为认定为洗钱犯罪。1997年《刑法》的修订正式确立了洗钱罪的罪名,并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明确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三类。在其后发布的《刑法修正案(三)》(2001年)和《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中,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外延从四类扩大至七类,增加了恐怖活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明知”“协助”等规定,突破了以往洗钱“事后不可罚”之立法局限,构建了自洗钱独立定罪入刑的法律新框架[3]。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立法演进
该罪始源于赃物罪,最早出现在2007年5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4]中。该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实施买卖、介绍买卖等掩饰、隐瞒行为的,应依《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科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该罪名的正式确立则是在基于2007年10月两高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中,该规定明确取消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确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二、二罪的同质性研究
(一)均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
为了充分保护本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行法律规定,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须在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也即上游犯罪经依法裁判后方可认定,但此规定仅为认定该二罪的一般原则。特殊情况下,如:上游犯罪还有难以查清的其他事实或者上游犯罪嫌疑人一时难以抓获等,导致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那么本罪只要达到查证属实的标准,就可予以认定。值得说明的是,对于上游犯罪行为人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情形,只要达到查证属实的标准,也不影响本罪的认定。
在谭某松案(案号:(2014)临刑初字第5号)中,被告人谭某松明知没有合法来历证明的摩托车系犯罪所得,仍用800元低价予以收购,虽然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审理本案时尚未被抓获,更没有经过法庭裁判,但结合被害人的陈述、车辆购买证明等证据,完全可以凭现有证据证实上游犯罪事实的存在,因此本案中即使上游犯罪未依法裁判,但客观上已经达到了查证属实的标准,所以并不妨碍对谭某松本罪的认定和量刑。
在元某案(案号:(2013)大少刑初字第11号)中,被告人元某在经营元记金银加工店期间,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5700元收购了黎某某在大城县县城内抢劫所得的两条断裂损坏的黄金项链。虽然在上游犯罪中,公诉机关因黎某某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依法撤回起诉,但在本案中司法机关对元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依法并不受此影响。
(二)均存在掩饰、隐瞒的主观故意
认定洗钱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时,须证明当事人在主观上对掩饰、隐瞒对象是或可能是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具有明知的故意。这种所谓的明知,除了可以直接证明的以外,还应当充分结合被告人认知能力的有无高低、犯罪所得的数额大小、转换转移所得的方式等主、客观因素来综合认定。
在张某泉案(案号:(2010)南刑二终字第205号)中,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张某泉明知案涉车辆系盗抢所得,但综合考量行为人在明知交易的是套牌车,且是在非正规交易场所以明显低于同类车市场价格的情况下购买的,已完全可以合理推断出行为人不可能不知道案涉车辆系犯罪所得,即可以推定被告人存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故意。
三、二罪的异质性研究
(一)上游犯罪种类存在差异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是特定的,仅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类,也即:只有针对这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实施的掩饰、隐瞒等行为方才构成洗钱罪,否则只能以掩饰、隐瞒罪论处。
在陈某案(案号:(2018)川3423刑初76号)中,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明知妻子沙某的巨额所得与其自身的职业及职业收入明显不相符,而是通过贩卖毒品所得,但仍然为其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帮助沙某掩饰资金的来源和性质,该行为符合洗钱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依法应以洗钱罪论处。
(二)所侵犯的法益存在区别
该二罪分别设置于《刑法》分论的不同章节之中,显著体现出二者所侵犯的法益存在不同。掩饰、隐瞒犯罪设置于妨害司法罪之下,该罪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司法机关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对上游犯罪赃物的追缴[5]。洗钱罪设置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下,该罪侵犯的法益除了追查上游犯罪和追缴赃物的司法活动外,更侧重的是对金融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
在揭某春洗钱罪二审案(案号:(2017)赣01刑终92号)中,抗诉机关认为:揭某春在司法机关对其女揭某珍已立案查处的情况下,仍通过卖出股票、存入银行等方式掩饰、隐瞒揭某珍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其犯罪行为不仅严重妨害了司法秩序,更严重对抗了金融机构关于客户尽职调查和可疑交易监测的反洗钱监管要求,严重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以洗钱罪论处。二审法院采纳了抗诉机关的意见,撤销了一审中对揭某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改判揭某春构成洗钱罪。
(三)行为性质的区别
掩饰、隐瞒犯罪之行为性质主要体现在对上游犯罪所得及所得收益本身的掩饰及隐瞒,而洗钱罪之行为性质则主要是侧重于对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性质与来源进行掩盖及隐瞒,也即存在将赃款“漂白”、使违法所得“合法化”的目的[6]。
在袁某芳洗钱罪案(案号:(2018)渝0105刑初1338号)中,被告人袁某芳辩称自己虽然知道案涉资金系弟弟袁某圣贪污受贿所得,但其始终是在袁某圣的指示下保管资金、购置房产车辆,而这仅仅是一种协助使用犯罪所得的行为,因此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袁某芳以本人名义将犯罪所得存入银行账户并以自己和丈夫名义购置房产车辆的行为本身已突破了对案涉资金的物理占有与使用,客观上实现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手段改变案涉资金的性质和来源,主观上存在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意图,因此依法应以洗钱罪论处。
(四)量刑存在差异
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依法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关于情节严重的情形,现有法律已有明确的规定。如:掩饰、隐瞒金额巨大超过10万元的;或掩饰、隐瞒次数频繁超过10次的;或掩饰、隐瞒的金额和次数达到一定标准(3次且5万元以上);或掩饰、隐瞒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如公私财物受到巨大损失、严重妨害对上游犯罪的追究查处等。
犯洗钱罪的,一般面临没收实施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关于何为情节严重,并无像掩饰、隐瞒犯罪一样有着明确的标准。在周某洗钱罪再审案(案号:(2017)湘0603刑再1号)中,被告人周某按照其同学丁某的指示,提供银行账户,并通过转账、提现等方式协助转移受贿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达1315万余元。再审审理中,检察机关提出原审被告人周某属于情节严重,原审判决对其量刑畸轻。但审判机关则提出因洗钱罪关于情节严重的标准和认定,至今无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在审判实务中,洗钱罪的具体量刑往往未适用情节严重条款,因此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不认定情节严重。
(五)是否属于不可罚之事后行为的差异
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言,根据其与上游犯罪的关系,掩饰、隐瞒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发生于事后的帮助行为,对此仅单独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毫无疑问。另一类是与上游犯罪存在事前、事中的通谋,对此该认定数罪还是仅认定前罪即由前罪吸收后罪呢?根据不可罚之事后行为理论,即在某个犯罪既遂,又实施了另一个犯罪行为,但如果后一个行为没有侵犯新的法益或者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就不可处罚[7]。因此,当掩饰、隐瞒行为与上游犯罪存在事前或事中通谋的情况下,不应认定数罪,应以上游犯罪的共犯论处。
但在洗钱罪中,由于本罪中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犯罪收益所得是法定七类上游犯罪所产生的,掩饰、隐瞒的主观意图在于通过“漂白”的方法将违法所得及收益合法化,且同时与上游犯罪存在通谋,那么洗钱罪的掩饰、隐瞒行为就因为侵犯了两类不同的法益而不再属于不可罚之事后行为,因而应对掩饰、隐瞒的行为与上游犯罪行为同时认定数罪。
在李某林犯贩卖、运输毒品罪、洗钱罪一案(案号:(2021)赣1022刑初124号)中,被告人李某林伙同他人开车从外地购买氯胺酮并运输回抚州进行出售,为了掩饰资金来源,在贩毒过程中先后使用付某等人微信收取转移毒资。如前所述,被告人李某林“自洗钱”之行为已因企图漂白资金性质、掩饰资金来源而突破了事后不可罚之限制,触犯了独立的罪名。最终,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数罪,即:被告人同时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和洗钱罪,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综上,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客观上即上游犯罪事实成立,及主观上即行为人具有明知的故意两方面具有相同点。区分该二罪的关键更多的在于厘清上游犯罪是否属于七类特定犯罪、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否具有多重性以及行为性质是否侧重掩饰隐瞒所得及收益来源和性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