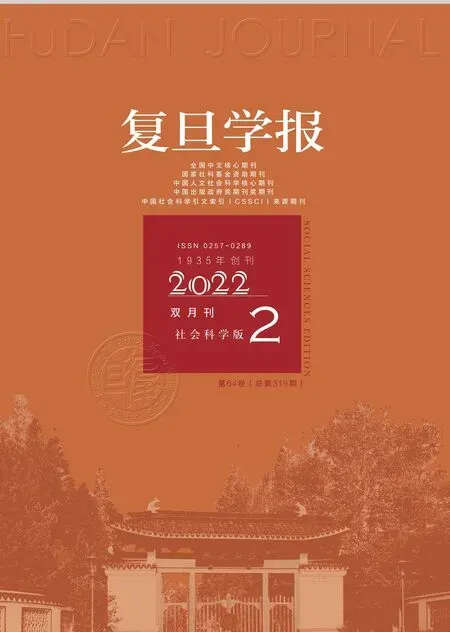列维纳斯的爱欲现象学及其东方回声:围绕《论家:个体与亲亲》的一个讨论
汪 沛
(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上海 200433)
列维纳斯在中国思想界激荡起重重回音并非出于偶然。列维纳斯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晦涩(ambigüité)大约是原因之一,这种含混的语言风格为不同角度的诠释打开了空间。同时,他个人的经历也带有诸多难以归类的特征:虽然在中国学术界看来,列维纳斯是法国哲学家,但他本是立陶宛的犹太人(某种东方人)。与更加学院派的哲学家相比,他极度突显的他者视角过于新锐;与后现代哲学家相较,不断诉诸《塔木德》解经传统的他又显得有些古旧;与当红的现象学家比起来,他虽然是最早把现象学引入法国的人,却也最早宣称自己已然与现象学方法相别甚远。归类的困难与诠释空间的广阔形成了正比,而这种杵在进退之间“站在门槛上”的特征恰好与中国当下的思潮形成了一种共鸣,而这也是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1)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思想背景之一。
以下我们会先讨论当前中国思想界进步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再来看这一思潮何以与列维纳斯的爱欲-现象学产生了轰鸣,最后对这一轰鸣所激荡出的“温暖现象学”做一分析,讨论《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与列维纳斯爱欲现象学的渊源。本文也尝试解释儒家在与西方(同时也是另一种东方)思想对话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同时揭示列维纳斯思想所震荡起的这一东方回声与列维纳斯的关系。
一、 进步的保守主义
进步的保守主义其来有自。进步意味着要尊重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例如反对杀害无辜的人、迫害、虐待、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而保守(conserve)则意味着要保存、保护(conserve)一个文化中原本就有的精华。如同贺麟先生八十年前所言:“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很新,满口的新名词、新口号,时而要推翻这样,打倒那样,试考查其实际行为,有时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而不自觉……既不能保持旧有文化的精华,又不能认识新时代的真精神……我们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2)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原载《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后收入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对传统观念批评容易,对流行意见检讨则难上加难,而当今我们仍旧对流行观念抱有一种轻佻的消费主义态度:只要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最好尽快有。随之而来的自然有很多小偷小摸和江洋大盗,似乎只要是思想界的新产品就很容易以引介之名拿进来展开说教。这种模式既不尊重这些流行观念,也不尊重自己的理解能力,只能徒劳地喊出一些教条的口号,于堕落之中假想自己在战斗。
贺麟先生当年已经极为反感对于新事物的盲目追捧,所以提出要从传统之中推陈出新,检讨传统观念中的僵化之处,同时也批判流行观念中的教条部分。(3)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每每讨论一个美德之前会先参考“流行意见”,而这种很直接的方法却往往被懒惰的现代人所忘却。我们习惯于认为最新的就是更正确的,却忘了有时候新潮只是时髦,未必就更真。既肯定传统中的精华,也肯定时代精神的指引方向。由对于传统观念与流行意见的双重检讨,达到对传统与流行中精粹部分的双重肯定——这种方法所相应的态度我们称之为进步的保守主义。每一种传统都在新的时代下值得拥有相应的进步,每一个社会都应当有独立于其他社会判断标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4)参见拙作:《平等、差异与等级——进步的保守主义视角》,《 东方学刊》2019年第4期。因此,进步的保守主义也不单单适用于中国社会,当代多极世界中其他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例如印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遇。
同时,进步的保守主义也不仅仅适用于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更进一步地说,甚至在基督教文明内部,相对传统的天主教与东正教也面临同样的处境。任何不那么“新”的思想要么被封为“传统”供起来,要么被打为“糟粕”直接扔走,似乎未经审查的流行观念也可以被默认为进步,好像只要有一点不接受流行意见的就是退步的泥古主义(traditionalism)。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什么重视习俗与传统的社群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与天主教传统价值的检讨与复兴息息相关。(5)作为社群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与查尔斯·泰勒的思想都有这种指向,参见查尔斯·泰勒著,张容南译:《世俗时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至于东正教传统复兴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亚历山大·杜金的著作。
列维纳斯比社群主义者们更早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流离的犹太人如何在现代国家中生活?如何在这样流浪的命运中保存犹太民族?如何和现代世界中独立的民族国家发生关联?如何理解犹太人与全体人类的关系?列维纳斯早期尝试通过爱欲-生育现象学来进行探索,总体的暴力不仅仅指向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其中也包含了一些自我批判的成分。不仅仅是犹太人作为他者来到了已经被其他宗教占据的土地,也是现代国家和基督教神学来到了犹太人的门前。真正的关系总是相互的,这和基于权力(总体)还是基于爱(无限)无关。《总体与无限》中爱欲-生育现象学为我们启示的层次远比文字本身直接展现的更为复杂,而这种幽微的复杂性也正是进步的保守主义所要求的。
二、 爱欲现象学
在西方哲学界谈论爱欲从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伯恩耶特曾经说过:“在1992年的我们都读过格雷戈里[弗拉斯托斯]论爱, 这篇论文经常被讨论、辩论、甚至反驳, 我们却很容易不理解写作和出版它所需要的勇气。早在1969年,爱还不是哲学研讨会上常见的题目。”(6)Miles F Burnyeat, “Gregory Vlastos,” Phronesis 37.2 9 (1992): 138.这段话是对当年古希腊哲学研究界的一个写照,而它也同样适用于出版于1961年的《总体与无限》(7)列维纳斯著,朱刚译:《总体与无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其中,列维纳斯在第四部分“超逾面容”中讨论了爱欲-生育现象学。这部分的严肃性与重要性长期以来遭到了忽略,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是列维纳斯写作的时候随意添加上去的。(8)参见Bettina Bergo, Levinas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108,转引自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62页。
爱欲-生育现象学当然不是列维纳斯随意写作的结果。从2009年起,法国学术界开始整理列维纳斯早期未曾刊发的手稿,其中第三卷有一部分集合了散落在笔记本、信笺活页和其他零散纸张上的内容,编纂者称之为“关于爱欲的哲学笔记”,由五个集子组成。在脚注中,编纂者对此有所解释:“这标题并不出自列维纳斯本人,然而其中内容全然与之相符。”(9)Emmanuel Levinas, Eros, Littérature et Philosophie : Essais romanesques et poétiques, not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thème d’éros (=uvres 3), par Jean-Luc Nancy et Danielle Cohen-Levinas (éd.), Paris, Grasset - IMEC, 2013 : 159.这部分主要讨论了“自我-他人”的关系,列维纳斯讨论了五种形式:物品交换、理智交换、共事关系、友爱和爱欲。他要追问的是,他人究竟显现于何种关系?自我的独特性(unicité)又如何能确立起来?他的答案很明确:只有在爱欲当中才有可能。
在未刊稿中,列维纳斯从被他视为最表层的社会关系开始分析,首先是物品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与我们打交道的人对于这一关系本身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换中双方的物品或者服务。当人们进入到了理智交换关系时,重要的则是双方共同探讨的问题或者真理。共事关系是列维纳斯分析的第三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因为偶然因素,我们与另一些人分享了共同的工作、国籍乃至命运,可谓关系紧密。但是,这种关系中的个体相互之间是一种肩并肩的关系,人们在其中仍旧不能认出每一个实存者的独特性。仅当人们进入友爱关系中,自我与朋友之间因为相似而融合在一起,然而又因为朋友是另一个自己(alter ego),所以朋友成了不具备他异性的对象。也就是说,朋友的个别性乃是基于与“我”的相似,两个相似的个体无法互相认出对方的独特性。在进行重重还原之后,列维纳斯发现并确认,作为真正具有他异性的他人首先出现于爱欲关系之中,因为爱欲中的爱人作为女性展现了彻底的他异性,而这一他异性进一步延伸至孩子的他异性,进而由于与这样真正的他者有爱欲关系,主体的独特性才得到彰显。(10)更多的讨论参见拙作:《作为他人的他人——从〈关于爱欲的哲学笔记〉中“自我—他人”关系类型来看》,《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2期。
显然,在未刊稿里,爱欲关系对于理解他人之他异性至关重要。未刊稿残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说明《总体与无限》中对爱欲问题的讨论并非仅仅是信手拈来的篇章,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列维纳斯在早期作品中对爱欲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追问视角:他人何以呈现为具有他异性的他人?爱欲中他人的独特性如何证成?我们又如何从爱欲中实存者的独特性来推及所有实存者的独特性?
在《总体与无限》中,爱欲是为了超逾面容而出现的。面容指的是不断突破光照所赋予实存者的外在可塑形象的形式化的自我呈现,突破光的规定,展现出不同于普遍匿名之光的风貌,列维纳斯将其称为“去形式化”:拒绝形式之光的照亮,拒绝被大全总体同一化,这样的他人彰显了无限观念。这种不同与相异意味着临显于面容之中的他者具有绝对他异性,就是他人。这样的他人不同于在光之世界有所栖身的主体,他人是赤贫的鳏寡孤独,同时又因其他异性处于比主体更高的位置。他以赤贫者的身份呼求主体的欢迎,同时又以高位者的身份向主体发出命令:“汝勿杀。”
主体的回应承担起了他者的呼唤,主体将自己置身于与他人的话语的关系中。这样一来,有限的主体就在与面容的关系之中获得了无限观念,进而从大全整体中剥离出来,获得了个体化。但问题在于,临显于面容之中的他人实质上又是面容模糊的,因为面容虽则不同于大全整体,却并不能具体化为某一个别的实存者。于是,与面容的关系只能实现主体的独特性而无法实现他人的独特性。这就是为什么“超逾面容”作为一种需要被提了出来。在这里,爱欲以另一种论证途径被带入讨论中来。
爱欲超逾面容,而爱欲又是充满两可性(ambigüité)的。“两可性”这个词本来就有两种含义:一种指的是二义性,就是能够同时以两重相互矛盾的意义来理解某个事物,从而造成暧昧不清的状态;另一种则是模糊性,并不是指同时呈现相对的意义,而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关于这种两可性的第一层含义已经得到了很多揭示,我们更希望探讨两可性的第二重含义:摆荡与摇曳。
列维纳斯给出爱的两可性的第一个方面:“从本质的某方面来看,那作为超越而指向他人的爱,把我们抛回内在性本身这边(en deçà)。”(11)列维纳斯著,朱刚译:《总体与无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4页。这种运动虽然朝向大写的他者,然而主体却寻找着“开始寻找之前就已经与之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尽管他是在外在性中找到它的”。(12)③④ 列维纳斯著,朱刚译:《总体与无限》,第244、245、245页。也就是说,在这种运动中,虽然主体试图寻求外在于自己的实存,但是它探寻的准则却是与自己内在息息相关的品质。这就依旧是在光的世界中认出并且寻找与自己相像而亲熟的实存,于是,对于运动之朝向还不曾有任何选择,方向就已经确定,犹如命中注定(prédestination)。在这种情况下,爱具有被还原为这种彻底的内在性的可能。
列维纳斯援引柏拉图《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所讲的故事(13)参见柏拉图著,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第309~314页,189d~193a。,来进一步说明这种可能性:爱在于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在于把分离的两半重新煅造在一起。故事的隐喻指向这一还原,本来应该时时更新、毫无止境地朝向未来的欲望(désir)就地打破,转变为需要(besoin),而且竟然就像那些最为自我主义的需要那样得到了满足。两个分离的半人终于黏到了一起,两个存在成为了同一个,自我(le moi)回归到自身(le soi)。爱欲的这种可能性与列维纳斯未刊稿中“自我-他人”关系类型中的友爱完全一致,在那里,列维纳斯也同样引用了阿里斯托芬这个神话。指向他人的爱就是友爱,这一运动在光芒之中向着他人前进,却由于自我所具有的特质而落回自身,运动停止了,超越不再可能。直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也只是爱的一种可能性,即最为鲁莽的爱可能会被还原为需要。
但是,爱的两可性在于,爱不仅仅有可能落回自身,“爱也超逾(au-delà)被爱者”。(14)③④ 列维纳斯著,朱刚译:《总体与无限》,第244、245、245页。这种情况下,从被爱者的面容背后透出来依稀晦暗的光线,光源来自比被爱者更远的地方,那是“怎么也不够未来的未来,比可能更远”(15)③④ 列维纳斯著,朱刚译:《总体与无限》,第244、245、245页。的地方。它从完全彻底的将来(avenir)那里投射过来,它远远超出了“我”或者被爱者,这意味着一种超越性。“晦暗的光线”,这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用词,光何以会是晦暗不明的,这种晦暗的光线不同于理智的普遍之光,它并不意在揭示、理解、吞没“我”或者被爱者,这矛盾的词汇预示着将要临到(à-venir)的事件,也就是我们将要谈到的生育和无限时间的诞生。
这样看来,爱欲运动要么落回内在性,要么超逾被爱者。爱的两可性在友爱与爱欲之间的滑动,大写的他人在爱的两可性之中唯有一种机会持守自己的他异性,即是在爱欲之中。哪怕他人显现为需要的对象,也同时能在爱欲中与将来(avenir)发生关联,这种关联揭示出不同于自我同一性的主体,通过生育,通过实体转换,它实现了不能被满足的形而上学的欲望。
作为主体的爱者与作为他人的爱人之间永远有一不可跨越的间隔,这种间隔意味着爱欲中的二元性永远也无法被克服,这就是爱欲中的悲怆。这种悲怆意味着爱人一直保存着他异性,保持着他异性的他人就是对大全总体的溢出和超越。在爱欲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中,爱人就能够作为独特的个体浮现出来,主体的独特性基于爱人的独特性。
三、 实体转化
就在爱欲的二元性发生之际,生育同时产生了,因为主体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总体性的主体了,他的时间形式爆裂了,他变成了别样的(autre)他者(autre),列维纳斯称之为“实体转化”(trans-substantiation),也就是一个实体转化为另一个实体。爱欲的悲怆延续到了代际关系之中,父(母)与孩子并不是同一实体,也不谋求某种同一性的回归。因为孩子是属于未来的实存者,孩子来到世界是理性筹划与知识权能之外的事件,所以我们也不能以普遍的知识或者权能的思路来理解孩子。正因为孩子处于权能之外,所以孩子也是不同于整体大全的实存者。
父亲不占有孩子的实存,孩子是父亲的他者(autre),是别样于(autre)父亲的实存者,是父亲在爱欲之中从主体位置上撤下来以后所成为的他者(autre)。孩子是开启了崭新的时间端点的实存者,更新了父亲的生命,为父亲的生命带来了青春的律动。通过打开新的时间端点,孩子也实现了对大全总体的超越。同时,父亲又是儿子,(16)列维纳斯讨论生育的时候只讨论“父-子”关系,但这是一种哲学上的隐喻,并非生物学的描述。因为孩子从父亲生出,父亲的实存生育出孩子的实存,父亲的实存在孩子的实存之中获得了全新的展开,这一全新展开与父亲的实存又有着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同于同一性,并不是要把儿子塑造成与父亲同样的实存,而只是指出实体转化之中主体历史的统一性。于是,“父亲是儿子”这一申言中“是”作为系动词展现出了不同于同一性的另一种样式,它能够展现出实存中的复多性。儿子的独特性来自于父亲的独特性,而父亲的独特性是我们在爱欲之中通过爱人的独特性确立下来的。儿子是快感之中撤离主体身份的爱者所成为的他人,每一个儿子都与父亲有着唯一可能的关系。
爱欲之中相爱者的独特性都已确立,生育之中父子的独特性也得到了确立,我们就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兄弟关系。列维纳斯不是经验地讨论兄弟关系,而是把论题放在了“人人皆兄弟”这样的宏大视角之下。论证至此,被光芒照亮的大全总体世界已经彻底坍塌,由一个个具有独特性(unicité)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呈现了出来。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实存者有权能占有另一个实存者。于是,暴力被杜绝,个体之间不是不同意志的对抗,而是由温存蕴藉的交互性的爱关联起来。
这一富有传奇浪漫色彩的社会构想,从根本上来源于列维纳斯对阴柔被动气质的赞许。唯有我们在爱欲之中看到的那毫无戒备、被动温柔的女性所带来的完全相异于阳刚的另一种气质,才使得这样阳刚的主体学会体恤、学会主动放弃权能、学会以爱而不是以权能来看待世界。就在与一个个别的爱人的关系中,主体借此呈现出了自己的名,也能指出儿子的名,正是这种爱,通过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铺展到了整个社会。至此,我们可以说,倘若没有爱欲这种亲熟关系中女性阴柔被动之他异性,实存者的个别化绝无可能,社会中的亲爱与和平也遥遥无期。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爱欲-生育现象学中提到的生育,也即“实体转化”原本是一个天主教词汇,通常译为“变体”,在宗教中特有的内涵即是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祝圣饼和酒时曾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以后教会在作弥撒时由主礼的神父照此述说。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观点,此时饼和酒的质体已转变为耶稣的肉和血,原来的饼和酒只剩下五官所能感觉到的外形。”(17)丁光训、金鲁贤:《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列维纳斯的借用中有一个小小变化,即把前缀“转化”(trans-)与词根“实体”(-substantiation)间隔开来,更像是取其字面意思,就是一个实体转化为另一个实体。但这里又有一种隐喻意义上的翻转,就在爱欲-生育的过程中,主体因为这种爱的转变,在成为别样的(autre)他者(autre)之时,也拥有了神圣性,就像饼和酒转变为耶稣的肉和血那样;反过来,每一个实存者本身原本也是神圣的,而这种神圣性需要在爱欲-生育中得以揭示。
“实体转化”的提出,与列维那斯对犹太人的二战经历的思考相关。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杀戮该以何种方式被铭记?犹太民族在大地上如奥德赛般游荡所遭到的总体性创伤又该如何得以净化?列维纳斯对总体、阳刚、权力、知识、男性这一系列星座式的观念的批评毋宁是一种控诉,他呼吁无限、阴柔、爱、秘密、女性的力量,用爱为僵化的主体带来生机和青春的活力,在爱欲的黑夜里净化总体的罪恶与伤痛。
拯救主体,这是《总体与无限》的目标。爱欲-生育现象学很明确告诉我们,唯有阴柔的女性力量可以做到。这与列维纳斯在未刊稿中热衷于反复引用并分析的《浮士德》的主题密切相关:“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属人的维纳斯,把快感与简单的愉快相似对待,属天的维纳斯,是对善的凝思,两者之间所忽略的永恒的女性,成为了爱欲的核心概念。”(18)Emmanuel Levinas, Eros, Littérature et Philosophie : Essais romanesques et poétiques, not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thème d’éros (=uvres 3), par Jean-Luc Nancy et Danielle Cohen-Levinas (éd.), Paris, Grasset - IMEC, 2013: 182.两个维纳斯就是《会饮篇》里包萨尼亚所讲的两个爱神,属人的爱神引人眷恋肉体,而属天的爱神鼓励人们热爱灵魂的美德。(19)参见柏拉图著,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第299~305页。“女性——永恒的女性——由神秘组成其存在。”(20)Emmanuel Levinas, Eros, Littérature et Philosophie : Essais romanesques et poétiques, not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thème d’éros (=uvres 3), par Jean-Luc Nancy et Danielle Cohen-Levinas (éd.), Paris, Grasset - IMEC, 2013: 186.永恒的女性则是爱欲中的神秘爱人,是主体永远无法抵达的他者,是一切阴柔被动的能量,就如同列维纳斯所理解的理念中的犹太人 。在列维纳斯心中,二战后的犹太人就当是这样的:大地或许已经被这些人或者那些人占有了,但犹太人不在大地上扎根,不企图占有,只是流浪、散落、与他者(/无限)相遇。在主体发生实体转化的时刻,主体的隐喻爱人不也经历着实体转化吗?犹太教的智慧如果仅限于民族之内,不也自我封闭成为了某种大全总体吗?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总体性的批判也是对于犹太民族的自我批判。列维纳斯要求的实体转化,指向的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他也要求犹太教指向一种更普遍的伦理价值 :“人人皆兄弟”式的正义与和平。
爱欲-生育现象学明确将亲熟性之中的爱欲推演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哪怕从未与“我”真正地邂逅相逢,但只要拥有人格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样的实存者就与我情同兄弟。面对他者,被父亲的爱欲所拣选出来的儿子就有天然地侍奉他者的意识,他意识到自己对于他者负有责任,他成为了社会中的实存者,成为了为了“他者而实存”的实存者。这也是列维纳斯所说的,爱欲行进至比面容更远的地方,却又没有走得更远。“爱欲-生育”在超逾了面容之处又反转落回于此,爱欲出发于私密性却又回到了社会性,爱欲之两可性在这里再度得到证实。
爱欲-生育现象学所指向的伦理学天然地有一种进步的保守主义风格,正是因为它无处不在的两可性保证了这种复杂。无限的时间是由死亡与复活构成的,因此是不连续的。这要求主体不断地在爱欲与父子关系中去进行实体转化,这种实体转化一方面是回溯主体本身,一方面要求全新的别样(autre)的他者(autre)。爱欲-生育现象学也是列维纳斯早期对于以流散作为命运的犹太人的处境不断思考与推敲的结果:犹太人在被其他宗教所占据的现代国家中如何生存?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正是这些相似的问题意识在中国(恰恰不是首先在西方国家)激荡起了同样具有进步保守主义风格的回声。
四、 作为回声的“温暖现象学”
列维纳斯于很多书名中都有“与”,例如《时间与他者》(21)列维纳斯著,汪沛译:《时间与他者》,《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22)③ 列维纳斯著,王士盛,王恒校译:《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3页。,但是《总体与无限》书名中的“与”有着特定的含义。列维纳斯曾经自己解释道:“在对总体的批判中——把‘总体’和‘无限’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这一做法本身就隐含着对总体的批判——矛头所指向的是哲学史。”(23)列维纳斯著,汪沛译:《时间与他者》,《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24)③ 列维纳斯著,王士盛,王恒校译:《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3页。因为在这里,“总体与无限”恰恰不是“总体的无限”或者“无限的总体”,而是反过来,这个连词“与”要在“总体”和“无限”之间划出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彰显列维纳斯对于西方哲学史中“总体性乡愁”的批判。当列维纳斯谈论不同于“总体”的“无限”之时,他指的是对于“总体”的“时间观念的去形式化”(25)Emmanuel Levinas, Entre nous. Essais sur le penser-à-l’autre (Paris: Grasset, 1991) 263.:人生而有死,有限的形式化的时间在主体与他者(也就是无限)相遇之时爆裂了,成为了别样的(autre)他者(autre),与主体毫无叠合的真正他者才能带来这样的深刻转变。主体不是要回归大全总体中成为匿名的一个单子,而是在和他者的相遇中,在与他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间隔中真正认领了自己的独特性(unicité)。
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以下简称《论家》)的副标题同样富有深意,也体现了“爱欲现象学”与“温暖现象学”的不同之处。这是一本关于家的书,但副标题指的却是书中所提到的“双重本体”。(26)参见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第一部分。这不仅意味着当今天我们谈论家的时候,其实谈论的是家中的人的问题,即人的双重本体:“个体为重”“亲亲为大”;同时指的是,在当代中国,对于“个体”与“亲亲”的问题,首先要在家这个范围里展开讨论。这也让我们想到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常识:成人之道总是从家庭开始。那么,“个体与亲亲”中的“与”恰恰不同于“总体与无限”中的“与”,同样的连词在此表示一种融合与兼顾。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推进一点对于“双重本体”的分析。诚然,“双重本体”旨在兼顾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与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27)参见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第10页。然而“个体”仍旧排名在先,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是整本书讨论的基础。这本意在当代中国拯救“家”的书,拯救的更是家中的人。首先要拯救的是个体,才能有真的“亲亲”。健康的个体首先要在家中出现,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也首先要在家里落实。这里暗含的一个在先的、不必言明的前提是,现代家庭里的“个体”首先成为了一个问题,正因为假的“亲亲”占据了太多的空间而真正的“亲亲”则迟迟无法出现。
如何确立起个体?如何有真的亲亲?这恰恰是有别于“爱欲现象学”的“温暖现象学”所要解答的两个问题。温暖现象学在方法上与进步的保守主义是相契合的:对于家庭中传统的黏连和现代人的冷漠都做出了批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个体与亲亲这样的双重本体。如果没有体会对于假的“亲亲”与假的“个体”的识别与批评,就很难理解《论家》这本书要建立双重本体的苦心。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花了一整章的篇幅讨论列维纳斯的爱欲-生育现象学,而不是有关面容的章节。一般说来,列维纳斯谈论面容的部分或许更适合来讨论个体。然而,正是因为爱欲-生育现象学的两可性与“个体与亲亲”的两可性产生了共鸣,这共鸣恰恰是兼顾了进步与保守的两个向度。
温暖现象学之所以有别于爱欲现象学,在于它使得这种两可性更进一步。爱欲现象学止步于拒绝同一的暴力,而温暖现象学还要拒绝他者的疏离,这一点在伦理生活中也是同等重要的。在当代精神分析的研究中,共情、信任、亲密感、稳定性与温暖对于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边缘性和精神病性的病人在临床上会体现出这方面的偏差。客体关系学派提出了“温暖-伦理学”(warm-ethics),指的是有些病人抱怨自己遭受着类似压抑、恐惧、强迫、焦虑、抑郁等痛苦,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和“温暖”有关的亲密关系中出现了紊乱。有些病人是因为共情能力的抑制,或者亲密感和稳定性不足,才会导致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出现困难,进而表现出临床症状。(28)参见J·布莱克曼著,毛文娟、王韶宇译:《心灵的面具:101种心理防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那么,同一(总体)的暴力是典型暴力,他者(无限)的疏离是不是该被理解为一种冷暴力呢?我们可以从身体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亲亲,是一个典型儒家概念。之所以列维纳斯与儒家可以有所交汇,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于对身体的珍爱与重视,但仔细考察其实又有根本差异。根据孙向晨的考证与阐发:“‘亲’乃是由‘相视’而来一种强烈感受性;这种感受性完全是非认知性、非言语性的,比之‘认知’关系、‘交谈’关系更基础,在‘亲亲’之爱中有一种超越于言说的深切‘表达’。罗汝芳甚至以婴儿初生时第一声‘哑啼’来刻画‘亲亲’之源初的‘依依恋恋’,并把这种‘亲亲’之爱理解为‘赤子之心’……‘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29)孙向晨:《亲亲:在同一与他者之间》,中山大学哲学系“列维纳斯的中文历险”学术研讨会论文,2021年4月,参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亲亲”之所以不同于“爱欲”,在于这种关系基础的身体不一样。“亲亲”要义在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无论是经典儒学所强调的“父子”还是罗汝芳这种特殊诠释中的“母子”,亲亲关系首先由孩子和父母中的一位构成。
然而,列维纳斯描述的却是另一幅“个体与亲亲”的图景,自我与他人的最根本差异(也是最真实的关系)首先出现在不同性别之中,具体地说,出现在阳刚的主体与阴柔的爱人之间。亲亲之爱首先是慈爱与孝爱,爱欲现象学讲的则是男女之间的爱欲。温暖现象学中的他者原型是父母,爱欲现象学中他者原型是爱人。那么,意在整合亲亲与个体、传统与现代、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温暖现象学在身体关系和客体关系的层面上首先就有完全不同于列维纳斯的前提,也就是默认父母与孩子的距离比爱欲双方之间的距离更近。(30)更多有关中国哲学与身体的讨论参见杨儒宾、张再林编:《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考虑到列维纳斯也并没有设定主体与爱人的距离很远,只是这个很近的距离原则上不可以被跨越(然而在摆荡于需要与欲望之中的时候,偶尔也会跨越这个距离),我们有理由相信温暖现象学一定要逾越这个间隔。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虽然儒家讲求“礼主别异”、“熟不废礼”,也很强调差异与独特,然而礼本身其实是一个总体性的结构,作为这一奠基的亲亲更是一种同一的爱,而不是有明确间隔的爱。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全篇唯一能公开肆无忌惮表示亲昵的对象,就是他的母亲王夫人,这种亲亲之爱是被礼教所默许甚至鼓励的。亲亲之中我们也可以谈论现代权利所塑造的个体,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只有现代权力所塑造的个体之间才有真的亲亲。亲亲中的个体是紧贴在一起的,不然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同情共感”。与亲亲相关联的“忠恕之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表达了这种可以设身处地在别人位置上感受的可能,这一点被温暖现象学阐发为人类生存之间存在的“亲切性”(31)孙向晨:《亲亲:在同一与他者之间》,中山大学哲学系“列维纳斯的中文历险”学术研讨会论文,2021年4月,参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也是客体关系学派中温暖伦理学所讨论的共情、信任、亲密感、稳定性与温暖。
列维纳斯也讨论过这种同理心,不过同理心是属于友爱的美德,在未刊稿中列维纳斯写道:“在友爱之中,依恋才是首要的……我与我的朋友,我们通过和对方的关联相互定义。他是灵魂伴侣(知己,l’me sœur),是我的‘另一个我’(至交,alter ego)。Oreste与Pylade就是一对关联项。友爱的关联就像小弹珠与它所停在的凹槽的关系。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的神话,两个存在(l’être double),与其说是爱,毋宁说关涉友爱。友爱之中一切动力都退席:朋友们相互占有,毫无忧虑,不存在什么举动使得友爱本身能够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只要去感受与我们的脉搏相关联的那一实存的搏动,就在我们身边,并充实着我们的脉搏。于是,友爱的他异性失却了它的他异性。”(32)Emmanuel Levinas, Eros, Littérature et Philosophie : Essais romanesques et poétiques, not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thème d’éros (=uvres 3), par Jean-Luc Nancy et Danielle Cohen-Levinas (éd.), Paris, Grasset - IMEC, 2013: 173-174.如果列维纳斯的哲学里有某种温暖的可能,大约只能出现在友爱之中。要是没有这种紧贴对方的同情共感,何以能感受温暖?但温暖的“代价”是失去彻底的他异性,自我的面目变得模糊而匿名,在友爱中耽溺于一种需求的满足,而失去真正追求独特的与他人的关系的机会:“处在他的位置,藉由我自己的情感(sentiment)去重新体会我的朋友的情感,为他的欢欣而开心,为他的痛苦而哀恸。这样一来,他的他异性就一直在递减。”(33)Emmanuel Levinas, Eros, Littérature et Philosophie : Essais romanesques et poétiques, not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thème d’éros (=uvres 3), par Jean-Luc Nancy et Danielle Cohen-Levinas (éd.), Paris, Grasset - IMEC, 2013: 192.这种友爱关系是圆融和气的,在爱欲的两可性中它多数会在一开始时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列维纳斯会用蒙田《论友爱》里的修辞“柔和的炽热”(34)Emmanuel Le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p. 286.来刻画爱人的临显。
与友爱的沉醉相比,爱欲现象学则要求了一种斗争,这点在未刊稿中反复出现了数次:“爱往往被呈现为两个存在者的融合,其实却以某种方式是……一种斗争——‘维纳斯的斗争’。一个存在找寻着另一个存在,但是这一找寻的所有尖锐都由那被找寻的存在者的陌异性组成……抚爱之不可把握,是当我们以一种要去把握的姿态去接近他人之时,便不可把握。它在把握与松开这一层面之外。他是陌生人,就在陌生人的形式之中。抚爱所探求的并不是对他人的占有或者认识,也不是与他人的混同。所有这些显示都牵连同一性。他的陌异性之中的陌生人,从定义上就是不可通达的。而这种不可通达的可通达性,这种与陌生人冲撞和回弹的方式就是抚爱的本源性本身。”(35)Emmanuel Levinas, Eros, Littérature et Philosophie : Essais romanesques et poétiques, not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thème d’éros (=uvres 3), par Jean-Luc Nancy et Danielle Cohen-Levinas (éd.), Paris, Grasset - IMEC, 2013: 41, 42-43, 48.爱的本质是斗争,这种斗争意味着主体与爱人之间的激烈张力,要求爱欲关系的极度亲近之中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距离。“他异性”与“陌异性”这两个词在列维纳斯未刊稿中有一些使用上的混同,但指向很明确,爱人是无法被对象化的、无法认识、不可通达,只能永远不断去寻找。
就像《总体与无限》结语中所说:“多元性的统一是和平,而不是构成多元性之成分的融贯一致。和平因此不等同于斗争的终结,斗争的结束是由于没了斗争者,是由于胜败已定,就是说,是由于一切都归于死寂,或未来成了普遍王国。”(36)列维纳斯著,朱刚译:《总体与无限》,第299页。显然,爱欲-生育现象学所开启的无数断裂的无限时间要保证的是真理与和平,这一过程伴随的是个体与大全总体的永恒斗争,一次又一次打碎有限时间的形式。收敛、阴柔的家与阳刚的、英雄式的国家恰好相对,人人皆兄弟的浪漫与国家的匿名普遍性相对,家的爱欲-生育所开启的有中断的无限时间与国家的无中断的有限时间相对,在这种爱的斗争中和平才能诞生。
显然,儒家温柔敦厚的总体气质拒绝这样极端的描述。在民族国家还未在世界上出现之时,儒家所理解的家与国家的关系毋宁是隐喻式的。齐家才能治国,家本身就是公共空间,“亲亲”确立起来的“家”可以把世界“拉近”身边。(37)③ 参见孙向晨:《亲亲:在同一与他者之间》,中山大学哲学系“列维纳斯的中文历险”学术研讨会论文,2021年4月,参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儒家的“亲亲”以其高浓度的同理心与亲切感使得这种家的温暖无限弥漫开来,以至于有“天下一家”的理想。这种天然的温暖犹如母亲的怀抱,对任何人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精神分析:快乐与过度》对于列维纳斯的一种批评:“列维纳斯认为,所有相异性的经验都以大他者整体的矛盾性在场为前景,而大他者最终回到圣经中的上帝以及上帝与其子民联盟的理论。然而弗洛伊德认为,大他者就是旁边的这个人。他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但是他对于我们的存在与思想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特征连接着一些细节,通过这些细节,大他者造就了我们的快乐和不快。”(38)莫妮克·达维德-梅纳尔著,姜余、严和来译:《精神分析:快乐与过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8页。“亲亲”就是要把他者拉回到身边的这个具体的“旁人”——这个人的父母——而不是抽象地、隐喻式地谈论的“主体的爱人”这种宗教化的符号。温暖现象学要求更多的具体化与个别化,在某一个核心家庭中,在这个核心家庭所处的大家庭中,怎么去培养健康的个体,怎样体会家的温暖,又如何推己及人,兼济天下。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某种总体性的话语之中。就像孙向晨文章中承认的那样:“列维纳斯说,西方哲学对‘总体’的乡愁无处不在。确切地说,人对‘家’的思念无处不在。”(39)③ 参见孙向晨:《亲亲:在同一与他者之间》,中山大学哲学系“列维纳斯的中文历险”学术研讨会论文,2021年4月,参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温暖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既超逾(au-delà)列维纳斯,又没有超逾(en deçà)列维纳斯。就像德里达所说,我们阅读列维纳斯之时犹如海浪一次又一次地拍打着礁石,温暖现象学就是这样旋回的阅读所激荡出的回声:它不仅仅摇曳于爱欲与友爱之间,也震荡于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之间、正义与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