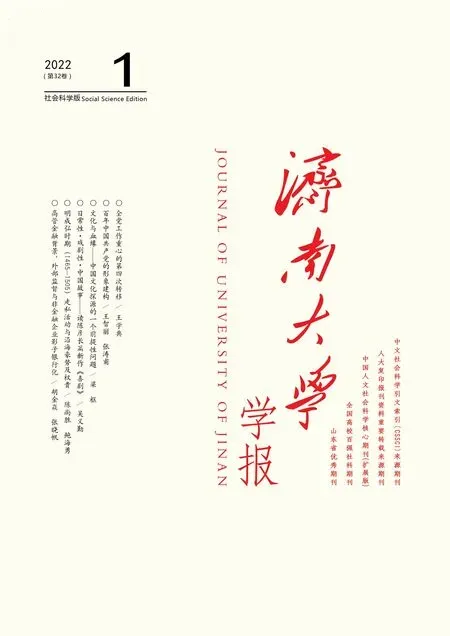明嘉靖《全唐诗选》的诗学理念
孙欣欣
(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在唐诗的传承体系中,唐诗选本居功甚伟,它是唐人别集之外唐诗传播的又一主要形式,也是唐诗经典化的重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编选的唐诗选本不下700种,其中存世选本超过470种。这些选本为我们开展唐诗传播、唐诗经典化以及历代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唐诗的编选至明代进入繁荣阶段,存世选本达137种,数量远超唐、宋、金、元时期唐诗选本的总和,这些选本根植于明代土壤,受明代特有文化与诗学背景的滋育而发展起来,并逐渐经形成较为成熟完整的体系。在一百余部存世唐诗选本中,除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等著名选本外,每一阶段有代表性、有价值的选本都亟待我们去挖掘整理、深入研究,明嘉靖年间李默、邹守愚所编《全唐诗选》即为其中的一部。
一、养性情之中和的编选宗旨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李默、邹守愚《全唐诗选》,嘉靖二十六年曾才汉刻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双鱼尾,版心刻有卷数及页数。李默(1499-1558)字时言,号古冲,瓯宁(今属福建)人,博学多才,著述颇丰,有《朱子年谱》《建宁人物传》《群玉楼稿》等传世。邹守愚(?-1556)字君哲,一字一山,莆田(今属福建)人,著有《俟知堂集》。
该书共十八卷,据邹守愚《全唐诗选序》所言,入选唐诗共计1800首,而据笔者统计,实际选诗为1957首。其中卷一至卷二为五言绝句,共选诗277首(后附六言诗5首);卷三至卷四为五言律诗,共选诗295首;卷五为五言排律,共选诗91首;卷六至卷九为五言古诗,共选诗382首;卷十至卷十二为七言绝句,共选诗430首;卷十三至卷十四为七言律诗,共选诗189首(后附七言排律2首);卷十五至卷十八为七言古诗,共选诗286首。据邹守愚自序可知,此书编选缘于嘉靖十六年二人的一次聚会,由李默提出并授意于邹,书成后李默手校并为之题名曰《全唐诗选》。嘉靖二十五年邹守愚又删改其中的十分之一,嘉靖二十六年付梓刊刻。
关于此书之编选宗旨,邹氏自序中并未明确说明,但从字里行间亦可捕捉其大意:
夫论撰之指,知者屡作,如沧浪诸人所云,至矣,然不能加也。余搜其情,匠心藻咏,罕袭故常;聆其音,比物丑类,谐于宫商;要其道,群伦止义,不淫不伤,其大都由汉魏而上,泽于
《风》《雅》,炳炳如也。嗟乎!虽诸作者不相为同,然翰勋诗史所在,宁不有神明护持者邪?余性酷嗜心韵,非适俗,时取哦咏如其身践,更其劳苦欢忻㥪㥪其胸腹而为之者,琅然如金石,足可怡悦,不更为也!即有为者,毋亦其糟粕渣滓矣乎?①《全唐诗选》卷首,明嘉靖二十六年曾才汉刻本。
邹氏指出,论诗已有严沧浪等人撰述于前,且精深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全书他并未做任何评论,只是依高棅《唐诗品汇》附入严羽等诸家评语。然而对入选诗作他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那就是上承汉魏、泽于《风》《雅》,符合儒家诗教。对这些作品,他认为只需用心体会,足可怡悦精神,无需他为。
显然,邹氏对选诗意图阐发得并不够详细具体,好在书中所存米荣《刻全唐诗选序》及曾才汉《全唐诗选后叙》对此书编选之旨又做了进一步补充。米荣曰:
夫诗之作,其来尚矣,必发于中和,然后能感人心,以裨世教,非特取其音律体制之工也。昔者圣人删述六经,其去取也严矣,匹夫匹妇、闾巷歌谣之言而亦笔诸经者,以其或渐王化、或罹事变,触于中而形于咨嗟咏叹者,皆真性自然无所为而为也。故观此可以识性情,可以验风俗,可以考政治。是诗也所以寓教也,可少乎哉?……然至灵者,性也,而见有明暗,言有得失者,心之存与不存焉耳,方其心无所放而形于吟咏,有以合乎中和而进于古人者,未尝不散见
于诸家,吾录其纯正而舍其偏驳,采其实用而略其虚夸,则诸家之作皆可以班李杜而肩古人也,皆可以养吾之性情而不戾于中和也,抡选之功不有待于人乎!②米荣:《刻全唐诗选序》,明嘉靖二十六年曾才汉刻本。
他同样指出诗歌的政教之用,认为诗歌具有识性情、验风俗、考政治的功用。不仅如此,序中亦见程朱理学之影响,朱熹曾于《答张敬夫》中云:“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③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43册,第713页。主张通过已发之心来体会未发之性。《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页。是讲感情抒发应节持有度,不能过分,才可达到中和。而米荣亦将“性”作为至灵之本体,“心”为已发。在他看来,见之明暗、言之得失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存心”,只有“存心”才可体会至灵之性,方可达到中和。他认为此选正是选录性情纯正、具有实用教化功用的诗歌,而这些诗歌“皆可以养吾之性情而不戾于中和也”。同样,曾才汉叙中亦言:“夫温柔敦厚,诗教本原,学者必求雍睦和平以理性情之正,而诗其可少哉?自唐以诗取士,故说诗者必举唐为称首,无亦以其体裁备而寓意深也。”认为唐诗被论者称首的原因不仅在于各体兼备,还在其寓意深远,所寓之意当然是儒家诗教温柔敦厚之旨。序中他还指出,此选并不独尊盛唐、专崇李杜,而是四唐皆选,正因为这些入选诗歌可理性情之正,可扫除人之贪、倖、隘、诞之弊,那么“凡贪、倖、隘、诞之弊悉已扫除,而性情中和、德业纯正矣。然则公寓微意诗教指南不于兹可见耶?学者究心是编,则唐诗诸集可以不必遍观,而涵泳性情、比兴时物,优柔平中、和畅顺适,所谓直、温、宽、栗之九德可以咸事矣。是编为教,其益容有方耶!”⑤曾才汉:《全唐诗选后叙》,明嘉靖二十六年曾才汉刻本。
综观上述三家序言可见,《全唐诗选》是一部以儒家传统诗教为宗旨,强调诗歌教化功用的唐诗选本。此本倡导温柔敦厚、雍睦和平之风,重视诗歌对人之性情的归正与涵养作用。如此选诗或与两位编者的仕宦身份有关,李默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选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历兵部员外、吏部郎中、浙江布政使、吏部侍郎,进本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加太子少保。邹守愚为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任户部员外郎、广州府按察副使、湖广右布政使参政、户部侍郎等职。作为馆阁之士、朝廷重臣,二人选诗自不可避免带有政教色彩,如若进一步追溯其思想来源,则又与永乐朝以来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文学思潮一脉相承,这一思潮以儒家政教观为核心,追求温厚平和之风,力求表现性情之正,而其思想根源则是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家既主张传统诗学命题“吟咏情性”,同时又强调诗本源于性情之正,是指诗歌所表达的情感符合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诗歌以表现“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①朱熹:《诗经集传·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册,第748页。为正。朱熹曾将《国风》中的二十三首情诗斥为淫奔之诗,就在于这些诗所表现的情感不符合儒家性理善的要求,并且从“正人性情”的角度肯定“《诗》教”的基本价值。至明代,《四书大全·大学或问》亦讲正心,即去除邪思妄念、利害情欲,使之归于正。李、邹二人不仅身为朝廷重臣,且同为福建人,而福建向为理学重镇,自宋代始,文人即崇尚理学,重视诗文的教化作用。那么,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李、邹二人来说,在浓厚的理学氛围熏染下,选诗受其影响亦在情理之中了。我们知道,明初台阁文学思想的核心政教观在景泰之后虽逐渐淡化,但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此一种之文学观,乃是我国古代正统的文学观念。不论文学思潮如何之演变,它依然要存在下去,只是表现形态与程度不同而已。有时处于主流地位,有时为其他文学主潮所遮蔽,但一有条件,它就回归。”②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6页。《全唐诗选》的编撰或可视为此种文学观在选诗领域的回归吧。
二、得风雅性情之正的选诗特色
《全唐诗选》编选之前已有不少唐诗选本问世,正如曾才汉所言:“简册浩繁、名类叠出,有《唐音》、有《正声》、有《品汇》、有《会编》,学者殆难遍览,乃择盈帙,用示式矜。”③曾才汉:《全唐诗选后叙》,明嘉靖二十六年曾才汉刻本。实际上,《全唐诗选》在编选时的确参考了以上各家选本,如前引邹守愚序中所言:“要其道,群伦止义,不淫不伤,其大都由汉魏而上,泽于《风》《雅》,炳炳如也。……余性酷嗜心韵,非适俗,时取哦咏如其身践,更其劳苦欢忻㥪㥪其胸腹而为之者,琅然如金石,足可怡悦,不更为也!”这与天顺年间康麟所辑《雅音会编》自序中的观点乃至表述都颇为相似,康麟曰:“诸家之音舂容浑厚,清新俊逸,皆发于性情之正,《三百篇》之遗意蔼然尚存,非后世争妍斗靡者之可比也。尝于退食之余或诵或咏,如作咸英,如奏韶頀,不觉夫性情之舒且悦也。吁!诗之为用大矣。”④康麟:《雅音会编》,明万历二十二年沈藩重刻本。二人皆阐发了所选唐诗上承《三百篇》遗意,读之可舒悦性情的作用,可见李、邹编选唐诗在某种程度上或是受了康麟《雅音会编》的启发。当然,《雅音会编》是以平声三十韵为纲,依《唐音》《三体唐诗》《唐诗鼓吹》《唐诗正声》《光岳英华》等选本以及李、杜、韩三家集汇编而成。而《全唐诗选》的选诗来源则是高棅《唐诗正声》《唐诗品汇》以及杨士弘《唐音》。
具体来看,《全唐诗选》是以《唐诗正声》为主要参考底本,前者选诗近两千首,后者仅九百余首,在体量上超出其一倍之多,超出的部分皆据《唐音》《唐诗品汇》增补。例如:李、杜之诗《唐音》并未入选,《全唐诗选》则在《唐诗正声》基础上补入《唐诗品汇》之诗。如杜甫五绝、李白七律,《唐诗正声》各入选3首,《全唐诗选》入选诗歌与之完全相同,顺序也完全一致;又如杜甫五古,《唐诗正声》入选38首,《全唐诗选》亦悉数选入,顺序亦大致相同,只是比《唐诗正声》多选了3首,均出自《唐诗品汇》;《唐诗正声》未选杜甫七绝,《全唐诗选》入选7首,亦出自《唐诗品汇》。其他各体莫不如此。中晚唐诗人在《唐诗正声》中入选比例较小,《全唐诗选》则依据《唐音》补入。如中唐诗人张籍,《唐诗正声》入选其诗14首,排名较为靠后,而《全唐诗选》选其诗却多达61首,在所有入选诗人中位列第七,除《唐诗正声》所选外皆来自《唐音》,特别是其五、七言律诗,《唐诗正声》均未选,而《全唐诗选》则据《唐音》补入,顺序亦完全相同。又如晚唐诗人李商隐,《唐诗正声》仅入选其5首诗,而《全唐诗选》却入选其诗51首,位列第九,除《唐诗正声》所选外亦来自《唐音》。此外,《全唐诗选》又依《唐音》增入了六言诗和七言排律。
那么,李默、邹守愚选唐诗为何要以《唐诗正声》为主要参考底本?这一点还得从《唐诗正声》的编选宗旨中寻找答案。在《唐诗正声》之前,高棅已编选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唐诗品汇》,然因其广罗唐诗、力求全备,造成了选诗的“博而寡要,杂而不纯”,高棅本人的选诗标准也不得不堙没于浩繁的卷帙之中。因此,他剪除杂芜,取其精要纯正者又编成一部《唐诗正声》,在《唐诗正声凡例》前他指出此选“题曰《正声》者,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矣”①高棅:《唐诗正声凡例》,明万历七年重刻本。。可见,“得性情之正”正是此书编选的重要宗旨之一。所谓“得性情之正”,高棅进一步作出解释:“诗者,声之成文也,情性之流出也。情感于物,发言为声,故感有邪正,言有是非。唯君子养其浩然,完其真宰,平居抱道,与时飞沉,遇物悲喜,触处成真,咨嗟咏叹,一出于自然之音,可以披律吕而歌者,得诗之正也。其发于矜持忿詈谤讪侵凌,以肆一时之欲者,则叫噪怒张,情与声皆非正也,失诗之旨,得诗之祸也。观者先须遗妄返真,秉心明目,然后辨是非,察邪正,以定其取舍,而有迷谬者寡矣。”②高棅:《唐诗正声凡例》,明万历七年重刻本。看来高棅此选同样是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追求诗歌的性情之正,强调诗歌涵养性情的作用,这与李、邹编选唐诗的宗旨不谋而合。进一步追寻开来,我们发现,高棅与李默、邹守愚一样同为福建人,如前所述,福建向为理学重镇,宋代著名理学大家朱熹曾在此生活、著述、教学长达五十余年,他将训诂与义理相结合,形成朱子理学。至明代,福建理学传统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愈加浓烈。高棅、李默、邹守愚三人或许正是受到这相同地域的学术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才呈现出思想的趋同,而这正是李、邹二人将高棅《唐诗正声》作为主要参考底本的深层原因。
当然,《全唐诗选》在对前人选本的择取过程中也融入了选家自己的诗学旨趣,体现其独有的选诗特色。首先,重新确立李白五古的正宗地位。李白五古在高棅《唐诗品汇》中位列“正宗”,共入选196首;杜甫五古则位列“大家”,仅入选84首。而在其《唐诗正声》中,李、杜五古的地位却发生了置换,杜甫五古入选38首,超过了李白的35首。原因在于,杜甫的五言古诗,无论是《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还是“三吏”、“三别”以及入蜀纪行诗等,皆体现其融合晋、宋以来五言诗的韵式、句式之变而带来的对五言古诗的新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诗人深厚的家国情怀,而这一思想内容最能体现《唐诗正声》“得性情之正”的选诗宗旨。相对而言,李白五古在此方面无法与之相较。而《全唐诗选》虽是以《唐诗正声》为主要底本进行诗歌删选,但是对李、杜五古的态度却与高棅不尽相同,李白五古入选数量(51首)再一次超越杜甫(41首),重回正宗之位。与杜甫相比,李白是一位主观色彩浓烈、个性十足的诗人,因而他的五言古诗大都重在主观抒怀、谈玄理,无论是咏古人古事还是咏物,皆以比兴寄托为主,将情寓于景与物,这些景物乃为诗人主观情感之外化,是一种比托之物,是写意式的主观印象或想象。这一风格在其《古风五十九首》等直抒胸臆的咏怀诗中表现最为突出。而从《全唐诗选》所选李白五古来看,《古风》《感兴》《寓言》《拟古》等“古风体”咏怀古诗入选数量多达16首,这类诗继承发扬了《诗》《骚》和汉、魏、晋古诗的“兴寄”传统,无论是写历史人物还是写神仙故事,皆以比兴、象征、寄托等手法寄寓深刻的精神内涵,注入诗人自己的灵魂,使诗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深厚的文化意蕴。以《古风五十九首》为例,李、邹二人在《唐诗正声》基础上又增选了6首,分别是其十一“黄河走东溟”、其十五“燕昭延郭隗”、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国”、其三十二“蓐收肃金气”、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其三十八“孤兰生幽园”。这些诗或表现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楚;或哀叹时光流逝、功业无成的无奈;或流露对社会现实以及统治者的不满。然而此等情绪的表达并非直接铺陈,而是通过比兴等手法展现出来,如其十一“黄河走东溟”,以黄河滚滚东去不停留,太阳东升西落不停歇起兴,引发诗人对年光短促的悲叹,他感叹流光飘忽,岁月匆匆;感叹自己春容已去,功业未成。又如其三十八“孤兰生幽园”,通篇以孤兰作为比兴之物,虽有逸才,却被众草所没,遭小人谗言,恐时光易逝,才未见用而身已衰老,故以“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为喻,渴望德高望重者提携。这些感叹生命、感物兴悲的作品继承了《诗经》的比兴艺术传统,正如《御选唐宋诗醇》所言:“白古风凡五十九首……其间指事深切,言情笃挚,缠绵往复,每多言外之旨……岂非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乎?”①《御选唐宋诗醇》卷一,清乾隆二十五年重刊本。当然,在内容上,《古风五十九首》中的一部分作品也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讽时事,现实感很强。如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天宝十载杨国忠挑起西南边境的战争,驱使人民远征云南,此诗即是描写此事。整首诗运用对比、问答等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巧妙融合在一起,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对战士们可悲的命运表示深切同情,集中体现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御选唐宋诗醇》评此诗曰:“‘群鸟夜鸣’写出骚然之状,‘白日’四句,形容黩武之非。至于征夫之凄惨,军势之怯弱,色色显豁,字字沉痛。结归德化,自是至论。此等诗殊有关系,体近《风》《雅》。杜甫《兵车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敌,不可轩轾。”②《御选唐宋诗醇》卷一,清乾隆二十五年重刊本。总体而言,李白五古上追风雅,承汉、魏古诗之传统,得五古体裁之正,可谓集汉魏六朝古诗之大成。由《全唐诗选》对李白五古的重视可见,在诗学观上李、邹二人还是受到复古派“古体尊汉魏”思想的影响,当然,在选诗上,这确又与其“群伦止义,不淫不伤,由汉魏而上,泽于《风》《雅》”的宗旨相符合。
其次,对中晚唐诗人给予高度关注,集中体现在对李商隐以及张籍、王建诗歌的选取上。在《全唐诗选》入选诗人中,排在前六位的是:杜甫、李白、王维、刘长卿、岑参、韦应物,这与《唐诗正声》完全相同。但是接下来排在第七位的是张籍,选诗61首,第九位是李商隐,选诗51首,第十三位是王建,选诗44首,三人在《唐诗正声》中仅入选14首、5首和11首,排名较为靠后。其中李商隐诗虽完全出自《唐音》,但是《唐音》大都将其列入“遗响”,对其态度与《唐诗正声》并无二致。而《全唐诗选》却将《唐音》列入“遗响”的李商隐诗全部选取,足见其对义山诗的偏爱。在51首入选作品中数量最多者为咏史诗,如《汉宫词》《宫词》《龙池》《咸阳》《吴宫》《贾生》《四皓庙》《过楚宫》《咏史》《茂陵》《马嵬》《筹笔驿》《隋宫》《九成宫》《槿花》《楚吟》等。咏史诗是李商隐政治诗的典范之作,大都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同时又借古讽今,托古述怀,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慨,在表现手法上则延续了《诗经》所开创的比兴艺术手法,具有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如这首《筹笔驿》:“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诗人通过对筹笔驿这一古战场的游览凭吊,称颂诸葛亮卓越非凡的成就,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颇具杜甫七律沉郁顿挫之风。诗人并不单纯议论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一生的丰功伟绩,而是将自己的深切感受寄于这位古人身上,进一步引申发挥,使寓意更深一层。管、乐与关、张的典故运用,不仅超越了时空,而且不问古今、虚实并用,进一步升华了主题,寄意深远,耐人寻味。李、邹二人对这些咏史诗情有独钟,一方面在于他们都是政治家,以咏史为题材的政治诗与他们任官为政的政治心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李商隐诗高超的艺术成就也是其被大量选入的重要原因,其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风格独特,造诣颇深,除咏史主题外,爱情主题如《夜雨寄北》《昨夜》,表达对亡妻的深切思念;感怀主题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无论咏史诗、爱情诗、感怀诗抑或是无题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如这首咏史主题的《龙池》诗:“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此诗讽刺辛辣,揭露大胆,然而用语却无一字针砭,深藏不露,含蓄委婉,揭开了在礼义廉耻封建帷幕重重遮掩下的极为丑恶的乱伦关系,表达了诗人对封建帝王骄奢淫逸生活的不满,对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嘲讽。诗人写寿王,只着一“醒”字,极为警策,其中隐含着他的痛苦、郁闷以及强烈情感无处宣泄的悲愤,而这一描写恰恰是对玄宗的强烈谴责。整首诗未着一字嘲讽之语却让人深感嘲讽之意,是一篇语极含蓄而讽意弥深的佳作。正如清代吴乔《围炉诗话》所评:“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义山刺杨妃事之‘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是也……其词微而意显,得风人之体。”①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76页。手法婉曲而意旨暗显,不仅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特点,更是李商隐近体诗突出的艺术魅力。《全唐诗选》入选李商隐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数量最多,其中七绝29首、七律11首,占其所有入选诗歌的五分之四,足见李、邹二人对这一艺术风格的极度欣赏。
中唐著名诗人张籍在《唐诗正声》中仅有14首诗入选,排名比较靠后,而《全唐诗选》却选其诗61首,位列第七,甚至超过了储光羲、王昌龄、孟浩然、高适等盛唐名家。在这六十余首诗中,七古一体入选最多,达20首,除《唐诗正声》中选入的《送远曲》《征妇怨》《寄衣曲》《节妇吟》《各东西》《白头吟》外,又增加《楚宫词》《羁旅行》《贾客乐》《车遥遥》《江南曲》《吴宫怨》《北邙行》《乌啼引》《白苧词》《古钗叹》《促促词》《燕客词》《猛虎行》《牧童词》等16首,这些诗皆为乐府诗,是张籍诗歌成就最突出的方面。同样,王建在《全唐诗选》中选诗数量亦超过高适、李颀等盛唐名家,其入选的44首作品也是以乐府诗为主,如《望夫石》《寄远曲》《短歌行》《羽林行》《田家行》《温泉宫行》《北邙行》《凉州行》《寒食行》《促刺行》《射虎行》《镜听词》《精卫词》《神树词》等,多达20余首。张、王乐府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揭露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穷兵黩武等罪恶行径,给予遭受剥削、压迫的广大人民以深切同情,题材广泛,主题深刻。在艺术上,张、王乐府善用比兴、白描及对比、衬托等手法,通过对事实和人物语言的描写表现深刻主题,语言通俗凝炼。如张籍的《征妇怨》描写唐代中后期契丹大举入侵,唐军在辽河之战中溃败,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整首诗以妇人的口吻,极言战争之苦,强烈控诉战争的残酷,控诉战乱带给人们的灾难,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王建的《羽林行》不仅谴责羽林军中恶少的嚣张不法,更是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集团,表达出诗人对朝廷的极度失望之情。而《全唐诗选》的编者李、邹二人皆为朝廷重臣,为人耿直,刚正不阿。李默任内秉公持正,选拔贤能,澄清吏治,坚决不与严嵩势力同流合污;邹守愚为官决狱公平、设策赈济、体恤百姓,他本人则在河南的一次地震中赈贫民、掩露胔,因过度劳累而死于任上。他们如此看重张、王建乐府,大概就在于这些诗对身处仕途之中的他们来说最能与之产生心灵的共鸣,体会也最为深刻。从选诗角度看,张、王乐府注重时事,重视诗歌教化作用,存《三百篇》遗意,它们与此书重儒家诗教功能的编选宗旨正相吻合,正如清代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所言:“乐府古词,陈陈相因,易于取厌。张文昌、王仲初创为新制,文今意古,言浅讽深,颇合《三百篇》兴、观、群、怨之旨。”②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9页。
三、《全唐诗选》的价值
自元代杨士弘《唐音》始,高标盛唐已成为一种倾向,明初高棅选唐诗仍然以盛唐为宗,成为“馆阁宗之”的范本。明代中期以来,唐诗的编选大量出现,而此时的诗坛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诗派先后主盟,他们高举“诗必盛唐”大旗,倡导古体尊汉魏,近体崇盛唐,中唐而下一切吐弃,在对唐诗的体认与接受中注重体格声调的辨析,形成了以格调论诗的诗学思潮。在此影响下,各家选本大都以选盛唐诗为宗。如胡缵宗编《唐雅》八卷,选诗重盛唐,尤以李白、杜甫、王维诗最多。蔡云程《唐律类钞》二卷,专从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中择取五、七言律诗五百首,分类而编。选诗以初、盛为多,中唐次之,晚唐间取之。蔡氏在自序中称:“自《风》《雅》《骚》《选》之迭变,至唐人始以律名家,于体为近,于词为精,于法度森整之中而格律浑雄,意兴超逸,斯亦善之善乎?”①蔡云程:《唐律类钞》,明嘉靖刻本。其以盛唐为宗,讲求法度与格律的宗旨与格调论者同气相求。嘉靖三十一年张逊业所刻《唐十二家诗》,选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十二家诗集各二卷,分体编排,着眼于体格声调的源流变化,将十二家确立为可取法的对象。该选所定十二家,在当时颇具影响,也一直为后来的格调论者所遵循。而此时在以格调论为主导的唐诗选本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李攀龙的《唐诗选》。该书在选诗上明显重初盛而轻中晚,在诗体辨析上更为严苛,在审美风格上偏执于冠冕整齐、声响宏亮一格,执着于他心目中的“正”体,对“格调”要求甚为苛刻。
但是,前、后七子以盛唐为宗的格调论诗学思想却有其先天的局限性,简单地以时代论高下,厚此而薄彼,是无法得见唐诗之整体风貌与成就的。于是,在选诗领域也有人别开新面、另奏新声,显示出与之不同的诗学观念。如樊鹏《初唐诗》三卷,只选择贞观至开元间的律诗,供时人师法。他在嘉靖十二年(1533)春的《编初唐诗叙》中云:“诚以律诗当于初唐求之,古诗当于汉、魏求之,此则编诗意也。”②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19页。其中虽见复古派格调论之影响,但又对“诗必盛唐”有所突破,体现出对初唐律诗的偏好。蒋孝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编刻《中唐十二家诗集》七十八卷,选录独孤及、刘长卿、卢纶、钱起、孙逖、崔峒、刘禹锡、张籍、王建等十二家诗。蒋氏在自序中认为中唐诗“虽不能窥望六义,而格深律正,所以寄幽人贞士之怀,以发其忧沉郁抑之思者,盖已妙具诸品矣”。对中唐诗具有寄托、抒发真情的作品是予以肯定的。薛应旂在为其作序时称中唐诗:“沉涵超悟,舒愫发情,不靡不弱,宛然真切,而三百年污隆升降之会,一讽咏而可得矣,虽其人品造诣不能皆同,而言有可取,固不当以人而废。”③蒋孝:《中唐十二家诗集》,明嘉靖二十九年蒋孝刻本。对中唐诗不靡不弱、宛然真切之作亦表认可。同样,李默、邹守愚所编《全唐诗选》亦通过选诗冲破了复古派诗必盛唐的藩篱,而且它不是以专选初唐或中晚唐诗的做法来体现这一意图,而是通过对四唐诗歌的总体把握,衡量优劣,以选诗比例呈现出来。且看它与《唐诗正声》的选诗情况对比,《全唐诗选》初唐诗240首,占12.5%,盛唐诗732首,占38.18%,中唐诗685首,占35.73%,中唐诗685首,占35.73%,晚唐诗240首,占12.5%;《唐诗正声》初唐诗92首,占9.9%,盛唐诗474首,占51%,中唐诗304首,占32.7%,晚唐诗58首,占6.2%。从选诗比例来看,《唐诗正声》是典型的以盛唐为宗,其入选数量超过了半数以上,而《全唐诗选》虽然也是以盛唐为多,但与《唐诗正声》相比,盛唐诗的选取比例却有了明显下降,且与中唐诗的入选数量极为接近。初唐、中唐、晚唐诗的入选比例在《全唐诗选》中都有所提升,初盛唐与中晚唐诗的入选比例相差无几,这种选诗比例在明中叶四唐皆选的唐诗选本中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对晚唐诗,《全唐诗选》的选取比例较《唐诗正声》翻了一倍之多,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种难得之异响,即便是一些意欲突破盛唐藩篱的唐诗选本,也仅仅是停留在对中唐诗的宽容对待上,对晚唐诗仍持否定态度,如黄贯曾编选《唐诗二十六家》五十卷,在自序中黄氏认为:“自武德迄于大历,英彦蔚兴,含毫振藻,各臻玄极,虽体裁不同,要皆洋洋乎尔雅矣。”因而在其所选二十六家中,包括了皇甫曾、皇甫冉、权德舆、李益、司空曙、严维、顾况、韩翃、武元衡、李嘉祐、耿湋、秦系、郎士元、包何等中唐诗人,而对晚唐诗人的态度却是:“元和以后,沦于卑弱,无足取者。”①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明嘉靖三十三年黄氏浮玉山房刻本。同样,顾应祥辑《唐诗类钞》八卷,顾氏自序中认为:“古今论诗者必曰唐诗,选唐诗者非一家,惟襄城杨伯谦《唐音》最为严格,分别始音、正音、遗响,非合作者弗录。予自入仕以来,每携一帙自随,然中唐以后多有杰然脍炙人口者俱不见录。”于是摘其中为世所称者增入。而对入选晚唐诗,顾氏却解释道:“夫伯谦之意正病诸家所选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乃今复以晚唐入之,欲以便观览云尔,非选也。”②顾应祥:《唐诗类钞》,明嘉靖三十一年自刻本。可见其编入晚唐诗歌并非选的结果,并不表明自己对晚唐诗的认可,只不过为了便于观览而已。而《全唐诗选》对晚唐诗的态度却并非如此,它冲破了时代牢笼,肯定晚唐诗人在某些诗体中的重要成就,如晚唐诗人擅长的七绝一体,《全唐诗选》入选数量为132首,仅次于中唐的183首,而超过了盛唐的102首,这就使许多有艺术价值的晚唐七绝得到认可,如若不分体制、不分诗人,仅以时代论之,则这些具有艺术魅力的佳作将如同在其他同时期以盛唐为宗的唐诗选本中一样被无情地抹杀淘汰掉了。
客观来看,中唐与晚唐诗确有失之于偏的局限,总体成就比不上盛唐诗,但如果因此而完全否定之,亦不符合唐诗发展的实际。明中叶如《全唐诗选》这类中晚唐与初盛唐并重的唐诗选本的出现反映出时人对“诗必盛唐”观念的突破,而这种诗学观念的变化,其实在后七子内部就已开始了,如王世贞兄弟就已开始从诗歌发展渐变的角度重新审视唐诗,打破了“四唐”的绝对界域,对中晚唐诗态度较为宽容。《全唐诗选》则以选诗的方式参与其中,在具体选诗中,中唐诗人张籍和晚唐诗人李商隐入选诗作甚至超过了储光羲、孟浩然、高适、王昌龄、李颀等众多著名盛唐诗人,入选之诗皆为后世所称道的名篇佳制,可以说,这部唐诗选本不仅彰显了选家崇尚儒家诗教、提倡“得性情之正”的编选宗旨,并且各体皆备,四唐皆有所重,具有较高的选诗价值,最为重要的是,它在客观上为中晚唐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