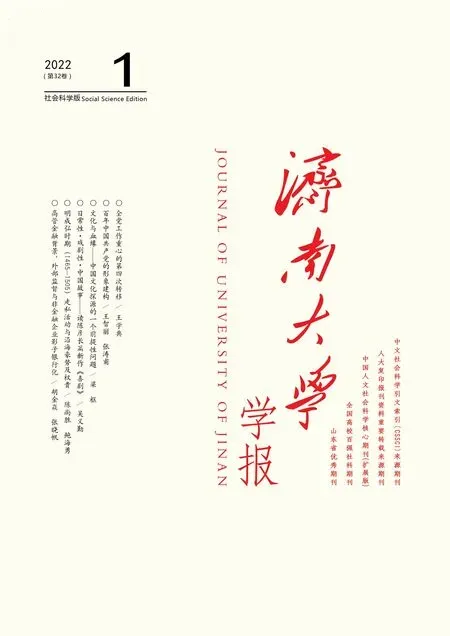日常性·戏剧性·中国故事
——读陈彦长篇新作《喜剧》
吴义勤
(中国作家协会,北京 邮编 00013)
在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场域中,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主角》堪称是“横空出世”之作。他以朴素、传统的手法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描摹生活和人物本身的丰富与浑厚,复活、呈现并验证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魅力,给当代文坛带来了持续的冲击与震动。而由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戏剧三部曲”收官之作《喜剧》则既延续了前两部长篇绵密、坚实的现实主义品格,又以更强的故事性和更尖锐的当下思考引人注目。小说通过喜剧这一介于传统与现代的戏剧形式,关联广阔时代生活和不同人群,塑造了贺少天、贺加贝、潘银莲、南大寿、万大莲、贺火炬等各具特色的典型形象,挖掘他们的心理世界和情感世界,从特殊的情感和心理维度完成了对现代人内在精神结构的解剖以及对当今时代各种荒诞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
一、日常性与戏剧性:陈彦小说的“不奇之奇”
《喜剧》是一部兼具“戏剧性”与“日常性”的小说。一方面,叙事动作性强,人物和故事情节充满传奇性。小说保持了戏曲戏剧对语言和动作描写的重视,注重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人物,揭示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情感状态,尤其是对人物内在心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冲突性有着丰富细致的表现。相貌丑陋得不凡的丑角父子三人,贺加贝带荒诞悖论色彩的命运遭遇,贺少天对喜剧时代即将来临的预言,贺氏父子的绝活儿,贺加贝对万大莲始终不渝的单恋,潘银莲的忍让、包容,乃至万大莲与潘银莲难分彼此的长相容貌等,这些人物和故事都带有程度不同的超越生活常见形态的传奇性。作家将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生活经历进行艺术化简处理,删削那些与人物和情节无关的生活内容,强化冲突和人物、事件之间的因果逻辑,将原初形态的生活经过集中提炼而成为戏剧性的人物、冲突性的事件和情节结构,使戏剧与时代、演员和观众、喜剧与悲剧与闹剧之间呈现出短兵相接的状态,形成一种充满紧张感的张力关系。同时,《喜剧》还多方运用巧合(如万大莲与潘银莲容貌的极端相似)、突转(如当贺氏父子喜剧演得热闹红火时,贺少天被发现已患癌症晚期;贺加贝在高档别墅区买楼时,万大莲恰好因丈夫的犯罪行为而逃离别墅)、误会(如贺火炬因对贺加贝、潘银莲夫妇的怀疑和不满,而发生兄弟失和、叔嫂矛盾之事)等艺术手法,让矛盾冲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迅速形成、发展、激化、推向高潮并迅速得到解决,使小说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和传奇性不断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喜剧》又注重呈现“戏剧性”背后的“日常性”,尽力避免因人物事件的离奇性而造成不真实感。作家将笔墨和笔力集中于平凡人物的现实人生,注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展现人的命运遭际,揭示作为“社会典型”而非“抽象人性”的人物之内心世界,表现生活和生命本身的“内在戏剧性”,书写生活和人的“不奇之奇”。贺少天是闻名遐迩的“大艺术家”,贺加贝、贺火炬兄弟虽然比不上父亲,但也是广有影响的著名丑角演员。作为现实中的人物,他们的相貌、扮丑技艺和绝活儿,无疑具有一定的神秘性、传奇性,但作家没有刻意突出其荒诞怪异,没有夸大这种传奇性、神秘性,而是在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中,通过鲜活的生活画面和平常的人际关系、矛盾冲突,在世情和民情的层面及向度上,自然而然地写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不无烦恼、痛苦和无奈的人生体验。
在《喜剧》中,既有对人物心理的矛盾性的揭示,力图展现人物内心情感的复杂性,这是陈彦小说的现代性表征,其中有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中外现代文学大师的影响;又超脱了个人与社会与时代之间的对立性设置,不同于现代文学创造作为典型的个人以显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和现代性本质。在小说中,个人不仅是她或他自己,而是一个具有相对恒定性和稳定性的整体。这个整体或者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或者是传统文化、思想、道德和美学的艺人形象。在他们身上,陈彦表现了一种民胞物与的传统人道主义悲悯,和对其个体心理情感、生活命运的热切关注,同时,又在他们身上体验并发掘到更多更丰富的东西——人性、情感、欲望等。
二、真实性与荒诞性:穿透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学方式
《喜剧》是一部在现实性、历史感和真实性等方面带有典型陈彦气质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以饱满、厚重、细腻的笔墨呈现了当今中国日常性、社会性的广阔“真实”:通过丑角人物的行迹、命运写戏曲在当下现实中的命运;通过丑角、喜剧,关联广阔的城乡和更广泛的人群,写出当下社会生活的真实一面;通过人物之间的爱情、亲情、家庭、婚姻等,写出当下民众的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的真实。当然,作家并不满足于这种日常性层面真实感的表现,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日常性的层面和境界,他试图通过超越经验性的现实描述,进入另一个世界和境界。这表现在:其一,通过贺少天、潘银莲等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情感结构。这些人物都表现了喜剧/戏剧与中国/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贺少天、潘银莲尤其是前者,在小说中并不占有太多叙事篇幅,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贺少天寄托着作家对喜剧之为喜剧的“本”性思考,小说通过他,侧重于从艺术方面表达戏剧如何契合时代变动中的国人审美趣味。潘银莲虽非戏剧艺人,但她却从艺术的现实基底意义上,构成对喜剧/戏剧的“根”性观照,小说通过她,侧重于从生活方面表达喜剧/戏剧如何贴近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和道德经验。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戏剧如何变革,都要守持艺术(美)之“根”之“本”之神髓或更本真的生活与生命形态。如果说,贺少天与《主角》中的“忠孝仁义”和秦八娃一样,代表的是一种面对时代挑战却又生生不息的艺术美学传统,那么潘银莲则类似《主角》中的忆秦娥,代表着一种遭受现实挑战却绵延持久的伦理道德传统,他们分别在伦理和审美向度上蕴含作家对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思考。事实上,伦理与美学的“传统”并不与“现代”“时代”矛盾而不兼容。对于小说来说,这一问题以人物、形象和情感的方式得到具体的颇具复杂性的表现。同时关联二人也即关联这两种传统的人物主要是贺加贝,贺加贝与贺火炬在喜剧演艺问题(实际上也是喜剧在现实中的“演绎”)上的歧见,贺加贝与潘银莲在感情、婚姻、家庭问题上的矛盾,则突出了现时代社会现实中“审美/艺术”和“伦理道德”问题上的分流、分化与分歧。就此而言,贺加贝是一个叙事结构中的网结,也是传统说书艺术或民间说唱文学中的“扣子”。作为文学形象的“贺加贝”,是一个体现着作家“结构意识形态”的人物,他是“形式”也是“内容”。换一个角度看,在审美/艺术问题上,贺加贝与贺少天、贺火炬形成对照;在伦理道德问题上,贺加贝与潘银莲、潘银莲与万大莲、潘银莲和她的嫂子“好麦穗”同样形成对照,这何尝不是一种兼具“形式”与“内容”的戏剧性设置?
其二,由日常性生成荒诞感,揭示存在于常态生活和生命中的荒诞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喜剧》是现实感与荒诞感的融合。小说扉页关于喜剧/悲剧、虚构故事/对号入座的表述,便是这一荒诞/现实的直观表述。
《喜剧》的荒诞不是《等待戈多》式“荒诞派戏剧”那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荒诞,它所传达的不是普遍的生存的无聊、空虚、绝望和意义缺乏、真理隐遁。《喜剧》的荒诞,近似宗璞、王蒙的“中国荒诞派小说”,有着中国的现实情景做根底和依托。作为生活与生命的常态,“荒诞”通过强烈的戏剧化场景、细节,揭示一种现实中的怪诞体验和荒谬感受。如贺少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不仅完全有违逝者初衷,更因过于郑重其事而又喧嚣闹哄几乎变成闹剧,此可谓悲、喜、闹难辨。再如贺加贝对万大莲痴情不改,却不断落入与若即若离的万大莲共同编织的“心造幻影”中,此可谓真假难辨、“虚实相生”。贺加贝、潘银莲夫妇本意为贺火炬做长远规划,却遭到后者的误解,兄弟阋于墙。著名喜剧编剧南大寿经历屈辱后放弃喜剧,最终以散文家和动物保护协会名誉顾问闻名于世。传统喜剧没落后,喜剧笑点和“包袱”要靠电脑和数字模型计算出来;葫芦头泡馍生意红火的老板王廉举转行喜剧演出,历经大红大紫,最终落得街头卖艺,等等。红火与塌火、快乐与悲伤、痛苦与欢乐,彼此轮换、纠结、缠绕。可谓日常中的荒诞,充满荒诞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中的常态”而已。《喜剧》的荒诞源自生活经验和个人生命体验,是生活、世态中的荒诞一面使然,蕴含作家对现实社会和世道人心的体悟和理性认知,体现着作家对世间之人与事深感可笑、可悲或可悯的态度,由是在文本中生产出杂糅幽默、讽刺、戏谑、调侃、夸张等包含复杂意味的喜剧效果。此外,小说中那只被潘银莲收养的流浪柯基犬,也颇有魔幻色彩。柯基犬令人心酸的坎坷经历,折射出现实中的残忍与残酷、无趣与无奈。通过柯基的“魔幻之眼”看到的同样是“现实”的荒诞。柯基犬的遭遇、见闻及其所关联的小说人物置身其中却不自知的“视角”,藉由一种对照和反讽的叙述,提供了对现实和人性的具有弥补性效果的体验与认知。在此意义上,流浪犬的“魔幻性”提供的却是一种现实主义式的生活和人性景观,是一种生活中不为常人所关注的隐秘面。
《喜剧》的荒诞感是生活、人性、世道人心中的荒谬、荒唐、怪异的文学表现,属于我们所在的当代现实,有着民族感、历史感、现实感和时代感。小说以荒诞、魔幻的形式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现实机理与肌理。那些不合常情常理仿佛不正常的不可能之事,以乖谬、歪曲或荒诞的形式发生与存在,而它们对人物的命运轨迹起着根本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构成当代中国暗流涌动的世情画面。看似夸张幽默、令人莞尔却又无可奈何的尖锐的现实,在陈彦笔下得到了兼具同情、反讽和批判的揭示。
三、寓庄于谐和“含泪的笑”:思想性、时代性、批判性之艺术表达
《喜剧》是一部充满对时代、现实严肃思考的具有现实主义思想力量的小说。杨辉称其为“寓意小说”①杨辉:《须明何“道”?如何修“艺”?将何做“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陈彦以贺氏喜剧的兴衰沉浮,通过编剧、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揭示喜剧与时代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展现喜剧的多种实践形态与内涵,表达对喜剧及其关联的现实生活和人性的严正思考。
《喜剧》中贺氏父子的“戏曲改良小品”对人物相貌、装扮和声色技艺的追求,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日益世俗化、商业化的氛围中不断走向畸型的繁荣。在小说中,普通市民和乡民观众在观看戏剧表演时喜欢“戏”的内容及剧中热闹的部分甚于演员自身的表演,更关心技术层面,而非艺术层面。而丑角、扮丑、唱丑在“热闹”和“技术”上更受观众欢迎。比起生角、旦角等角色行当,丑角更能以科诨表演博观众一乐,即便在这些嬉戏逗趣中多无聊、庸俗、低俗成分而缺少深刻内涵。出洋相、作怪样也能够活跃气氛,娱乐观众。因此,当秦腔等传统戏曲以及万大莲、廖俊卿和秦腔剧团走向衰落时,贺氏喜剧却随时代大潮迅速走红。当贺氏喜剧、贺加贝等专为迎合观众趣味放弃戏剧的美学品味和严肃的教化作用,制造噱头,与低俗趣味妥协,失去品味追求和艺术底线时,喜剧也就被搞得不伦不类,日趋败落,沦为一种表演夸张,以插科打诨和制造噱头吸引观众的低级滑稽文化。喜剧之热火与塌火,除了时代原因,亦有观演关系的处理:完全排除夸张和噱头会失去观众,从根本上影响喜剧发展;完全迎合观众的趣味而缺少现实的切实关注和对艺术品质的尊重,喜剧也只能成为市民生活的点缀和小玩意儿,同样会失掉它的价值。
陈彦将戏剧(戏曲)作为小说观照对象,有着时代动因——“民族文化伟大复兴”。对此,小说在叙述贺火炬重返西京,欲重振喜剧事业时写道:“西京秦腔团这时也在慢慢恢复元气,说是又要重视传统文化了。”但《喜剧》也颇有意味地写道,在解放前,贺少天所在戏剧班子一时被“国军”征为慰劳队,一时被“共军”编成文工团,一会儿被打耳光,一会儿被戳红缨枪的颇带喜剧色彩的悲惨经历,却成为喜剧与历史、时代之错位乃至悖谬关系的症候性写照。《喜剧》特别关注这种喜剧艺术和喜剧艺人的吊诡性处境,如贺少天对“喜剧时代”来临的前所未有的准确预言;如曾经红火一时的旦角、生角、净角在“新时期”的没落;如贺加贝是个喜剧演员,却始终经历着悲剧性或闹剧性的情感波折,甚至其个性气质与所演角色也是偏离和乖谬的:他在台上演出时,“剧情要求他色胆包天、气焰嚣张,他却偏是缠绵悱恻、羞羞惭惭”;再如,为了适应观众趣味和要求,贺氏喜剧多番实验,甚至动用高科技手段,却离喜剧的本真和神髓越来越远。对于个人来说,悲欢离合,悲喜交集,人生多番滋味纠缠难言;对于喜剧来说,既要不拘泥僵化、与时俱进,又不迎合观众趣味,被时代风潮裹挟,既要守住初心本心,又要做出调整和“修订”,何谓艺术本心喜剧本真?如何调整“修订”?其依据何在?尺度如何把握?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这一带有原命题性质的大话题,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
喜剧是幽默、搞笑、滑稽、调侃、讥讽、教训等多种元素均包容其间的艺术形式。它或者体现为酸辣尖刻的嘲讽,或者体现为冲淡自然的幽默,或者以噱头笑料营造滑稽效果。喜剧可以批判,亦可歌颂,它可以沦为无聊的文字游戏,亦可表达严肃的、悲剧性的崇高主题。喜剧可以迎合时代失去批判功能,亦可以成为特定文化情境中的异质性力量,它可以逃避现实、粉饰现实,又可以挑战现实、对抗现实。寓庄于谐,是《喜剧》的基本手法;“含泪的笑”是小说的基本美学风格;以杂糅写实、荒诞和魔幻甚至“元小说”手法(借柯基犬之口说出小说的情节发展和结尾),对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及令人痛惜、心酸之人事的讽刺与同情,使《喜剧》具有讽刺性写作的内在品质。
陈彦虽然受到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但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之民间性、草根性的认知和理解,又使他的写作与通常所谓启蒙主义精英文学区别开来。《喜剧》既非启蒙主义写作,亦非民间主义和趣味主义写作。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主角》之后,陈彦以丑角、喜剧的形式,对“另一种”更加具体的戏曲与小说融合方式的探寻,也是作家对更适宜、更有力的“理想喜剧”(非文类意义上)的探寻。《喜剧》是否定的、解构的,也是肯定的、建构的,其中有讽刺、批判,也有调侃、嘲谑和滑稽。这一杂糅理性与感性、清醒认知和感觉狂欢色彩的特点,不仅体现在贺加贝、王廉举、史托芬、潘银莲等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贯穿小说的向上生长或向下探源的执着不息的精神力量上。这是一种包含作家理性精神、民族意识和伦理正义的、进入历史的向上向前的努力。
陈彦的小说以戏曲为装置,连接了个人与社会、民族、传统文化智慧,建立了个人与民族、世界和人类之关系。同时,陈彦的“戏曲”又具有“语言”和元符号的性质,潜在地反驳了专注个人、内心和私人生活的创作倾向,干预了惯常小说叙事姿态、立场和美学品质。如果说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源自语言的创造性功能,那么戏曲(传统)与流浪狗(现代主义)的介入,使《喜剧》不再停留于反映、再现性表达,而是借助戏剧的创造性功能,展示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结构和精神结构。相比悲剧的沉思表情,喜剧仿佛天生带着一副欢乐的面孔,其切近的生活性、世俗性和生命本性特征,使之始终面临着如何避免庸俗化的问题。陈彦在《喜剧》中通过南大寿之口将庸俗化称为“杂耍”“搞怪”“胡球鸡巴闹”,称“那不是艺术”,“现在的喜剧不叫喜剧,那叫把人压倒,硬咯吱人的脚心板哩”。基于生活和艺术的辩证法,陈彦并没有将时代与喜剧作直接的对应,悲剧还是喜剧的认定,取决于不同的视角、存在环境和生命感受,小说借追随潘银莲的流浪柯基犬写道:“喜剧让人智慧而陶醉;悲剧让人开悟而警醒;而正剧,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活,离喜剧和悲剧也就一步之遥。”悲喜与否具有相对性、具体性、偶然性和变易性。这是艺术的、美学的辩证法,也是对时代生活之复杂性与可能性的认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与时代、现实和世界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时代、现实与历史、传统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这个时代和它的历史连续性中,通过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实践,在交汇、融通、激荡的全球化语境中,在“液态”流动的高度现代性情境下,建立自己稳定、切实和开放的个体和民族群体文化认同。
四、“传统”和“乡村”:在当下进入中国之心
陈彦运用小说的形式,以戏曲、戏剧和角色行当为入口,描述并反思审视那些偏离艺术和人性人伦轨道的人物行为,确立道德立场和超越意识,借助传统文艺范式模型,重述民众熟知的故事,将所谓低级的喜剧形式吸纳进一种二元性道德系统,在长篇小说中探讨伦理道德文化和艺术等问题,探讨艺术的承传与革新,艺术与时代生活之关系,思考艺术的人性基础、民族意识以及更扩大的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的生活是正当,如何获得个人以及超越个体之人的尊严等问题。
上述问题,可简要概括为:个人/族群如何在传统/现代之复杂关联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本,如何在高度现代性语境中建构有效的主体认同。个人的身份不能只在当下的经历和体验中找到,中国的身份亦摆脱不了“传统”的根基,但“传统”并非对抗现代或西方的工具、手段,它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建构自身主体认同的一个价值向度,其意义不能只在对抗现代西方的冲击、渗透时获得,否则,它只是一个东方主义式的被动被凝视的存在。“传统”作为一种现代的发现或发明,不应只存在于学术话语和理论思辨中,它更作为一种现实实践形态,存在于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生活中。
《喜剧》以“传统”和“生活”为资源,以长篇的形式探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具体的个体的连接方式。陈彦的思考和探寻,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现代性个人主体和国族主体建构的一种变奏。在当代都市生活之外,《喜剧》发掘了生活深层的另一个世界,重构、重显“传统”和“乡土”的普遍性。
首先是“传统”。小说中的“传统”包括伦理道德传统和美学艺术传统,主要通过戏曲戏剧艺人及相关的其他人物形象(如潘银莲、潘五福、罗天福等,尽管并非戏剧中人,却一则他们与戏剧相关,二则其本身也承载传统伦理观念)塑造得以体现。民族戏曲、戏剧是一种从我们自身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艺术形式。与话剧、歌剧等借鉴西方却被视为普遍性的现代艺术相比,戏曲、戏剧具传统性、本土性、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同时,这些独特的传统,其意义也需在当今语境下加以理解和诠释,以重新认识其“好处”和“不好处”。好处与不好处,自是相对而言,且二者相互缠绕纠结,常为一体两面的存在。如陈彦所言:“现代性是和传统对照出来不是孤立形成的。没有传统,也就没有现代。有些现代是对传统的反叛,而更多的现代仍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社会肯定要向现代化进发,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现代和传统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撕裂,而是水乳交融、轩轾难分的,是驮着历史辎重前进的演进关系。”①刘茜:《陈彦:“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中国文化报》,2021年1月26日。关键问题是,现代生活、时代发展对艺术之特质、功能及表现形式与程式,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观众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亦有新变,这对既有传统观念及其表现形式也有了新的要求,戏剧——秦腔、喜剧,既深刻扎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它在当下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喜剧》《主角》分别写出了喜剧和秦腔在当下遭遇的困境和转型的可能,并对其进行了颇具根源性、本体性的思考。
其次是“乡村”。在老一辈戏曲戏剧艺人那里,“传统”显示为一种“乡愁”式的美感经验。他们意识到无可阻挡的时代巨变,意识到自己所信仰和坚持的技艺,正在年轻人的趣味和喜好面前,失去曾经的魅力。陈彦以挽歌的形式写出了这种“乡愁美学”,也写出了这一老魂灵新生的必要和可能。在陈彦小说中,“乡土”既是与市场消费文化主导下的当代都市空间相对的另一处“异质性空间”,更是戏曲得以产生和获得持续生长动力的“民间”。就前者而言,《喜剧》写到潘银莲潘五福兄妹,潘五福好麦穗夫妻,好麦穗与其情人这对亡命鸳鸯等“乡村世界”的人物,他们的世界同样是驳杂的而非纯粹的美与善的世界,却沉实而饱满;相对于过于势利和世俗的扁平化的都市空间,它包含的情义,它的立体性和饱满性、充实感,却是都市所不能相比的。它与“土”相伴,从“土”中获得营养和滋养。相对于动荡不居,充满流动感和机动性的时代生活,它处于底层和偏远荒僻之地,但只有依托它,居于大地和世界之中的人,才能创造出比平面化的“当下”更高的更具超越性的生活,而在彼岸消失时,才能避免沉沦于“当下”。因此,《喜剧》中的“乡土”,既是过往和历史,又是赋予“现在”以可期望的前景和可能的“未来”。相对于当下,它是一个异质性空间,其异质性建立于不同于“当下”的既在历史之中却又超越历史的时间性——一种独特的历史性。相对于历史与时代之宏大,它是“小”的;相对于历史与时代叙述之身居高位,它处于“下位”,但它能以小见大、自下而上。存在于宏大叙事和大写历史中的小与大、上与下的结构性关系,并未在此消失,这就是陈彦小说中“独特的历史性”。而这便是陈彦在《主角》之后,通过《喜剧》重构普遍主义和总体性美学的历史哲学依据②关于《主角》的历史主义叙事哲学与现实主义总体性重构问题,可参看,王金胜:《现实主义总体性重建与文化中国想象——论陈彦<主角>兼及<白鹿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喜剧》藉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力量,体现着共情的力量,通过人物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感同身受人物所处的情境、所遭遇的生活和心灵的困境,感同身受他们及塑造他们的作者所投入所倾注的情感和态度。同时,小说又没有沉溺于人物的心理、情感,而是由内心而向外延伸、辐射。这既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主观性,使情感走出封闭的内心走向广阔而复杂纠缠的社会生活。正如《主角》没有停留在主人公忆秦娥的个人生命体验或其心灵世界中一样,《喜剧》同样没有聚焦在一位或几位丑角艺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而是通过喜剧这一艺术门类和丑角行当,容纳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面向。如此叙述,既有共情,又暂且跳出了内心,减弱了内倾性,而多了一份沉静和通透。《喜剧》的现实观照是关于中国现实心理和精神结构的,而非追随时代做镜像式的反映。小说中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属于人学意义上的人,但也都是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他们都有这个时代的心理、性格,也有时代性所不能涵盖的、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世俗性、历史性和文化性格。他们的遭遇是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普通人都可能会遭遇的问题。小说在“问题”中塑造人物,描述他们应对问题的方式,由此在社会现实、时代生活和心理结构、情感结构之间建立呼应和联系。这种叙事方式,或可称为陈彦式的世俗心理结构分析。《喜剧》《主角》采用的便是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在地性”中国现实主义,不仅是贴着地面,贴着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和当下中国现实状况的思考,也是进入“中国之心”的思考。
当然,《喜剧》人物塑造和人物关系设置上的戏剧化倾向也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小说中,个人的有限性和超越有限性的无限追求之间,个人情感愿望与理性和伦理道德规范之间,人物的丰富性、人物关系的矛盾性与人物塑造上某种程度的脸谱化和叙事的程式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龃龉或不协调。从另一角度看,按照现代小说的艺术惯例,陈彦小说人物塑造有扁平化特点,人物设置也倾向于矛盾冲突关系。“中国戏曲的脸谱化,有其弊端,也有好处。弊端是一眼望穿,难有惊喜改变;好处也是一目了然,明牌亮打,观众不易上当受骗。”①陈彦:《喜剧是人性的热能实验室——长篇小说喜剧<后记>》,《文艺报》,2021年3月5日。《喜剧》在人物上,体现着陈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选择。这不仅是一种美学选择,也是一种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的选择。这一选择发生在陈彦获得“现代”和“传统”的双重自觉之后,因此是颇有意味的,颇有赵树理经历“新文学”挫折之后,对民间文化传统和民间说唱艺术如民间故事、快板、戏曲曲艺的选择。只不过,在陈彦这里,人物不再是竹内好所称赵树理小说人物时所说的“个人就是整体”的状态,“个人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这个这一形式出现的”;或者说,陈彦小说更具“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的现代性②[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韩意译,阮其灿校,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