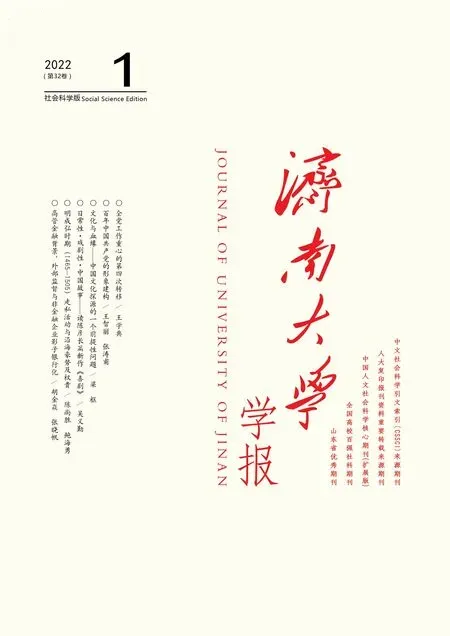历史剧语言如何“古今共通”
——以郭沫若历史剧《虎符》的修改为中心
宋 宁,魏 建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历史剧的语言是历史剧创作中的一个难题,既要让现代观众听得明白,又要能够营造古代氛围。语言问题就成为制约历史剧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当代影视历史剧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为此,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古今共通”的历史剧语言原则,为解决历史剧语言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然而,迄今学术界对于郭沫若历史剧语言观的形成和内在机制,及相应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缺乏深入的探究。《虎符》是郭沫若在1942年创作的一部历史剧,此时他的历史剧语言已经十分成熟,其后他对于《虎符》的两次修改也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①《虎符》创作于1942年2月2日至11日,同年3月26日起在重庆《时事新报》连载,10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发行,是为“初版本”。之后郭沫若做过两次修改,分别是1948年3月在香港的修改,1949年8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是为“上海群益修改本”;以及1956年7月在北戴河的修改,收入《沫若文集》,形成“文集本”。。这为讨论郭沫若历史剧语言观念和实践提供了极佳的案例。本文便以历史剧《虎符》的修改为中心,探讨郭沫若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实践历史剧语言的“古今共通”。
一、“古代的幻象”与“古今共通”
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古今共通”的历史剧语言原则,“反正是幻假成真,手法干净些,不让人看出破绽,便是上选。大概历史剧的用语,特别是其中的语汇,以古今能够共通的最为理想,古语不通于今的非万不得已不能用,用时还须在口头或形象上加以解释,今语为古所无的则断断乎不能用,用了只是成为文明戏或滑稽戏而已。”①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2月14日,第4版。郭沫若的论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幻假成真”的效果,历史剧语言要让观众沉浸在古代氛围中,“不让人看出破绽”;二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要重视“古语”与“今语”的互动关系。这体现了郭沫若对于自己历史剧创作的反思和概括,以及对于历史剧语言论争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首先,郭沫若提出历史剧语言应该“幻假成真”,实际上认可了历史剧语言论争中“古代的幻象”的说法。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戏剧创作中,常常出现古代人物说现代语言、变成作者传声筒的现象。如《卓文君》中卓文君说:“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便是我自己做人的责任”等②郭沫若:《卓文君》,《创造》(季刊),1923年第2卷第1期。。当然,历史剧语言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亟待解决的难题。1927年,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续)》中说,“郭沫若底作剧,我以为,并不是对于戏剧的艺术有特殊的情绪,只是因为剧中的人物可以张开嘴大说话罢。所以,一切剧中人的嘴,都被他占据了,用以说他个人的话,宣传他个人的主张去了。”③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续)》,《狂飙》,1927年第13期。1932年,余上沅在《历史剧的语言》中说,“在现在中国的历史剧里,许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上上下下的语言,无非是连串故事的对话,绝无个性可言。要有个性,也只是作者的个性。作者拿演员做号筒,发挥他们自己的思想。”④余上沅:《历史剧的语言》,《新月》,1932年第4卷第3期。他所指摘的作品有郭沫若的《聂瑩》、顾一樵的《岳飞》《白娘娘》、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长城之神》等。除了批判当时历史剧在语言上的缺失,批评家们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顾仲彝认为:“要绝对用古代语来写历史剧,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并且也似乎可以不必。不过语气音调非仿古不可,或创一种特别语调,以示于现代。”他指出《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对话是“值得编历史剧的人摹仿的学习的”⑤顾仲彝:《今后的历史剧》,《新月》,1928年第1卷第2号。。余上沅建构了系统的历史剧语言理论,包括“都要恰合身分”“历史上的正确”“戏剧上的正确”“顾到舞台上的表演”等。更重要的,他提出了“古代的幻象”说,对历史剧创作解决语言问题很有启发性。因为,“古人用什么样的语言,只有古人知道,即或我们考证出来了,写在纸上,说出口来,也没有人能懂”,所以,“才避去完全现代的语言”,“并且不可有戳穿西洋镜的调子,声口,总要叫人听到耳朵里不觉得它新,却相信它古”,“给人一个古代的幻象”⑥余上沅:《历史剧的语言》,《新月》,1932年第4卷第3期。。可以说,余上沅的“古代的幻象”说是顾仲彝的“仿古”说的进一步发展。其后,用观众“相信它古”的历史剧语言营造“古代的幻象”的方法,逐渐成为戏剧家们的共识,成为进一步实践和探讨的基础。
其次,郭沫若的“古今共通”,还包含了“古语”和“今语”的辩证论述,成为历史剧语言实践的指南。当剧作家们都意识到应该营造“古代的幻象”之后,那么关键问题是如何创制这样的历史剧语言,对此每个剧作家采用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并不相同。1937年,陈白尘、夏衍、张庚等十人在《历史剧的语言问题》的座谈中,从不同侧面对历史剧语言提出看法,涉及文言、白话、现代语加工,欧化语言与观众理解等方面,都趋于赞同使用一种既有历史感,又要被观众理解与接受的语言。陈白尘发言说:“在写太平天国时,碰到了数不清的难题。其中最棘手的一个是:‘用什么语言呢?——是毫无顾忌地使用现代语呢;还是用历史的语言?’‘历史语言’是怎样一种语言?太平天国时代又该怎样?——天晓得!”他采用的办法是“(农民的语言)-(现代语成份)+(太平天国时代所特有的一些语汇)=太平天国语言(?)”⑦白尘、夏衍等:《历史剧的语言问题》,《语文》,1937年第2卷第2期。。陈白尘为了营造太平天国时期“古代的幻象”,创造了相应的历史剧语言,但他的语言公式只适用于这一部历史剧。夏衍在发言中总结了自己历史剧创作时语言运用原则:“一是不使历史上的人物说现代话”;二是“用历史上的语法也得尽可能的使之平明易懂”①白尘、夏衍等:《历史剧的语言问题》,《语文》,1937年第2卷第2期。。总之,能够营造“古代的幻象”这一历史剧语言的目标,成为当时戏剧家们的共同追求,虽然他们的表述、侧重不太一样。从这一层面看,早期历史剧的语言过多承载新思想,直接造成其发展的缺陷,需要“纠偏”回到戏剧艺术本体,回到舞台和演出实际。
对郭沫若来说,他的历史剧创作从不成功走向成功,戏剧语言的变革是其中重要的因素。1937年11月,他在20年代创作的独幕剧《棠棣之花》和两幕剧《聂瑩》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五幕剧《棠棣之花》。这部历史剧获得很大的成功,出乎郭沫若的意料,给他很大信心,引发他创作了系列抗战历史剧。“真没有想出《棠棣之花》,在最近竟搬上了舞台,而且大受欢迎。”②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2月14日,第4版。对比早期和抗战时期不同版本的《棠棣之花》,很容易发现戏剧语言的巨大改变。比如:
聂嫈:自从夏禹传子,天下为家;井田制度,土地私有;已经种下了永恒争战的根本。根本坏了,只在枝叶上稍事剪除,怎么能够济事呢?(1920年《时事新报》版)③郭沫若:《〈棠棣之花〉汇校本》,王锦厚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第10页。
嫈:是的,你这次去访严仲子,我正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体呢。(1942年重庆作家书屋版)④郭沫若:《〈棠棣之花〉汇校本》,王锦厚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第10页。
1942年版本的人物语言是日常化、口语化的,虽包含“救国救民”的新思想,表达却比较自然。而早期版本的人物语言完全是书面语。郭沫若显然关注着历史剧语言的探讨和发展,接受了历史剧语言营造“古代的幻象”的共识。他结合五幕剧《棠棣之花》修改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古今共通”原则,阐述“古语”和“今语”的辩证关系,并不断进行相应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
二、吸纳“旧小说式的白话”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选取的题材以先秦史料为主,可以说他的历史剧大多表现了很古的历史。有趣的是,除了一些器物、官职的名称,他的历史剧语言却并非很古,但观众既“相信它古”又很容易接受,确实达到了“古今共通”。实际上,在这些抗战历史剧中,郭沫若创制了一种独特的戏剧语言,脱胎于欧化的新文艺语言,又大量吸收所谓“旧小说”的语言。这种能够为市民大众所接受的戏剧语言,成为他的抗战历史剧演出成功的重要保证。例如“事体”一词,被郭沫若广泛用于抗战历史剧创作中。上文所引五幕剧《棠棣之花》的聂瑩台词中出现了,“是的,你这次去访严仲子,我正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体呢。”其他剧作中也常见,尤其在《虎符》中一共出现了45次。比如:
太妃:那你就到外边去,同侯姐姐一道照应着外边的事体。朱女:是。(由园门下)
又如:
太妃:侯先生,你真是好不容易到我们这里来,你来有什么见教的呢?
侯生: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体,是用不着来麻烦太妃的,一来是公子上朝去了,二来呢是
想向太妃请安。又听女儿说:君夫人也在这儿,所以我一并来请安来了。(欠身)⑤郭沫若:《虎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2年版,第36页,第39-40页。
可以看出,郭沫若的《虎符》等历史剧的语言,已然是十分流畅的口语,且别有韵味。这种戏剧语言显然学习了“旧小说”的语言,包括句式和语汇。“谨慎言语”“见教”“请安”“事体”等语汇,既让读者和观众感到“古”,又十分熟悉亲切。其中,“事体”一词本是吴方言,表示“事情”的意义,但通过晚清小说、民国通俗小说的运用,已经成为大众读者熟知的词汇。可见,郭沫若通过吸纳市民大众所容易接受的“旧小说”的语言,实现了历史剧语言的“古今共通”。因为,一方面,“旧小说”的语言来源于明清白话小说,与现代口语有一些距离,具有“古”的感觉,能够让观众产生“古代的幻觉”;另一方面,“旧小说”的语言在晚清小说、民国通俗小说中依然在使用,当时的大众读者十分熟悉,很容易接受,也属于“今”的文艺语言。而且,晚清小说、民国通俗小说生产和传播的中心是开埠之后的上海及其周边城市,“旧小说”的语言中逐渐加入了许多吴方言和“上海土白”的语汇,这些语汇是“活”的口语,同时也能够为全国大众读者所理解和欣赏的口语。
采取“旧小说”的语言,并不是郭沫若一时兴起,首先,这种改造自己早期戏剧语言的路径,脱胎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革命文学阵营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成型于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民族形式”大讨论。1930年,郭沫若鼓吹“普罗文艺的大众化”时,强调新文艺的通俗化,要肩负“教导大众的使命”。他指责“从来的文人有种怪癖,便是怕一个‘俗’字”,“譬如我们的戏剧文学便总爱采取最新式的带着些表现派的趣味的形式……”并主张“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家应该要充分的做一番俗事”,“戏剧方面我觉得旧戏的皮簧也很可以利用。(须知我们是利用,不是改良!)”“一切制作都应该以能影响大众为前提,这是我们的文艺的尺度。”①麦克昂(郭沫若):《普罗文艺的大众化》,《艺术》,1930年第1卷第1期。郭沫若比较宏观地谈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但指出新文艺创作要不怕“俗”,可以利用大众喜欢的旧形式。
其后,瞿秋白与茅盾发生论争,把文艺大众化讨论引向具体的文艺语言问题。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中,把“五四式的所谓白话”贬斥为“新文言”,还不如“旧小说式的白话”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虽然读出来也并不是现代中国人口头上说的话,而只是旧戏里的说白,然而始终还是读得出来的,可以懂得的。因为这个缘故,旧小说的白话比较的接近群众,而且是群众读惯的”。然而,瞿秋白反对现有的各种文学语言,宣称新兴的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而新兴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们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着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所以,“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运用最浅显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这里,应当预防可能的错误——是盲目的模仿旧小说式的白话,——我们决不应当容许这种投降政策。”②宋阳(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1期。显然,瞿秋白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的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但他的大众文艺语言的设想却是脱离现实的。
对此,茅盾表示多方面的质疑。其一,他反对把五四新文学的语言称为“新文言”,认为新文学的白话已经通过基础教育获得了广泛接受,“如果现在一个小学三年生中途辍学而做工人”,就会对新文学的小说“比较的接近”。其二,茅盾认为“旧小说”能够得到大众的欢迎,“这原因并不全在旧小说的文字能叫大众上口”,还在于能够感动大众的“描写方法”,“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其三,茅盾“亲身去调查一下”,发现所谓无产阶级的“一种中国的普通话”根本不存在。“即五方杂处的大都市的上海工人虽然各省人都有,然而他们‘通用语’的趋势却是‘上海土白化’”;“又各工人区域每因其何省工人占最多数而发生了以该多数人省分的土话为主的‘通用语’”③止敬(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2期。。也就是说,各个区域工人的“通行语”都受到“上海土白”的影响,但各区域工人的“通行语”还是以各省土话为主,并不能跨区域相通。他退一步讲:“上海白作为基本的‘普通话’可以做工具。”“我以为土话的大众文艺比之宋阳先生所谓‘真正现代中国话’的大众文艺,可能性更大。”总之,茅盾倾向于坚持新文学的白话,通过借鉴“旧小说”和“土语”发展新文学的白话,“只要从事创作的人多下功夫修炼,肃清欧化的句法,日本化的句法,以及一些抽象的不常见于口头的名词,还有文言里的形容词和动词等等,或者还不至于读出来听不懂。”④止敬(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2期。实际上,茅盾此时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他把自己的文艺大众化理念付诸实践,《子夜》出版后果然深受大众读者欢迎。“正是通过向‘旧小说’学习,追求雅俗共赏,茅盾解决了新文学长久以来存在的语言过于欧化的问题;在当时,也还没有其他新小说家像茅盾这样善于讲故事。”①葛飞:《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代的读者趣味》,《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但当时革命文学阵营的批判家大多指责茅盾的这一创作倾向,因为这无疑属于瞿秋白所谓的“投降政策”。
然而,抗战全面爆发后,文艺界做出调整,文艺大众化的目标,也变成宣传抗战,团结一切力量抗战。郭沫若认为:“一切文艺活动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的这一点,集中在能够迅速地并普遍地动员大众的这一点。这对于文化活动的要求,便是需要他充分的大众化,充分的通俗化,充分地产出多量的成果。”②郭沫若:《抗战与文化》,《自由中国》(汉口),1938年第3期。不久,他在《“民族形式”商兑》中指出,民族形式的源泉是“现实生活”,从“民间形式”和“士大夫形式”中都可以摄取营养,“象旧小说中的个性描写,旧诗词的谐和格调,都值得我们尽量摄取。尤其是那些丰富的文白语汇,我们是要多多储蓄来充实我们的武装的。”③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大公报》(重庆),1940年6月10日第3版。应该说,这种战时文艺思想也是文艺界的共识。只要有利于抗战,只要能够发动大众,借鉴通俗文艺、“旧小说”完全不成问题,反而值得鼓励了。此时,郭沫若在创作《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抗战历史剧过程中,无疑也以“动员大众”为目的,推进戏剧创作的通俗化,包括采用为大众化所接受的戏剧语言。经过1930年代初茅盾对文艺大众化论述和实践,最便宜可行的路径还是改良新文学语言,借鉴“旧小说”和吸收“土语”,解决新文学语言的欧化问题,从而获得广大读者大众的欢迎,而郭沫若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其次,郭沫若采用“旧小说”的语言,还由于他与上海出版界、文艺界和市民大众的广泛接触。1919年在日本读书时,郭沫若就开始订阅上海《时事新报》,并在副刊《学灯》编辑宗白华的赏识和帮助下,集中发表一系列新诗和文论,一举成名。他与宗白华、田汉三人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宗白华致田汉的一封信中说:“但我近有一种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予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样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④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公司,1920年版,第1页,第28页。不久,田汉致郭沫若的信中转述了宗白华的话:“看到他那封信中间说:他近有一种很可喜的事体,……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⑥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公司,1920年版,第1页,第28页。初出茅庐的郭沫若对于宗白华激赏自己的这一“事体”,估计会留下深刻印象。其后,郭沫若多次居住在上海,对于上海市民大众欣赏的通俗文艺语言愈加熟悉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郭沫若回国后也是居住上海,而在11月修改旧作创作五幕剧《棠棣之花》时,可以猜想,他便很自然地吸取了大众读者容易接受的“旧小说式的白话”,包括那些晚清后进入“旧小说”的“上海白话”。因此,郭沫若吸纳“旧小说式的白话”,推动了抗战时期新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也实践了他所设想的“古今共通”的历史剧语言。只不过,他在此时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主要解决的是“仿古”问题,目的是能够营造“古代的幻象”,避免“滑稽戏”的出现。而随着时代政治的变化,“今语”的新要求出现,他开始重视历史剧语言在“今语”层面上的修改和调整。
三、“今语”的新要求与历史剧语言的当代性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集中修改了一遍他的抗战历史剧。这一次集中修改,除了少数大的改动,比如《高渐离》的结尾,大多数是语汇、字句的改动。具体到《虎符》而言,也是如此,“我把本剧重新校阅了一遍,添改了一些字句。”⑤郭沫若:《〈虎符〉校后记》,《虎符》,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年版,第163页。李畅比较了1949年群益修改本与初版本的《虎符》,“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郭沫若把初版本中所有的共42个‘事体’全部改为‘事情’或‘事’,也就是彻底放弃了‘事体’这一说法。”她认为“事体”是“上海方言(吴方言)”,“看来郭沫若为了剧本能被更广泛的群众接受,他舍弃了方言而选择了最具普遍性的词语,这么做十分高明。需要补充的是,这一时期,他对《屈原》和《高渐离》的修改中同样把所有的‘事体’改为‘事情’或‘事’。”①李畅:《历史剧〈虎符〉的版本与修改》,《四川戏剧》,2008年第3期。实际上,郭沫若此时参加了香港的“方言文学”运动,所以,他修改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体”这一语汇是“方言”,而在于“事体”从晚清以来已成为深受市民大众欢迎的“旧小说”、通俗小说中的语汇。郭沫若把“事体”换成“事情”,是为了学习“解放区文艺”,使他的历史剧语言符合“今语”的新要求。
郭沫若支持香港的“方言文学”运动,实际上是赞同以解放区文艺为样板的文艺大众化。1948年初在香港文艺界开展的“方言文学”,是汇聚到香港的左翼作家们推动的。茅盾曾指出:“我对于此次论争是把它当做‘华南文艺工作者如何实践大众化’来了解的”②茅盾:《杂谈“方言文学”》,《茅盾全集》(第23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446页。原载1948年1月29日香港《群众》周刊第2卷第3期。。而冯乃超、邵荃麟执笔的总结中明确地说:“革命的大众文艺(方言文艺在内)的主要敌人是反动的大众文艺,那是因为它根深蒂固地盘据在人民的文艺生活里面,它所用的言语是从民众的口头文学发展出来的,因此比较的接近群众。我们要战胜这个敌人,就应该区别我们的言语和旧小说式的白话,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发掘其有生气的,吸收其精华,排泄其渣滓,这样才能挖掉反动文艺的根,建立人民的大众文艺,……”③冯乃超,荃麟:《方言问题论争总结》,《正报》,1948年第69、70期合刊。“方言文学”运动参与者们讨论如何建立粤语的方言文学,目的是为华南工农大众服务,而在此过程中要打败“反动的大众文艺”,“应该区别我们的言语和旧小说式的白话”。于是,“旧小说式的白话”重新被打入了另册,不符合“革命的大众文艺”的要求。在这场“方言文学”论争中,郭沫若表示“在我个人也是举起双手来赞成无条件的支持的”,“假使是站在人民路线的立场,毫无问题,会无条件地支持方言文学的独立性。我们既承认了文学应当以人民大众为对象,那就必须制作为人民大众所了解的东西。”④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文艺生活》(海外版),1948年第1期。因此,如果“事体”只是方言语汇,并不一定要全部改换,关键是其“旧小说”的色彩太浓,为了“挖掉反动文艺的根”必须去除。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讲话》精神的引导下,解放区文艺大众化是尽量运用工农兵(实际上主体是农民)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吸纳他们能够懂得的方言、口语。而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工农大众的能够接受的语言成为文艺“今语”的新要求。此时,郭沫若对于《虎符》语言的“添改”,就是为了符合“今语”的新要求,呈现“人民大众”的意识,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意识。如:
平原:我们所缺乏的就是人手和武器,假使我们有充分的武器和人手,我老早就可以把敌人赶出国境的。……(1942年初版本)
平原:我们所缺乏的就是人和武器,假使我们有充分的武器和人手,我们老早就可以把敌人赶出国境的。……(1949年群益修改本)
郭沫若把作为士兵的“人手”改成“人”,把平原君夫人自称的“我”改成“我们”,隐含着对人民大众的肯定。当然,郭沫若对于抗战历史剧的这一修改方向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的第二次集中修改。比如:
妪乙:秦国的兵也真果是可怕,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杀就是几十万啦。(1942年初版本)
妪乙:秦国的兵可真也可怕,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杀就是几十万啦。(1949年群益修改本)
妪乙:秦国的将军们真也可怕,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杀就是几十万。(1957年文集本)
1948年去掉了“果是”一词,还只是把这一句改得更顺畅,更口语化。1956年把“兵”换成了“将军们”,这一修改显示了郭沫若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敏感意识。因为秦国的普通“兵”也属于下层人民,更应该谴责的是秦国的统治者和“将军们”。
如果说郭沫若在抗战时期认为戏剧“始于民众,终于民众”①郭沫若:《戏剧与民众》,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15日第4版。,这一“民众”主要指市民大众,他在创作中不断接纳、采用符合市民大众审美的戏剧语言、情节设置等,寻求民族国家意识与市民社会的有效契合点,可谓是郭沫若抗战历史剧成功之处。那么,在香港时期,“方言文学”运动意味着解放区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和方式,正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逐步推广到全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要转变小资产阶级立场,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郭沫若修改抗战历史剧时,也从面向市民大众改变为面向人民大众,删改抗战历史剧中的“旧小说式的白话”,建设“革命的大众文艺”。实际上,他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抗战历史剧在都市剧场里的演出是十分成功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比如,1947-1948年间,祖国剧团、军剧21队在京津两地演出《虎符》,当时有报道称:“不但园方欢喜,堂方欢喜,就连存车也欢喜,门外小贩也欢喜,三轮车夫也欢喜,卖说明书的小孩儿也欢喜,观众看完了当然也欢喜,此之谓‘皆大欢喜’。”②郭枫:《〈虎符〉演出花絮》,《戏世界》,1947年第8期。然而,郭沫若已经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自然不能满足于剧作受到市民大众的欢迎,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欢迎,而是努力建设“革命的大众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使他的历史剧语言符合“今语”的新要求。
四、历史剧语言的规范化与文艺大众化的新起点
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现代著名作家在出版旧作之际都进行了较多的修改。郭沫若又一次集中修改了他的抗战历史剧,收入《沫若文集》中。就《虎符》来说,修改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把文言的、方言的、不规范的字词换成常用字词,或者删去,如“断不会”改为“就不会”;“便”“曾”改为“就”;“姊妹”改为“姐妹”;“子息”改为“儿女”,“顽嚣”“乖僻”改为“不好”;“分工而作”改为“去工作”;“章法”改为“调子”;“追述一遍”改为“说一遍”;“除非”改为“还不如”;“络续”改为“陆续”;“诱你”改为“逗你”;“晓得”改为“知道”;“待到”改为“等到”;“国祚”改为“祖国”;“忖度”改为“揣测”;“谢罪”改为“请容恕我”;“法术”改为“本领”,等等;删去“好的宗族”“小小的家祭”“传达我的意旨”“敬请”“恳切的向你请教(拱手)”“一并来请安来了”,等等。二是修改一些语法有问题或者有文言句式倾向的句子,如“把我太看得珍重了”改为“把我看得太珍重了”;“怎么侯妹妹也来了呢”改为“侯妹妹怎么也来了呢”;“准备明天去上她母亲的坟的”改为“准备明天去跟她母亲上坟”;“不满意于我”改为“很不满意”,等等。三是删去语气词,删得最多的是“啦”,其次有“吗”“咧”“吧”“啊”等。四是标点符号的修改,把一些逗号改为句号,实际上是把长句改为短句,减少了欧化的长句。很显然,1956年郭沫若对《虎符》进行修改时,十分注重历史剧语言的规范化问题。
作家在50年代对自己作品进行规范化修改的行为,曾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甚至有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普通话写作”,“从5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着对作家思想改造运动展开的是对方言文学的遗弃、对欧化与文言的清除,全力加速了语言的统一化、规范化进程,这一过程几乎可以概括为朝普通话写作方向迈进。”认为“郭沫若通过修改旧作企求达到思想改造与普通话写作的双重目的”,并根据《虎符》修改不均匀的情况推测郭沫若“心态时见烦躁”①颜同林:《<虎符>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1期。。
然而,不宜过分解读郭沫若在上世纪50年代修改旧作中的思想改造意味,也不应忽视他推动语言规范化的主动性。其一,郭沫若在抗战后期已经形成“人民本位”思想,提倡“人民的文艺”,早在香港时期就开始根据新的意识形态修改历史剧。上世纪50年代的集中修改旧作可视为香港时期的延续。其二,郭沫若一直坚持五四新文学的道路。尽管他同意五四新文学语言有欧化的弊端,还没有完全达到言文一致,但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讨论、香港时期“方言文学”论争中,他的着眼点都是新文学的进一步完善。他认为“民族形式”是“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文艺家不仅要活用国语,而且要创造国语。”②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大公报》(重庆),1940年6月10日第3版。他视“方言文学”为文艺大众化的手段,主要为了普及,“所以,方言文学的建立,的确可以和国语文学平行,而丰富国语文学。”③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文艺生活》(海外版),1948年第1期。也就是说,郭沫若一直认为新文学应该是国家通用语文学。其三,语言规范化也可视为文艺大众化的新起点。郭沫若称得上语言文字改革的建言者和顶层设计者之一,他的新文学发展观、文艺大众化的态度有效地贯穿于语言文字改革、普通话的推广中。1949年8月25日郭沫若与茅盾、马叙伦三人联名复信毛泽东,就吴玉章提出的文字改革问题发表看法,认为“重点试行新文字,条件尚未成熟”,统一的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国语(即普通话)是推行中国拼音文字的先决条件,等等④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4页。。由此拉开了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大幕。郭沫若作为文化界和政府领导人,对整个进程十分关注,全力推进。他认为普通话是文字改革的前提,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话在以加快的速度采取着一定的标准音而趋于统一,这是必然的趋势。几十年来我们的话剧、电影的旁白、歌唱和广播等,都在遵循着这一趋势进行。在目前,留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更加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促进这一趋势的前进。”⑤郭沫若:《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中国语文》,1955年第41期。郭沫若指出了话剧对于普通话形成的作用。另外有专家强调:“在全国广大地区,许多人都是通过舞台上演员的语言来学话的。无疑地,话剧是推广标准语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剧作家们对语言的使用也应当注意,因为演员是根据剧本上的语言来进行表演的。”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汉语规范化问题座谈会》,《中国语文》,1955年第37期。因此,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集中修改抗战历史剧等旧作,主要着眼于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减少了“古语”,重视“今语”。历史剧语言变得简洁凝练,有时甚至削弱了营造“古代的幻象”效果。但同时,他也为人民大众提供了规范化的通用语版的文艺经典,是文艺大众化的新起点。
结语
郭沫若的抗战历史剧《虎符》的创作与修改,生动地诠释了他的“古今共通”历史剧语言原则,及其内在机制中“古语”与“今语”辩证发展关系。一方面,我们应该高度评价郭沫若对于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因为郭沫若不仅使历史剧发挥了抗战宣传的巨大的实际功效,呈现出历史剧语言艺术的新高度,而且经过几番修改,提供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艺经典。另一方面,“古今共通”这一语言原则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并非一劳永逸地完成,国家通用语与古文、方言和外语的互动,将一直激发包括历史剧在内的文学语言的不断创新。如何面向时代选取具有“古今共通”效果的语言,如何达到“古语”与“今语”的动态平衡,对于当下话剧历史剧和影视历史剧而言,不失为提升艺术魅力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