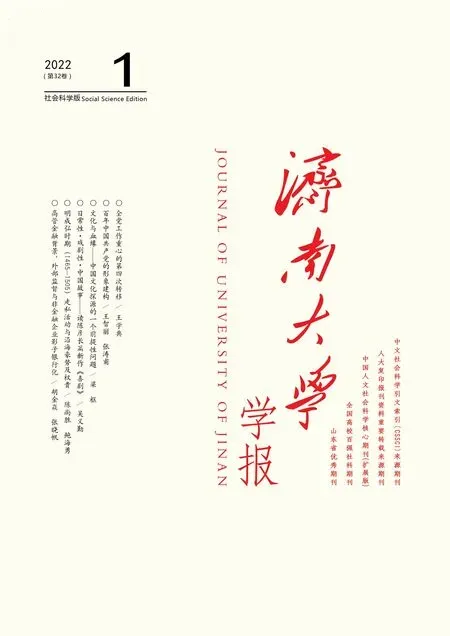十八世纪意大利的主权性论战:管辖权之争
赵明晨,宋协娜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103)
17到18世纪意大利的“主权性论战”与发生在东方的“中国礼仪之争”,一起构成了主权时代关于主权性论争的前现代政治话语和历史叙事。作为一个秩序性理想和观念的主权,诞生于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教权与王权或自治权之间的斗争中,或者说诞生于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其在现代早期的话语形式,先后出现了以让·博丹为代表的君主绝对主义范式、以詹姆斯六世为代表的神性王权主义范式和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范式,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反对教皇至上主义和普世教会绝对权力,以使本土君主个人或共同体获得至高性权力,从而削弱或解构作为外部至高权威的罗马绝对权力和世俗管辖权。中欧新教改革、英国圣公会运动和法国高卢主义,这些教会民族化的发展进程,使主权权利走出了中世纪“双剑”桎梏,特别是三十年宗教战争后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确立了现代国际秩序的“主权性”特征,标志着神权世界的瓦解。然而,伴随新教改革和主权原则确立后出现神圣罗马帝国的民族化——德意志化趋势,“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中欧政教合作体系结束(尽管其中始终充斥着权力争斗),教皇国转而借助正处于海外殖民扩张的17、18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国的民族国家力量,加快了在全球传教并重构“世界帝国”的步伐。在这段时间里,天主教不仅试图收复因新教改革导致的失地,他们还寻求使分裂的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在全球探索和殖民扩张中遇到的民族和人民皈依①Celeste McNamara,The Bishop's Burden:Reforming the Catholic Church in Early Modern Italy,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20,p.213.。在这种背景下,旨在反对宗教改革和扩大天主教势力的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the Paris Foreign Society)等宗教组织的兴起,往往被认为是“从原本那些支持海外传教的君主手中接过了使命”②Joseph Griffin,“The Sacred 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Its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Antecedents,”in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s,1450–1800,J.S.Cummins(ed.),Aldershot:Ashgate Variorum,1997,pp.57–95.。1700年克莱门十一世上任,奉行更加激进的天主教扩张,向世界更遥远的地方派遣传教士,东方的“中国礼仪之争”与西方以“管辖权之争”为特征的意大利主权性辩论愈演愈烈。作为本质上的主权性冲突,内含教皇权的论战实际上象征着罗马教皇国超越原有的天主教领域,以构筑“天主教地缘政治秩序(Catholic geopolitical order)”③Noel Malcolm,Agentsof Empire:Knights,Corsairs,Jesuitsand Spiesin the Sixteenth-Century Mediterranean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300.。
一、“管辖权之争”:“主权性论战”的范式问题
在17-18世纪欧洲论争场中的东方“中国礼仪之争”,实际上是以经院哲学为基础的神学政治对东方以礼制为基础的伦理政治的范式性挑战。无论是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罗马教廷,还是耶稣会在法国的反对者,如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及詹森主义者如帕斯卡尔,天主教各派别,都围绕以“敬天”“祭祖”“历史”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礼仪、习惯的辩论、适应、“索隐主义”④David E.Mungello,Leibniz and Confucianism:The Search for Accord,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7,pp.39-68.或反对,甚至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史之中加以解释⑤[法]李明(Le comte):《中国近事报道》,郭强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59页。。这种神学政治对东方伦理政治范式的挑战,内含着基督教世界的至高权威性——教皇至上主义,即罗马教廷所坚持的普世至高性地位:上帝不仅把意大利托付给了罗马教皇,不仅把欧洲托付给了他,还把非洲和亚洲都托付给了他,“万国服从你的权柄,跟从你的信仰(totius scilicet universa regna tuae subiecti potestati,tuaeque fidei commisit)”⑥Paolo Giustiniani,Pietro Quirini,“B.Pauli Iustiniani Et Petri Quirini Eremitarum Camaldulensium Libellusad Leo⁃nem X Pontificem Maximum,”in Annales Camaldulenses ordinis Sancti Benedicti,9,Anselmo Costadoni,Giovanni-Benedetto Mittarelli(ed).Venice:Aere Monasterii Sancti Michaelis de Muriano,1773,p.617.。然而,在前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之中,皇权、礼法、朝贡之中蕴含着特有的“主权性”权力秩序,即以“天下”“四海”“海外”“天子”“君臣”“华夷”的礼序践行,来实现着东方固有的君主主权——以“皇权”至高性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欧洲论争场域中的东方“中国礼仪之争”不断演进,从适应政策到18世纪罗马教皇的绝对主义,从外部强加于东方主权之上,最终导致双方最高权力的介入和禁教令的颁布。此后,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甚至包括德国浪漫主义者赫尔德,则跳脱了罗马绝对主义权威和普遍历史范畴,从相对主义的自然法视野和真实的民族史中,对这段论争进行了新的理解——一种学术化和客观化的方式。
在欧洲业已进入主权时代的政治意识、话语和环境中,关于中国和意大利的辩论话语在彼此之间,以及两者与同时代的英、法话语范式之间显示出显著的不同步性、非对称性,这体现了意大利和东方的既有历史特征,也反映了主权话语和观念体系固有的“范式性差异”。在东方,它是以“礼序”话语为特征的,在意大利则表现为“管辖权”问题。这是由于“主权”尚未以现代性话语、权力秩序想象进入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和思想之中。主权话语的缺失,原因是复杂的,历史地看主要是:①17世纪中期的欧洲,无论是政治现实还是政治话语都已进入主权时代,但意大利此时仍呈四分五裂状态。作为天主教大本营,由于没有经历中欧那样的新教改革,更少有自然法哲学的渗透,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亚平宁半岛缺乏类似英国的现代政治话语转向,经院哲学仍然占据主导,因此也无法基于自然法学说来重构主权秩序和解构教皇权威。②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意大利统一愿景和对罗马教廷的抵制,更多的是如马基雅维利那样寄希望于强有力的地方君主,通过在天主教规范内支持君主主义的“宗教—政治”这一路径,来实现管辖权在地方君主-诸侯中的回归。由是,意大利的主权问题,就表现为一场围绕“管辖权”的教皇和世俗君主之争。
作为意大利民族意识和国家统一的重要观念基础,“管辖权”以主权性观念面貌出现,应该说是一个“后中世纪”产物。它首先是一场君主及其辩护者对罗马教廷及其辩护者的对抗,寻求脱离教廷管辖权(jurisdiction)而实现教会的世俗君主管辖权的恢复,其实他们争取的是一个天主教范式内的“有限主权”。君主管辖权与“民族教会”(National Church)相互交织,表现为一个“反罗马(Anti—Rome)”或“反教廷主义”的景观。对17-18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局势,J.O.林赛认为:“在意大利几乎每个国家的教会都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①[英]J.O.林赛:《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旧制度1713-17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页,第127页。,教会权力是所有意大利思想家和改革家无法逾越的焦点;而约拿丹·巴里(Jonathan Parry)则在周围强权介入意大利的情况下,更强调这是一个寻求作为“民族身份”或“国家地位”(nationhood)②Jonathan Parry,The Politcsof Patriotism:Englisn Liberalism,national identity and Europe,1830-1886,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21.的过程。19世纪中期意大利统一之前,作为统一基础的“主权”归属辩论,在欧洲启蒙运动背景中是以包括“詹森主义者”(Jansenist)、君主主义者(Re⁃galist)在内的“反罗马”“反教廷”作家为主力军来完成的。按照S.J.巴内特的说法,这是意大利天主教内反对派(从某种程度上)在反抗罗马人的“僭政”(tyranny)③S.J.Barnett,The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The myths of moderni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168.。然而,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哲学上的启蒙,不如说是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宗教”斗争,即“反教廷”作家与罗马教皇及其辩护者围绕着教会管辖权进行的长期辩论,是以世俗君主对教会管辖权的要求和行动为归依的。这就不同于起源地——法国的詹森主义者,他们有共同“反教廷”的启蒙思想同盟军,甚至有时还能得到希望排斥教皇而集中权力的国王的支持。意大利“反罗马”者,如“詹森主义者”,在寻求教会对于教皇的独立性之外,其必须更多地依赖意大利各地方国家君主们的政治保护和支持;其对教廷的对抗,只有与君主对领土内教会的改革具体行动相结合时,才能将天主教改革愿景变为现实,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迎合或者兑现了君主主义。所以,“反罗马”的君主管辖主义成了詹森主义者与君主主义者的共有范式。如在1722年,保罗·皮尔萨为威尼斯共和国而“支持(世俗)君主权利”、反对“教皇至上论”,认为君主的“许可”对实施教会的法规应具有权威性,并认为教士有权对教会上级领导的专横行为向世俗的统治者提出申诉④[英]J.O.林赛:《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旧制度1713-17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页,第127页。;彼得罗·詹诺内(Pietro Giannone),通过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历史阐述,表达了对18世纪仍存于罗马的中世纪教权主义的不满。他们围绕“教皇国”世俗权力的合法性、君主对教会的管辖权、教皇国领地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挑战。
二、主权性辩论者:詹森主义者
“詹森主义”(Jansenism)发源于法国,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对荷兰天主教神学家科尼利乌斯·奥托·詹森(Cornelius Otto Jansen,1585-1638)所代表的天主教内复兴运动的指称,它寻求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既认为当时天主教神学偏离正道,又反对新教救赎观,其影响波及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地区。共有这一身份范畴的人们,被称为“詹森主义者”,因他们各自所处国家现实政治和追求上的差异,并不具有同步而统一的身份定义。在法国,它从17世纪的纯粹神学教义争论发展到18世纪的党派化争论——帕斯奎尔·奎斯奈尔(Pasquier Quesnel)在17世纪末将其发展成了一个政党,它成为团结“好法国人”(good Frenchmen)、国民(nationals)或者詹森主义者(Jansenist)的力量,反对一切教皇干预法国内政,反对一切教会或王权专政、反对基于承认祭司或圣职人员中介力量的僧侣主义(sacerdotalism)个体和团体,特别是反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礼仪之争”中,作为天主教内的一个派别,其也从教义上反对中国礼仪。1759年一个匿名作者的小册子中写道:“很多自称詹森主义者,完全是出于党派精神,实际上其中一些完全不懂詹森主义的含义,他们仅仅出于对耶稣会士(Jesuits)的仇恨,出于对教皇克莱门十一世通谕(Unigenitus Dei Filius,1713)毕恭毕敬的深恶痛绝。”①Dale Van Kley,The Jansenist and Expulsion of the Jesuits from France 1757-176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6.因此,事实上18世纪实现政治转向的詹森主义失去了神学焦点,其思想往往被认为是“相对琐碎的思考”②Nouvelles Ecclesiastiques,ou Memoires pour servir I'histoire de la‘bulle Unigenitus’,May 1,1759。其在谋求法国教会自主地位时往往与反对教皇至上的天主教教会自治运动(高卢主义)、君主专制主义者相耦合,然而形成短暂一致之后,许多詹森派想要继续推行某种形式的君主立宪制,寻求削弱君权对教会的干预,从而在实际中获得更大的教会自由时,便被理解为是对波旁王朝专制主义的极大挑战。于是,路易十四放弃了1682年限制教皇权力的原则,转而与仇视詹森派的罗马教廷结成联盟;与此同时,詹森主义者正与以巴黎高等法院为中心、反对国王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1730年路易十四将谴责“詹森主义”的1713年教皇通谕颁布为法律,詹森主义在法国开始式微。
詹森主义者与启蒙思想家虽然共享了某些理念,如一致蔑视中世纪的“教皇至上”(Papalism),按照R·W·格里夫斯的说法就是:“轻率的改革家们”主张维护君主的权力,因而与理性主义的国家至上论思想倾向十分吻合③[英]J.O.林赛:《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旧制度1713-1763年》,第125页,第121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权威是他们的价值终点,以天主教会自由和权威为归宿的他们,与世俗化的欧洲启蒙价值实际上有着巨大的分野,如对待自然神论等议题。换言之,即使法国詹森主义确实代表了很多人的“政治—宗教”观点,并认为自己在挑战波旁王朝极端主义过程中,保护了其所认为的“人民”和高卢教会的传统“自由”——正如法国主教们要求与罗马教廷共同担任宗教法官时所言“我们只是要求不要让罗马教廷有机会认为我们仅仅是他命令的执行者而已”④[英]J.O.林赛:《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旧制度1713-1763年》,第125页,第121页。,但对于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和卢梭们所处的18世纪自然法哲学和权利政治话语而言,无论是反教皇,或者为君主立宪,法国詹森主义者在针对罗马教廷和法国君主两个权威时,所追求的“独立”与“自由”的范畴仍然是教会式的,它已然站在了基于现代自由的对立面,因此,它往往被视为保守的“宗教狂热者”。
詹森主义的意大利范式却不存在它在法国的保守性特征,S.J.巴内特甚至将之视为“先进的”⑤S.J.Barnett,The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The myths of moderni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169.。这种相对的“先进性”,是基于管辖主权教会(sovereign churches)的君主主义对罗马神权政治的先进性。在教义上,意大利詹森主义者对经院哲学充满蔑视,这从皮斯托亚会议(the Synod of Pistoia)上便体现出来,他们往往沉湎于研究圣经和原初传统,似乎很少接受圣奥古斯丁之后的任何权威学说①Charles A.Bolton,Church Reformin 18th Century Italy,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9,p.23.。在政治方面,缺乏强大中央权力的意大利半岛,詹森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反对专制君主对教会的权利,而是支持君主共同反对“罗马教廷”,后者被认为是推翻了早期教会的“国家—教会”(State–Church)传统,进而使意大利落入到“封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对于詹森主义者而言,教会解放在意大利半岛还处于第一阶段,就是使封建贵族形成一个可以对抗罗马的君主力量,而不是沦为“罗马的附庸”。对此,当代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尼德托·克罗齐就直接指出:“那些大大小小的贵族男爵,几乎使臣民无法服从于君主国,使得每处封地都成了一个微型国家”②[意]克罗齐:《那不勒斯王国史》,王天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因而,君主或主权者对罗马教廷挑战的意义,在意大利半岛“多中心(polycentric)”政治现实和周边强权干预的环境中尤为突出。在18世纪由众多政治实体构成的、以罗马教皇国为中心的“教会——国家”形态呈现于意大利,并开始出现权力首先向各个世俗君主集中的进程。来自法国“反暴政”的术语进入到政治环境截然不同的意大利以后,发生了转义。诞生于法国宗教战争的《论反抗暴君的自由》(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一书,原是为反对法国的天主教国王而创作,反映了经过宗教改革后已经接受了人民主权理论(非世俗的)的新教徒,对奉行绝对主义专制的“暴君”的反抗,是一次基于契约优先(非世俗的)的“人民全体高于国王”③[法]拉博埃西,布鲁图斯:《反暴君论》,曹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页。的宣示;然而,类似“暴政”概念,在意大利却不是指向专制主义统治者,而是在詹森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与教皇国激烈交锋中,指向了其所反对的旧政权——中世纪式的罗马教皇国及其神权政体或教皇君主制,甚至于其对欧洲教会的普世统治。尽管有批评者认为,意大利詹森主义中的天主教启蒙很可能使教会更加依赖国家,严重损害教会的独立性④S.J.Miller,Portugal and Romec.1748–1830:An Aspect of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Rome:UniversitàGrego⁃riana Editrice,1978,pp.2-4.,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意大利,支持“国家(state)”,甚至是君主绝对主义权力,甚至在教会内都被认为是进步的,而不是相反,这是使意大利半岛脱离中世纪、趋向大陆普遍情况的重要一步。回顾意大利文献,文艺复兴时期以降,佛罗伦萨人但丁的《君主国》(1314)、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和平保卫者》(1324),以及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13),及至18世纪摩德纳的洛多维科·穆拉托里(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所写的“良善君主(buoni principi,1749)”,均将摆脱后罗马帝国的分裂和战争状态、实现意大利半岛和平、统一及政制理想,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身上,这一点在意大利是人文主义复兴以来的传统,隐含了某种程度的“反罗马”属性。
18世纪的詹森主义者对罗马教皇专制和迷信的批评,并未逾越天主教本身。这是由于任何逾越天主教义本身的论证都有可能使自身被视为异端而受到迫害。1715年,保罗·亚历山德罗·马菲(Paolo Alessandro Maffei)注意到,在罗马,“任何被称为学者(Scholar)的人,都会立即获得异教徒的头衔和声誉”⑤E.Morelli(ed),Leletteredi Benedetto XIVal Card.De Tencin.Vol.2(1748-1752).Roma:Edizionidi Storia e Let⁃teratura,1965,p.193.。一元化仍然是当时意大利的主要意识形态,任何相对主义的知识在绝对主义的教义面前都是邪说。同时,因为不同于英国和法国,自然神论和新教伦理在意大利是缺失的,对于教权改革的讨论话语和论据,也就只能集中于天主教范式之内,意大利还缺乏足够的宗教宽容或者更多的讨论范式。对此,一些游历外国的意大利人很快就进行了比较。意大利著名学者彼得罗·维里(Pietro Verri)于1766至1767年间对伦敦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访问,他将英国与意大利半岛相比较,并对这个明显宽容的社会运行方式进行了报道:“这里甚至没有人谈论宗教”。在1766年12月21日他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不同教派的成员如何每天一起做生意,而不必考虑和谈论他们之间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于是,对英国“自由”(liberta)的印象,就保存在了其关于出版、信仰和讨论等方面的记叙中①G.Gaspari(ed),Viaggio a Parigie Londra(1766–1767):Carteggio di Pietro e Alessandro Verri,Milan:Adelphi Edizioni,1980,pp.168-169.,也延伸到了如何看待政治问题上。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当时意大利地区广泛的宗教审判和严厉的图书审查制度与现实,“禁书目录”(Indices of Prohibited Books)定期列出天主教徒不得阅读的书目②Ole Peter Grell,Roy Porter:Toleration in Enlightenment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31.。意大利地区的“反罗马”争论者,必须相当谨慎地避免涉及神学教义的议题。因此,尽管有评论者将詹森主义者看作是天主教内的“穿长袍的加尔文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更像S.J.米勒所描述的那样:“詹森派只是一个天主教启蒙的‘极端主义派别’”③S.J.Miller,Portugal and Romec.1748–1830:An Aspect of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Rome:UniversitàGrego⁃riana Editrice,1978,pp.2-3.。
三、主权性论战的焦点:对罗马“篡权论”的诘难
“篡权(usurpation)论”是“反罗马”或“反教廷”者主权性论战的重要焦点,是对罗马教皇世俗权利批判的主要形态,其核心是谴责中世纪和当代的教皇篡夺了国王的神圣管辖权、插手国家的世俗事务、积极寻求开拓世俗领域的权力并形成了君主专制形式的教皇国(Papal States)。科林·莫里斯(Colin Morris)更是将这段历史概念化为“教皇君主制”(Papal Monarchy)的历史,认为其与“国家权力的无效性”是相适并存的④Colin Morris,The Papal Monarchy:The western church from 1050to 12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教皇国由教廷以中世纪盛行的方式统治,教会等级制度也作为教皇的世俗附庸:由主教统治的公使馆(legations,设置于主要城市和地区)和代表团(delegations,设置于次要地区)的枢机主教。这一世俗权力往往是建立在“钥匙的统治”基础上的,一如红衣主教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在其1869年《教牧书信》中所写的:“最高和最终的权力,无论是在管辖权上还是在信仰上,或者是司法之钥(clavis jurisdictionis)和知识之钥(clavis scientiae),首先并且永远地交付给了彼得,在他身上……他的继任者(教皇)。”⑤Henry Edward Manning,The Oecumenical Council and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Roman Pontiff:APastoral Letter to the Clergy,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869,p.147.同样,主教加塞尔(Bishop Gasser)在梵蒂冈第一次会议(Vatican Council I)上代表发言时,提到“教皇的最高职权含有管辖权,因为教皇有两把钥匙,一把是知识的钥匙,一把是权力的钥匙⑥Jean-Pierre Torrell,La Théologie de l'épiscopat au premier concile du Vatican,Paris:Les Editions du Cerf,1961,p.176.。“世俗统治”无论是被批判者和历史学家描绘为出于堕落和贪欲,还是被企图力证有其客观的需求,动荡的中世纪历史中,如果没有独占的领土和财富,教廷在半岛上的安全性和政治影响力就会减少;然而,对其管辖的广阔土地、遍及欧洲的有组织的上层结构及蕴含其中的排他性权利、横跨欧洲的教会财产等的垄断,同时也构成了罗马及其意识形态的致命弱点。本质上,具有王权至上主义者(或称作君主主义)倾向的意大利作家,对罗马神权政治的争论和对长期以来教廷对半岛不同部分的宗主权(suzerainty)主张和统治现实的反驳,均是意大利君主们在其自有领地的教会内为收回“失去的管辖权(lost jurisdictional rights)”而辩护的组成部分①S.J.Barnett,The Temporal Imperative Criticism and Defence of Eighteenth—Century Roman Theocray,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22(2001),p.472.。在这里,他们的争论聚焦于两点:教皇世俗权威的“僭越”和君主对教会管辖权的传统。
(一)教皇对原属于君主的世俗权威是否有“僭越”或“篡权”之嫌
1.关于教皇对原属于君主的世俗权威是否“僭越”或“篡权”,往往是首先通过回归到圣经文本的解释来进行辩论的。他们批判教廷无视耶稣基督的教导:“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Regnum meumnon est de hoc mundo),而是按照古代异教(前基督时代的罗马多神崇拜)的模式,自封为祭司—国王。科西莫·阿米伊(Cosimo Amidei)就在其1768年首次出版的《教会与共和国的界限》中,对属世王国和精神王国、对一方的精神责任与另一方的世俗责任进行了绝对的区分,并认为“在一方与另一方的权力之间存在迥然差异”②Cosimo Amidei,La chiesa ela repubblica dentro iloro limiti,Firenze:Maspero Libri Antichi,1768,p.16.。然而,这一指控,在意大利半岛产生的冲击力并不够强大,因为教皇国已经通过天主教教义强化了世俗统治的神圣性基础,即关于“赐予权柄”的说教:耶稣把一个特定的权柄交给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一“钥匙的力量”以及“喂养我的羊”(Feed my sheep)的托付,被解释为:管理上帝之家,也就是教会的权力③United States Catholic Conference,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Citta del Vaticano: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2000,p.142.。其中“束缚和放松”的权力,则意味着在教会中赦免罪恶、宣布教义审判和作出纪律决定的权力。耶稣通过使徒的职事,将这权柄交给教会,特别是通过彼得的事工,他是唯一一个特别托付王国钥匙的人。而在彼得之后,便是被视为其继承人的历任教皇。事实上,针对当时的此类指控,那不勒斯的尤塞比乌·斯科蒂(Marcello Eusebio Scott)以“教皇的普世君主制”(Della Monarchia universale de’papi,1789)做出了回应,体现了其在那个时代教皇至上的政教推崇。
2.从历史中寻找教皇对法兰克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特权的“篡权”证据。一般认为,教皇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之间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756年法兰克国王佩平(Pepin)对教皇的领土捐赠(随后得到查理曼大帝的确认),从此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有两个因素构成了“两个权威”互构的核心:一是对欧洲教会的罗马管辖权进行精神辩护的需要,二是在一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多中心半岛上保持独立和安全的需要。前者使“双剑说”从埃德加国王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支持与合作的双剑”——“君士坦丁之剑”和“圣彼得之剑”,进一步发展到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的“精神与物质之剑”④Alice Chapman,The Cooperation of Sacred Authority and Temporal Power,Turnhout:Brepols Publishers n.v.,2013,p.145.,再被之后的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英诺森三世继承并发展为教皇权高于普世教会、王权为保卫教会而存在和王权附庸化的教皇至上主义,这一“僧侣主义”进程使教皇凌驾于各地教会和各王国的国王之上。后者则是因为意大利半岛地处地中海通向东方的贸易通道而常常被视为战略要地,从而被相互敌对的外部势力所争夺,先有东方的奥斯曼人,后有来自英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在南意大利的扩张,来自法国、德意志、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扩张,一直持续到1861年统一复兴(Risorgimento)之前,该历史现实迫使罗马教廷走向官僚化和国家化。然而,“反教廷”作家反对领土化和国家化的教廷,认为其只有当教皇作为神圣罗马皇帝(从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加冕算起)的附庸——在该领土上服从于帝国意志时,才获得对帝国范围的教会某种默认的管辖。因此,倘若教皇拒绝承认帝国的统治地位(封建君主权位),其本质上就篡夺了帝国特权:是对由他加冕为唯一基督教帝国皇帝(在与教皇争夺帝国权力时,德意志帝国皇帝往往将自身权利直接溯源至上帝和查理大帝,而非圣彼得或教皇)、并被誉为“罗马人的国王”“基督教世界的现世首脑”“信徒们的世俗领袖”①[英]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8页。的“僭越”;教皇将自身霸权凌驾于现实之领土国家之上,“就像真正的世俗君主一样”,罗马教皇的领土帝国野心,使其“不放弃任何世俗的、和平或战争方案”②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Annali d’Italia(12 vols,vol.4),Milan:Venezia:Dal Premiato Stab.Di G.Antonelli ED,1744,pp.164-165.。这是中世纪以来其对奥古斯丁“双城理论”中帝国保护教会的尘世特权的“窃取”。
(二)君主对教会管辖权的传统之辩
关于君主的教会管辖权辩护,事实上是詹森主义者对教会自主性,即教会自由问题妥协的结果——追求罗马与君主的“共同管理”,这是因为继被认为异端的新教改革之后,任何在天主教内使地方教会,或者民族教会(National Church)完全排除教皇权威,例如实现主教自主选举、任命,以及限制教皇在开除教徒和纪律约束方面的权力,都可能触发异端化的反应。在1720年代,阿尔贝托·拉蒂卡蒂(Alberto Radicati)就在这样一个管辖权之争背景下对宗教裁判所发起了攻击,他声称,罗马过去曾使用宗教迫害,动用宗教法庭和教廷司法垄断对教会事务的管理,以牺牲国家(State)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权力③A.Radicati di Passerano,“Discours VIII:Recueil de pieces curieuses,”in Politici ed economisti del primo Settecento:Dal Muratorial Cesarotti,Roberto Ajello(ed),Milano:R.Ricciardi,1978,pp.51–68.。对于罗马教廷僭越国家权利的此类指控,教会方面往往凭借“彼得教义”,将那些反对教皇垄断教会事务绝对权威的行为视为反基督的挑战。正如奥尔西(Gi⁃useppe Agostino Orsi)枢机主教,在其《关于罗马教皇对普世会议(或大公会议)的绝对权威》中提醒读者的那样,基督已将天堂的钥匙授予了他的罗马主教继任者④Cardinal Orsi,Della infallibilità,e dell'autoritàdel Romano pontefice sopra i concilii ecumenici(2 vols,vol.1),Roma:Pagliarini Mercanti Libraria Pasquino,1741,pp.5-6.;此外,教廷辩论家乔瓦尼·马尔凯蒂(Giovanni Marchetti),也在其《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威》中提及,教皇在教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罗马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可以追溯到耶稣本人⑤Giovanni Marchetti(Archbishop of Ancyra),L’Autoritàsuprema del romano pontefice,Roma:nella stamperia di G.Zempel,1789,‘Al Lettore’,pp.5-6.。因而,对于詹森主义者而言,如何在不引发教义反击和宗教迫害的情况下,对君主的教会管辖权进行辩护,从而迎合世俗君主的权力扩张愿望,这成为一个课题:他们选择了引入君主管辖权的竞争,力辩“共同管辖”的正当性。
对君主管辖教会的历史传统进行发掘和叙述,不仅可以避免挑战普遍历史和罗马绝对主义权威,而且能开辟“经验历史”的辩论场:围绕基督从未把君主从教会管理中排除出去的历史证明。洛多维科·穆拉托里将君主与罗马教廷对教会的共同管理进行了历史追溯,他汇编了一份历史记录,认为中世纪早期的教皇们利用君士坦丁堡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逐渐减少的事实作为借口,篡夺了帝国的统治权,对罗马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教皇统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在拜占庭权力无法保护的意大利西部,教皇国成为教会自组织化的一个结果)。但他谨慎地断言,直到8世纪中叶,教皇和罗马人民仍然服从君士坦丁堡,当选教皇继续受到皇帝的确认。从这个角度来看,教皇只是一个代表君士坦丁堡而在罗马的管理者,充其量,教皇在默认(因拜占庭对该地区的权力缺席)情况下获得了罗马及其周围地区的高度管辖权,但从未获得合法统治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国家理所当然地在最高层面干预教会管理,统治者仍然保有干预教会司法事务的权利,对教会矫正及其管理的干预是它们的职责,并认为,这种神圣赋予的合作关系因中世纪教皇世俗权力扩张而终结①S.J.Barnett.The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The myths of moderni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173.。他将这种谬误归咎于过去的教皇和后世默认的谬误传承,而不是归咎于当时的教廷,希冀以这种宽容姿态换取时任教皇对历史性谬误的承认。这种修辞避开了可能的异端指控:这些管辖权是由于罗马教廷篡夺了世俗统治权、并将教廷和欧洲教会从世俗统治(secular rule)中分离出来而失去的,对于世俗权利的让渡和共同管辖权的恢复,仅仅是回归早期教会传统。而事实上,教皇们对此确实没有提出抗议②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Dissertazioni sopra le antichitàitaliane(3 vols,vol.3),Milano:a spese di Giambatista Pasquali,1751,pp.460-468.。作为君主(主权者)享有教堂管理权的历史佐证的追溯,在穆拉托里看来,这捍卫了摩德纳君主关于在摩德纳教会内的管辖权主张,摩德纳统治者收回司法权或管辖权是正当的。
(三)管辖权之争的衍化:世俗事务的君主管辖权利
管辖权之争还从君主对教会的管辖权,发展到君主对世俗事务的管辖权上。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意大利这一争论日益激烈,詹诺内始终坚持世俗权力的“管辖主义”立场:“教会曾经并且仍然存在于共和国中,而非共和国存在于教会中”③Pietro Giannone,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vol.1),Napoli:Nella Stamperia DI GIOVANNI GRAVIEE,1770,p.62.,他要求减少教会法庭,取消任何形式的宗教裁判。雷吉纳尔多·坦季尼(Reginaldo Tanzini)则表现得更激进一些,他于1776年在佛罗伦萨发表了一篇充分展示意大利改革时代精神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真理开始以其真正原则为人所知的时代,人们对事物的审视不再基于偏见,人们正试图界定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界限。”④Gazetta ecclesiastica,ossia Raccolta di notizie e documenti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corrente della Chiesa dell'anno 1776.Rod.33-34.无论是婚姻契约还是财产,其管辖权都应来自国家,而非教廷。他认为国家有权控制或改造修道院,并建议将更多修道院改造成学校和医院,因为教会拥有财产的合法性来源不是源自神圣权威,而是统治者的善意和馈赠。因此,当统治者给予其这些权利时,他也有权收回或限制它们。西庇奥·德·里奇(Scipio dei Riccic)受朱利奥·鲁塞莱(Giulio Rucellai)的影响——1734年到1778年其在托斯卡纳进行了许多重大政治改革,也对托斯卡纳仍然盛行的中世纪封建法和习俗进行了彻底改变,冒着巨大的反对,废除了神职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⑤Charles A.Bolton,Chruch Reform in 18th Century Italy(The Synod of Pistoia,1786),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9,p.5.。面对世俗管辖权的改革浪潮和反对宗教裁判的国家主义思潮中,作为教皇国法恩扎(Faenza)教区的宗教裁判官托马索·文森佐·帕尼(Tommaso Vin⁃cenzo Pani),于178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对异教徒的惩罚与神圣宗教裁判所的审判》(Della Pu⁃nizione degli eretici e del Tribunale della Santa Inquizione)的文章对宗教裁判进行辩护,他意在阐明这样一个立场:如果没有积极的宗教裁判所,天主教信仰的存亡将处于危险之中,既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将会崩溃。基于此,他抨击了当时批评宗教裁判所工作的作家们,将他们称之为“可笑的创新者”。这与彼得罗·维里的观点相对立,后者在18世纪末回忆认为,罗马“建立一个独立于君主的管辖权,可以使用武力、监禁、酷刑和没收财物,而在这些情况下,君主根本不起作用。这是荒谬的。”⑥P.Verri,“Memoria cronologica dei cambiamenti pubblici dello stato di Milano 1750–1791,”in Lettere inediti di Pietro e Alessandro Verri(vol.IV),Carlo Casati(ed),Milano:G.Galli,1879,pp.360-361.威尼斯、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等主权实体(sovereign entities,它们有的是城市共和国,有的是王国)的“反教廷”作家,反对罗马对其“民族教会”的全面管辖权(full Roman jurisdiction),冒着罗马宗教裁判所指控的风险,撰写并发表一些著作,与居住在教皇国或其他与罗马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国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相比,他们的写作和出版往往具有相对的自由。例如,在18世纪,百科全书(Encyclopèdie,狄德罗)在1759年被列入教皇禁书目录后,威尼斯却从未将其禁止,它的意大利译本就出自那里。
四、领土场域的君主管辖权辩护
詹森主义者为“反罗马”、争取教会的君主管辖权辩护,与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反罗马”者具有了价值耦合,不同的是后者更加具有民族或国家意识,即便他们仍然留在教会圈子里,以获得更好的宽容和安全。因为,正如N.戴维森(Davidson)所表达的那样:“从1690年代的瓦莱塔(Valletta)到1780年代著有《立法科学》(The Science of Legislation)的盖塔诺·费朗杰里(Gaetano Filangieri),启蒙运动的作者也仅仅是对那些既接受上帝的存在,又接受善恶有报的来世观念之人保持宽容。”①Nicholas Davidson,“Toleration in Enlightenment Italy,”in Toleration in Enlightenment Europe,Ole Peter Grell,Roy Porter(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237.因而,在一个普遍天主教徒及绝对主义秩序中,自我的异端化是无法想象的。
(一)王国领地管辖之“善”的辩论与现实局限性
倘若大多数挑战者都努力避开对教皇攻击的话,那不勒斯的皮埃特罗·詹诺内则是一个例外,他在1723年完成的《那不勒斯王国史》(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也译作《那不勒斯王国民间史》)中,开门见山写道:“我要写的那不勒斯王国史,不是为了让读者听到战役的喧嚣和武器的轰鸣,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已使那不勒斯成了战争的舞台。……(我所要写的)将是整个文明的历史,所以,如果没错的话,它将是一部论述高贵王国的政治史、法律史和风俗史。”②[意]克罗齐:《那不勒斯王国史》,第144页,第142页,第159页。詹诺内在关于教会司法权或管辖权的历史部分中将其勾勒出来,作为一个真正的“王国的历史”,不是“国王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对涉及整个欧洲共同真理的普遍描述,而是那不勒斯土地上人们的特殊史——这一摆脱普遍主义历史的相对主义意识,并非如法国宫廷布道师、君权神授的集大成者博絮埃(Bossuet)兼顾普遍圣史和国别史那样去修复两者的裂痕:一边是他心目中的唯一的、历史性的信仰和教会,一边是他心目中唯一的、由上帝支持的君主制——法兰西君主制③[法]雷努姆:波舒哀的《论普遍历史》,参见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蒋开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詹诺内在绝对主义的罗马,制造出一个主体相对性的裂痕,这早于伏尔泰的《风俗论》而具有民族性的相对主义视野。对此,孟德斯鸠也曾在其笔记中表示,希望能写下“像詹诺内的那不勒斯王国史一样的法国王朝文明史。”④[意]克罗齐:《那不勒斯王国史》,第144页,第142页,第159页。这样一个将那不勒斯从普遍救赎史中解放出来的独立叙事,催生出了统治史的民族传统和记忆。再如,1734年,A·杰诺韦西在其《贸易课程》中写道:“把国王、和平与我们的真正自由、伟大还给王国,是上帝的意愿,如果没有一个自己的王国,任何人民都不能说自己是自由的。就人类历史而言,一个被奴役的省份是不会出名的。”⑤[意]克罗齐:《那不勒斯王国史》,第144页,第142页,第159页。对王国之善的理想化与有意识化,其本质上是因为君主专制成为满足一些要求的最佳工具,就如但丁(Dante)认为“君主或皇帝('Monarch'or'Emperor')是一国和平和世界幸福(well-being)之所系”⑥Dante,Monarchy,Prue Shaw(trans.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11.,也如马基雅维利赋予君主获取和维持政权的“能力”(Virtù)⑦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Peter Bondanella(trans.a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7.以“德性”,王国或君主国承担着当时众人致善的职责。在18世纪意大利半岛各国内,一方是希望主权扩权的君主利益,一方是希望减轻赋税、增加财富、司法公正的(非贵族)臣民利益。G·阿尔金托与詹诺内等人,呼吁将领地交付国民,教会司法权中的庇护权和其他过分的权力应得到限制,后者更是认为,不经王权承认的开除教籍于法无效,书籍审查只能由王权严格操作,税收应加于教士的所有财产,禁止教士再购买土地,禁止给付“什一税”等。当时,教会财产在各国土地和财富中占有超高比重,在皮特蒙德,教会成为君主扩税的第一阻碍,最富饶的土地有大约1/3掌握在神职人员和贵族手中,他们还享有80%以上的免税特权①[英]克里斯托弗·达根:《剑桥意大利史》,邵嘉骏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77-78页。;在阿格罗罗马诺(Agro Romano)61%的土地掌握在113个家族中,在那不勒斯一度有将近八成的财富被教会直接或间接占有。这些封建贵族与罗马教廷交织在一起,阻碍了君主领土扩张和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步伐,同时封建特权——免税,也使得国家征税落到了底层臣民头上,改革就具有了要求减轻赋税的底层动力。帕尔马公国首席大臣杜蒂洛(Du Tillot),在1764年禁止(教会寺院土地或不动产)死手保有(mortmain),就在于因教会占有造成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市场流动性,这也反映了新兴商业阶层对重新分配财富的愿望。对于詹诺内而言,教皇篡夺世俗管辖权和教会暴政,使基督徒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宗教欺诈之中。教皇为了积累权力和财富而腐化了教义,并培养了迷信。他们发明了炼狱(purgato⁃ry)的概念,使罗马教皇找到了通向因(信徒)轻信而取之不尽的财富天堂之门——贩卖赎罪券;由于类似贪婪的动机,教皇们还恢复了对异教徒形象的崇拜——与神圣教义等教会事务相比,教皇和主教对巨大财富和世俗统治的世俗事务反而更加熟练②Pietro Giannone,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vol.1),Napoli:Nella Stamperia DI GIOVANNI GRAVIEE,1770,p.461.。这一王国管辖之“善”与教皇管辖之“恶”,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王国管辖之善和教皇管辖之恶的论述,戳中了几个世纪以来教皇国自身的异端化本质,因而,极易激起罗马教廷的愤怒,使为王国辩护的作者常常处于地方君主和罗马教廷博弈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不仅在于其论证是否触犯了教义和教廷,更在于其所代表的君主能否给其庇护。詹诺内就在罗马给那不勒斯的施压中,逃离了那不勒斯,但最终成了宗教裁判所的目标和受害者。意大利的其他国家,如曼图亚公国、米兰公国和帕尔马公国,在欧洲来说是小国,但相对于卢卡共和国和圣马力诺共和国来说仍然很大。在通常充满敌意的欧洲环境中,当竞争大国仍在寻求半岛上的领土和影响力时,这些小规模权力实体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战略联盟。伴随半岛上较大邻国和整个欧洲之间的力量平衡变化,半岛内部的联盟也在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导致与罗马关系的降温,或者相对较小的孤立国家可能寻求改善与罗马的关系。他们与罗马重新结盟或缓和紧张关系,将导致这些君主们对原本其支持的进步和改革臣民、辩论者不再那么包容。因此,在一个时刻面临异端指控风险的环境下,意大利各个国家的实权者、高级教士和作家均难以获得无条件的支持。用当代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话说就是,正是那些“寻求教皇保护的国王的奴性”③[意]克罗齐:《那不勒斯王国史》,第145页,第161页。,那些所谓的“王权的同道和朋友”④[意]克罗齐:《那不勒斯王国史》,第144页,第142页,第159页。,不断谋杀着王权的辩护者。因此,“反教廷”作家并非“旗手”,其所作的管辖权改革主张和辩论也不是“战斗檄文”和号召,而是只有当意大利各国君主在对教会和世俗事务管辖权采取主权化行动时,他们才能安全地发声。他们的声音是对天主教和君主改革的“伴随行为”,一种辩护和回响。例如,对酷刑进行人道主义思考的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写作《论犯罪与刑罚》时,就被认为属于这种情况,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对此评价道:“在切萨雷·贝卡里亚写下第一个字之前,法院和法律界就已经结束了酷刑”⑤O.Chadwick,“The Italian Enlightenment,”in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R.Porter and M.Teich(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99.。
(二)教皇国领地的“非法管辖”问题
对教皇国领地管辖权的论战,既是君主管辖权或者领土性君主主义辩护的新战场,也是避开更为核心的教义问题所作的辩论选择——即在更安全的领土问题上反对罗马管辖权。像米兰的彼得罗·维里兄弟,以及切萨雷·贝卡里亚就在编辑《百科全书》的意大利微型版本——《咖啡杂志》(Il Caffè,1764-66)时,就显得格外谨慎,他们努力避开宗教和教会改革的词条和话题,并拒绝了《百科全书》启蒙思想家们对其前往巴黎的邀请。同时,在长达两年、出版的一百多篇文章中,没有一篇直接攻击教会及其迷信、历史或教皇世俗统治的内容,而仅仅是将撰写放在了诸如贸易、农业、法律和科学等问题上。因此,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启蒙运动相比,意大利贵族知识分子往往被认为是徘徊于“旧封建主义特征和特权、欧洲专制主义和哈布斯堡帝国多民族多元性之间”①Giorgio Roverato,IL CAFFE',Treviso:Tipografia Longo e Zoppelli,1975,p.10.。然而,与知识分子或作家相比,大多数君主或政权的兴趣仍在于对罗马君主制展开攻击,因而他们表现出对此类作家的宽容,甚至支持、赞助,因为君主们依赖于作家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支持,以收回自身管辖领地内业已失去的君主管辖权,并阻止教廷的扩张:罗马对主权实体(sovereign states)教堂土地的主张,如罗马对帕尔马、那不勒斯等国的宗主权,以及对费拉拉、科马乔的统治权要求——即便有时仅仅停留在宣传水平上,也足以让地方君主感到担忧。因此,无论是希望收回教会主权,还是反对失去领土管辖权的君主,都支持了对教皇国领土权属的论战。
这类辩论往往是通过对教皇国早期领土的“收受”与法国国王佩平的“捐赠”的非法性指向进行的。如前所述,关于“收受”的合法性已经被天主教“彼得教义”所神圣化,任何对此的攻击,无论是对教义上的,还是对教皇世俗堕落的攻击,都被以异端化处置。所以,对领土权属的辩护,就转移到了教皇国领土溯源的佩平“捐赠”合法性上。拉文纳地区(Ravenna)——意大利东北部领土,由法国佩平国王捐赠给罗马,为领土的教皇国奠定了基础,该地区在751年被伦巴第人和佩平占领之前,它一直是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中心,754年开始被大主教控制,但从查理曼大帝(佩平之子)到兰伯特·兰贝托,北方的德意志帝国权力在该地区始终是直接和持续存在的②Veronica West-Harling,Three empires,three cities:Identity,material cultureand legitimacy in Venice,Ravenna and Rome,750-1000,Turnhout:Brepols Publishersn.v.,2015,p.235-236.。因此,对于教皇国领土主权来源的非法性辩论,出现了两个基点:一是所捐赠土地为佩平的“非法所得”,使得捐赠无效。洛多维科·穆拉托里在他的一封题为《使徒的世俗统治》的信中,展示了包括他在内的管辖权主义批评家的观点③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Osservazioni sopra una lettera intitolata:Il dominio temporale della Sede Apostolica so⁃pra la cittàdi Comacchio per lo spazio continuato di dieci secoli,distese in una lettera ad un prelato della corte di Roma,Modena:editore non identificato,1708,p.168.,他们认为教廷所主张的罗马统治权的基础——佩平的捐赠是非法的,佩平向罗马捐赠的领土和人民“不是他的”,征服得来的土地并不足以说明其财产合法性。二是教皇窃取了拉文纳土地的管辖权。穆拉托里和大多数对罗马世俗统治持批评态度的人相信,征服后,佩平和他的加洛林王朝继承者对其捐赠的领土一直保持着高度统治权,管辖权并不属于教皇,而是仍然属于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们。
对于捐赠土地非法性和拉文纳地区的权属争论,罗马方面进行了回应。红衣主教奥尔西在《罗马教皇世俗主权和统治的起源》(Dell'Origine del dominio e della sovranitàtemporale de'romani pontifici)一文中声称,从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开始,希腊(拜占庭帝国)皇帝和(之后的)神圣罗马皇帝,都没有对罗马及其领土、拉文纳地区拥有(封建君主)领有权。教皇们也并未侵占东方皇帝(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皇帝)财产;相反,人民已经摆脱了东方皇帝的枷锁,按照人民的意愿,将自己置于罗马主教——基督代理人的统治之下。对于奥尔西和其他支持教廷作家而言,佩平的捐赠确实是自有产权(Freehold)的馈赠。因此,在竭力维护其世俗统治权时,罗马并没有践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世俗权利。相反,它只是捍卫其天赋权利。由于罗马主教被认为是圣彼得的继任者,教皇世俗权力由此产生:为答谢罗马的神圣恩典而进行的领土捐赠和一个善意的政治回报①Giuseppe Agostino Orsi,F.Filippo Angelico Becchetti,Storia ecclesiastica,Roma:nella stamperia,ed a spese di Paolo Giunchi,1780,p.6.。换言之,当法兰克王国转向帝国扩张时,它寻求了来自罗马的意识形态支持——一种被神圣加冕的基督教帝国。因而,佩平捐赠领土作为世俗政治视域中的交易,被罗马教义内化为“神意使然”。历史事实说明,除非冒着成为异端的风险,进行超越教义话语、转换范式的哲学批判——如英、法民族国家和主权观念诞生过程中的自然法范式,否则,天主教义范式内的质疑和辩论,都会得到相似的回应。
(三)对教皇国领土主张的反驳与回应
除了教皇国领地外,长期以来罗马还在谋求对更多地方,特别是对意大利的地方国家进行扩张,如对费拉拉、科马乔的控制权之争,这引起了在该地具有利益的莫德纳公爵的不满。作为对君主领土和世俗管辖权利的一般性辩护,同时也为了支持他所在的摩德纳王公的领土主张,穆拉托里写下了《教皇世俗统治的谬误》(Della Fallibilitàdei pontefici nel dominio temporale,1872年才被后人发表)②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Della Fallibilitàdei pontefici nel dominio temporale,Modena:Andrea Rossi,1872,pp.1-2.。他直截了当表明,教廷篡夺帝国世俗权利并进行世俗统治的做法绝非正确,他将主题限于挑战教皇世俗统治的范畴,而不必挑战罗马在精神上的绝对权威。除穆拉托里外,詹诺内也对领土化的教廷提出质疑,认为在中世纪,教皇不再是基督的牧师,而是成为君主,像所有君主一样,他们依附于地上的领地,使自己成为军队统帅③Alfonso Prandi,“La Storia ecclesiastica di P.Giuseppe Orsi e la sua Genesi,”Rivista di storia della Chiesa in Ita⁃lia,Vol.34(1980),pp.435-438.。翻看历史,这类指控是真实的,教皇不仅号召了十字军东征,建立起了教皇直属的骑士团国家,洗劫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而且还长期以来对德意志皇帝具有僭越之举。对于此类攻击,枢机主教奥尔西在其著作《罗马教皇对隶属于他们的世俗国家的统治与主权之起源(1742年)》④Giuseppe Agostino Orsi,Dell’originedel dominio edella sovranitàde’Romani Pontifici sopra gli stati a loro tempo⁃ralmentesoggetti:Dissertazione(1742),London:Forgotten Books,2019,pp.12-15.中,为教皇的世俗统治和领土国家合理性进行了辩护,成为18世纪最庞大的罗马教廷官方历史辩护书。与奥尔西合著该书的另一名教廷作家贝克蒂主教(Becchetti),对穆拉托里的攻击超过了其他任何作家,但是,其言论并不是仅仅针对穆拉托里而作的新阐发,而是对15-16世纪新教改革以来的系统性回应,是一个“反宗教改革”在18世纪的意大利回响。准确来讲,奥尔西和贝克蒂在十八世纪支持教廷的历史编纂学,就内容而言,是传承于甚至有时候并不超越巴罗尼乌斯(Baronius)的《教会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stici,1588-1607)。其他教廷作家,诸如朱塞佩·皮亚蒂(Giuseppe Piatti)的《罗马教皇重要编年史》(The Storia criticocronologica de’romani pontifici,Naples,1765–1768),以及安东尼奥·桑丁的《罗马教皇的历史纪年》(Vitae pontificum Romanorum ex antiquis monumentis,Parma,1739)也大多只是对巴罗尼乌斯作品的重述。用詹·马歇尔森的话说就是,“编年史”启发着全欧洲信奉天主教的“当地男爵们”(local Bar⁃onios)去书写他们家乡或地区的神圣(普遍)历史。的确,建立在“彼得磐石”的巴罗尼乌斯的“亘古不变(ever the same)”的论点是如此大行其道⑤Jan Machielsen,“An Aspiring Saint and His Work:Cesare Baronio and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Annales ecclesiastici(1588–1607),”Erudition and therepublic of letters,Vol.2(2017),p.239.,在18世纪意大利教廷作家中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结语
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论及18世纪意大利改革时所言:“无论是巩固王室专权,还是实施改革思想,第一个障碍是教会,他利用其地位和传统原则加以阻碍。国家用战争来反对教会,限制其司法权和特权,减少其收益,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附属于自己。”①[意]路易吉·萨尔雷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沈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86页。在天主教启蒙与君主主权重塑国家的二元交织进程中,意大利这一改革时代的主权性论战,为半岛各地君主对领土内的教会和世俗事务的主权性主张和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罗马教皇国势力开始式微,推动了意大利基于君主权力之上的主权统一进程,并为法国大革命后共和主义兴起做了铺垫。然而,该论战的“政治—宗教”特征也有其局限性:寄托于“良善君主”与罗马的携手合作,而不像北方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家们那样用自然法将教皇完全阻挡在新的“政治之体”之外,穆拉托里在《服从良善君主的公众幸福》(1749)中,便认为作为理想国家权力形式的君主专制主义,是根据神授的权利而来的,强大且良善的君主不应让教会篡夺他的特权,而应与教会携手合作,促进一个公正的基督教联邦②Lodovico Muratori,Della Pubblica felicità:oggetto de’buoniprincipi,In Lucca,1749,p.2,改革思想家的理想国和君主权大厦没有离开天主教教义的基石。因而,于学术而言,“主权性”论战的分析和考察,对理解启蒙时代的意大利改革意识和统一国家形成当有裨益;于现实而言,对1870年后退居梵蒂冈的教皇国的国际关系理解,以及当代中梵关系如何在坚持现代国家的主权权利、国际准则前提下,实现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亦有历史镜鉴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