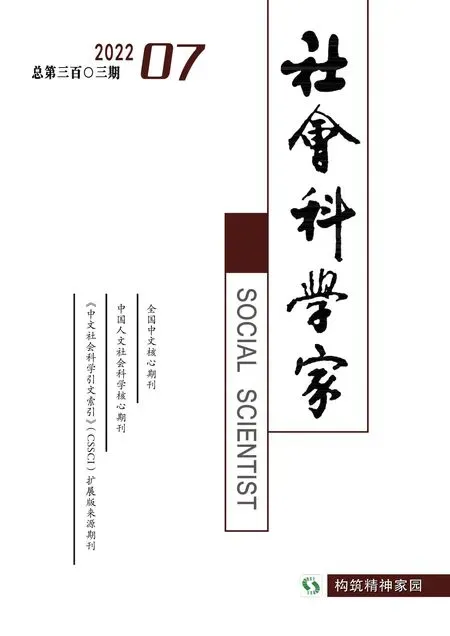出发与回返之间的生命选择
——《诗经·君子于役》的教育哲学阐释
刘铁芳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个民族在其开端,总是以某种诗性智慧开启民族之为民族的独特蕴含,也开启这个民族的教化之路,一部《诗经》开启中华文明的诗性教化之路。《诗纬·含神雾》有言:“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姓之宗,万物之户也。”《诗经》之为“经”,正是因为在“诗”之中传述着个体成人的经纶典则。孔子有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之为诗的典范,就是因为其间所敞开的无邪之生命意志。亦如《尚书·尧典》中所记舜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的指向正是超越个人之上的“道”,诗一开始就不单纯是抒写个人性情,而是为了传达人之为人之“道”。《诗》之教无疑奠定周以来民族教化的基础形式。《诗》之教的展开,乃是直接地通过《诗》之起兴,带出个体无邪的存在,进而纯化个体人心,带出个体合德的存在;而在更深的层面,则涉及个体人心教化何以可能的内在基础。换言之,《诗》之教乃是以诗性的方式开启个体成人的初始性视域,潜移默化之中,奠定个体成人之原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个体成人正是《诗》所孕育的原型在礼乐之教中的进一步展开。
一、《君子于役》:出发与回返之间的生命打开
我们来看《诗经·王风》第二首《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是一首“妻子怀念行役无期不能归家的丈夫”[2]的诗歌。这里的“君子”,“在当时统指贵族阶层的人物,但诗中‘君子’的家中养着鸡和牛羊之类,地位又不会很高,大概他只是一位武士”[3]。因为有“鸡栖于埘”“羊牛下来”,这里的贵族一般也是指底层的贵族。“君子于役”的“役”,没有确指,“大多数情况下,应是指去边地戍防”[4]。君子于役,即君子在外服役。钱钟书这样分析:“君子于役,初非一端。击鼓南行,零雨西悲;六辔驰驱,四牡騑嘽;王事靡盬,仆夫况瘁。”所谓“击鼓南行,零雨西悲”,这是指士卒戍边远征者;所谓“六辔驰驱,四牡騑嘽”,这是指使臣奔走王事者;所谓“王事靡盬,仆夫况瘁”[5],这是指马夫随军劳顿者。钱钟书进一步认为,《君子于役》之“苟无饥渴”即《采薇》之“行道迟迟,载饥载渴”[5],也即妻子思念远戍丈夫的忧虑之辞,故《君子于役》乃是写妻子对远役丈夫的思念之情。如《毛诗序》云:“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亦如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曰:“妇人思夫远行无定也。”
服役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代表着个体成人的国家之维。君子服从国家需要去服役,代表着个体人生之出发。“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是一幅归家的场景,隐含着的正是对于役的君子早日回返的期待。出发的起点是家,出发是为国服役,是从家出发而朝向国的生命行动;回返乃是回返家乡,重新回到出发的地方。出发与回返之间正是家与国的相互牵连。出发是为了国的出发,同时又是寄托着回返之路的出发。出发敞开个体的现实人生,回返给予个体以温暖妥帖的意义关照。联结出发与回返的纽带正是在爱的牵挂之中展开的日常生活。出发与回返的统一正是家国一体在个体生命之中的实现。出发与回返的主体是于役的君子,目送着出发与期待着回返的是在家的思妇。在出发与回返之间,是在家之思妇与于役之君子的彼此相望,是人与人之间爱的连接。“等待,等待,这是中国最早的诗意,也是人类最原初的诗心。一个是男,一个是女,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国,一个家……简单而朴素,古老而现代”。[6]
非常有意思的是,古希腊《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讲的出征、出发,而《奥德赛》讲的则是回归,这预示着出发与回归,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伊利亚特》蕴涵的是人类生活的‘出征’模式,即那种为美而战斗而牺牲而捍卫尊严的永恒精神;而《奥德赛》则意味着‘回归’模式,即那种出征之后返回自身、返回家乡、返回情感本体的永恒眷念”。[7]出发与回归、爱与相守相望,就成为古老而现代、永恒而常新的生命主题。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提示着作与息的统一性。作就是平民个体的出发,是离家向着远方而作;息就是回返,是向着家的回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之夕矣”的特殊意义。夕阳西下,天地万物逐步归于平静,白天忙碌的生命都在回返自己的归宿。“农作的日子是辛劳的,但到了黄昏来临之际,一切都即归于平和、安谧和恬美。牛羊家禽回到圈栏,炊烟袅袅地升起,灯火温暖地跳动起来,农人和他的妻儿们聊着闲散的话题。黄昏,在大地上出现白天未有的温顺,农人以生命珍爱着的东西向他们身边归聚,这便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最平常也是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时刻”。[4]这里所传达出来的正是对生命寻求归止的期盼。《大学》引《诗经·绵蛮》有云:“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出发在外,心有所“止”。黄昏之际,正是万物归止的时刻,恰恰于役之君子了无归期,故唤起在家之思妇以无限的哀愁,所谓“暝色起愁”[5]即从此开始。
这其中所传达出来的正是传统农耕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基于自然秩序的生存方式及其价值理想。《汉书·地理志》有云:“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周先民所形成的农业传统,无疑给周人的社会发展烙上了农耕文化的印记。“传统农业社会,生活节奏单纯而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业人生的生命节奏,为大自然的生命节奏。黄昏成为一天中最为宁静的时刻,最具有家庭本真意味的时刻。人的生物节律,情感节律,心理节律,同大自然的生命节律一道,同趋于平和与安宁。于是和平与安宁生活之向往,不复仅仅来自思妇之思念中,于是《君子于役》所开创的黄昏思念,成为所谓‘最难消遣’之中国诗美感体验”[6]。正如许瑶光《再读〈诗经〉四十二首》第十四首所云:“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5]用钱钟书的说法,“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昏黄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5]。在这里,黄昏不仅仅是作为日暮之际的自然时间,同样是作为亲人回家、一家团聚的心灵时间。所谓“暝色起愁”正是暝色之中起兴个体生命的相思之情,由此而让自然时间转化成蕴含着个体生命想象的心灵时间。
二、哀而不伤:天人之际、家国之间的生命选择
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这首诗一开始就写明思妇对丈夫远方行役的关切与盼丈夫回来的思念;接下来抓住“日之夕矣”这一典型时刻,反复提及“鸡栖于埘(桀)”“羊牛下来(括)”,家畜伴随日出日落而有出有回。“太阳每天都有升起亦有落下,而有生命的人却出而无归。于一片温暖的亲切景物中,托起无限伤心,似乎整个宇宙大地,都在为有情之生命作证;整个宇宙山川,都在为思妇的情意拍和,于是思妇的心声,犹如有着一幅极为宽广深厚又极为单一纯粹的交响音乐,与之相伴与衬托。因而,思妇的思念,不仅为思妇一人之思念,而成为整个山川宇宙亘古而今的永恒思念”。[6]正是在这里,这首诗着眼于日常生活基本视域的打开,却在更宽广的视域之中关联于宇宙与生命,关联于个体在世的根本意义问题。这里所敞开的个体在世的基本问题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这里直接地提示的是个体成人的天地视域。天地作为个体成人的基本视域,并不仅仅是纯然物理性的,同时也是伦理性的,潜移默化地提示着个体成人的价值祈向。白天,鸡出来觅食,牛羊出去吃草,农夫出去劳作,傍晚一切都趋于回返。这是基于自然秩序而展开的日常生活序列。这其中,至少隐含着如下关键质素:养鸡、放羊牛,这是质朴的日常生活;黄昏之际,鸡羊牛按时回来,这是有序而安宁的日常生活;早出晚归,这是一种可期盼而充满希望的日常生活。“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就是传统农耕文明所奠定的中华文化初始阶段个体生存的基本视域,其间蕴含着个体成人的基本价值,珍视日常生活,珍惜日常生活的质朴、和谐、安宁、温馨等基本价值。
其二,“君子于役”,这是个体成人对服役于国之责任承担,“鸡栖于埘”“羊牛下来”同时又是对家的描述,由此而呈现出来的乃是个体成人的家国视域:一端是国,一端是家;“君子于役”本身乃是对国之责任担当,“君子于役”的担当同时又是对家(园)的保护;“君子于役”的最终目的是国之安宁、富足,为了家园的平安与幸福,家的平安与幸福又成为“君子于役”的内在力量。由此,家与国紧密相连。
其三,“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里所传递出来的是思妇对丈夫的无限深情,也即人与人之间的无限深情。君子行役在外,不知何时能归。思妇在家所能做的,除了悉心照料身边的事物,安顿日常生活,就是寄托无限的相思。“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勤劳的家庭主妇,黄昏时分独自操持着各种家务,一边忙着手里事情,一边却在谛听、捕捉着丈夫回家的声音”。[8]无比地期待丈夫归来,而又无法预知丈夫的归来,最后一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表明思妇设身处地地体验丈夫的处境,寄托着思妇对丈夫的无限牵挂与温暖关怀。“‘君子’既然永无归期,怎么办呢?只希望他在外面不要受饥受渴吧!在无可奈何之中,思妇没有怨怼,没有绝望,没有崩溃,借祝愿亲人,聊以安慰自己、解决自己,以‘苟无饥渴’的心愿,来结束无边的思念”。[6]这里隐含的是思妇向着丈夫整体地打开自我的生命意向,以及在这种生命意向之中所包蕴着的对丈夫的期待、理解、关心,“以亲人为重,置己身于不顾”[6],以及接纳“曷至哉”“曷其有佸”之事实后所显现出来的生命之平静与安之若素。
这里涉及民众如何看待于役问题。“风诗中有一种抗议,针对的是征役过重的虐政。农耕生活养就的民性,是安土重迁,特别怕背井离乡,脱离熟悉环境出远门。这也真是其来有自,农耕侍弄的是土地,土地是真正的‘不动产’,谁也不能把它带走,所以乡井观念也就特别强烈……可是,人民再安土重迁,国家的一些事情也得办,边疆要塞得守,一些日常征调也得有,一般农民也就难免作为战士或役夫去出差外遣。国家政治清明,做事公平,人民不习惯,也可以接受;到了末世,征役严重,人民就要抗议了。这样的声音,就记载在春秋时期的《国风》诗篇中”。[8]这首诗写于平王东迁之后,其中蕴含着人们对待于役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于役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隐约传递出人们对没有归期之于役的不满,甚至怨恨。“《诗经》中的乡土情结表现在久役的军士身上。由于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上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因此他们对于战争有种普遍的厌恶情绪,他们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9]这首诗并没有直接写行役的兵士,但亦间接而充分地写出了兵士的牵挂所在。正如《诗经·唐风·鸨羽》所言:“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亦如《诗经·小雅·出车》所写:“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如果说《君子于役》乃是站在思妇的视角来表达对征夫的关爱,那么《鸨羽》《出车》就是站在兵士的视角抒发对黍稷所代表的故土之眷念。“这些久役的兵士,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戍守在不同的地方,但他们的心灵深处,无不有农耕文化的烙印,有着对大自然节律变化的敏感和对土地由衷的眷念之情”。[9]于役固然必要,但连年征战,让人们不能种植作物,难以养家糊口,及早返乡就成了于役者迫切的生命期待。这些诗篇以真挚感人的艺术揭示了农耕文化背景中的古典先民的基本特征。“诗的内容不外爱家、想家、成家。身为战场士卒,日思夜想的却是自己那个农夫的家。诗篇中的家,有昆虫、有瓜果、有鸟儿,全然是农村的光景。他们不以征战为荣,家乡才是最让他们牵肠挂肚、愁肠百转的‘那一个’。家乡哪怕已经变为潮虫、小蜘蛛的天下,哪怕是萤火虫乱飞,野鹿乱跑,与征役的处境比,也百倍千倍地可爱。他们渴望回家继续做农夫。诗篇以杰出的艺术,展现了农耕文化所造就的先民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可称之为农耕文化造就的特有的善良”。[8]
君子于役,当归之时而不归,怨恨之情是必然的。有人认为,“诗的主题是不满徭役的沉重的,但对此并不直说,而是表现女子对在外丈夫的无限牵挂,以此显示徭役对民众的伤害。诗的格调是平静的,人物内心活动却是千回百折的。‘鸡栖’‘牛羊’的描述,使诗篇极富生活气息。其格调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来概括是十分合适的”[10]。在这里,对行役的怨恨尽管是隐在的,但无疑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如此,整个诗篇显现出来的温馨与恬静之中的无限期待与对亲人的无比牵挂,其间弥漫出来的人性与人情之美远远地超越了对现实境遇的怨恨。由此而显现出来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生命气息,正是温柔敦厚这一古典诗教精神的体现。
三、人天合一、家国一体的生命范式:个体成人的原型
孔子有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兴乃是个体置身天地之间而“感发志意”[11],观、群是个体置身社会之中而体察人事、融身他人,怨是个体抒发自我向着他人与世界的情感好恶。如果我们把《君子于役》作为一个民族发端之际的典型场景,我们就可以从中还原出古典中国之个体成人的内在基础:人天合一给予个体成人以本体性的基础;家国一体给予个体成人以现实性的社会空间之打开;个体内心向着他者的充分打开,也即作为孔子仁爱心灵之奠基,给予个体成人以内在心灵基础;基于天地自然的感兴给予个体成人以活在现实之中的价值参照,并触发个体在世的美好生命想象,由此而使得感兴成为个体成人的基本路径。
天地乃是个体成人的基础性视域,家国乃是个体成人的社会性视域,情感乃是个体成人的内在性视域。综合起来,这首诗所敞开的古典中国个体成人的基本范式,那就是以天地为基本视域而展开个体的现实人生,深情地活在家国之中,活在人与人的温暖联结之中。亦如《诗经·邶风·击鼓》所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征前夫妻告别时,面对生死聚散许下诺言,期待能携手到老。由此,个体成人的理想发生方式则是:个体活在天地时序之中,以身体感官与天地万物相遇,天地万物的变化提示着人的生活的基本范式,个体以审美感兴的方式活在天地万物的变化之中,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其中,活出自然提示于个体的和谐、秩序与安宁。在这里,感兴的基础正是人与天的内在贯通性,也即人与天的整体关联与内在一致性。由此,征战的目的乃是为了让人们深情地活在天地之中成为可能,以免出现“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击鼓》),相亲相爱的人们无法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们再来看《诗经》中的几首诗: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国风·邶风·北风》)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郑风·风雨》)
不管是“北风其凉,雨雪其雱”,还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这里所提示的都是个体生存之恶劣环境,这里的恶劣环境直接地是来自自然的,但实际上自然环境本身的恶劣乃是象征性的,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的;“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则是置身恶劣生存环境之中个人的选择,也即携手与好友同行,或者亲密之人的相遇。这里所提示的乃是置身周遭复杂天地人事之中个体生命选择路向,那就是转向他人,以人与人的温情联系来裨补天道的不足与人事的匮乏。活在天地苍茫、人事莫测之中,个体的力量有限,但我们可以凭借人与人的温情联结而获得生存的勇气。置身茫茫的天地人事之中,唯有人与人的温暖联结才是个体生命的终极依托,是个体活在复杂世界之中生命勇气的根本来源,是一个人坚定地活着的理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也成为个体在世的本体依据。这其间,隐含着的正是孔子“仁者爱人”之实践得以可能的内在心灵基础。
这里实际上还涉及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所代表的人天、人人和谐的生活理想乃是农耕文化背景之中所孕育的个体生存的基本范式,也是个体成人的根本依托。正因为如此,常年在外的兵士“且不怀归”之“归”不仅仅是回到家乡,也是回到个体生存的基础形态,亦成为个体生命的基本眷念所在。“这类一往情深地企望和平宁静的乡村生活的思想情感,在农业民族中千古不衰,所以‘安民以固邦本’就成为中国一条传之久远的治国方略;热爱故土,依恋家乡的乡土情结就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中间传承不衰”。[9]乡土不仅给人们提供了生存的基本保障,而且孕育了个体精神生活之本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经·王风》本身就是周代社会变迁的结晶。王之地在今河南洛阳地区,此地西周称雒邑,周平王率众东迁于此。《王风》篇章即来源于东周王室直属地区,之所以被称为“风”,是因为此世周天子权威下降,与诸侯无异[10]。“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3]时过境迁,社会离乱,人民难免遭遇过重徭役之苦。生逢乱世而烙印在人们心中的,正是活在天地之中而又置身家国之际,寻求以人与人之间温暖联结作为个体在世的根本依据。用孟子的说法:“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2]《诗经》本身就是一种置身天地人事之中而寻求个体生存之内在价值秩序的努力。
如果说个体成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族类生命的复演,那么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初始阶段的生命打开方式,实际上潜在地构成民族发展历程之中个体成人之初始形态。我们今天已逐步进入信息社会,离传统农业社会越来越远,但文化及其所形塑出来的生命意向乃是代代相续、绵延不绝的,这意味着我们今天依然离不开我们民族奠基阶段所敞开的生命结构,作为我们今天个体生命打开自身的基本方式,并由此而廓开个体生命意义之本源。正因为如此,《诗》才得以显现为“经”,也即经由《诗》所编织的正是民族个体生命之自我大开的经纶。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地重返《诗经》,乃是回到我们文化价值生命的起点,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之生命成长的自我回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