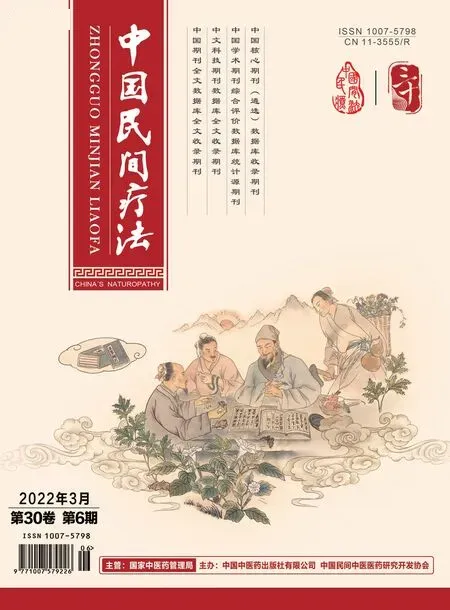基于“随其所得而攻之”浅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分期论治转化思路※
高 宇,张福鹏,郝淑兰,王晞星
(山西省中医院/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12)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在这场抗疫大战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新冠肺炎属于中医“疫病”“瘟疫”范畴,中医主张审证求因与辨证论治。全国名中医、国医大师王晞星教授亲临山西抗疫一线,为山西抗疫工作“医务人员零感染,确诊病例零死亡,痊愈患者零复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形成了山西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思路,带领团队研制开发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的新药制剂。本文基于张仲景《金匮要略》中“随其所得而攻之”理论,通过分析新冠肺炎各期病机演变及证治转化阐释王晞星教授防治疫病的思路。
1 “随其所得而攻之”是新冠肺炎辨治的理论基础
“随其所得而攻之”见于《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历代注家对此条文的释义可谓见仁见智,尤在泾在《金匮要略心典》中的“无形之邪与有形之邪相合”学说侧重于谈病因:“无形之邪入结于脏,必有所聚,水、血、痰、食,皆邪薮也。如渴者,水与热得,而热结在水,故与猪苓汤利其水,而热亦除;若有食者,食与热得,而热结在食,则承气汤下其食,而热亦去。若无所得,则无形之邪岂攻法所能去哉。”[1]病邪在里,与水、血、痰、食等有形之邪相结合,医者当随其所结合的病邪施治,“攻”即祛邪。清·张志聪提出“随其所得”乃随五脏之欲恶,“攻”之乃合五脏之五味而治,“如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渴者,脾苦湿而津液不输也,故宜用猪苓汤之甘淡”[2]。《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曰“得者,合也”,如“其”为五脏之病,“攻”指随五脏所合之腑而治,即脏病腑取,如“渴系肾脏之病,而猪苓汤利膀胱,肾合膀胱故也”[3]。无论是“随其所欲而攻之”还是“随其所合而攻之”均侧重于谈病位。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中释义的“随证而治之”理论意在谈治法:“此概言诸病在脏之属里者,治法有下之、泄之、夺之、消之、温之、和之、平之,各量轻重从宜施治,务去其邪以安其正,故引渴病以此类之。”[4]其中“所得”为病机,或气血阴阳,或内外虚实,“攻”为治法,补法、消法、下法、和法等。医者权衡“所得”不同施以相应的治法,使补虚则正扶,邪祛则正安,是仲景辨证论治思想的体现。
新冠肺炎是一个进展性的全身疾病,中医认为,该病内有脏腑气血虚弱在先,外有“疫疠之气”侵犯入体而发病,在体内与湿、热、痰、瘀、毒相合为标,并进一步导致气血受损,脏腑功能失调,标实与本虚相合为“所得”。一方面,正气亏虚是疫病是否发生及发病后病情轻重的重要因素。《黄帝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吴又可《瘟疫论》述“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另一方面,疫疠邪气侵犯人体,导致人体气、血、津、液输布失常。气机阻遏,津停成水,熏蒸酿痰成瘀,痰、瘀、热互结为毒,最终形成湿、热、痰、瘀、毒等多种病理产物。可见邪盛、正虚均为其“所得”,“所得”多端,病机传变。随着病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引起机体正邪相搏,虚实消长,机体内环境发生变化,且多种病理产物兼夹,导致病机传变,变证丛生,病势复杂,病情缠绵。“得”之相合差异,“攻”之所治不同:机体虽同受乖戾之气,但因人体阴阳、气血、体质不同,病邪从化与传变因人而异,病机也将随之变化。故在新冠肺炎各期的治疗中,应注重其“所得”及相合之“得”的转变,审各期之“因”,攻不同之“邪”,针对各期“所得”采取不同的“攻”法,促进疾病向好发展。
2 早期以湿温相合,治以透邪外达
武汉2019年冬季的气温较往年偏高且多雨,该地区新冠肺炎患者初起症状多为低热或不发热、身热不扬、干咳、神疲乏力、脘腹胀闷、恶心欲吐、纳呆、头身困重、舌淡红、苔腻、脉濡数。新感疫气,温热邪气首犯华盖之肺,肺失宣降,故干咳;此时人体正气较足,邪气尚浅,湿邪未深,邪正交争尚不剧烈,“入于膜原,伏而未发,不知不觉”(《温疫论》),故不发热或热势较低;热处湿中,湿为热遏,以致发热在里,热势不扬;湿性重浊,困于肌肉关节,故身重肢倦、乏力;湿热困脾,使脾阳不振,运化无权,则脘腹胀闷、纳呆、恶心欲吐。早期湿邪轻浅,故舌苔多为薄腻,舌色淡红,热象尚轻,故苔色黄或白。王晞星教授认为早期“所得”为温热与湿邪相合,湿重于热,病位涉及肺、胃。吴鞠通云“徒清热则湿不退,徒祛湿则热愈炽”,故治宜清热化湿、宣肺和胃,但重在祛湿,使湿祛而热无所依,选藿朴夏苓汤加减治疗。方中藿香疏风祛湿;厚朴既助藿香燥湿和中,又合二陈汤行气除满;茯苓渗湿,助水道畅通,使湿有去路;加苍术、豆蔻增祛湿化浊之力;柴胡、黄芩透散邪热;金荞麦清热解毒,祛肺卫邪气;配党参健脾以助运。诸药合用,发汗不伤津,行气不伤正,辛燥不伤阴,透化湿邪转气而出,湿邪祛则脾胃无伤,避免邪热进一步传变。
3 中期以痰毒为重,“攻”以疏导祛邪
随着病情加重,疫戾湿毒由表入里,由卫分渐入气分,正邪交争剧烈,出现身热不退或往来寒热;脾胃居于中焦,处中而受,则阳明不降,脾失升清,气机壅滞,津液不行,水不上乘,则见口渴,不欲饮水;湿浊不化,久居成痰,痰湿蕴久化热成毒,痰、湿、毒搏结,盘踞中州,阳气布达受碍,可见乏力倦怠、纳差、腹胀等症;痰邪上犯于肺,清阳阻滞,则咳嗽多痰,气短喘憋;痰毒内陷,则见舌质红或暗红,苔黄厚腻,脉滑数。钟南山院士通过尸检发现,肺没有严重的纤维化,而是有大量很黏的痰。故痰毒是新冠肺炎中期重要“所得”,早期到中期的病机由湿温犯肺胃转化为痰毒内陷中焦。故“攻”以祛痰化湿解毒为先,同时重视脾土,遵循《景岳全书》“化痰当先治脾”的理论:“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王晞星教授以千金苇茎汤为主方加减治疗。方中冬瓜子清肺化痰、解毒利水,与桃仁、薏苡仁、芦根、浙贝母合用清肺去痰排毒。豆蔻、藿香、薏苡仁芳香化湿、行气宽中,疏导中焦脾气,渗湿利水,使湿热从下焦而祛;配以牡丹皮、桃仁凉血活血,可预防肺间质纤维化[5]。药理学研究表明,加味千金苇茎汤能抑制肺炎性物质渗出,同时促进炎性渗出物吸收[6];黄芩、连翘清热解毒,可抑制病毒繁殖,减缓炎症进展[7-8]。全方以“疏”为核心,气畅则湿祛,导痰则毒减,其疫自消。
4 重症期气虚水犯,宜攻补兼施
重症期多为发病后1周,因细胞因子风暴出现如低氧血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危症,同时引起心、肝、肾等脏器损伤[9],是致死率最高的时期。中医认为,此时疫毒强烈,且机体受病毒侵袭日久,经激素、抗生素等药物治疗,肺脾气虚,水液代谢失常,气虚不能摄津,水液外渗,如大水泛滥,势不可挡,大量水液蕴积,从热化痰,痹阻肺络,引起肺实变;正虚无力“抵御外敌”,导致湿热疫毒长驱直入,进一步弥漫三焦,危害上下。气不摄津是新冠肺炎重症期病情转重的关键转折点[10]。首先,肺脾气虚,水液代谢失常,肺中阴津外渗化为痰湿,湿性黏滞,病理学可见大量的炎症细胞因子在肺内聚集,造成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及肺泡上皮细胞弥漫性损伤,大量渗出液聚集,引起级联瀑布效应,从而引发细胞因子风暴[11]。其次,痰湿蕴肺,阻遏气机,气不行血,血滞为瘀,病理学显示肺内静脉血管扩张、充血,临床可见发热、干咳、痰黄黏或痰中带血、喘憋气促、呼吸困难、紫绀、舌红或紫暗苔黄腻、脉滑数等肺痹证。再次,水饮化热,化瘀成毒,痰、瘀、毒炽盛,热入心包,蒙蔽神窍,可见神昏谵语、烦躁、脉浮大无根,进一步发展可成脱证、闭证,实属危厄。最终,水湿泛滥,“湿胜则阳微”,日久肝失疏泄,伤及元阳,真气耗散,气阴大虚,则见疲乏倦怠、纳差、呕吐不能进食、咳逆上气、胁肋疼痛、动辄气喘、水肿、泄泻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8版)》也明确提到患者存在肝细胞变性、灶性坏死伴中性粒细胞浸润,肾小球毛细血管充血及偶见节段性纤维素样坏死,肾间质充血及微血栓形成,近端小管上皮变性、部分脱落等病理改变[12]。
可见,肺脾气虚、水犯三焦为重症期关键“所得”,治疗的重点在于泻肺利水,全力保肺,兼顾心、肝、肾,以宣上、畅中、渗下、扶正为大法,选用葶苈大枣泻肺汤合三仁汤加减治疗。葶苈大枣泻肺汤可降肺气,泻肺水、肺热,疏利三焦气机。《金匮要略》云:“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张璐《千金方衍义》指出:“葶苈破水泻肺,大枣护脾通津,乃泻肺而不伤脾之法,保全母气以为向后复长肺叶之根本。”研究证实,葶苈子可通过调节炎症相关信号通路抑制细胞因子风暴的爆发,从而抵抗新冠肺炎[13]。吴鞠通《温病条辨》提出:“唯以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方中苦杏仁辛宣肺气,以开其上;豆蔻苦辛温通,以降其中;薏苡仁淡渗湿热,以利其下。三药共用,可起宣上、畅中、渗下的作用。配白茅根、生地黄、牡丹皮凉血止血,解肺络之毒,化肺络之瘀;黄芩、茵陈、五味子入肝经,防止肝损伤,并促进肝细胞再生[14-16]。全方通导三焦气机,分消痰瘀毒邪,补益肺脾气阴,利而不峻,温而不燥,扶正方可逐邪,攻补辨证施治。
5 恢复期“所得”正虚为主,扶正为“攻”之根本
处于恢复期的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治疗,体温恢复正常,呼吸道症状明显减轻,影像学检查可见肺内炎症吸收、纤维条索灶。但笔者发现仍有部分恢复期患者核酸检测未转阴,且多次复查依然为阳性,无法出院或解除隔离。该类患者常见气短,倦怠乏力,纳差,口舌干燥而渴,大便溏泄,舌淡胖、苔白,脉虚弱。此属“正虚邪恋”,正如叶天士所云:“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王晞星教授认为“正虚”在于肺脾气阴两虚,“邪恋”在于湿毒不化、余热未清,病程尚未结束。肺气损伤较重,肺主气、司呼吸的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故气短;湿热疫邪困脾日久,胃气未舒,脾气未醒,脾气亏虚,脾运化水谷精微与水液的功能仍较弱,气血生化乏源,则倦怠乏力、纳呆、便溏;湿热毒邪留恋,耗气伤津,肺胃气血不能布津,见口舌干燥而渴;气血受损,不能充脉,故脉道虚弱。此时湿热余邪与气阴两虚并存,以虚为重,宜以补肺健脾、扶助正气为主,以清涤余邪,改善预后,予补中益气汤合生脉散加减治疗。补中益气汤可补益肺气、健脾运脾,“脾胃一虚,肺气先绝”,脾为肺之母,故后天之本强健则肺不得侵,培土以生金,达到肺脾双补的功效。其中黄芪、党参不可重用,防邪热流连。生脉散一补一滋一敛,益气养阴生津。再配以砂仁、焦麦芽醒脾开胃,桑白皮、竹叶利水以消余热。全方扶正不留邪,肺脾功能得复,气血津液生化有源,湿热余邪可出,机体免疫力增强,从而促进核酸转阴,防止复发。
6 预防期以扶正固本为主“攻”
新冠肺炎病邪势强,且传染速度极快,老年人、儿童及素体虚弱、易感者,以及发热门诊与定点收治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等尤其需要注意防护。因此,保护广大易感人群,避免患病人数持续增加是防疫的关键。《灵枢·逆顺》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未病先防的理念是与疫病斗争的法宝之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正气虚弱,卫外不固,抗邪无力,疫毒邪气乘虚而入,阴平阳秘失衡,疾病发生。因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有效固护人体正气,提高人群的防病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玉屏风散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临床疗效肯定[17-18]。玉屏风散由炙黄芪、白术、防风组成,具有益气扶正、固表止汗功效。黄芪得白术则气旺表实,汗不外泄;防风走表散风邪,合黄芪、白术以益气固表祛邪。再配金银花、连翘相须为用,可起清热解毒之效。药理学研究表明,金银花、连翘配伍具有抗炎、调节免疫、解热、镇静等作用[19]。全方清养肺气,补中寓疏、散中寓补,固表不留邪,祛邪不伤正。王晞星教授提出,预防方应避免使用大剂量补益温养之品,防滋腻碍脾,亦不可使用过多辛温、苦燥或苦寒药物,防止阴虚津伤。
7 小结
追述中国历史,数千年来我国人民在与疫病千百次的斗争中,因有中医药的参与,抗疫才能成效。如今中西医协同诊治,取长补短,使疫情能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得到控制,从而缩短疫病疗程,防止病情恶化,降低瘥后人群的复发率和核酸复阳率。“随其所得而攻之”是仲景思想,在疫病防治中体现出两大优势。一是审因论治,以证为纲。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是一个动态变化、不断修正的过程,在临床中应“有是证则投是药”,关注当下病理因素与病机特点,随其性变而治之,以应对病毒种类的多样性、病毒变异性和耐药性等诸多问题。二是以人为本,治病治人。中医治疗的不仅是疫病,更注重的是治人,人与人的体质不同,所患基础疾病不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其临床症状、病机变化、病情发展、转归亦有所不同,故宜“一人一策”,万不可“一方打天下”。在疫病防治中,临床医师还应注意地域、时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笔者在临床中将不断总结新冠肺炎的分期论治经验,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