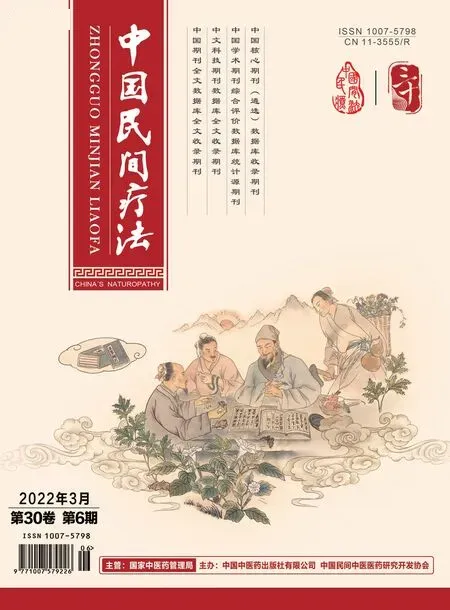《针灸大成》中的临床诊疗特色及其时代价值※
马巧琳,胡 斌,席林林
(1.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450046;2.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8)
杨继洲,又名济时,明代三衢(今浙江衢县)人,世医出身。杨继洲在家传医书《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广泛节录其他针灸文献资料,结合其临床经验加以注解,并附其诊疗病案,撰成《针灸大成》一书[1]。学习《针灸大成》,我们不难发现杨继洲医术高明,针药兼精,对内、外、妇、儿各科病证都有深刻见解,临床诊疗特色突出,对现今针灸研究和临床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将其临床诊疗特色阐述如下。
1 治疗范围广
杨继洲临证经验丰富,善于运用针灸或针药结合治疗各科疾病,除了在卷八临床各科病证的针灸治法、卷九《治症总要》等内容中加以介绍外,在医案部分也有集中体现。医案共存33则,患者包括男女、老幼,病证涉及手臂屈伸不利、腰痛、两腿风、痹证、痿证、口眼斜、产后风、痰核、结核、便溏、泻痢、迁延痢、疳疾、便血、痞疾、痞块、食少、膈气、中风、血崩、气厥、急惊风、癫狂、痫证等[2],显示了其深厚的临床造诣,也拓展了针灸疗法的临床应用,并进一步推动了针灸治疗学的发展。
2 针、灸、药并重,长于针灸
针、灸、药结合的思想源于《黄帝内经》,历来为后世医家所重视。杨继洲着眼于疗效,指出由于不同疾病的部位和性质不同,治疗方法也应有所区别,主张针、灸、药配合运用;针对当时部分医家忽视针灸的情况,提倡治疗手段不可偏废,应当重视针灸[3]。如《针灸大成》卷三提出:“然而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在血脉,非针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焫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其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故药与针灸不可缺一者也。”“时可以针而针,时可以灸而灸。”“夫何诸家之术唯以药,而于针灸则并而弃之,斯何以保其元气,以收圣人寿民之仁心哉?”《针灸大成》33则医案中,针灸医案就有29则,包括针灸配合13则、单纯针治9则、针药结合3则、针灸药并施1则、单纯灸法l则、灸药并用1则、指针联合药物1则[4],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杨继洲针、灸、药并重,长于针灸的临床治疗特色。针、灸、药并重,相互配合使用,针灸治其经,药物调其脏,既可取长补短,减毒增效,又可扩大适应证,缩短疗程。
3 配穴特点
3.1 取穴精练 《针灸大成·策》曰:“执简可以驭繁,观会可以得要,而按经治疾之余,尚何疾之有不愈。”“不得其要,虽取穴之多,亦无以济人;苟得其要,则虽会通之简,亦足以成功。”杨继洲临证取穴精练,《针灸大成·治症总要》用穴171个、《针灸大成·胜玉歌》用穴65个、《针灸大成·医案》用经穴24个,且《针灸大成·治症总要》中所选的穴位基本涵盖了后两篇,由此也可大致推算杨继洲的常用腧穴。值得注意的是,《针灸大成·医案》中的33则医案涉及内、外、妇、儿各科病证20余种,仅用腧穴24个,其中除1例用了十三鬼穴外,用1个穴位者有9例,余多仅用2~3个穴位[5]。如治“宋氏子痞疾”案,针章门;治“夏中贵下肢瘫痪”案,针环跳;治“蔡氏女风痰阻滞经络”案,针内关;治“李氏祖夫人产后风”案,针太溪、血海、三阴交为主;治“王公痰核阻于咽喉”案,针膻中、气海、足三里且灸等。这些均体现出杨继洲临床取穴精少、疗效显著,为后代针灸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2 远近结合,善用特定穴 杨继洲配穴相当灵活,不拘泥于病变的局部,远近结合,且善用特定穴。配穴远近结合的特点可从杨继洲选用各个穴位的次数中明证。《针灸大成·治症总要》中所用穴位四肢9个,头身10个,出现10次以上的腧穴有合谷(58次)、足三里(46次)、三阴交(26次)、曲池(24次)、中脘(22次)、水沟(19次)、委中(19次)、百会(17次)、大椎(17次)、行间(15次)、中极(15次)、气海(15次)、肾俞(13次)、悬钟(绝骨)(12次)、昆仑(12次)、膻中(12次)、支沟(12次)、承浆(11次)、膏肓(10次),其中特定穴占89%。《针灸大成·医案》所用的24个腧穴中四肢、头身各12穴。其中背俞穴3个(肺俞、肾俞、心俞),腹募穴3个(中脘、膻中、章门),五输穴6个(曲池、足三里、合谷、列缺、中冲、照海),络穴3个(内关、长强、鸠尾),交会穴4个(环跳、膏肓、巨髎、肩髃),其他经穴3个(气海、食仓、俞府),经外奇穴1个(印堂),阿是穴1个,其中特定穴占83%。
特定穴是十四经脉上具有特殊治疗作用和特定名称的一类腧穴,杨继洲根据辨证灵活选用,故临证取穴虽少但疗效卓著。如“夏中贵下肢瘫痪”案,针环跳即能动履。环跳是足少阳、足太阳交会穴,刺之能疏通足少阳、足太阳经络,使气血通畅,濡养肢体,瘫痪得愈。又如“杨后山公乃郎疳疾”案,取章门。章门是八会穴之脏会,又是脾之募穴,还是足厥阴肝经、足少阳胆经交会穴,可消积散结,调理脾胃。书中处处彰显着杨继洲对特定穴的重视,直至如今,其中的大多数特定穴在临床上仍备受推崇。
3.3 重视任督二脉腧穴 任脉、督脉分别又称为“阴脉之海”“阳脉之海”,对调整全身阴阳气机有重要意义,任督二脉的经穴往往对全身症状有调节作用。杨继洲临床重视任督二脉腧穴,《针灸大成·治症总要》中出现10次以上的19个腧穴中,任督二脉经穴有8个(中脘、水沟、百会、大椎、中极、气海、膻中、承浆),占腧穴总数的42%,占腧穴选取总次数的38%。《针灸大成·医案》所用24个经穴中,任督二脉经穴有膻中、气海、长强、鸠尾、中脘5个,占23%。其中,中脘在不同医案中重复选用4次,膻中、气海重复选用3次,可见杨继洲重视并善于使用任督二脉腧穴。
3.4 以奇辅正 经外奇穴是不属于十四经系统的经验有效穴,有明确的位置及固定的名称。杨继洲临床重视奇穴的应用,审慎选取奇穴配合经穴,使“各得其当”。《针灸大成·策·穴有奇正策》曰:“而奇穴者,则又旁通于正穴之外,以随时疗症者也。”指出奇穴对经穴的配合辅助作用,认为这种以奇辅正的取穴法需要依据临床实际,“至于定穴,则自正穴之外,又益之以奇穴焉……民之受疾不同,故所施之术或异”。《针灸大成·策·穴有奇正策》论述奇穴79个,这是杨继洲基于当时针灸学水平提出的,也是对古代医家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时至今日仍被临床广泛选用。此外,还有《针灸大成·胜玉歌》中提到的膝眼,《针灸大成·医案》中提到的块中、食仓、印堂,《针灸大成·治症总要》中提到的太阳、印堂,《针灸大成·策》提到的百劳等。
4 针刺重方法
4.1 重视针刺手法的承古拓新 杨继洲重视针刺手法的继承,广集博采,除整理家传的许多手法外,还广收前贤手法,并结合其临床实践对这些手法加以论述[6]。《针灸大成·三衢杨氏补泻》中论述的“下手八法”“十二字法”“二十四法”均为杨继洲在历代各家针法的基础上结合其经验形成的,包括了数十种单式及复式补泻手法,论述系统详细,分类清晰明了,方法全面实用。在《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一卷中又进一步对多种单式、复式手法进行了详尽说明。杨继洲的针法不仅多种多样,而且新颖独特。如基于元·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对偏头痛一针两穴的治疗方法,发展了多种透穴针治法。《针灸大成·玉龙歌》载:“偏正头风痛难医,丝竹金针亦可施,沿皮向后透率谷,一针两穴世间稀。”对偏正头风之有痰“风池刺一寸半,透风府穴,此必横刺方透也”,对偏正头风之无痰“合谷穴针至劳宫”,用“横针透膝眼”治疗两腿疼痛、膝部红肿,以“液门沿皮针向后,透阳池”治疗手臂红肿、腕痛者等。又如“李公胃旁痞块如复盆”案,用以盘针之法,配合灸食仓、中脘,以消痰散结,其中盘针法是针体大幅度盘旋转动的一种和气补气法,可使气至而调和,加强针感,促使痞块消散。《针灸大成》记载的诸多手法流传至今,也被后世广泛应用。
4.2 强调补泻手法 杨继洲临床强调针刺的补泻手法,将穴法与手法有机结合,是取效的关键。《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答》曰:“补针之法……行九阳之数,捻九撅九……以生数行之……凡泻针之法……行六阴之数,捻六撅六……以成数行之。”采用九六补泻和生成补泻法,以捻针次数决定补泻,补用九阳数或生数,泻用六阴数或成数。在《针灸大成·医案》中多以九六言手法。如“陈相公长孙胸前突起”案,针俞府、膻中,行六阴之数,以泻其痰气、宽胸散结;“吕小山臂结核”案,针曲池,行六阴之数,以清热活血散结;“王公弟心痛”案,针照海,行生数,以滋肾水而抑心火,针列缺,行成数,以化痰浊而开心窍;“田春野公乃翁患脾胃之疾”案,取中脘、食仓,每穴各灸9壮,更针行九阳之数,以温补中焦、健脾益胃。时至今日,这种重视针刺补泻的思想仍是针灸学科教学、科研、临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重视临床规范和安全性
杨继洲临床非常重视治疗的安全性和规范性,这点在他对针刺和艾灸刺激量的认识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5.1 平补平泻和大补大泻 杨继洲根据针刺补泻刺激强度的不同,将补泻手法分为平补平泻和大补大泻两种[7]。《针灸大成·刺有大小》曰:“有平补平泻,谓其阴阳不平而后平也。阳下之曰补,阴上之曰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有大补大泻,唯其阴阳俱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惧补惧泻,必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此乃调阴换阳。”
5.2 诸阳之会不可多灸 杨继洲认为对头部不宜多灸。《针灸大成·策·头不多灸策》曰:“首为诸阳之会,百脉之宗,人之受病固多,而吾之施灸宜别,若不察其机而多灸之,其能免夫头目旋眩、还视不明之咎乎?不审其地而并灸之,其能免夫气血滞绝、肌肉单薄之忌乎?是百脉之皆归于头,而头之不可多灸,尤按经取穴者之所当究心也。”古人施灸,动辄数十壮、百壮甚至数百壮,头部为诸阳之会,肌肉单薄,确不宜多灸。杨继洲“头不可多灸”的观点,现代临床仍然非常重视。
6 临证通权达变
《针灸大成·策·诸家得失策》曰:“其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指出临证施治,贵在权变,若墨守成规,就不能准确应对变化多端的疾病。
6.1 治法灵活,简便效验 杨继洲临证治法灵活多样,但以简便效验之穴为首选。《针灸大成》所载杨继洲医案中,治法丰富多样,或针,或灸,或药,或二法同施,或三法并用,或据实施治,因此在临床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疗法的优势,也充分体现了杨继洲“时可以针而针,时可以灸而灸,时可以补而补,时可以泻而泻,或针灸可并举则并举之,或补泻可并行则并行之,治法因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的临证理念。“许敬庵公湿热腰痛”案中,患者平素惧针,杨继洲先以手指于肾俞行补泻,待疼痛稍减,使空腹服以除湿行气之剂,一服而安。杨继洲灵活变通,用指针和药物替代针刺治疗,同样达到了愈疾之效。
6.2 重视子午流注,但不拘泥于日忌、人神禁忌 杨继洲非常重视子午流注的临床运用。如“张相公长孙泻痢半载”案,认为“泻痢日久,体貌已变。须元气稍复,择日针灸可也”。又如“陈相公长孙胸前突起”案,认为“此乃痰结肺经而不能疏散,久而愈高,必早针俞府、膻中”,后“择日针,行六阴之数,更灸五壮,令贴膏,痰出而平”。杨继洲临证不为鬼神所惑,不为前人所囿,师古而不泥古,结合自身经验对各种病情做出客观评估后施治。《针灸大成·人神禁忌》曰:“若急病,人尻神亦不必避也。”其临证遇暴急之疾,多不拘时日,每获奇效。如“熊可山公泻痢”案,“绕脐一块痛至死,脉气将危绝,众医云不可治……以脐中一块高起如拳大,是日不宜针刺”,但杨继洲不拘日忌,急针气海,灸至五十壮而苏。又如“王会泉公亚夫人危异之疾”案,病者“半月不饮食,目闭不开久矣,六脉似有似无”,但适逢人神禁忌,杨继洲认为必以针方可苏,若择他日则延误病情,故当即刺内关二穴,人醒目开,能食米饮,后徐以乳汁调理而愈。
6.3 灸亦有法,不拘泥于成数 杨继洲临证用灸灵活,认为灸亦有法,不可拘泥。《针灸大成·策·穴有奇正策》曰:“然灸亦有法矣,而独不详其数者,何也?盖人之肌肤,有厚薄,有深浅,而火不可以概施,则随时变化而不泥于成数者,固圣人望人之心也。”进一步举例说明少商“灸不可过多,多则不免有肌肉单薄之忌”,章门“灸不可不及,不及则不免有气血壅滞之嫌”,少冲、涌泉“灸之过多,则致伤矣”,膏肓、中脘、足三里、曲池“灸之愈多,则愈善矣”。在“箕川公长女惊风”案中,患者势甚危笃,杨继洲灸中冲、印堂、合谷各数十壮,并针对刺激量的问题,指出应当根据其病情之轻重而定,若依古法而止三五壮则难以奏效。
7 重视总结
杨继洲出身于世医之家,祖传医籍甚多,其不仅注重广泛阅览,同时还重视经验的总结[8]。在《针灸大成》中,杨继洲对所录的其他针灸文献,结合其临床实践感悟进行注解。书中的30余则医案记载了其1555—1580年的一些医事活动,涉及内、外、妇、儿各科疾病,记载大多全面具体,辨证独特,施治得当,取穴,用药精练,疗效确切。这些医案可以说是针灸古籍中医案保留最多、最详尽的,对后世整理分析杨继洲的学术思想并应用于临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