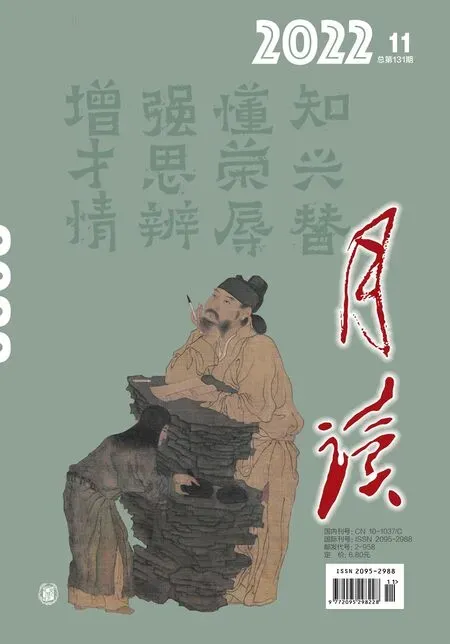庄子思想从何而来?
——走进庄子的世界(四)
◎ 王景琳 徐匋
庄子是一个极为特异的存在。认识他的思想学说,仅仅了解这个人,他的身世,他的交游,他的生活环境,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得了解他曾接触过什么样的思想潮流。毕竟庄子思想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突然间便像石猴子那样横空出世了。如同任何一种思潮、流派的出现一样,庄子一定也是有其师承渊源的。
那么,庄子这么一棵参天大树,他的根在哪儿呢?
约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整理的《庄子》一行世,便被司马迁相中,记在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里。庄子之传虽短,信息量却很大。司马迁不仅记下了庄子的名姓故里生活时代、《庄子》一书的字数,还说庄子书读得多,学问无所不包,但从根本上说他的学说是从老子那儿传承过来的。司马迁还把庄子放到了孔子及儒家的对立面,特别强调庄子诋毁孔子之徒、“剽剥儒墨”,还说这是“以明老子之术”。
司马迁对庄子思想渊源的这几句评语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原本自甘恬淡寂寞的庄子被戴上了反孔反儒的大帽子不说,还成了孔子反对派的一面旗帜。后来谁对孔子不高兴,谁想骂儒家,都会拉上庄子助阵。问题是,庄子真的反孔吗?庄子学说是不是果真如司马迁所断言的那样,与儒学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历史的真相又究竟是如何的呢?要想正本清源,我们还得花点工夫,回到庄子的时代,还原庄子生活的现场,去调查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一、“其学无所不窥”
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在评论庄子的学术渊源时,有一句话特别重要,不容忽视,这就是“其学无所不窥”,意思是说庄子无所不学,学识渊博。这个评价确实抓住了庄子学问的根本特点,堪称点睛之笔。司马迁看到的《庄子》有十余万言,比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三十三篇计六万五千余字的《庄子》字数多出了将近一倍。唐代陆德明说是晋郭象勘定《庄子》时删去了其中“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经典释文序录》)的十九篇文章。很可惜,这些被删去的文章久已失传,但仅就现存的三十三篇来看,庄子“其学无所不窥”也是名副其实的。
庄子究竟读过多少种书?很难估计出个数目来。我们只知道他在《逍遥游》中提到志怪之书《齐谐》,那条由鱼卵化身为鲲再展翅飞上九天的鹏的故事,最早就是这本书所记述的。此外,庄子再没有提及任何其他书名。但是《庄子》书中所涉及的天上地下,方方面面,都说明庄子不但博览群书,而且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没错,庄子的确有着“葱茏的想象力”,但《庄子》一书所涉及的内容之丰富、领域之广阔,显然不是仅仅凭着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就能杜撰出来的。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所谓“重言”,就是历史人物说过的话。老子的事迹,在《庄子》中有不少记载。其中孔子问学于老聃,还有春秋时卫国政治家蘧伯玉的言行,以及其他一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不能仅仅视为是寓言。这些记述显示出庄子有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庄子》中还收录或提到了大量昆仑、蓬莱两大神话系统中的上古神话传说,其丰富程度不亚于屈原的《楚辞》。此外,早期的《庄子》还记述了相当一些与地理有关的资料,陆德明所谓“或似《山海经》”,指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即便是后来经郭象删节过的本子,我们也仍然可以见到有关地理记述的蛛丝马迹。陆德明还说早期《庄子》中有“或类《占梦书》”的篇章,意思是《庄子》中曾记述了一些占梦官对梦的解释及预言。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庄子》中有关梦的记述或解说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占梦书》的影响。
庄子读书涉猎极广,几乎涵盖了天下人文自然的全部学科。无论是天文地理,自然万物,还是历史哲学,社会心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谓是上穷“太极之先”,下究“六极之下”。单单看一下庄子对宇宙起源的探索与认识之深,就可以知道庄子的学问有多么了不起了:
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
这段话,乍一读是不是有一种读天书的感觉?庄子到底要说什么呢?字面上看,庄子好像是在故弄玄虚,成心跟人兜圈子,把宇宙的起源与人类认知的发展关系说得玄而又玄。实际上,庄子真正要阐发的就是:从人类知道宇宙万物有一个开始、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形成一个概念的时候,宇宙万物就已经存在了。人意识到宇宙万物的存在,宇宙万物存在着;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仍然存在着。宇宙是没有开始与终结的。在无限的宇宙中孕育着一个空空的“无”,终于在某一个刹那间,“无”产生了“有无也者”的时代,而后才有了“有‘有’也者”的时代,也就是现在人类生活的时代。这段话,单凭着仰望星空冥思苦想是写不出来的。庄子一定深入研究过前人有关宇宙起源的各种诠解,特别是老子的学说,经过多方探索之后才写出了如此深奥的文字。庄子对宇宙无限性以及人认知的局限性的认识,即便是在今天,也足以让人惊叹。
更令人叹服的是,庄子居然对医药学、人体解剖学、生物学也有相当的了解。他知道人体有“百骸、九窍、六藏”,还知道人的情绪与健康有关:“无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德充符》)他还谈到人长期睡在潮湿的地方便会得病,甚至半身不遂,而泥鳅生性就喜欢这种地方;人站在树上会产生恐惧感,而猿猴却不会。麋鹿喜欢吃草,蜈蚣以蛇为美食,猫头鹰、乌鸦爱吃老鼠,麋与鹿可以交配,泥鳅与鱼生活在一起等等。
不过,如果把庄子的“其学无所不窥”仅仅局限于对书籍的广泛浏览,那还不算真正理解庄子学问的渊源。庄子书确实读得超级多,囊括一切,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庄子尤其善于观察、学习书本之外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最可见出庄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人云亦云的人。用今人的眼光来衡量,庄子算得上是一位最早走出书斋,打破书本束缚,从自然环境、日常生活、以及人类各类生产活动中汲取知识养分,丰富、扩充自己治学领域的先驱者。庄子的时代,“虎妈狼爸”还没有诞生,至少没有类似高考升学之类的外在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庄子是幸运的。他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选择任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沉醉其中,倾心钻研,不必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庄子的“其学无所不窥”源于他对世间万物都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兴趣。对周围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带点技术性的活计,庄子似乎格外着迷,观察得特别细致,精准入微。像陶、木、漆、屠、洗染、画等手艺,甚至是抓蝉这样的活动,他都写得惟妙惟肖,十之八九其中浸透着他自己的亲身实践与体验。如庄子写“轮扁斫轮”,一上来就说制造车轮是一门对手艺要求非常高的技艺。辐条与车毂之间的榫接,松了不行,紧了也不行,必须得分毫不差才能保证车轮运转灵活自如。庄子还特别深有体会地说,这种功夫,要靠长期的实践才能做到得心应手,用语言是无法传授的。(《庄子·天道》)庄子还经常发表有关如何挑选木材的高见,诸如哪些木材“中绳墨”“中规矩”,适于做器物;哪些木材容易腐朽毁坏、招惹虫蠹,什么也做不成等等,都说明庄子对学问对知识的渴求是不拘一格的。
就是被众多文人视为低微粗鄙的活计,也仍可以成为庄子学习研究的对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人所皆知的“庖丁解牛”了。庄子对牛体结构的洞悉,对庖丁用刀的精确描写,对解牛过程的娴熟,相信他一定花了相当的工夫去理解所谓“大郤”“大窾”“技经肯綮”以及“大軱”之所在,并直接从庖丁那里获取了大量一手解牛经验,才真正掌握了从解牛开始的“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到最后“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的解牛全过程。倘若他只是像文惠君那样站在旁边观看,就是看上多少遍,也无法得其皮毛。也正因为如此,血淋淋的解牛之事,才能被庄子写成了一段声色并茂的精彩艺术活动。
像解牛这样的事,在一般文人士子眼中,当然算不得学问。孟子不就说过“君子远庖厨”这样的话吗?不过,假如读了孟子在此前说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几句,就知道孟子所谓的“君子远庖厨”其实是为了不影响自己食欲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说白了,就是一种“装”。而庄子在血腥的屠宰场却是把牛体的结构、解牛的流程、庖丁如何用刀才达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当做一门学问来探究的。
其实,解牛之事,也不止庄子一人写过。早于庄子的管子在《制分》中是这样写的:“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间也。”而庄子之后的贾谊写的是:“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象理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治安策》)同样的题材,出自同样著名的写手,可面貌、风格却迥然,庄子写作之生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不能不归功于庄子对世间万事万物所具有的强烈求知欲与兴趣。
总之,司马迁对庄子“于学无所不窥”的评价,的确点出了庄子学说渊源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与老子貌合神离
说庄子“于学无所不窥”,涉猎的学问包罗万象,涵盖了天体宇宙、自然万物、思想文化等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此话的确精辟。但是如果你就此把《庄子》当作一部类似百科全书的“类书”来看,或者把庄子视为是一个“杂家”,认为其书的特点仅仅是“杂之广义,无所不包”(纪昀《杂家类叙》),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庄子固然博采众学,知识渊博,无所不包,对世间万事万物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文章写得更是“洸洋自恣”,但要追根溯源,还是要追到老子那里,其学说的核心还是落在说“道” 论“德”上,因此,《庄子》不是“类书”,也不是“杂家”,而属于“道家”学说。庄子思想也是有“源头”的,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在这一点上,司马迁确实独具慧眼,一语就点中了庄子的穴道。
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道家”最早称作“道德家”,是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最早提出来的。后来“道德”一词盛行,与司马谈“道德家”所定义的“道德”出现了歧义,于是“道德家”就被简称为“道家”。司马谈在他的文章中归纳了六家的主要特点,却没有开出一份各门各派的清单来,自然也就没有提到老子庄子的大名。那时节“黄老”并称,老子的名声已经如日中天,被汉初帝王捧得很高,而庄子还是默默无闻之辈,自然也攀不上老子这个阔亲戚。后来,司马迁作《史记》老子列传时,附带着也作了个庄子列传,这才开了将老子庄子并称的滥觞。
汉初“黄老”被当做治国的主导思想,可是不久“黄”就让了位;而谈“道”谈得相对更多的庄子就顺理成章地排在了老子的后面,成了“道家”的代表人物。名称上看,老子的名气一直压庄子一头,可是从魏晋开始,在文人士大夫心中,两个人的位置就已经调了个个儿了。
庄子学说的形成无疑受到了老子的深刻影响。老庄两人都谈“道”,老子开口就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一章)庄子也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而且两人都注重“道法自然”,都讲“道”与“自然”的关系。乍一看,庄子的“道”长得跟老子的“道”确实很像,但细细琢磨起来,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总有些什么不对味儿的地方。原来,庄子的“道”从源头那里涌出不久便开始分流,与老子貌合神离了。
老子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世上万物,一切的一切都是“道”生出来的。庄子也说“生”,提出“道”可以“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可是庄子更重视的却不是“道”的“生”,而是“道”的“通”。请注意了,这可是理解庄子的一个关键词!庄子认为“道”能“通”一切。所以到了庄子那儿,巍巍泰山不大,秋毫之末不小;厉人不丑,西施不美;大小美丑高低贵贱,统统没有了差别,万物一齐。
在老子看来,“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就是说老子心目中的人、地、天、道都大,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层次的不同,人无法与“道”相比,却又远远高于万物之上。而庄子说的却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就是说世间万物,包括人,都是“道”的体现,其表现形式、外在形态可以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骨子里却是相通的,即“道通为一”。更重要的是,由于世间万物都是“道”的体现,人与天地、人与“道”之间也就没有了高低尊卑的区别。这是不是有点石破天惊?想必现在大家也都看出来庄子是如何与老子貌合神离的了吧?
老子与庄子同根同源的“道”在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社会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老子的“道法自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讲的是君王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甚至是驾驭群臣百姓的一种手段,“无为”的目的是“无不为”。如果就立场来看的话,老子的屁股是妥妥地坐在了君王的一边,他花费了五千言来为君王出谋划策。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第三十七章),其口吻完全是劝诫。说白了,就是为君王开出了一张治世药方而已。因此老子的思想往往被君王视作御人之术,例如汉初文、景二帝所推崇的“黄老之术”就有这个意思。
而庄子不同。庄子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混乱看得十分透彻。他清醒地意识到造成黑暗混乱的“根”就出在君王那里。因此,他对所谓治理天下毫无兴趣,或者说不屑一顾。就立场而言,庄子与老子最大的不同,是庄子完全站在了君王的对立面,或者说是从臣民的角度,去关注人在这个黑暗混乱的社会应当如何生存,如何面对纷乱复杂的社会及人事关系,如何在筋骨盘结的社会中保全性命,如何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如何徜徉于“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的大树下,逍遥自在,躺平纳凉。
“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坐的位置不同,也就带来了老子庄子关注点的不同。老子关注的是治理天下的手段与策略:“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老子还真是智者,一眼就看穿了:老百姓只要有饭吃,身体强健,就够了。至于心志、知识、欲望之类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杜绝。对聪明人更是要让他们心存畏惧,不敢妄为,这下就可以天下大治了。看看,老子出的,简直就是愚民的招数!庄子却从来不关注这样的问题,更不曾像老子这样处心积虑地为统治者支招。当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说的是,您老人家还是回去吧。我要天下有什么用?厨子纵然不下厨,主持祭祀的也不会越俎代庖的。 (见《庄子·逍遥游》)许由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庄子本人的态度。
庄子对老子提出的政治理念、社会变革、治理天下完全没有兴趣,他所关注的是人应当如何活着,如何处世,如何通过“丧我”“坐忘”,忘记个人的执念,不在意现存的一切,超越现实世界对人的种种束缚,来获取一种“无名”“无功”“无己”的全新的人生体验。可以说,老子所关注的是现实的、功利的,而庄子所关注的则是理想的、精神的、超越的。特别是庄子从“道”生发开来的那种蔑视世俗权贵、独往独来的清高孤傲的精神,老子是没有的。
总之,老子思想虽然是庄子学说的重要源头,但分流之后的庄子又与老子貌合神离,骨子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不但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的色彩有异,味道有别,后世所谓“道家精神”中的“道”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庄子的分量也比老子重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