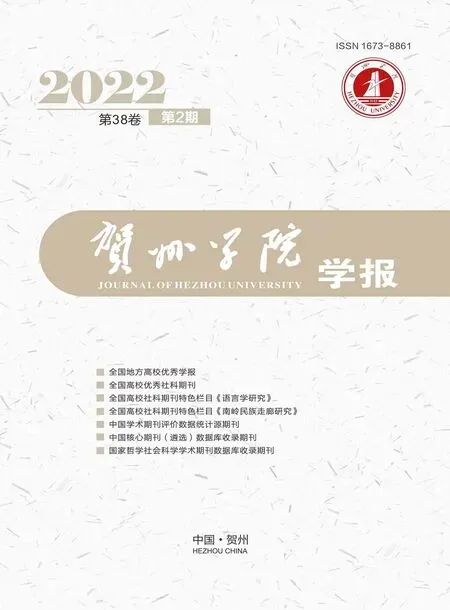广西富川民间土地契约文书的地亩计量探析
——南岭走廊民间文献俗字研究之三
陈才佳,刘译蔓
(贺州学院 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广西 贺州 542800)
一、富川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
富川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四面环山,地势北高南低。东是姑婆山,西有西岭山,南盘天堂岭,北卧黄沙岭,境内群山起伏、山峦叠嶂,地处都庞岭和萌注岭余脉的峡槽之间,秋冬北风直灌,风大而急,素有“大风走廊”之称[1]42。富川地形多为山地、丘陵、台地、石山、平原和水面,有“五半山岭四平原,半分川水绕田园”之说。县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气候温和,降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1 600多毫米,并不缺少雨水。但是,丘陵和台地占比甚多,地势高出水面,土质疏松渗水性强,雨水难以储存,导致地表严重缺水。清季民国时期富川县财力物力有限,无法修建大型水库蓄水用于灌溉,因而县域干旱较为严重,旱地面积比水田多,尤其是北部地区。
按富川民众的说法,旱地一般包括山地、林地、园地和畬地等①。山地指海拔在500 米以上,起伏大且坡度陡峭,呈脉状分布的地形,一般适宜多种植被与经济林木生长,陡坡多种植松树和杉树,缓坡则以种植油茶树为主。丘陵指海拔在500 米以下,坡度较缓、起伏不大的低矮山丘,一般种植油茶树等经济作物或玉米等粮食作物。台地指由低山或丘陵向平原过渡、平坦似台状的一种地貌形态,以种植红薯、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或种植花生、油茶等经济作物为主。在富川乡村民众的认知中,园地比畬地面积大,一般指种植有油茶、果树及其他树木的地块。而畬地一般指菜园,是种植蔬菜的地块。这只是基于自我认知的分类方法,并非严格的科学分类。为尊重民众的传统认知习惯,本文在分析契约文书中的地亩量词用字及其含义时,保留其中关于土地类型的传统表述形式。在此基础上,逐一探讨契约写本中地亩的计量方式。
富川民众根据自然地貌对旱地类型作出分类,但计量却采用非亩制化方式,其中原因与当地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在清季前后,富川县域乡土社会基本形成了地域性的土地交易方式。
一是亲缘文化助推土地交易的模糊计量方式。在富川土地契约写本中,私人土地所有权受宗族共同体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诸如“自问房亲叔侄”“托中问到房亲”,先问尽房族是否有人承买,而后才到乡邻。基于宗亲或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土地买卖,彼此较为熟悉,大家相互信任,因此不用亩制计量,可以根据自己多年耕种估算的播种量或收成量或放肥量等,抑或根据每年纳税量来计量地块的实际价值。
二是诚信文化保证土地的交易实施。在富川县民间契约文书中有格式化的表达,涵盖了土地契约的各要件,契约文书的具体内容为:卖主(业主)→出售原因→土地位置→土地数量(标的:实物计量∕纳税计量∕土地时价)→(中人引荐)→买主承买→钱契交割→业主担保事项→中人、业主签字画押→买卖时间等。就契约法律规范而言,这种契约写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书,其最核心的要件没有土地四至和具体面积表述,因此,研究的起点更适合在一个较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我们认为,一定区域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调适人们关系的规则,可称之为“民间法”。在清季民国时期的富川民间社会,老百姓进行某些契约行为时,仍遵守着奉行了上百年的民事习惯。如土地买卖标的惯用“实物[秧(稝)∕穗(把)∕斗(禾)∕灰(担)等)+ 税收 + 时价]”②表述,并未呈现具体的土地面积。这是一种民事习惯,其内容具有显著的地方性文化特征。
二、富川的旱地计量方式及其用字
县域乡土社会对于不同类型旱地的交易,契约文书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县域间因语言群体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计量方式及其用字,或同一语言群体因用字习惯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俗字,在契约中都有所表现。一般地块称量词有“块、坵、边、节”等,地亩计量词有表种子量的“斗、升”等,也有表放肥量的“灰”等,最核心的要件是表地价的“时值价银(钱)”,每份契约文书都有“时值价银(钱)XX”的类似表述。这样,核心要件与前面“量”项组合便构成了旱地的多种计量方式。
(一)旱地计量及其用字
常年耕作的生产用地,根据用途又分为畬(菜)地、园地、林地、塘基地等等,笼统以块、坵、节等称量,辅以时价计量,实际上土地的面积并未直接出现。一般只能根据当时价格推算出土地的大致面积,这也是土地以实物计量历史的延续。在表达中,往往是以“称量(块∕坵∕节)+实物(斗∕升∕觔∕价钱)”来认知旱地面积大小的。
1.块+地价
在富川民间契约文书中,有许多以量词“块”加地价的自表述。如:
(1)立写地契卢赐华,情因为妻无钱出办,自将祖遗地坐落土名社屋背山脚地乙(一)块,将来出卖。……当中三面言定,时值价钱乙(一)仟三百文正(整)。即日契价两交,系是赐华接受回家办用。其地立写限卖十年周满方可任从卖主归赎,自愿甘心,永无异人(言)。立写卖契乙(一)张付与买主収(收)执为(据)。(NO.03707)
(2)立写地契人唐益义,今因无钱正用,自将身己下坐落土名山尾尾地一块,将来出当。请(亲)自上门问到唐益俊承当,价钱二千文,本行利加三,任从当主亲手接受回家正用,其地当后不得异言,所立卖(当)契一(纸)付当主收执是实。(NO.03709)
两件契约都是关于土地典卖事项,地块都以“块”称量,契中没有表明面积、四至等要素,议定“时值价钱乙仟三百文正(整)”“价钱二千文,本行利加三”是契约内容要素中的最核心要件,表明了地块的时价。可以说“块”是个模糊的量,无法准确表明地块亩数,但按时价可以推算出地块亩数,也算是一个间接计量。两件契约的差别在于:契(1)是土地出卖,标明“十年期限满后卖主可以归赎”;契(2)是出当,没有标明赎回期限,这也就意味着当主在经济条件允许时随时可以赎回。这两件契约都出现“一地两主”情况,即卖主(地底权人)和买主(地面权人)各自拥有自己的权属,地权没有完全转移,这是传统乡村特殊的地权形态。
2.坵+斗+地价
在富川民间契约文书中,许多在原有“块+地价”表述的基础上增加了撒种量,对地块面积计量似乎严谨了一些,但也只能是个概数。现摘录二则如下:
(1)立写永远杜卖田地契人杨通达,今因无银正用,自将分下祖业坐落土名鸡光栎脚井田乙(一)坵,该禾五十禾花,原税乙(一)分。又土名凹子脚地二坵,该麦种乙(一)斗,将来永远出卖与人。……两家兼中三面言定,时值田地价银壹佰肆拾弍(二)毫正(整),即日立契银契两交清白。系是杨通达亲接回家正用。……立永远断卖(纸)乙(一)张,付与买主收执存照。(NO.04461)
(2)立写永远杜卖断地契人杨成年,今因银正用,自将买受地坐落土名枫树湾大地乙(一)坵、傍边小地三坵,共肆坵,该麦种八升,将来出卖。……二家兼中三面言定,时值地价艮(银)壹百毫正(整),即日立契银契两交清白,系是杨成年亲接回家正用。……附(付)与买主杨成京收执存照。(NO.04464)
两件契约内容都是土地买卖,以点种容量“斗”或“升”麦种计量间接换算地块面积,但两者也有不同,前者是出卖田与地,后者是出卖地。契(1)中“井田乙坵,该禾五十禾花”,根据清光绪《富川县志》记载,东山泉涌水灌润为井田[1]卷一,亦属冷水田,产量不高,割稻穗更节省劳动力。“禾五十禾花”相当于“禾五十把”稻穗,根据田野调查结果,1 把约等于12斤,即可以收稻穗把数计量田亩数。“地二坵,该麦种乙斗”和契(2)中“大地乙坵、傍边小地三坵,共肆坵,该麦种八升”,根据1 斗=10 升的容量关系,两件契约中的地块面积是一大一小。以种植麦种量换算地块面积,然后再辅以地价衡量,属于典型的种子容量计量方式。
3.坵+崩+稻穗
在富川民间契约中,以插秧量、时价禾(稻穗)计量,这类比较少见。如:
“觔”同“斤”。《龙龛手鉴》:“二俗,音斤。”《字彙·角部》:“觔,今俗多作‘斤’字。”《淮南子·天文》:“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觔。”该契写明熟地两块、“该秧二崩”,以插秧量换算地块面积,说明该熟地很可能通过人工灌溉可种植水稻,因此才出现以“崩”计量的情况,有“稝”及其通用字“崩”“塴”“禾崩”“颁”等专用于秧苗量的单位词,再辅以“时价禾老秤二百斤”,则可以推算地块的大概面积。推算该熟地的面积,一是根据“3 稝约等于 1 亩”或“2.5 稝约等于 1 亩”的估算[2]13-14,二是根据当时亩产量测算。
4.担+时价
在富川民间契约中,发现一些以放灰量计量地块面积的契约。如:
(1)立写永卖地契人钟杨应,今因无钱使用,自身己分下族地坐落土名乳地虎头山脚地上下两边,该灰弍(二)担,将来断卖,乙(一)寸不存。……当中三面言定,求卖地价钱壹仟文正,就日求契交足,亲手接回家正用。……付与买主收执为(据)。
(2)立写永卖荒地人赵福秀,今因无银使用,自身己分下祖地坐落土名乃虎头山脚平地一块,该灰乙(一)担,将来永远断卖。……三面言定,时值价银贰拾伍毫正(整)(整),即日立契交足,亲手接回家使用。……今立有凭付与买主收执为(据)。
从显示的地名看,二则地契应是同一地方,即虎头山脚,在今富川瑶族自治县麦岭镇虎头山。“乳地”也有写成“乃地”的,“乃”的本字应是“奶”。该类契约以实物肥料“灰”的担数计量面积,仅仅是一个概数,在富川其他村落亦有类似的发现,如麦岭高桥村、莲山镇大莲塘村等。我们在相关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时,基本确定了“一担灰”的面积概数。
笔者在麦岭高桥村调查时,义家云(50 岁)说:“在我的印象中,我父母种地是用草木灰或草皮灰的。有条件的泼些粪水发酵,没有粪水的直接用草木灰或草皮灰,因为那时候没有化肥。用化肥是后面的事情。这些是我亲眼所见的,印象很深。听老人家说,一般‘一担灰’是0.8~1.0 分,这完全是靠经验丈量的结果,肯定不是精确的面积。”在场的同村妇女杨氏(60 岁)也说:“家云讲的都是事实,我年纪比他大些,十几岁就做农活了。种红薯、花生豆、豆角时疏密不同、放灰大小抓不同,面积也是个大概,不可能像现在量这么清楚。”高桥村是距离虎头山最近的村落,这是我们选择高桥村的原因。可遗憾的是,当年的虎头村已经不复存在,其中原因当地人也说不清楚。
在富川南边的大莲塘村,我们走访了不少老人,他们基本上也认为“一担灰”丈量只是个大概。其中,黎小苟记忆最为深刻,她说:“我小时没钱读书,十几岁就开始做工(农活)了,插田种地样样都做。记得那时的肥料就是大粪、火灰,种菜主要用尿水,不够的话也用粪水。旱地种落地豆、绿豆、番薯主要放点灰,有灶头灰和垃圾灰,粪水多余的就用粪水沤一下,肥力会好些。一担灰一般放0.8 分地左右。种田主要靠粪水,粪水不够,就放点灰,用灰代肥,每根禾蔸放一抓灰,禾蔸比落地豆要疏朗些,一担灰能放1 分田左右。”黎氏丈夫钟荣寿(79 岁)在旁也说:“我妻子讲的都是事实,我也在生产队干过,主要靠农家肥。队里还要铲草皮烧草皮灰,也有捡牛粪的,肥料奇缺。一担灰能放多宽的地印象很深。”富川县域南北村寨相关“一担灰”计量的面积基本一致,我们认为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二)园地及其计量用字
园地一般指地上有附着物,面积比较大且四至清楚的地块。园地类也多以“块+地价”表述,主要有畬(菜)园、木园等。
1.畬(菜)园主要指在村寨附近以种植蔬菜等为主的地块。现摘录二则如下:
(1)立卖菜园字周绍香,今因家下缺乏正用无出。自愿将祖遗之园将来出卖,请中问至昌贤处说合,出钱承买,时值价钱弍(二)拾捌千文正。……自卖之后,任其钱主管业耕种,永无抽赎等情,今欲有凭,立卖为据。(未编号)
(2)立卖园地契人唐神章、唐仁兴,今因无银正用,自将祖业坐落土名屋背后园乙(一)块,将来出卖。……当诸面言定,时价园地价银壹佰毫正(整),即日立契交足,亲手接受回正用。……今立写为凭,付与买主收执为(据)。(NO.03743)
这类契约在表述中只有“地块时价”等核心要件,而且交易货币不同,要用时价换算地块面积比较棘手,必须要深入了解当时土地买卖的价格才能厘清。
2.木园类在富川民间契约中,占据大多数。主要以种植油茶、树木等地界分明的地块为主。现摘录三则如下:
(1)立写永远断卖茶木园人盘铭安,今因无钱使用,自将茶树园坐落土名半山脚茶树木乙(一)园将来出卖。……当二面言定,时值价银叁拾乙(一)毫文正(整),即日立契交足,亲手接收回家正用。……断卖(纸)乙(一)张付与买主为凭是实。
(2)立写永远断卖茶木园契人盘铭安,今因无钱使用,将茶树园坐落土名半山脚茶树木乙(一)园,将来出卖。四至分明,东至墙寨……自己上门问到老村钟世盛家承买地泥,当二面言定,时值价银叁拾乙(一)毫文整,即日立契交足,亲手接回家正用。其茶树木园卖后任从买主耕种管业,日后不得异言,今有所立不得反悔,如有永卖纸乙(一)张付与买主收执为凭是实。
(3)立写断约人潘有才,今因家下无银使用、无路出办,子母商议,自将己业土名松木冲杉木壹林,东边金保为界……请中人潘吉养上门问到同村岑求光允从承应,时值价银陆万元正(整),即日立约交足,潘有才亲手接受回家正用。……立写乙(一)纸付与买主永远管业收执为照。
此类契约写本格式要件缺少地块的市亩或实物计量,只表明地块的时价,清季民国园地契基本相同。如“时价园地价银壹佰毫正(整)”,说明该园地在民国十九年(1930 年)地价银“一百毫”,这是卖地当年地价。根据相关史料也只能推算个大概,因为在富川受局部生态、水肥、年成等因素影响,地价是动态的。
三、土地契约计量方式及其用字的特点
县域土地契约写本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综观水田、旱地、池塘、林地、宅基地、阴地等都没有标明地块的公制面积,水田多以插秧量“稝”,以收穗量“花”计量,或以“税+时价”,而地则以“块+时价”或以“灰(担)+时价”计量,地块面积计量取向于感性化或模糊化,但并不影响土地的买卖、典当或调换,表现了不同于周边地区的一些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计量用字的约定化。在土地计量中,村落社会约定俗成了自己的计量方式。不同语言群体因思维方式与认知水平差异,计量方式也各有差别。富川南部许多梧州话群体及平地瑶以实物“插秧多少稝”计量田亩,而北部都话群体则以实物“收禾多少花”计量田亩。当然,还有部分群体采用其他计量方式。一种计量方式的确定就用一个代表字书写,但在传播过程中,或因文化程度、或因近音借用、或因以禾类化、或因误写等因素影响,不仅出现了特殊的计量单位,而且出现一字多体。如:“稝”在村落民间契约书写里出现了“禾崩、崩、 、塴、颁”等多个写法。“花”在民间契约类化为“禾花”,在清季时期使用频率非常高,到了民国时期的民间契约书写才出现“花”。都话人“花”读 fu52∕53,因其居住区域缺水水稻产量低,便以收割稻穗为主,由此以“花”计量田亩。这些计量单位用字约定俗成,在当地田地典当买卖中,得到了村落社会的普遍认同。
二是土地计量的非亩制化。清季至民国期间极少发现富川以亩制计量的民间契约,土地计量去亩制化是普遍现象。包括水田、畬地、园地、林地等。其中水田多数以“产量计面积”,如:“该禾四十禾花,原税乙分”(NO.04448),“该禾四十把,该税弍分”(NO.04237),“该禾伍十禾花,原税壹分”(NO.04456),“该禾十二把,该税八厘”(NO.04253),“禾花(花)”即是“把”的意思,1 花(把)约等于12 斤。以“下种计面积”的有两类,一类以下种间接计量即以“插秧量计量”,如:“该秧乙稝,税七厘,将来出卖”(NO.01462),“该秧六禾崩,原税三分,将来出卖”(NO.01454),“该秧塴半,民税一分半,将来出卖”(NO.01482),汉族梧州人2.5 稝约等于1 亩,福利豹洞瑶族3 稝约等于1 亩;另一类以“下种子计量”,如:“谷种弍斗,民税八分,将来出卖”(NO.04545),“谷种弍(二)升,原税乙(一)分正(整),将来出当”(1925 年,未编号),根据当时富川1 斗约等于15斤,再结合邻近县 10 斤谷种折合亩制情况[3]277,即可推知大约面积。旱地也有以“下种子计量”现象,如:“土名凹子脚地二坵,该麦种乙(一)斗,将来永远出卖”(NO.04461)。另有以“下肥料计量”现象,如:“虎头山脚地上下二边,该灰弍(二)担,将来断卖”(1865 年,未编号),“虎头山脚平地一块,该灰乙(一)担,将来永远断卖”(1920 年,未编号)。这种以产量、撒种、放肥多寡粗略框算田土面积的动因,应源自边远地区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反映在人们对土地的看法上,自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格精细。从南方各省方志谱牒史料考察,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以稻穗把数、撒种籽量来折算土地面积的现象。贵州思南府、黎平府的古州、永从以及广西、湖南的一些地区,都属此种情况[4]53。
四、余 论
通过对富川民间契约文书系列的考察,可知当地存在着以插秧量“稝”、以收穗量“禾花”“把”、以撒种量“斗(升)”、以放肥量“担”作为田地计量单位的情况,“禾花”比较特殊,兼有收成产量和田土计量双重任务,契约文献与田野调查的有机结合,参照地方史志资料,推算出了“禾花”与“亩”的换算关系。但此处尚有一个问题,即富川为何使用一组特殊的田地计量单位,用于收成、撒种及放肥的计量,又用于计量田地的面积?富川是典型的山区地形。县域内四面环山,地势北高南低。或因谷深坡陡,或因岩溶地貌,或因丘陵地貌普遍缺水,尤其是北部麦岭、葛坡一带。《富川县志·舆地》记载:“旧垦田土随地制,西山流高,借势开渠灌溉而为冲田;其流远崖高者,筑堰灌水为坝田;东山泉涌分流灌润为井田;平岗汙泽筑堤蓄水留杠以时泄润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则塞坝激水、架筒转车以灌润为车田;又有高旷之处垦种稻谷,早禾乘春多雨早种早收,无雨则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槹,皆费人力,为功甚劳。”[5]卷一南部平原地带的莲山镇大莲塘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民谣:“莲塘垌,莲塘垌,一个田头一个洞,三天不下雨,男女都无空。”[6]128冲田、坝田、井田、塘田、车田及旱田不仅产量低,而且土地面积狭小零碎、极不规整,很难以亩制丈量、计算面积,因此,富川民间从感性视角,使用以产量、播种量及放肥量换算田地面积的计算方法,充分体现了富川各语言群体的生态智慧。
富川老百姓精心保护下来的珍贵文书档案,是各语言群体在民间契约中的“自表述”和“自书写”,是研究清季民国时期富川历史、经济、文化不可或缺的本真史料。它全面反映了清季民国时期富川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图景,蕴含着各族语言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信息,是研究南岭走廊各民族历史文化与交往互动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从富川民间契约文书和地方文献中有关田地收成、撒种、放肥与土地面积的特殊计量单位“稝(崩、塴、颁)”“禾花(花)”“把”“斗(升)”“担”等入手,我们深入调查和分析了富川民间契约中特殊的计量用字和主要特点,不仅从中窥见富川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和生态智慧,同时也为学界研究富川民间契约文书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成果。
注 释:
①本文所指旱地面积,包括国家自然资源、农业和统计部门的土地分类统计中的旱地(种植旱地作物的耕地、水浇地),也包括不归入其中的林地、山地、畬地及茶园等用于种植树木、油茶、蔬菜等地块。
②契约文书的俗字、繁体字、异体字等均在后面加圆括号注明规范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