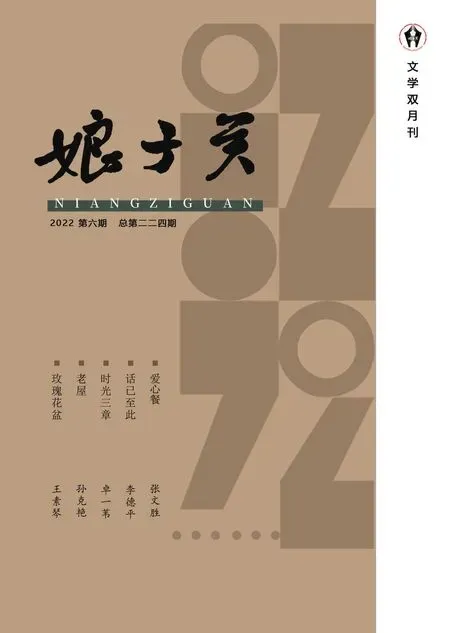话已至此
◇李德平
作家背后的“影子”
作家李劼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著有“大河三部曲”(包括《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长篇小说)。同时,李劼人也是一名翻译家,译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其当时译名为《马丹波娃利》)等作品。阅读《死水微澜》,无论从行文结构还是思想立意,让我们不难想到《包法利夫人》的深刻影响。
其实,很多作家背后都有其他大师级作家的师承影子。比如江苏作家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应该就受到曾在南京旅居15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大地》的影响。同样,张翎的《劳燕》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王小波小说与莫迪亚诺、杜拉斯等人的关系……都有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的联系。
读作品其实是玩捉迷藏。每一个作家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有自己的学习借鉴成长历程。知道了这种隐约的“师承”关系,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的理解。
在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旧瓶里装新酒,这是一种很好的创作办法。但环顾四周,现在不少作家生吞活剥,不但不问青红皂白一把夺过名家的瓶子,而且顺便将名家酒瓶中的“味道”照单全收。
按照鲁迅书账买书的孙犁
孙犁一生追循鲁迅先生,买书也受鲁迅的影响,他的许多书都是按照鲁迅的书账,或是鲁迅给别人开列的书目,或是鲁迅文章中提到的书名,来寻觅、购买的。鲁迅的书账,成为他按图索骥的工具;对不在书账里的书,他有时会生出一种不信任感,以至于不去买它。
孙犁为什么要循着鲁迅的脚步买书?其一,因为孙犁一向景仰鲁迅先生,他知道鲁迅是大文豪、大学问家,对各类文化典籍非常熟悉,又有极高的鉴识力,他购置、推荐的书籍都是值得阅读的好书,可以作为买书的样板。其二,孙犁是想当藏书家的,欲寻购的大多是古旧书;鲁迅也是藏书家,对古旧书有特别的眼力,其书账所记或书目推荐的书,也以古旧书居多,所以孙犁把鲁迅当成购书的“向导”。
文艺创作应关注“不一般”
1963年,曹禺写话剧《王昭君》时接到通知,让他去体验生活,着手写现代戏。蓝天野被派去随从。曹禺告诉蓝天野,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发生了你有兴趣、感觉“不一般”的事件,甚至一个人名,都要把它记下来。
有一次,曹禺到北京人艺看演员排《王昭君》。看完后曹禺对蓝天野说,有一场他是按喜剧来演的。蓝天野当时胆怯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理解偏差了,反复琢磨他的话、反思自己的表演。
蓝天野说,从曹禺身上,自己深刻体会到,文艺创作是创造,要关注“不一般”,不能甘于平庸和复制。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都要永怀谦卑好学之心,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知道的不装懂,沉下心学习知识、体验生活,“如今,无论我是排戏还是导戏,常会想:如果曹禺先生在世,他会怎么看?是不是达到了北京人艺应有的标准?”
创作谈往往是不可信的
近些年来,作家写创作谈似乎成为一种潮流,在访谈中也通常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但要由此对照他们的创作,却多少有些落差。相比写小说,现在的作家似乎分明更擅长谈小说。
作家宁肯因《蒙面之城》《三个三重奏》《中关村笔记》《北京:城与年》等瞩目文坛。长于文体实验的他,把部分创作谈、对话也纳入散文集中。说到创作谈、访谈的“泛滥成灾”,宁肯说,这种现象的流行,可能和推广作品有关,一个东西发出来,选刊选了,或媒体宣传,创作谈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催生创作谈的繁荣。其实创作谈和创作完全是两回事,作家的话(创作谈)往往是不可信的。
对话要跳出专业的藩篱
现在强调跨学科对话,但很多时候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对此,哲学家陈嘉映说,所谓跨学科对话,是因为大家对某些共同的思想问题感兴趣。对话的参与者一般都学有专长。各自所长的东西当然有用,但是在思想对话中,专业训练的作用是帮助你更好地思考我们的共同问题,而不是用专业门槛来限制共同问题。每一个对话人,不管你是哪个领域的专家,都要跳出自己专业的藩篱。对话不能设置太高的专业知识门槛,要淡化学科背景。
不管你读了多少书,讨论共同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像之前没读过似的。对话时不能动不动就拿出自己的专家身份吓唬人,更不能端出自己的一个什么理论作为讨论的前提。对话不能依赖于各自的理论。现在每个教授都有花样翻新的理论,对话的双方得弄通多少理论才能开始对话呀?能够脱开特定的知识、特定的理论,才是思想层面的对话。各自抱着自己的理论就无法对话了。你的理论呢,你自己有兴趣,你好好去建构吧,到了问题上,我们不用你的理论也能发言。我们走在一起对话,正因为我们读的书不同、所熟悉的理论不同,但我们的问题是共通的。
主要看气质
《世说新语》记载有这么一件事,说的是西晋初年的事。
太原人贾充,三国魏时任大将军司马、廷尉,为司马氏心腹,晋初任司空、侍中、尚书令。他的前妻李扶是“官人”李丰的女儿,可谓门当户对。
李丰曾仕魏至中书令,因忠于曹魏,被司马昭所杀。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丰被杀后,子女亦受到牵连,命运发生逆转。李扶与贾充如飞鸟各投林,离了婚,被流放到边远地方,后时来运转,遇赦得以回来。
贾充在李扶遇赦归来之前,已经另觅新欢,娶了城阳太守郭配之女(名玉璜)为妻,晋武帝特别准许贾充设置左右两位夫人。李氏心里有气,住在外边,不肯回到贾充的住处。郭氏假惺惺地对贾充说,想去探望李氏表表姿态,贾充说:“她的性子刚直,又有才气,你去看望她还不如不去。”
心高气傲的郭氏偏偏不听劝告,盛装打扮,华丽丽地带了很多侍婢去李氏住的地方显摆。进门后,李氏起身相迎,郭氏不知不觉地双腿弯曲,就跪了下去行再拜之礼。回到家后,她沮丧地把情况告诉贾充,贾充揶揄道:“我曾对你说过什么?”
高长虹摆筷有规矩
高长虹是现代文学史上狂飙社的盟主,在长达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20多种,约180万字,是当时杂文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高长虹读书废寝忘食,最怕别人说话打扰。他给夫人定了一套规矩:吃饭时,两只筷子放在碗上,表示已吃饱;放在桌上,表示还吃一碗;一只筷子放在碗上,表示还吃半碗。大年初一,夫人按规矩送来饺子和油醋就出去了,估计他快吃完了,进去看筷子是怎样放的,只见高长虹满嘴黑墨,痴痴地看书。原来他蘸着墨汁把饺子吃光了,油醋却一点没动。
吴小如的“两条宗旨”
吴小如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被认为是“多面统一的大家”。著有《台下人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书廊信步》《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莎斋笔记》《常谈一束》《霞绮随笔》等。
说到写学术论文或读书笔记,吴小如说自己只抱定两条宗旨:一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一间,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否则宁缺毋滥,决不凑数或凑趣。二是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要自信,却不可自命不凡;要虚心,却不该心虚胆怯。因为只有昧着良心写文章的人才会心虚胆怯的。
曹雪芹的伟大分为两极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说,曹雪芹的伟大,分为两极。
一是细节伟大,玲珑剔透:一痰、一咳、一物,都是水盈盈的,这才是可把握的真颓废,比法国人精细得多了。波德莱尔不过是刘姥姥的海外亲戚。
再者是整体控制的伟大:绝对冷酷,不宠人物。当死者死,当病者病,当侮者侮。妙玉被奸,残忍。黛玉最后为贾母所厌,残忍。他一点不可怜书中人,始终坚持反功利,反世俗,以宝玉、黛玉来反。
被结构耍了的作家们
曾因《受戒》《大淖记事》等而深受读者喜爱的汪曾祺,喜欢宋人笔记胜过唐人传奇,觉得它短,而且不像唐人传奇一样偏重讲故事。1988年,他在接受香港作家施叔青采访时说,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
汪曾祺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可以说是具有连续性的散文诗;萧红的《呼兰河传》全无故事;沈从文的《长河》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潮、悬念,只是平平静静,漫漫向前流,是一部散文化的长篇小说。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像水。
散文化的小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结构松散,拿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比较一下,就可看出结构上的异趣。莫泊桑、欧·亨利耍了一辈子结构,但他们显得很笨,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这两个作家的小说,人为的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转变多样。打破定式,是这类小说结构的特点,古今中外的作品,不外乎是伏应和断续,超出了,便在结构上得到大解放。
忆秦娥的主角情结
著名编剧秦八娃写出原创新戏《梨花雨》后,竟然决定主角由忆秦娥的养女宋雨担纲。这让年过半百的秦腔名角忆秦娥感到十分落寞,想到这么好的戏剧本子,主角竟然与自己无缘,内心有一种失重与坠落的感觉,认为把自己晾在一边,有些过气的味道。忆秦娥太爱《梨花雨》中的这个角色了,觉得主人公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并且实在不愿意从舞台中心突然退居一旁,哪怕是自己的养女,她也有些接受不了。
对此,秦八娃说,“秦娥,你把主角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了。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尤其这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你希望自己是秦腔的绝唱吗?”
秦八娃接着说:“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若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一行才会大有希望的。我懂得你内心的苦处,尤其到了这个年龄,对舞台更有一种恋恋不舍。可这不是让你退出,我以为是让你前进。你还能继续演你的戏、排你的戏。需要我改,我还给你改戏。但如果宋雨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忆秦娥,那你岂不是能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这个舞台上吗?你都没好好想想这个道理?”
这让我想到当下文艺事业中的师徒(师生)传承关系。有些“名角”占够了风头听尽了好,即将退休还牢牢占据“舞台中心”,生怕“教出徒弟,饿死师傅”,徒弟抢了自己的风头,常常留有一手,不给其显山露水的机会。结果到头来,自己的手艺、学术、思想没有及时传承,最后活成孤家寡人,艺术生命得不到薪火相承、拓展延伸;徒弟永远站在后台观望,得不到在舞台锻炼的机会,延迟了艺术、学术生命的早日绽放。
关于当下的师徒(师生)关系,其他领域不大清楚,在文学评论界,夏志清与王德威的师徒传承,孙绍振对谢有顺的赏识提携,谢有顺对李德南的推荐支持,陈思和对张清华的指导引领……正是这样的“师徒传承”,延续了导师的学术生命。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本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不必惊讶,也不必惶恐。让自己的手艺、学术、思想“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舞台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请问各位大师,你做好让出舞台中央、扶掖推出新人,或者接受弟子的光芒有一天压过你的心理准备了吗?
王安忆的文学症候
“烧饭的女人虽是壮年,四十来岁,却是个无儿女的寡妇,缺乏情欲的生活,人性多少变得枯索。”这是王安忆长篇小说《匿名》中形容九丈镇民政养老院女人的句子。
《匿名》是近年关于隐逸、失踪叙事的一部极其难得的长篇小说。它将大上海的“吴宝宝”通过一系列变故“流放”到蛮荒不毛之地,开启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命运。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重塑“虚构”在小说中的作用,可谓一次艺术的探险,尤其是其中关于人生、世界的哲学思辨,更是加重了小说的“文哲不分家”色彩。
失踪逃离、艺术探险以及生活的迷途,近年中国作家似乎很迷恋这个创作母题。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除王安忆的《匿名》外,鲁敏的《奔月》、李燕蓉的《月光花下的出离》、贾平凹的《极花》、石一枫的《向死而生》皆属此类。它们的特点是采用极端化视角,“一意孤行”,通过绑架、车祸、隐逸、人口拐卖等异常方式,把要描写的人物放置到一个陌生、孤绝的环境,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从而展示人生和命运的种种,重构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
王安忆是位大作家无可争议。但不知为什么,读完《匿名》,老让我想起本文开头引用的这段话。王安忆的小说,艺术感无可挑剔,但正像小说中描写的这位“缺乏情欲的生活,人性多少变得枯索”的寡妇一样,很多作品读起来苍白失血、枯燥乏味,缺乏生活的多姿情味。不信的话,你重新翻开《长恨歌》《天香》等仔细咀嚼品味。
当一个作家艺术感觉驾轻就熟、物质条件安稳优渥,过起“贵族生活”的时候,某种危机也会随之而来。正像某首歌唱的,“别让你的秀发埋没了光彩/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别再默默不语守着你的窗台/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当下很多重量级作家画地为牢、闭门造车,亟须“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接触人间烟火起息,融入这活色生香的珍贵民间。
不能了解的知识,即使记得又有何益?
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他说,大凡编纂教科书,总是找对于那一门学问略有研究的人。对于长期研究的学问,他们往往觉得重要和容易。这样不可不知,那样又不可不知;这样不难了解,那样又不难了解;于是材料愈聚愈多,导致学生的消化力不胜其任。不能了解,即使记得亦有何益?况且总是要忘掉的。而勉强记忆,以及过于努力,强求了解,实于真正的了解有害。
初中学生读历史,实在只要知道一个轮廓,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都丧失掉的。我们现在问:有一条河,其下流是定期泛滥的,因此遗下很肥沃的土地,为世界上最古文明的源泉。这是什么河?在什么国里?不常读书的人,或者仓促之间,竟记不起尼罗河、埃及的名字。然而只要这个人,是受过教育;他所受教育,不是白受的;总记得这条河是在非洲的北部,决不会误以为在欧洲在亚洲,而河流与文明的关系,与最古文明的关系,他也还是了解的。如此,这个人的书,就算是没有白读。
反之,在科举式的考试下读书,即便将尼罗河、埃及等名词背得滚瓜烂熟,而这一条河在历史、地理上有何等关系,与人有什么关系,竟茫然不知。有时或者会照书上所说的默写、背诵出来,而于这句话的内容其实并没有了解。这种教育,就算白受了。
因此在《吕思勉讲中国史》这部书中,吕思勉力矫此弊,凡是不必要的材料都尽力删除,不必要的人名、地名等概不揽入。譬如“近代史”叙清代的学术,只说明考据是怎样一种学问、有什么用处,清代考据家的名字一个也没有列入。吕思勉说,这在以博闻强识为读书,以读书为学问的人看起来,可能是笑话。然而既不懂得他们的学问,知道了戴震、惠栋、段玉裁、余箫客等名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很怀念从前的民间社会
《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这些讲述“名臣断案、侠客锄奸”的故事,一度令少年时期的木心十分着迷。尤其是《三侠五义》这一大读物,当时家喻户晓,后改成《七侠五义》,结构完整,故事奇妙多变,文辞流利明白,比现在的警匪片、侦探片、武打片精彩得多了。
小时候吃过晚饭,佣人就在家里讲这些,讲到忘记时,“日行夜宿,日行夜宿……”但不肯翻书。因为这些,多年过后,木心在谈到19世纪的中国文学时,往事历历浮现,“所以我很怀念从前的民间社会,可惜不再来了。我也不过是享受到一点夕阳残照。那时年纪小,身在民间社会,不知福,现在追忆才恍然大悟,啊呀啊呀,那可不就是民间社会吗?”
木心是当代著名的作家、画家、才子。我们观他的作品会发现,很有见识和书卷气,充满“贵族气息”。但他的才华和作品也不是没有问题,也有局限,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木心自己说的,脱离了民间社会。所以很多时候感觉他的行文和演讲是浮光掠影地“掉书袋”,从书卷中来到书卷中去,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气息味道太淡,让人读起来总有一层隔膜。
反观当下,很多作家、艺术家之所以成不了大气候,犯了跟木心同样的毛病,就是过早地进入“象牙塔”,没机会接触真实而活色生香的民间社会……
《红楼梦》是她这辈子唯一的“情敌”
作家兼记者的赵京梅与一代红学大师周汝昌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到周汝昌家拜访时,他的老伴毛淑仁女士还健在。不记得怎么聊起天儿来,毛淑仁对赵京梅讲,她平生最不喜欢《红楼梦》。赵京梅当时感到匪夷所思,回到家里才越想越明白:《红楼梦》是她这辈子唯一的“情敌”,而且这个“情敌”强大到她终生无法战胜,以至于只剩下无奈……
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一起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视研究《红楼梦》如生命,尽管多少年耳聩目盲,却始终痴情难改。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
但作家的幸运或者读者的幸运,并非家人的幸运。毛淑仁最不喜欢的就是《红楼梦》,换句话说就是,她最爱的是周汝昌先生,是《红楼梦》分去了周先生本应全部赋予自己的爱。
其实不止周汝昌先生娶了“红楼梦”。作家阿来在央视《开讲啦》中也说道,自己每年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青藏高原的地域当中行走,跟这儿的雪山、河流在一起,“我和故乡就是最伟大的爱情”,比起故乡的山河,妻子是第二位的。当阿来的妻子听到这段话,不知会做何感想。
滚滚红尘,痴痴情深。提起自己的作家丈夫,有多少妻子恨不得把家中所有的书架、书柜和图书都一股脑清理得扔到垃圾桶里去啊……
阎晶明眼中的文学批评怪现状
阎晶明是从山西走出的一位文学批评家,曾与董大中、蔡润田、杨占平、谢泳、赵勇等人主持《批评家》杂志,书写了山西文学评论界的不朽神话。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各奔东西、风流云散,但作为文学评论队伍中的一员,我还是常常怀念他们。
在《批评的眼光、态度及风格》一文中,阎晶明提到当下文学批评的怪现状。他说,我们在描述创作总体走向时,最易彰显冷静的批评态度,精神的匮乏、艺术的造作、语言的苍白、形式的单调,都会成为评价某类文学创作或某一种创作流派时的基调。在谈到批评理论时,理论的阐述、大师的训导、潮流的评析、倾向的质疑……都可以见出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心中自有一套或成熟、或生猛的论述。然而,如果是评价一位具体的作家或一部(篇)具体的作品,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常常失去批评的勇气,变得一团和气,热情有余而质疑不足,很容易让人产生批评尺度何在的疑问。
阎晶明认为,理想的批评,应当是批评家以真诚的态度面对作家,以阅读的感悟和理论的武器解剖作家作品,寻找作家的创作规律,总结其创作的特点和风格,并从这风格和特点中发现其优长和局限。当批评家把这种优长和局限和盘托出时,达成与作家对话的目的,告诉他在创作中已经做到的和仍待提高的地方。
弱弱问一句,这样看起来简单的操作操守,我们身边的批评家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编剧质疑道:“导演,那您不是等于否认悲剧的价值吗?”
蔡晓光斜着眼瞥了编剧几秒钟,目光从编剧脸上缓缓移开。他环视众人,不以为然地反问道:“悲情剧和悲剧是一码事吗?悲剧那是深刻的文艺。比如《李尔王》,比如《德伯家的苔丝》,比如《第六病房》,咱们当下怎么深刻?我知道你们内心里都咋想的,总想搞出点儿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是不是?我就不想吗?但是能够吗?最有能耐的编导,也只不过能搞出《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类爱情悲剧!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类东西,再就没搞出过什么高品质的悲剧来。中国连《复活》那样的作品也写不出来!所以,我要求大家摆正位置,都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咱们只不过是吃电视剧这碗饭的人,大家多年来一直不离不弃地跟随我,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别把道走偏了,把饭碗给摔碎了。认认真真地搞出些平庸的东西,这是咱们目前能做的,实际上并没有人真比咱们做得更好,明白吗?”
人世间多少想通过主旋律作品流传千古、争名夺奖的作家、艺术家,在深夜里没事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坐下来喝杯茶,好好琢磨一番蔡晓光导演的话,或许会心平气静很多。
按照文学史写作的青年作家
陈彦的《主角》、滕贞甫的《刀兵过》,是近年看到的两部别有特点的长篇小说。说是别有特点,其实是一次艺术的“大撤退”,倒退到古典小说传统,即通过古老的叙事结构和对典型人物的典型刻画而传达作家的小说观和艺术理想。这在文学界讲究先锋性、现代性的今天,似乎有点格格不入。
其实,各种思潮皆有复古的可能,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有时候最落后的也是最先锋的,最小众的也是最大众的。当下所谓有现代性、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海了去了,但具有传统意味的小说反而成了稀缺珍贵、曲高和寡的小众艺术,与非遗保护堪有一比。
某天有位作家朋友跟我说,当代作家像冯梦龙等古代小说家一样,写成章回小说或许也会赢得成功。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很多作家是不读古典传统小说的,想写也没有这个能耐和根基。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某“大评论家”对某“著名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解读,称其作品如何融合隐藏着高妙的“红楼梦笔法”。其实,这个作家至今没读过《红楼梦》,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世界上没有落伍的流派,只有落伍的作家和作品。现在人们过多看重流派分类,特别是年轻作家,多上了几天中文系,参加的各种培训班也多,新书的作者简介部分,都写着“某某文学院高级研修班学员”字样唬人,一上来就是玩创意写作训练,按照西方文学史套路出牌,进行“教科书式”写作,让人怕怕的,唯恐避之而不及。
文学创作,更多的需要天赋、性灵、感情和生活的投入,专业训练和文学史学习这个可以有,但一定要适度,千万别被它牵着鼻子走,南辕北辙,误入歧途。有人被誉为“某地的卡夫卡”“某地的马尔克斯”“某地的米兰·昆德拉”“某地的博尔赫斯”……不知是赞扬他还是批评他。离开大师仿佛失了魂魄。这样的作家,再怎么模仿大师模仿得惟妙惟肖,也永远是个小作家。请问,“你”去哪里了?
看书名即可,或者三观崩溃
现在是一个看书名、看作者颜值的时代,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书名越来越长,越来越鸡汤,作者照片越来越高大上,越来越漂亮。
《被嘲笑过的梦想,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发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姑娘,脱贫比脱单更重要》《所有的奋斗,都是一种不甘平凡》《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浪费生命》《你以为的极限,只是别人的起点》……没错,你看到的这些都是书名。
有些书,是不需要读的,据说假装读过一本书也是一门学问,核心就是记住书名,不浪费时间进行浏览翻阅。鸡汤文有价值,核心在于信与行。如果你认可信服某段鸡汤的价值理念,就请把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诸实践到“行”上。如此这般,鸡汤才能真正起到励志成功的作用。
其实不止鸡汤图书,严肃纯文学也有不正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套“民国大师经典书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先不说作者,只说书名,《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烟雨纷繁,负你一世红颜》《时光阡陌,你一直未曾走远》《烟花易冷,那些我们不曾懂得的爱情》……
看完作者(分别为鲁迅、胡适、沈从文、张恨水、周作人、徐志摩),你会三观崩溃,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读了“假大师”的作品……
莫言的爷爷原来叫“蒲松龄”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经在瑞典学院发表主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演讲。这篇演讲讲了很多故事,其中最后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是,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莫言在演讲中说这个故事是听自己的爷爷讲的。这些民间故事让莫言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存在。
近日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随手一翻,看到一个故事,名字叫作《孙必振》,故事不长,全文如下:
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读完恍然大悟,原来莫言的爷爷还有个不为人知的小名。这个小名叫作“蒲松龄”。一笑。
“斜杠”作家越来越多
2020年的《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徐小斌:理想主义的一颗棺材钉》的报道。关于徐小斌的介绍是这样的:生于1953年。作家、编剧、画家、刻纸艺术家,主要作品有《羽蛇》《海火》《双鱼星座》等。
看到这里,忽然想到:现在的作家,都是“多栖”人才、“斜杠”作家,除了写作,兼职从事其他艺术门类的人越来越多。写不动了“换脑”从事绘画、书法、收藏、编剧,拍电影、做电商,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而且经济回报似乎要比创作高出好多好多……文学创作的溃败,首先从作者简介的“不务正业”开始……
大器晚成的陈彦,这样书写“艺痴”
陕西作家陈彦在小说创作领域可谓大器晚成,长篇小说《装台》和《主角》甫一出版即获得文坛好评,《主角》更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这部小说有千般好,但我认为塑造的最好的角色是司鼓的胡三元。从戏曲角色的角度来说,黑脸龅牙、疾恶如仇的胡三元应该属于“净”(大花脸)角色。胡三元性格突出、爱好专一,眼里揉不得沙子、脑子管不住双手,一生酷爱秦腔司鼓艺术,可谓“艺痴”。
胡三元对敲鼓痴迷到何种程度呢?书中说,即便在监狱服刑中,胡三元对敲鼓依然不改初衷,见啥都要敲几下,不是拿指头敲,就是拿筷子敲。床沿、门框、水管子,逮啥敲啥。连好多犯人的头、背、屁股他都敲过。凡能敲的东西,他都敲遍了。凡能没收的,狱警也都给他没收完了。可他拿起臭鞋底子,还用指头敲得梆梆响。叫他去给号子刷马桶,他在马桶上也敲。
按照曾经的相好胡彩香的说法,胡三元“一天到晚就是拿一对鼓槌,敲死样地乱敲。你让他帮忙刷碗,他会拿筷子敲;你让他帮忙蒸皮子(凉皮),他会拿铲子敲;你让他扫地,他能拿扫帚敲;你让他摆桌子,他能拿指头敲。百做百不成的货,几时不敲死,他都住不了手的。”“那双贱爪子,几时不敲得抽风,不敲成半身不遂,不敲死,他都是不会回来的。”
能这样痴迷一项艺术的,在我们身边还真是少见。我们经常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此说来,胡三元绝对能算得上一个。
艺林如武林
艺林如武林,处处有玄机。一些艺术界高手,未出名前默默无闻,但冷不丁地冒出来,别人本以为是个嫩芽“新人”,结果犹如悟空出世,飞沙走石,神通广大,让人花容失色,大吃一惊。
比如很多人听说过张抗抗,认为是个大作家。没想到有一天,一个在文坛上从未露面的叫作姜戎的人冒出来,直接拿出一本《狼图腾》,瞬时秒杀文坛,惊艳全国。“度娘”上一搜,原来这个人就是张抗抗的丈夫。
再比如现在国际知名的导演李安,很多年前却是名不见经传,人微言轻。没人给他投资,只能依靠妻子的工资来养活。正是在“吃软饭”的6年时间里,李安静心学习剧本写作、拍摄手法和制作技巧,终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再比如王小波,辞职一心从事小说创作,但生前文坛上几乎没人知道他,生活差不多全靠妻子李银河所“包养”。当有人知道他是真正的火云邪神一般的“文坛外高手”的时候,已经告别这诗意人间,让人扼腕叹息,望尘莫及。
再比如鲍鹏山,通过百家讲坛讲《水浒》,很多人知道了他。其实在上世纪末或者本世纪初,我就在陕西一本叫作《美文》的杂志上看过他对诸子百家的独到解读,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家里至今存有一本他的《先秦诸子十二讲》,不时翻阅。也许是在一所并不著名的大学做老师,影响了他快速成名的速度,但你根本阻挡不住一个人摧枯拉朽、超越前行的脚步……
说了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艺术家,再说一下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周星驰导演的《功夫》中的火云邪神(梁小龙饰),陈德森导演的《一个人的武林》中的封于修(王宝强饰),徐浩峰导演的《师父》中咏春拳武师陈识(廖凡饰)……在开始露脸之前,都是其貌不扬的人物,但一出手,几乎天下无人能敌。
高手在民间,大野龙蛇。我们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求艺、创作态度,不断追求上进。否则,姜戎、李安、王小波、火云邪神、封于修、陈识……这些卧虎藏龙般的高手,或许有一天会忽然冒出在你面前公然“踢馆”,让你从此六神无主,没了招架。
好作家印数仅三千册
夜读王祥夫的随笔集《以字下酒》,感觉写得真是好;文图结合,印刷精美,制作得也很好。但这么好的作家作品,那么知名的出版社,印数却仅有区区3000册。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市场影响力尚且如此,更何况名不见经传的甲乙丙丁如我辈。想到此,感慨良久,不胜唏嘘。
好奇的猴子
须一瓜小说《淡绿色的月亮》,讲的是在遭遇深夜抢劫中,妻子芥子认为自己强壮魁梧的丈夫桥北没有尽到挺身而出的责任,是个窝囊废,从此夫妻之间心生罅隙,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和世界。这篇小说中,大故事中还套着两个小故事,都是警官谢高向受害人芥子讲的。
第一个故事是说,从前沙漠上有一只聪明的猴子,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可是有一天,它在一块大石头下面突然看到一条毒蛇,当场就吓晕过去。它知道那块石头下面有条蛇后,每一次经过那里,都忍不住想翻开石头看看,可是,每次翻开石头,它都看见了那条毒蛇,结果,每次他都会被吓晕过去。即使这样,每次路过,它还是想看石头下面的东西……
第二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在省公安厅的选调生,在基层锻炼期间因追捕通缉犯而受伤。手术的时候,辖区很多老百姓自发去看望他,送水果,送土鸡,熬营养粥。当年度,这个选调生就被评为区人民满意好警察,并记三等功一次。可是现在,这个人早就放弃了锦绣仕途,甚至不愿再做警察。原因是他在火车上遭遇过一次匪徒打劫,只保护了有限的几个陌生人,而没有进一步挺身而出,和匪徒拼个鱼死网破,事后遭到车厢几乎所有人员的攻击和误解。人们对车厢里只有一个警察却需要面对七八名歹徒,而且有两把刀紧紧顶在他腰上的事实视而不见。从此,这位人们心中的好警察臭名远扬、内心崩溃……作为势单力薄的警察,两害取其轻,虽然是更正确的抉择,但总有人心安理得地宁愿看到烈士,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英雄梦破灭,永远不会原谅这位警察,认为他活该。
故事讲完后,谢高对芥子说,“我知道他过得很不好。因为还有更多的、像你这样的人,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他的压力太大了,经常彻夜失眠。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他知道他对不起很多人,所以,他很想忘了那些事。可是,每天都会有人提醒他,煎熬着他。他想忘也忘不了了。他不愿看到石头底下的东西,可是别人会翻给他看。他只能远离沙漠,逃离那块石头。”
我们很多人其实就是那只猴子,原来生活得挺好,石头下面有什么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不该探究的,就要学会放过去。但我们总是绕不过去,折磨自己。因为女人总希望男人是勇敢的,他有勇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己心爱的一切。
可事实上是,即便自己的男人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结果也可能仍然是保护不了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东西。有些事情,一旦想起,就再也不一样了,即便不愿意这样,也永远回不去了……看过一句话:所有小说里哪一种情节都会落伍,只有写人性的情节永远不会落伍。信然。
“走弯路”的庐隐
庐隐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重量级女作家,以《海滨故人》等享誉文坛。在关于庐隐的文学价值及文学史传播方面,著名文学批评家茅盾是极其重要的推动者。在其撰写的《庐隐论》中,茅盾认为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是被“五四”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女性,是“五四”的产儿,对庐隐身上带着的“社会运动”的热气以及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寻找题材大加褒扬。
茅盾指出庐隐的小说“展示了其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使得庐隐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价值获得某种提升;另一方面庐隐以此为标准削足适履,表现自己并不熟悉的“社会生活”,走了一段创作的“弯路”。庐隐放弃熟悉的领域,去追求题材的丰富性,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她因此而确实获得更多的发表作品的机会;另一方面却是以有意无意间牺牲自己所长为代价。
没有亲身经历和体验,再加上想象力的有限,在这些被夸奖为“社会题材开阔”的作品中,庐隐显现了创作者的吃力。她无法传达出一位女工的生活经验,也无法表达生活在困苦中的人们的心声。庐隐的创作及发表经验,既可以为上世纪20年代爱好文艺的女学生如何在新文学期刊的帮助下成长为女作家提供佐证,也可以看作一位女作家所采取的“策略”或是所作出的“牺牲”。
1922年底,写作经验日趋成熟的庐隐开始回归自我,创作了一系列以女学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即《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从这些小说开始,庐隐为文坛提供了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也找到了一种与个人气质相吻合的表达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张莉教授关于茅盾批评引导庐隐创作的观点,值得每一个作家省思。作为作家,我们可以为某位呼风唤雨的大评论家对自己作品的认可而信心倍增,但一不小心也容易邯郸学步、画地为牢,被带入沟里而无法自拔。
以前的人长话短说
谈到“漫说文化”丛书,陈平原说,以前的人长话短说,今天的人生怕不够面面俱到。“五四”到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擅长写短文章,寸铁杀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一个片段一个侧影就打住了。即使比较长的,也就是三四千字,一般一两千字就是一篇。他们的美文、随笔、杂感、小品都很好,那个风气、那种状态下写的那些“小文”能够留存下来。
今天的人一篇散文动辄上万字,面面俱到,生怕别人攻击他不够全面,反而难以留存久远。同样,以前“小而可贵”的书不少,今天的书越写越厚。有些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多情况下不完全是专业论述,而是舍不得割舍,学不会剪裁,罗列一大堆材料。正因如此,我对北京出版社之前出版的“大家小书”系列十分推崇。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应为自己留出时间,多读一些“薄薄的厚书”,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