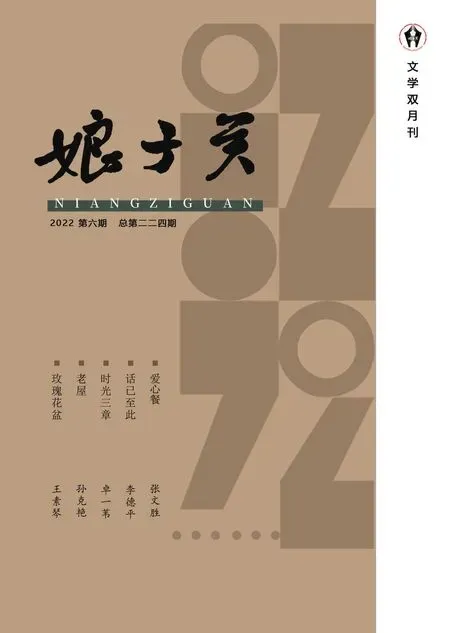雄奇磅礴 超以象外
——品读张四春先生的绘画艺术
◇张旭东
早在许久以前,就听闻张四春先生的大名。作为中国美协会员、山西省美协常务理事、山西省工笔画协会副主席、山西作家书画研究院特聘画家、阳泉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一直钟情于翰墨,笔耕不辍,绘就出很多足以流传千秋的国画作品。
我曾多次参观过市里举办的大型书画展览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四春先生的画作,远远看去,大气磅礴,云雾苍茫。赞叹之余,总会被这种沛然而莫之能御的气势所折服,因此便有了想写些什么的冲动。尽管作为晚生的我才疏学浅且与先生素未谋面,但依然愿以绵薄之心慨然而书,为国画艺术,更为先生对祖国山川深深爱恋的赤子情怀。
张四春先生的山水画以浅绛设色居多,从笔墨间透出的变幻与灵动可以看出,他自中国传统的古典山水范式中兼收并蓄,在“法古而不泥古,源古而高于古”中自成一格,受到了中国山水画界的广泛赞誉。先生笔下的山水世界,把大自然的深度与厚重挫于笔端,给人以雄浑深邃的无穷意境。无论是飞瀑溪泉、怪石嶙峋、苍然古木,抑或是山峦奇崛、曲径通幽、茅舍缀景,无不呈现出积健为雄的浑灏之胜慨。对山石、林木、岚光、烟霭、云雾的写意,情趣盎然,写尽千山万水之神韵。先生的画作多采用高远和深远的构图,气象凝重,林树丰富多变,把北方山石的质感,云树的苍劲表现得淋漓尽致,所用的披麻皴、雨点皴、乱柴皴、折带皴,或秀润,或骨感,把万壑千岩描绘得莽莽苍苍。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一书中写道:“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可以说,中国山水的传统所营造的,是师法于自然,却有别于自然的另一重化境。张四春先生曾经入选全国首届中国山水画展的作品《春风徐来》,就是这样的一幅杰作。
在画中,先生所营造出北方高山大壑的雄伟气势与早春时节清新恬淡的气息扑面而来。画面近景是一组组碎石与生长其上的杂树,中景以弯转的山石、轻薄的云雾相衔接过渡,承接四座山峰。主峰居于画面左中位置,在树木丛生的沟壑之间,溪涧从山谷间若隐若现地潺潺流下。深山中,有粗壮的大树、虬枝盘旋的古木,有的用双构、有的用胡椒点、有的用菊花点,变化万端。山石亮处皆以浅浅的赭石渲染,暗处则用湿墨相衬,远望水汽氤氲,为这早春季节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而入选全国第七届美术大展的作品《大风从门前刮过》则以一种动态的美,把一帧极具时代感的画面,以写意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新旧时代交通对比的景象。近处,一条留白的蜿蜒小路盘旋在一座山头,画面中这条小径的沧桑感仿佛一下子把人们拉回到古代时光当中。从深沟底、树草间绕来绕去的古道,显然见证过无数行旅人满面尘霜的容颜,见证过驼铃悠扬的艰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跟不上社会飞速的脚步。从画面右边贯穿全幅的一条高速公路,成了整幅画的中心,这条路连接着大山深处,通往希望的远方。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有客车、大货车、小轿车,均以淡淡的朱砂或藤黄设色,比例适中,与山峰形成鲜明的对比。远山是用小披麻皴勾描山峰,层层叠叠,圆润而阔大,极具震撼力。
从这幅画中可以读出张四春先生的艺术主张,他饱蘸对时代的炽热情怀之墨,挥洒讴歌社会变迁之笔,用情,用爱,皴擦出独具创意的精神高峰。
中国山水画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人物画中分离,至隋唐时代成为独立画科,到五代、北宋成熟起来,逐步形成了特有的美学内涵。早在唐、五代时,人们就认识到绘画艺术的本体是“意象”,绘画艺术的创造,也就是“意象”的创造。于是,“同自然之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等美学命题相继兴起,成了光照千载的翰墨之道。
大唐画家、绘画理论家,山西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彩。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风不待五色而綷。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以水墨代替青绿着色的山水画,从此踏入一个新的阶段。再如王维的《山水诀》一开始就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由此得知,水墨的颜色最符合造化自然的本性,因此水墨山水画在绘画中占有最高的位置。
从张四春先生的画作之中,我看到了继承与创新的水乳交融。先生取景造境眼光独到,笔墨意趣纵肆而飞动,尤其是中锋用笔,一波三折,力度苍劲。曾入选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精品展的《高山流水》就是这样的力作。初观此图,近景有泉石老松之苍秀,中景有古木葱郁之繁茂,远景有重峦烟岚之缥缈,展现出一派苍茂野逸的山林韵致,加之淡淡的赭墨敷色,又烘托出静谧之感。细细观之,几棵虬曲老树姿态各具,用写意的笔势勾画,或如弯弓射月,或似蛟龙出海,或如冲天之矛,为画面增添了如许生命旺盛的张力。左边的一个临近流泉的平台上,一位老者盘踞而坐,正在临清流抚琴,右边的一位老者身负柴薪,手持策杖,正在专心地聆听琴声。再往上看,远山重峦叠嶂,巍峨耸立,山腰、山巅的蒸腾之汽如云似雾,使画面如仙境般奇幻而唯美。
这幅描绘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画作,在先生笔下展现得神采飞扬。“不装巧趣,皆得天真”的笔墨表现力与传奇故事完美交汇,传达着张四春先生心中审美意象的互动维度——万古琴音伴流水,千秋画卷写青山。
而另一幅获得国奖的《山居吟》,则是先生隐逸情愫的生动写照。画中岩峰雄如虎踞,在奇形怪状的山体之间,湍急的溪流欢快地跳跃着与世无争的脚步,五间深掩于林中的茅舍里,三位高士正把盏畅饮,似乎在吟唱着不为俗世所累的宫商之音。此图在技法上,先勾后皴,且施以披麻、牛毛等皴法,细密紧致,轻松而自然,给观者一种超脱之思。
在先生从艺几十年的时光中,他平日里不仅勤于练笔佳作迭出,而且遍访名山大川、风景名胜,画了大量的水墨写生作品,找寻到了一条在山水写景中创作的新路,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趣和极富魅力的笔墨风格。比如斗方画作《中条游纪》《云台纪游》《华山纪游》《壶关飞瀑图》《冠山松烟》等,无一不是先生游历、神思、沉淀、妙造后的逸品杰作。
在这些画中,有的取材细微,一丘一壑,一桥一溪,水中见墨,晕染并用,极具苍秀沉郁的美感;有的因物立意,所画之景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形象雄阔,一派阳刚风骨;有的造型高古,用笔兼工带写,老树的超拔气概,生命顽强的表征,树干上瘤疤所记录的成长艰难纤毫毕现;有的风格飘逸,将线条勾勒与墨色晕染并用,留白巧妙,疏密有序,虚实相生,彰显着刚健与柔美的意象之境;有的在水墨淡彩之上薄罩青绿,用色明丽,画境中的雅气、静气,沁人心脾。
先生有句话很经典:“用艺术之笔描绘出反映时代的画卷,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更是伟大使命。”听到这样的话,心中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展读张四春先生的诸多绘画作品,有一大部分是生猛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力,透视着与社会、生活、民众、家乡息息相通的时代印迹。这些作品思想性、情感性、艺术性兼具,有道德、有温度、有筋骨、接地气,牢牢植根于大地,用或长或方的画卷回答着人们的审美需求和艺术心声。例如获得国奖的作品《清风》、《九关万仞》、《大地的脊梁》、《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年画《合家欢乐》等,都是用心、用情、用爱着意描绘出的时代画卷。先生用朱砂晕染出红色文化的热烈,用赭墨皴擦出家乡山河的壮美,用青绿描摹出自然生态的景致,用五彩描画出和谐社会的家庭温情,帧帧画作优雅、素朴、崇高而隽永。
寄情于画,以诗言志历来是画家切身感悟的真性流露。张四春先生从艺几十年来,秉承诗、书、画、艺的古老传统,国画中所题的诗可谓是简约中见博大,平实中显生趣,自然中蕴哲思。比如《四条屏》中所题“春风徐来景色新,景中还含往年英。茅荻客语论何事?静观青山与白云”。一种豁达的心境仿佛可以融化世间的任何块垒;又如题画诗“风蒲水阔到黄昏,烟楼天空没远邨。画碧澄波寒浸月,荒山无处觅隐君”。深深地表达着先生沉浸于山水画卷的那份自得与从容,听风赏景,与云漫步,悠然观清流;再如题画诗“山无成法任意皴,雾出四面入画屏。沵有小筑人不识,非是琴声何处寻”。不仅把先贤石涛所言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阐述得浅显易懂,更把山、水、雾的美态叙写得引人入胜,加之与画中动态的碧波清音之韵,雾锁冈峦的缥缈之姿,还有点缀于山间的亭台相伴,远远一望真恨不得走入画中隐居在此,一任岁月更迭,不再谈红尘俗事。还有“轻利丹青实,远名画不媚”的风清骨峻,不屈气质的心灵呈示,“荒邨有高士,山野奏笙簧”的羡慕之思等等,无一不是先生内心世界与山水世界完美交融的鲜亮展现。
之所以用“雄奇磅礴,超以象外”来概括张四春先生绘画艺术的美学品性,是因为先生在笔与墨,水与颜料,意境与气韵之间,“师古而不泥古”,绘画作品透露出一种豪放、浑厚、大气、豁达的美学表征。可以肯定的是,先生雄浑壮丽的绘画作品,审美底蕴来自博大的人文情怀,来自人生体验的深邃思考,来自天赋性情的相互交汇,进而转化为艺术壮美的高逸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