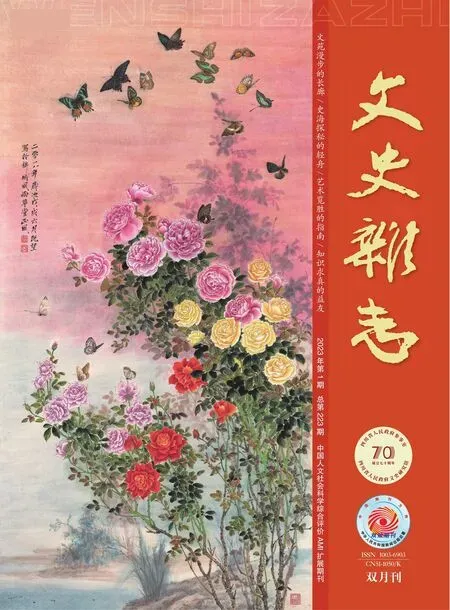沈三白与华萼
江苏 张一民
2008年12月某日,我在华夏收藏网上,见到有收藏爱好者发布了一幅色泽古旧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图》,缣幅左侧上方有题诗,曰“牛郎织女隔绛河,又喜秋来一渡过。岁岁寄郎身上服,丝丝是妾手中梭。剪声不觉和肠断,线脚哪能抵泪多。长短自然合新样,不知肥瘦但如何?”落款为:“雨堂外史华萼”,钤有白文“华萼”和朱文“春楼”印两方。从题诗的口吻和落款印章的称谓,知作者是一位女性,这使我想起了《浮生六记》的作者沈三白(即沈复)的姬人,名字也叫“华萼”。
沈三白在前妻芸娘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三十日去世以后,即入四川巡抚石琢堂幕下。嘉庆十一年十月初,三白又悉其子逢森在故乡病夭,悲怆万分;石琢堂闻之,亦扼腕痛惜。为了使三白有嗣可继,琢堂遂赠一妾与三白,使得沈三白“重入春梦”。
民国初年,藏书家陈乃乾收得沈三白藏印拓文及手迹,据他以笔名“乃公”发表在上海《小日报》1934年8月23日第2版上题为《沈三白遗迹》一文介绍,该印拓文有“曾经沧海”“雪月浸梅花”等闲印,又有“华萼”“宛如”“宛如女史”等名号印。手迹是沈三白题跋,曰:“楚桥先生为余镌,又为余姬人作小印三方,追汉摹秦,褒词无措。余耽此已四十年,自谓深得南宗之秘,今则退之三舍矣。长洲三白沈复”。题跋下钤“沈”“复”小章。陈乃乾曾将此件(印拓文及手迹)拿给文坛好友俞平伯先生鉴赏,俞为题七律一首,发表在《星报》1948年3月5日第二版署名平伯撰写的《沈三白之印》文中,其诗云:
曾经沧海难为水,尘梦温时不驻春。
故黛芸香总消歇,新枝华萼可重芬。
翻征玉筋绸缪共,谁见青衫涕泪频。
五柳园中一宵火,栖鸦无处吊斜曛。
沈复在跋中提到为其姬人治印的楚桥先生,姓黄名学屺,字孺子,号楚桥,江苏如皋人,工诗文,精研六书篆隶之学。他治印古朴有致,疏朗潇洒,白文工整,用刀沉着痛快,朱文线条雅正秀润,其成就得到朱珪、梁章钜、石琢堂等人的推崇。如皋冒鹤亭曾为其《印稿》作序,而沈三白晚年曾在如皋作幕,与冒鹤亭亦有交往。由此可见,这件文物中的手迹有可能为沈三白手书真迹,印章也确似沈三白请楚桥为其姬人所刻。但是有一点,陈乃乾先生对此认证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俞平伯先生也语焉不详,最终确认,还要有旁证资料来支撑。

俞平伯题诗手迹
时隔8年,也就是在2016年7月,笔者翻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2册,在康发祥《小海山房诗集》卷三中发现了《题沈三伯福携姬归去图》绝句三首,证实了陈乃乾、俞平伯先生的认定,华萼确有其人。
康诗前有小序,曰:
三白佐使琉球,姬人华萼字宛如,善舞枪击剑,出游必偕,特筑室于吴门,有终焉之志。友人携图征诗,余惜未谋面,走笔以应。
诗云:
天下奇人一再出,入扶馀与封疏勒。
尔挈红颜海外归,飓风酿出胭支色。
丰貂盛鬋姿容逞,枪舞梨花湿红粉。
相君不愿画凌烟,能如是乎汝偕隐。
秋风斜日鲈鱼香,三高二俊畴短长。
珠厓园里菟裘筑,闻说高风老是乡。
该诗作者康发祥(1788—1865),字瑞伯,号伯山,江苏泰州人,岁贡生,官太常博士,擅长诗古文,著有《伯山文集》《伯山诗钞》等。诗题中称沈三白为“沈三伯”,又将其名讳“复”误写成“福”,而在诗序中则称其字为“三白”,这可能是由于康发祥与沈三白素未谋面,对其姓名字号不甚了解而不确定以致误写。分析这三首诗,我们可了解到,“重入春梦”的沈三白对姬人华宛如关爱备至,“出游必偕”,甚至在佐助使臣前往琉球出席分封大典的航程中还带上她。经历了海上往返漂泊,在狂风巨浪的历练下,华宛如越发显得风姿绰约,芳容昳丽。她不仅是“美而韵者”,还会舞枪击剑,英姿飒爽,与儒雅倜傥沈三白正好相配,天造地设。沈三白《浮生六记》中原有第五卷《中山记历》一章,可惜已缺失。后有人声称发现佚文,然其所出示的记叙琉球经历中从未提及华萼。按照沈三白的情性和行文风格,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其作伪明显。从琉球归来后,华宛如尊重沈三白“不愿画凌烟”的选择,放弃使臣将委以重任的建议,效仿吴地历史上的“三高”(指范蠡、张翰、陆龟蒙)和“二俊”(指陆机、陆云)等人物,相携归隐田园,老此终身,成为高风亮节之士。康发祥诗中所谓“珠厓园里菟裘筑”,交代他们的归隐之地。“珠厓”通常指南海琼州,以临水靠山出产蚌珠而得名。这里用作借喻,“珠厓园”实际是指沈三白和华宛如于苏州邓尉山香雪海附近构筑的一处居所。每年春天,这里的梅花怒放如攒珠,形成花海一片,三白和宛如在此构筑的“菟裘”,不正是处在海之一隅吗?取名“珠厓园”最贴切不过。况且,沈三白素有梅花情结,自号梅逸,取“梅妻鹤子”之意,又常以梅花作绘画治印题材。嘉庆十年(1805年)乙丑孟春,43岁的沈三白与好友夏揖山及其家人游灵岩、邓尉,由费家河进香雪海观梅,绘《幞山风木图》。可能在那时,三白已经萌生晚年归隐的念头。所以,在道光三年(1823年)沈三白60寿辰时,无锡人顾翰作《寿沈三白布衣》诗,诗中有“期君结屋相往来”“岁岁同看邓尉梅”等句,即道出了沈三白的夙愿。

康发祥《小海山房诗集》之《题沈三伯福携姬归去图》书影
康发祥《小海山房诗集》所收诗按干支编年排列,《题沈三伯福携姬归去图》诗系于“癸未”,正是道光三年。此时有人为沈三白作画,又邀康发祥题诗,可能也是为沈三白60寿辰而精心准备的一份贺礼。对沈三白来说,佐史琉球,是他一生得意的壮举;携姬而归,也是他一段出彩的佳话。虽然发生在十四五年前,但绘画者能想起这样的题材,说明是动了心思的。其人与沈三白不止是一般地熟悉,而且是推心置腹的挚友,极有可能是“萧爽楼”中画友,诸如鲁半舫、杨补凡、袁少迂、王星澜等人中的一位。康发祥虽然未与沈三白谋面,但通过绘画者多少了解沈三白的风流逸事。他在诗中称三白为“天下奇人”,可见三白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这或许是因为《浮生六记》在此时已成雏形,且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缘故。
沈三白携姬自琉球回苏州还是布衣身份,为了维持生活,继续入馆作幕,在如皋又待了10年(1814—1823年)。他在香雪海构筑“珠厓园”,把华宛如安顿好,就开始了“如皋—苏州”两地奔波,和华宛如也有过陆陆续续的经年相思和小别重逢,所以才有其在《坎坷记愁》中所述的“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之一番感慨。他们真正的实现全身心归隐和厮守“菟裘”,可能是在沈三白过了60寿辰之后。
再照应文章开头所述的《七夕相会图》,该图题诗作者雨堂外史华萼是否就是沈三白姬人华萼?两相比照,有相似之处。一、同名同姓;二、通晓书画;三、夫妇曾有离别。当然,仅凭这几点,我们还不能将她们划上等号,毕竟还缺乏直接的证据;何况二人的号不同。(一号雨堂外史,一号宛如女史。)不过,历史上一人取几字多号的情况也是有的,但还要有待我们借助相关资料的出现和发掘来进行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