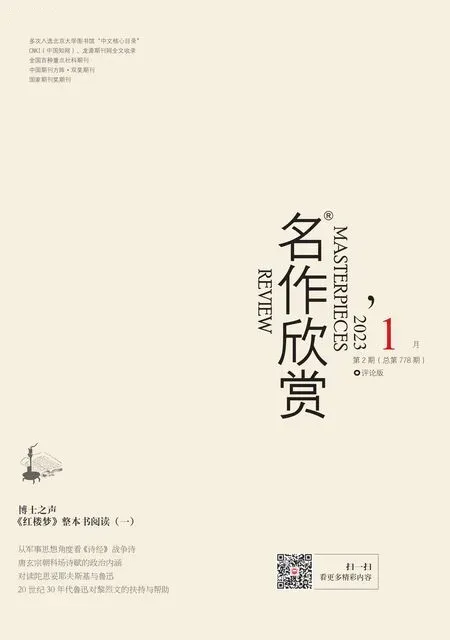“人以圈居”:接受美学视域下短视频圈层化审美研究
⊙吴娟 梁文勤[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0]
人以群分,即人总是乐于向存在相似特点的群体靠拢,包括境遇、兴趣爱好、地位,等等,所谓“性行相同,亦为其党”,圈子是常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群连接的一种模式。“圈层”一词最早出现于人文地理学科,后延伸到社会学研究体系。①现代媒介的技术革新与即时通讯的发达和社交平台的广泛运用,使人和人之间的社交突破了地理限制,实现了无限拉近,加之文化产业的高度发达,信息大爆炸时代的圈子,存在形式及规模与种类得到了新的拓展②,各类小圈子让性情相投的人们尽情享受着精神的交融,寻找着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网络的虚拟性也很大程度上消减了现实社会中的层次差异带来的距离感,或者说,网络圈子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与现实世界存在天然的隔膜,故而圈层在网络世界多表现为摒除显性层次感的纯粹的开放性的“圈子”,这点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青少年群体受社会现实影响较小,他们在交流择友上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喜好及精神层面的认可。青少年群体具有其独特性,一方面他们自我意识觉醒并慢慢成长,在向内心目标效仿的同时,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肯定,另一方面他们多数时间处于学校和家长的管理下,自我支配的时间多为碎片化的,故而他们在对象的选择与信息的甄别上尚有欠缺。移动端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已是既定事实,通过移动端看视频成为青少年消遣娱乐、放松精神的一大选择。基于此,我们试图从接受美学角度探讨青少年群体在短视频观赏对象呈现的圈层化的沟通方式,并寄以精准施策,力求为青少年们构建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互联网生态。
一、短视频审美圈层文化的形成
短视频行业的迅猛发展及短视频受众审美圈层的快速形成和稳固与移动设备的普遍使用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密切相关。传播媒介及周边技术早已突破了工具的窠臼,成为改变人类社会文化态势的力量,信息传播方式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带来社会文化态势乃至生活方式的变革。现代社会,数字化信息技术早已渗入人类的生存基因,电子媒介铺设的信息网络对人类社会的空间及文化仪式进行了重造。移动端展示的影像符号将文字、音乐、影响融合为一体,前所未有地方便了人类的语言沟通。伴随短视频发育成长的推荐算法更是做到了精准到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将短视频受众们欣赏视频时搜索、关注、停留、点赞、评论、转发等数据搜集后,根据对象的偏好和行为图谱给出大概的“用户画像”,然后有针对性并投其所好地推送内容以取悦用户,提升用户黏度,并进而做出更精准的“用户画像”。人们陷入了被动的舒适区,在推荐算法私人订制的圈子里打转,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海洋里的迷航和超载的问题,客观上也对受众圈层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是短视频审美圈层形成的主观原因,面对短视频携带的信息,受众进行解读的过程存在三种可能:主导的、协商的及对抗的。③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的解码过程在欣赏短视频时已初步完成,囿于各自的知识水平、经验、生活际遇等造就的偏好和各自的理解,受众在解读时难免会陷入一个大概的既有的区间,无论是个体寻找更多同道者的索求抑或信息技术有意无意的引导,他们总是能找到更多的携带相似信息的短视频或知识,强化对自己的肯定,以某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信息为核心,圈层在无意识间慢慢形成并壮大乃至形成集体意识,受众渐渐以集体意识特别是意见领袖的观念而非个体意识对信息进行解码,深化并加固圈层的壁垒。圈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个人意识与其他主流价值间的博弈提供了助力,同时外在的社会规约难以影响圈层内意见的交流与调和,圈层对一定范围内的话语空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垄断。
同时,APP 内嵌的工具降低了短视频制作的门槛,短视频制作者们不光有专业团队托底的从业者们,也不乏单打独斗的票友们,短视频的受众既是参与者,又是潜在的传播者和制作者,这些身份的互相转化使得以每一个受众为中心点形成了一个个的辐射圈,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圈层的传播和深化,这对大众话语权的扩张和个人诉求的满足及表达无疑是有益的。大众由传统媒体时代被动的信息获取者成为主动的提供者,自媒体、直播平台等则是短视频深化发展的必然成果,大众得到了自我创作与表达的平台。
以短视频的传播为代表的网络语言使用与传播小圈子的兴起以及人际关系中传统的血缘和地缘纽带的弱化,新兴的圈层文化传播现象开始在虚拟网络中广泛出现。④
二、短视频内容的圈层审美意指
短视频作为网络时代的新产品,其诞生之初即带有受众和互动的标签。“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⑤,精神产品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⑥接受美学视域下,短视频最终是制作者和接受主体一起完成的,开始是制作者生产了短视频,后来是接受主体的审美体验反馈至制作者,最后在一次次的不断磨合、接近中重构并确定圈层的主旨和意指。视频内容受众的圈层化可令受众享有更自我与垂直的审美体验,制作方亦可精准定位,创造具备更细化更鲜明圈层特征的视频内容以增加与受众的黏性。换言之,短视频制作者们根据前期市场调研并结合自身条件统筹确定视频的内容、风格、细节上的倾向性等,制造的“作品”上传到平台后,一方面对受众造成了影响,但另一方面受众们的点击、评价、转发以及再创作直接影响着作品的热度和传播度,有些时候制作方出于逐利的需求甚至失去部分自主权甘愿沦为大众的提线木偶。
接受美学认为审美有三个范畴:创作、感受和净化。亚里士多德认为“创作”(Poiesis 又译作“创造”)既指的是创造某物的能力,同时也是人们在这过程中得到的快感,即艺术生产的审美经验;“感受”(Aesthesis)又称为“审美愉悦”“审美感觉”,主要指的是审美活动的接受方面,是受众在欣赏时产生的复合的、明了的知觉;“净化”(Catharsis)音译“卡塔西斯”,亦译为“陶冶”,是人们在欣赏导向为激励性的诗歌、讲演等作品时情感激荡产生的快乐,心灵得到解放的体验⑦,是艺术与接受者之间交流性的审美经验。创作、感受和净化并非是有等级差别的层次不同的解构,而是一个结合体,即三者并非概念化认知中泾渭分明、条块清晰的封闭概念,而是审美经验内在的三个体验维度,它们共同构成了审美经验生产——接受——交流的整体图式。
短视频的传播过程将审美的三个基本范畴完美地融为一体,受众是感受者,同时又可以成为创作者,平台的反馈与交流机制则又可以为他们提供沉浸式的快乐。短视频制作者与受众在审美体验中的交互甚至是人性深度的一种自我探寻,在审美经验经过所有阶段以后,那种有限与无限沟通的审美同一性即向自己讲述一种可能性,就是不放弃对自身同一化的追问。⑧受众在短视频审美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本真之我”,当然,短视频审美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独具其“网感”审美体验,网感往往被看作是网络社会中的一套流行话语组合⑨,是源于网络经验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具体的表征为囊括了网络用语、思维习惯、网络视觉审美在内的审美集合。基于接受美学“作者——读者”的互动关系,制作者会根据“网感”的审美诉求创造出与圈层更靠近的短视频作品,加强圈层与作品的凝聚力,使受众形成相对集中的有别于圈层外人群之审美期待的审美诉求。
三、短视频审美圈层形成对审美主体的影响
短视频的传播客观上为大众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供应服务,并满足其应用或消遣需要,而对短视频平台而言,受众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商品存在的。平台一方面将短视频作为商品供给受众,另一方面受众的注意力也被作为商品贩卖获利,平台对短视频优劣的评判标准自始围绕着作品的被关注度,这无疑对短视频整体内容的庸俗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庸俗化的短视频内容渐渐让审美主体向同质化的方向发展,短视频内容影响了审美主体的意识,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短视频的形式大于内容,制作者将完整事件分割为碎片制作成短视频上传,将整个事件的重点模糊化和流俗化。审美意识是人对对象的感知,受众在进行审美活动时会不自觉地用过往经验对审美对象解析和理解,这其中必然倾注了一定的情感,而当审美对象由碎片化信息堆砌而成时,体验与感知混乱而混沌,审美活动只带来了时间的流逝和观感的盲目,碎片化的审美体验谈不上是愉悦的经历,审美应有的深度与人文关怀自也荡然无存。
青少年正处于性格形成期,知识储备与人生阅历尚处于稚嫩阶段,与成人相比更渴望认同感和体验感的交流,短视频的交互与实施分享等功能不仅满足了青少年表达自我的需求,也给予青少年们情绪释放的通道,使他们沉醉于享有一定话语权的满足中,短视频给青少年的审美观点、自我认知与道德观念的塑造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个人选择和大数据推荐的引导下,青少年必然渐渐与志趣相投的人无意识地走到一起并结成一个个松散的受众圈层,并在某一方向逐步深化。圈层化传播的实质是审美主体对同质的认同与建构,新的技术手段使得圈层的聚合超越了距离和时空的传统限制,这是技术革新的便利,也是青少年的想法与生活方式同化的表现之一。圈层给青少年构建了“共景式”的交流意境,青少年出于闲暇时间有限的天然限制,很难成为所在圈层的意见领袖,而在算法机械化思维对用户的图谱刻画及描摹后的判断下,适量的相关领域的内容会被推送给用户,这种审美消费似乎使受众变得更加愉悦。“凝视”是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中经常提到的重要概念,指带有权力运作、欲望纠结与身份意识的观看方法。⑩受众被赋予了“看”的权利,确立了自身的主体位置,被看者作为被“看”的对象,则被物化和他者化。拉康认为,凝视贯穿于看与被看的全过程,无处不在,既来自主体,也来自客体,这种自我与他者相互交织的关系主体的精神意象被逐步建构。在大数据时代,随着受众浏览时间的积淀,算法对之进行的刻画和描摹渐趋精准与固化,APP 也机械地依着刻画向其首先展示他最可能感兴趣的内容,用户可选择面被动地越来越狭窄。作为青少年是很难主动发现这点的,算法机制互动下的他们宛若被置身偌大的回音室内,同质化、娱乐化的信息不断回响,切断了青少年“信息偶遇”的几率,习惯于信息投喂和观点灌输,对同类同质者组成的圈层产生高度的依赖感,思维模式逐渐固化,逐渐处于“信息孤岛”之中。
短视频内容的整体质量也良莠不齐。流量为王的时代,相当数量的创作者被短视频作品门槛低、成本不高的优势吸引,“作品——读者”的原有审美关系趋向于广撒网式的“自产自销”,视频质量参差不齐、低俗化明显,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网红层出不穷,青少年欠缺深度思考和去伪存真的能力,极易被这些热闹而浅薄的内容吸引,渐渐沉浸其中,被视频输出的价值观浸润影响而不自知。这些价值取向有偏差的短视频对青少年造成的道德冲击和精神污染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建构,让他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产生失衡。同时,当认知一定程度上圈层化后圈层内部构成的虚拟景观社会共同为青少年寻求认同提供了重要渠道,也让他们越来越习惯和圈内人分享交流,用网络社交替代现实交际,习惯于虚拟的舒适圈中,造成对现实世界的认同及归属的消减。只有合理调整圈层关系,重视圈层文化内部净化,强化对青少年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的引导和熏陶,增强他们对短视频的批判能力,进而在网络媒体与现实生活的“虚”“实”之间找到平衡,才可以给青少年营造积极向上、氛围良好、活力满满的网络环境。
四、结语
“圈层审美”是受众接受的新常态,以接受美学“作者——读者”互动视角看,圈层审美的形成暗合了创作——感受——净化的审美体验过程,与受众不断提高的审美期待阈值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接受美学视阈下的圈层审美对审美主体有着重塑的作用,短视频推荐算法技术则是一把“双刃剑”,促进了审美圈层的快速形成和同质化、片面化、模式化的审美固化。短视频圈层传播过程中的“圈层化”正在铸就一种全新的“圈层化”生存,深刻影响了青少年的 生活状态与生活方式,接受美学始终注视主客间的融合和物我合一的心灵体验,强调受众与接受客体间的相互影响和生成。人是万物的尺度,健全的审美体验应该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要合理管控、正确引导,引领短视频内容的价值取向从“流量为王”转向“内容为王”,推动圈层文化从小群体、亚文化的桎梏中走出来,向“主旋律”“共同体”阵地前进,让短视频的圈层传播成为帮助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加油站。
① 张亚斌、黄吉林、曾铮:《“圈层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2期。
② 朱天、张诚:《概念、形态、影响:当下中国互联网媒介平台上的圈子传播现象解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③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358页。
④ 郑欣,朱沁怡:《“人以圈居”:青少年网络语言的圈层化传播研究》,《传播学研究》2019年第7期,第26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95页,第 95页。
⑦ 〔德〕 H·R·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顾静宇、张乐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⑧ 王岳川、胡经之主编:《文艺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
⑨ 路春艳、张琳瑜:《影感与网感的平衡——“年度精品网络电影”创作特征分析》,《艺术教育》2019年第6期,第107—109页。
⑩ 杜丽丽:《后视镜中的他者:“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历史想象和叙事重构》,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