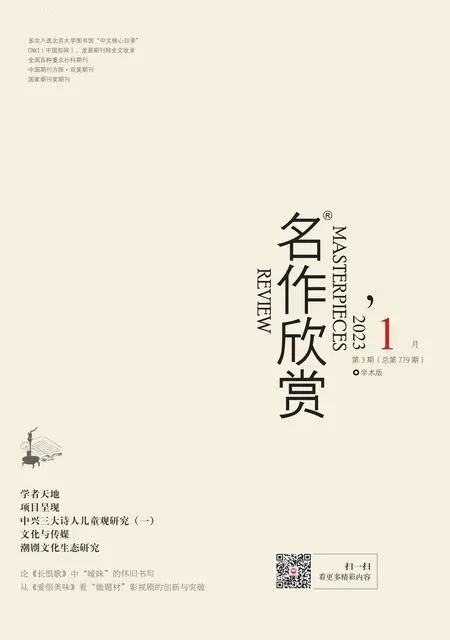黄省曾诗歌中的鹤意象研究
⊙唐一灵[安徽大学,合肥 230000]
黄省曾号“五岳山人”,其中的“山人”本义是指居住山间从事劳动工作的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隐逸风气的时兴,隐士群体不断扩张,作为隐居不出仕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过着山居生活,因而人们又以“山人”称呼“隐士”,并沿用至明清。
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就有隐士传统,这些超凡脱俗之士,往往逍遥于天地间,怡然自得、纵情自在。但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山人数量急剧增加,导致山人的行为和品格发生了异化,山人更多地被当作“终南捷径”,多有沽名钓誉之辈标榜不仕,实则借“山人”之名号赚取才名,以不愿出仕、多才多艺、好游多思等标签活跃于朝市,为求取财货干谒权贵,博取功名、涉足政治领域。在这样一个众人汲汲于名利的大背景下,淡泊名利的明代山人就显得尤其可贵,他们一开始未必没有入世济民的心态,只是终对浑浊现实和丑恶官场感到失望,转为追求个人心性之自由高洁,在清静的山林中寄托理想抱负。黄省曾自号“五岳山人”,正是追求着这一不与凡俗同流合污的山人精神,喜爱这样如仙人般逍遥于天地之外的品格。他将这一理想具象到自己的诗文中,就形成了“鹤”的意象。据不完全统计,在黄省曾的诗歌中,包含鹤意象的诗歌大约有四十九首,具体包括以下几种内涵。
一、仙人幻想
游仙诗在黄省曾的《五岳山人集》中比重较大,一般表达对神仙生活的向往,隐含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悲愤。在黄省曾想象的仙人生活中,鹤是仙人带有吉祥意味的坐骑,仙人通过仙鹤腾云驾雾,享有令人神往的绝对自由,自如地沟通天地和自然。在《秋胡行中》,黄省曾重复三句“我思鹤上游”,他书写仙人乘仙鹤,是无比向往仙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的象征。以及《鸡鸣高树颠》中“竦身绿云中,控鹤升九天”,借助王子乔“控鹤成仙”的典故,暗含得道成仙后沟通天地、遨游四海的愿景。这与黄省曾从小受佛道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有关,也与当时重道轻文的社会倾向性有关。黄省曾在《与文恪王公论撰述书》中说:“盖徒摭夫文之华,而道之精实诚有不在也。”道与文如影随形,显出他的文学中重道的倾向,蕴含着道学强调的超然物外、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意味,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扶桑篇》。
《扶桑篇》是一首游仙诗,前八句描写黄省曾幻想中的仙界盛景。挺直的扶桑枝,挂在东海的太阳边,扬起的枝条拂过天门,流转的光辉运行着天术。扶桑是一种神树,被认为生于东方日出之处,《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传说扶桑枝条飘荡,枝上悬挂十日,光明炽热。后写仙人活动:伴着神鸟采仙果,丹霞间飞动,跳着霓裳舞,弹着朱瑟,喝着桂酒,理着窗纱……
在黄省曾的笔下,仙人生活自由自在、欢乐愉悦,他们各司所职,各凭己心,不受凡俗的束缚。愈是将神幻的仙人生活描写得细致生动,愈是表现出他心中对这种极乐世界和无忧生活的向往和渴望。其中“王乔游并躯,洪崖谈接膝”,引用的王乔、洪崖,都是传说中登仙之人,从他们身上可以生发出仙人的品质特征:随着灵风腾跃的超然物外,与朗月争辉的高雅俊逸,仙风道骨、卓然不凡,都是黄省曾极力称赞的品质。
如此层层铺垫,是为了引出最后两句“鍊此龟鹤龄,悲尔蟪蛄质”,表现心中最深切的渴望,即对长寿的渴望。“龟鹤”与“蟪蛄”在寿命上差别极大。龟鹤是古人常用以比喻长生之物,《养生要论》曰:“龟鹤寿有千百之数,性寿之物也。”龟与鹤寿数之长,可达千岁。而蟪蛄常被用来表现人生的短暂渺小,如《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龟鹤与蟪蛄在寿命上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有了最后一句夸张的“寿与天地毕”,与天地齐平的寿命,其实是借夸张表达对长寿的强烈渴求。
黄省曾在这首诗中表达对神仙生活的向往和对长寿的渴望,正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悲愤的宣泄。在黄省曾想象的仙人生活中,鹤是仙人带有吉祥意味的坐骑,仙人通过仙鹤腾云驾雾,享有天地间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令人神往。而现实中的黄省曾在短暂的人生中郁郁不得志,又不断衰老,本就难以实现的理想抱负加上了时空的局限,显得更为紧迫。于是黄省曾在诗中将鹤比喻为长寿的仙人,期望着乘鹤飞升。这种带有仙人幻想意味的鹤意象,不仅体现在这首《扶桑篇》中,还有《琼花观》“安得丹如日,虚惭鬓巳星。紫烟乘鹤者,为我接霞軿”,因鬓生斑白而渴求成仙长生;《临病咏怀九首·其三》“古称鹤上人,谁当睹遨游。鼓瑟不为欢,令人哂蜉蝣”,人生渺小短暂如蜉蝣,而更期延年益寿、长生不老……黄省曾诗歌中的如此种种,神仙世界绚丽多彩、色彩斑斓,长生而永恒,这一方面是受道教文化的感染,另一方面也是想象力的驰骋,富有浪漫主义气息。
二、隐逸情怀
早在《诗经》中,“鹤”就已经蕴含了“隐士”的象征意义。《小雅·鹤鸣》中写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嘹亮,响彻天际,遍布荒野,正代表了隐居于此的贤者有济世之才和高远之志,虽栖息山林,避世不出,其高雅贤能的鸣叫声却闻名于外。生活在野外的鹤,有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习性,寄托了君子高洁的情操和远大的志向,“闲云野鹤”常被用来代指一种隐逸的境界。
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黄省曾的诗歌中亦常以鹤指代隐士,如《孟中丞望之觞予于顾华玉息园》“真惭野鹤能依凤,解使林驹不避骢”中有凤姿、卓尔不群的野鹤,《题毛中丞华山隐居》“鹤治标尘外,灵书閟枕中”中超尘脱俗的鹤,皆是隐士的象征,追求着个体的顺适和主体的精神。
更有《闲适》一诗,展现出黄省曾对隐士的独特理解。《闲适》中“鹤客”一词直接点出这是一首描写隐逸生活的诗,其中亦不乏隐逸生活的表现:隐士住在吴王宫南边一亩的地方,终日在山林里与高尚贤德的人才交往,一起伴着山间美景开怀畅饮。其中透露出黄省曾所喜爱的隐居生活:美好的景色常在眼前,知心的友人亦多来往。第三句“鹤客频嫌紫霞晚,山妻却笑青钱无”更添趣味,描写隐士言语。“鹤客”是不为凡俗所牵系、寄心山水的“隐士”;山妻为俗世所累,向丈夫抱怨着银钱的紧缺。鹤客只关心紫霞出来的早晚,心中被自然山水填满;山妻因操持家中柴米油盐之事,担忧着铜钱的有无,考虑隐居生活的财力依凭。于是有了尾句“仲尼有玉且不售,何必营营求尔沽”。黄省曾接着引用孔子有玉不售的典故,谴责世人为名利奔波劳碌,崇尚一种高蹈脱俗的境界。黄省曾笔下的隐逸生活,关注寄情山水的自在意趣,意图给自己构建道家出世的精神世界,却也可见这种出世的理想生活与现实的矛盾。世人非仙人,高蹈之意需要布帛菽粟的支撑。因而其在诗歌结尾提及孔子,在道家出世的思考中融入儒家入世的思想。他清醒地看到财力对于隐居生活的必要性,因而不否认用事,只是反对片面追求名利,而失去了个体的顺适安逸和心性的高洁纯净。
在黄省曾的诗歌中,鹤的意象只是载体,承载着他对隐士之风和隐逸生活的幻想,在这幻想中追寻着自我价值与自我认同。鹤那洁白的羽毛、纤细的脖颈、飘逸的姿态,给人以崇高尊贵之感;独来独往的习性又仿佛“遗世而独立”。孤高而独立的鹤意象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精神寄托,在黄省曾遭到罢黜或冷落却又无法脱离现实责难时落于笔端,使他能够将无人理解的满腔抑郁转嫁到鹤意象上。鹤清冷傲物的气质与黄省曾自身的气质相近,其笔下的鹤意象就像是自由而高洁的另一个自己、在隐居生活中愉悦畅快的另一个自己,因而在苦闷的人生中得到了心灵慰藉。他内心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有了孤鹤、野鹤的参照,自我孤高避世的情思得到了同类的认同,而能够面对自我、与自我相处,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黄省曾其实并未真正归隐,也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出尘脱俗的生活,但他在鹤意象里自行构建了隐居的精神世界,借以保证精神世界的宁静和谐。
三、怀才不遇
黄省曾“八岁而能文,十岁而通经”①,年少而才高,自幼扬名,可他却屡试不第,终身与功名无缘。身有雄才却无人赏识、无枝可栖,他将这种壮志难酬的悲愤寄放到黄鹤意象上。如《遣兴》“黄鹤不得意,来栖珠树中”;《五湖上寄廖冢宰》“白云那可系行色,黄鹤安能招锦鞯”。黄省曾将自己比喻为不得志的黄鹤,也就是不得志的贤才,才高运蹇、有志无时、有才无命,明明有能够一飞冲天的才华,偏偏沉于下僚、无人赏识。而在这种高飞黄鹤的比喻中,我们又可以窥见黄省曾并非全然的颓唐和愁苦,他仍然有一种自信,有一种愿景,相信终有一天自己的才华能够被人看到,期望能够招得“锦鞯”、大展才得。
在黄省曾的《折杨柳行》“时哉不停轨,黄鹤讵可招”中,诗人以黄鹤自托,引发诗人对于自身处境的审视,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理想追求。其中,“黄鹤”的寓意有三层。第一层是以黄鹤喻成仙之路,与前句“安得驾游鸾,碧汉追王乔”中的王乔相呼应。王乔骑鹤升天,黄省曾欲追其步伐寻仙问道,却也自知黄鹤非寻常人招手可来,只有时光不停流转,求仙之路遥不可及。第二层寓意是以黄鹤比喻一去不返之物,这就不仅仅是指求仙问道之路,更指不断流逝的时光,诗意更上一层。时光在客观上不可停,不可追,即使诗人主观上想要去抓住,想要在有限的时光成就自我,也终究为现实制约,难以实现远大的抱负。这也与第三层寓意相关,即以黄鹤代指贤才、大才,本该展翅翱翔,却困于方寸牢笼,不得施展自己的才华;志存高远却不能受到重用,空有名声而无人赏识,随着时光飞逝不断衰老,垂翅哀号,功业难成。
在黄省曾的这类诗中,鹤总是“孤鹤”,既是孤高之鹤,又是孤独之鹤,其清高雅逸之风骨使其无法融入黑暗浑浊的官场争斗去鼓噪争鸣,其超脱俗世之志使其少有知音蕴藉己心,多为庸碌之世人所不理解。于是,他笔下的鹤意象就成了他的灵魂伴侣,具有相似的人格意识和相似的处境,展翅而不得高飞,有才而不得舒展。
四、离愁别绪
鹤飘逸逍遥、乘风而去的特质,给人一种不可追寻的缥缈感,故而黄省曾也常借鹤意象来抒发离愁别绪。《和栗应宏送张子言游北岳》“饯琴挥鹤绪,离剑把星文”一句,“鹤绪”即“离绪”,那种行者前途不定、再见无期的缥缈感随琴声在心中似鹤飞般回荡盘旋、难以消散,挥剑欲斩愁绪,却难以断绝;亦指友人如飞鹤般远去,不知何时能够相见,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离情。《长安赠苏允吉》“皆抱鸾鹤思,同遵凤凰楼”中,“鸾鹤思”是别思也是称赞,鸾鹤有仙人之意,是黄省曾心中超然高蹈的象征,即黄省曾心中友人的形象。离别在即,他们怀抱着同样的志向奔赴自己的远方,心中不舍却又相互祝福。而《雨中过马禅》“鹤归僧起定,细饮竹炉泉”又写久别重逢之情,别鹤归来,人亦同归。鹤代表着远行久未见的游人,又是两人的信使,寄托思念也传递归来的消息。于是,友人置酒等待,只待相逢之时,开怀畅饮,一抒离情。
五、猿鹤
除了单独使用鹤意象的情况,黄省曾诗中也有以“猿”“鹤”同用的情况,表催怨之感或仙道之意。“猿”“鹤”同用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早有出现,在宋词中出现较多,多达一百〇五首,二者同样有长寿之意。《抱朴子·对俗》中记载:“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猿,猿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寿千岁。”②因传说中猿、鹤皆长寿而久居山林,被道教赋予了隐逸仙人的意味,修道之人在它们身上寻找长生不老、飞升成仙的秘密。二者亦同样有君子之德。《艺文类聚》卷九十引晋葛洪《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③君子不忘国事、眷念世人,秉持着济世情怀九死不悔、以身殉道却志向难成,于是死后成猿成鹤,哀转久绝,使得“猿鹤”意象暗含一种缺憾与无可奈何之怨。
黄省曾在诗中就巧妙地融入了“猿鹤”这两种意蕴。《朱振之馆鸡鸣山楼有寄》“一月安禅留不得,空令猿鹤怨遗文”,“猿鹤之怨”是文人历经宦海浮沉和人世冷暖之后,对污浊的政治现实和愚昧的世人感到失望,激起怨恨。曾经的执着和信念终成一场空梦,岁月蹉跎、庸碌一生,壮志终难酬。
《次方伯东桥诗》“惟愁劳梦卜,猿鹤怨山樊”,前句“梦卜”引周文王占卜得吕尚的典故,有帝王求良相的意味,隐含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而后山林中的猿、鹤悲怨鸣叫,暗含有一种不得志而隐的内涵。黄省曾在“猿鹤”意象中寄放了他追求隐逸和求仙问道的真实原因:世道多艰,即使心有鸿鹄之志,也只能在苦闷的现实处境中催生对归隐的向往,退居山林终是回避现实的无可奈何之举。
① 〔明〕黄省曾:《四库存目丛书·五岳山人集》,集部94册,明嘉靖刻本,第787页。
② 王明:《新编诸子集·成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三,第27页。
③ 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3—1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