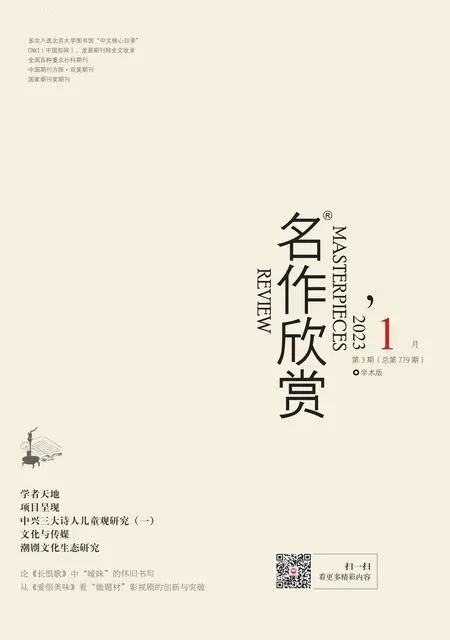论迟子建小说《烟火漫卷》中的城市书写
⊙宋成蓓[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烟火漫卷》是一部描述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的作品。《烟火漫卷》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作者塑造出了一个富有独特地域色彩的哈尔滨。
《烟火漫卷》虽然大篇幅地书写了个人命运和个人故事,但整体上呈现着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城与人的关系,或是城市本身的风貌,体现出哈尔滨这座城市独特的地域性。同时,《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又是迟子建眼中的哈尔滨。这座城市,“不仅负载着大量的文化积淀内涵,具有无穷的隐喻意旨,还饱浸了作者的审美情感,洋溢着某种内在的生命激情”①。在自然、历史、人生与城市的交织中,一以贯之的是迟子建对世间万物的“悲悯”注视,是这个“极地之女”(戴锦华语)以生命感染生命的脉脉温情。
一、烟火常燃——哈尔滨的风物民俗
哈尔滨鲜明的气候无疑赋予了作家文学表现的灵感,小说以清晨和夜晚的自然时间结构全文,其中贯穿着哈尔滨的四季风貌,自然环境是体现该地地域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迟子建的小说里,自然景物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客观存在,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和情感内涵,具有清晰的生命质感和喜怒哀乐的情感。比如写到松花江,“河流开江和女人生孩子有点像,有时顺产,有时逆生”②。倒开江时,“它们有的像热恋中的情人,在激流中紧紧相拥;有的则如决斗的情敌,相互撞击,发出砰砰的声响,仿佛子弹在飞”。
以哈尔滨气候变化与四季风貌的展现作为章节开篇,又延伸出了哈尔滨独具一格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初春冰雪消融,游人踏青畅游;夏季暴风骤雨,市民烧烤露营;深秋草黄叶落,天气转凉,人们及时进补,时蔬市场与补品店铺得以兴旺;待到严冬季节,松花江上的冰块被雕刻成冰雕艺术建筑。人间的烟火气在人们饭桌上的晨炊晚宴也能够弥漫开来,小说中就有大量的文字描绘了哈尔滨富有地域风味的炖菜。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写道:“如果细数哈尔滨永不落潮的生意,洗浴中心和澡堂子肯定位于潮头。”而且依据不同人群的消费能力,满足洗澡愿望的地方档次也不同。哈尔滨的街头,随处可见“松骨”这一类的灯箱牌匾,以致外来游客误以为“松骨”是地方特色菜。由此可见,哈尔滨洗澡的地方和经营蔬菜的地方一样,是哈尔滨人民生活所必需的。
“多数地方大半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产物。地方从未完成,而是透过反复的实践而生产——日复一日重复看似寻常无奇的活动。”③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韵味就隐匿于普通市民的日常之中,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烟火中得以延续。
二、人与建筑——哈尔滨多重维度的现代城市空间
哈尔滨是一座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外来相交织的城市。在展现哈尔滨城市的风貌时,作者将目光聚焦于承载着多年历史的老式建筑,正是这些见证城市变迁的建筑,隐含着哈尔滨这座城市悠久、漂泊与多元的精神文化气质,展现着哈尔滨不同于其他现代城市的独特一面。比如松花江上那座有百年历史的滨江铁路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桥衰老了,但仍然驻足江边,细数江水潮起潮落,见证百年来哈尔滨的人世变迁。这些颇有年代的建筑,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者,同时凝聚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其空间来保存着城市的时间记忆。如早年的“东省特别区图书馆”,历经战争炮火的洗礼,如今成为后辈瞻仰前辈、反思历史的东北烈士纪念馆。连同谢普莲娜的私人宅院,也共同见证了哈尔滨饱经沧桑的岁月。
机敏而鲜活的记忆会自动与地方发生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记忆自然而然是地方导向的,或者,至少是得到了地方的支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的面貌是千篇一律的高楼林立,人们只能从那些为数不多的古老的建筑中找寻当年的记忆,探寻这座城市逐渐失落的传奇。城市的古老建筑牵引着人们前去“怀旧”。“怀旧空间生产是地理空间的想象过程,在此过程中,集体记忆与怀旧联系密切,成为怀旧形成的基础,并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建构怀旧空间,进而塑造地方认同。”④正如马家沟河两岸保留的部分建筑,成为旅客寻访哈尔滨旧梦的地方。这些携带着历史文化印迹的建筑和空间,也许最终会面目全非,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却不会消散,人们可以凭借有选择性地记忆和想象,赋予过去以新的内涵,来缓解现代城市进程带来的精神危机。
除去地标性建筑,寻常院落“榆樱院”也承载着丰富的哈尔滨历史、文化和审美信息,俯瞰视角、游踪路线在某些时候也太泛、太多样了,像“榆樱院”这样更小、更浓缩的城市象征物,常常因其简约的风格而更有感染力。这是一个中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大体来说,傅家甸这一时期建筑的平面布局,还是中国传统的合院式,而主体轮廓和立面造型,却吸纳了西洋建筑的特点。”同样,这也是一座有故事的院落:“据说主楼最早是中国人开的戏园,后来成为俄国一个马戏团的住所,再后来被一个日本商人看上,做了日货专卖店。……榆樱院的左厢房过去是茶庄,而右厢房刘骄华婆家留下的房产,旧时做过绸缎庄和画店,是当年的明媚华丽之处,这里曾留下多少女人的脚步啊。”由此可见榆樱院历史悠久、包含多元文化的特征。
榆樱院又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空间,如同它那杂糅的建筑风格,院子里居住着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如果哈尔滨人的生活风俗给读者展示的是游客式的印象,那么榆樱院则使世俗的烟火气息得以具象化。除了黄娥和刘建国的主线故事外,这个院子里还容纳了其他一些小市民的喜怒哀乐,各色人物带着各自的欲望和烦恼在此登场,上演着一幕幕家长里短的悲喜剧。通过榆樱院这一重空间,众多人物在此会聚,使得《烟火漫卷》在此徐徐展开一幅众生百味图。院落里的居民,更接近普通百姓的底色,与“自然之子”黄娥、“道德楷模”刘氏家族、“混血气质”翁子安之间,形成了层次鲜明的对照。借由榆樱院,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多重精神文化维度得以展现。
三、带有个人印迹的哈尔滨——迟子建对城市的贴近和温情注视
迟子建是以乡土文学书写而闻名的。从《晨钟响彻黄昏》开始,迟子建将目光投向城市,在她逐渐融入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过程中,城市也逐渐进入其创作视野。其城市书写的背后仍然有着乡土的影子,毕竟迟子建的精神背景是乡土,她让宛如自然精灵的女性给城市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有时也在旁观的视角审视着这座城市的阴暗面。由于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最终,如包容乡村故土那样,迟子建以一如既往的温情悲悯的眼光,注视着这座城市的世俗生活、人物的悲欢离合,向世人展现着这股烟火的温暖所在。
谈到小说中的人物,黄娥是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在于她的美,更在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自然的气质。与《晨钟响彻黄昏》中的菠萝自由洒脱、不畏世俗相似,她同样遵从内心的情感。在送客途中,每当她与男性单独在一个小汽艇上,她便总是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与男乘客一番云雨。事后回到家,她便感到很惭愧,但这仍然无法抑制她的自然欲望。在卢木头死后,她用一种“自然”的方式埋葬了他,也打算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追随卢木头而去。为了给“杂拌儿”“寻亲”,她来到了哈尔滨。黄娥初入哈尔滨时,显得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比如她无法理解房子比人金贵、不时回忆起在七码头与动植物的对话。然而与菠萝选择抛弃老母和女儿,远走他乡不同,黄娥为了生计,为了“杂拌儿”,辗转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之中谋生。不同于菠萝对这座城市的抛弃,在与刘建国兄妹、谢楚薇夫妇的交集以及翁子安的照料追求中,她渐渐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魅力和温暖,给“杂拌儿”绘制的地图也是她用心感受这座城市的表现。黄娥的身上也映射着作家迟子建努力融入城市的身影。除却对哈尔滨细腻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描绘,迟子建通过黄娥等人物的行动,表达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贴近。
《烟火漫卷》讲述的是寻亲的故事。刘建国大半生都在寻找着铜锤,而黄娥也带着“杂拌儿”来到哈尔滨“寻夫”。寻找的背后,每个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刘建国不仅仅是不慎丢失了铜锤,在此之后还因失去理智猥亵了还是孩子的武鸣;黄娥也因意外气死了丈夫。本书的矛盾冲突还体现在当今家庭关系和理想人格的失范上,如老郭头家利益凌驾于亲情之上,刘氏家族也出现了道德传承断裂的局面。但《烟火漫卷》不如《晨钟响彻黄昏》所展现的那样令人窒息,黄娥和刘建国在罪恶面前,有过挣扎,有过逃避,最后采取积极的行动寻求救赎,在弥补对他人的“过错”之中获得了“灵魂的栖息处”。在平日里,他们也与人为善,乐于助人。这些善意,连接着刘娇华帮助狱友获得新生以及于大卫夫妇对刘建国的原谅、对“杂拌儿”的关爱,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温暖的人性之流。每个人怀着秘密和不堪,相遇在哈尔滨这座城市,却彼此把对方的生命照亮了。
“她始终是一个对人性、对爱持乐观信仰的人。她并不总是唱人生的赞歌,但恰恰是在人生的灰暗情境中,迟子建最能发现人性的闪光。”⑤迟子建悲悯地注视着笔下的每个人物,即使是面对老郭头这类小人物,也是以温和的笔触刻画着,使其在卑琐中也能散发着一丝人性的光明,她“具有超越具体时代和具体社会的既定意识形态的博大的情感,也就是悲悯情怀,即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一种超脱豁达,超越善恶、包容美丑,对人间万物一视同仁,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给予万物生灵的挣扎与生存的普遍的怜悯”⑥。最后,作者也给了他们较为温暖的结局,刘建国寻得铜锤,落脚兴凯湖陪伴武鸣;黄娥在小鹞子和“杂拌儿”的治愈下,对卢木头的负罪感有所缓解,也渐渐融入哈尔滨这座城市。这种精神救赎、完善自我是作家始终如一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诉求。同样,《晨钟响彻黄昏》也给故事留下了一个温暖的小尾巴:宋家文牵着马林果的手,带她去拜访画家郎乡,无限期地等待着菠萝的出现。因为心中怀揣着对菠萝母女的爱,宋加文得以在悲剧的事实中获得更为内在的幸福。迟子建不漠视生活中的苦难、人性的混沌和灵魂的撕扯,她和她作品里的人物一样,没有自怨自艾,自甘堕落,选择以平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命运、生活,积极向上地生活着。
四、结语
“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无穷的、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⑦一座城市,不仅可以在平常而不庸常的日常生活中获得言说的形式,也可以凭借人的怀旧,获得新的文化内涵。一座城市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构成的,城与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不同的人群,赋予了一座城市多重维度的空间。另一方面,地域性的背景并不妨碍作者思想的楔入,就像迟子建的哈尔滨书写中藏着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与探求,也贯穿着作者一如既往的温情目光。《烟火漫卷》与哈尔滨是相辅相成的,小说给哈尔滨增添了更多的独特性和神秘性,哈尔滨也成了迟子建小说世界以及当代文学独特的风景线。
① 贺仲明:《地域性:超越城乡书写的文学品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8页。
② 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 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中国台北群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 李凡、黄维:《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怀旧现象及地理学研究视角》,《人文地理》2012年第3期,第30页。
⑤ 吴义勤:《对于温暖的信仰——迟子建论》,见《守望的尺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21页。
⑥ 刘传霞:《迟子建小说创作论》,《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75页。
⑦ 〔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见《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