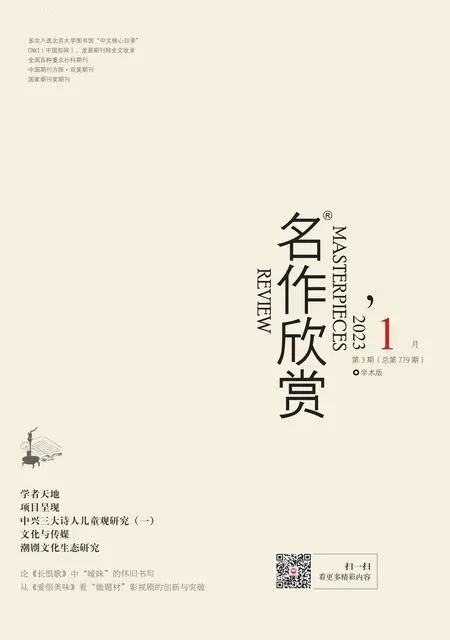造梦?抑或毁梦?
——论《长恨歌》中“暧昧”的怀旧书写
⊙周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207]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这座在中国近代史上最独特最耀眼的城市,再次作为重要的文化标志,引领了经久不衰的怀旧热潮。一时之间,各类以“老上海”为讲述对象的想象性或半想象性的文化或文学文本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比如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程乃珊的《上海探戈》《上海街情话》,电影《胭脂扣》《阮玲玉》《花样年华》等。这类怀旧文本呈现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贵族化”生活的想象,营造出一种优雅精致、华贵甚至奢靡的气氛,并最终形成一种对过去“海上繁华梦”的集体想象。然而,无论是在当时的上海还是今天的上海,其社会构成和文化身份均呈现出如此多元和复杂的特性,绝非怀旧文本当中一律的“精致化”想象所能一言蔽之的。这当中形成的明显的对立和矛盾以及背后折射出来的当代中国文化问题,才是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的对象。例如,怀旧文本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上海”形象?它们又是如何达成自己想象中的“上海”的构造?怀旧热潮如何影响和参与到上海城市文化身份建构当中?这些上海形象及其塑造过程与当代中国经验的存在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这一现象又是否折射出中国复杂的社会心态及其变迁过程?
在这一语境之下,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怀旧”元素的定位便显得十分复杂与暧昧。这部长篇小说从1995年开始在《钟山》杂志上连载,于1996年首次出版,讲述的是上海小姐王琦瑶一生的传奇故事。可以说,小说中的王琦瑶就是旧上海的化身,她的身上带有鲜明的属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风情和韵味。因此,《长恨歌》也常常被读者和批评家与“上海怀旧”联系在一起,成为怀旧热潮的典型文本。
然而有趣的是,“当《长恨歌》被舆论鼓吹为老上海怀旧热的扛鼎之作的时候,作家自己非但不领情,她还明确否认《长恨歌》与怀旧时尚的对应关系”①。据王安忆自己所言:“《长恨歌》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材料,但它其实是一个现时的故事。”②在读者与作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解读的张力背后,让人不禁深思,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所试图探究的上海之“旧”,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对“海上繁华”的集体造梦活动中,她是否也参与了“造梦”过程,抑或是在自己的文本叙事中形成独特的怀旧书写,从而呈现出了在其他怀旧文本中所被遮蔽的“老上海”面貌?
一、怀旧本质:“上海的芯子”
在《长恨歌》的开篇,王安忆首先从弄堂、闺阁、鸽子这些典型的上海意象入手,营造出作者想象中的上海的城市面貌。写弄堂而不是写外滩、洋场、公园,是作者刻意选择的结果。王安忆曾公开表达对历史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
众所周知,弄堂是上海最普通但也是最具特色的民宅建筑,是上海大部分市民的生存空间,曲折幽深,藏污纳垢,容纳着上海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也承载着上海人的生活态度、价值理念。置身其间的上海市民过着拮据甚至有些困苦的生活,日复一日的生存挣扎磨砺着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变得精于算计,同时也孕育了他们面对生活的韧性,于是上海人最本真的文化性格——韧性、精明与务实便蕴藏于里弄空间中。王琦瑶的前半生也曾生活于其他空间,但无论是精致奢靡的爱丽丝公寓,还是作为精神疗愈地的邬桥,都不是王琦瑶的真正归属地。王琦瑶的人生大部分是在平安里度过的,似乎只有这样的弄堂才能构成她的人生背景和生存空间,只有在这里她才能触摸到作为“芯子”的日常生活。
故事的主人公王琦瑶就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是普通的,代表着千千万万普通的弄堂儿女,但她又是不普通的,不像单纯天真的吴佩珍,也不像故作文艺的蒋丽莉,出身于弄堂里小门小户的王琦瑶有种特有的聪敏,那是在生活的挫折磨炼下养成的审时度势与工于心计。凭借着这般的美丽和一点聪敏的心计,王琦瑶为自己赢来了片场试镜的机会。也是在这里,她的美被早早地定下了基调——“她的美不是戏剧性的,而是生活化的”③。不久,王琦瑶的照片登上了《上海生活》的封面,但不是那些精心设计、全神贯注的照片,而是她穿家常花布旗袍,坐在石凳上作谈话倾听状的一张。这张照片算不上绝顶漂亮,却是温和厚道的,与细水长流的“上海的芯子”贴切得不能再贴切。之后,在程先生和蒋丽莉的积极努力下,王琦瑶在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俗称“三小姐”,这自然也是作者有意为之。比起皇后压倒群芳的华贵,亚后集万种风情于一身的妖冶,王琦瑶的美更具有生活化、日常化的特质,因为在王安忆看来,比起灯红酒绿、金碧辉煌的繁华景象,旧上海背后隐藏的世俗琐碎才是它的真面目。正如上海从来不缺浪漫与传奇,但那些普通的“王琦瑶们”和她们的俗世人生才是托起这座城市的根基。于是,带有家常、生活化之美的王琦瑶最终成为王安忆选择的故事主人公,成为柴米油盐的“上海的芯子”的一部分。
对于空间叙述和人物身份的选择,决定了其所浮现出的“怀旧”情愫的内质。在王安忆看来,这“芯子”便是上海文化的根基,也是她力图挖掘的上海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所谓的“旧”,不只是过去,更是未来,它已经溢出了被“怀想”的框架,而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想象的寄托。因此,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并未局限在贵族们的优雅奢靡的生活里,而是在时空、阶级、表现对象上都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面貌,这也使得她的怀旧文本更加客观全面、深入本质,在客体指向上比其他作家的怀旧文本含量要更加丰富和广阔。
二、怀旧符号:上海女人王琦瑶
对于《长恨歌》,王安忆曾谈道:“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④作为“城市代言人”的王琦瑶与上海这座城市相互映衬——上海的城市性格塑造了王琦瑶,而王琦瑶也代表了上海的城市精魂。
上海的精神,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对于上海人来说,日子是需要精雕细琢的。旗袍的样式、发髻的形状、皮鞋的亮度、点心的花样、窗帘的绣花,方方面面都是有讲究的。王琦瑶深谙其中的精髓,无论是调制爽口的饭菜、琢磨点心的新花样,还是服装款式的剪裁和配色的悉心搭配,每个细节都是她热心经营的结果,里面体现出的是她不凡的品位和无尽的生活智慧。可以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浸润在这般独有的优雅精致的精神和气质中,即使是日常庸俗的生活也流淌着细碎的诗意。
其次,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是以功利打底的,若想要在这样的城市中立足,精明与坚韧是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精明是能发现生活奥秘的精明,也是工于心计的精明。在与好友吴佩珍和蒋丽莉的交往中,王琦瑶进退有度,时时刻刻维系着自己的骄傲与自尊。对于程先生的情意,王琦瑶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当身居要位的李主任出现后,王琦瑶更是步步算计,如愿入住爱丽丝公寓,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当李主任意外身亡后,王琦瑶回归到了平安里朴素平淡的生活中,骨子里的坚强与韧劲则支撑起了她后半生漫长的岁月。从4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但引起外面世界剧烈动荡的大事件却没有在王琦瑶平静安稳的生活中留下太多痕迹。任凭外面风雨飘摇,王琦瑶依旧和朋友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围炉夜话”,打牌聊天、喝茶游戏,甚至谈情说爱,务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这样温馨的小日子正是王琦瑶用精明和坚韧构筑的,而这股务实和坚强的力量也体现出上海人在历经命运沉浮后凝练出来的生活哲学。
如果说弄堂里的日常生活塑造了王琦瑶精致细腻、精明坚韧的性格,那么历史的传奇曲折则在王琦瑶身上积淀下了旧上海的妩媚与风情,如同美酒随着时间的流逝香味反而愈加醇厚。作为城市的影子,王琦瑶的情感历程见证了世人对旧上海的想象与怀旧。在李主任看来,王琦瑶的身心所托给他带来的是动荡不安的时局里的一点安心;在温婉的水乡邬桥,王琦瑶的出现彻底刺激了小镇青年阿二,他在王琦瑶的身上看见了上海繁华锦绣的光影,他想,“这上海女人就是为了引诱他来的”;康明逊则捕捉到了王琦瑶身上的极艳与风情,捕捉到了上个时代隐隐约约的光色声影,于是他把王琦瑶当作时代的“遗物”来迷恋。然而,无论这件“遗物”多么迎合他的旧情,在面对现实的利益冲突之时,他又毫不犹豫地将这件“遗物”抛诸脑后;后来,具有怀旧情怀的“老克腊”向往20世纪40年代的时尚与风情,于是他对曾经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产生了感情,希望在王琦瑶身上“触及旧时光的核”。而当这股罗曼蒂克消散之后,老克腊终于看到了岁月在王琦瑶身上留下的苍老的痕迹,于是他用力挣脱了王琦瑶的挽留与哀求,最终选择回归到自己的世界。
无论这些人对王琦瑶怀抱着怎样的情感,无法否认的是,王琦瑶在他们的故事里都充当了一个怀旧的符号。众人试图将王琦瑶当作时空管道去联接过去的岁月,但往往只能无功而返。而当作为符号的王琦瑶无力承担众人加诸她身上的怀旧情绪时,她就只能面临被毁灭的结局。故事的最后,作者借王琦瑶之死对众人的怀旧进行了反讽——众人着迷的只是这座城市浮华感伤的外表,他们想象中的繁华景象如梦般脆弱,而他们的怀旧也如梦般虚浮易碎。
三、上海怀旧与城市身份建构
“怀旧”蕴藏的是一种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焦虑,“它的出现说明了现代人对剧烈分裂与显著变动生活的不满,继而转为一种寻求自我统一与连续性的弥补”⑤。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怀旧现象从个体、零散的形式发展成为集体的、普遍的、蔓延到各个领域的怀旧热潮,并且倾向比较统一地指向了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化”缩影的半殖民地时期老上海的繁华景象时,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现实状况和文化面貌便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是全国的金融、商业、生产、消费及娱乐中心,更是中国最早的国际性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没有赶上亚洲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国内的中心地位也被转移到了首都北京,繁荣与发展被骤然画上了休止符,现代化建设也一度趋于停滞。可以说,繁华已逝的老上海一直是潜藏在上海人内心深处的荣光与伤痛。
沉寂了半个世纪后,浦东的振兴使得上海又重新受到全世界瞩目,这个时候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构便成为一种迫切而显要的诉求。人们急需回答自己的城市从何而来的问题,也“迫切需要一个‘辉煌’的历史给自己垫底”⑥。于是,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便走入了他们的视野,并参与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构造之中。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当代的“老克腊”们对上海的怀旧其实怀念的是半个世纪前的繁华风光,经过他们的精细剪辑和拼接,老上海被重重切割,最终只留下那些光鲜亮丽的碎片来与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的想象相拼接,希望以此弥补历史感的“匮乏”,填补因时间和历史感的失落而造成的文化空洞。
当然,怀旧不仅是一种历史追忆,更深层意义上是一种价值观的承载,是对未来想象的寄托。而历史“幽灵”作为被召唤的结果“是一种实践的产物,特定时代的知识条件、认识兴趣、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要求错综复杂地交缠于其中”⑦。1991年,以浦东新区开发为契机,上海积极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到1999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更为明确地提出上海城市性质和建设目标是“基本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⑧。可以说,浦东新区的开发,乃至整个上海的发展是国家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步伐。“上海,基于它在世纪开埠时期曾是‘东亚最大的金融中心’,现在仍是其所处的长江流域中最重要的城市,更是整个地域之经济推动力,故此中国选择了上海来承担这个发展为全球化城市的重任。”⑨对上海特定时期的美化和怀念,给了国人重新确立上海经济文化中心的信心,以及我们本来就具备足够的实力和资源进行与国际接轨的构想,使之成为一面鼓舞国人重新塑造上海的国际形象和未来地位的旗帜。“上海”自此已经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城市,而且还承载了中国现代化的梦想。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怀旧派作家在文本中精心地刻画旧上海的繁华气派,努力地为世人营造了一个遥远旧梦的精致与优雅。然而他们对“物”与“上海”的解读,终究只停留在一个较为浅显的层面,未能对其本质和内核进行深入探讨,自然也就无法展现历史与文化演变的真实轨迹。相比之下,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一直在有意尝试诠释上海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构成性。她有意避开了其他怀旧文本的贵族化叙事,将视野下沉到上海的弄堂和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市民阶层身上,用弄堂的日常琐屑取代了街上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观。不可否认,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与当下具体的城市日常经验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为我们感知、理解或想象上海提供了更加全面和丰富的维度。但是,尽管《长恨歌》以其下沉的视角与其他怀旧文本的审美风格拉开了距离,但其对“物”的细致绵密的铺陈详述,以及王琦瑶身上带有的传奇色彩和旧时代情态,又使得《长恨歌》与时代的怀旧情绪产生了若即若离的、暧昧不清的关系。
当然,真实准确地还原历史现场显然并非“怀旧”的真正目的。虽然王安忆对上海怀旧中存在的“一元化”现象做出了质疑与反思,但是上海文化身份的混杂性与多元性也远非《长恨歌》和其他怀旧文本所能够直接概述。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本身是一种“叙述”,虽然任何关于历史和往日的复述都不会是客观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集体性的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繁华景象作为怀旧对象的热潮,以及其中在“叙述”时的选择性,还是能够折射出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精神发展的趋势与问题。从某种层面上来说,20世纪90年代对于旧上海的怀念,实际上是对新上海的一种想象,是为实现今日新上海经济之崛起而集体编织的“未来繁华梦”。于是,“新旧上海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瞬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性关系。它们相互印证、交相辉映。旧上海借助于新上海的身体而获得重生,新上海借助于旧上海的灵魂而获得历史”⑩。
作家们在对海上繁华的集体想象中虚构出精致神话,并告知读者,那光怪陆离、浮华璀璨的老上海,不只是存在于过去,而且也是“光明的未来”。可以说,上海“怀旧”面朝的不是自己的历史,而是未来自己的模样,或者说,“过去”就是“未来”。
①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383页。
② 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第66—70页。
⑤ 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⑥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5—20 页。
⑦ 练暑生:《如何想象“上海”?——三部文本和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的“上海怀旧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第107-116页。
⑧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循迹·启新:上海城市规划演进》,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⑨ 郭恩慈:《东亚城市空间生产》,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11页。
⑩ 旷新年:《另一种“上海摩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288-296页。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