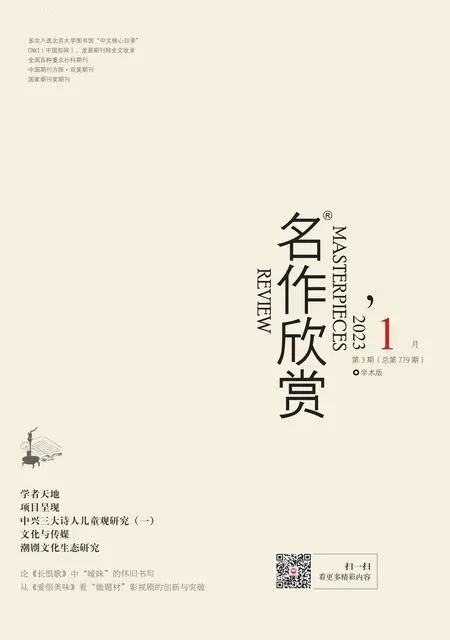论《千山外,水长流》的叙事特色
⊙王宇[北华大学,吉林 吉林 132013]
聂华苓一生中经历了多次迁徙,一路漂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因为曾亲身经历过漂泊无依的生活,她深知这种生活要面对的种种困境与辛酸,所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她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同在异乡漂泊的群体,对他们在异乡的生存困境、精神焦虑、身份建构与认同等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同时,聂华苓也通过持续不断的创作实践,开辟了独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本文试图从叙事视角、空间意象、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对聂华苓小说《千山外,水长流》的叙事特色进行探析。
一、灵活转换的叙事视角
在《千山外,水长流》中,聂华苓对叙事视角进行了合理的切换安排,实现了自然的过渡衔接,将主人公在不同阶段的处境和思想转变清晰地呈现在了行文中。
小说整体主要采用两种视角的切换进行叙述,在第一、三部分中使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除了开篇少量的背景介绍是全知视角,这部分主要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由作者作为叙述者承担叙事任务。选择限知视角进行叙事,也是出于增强故事真实感和逻辑性的考虑。因为莲儿去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去自己未曾谋面的父亲彼尔的家乡,找寻自己失去的“根”。首先她需要尽可能去了解父亲,因为在此之前在她的人生里,父亲只是一个空灵的幻想,她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所以找到父亲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与回忆对莲儿来说非常重要。但彼尔早已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去世,当时莲儿还未出生,远在美国的布朗和玛丽也只了解在美国生活时的彼尔,实际上小说里没有哪个角色见证过彼尔全部的人生,全知叙事显然是不合适的。莲儿最终靠爷爷奶奶对彼尔年轻时往事的回忆,彼尔留下的日记、笔记、照片等旧物中零散的信息以及母亲的书信,拼凑出了父亲的一生,而正是因为限知视角的叙述,才让莲儿看到了不同人眼中的父亲,让父亲的形象在莲儿心中鲜活起来。同时,莲儿还需要父亲家人真正的认可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明确,但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对于布朗夫妇而言,儿子故去多年后,突然冒出来一个混血孙女,也是无法轻易接受的,奶奶的敌意尤为明显。后来玛丽突然生病,成了横亘在祖孙二人之间的“冰山”融化的契机,莲儿在玛丽生病期间对二老的照顾让玛丽很受感动,直到在庆祝玛丽出院的聚会上,莲儿配合着林大夫带来的幻灯片,给大家讲述了自己从母亲书信中了解到的父母年轻时的往事,彻底解开了布朗夫妇一直以来的心结,双方终于理解了彼此,莲儿最终寻回了自己的“根”。在限知视角下,作者将叙事视野缩小到有限的范围内,读者、叙述者和故事里的主人公们一起,慢慢梳理拼凑出了故事的原貌,过程中也完整地展现了主人公思想的转变,最大程度地增加了读者的代入感,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避免了因为过分直接的情节讲述使故事显得苍白乏味,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亦由此释放,故事整体显得更加真实可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情,环环相扣的情节也不断吸引着读者阅读故事并沉浸其中。
而彼利、莲儿的朋友黛安、哈尔非等其他次要角色的出现,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和新的事件。别说是彼尔在中国的往事,就算是在美国发生的种种,在这些人中也找不出一个对读者而言有说服力的人进行全知叙事,故事里的所有角色限于种种原因,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各处发生的所有事件和当事人的想法。同时,作者要讲述的故事核心内容离次要角色也很遥远,甚至可以说与他们根本没有现实的交集,强行全知叙事只会使整个故事的可信度大减。
小说在第二部分中将叙事视角转换成了第一人称叙事,主视角转入风莲,作者选择用书信的形式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因为这部分主讲的是风莲自己的故事,关于她的爱情、亲情、友情和生活,也记录了她重要的人生节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大环境,她写下的信就件是她对自己人生的回望,而彼尔和金炎两位在她生命里极其重要的男性更是她回忆往昔时绕不开的人,他们是彼此青春岁月的同行人和见证人,由她来讲述彼尔在中国的往事再合适不过了。同时,书信也让风莲母女有了解开彼此心结的机会,因为在莲儿出生和成长的岁月里,莲儿和她都独自承受了许多痛苦,但母女间长期缺少交流的机会,双方的隔阂便一天天加深,只能自己默默忍受所有的辛酸痛苦,却没有勇气和机会向对方倾诉,寻求安慰。书信让母女俩不再有那种相对无言的尴尬,风莲可以用文字尽情诉说自己对女儿的爱,莲儿也在母亲的书信里彻底了解了自己的身世、父母年轻时的往事和母亲多年来的苦楚,她明白了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个体的身不由己,开始理解自己的母亲,两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疗愈心伤。读者们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更可以得到一种身临其境般的阅读体验,而且聂华苓在这一部分通过风莲的第一人称叙事,展现了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对个体人生选择、发展走向和思想性格的巨大影响。
总之,聂华苓通过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将自己对于历史、社会和时代大环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以及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注入了小说,使小说意蕴更加丰富。
二、独特的空间意象
空间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千山外,水长流》中,聂华苓就进行了巧妙的空间设计,借助独特的空间意象,来呈现故事中的诸多重要细节和情节,推动故事进程,表达作品主题,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丰满,也赋予了这些空间特殊的意义与内涵。比如小说中石头城的小石屋、墓地、水塔、白云酒店、爱荷华城中林大夫的家等空间意象,还有江河湖泊也是聂华苓笔下一种特殊的空间,它们都是小说叙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布朗山庄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成一片废墟后,布朗和玛丽宁愿改建曾经仆人居住的小石屋搬进去,也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成长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了他们平凡却珍贵的一生。而布朗夫妇改建后居住的小白云石屋,更像是他们平凡一生中美好回忆的储藏室。小石屋是个私人空间,屋里那些早已泛黄的老照片和陈旧的摆设、家具、物件都是布朗家曾经珍贵回忆的寄居地,布朗夫妇固执地要与它停留在一处,一同锁住永远也回不去的美好昨日。饱经风霜的小石屋既是一家人幸福时光的保管者,实际上也见证了新旧时代的交替、社会的发展变革以及被时代洪流裹挟着不得不往前走的许多普通人的无措与迷茫。同时,布朗山庄的小石屋和这里的一草一木,也是莲儿寻“根”路的见证者,在这个空间里,她一点点地将自己残缺的“根”拼凑完整,直到玛丽生命的最后时光,这家人终于冲破各方面的隔阂与误解,迎来全新的生活,虽然前路未知,但曾经的阴霾一扫而空。作者以这个空间为平台,通过莲儿和布朗夫妇、彼利等人的日常相处,展现了莲儿在陌生文化环境中经历的种种困难和尴尬情形,由此也呈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融合时面临的种种障碍。
墓地也是莲儿“寻根”路上一个重要的空间意象,彼尔和莲儿阴阳相隔,但当莲儿跪在彼尔的墓前:“莲儿的手仍不停地抚摸着覆盖爸爸的黄土,泪水扑簌簌流了一脸——这是她一生中最肯定的一刻:她的的确确是维廉·布朗的女儿,她的的确确看到爸爸了。”①
死亡无法阻止至亲间天然的情感联系,莲儿在墓地空间里得以跨越时空与生死,真真切切感受到父亲的存在,墓园里一个个属于布朗家族成员的墓碑,也让莲儿感受到布朗家族的“根”之所在,让她开始在心理上建立起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另外,彼利表弟和朋友一起住的水塔,表面上看是个狭窄简陋、幽幽暗暗的空间,但狭窄逼仄的空间里住着的却是开放独立、向往自由平等的青年男女,逼仄简陋的生存空间困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现实中的挫败与阻碍也挡不住他们实现理想的决心,他们聚在一起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充满干劲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娥普西河旁的小杂货店,在彼利和朋友们的改造下重获新生成为白云酒店,在这里来自不同国家、文化的人们终于不再针锋相对,而是放下了彼此间的成见,在夜晚的吟唱晚会上一同唱歌起舞,作者在此努力营造了一个没有纷争和差异的美好空间,由此也是在呈现她理想中来自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之间的相处之道。莲儿去往爱荷华城之后搬进了林大夫家,帮他照顾女儿、照顾家,用她的话说就是用劳力换饭吃。在个人居所这样一个私人空间里,莲儿与林大夫逐渐了解彼此,时常交流谈心,慢慢地莲儿也敞开了紧闭的心扉,放下戒备。这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反而成了莲儿的逃出口,让她有勇气面对曾经的伤痛,彻底拔除心魔,同时这一时期她已理解母亲,与奶奶的关系也开始转好,她开始走向真正的新生。
在聂华苓漂泊的人生里,一路上的江河湖泊几乎见证了她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她特殊的人生伙伴,所以她非常喜欢让水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意象与笔下人物的一生如影相随。比如在《千山外,水长流》中,风莲在动荡的岁月里辗转各地,犹如无根浮萍随水漂泊历经坎坷,水在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流动空间与风莲漂泊的人生紧紧相连,成为历史和风莲人生的见证者,历史旧事终被淹没在像奔流不息的江水一样永不停歇的时光长河中难寻踪迹,曾经的往事最后也成了只有一路上的江河湖泊和风莲知道的“秘密”。风莲随水漂泊的一生在她的一封信里被完整勾勒出来,也成了她的女儿莲儿寻根的重要依托,莲儿从长江一路漂泊到娥普西河,跨越千山万水最终成功寻回了自己的“根”,而奔流不息的江水带着她不断向前走,让她不再被过去的伤痛桎梏在原地,勇往直前地奔向崭新人生的同时,也在给她指着来时的路。
聂华苓笔下独特的空间意象,既是书中人物人生历程和社会时代变迁的同行人,也反映着作者的理想以及对历史、社会与人的存在本身的思考与体悟。
三、别出心裁的叙事结构
从聂华苓对《千山外,水长流》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和时间长短的选择上,我们可以想到,将如此漫长岁月里发生在两个国家、几代人之间的故事详略得当、完整清晰地展开,且不遗漏任何重要细节,是需要耗费很多心力对故事的叙事结构进行设计安排的。
全书分为三部分,但主要包括两条叙事线:一条是在第一、三部分中主讲的莲儿到美国后发生的故事,以及她整个思想和心理上的转变;另一条是第二部分用风莲的书信主讲她和彼尔年轻时的往事,在时间上就倒回了几十年前,在空间上则来到了中国。聂华苓在设计叙事结构时,选择通过不同角色的回忆以及主人公书信、日记、笔记等的穿插,让过去与现实彻底交融,空间也随之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不断变动,打破时空限制,建立起时空交叉式的叙事结构。比如在第一、三部分的叙述中就时常插入布朗夫妇对过去的回忆,或是石头城的曾经,或是与儿子彼尔有关的故事等,莲儿、林大夫等人的回忆以及彼尔在笔记本中写下的断想、随想也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适时插入,进一步完整了故事内容。第二部分风莲的书信里虽主要叙事线是她与彼尔的情感历程,但也是往事与现在的生活境况交织进行叙述的。作者通过不同时空交织的叙述,在故事推进过程中填补了许多细节内容以充实故事本身,并将整个故事铺展开来,避免了故事线混乱、内容表述不完整清晰等问题。同时,聂华苓还通过“眉批”让莲儿站在现在与过去的母亲对话,对处在人生不同阶段与境况中的母亲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彻底打破时空桎梏,让叙事更加灵活生动。
聂华苓通过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故事之间穿针引线,为读者清晰地呈现了故事完整的全貌,其中也隐含着作者对社会、历史、人性等问题的思考与体悟。同时,她在叙事结构上的排篇布局与巧思,也体现出她不断进行文学创作新尝试的实践与努力。
四、结语
聂华苓的小说意蕴丰富,在《千山外,水长流》中,她用灵活转换的叙事视角、独特的空间意象以及别出心裁的叙事结构,将几代人横跨两个民族和几十年岁月的爱恨悲欢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同时,她把个体在时代巨轮下的身不由己和辛酸痛楚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表现出她对那些在异乡漂泊无依之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焦虑,以及个体身份认同与建构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笔者笔力有限,只能对聂华苓作品的叙事特色进行简要探析,她的创作值得我们从更多角度整体进行把握。
① 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