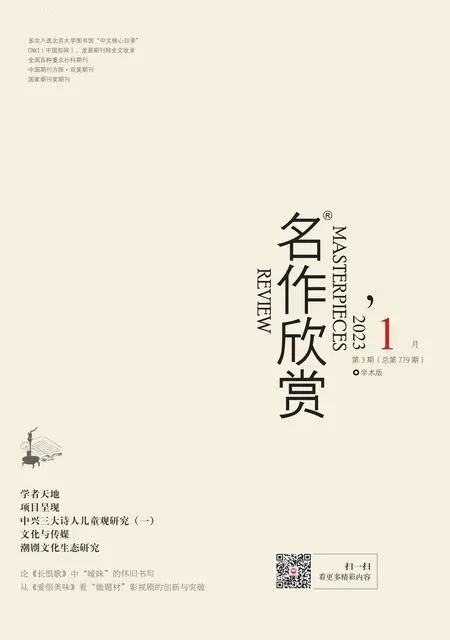必然的审判
——阿尔都塞视域下对卡夫卡《在法的门前》的一个诠释
⊙周政[汉江师范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
《在法的门前》是卡夫卡长篇小说《审判》中的一个故事。卡夫卡后来也曾单独将其抽出,收入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这篇文本因其篇幅短小却渗透出对法的深刻见解,历来受到众多批评家的关注。作为科班出身的法学博士和法务从业者,卡夫卡的作品如同法庭审理,审判者和被审判者相互对垒,主权者对主角审判并执行判决。卡夫卡的文本是缠绕而不具有切实意义的,这就为我们阐释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空间。本文试结合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法、意识形态学说与其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对《在法的门前》的文本中所渗透的法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如何规制个人进行尝试性的阐发,以期拓展对该作品的解读方法。
一、必然如此——法的运作机制
笔者认为造成乡下人悲剧结果的第一个原因,源于法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
“法”在法语中为“Le Droit”,而“droit”具有权利、公正、正当等含义,也译为“法权”;每个实践和被实践法权的自然人被称为法人。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武器,法首先必然是镇压性的,阿尔都塞立足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法意味着强制的阐释,对法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法意味着国家意志的威严强制,要强制则需要惩罚,要惩罚则必须要有镇压,所以必然要有所谓的镇压性机器,而这个机器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在宪兵(执行法律的军事部队),即镇压与惩罚的实体本身不在场的情况下,也就是并非“害怕宪兵”的情况下,人们遵守契约的原因,是因为法律意识形态的渗透,具体体现为意识形态在实践里的自动运转。阿尔都塞认为,法是一套系统化的、无矛盾的、倾向于完备的形式系统;而它要依赖三个部分来驱动:镇压性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的补充。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和国家运转机制是高度趋同的,两者是一体两面的。乡下人站在法的门前,就是站在了国家的门前;试图求见法的真身,就是试图探寻国家(法)的意识形态本质。
基于阿尔都塞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尽管“法应该永远为所有的人敞开着大门”①,但小说中的乡下人是注定无法进入门内的。守门人守在法的门前,这个 “身穿皮大衣,有着又长又尖的鼻子和又长又黑的鞑靼胡子”的守门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装扮。这种区别于乡下人的装扮是某种制服(uniform),象征着他是“有决定权的人”(qui de droit),他是不在场的事物——法的官方代表。
“不过,你要注意,我很强大,而我只不过是最低一级的守门人。里面的大厅一个接着一个,层层都站着守门人,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文中对于门后法的世界的具体样貌并无更多着墨,是否有更高级的守门人,甚至法的本真是否真的存在于此,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乡下人来说,这个自称最低级的守门人是实实在在的法的代表,是横亘于他和所欲求的法门之间的唯一障碍,是“有权的”。当乡下人问守门人以后可不可以放他进去的时候,守门人给出了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回答:“‘这是可能的’,守门人说,‘可是现在不行’。”这种法的意识形态实践者对实践边界的模糊化让法的系统与严谨在故事中变得模棱两可,没有了具体的法的条文,象征着镇压和暴力的法的最基层实践者,即守门人就成了法条的真正解释与裁决者。这时候,守门人作为法的镇压性的具象化,其威权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而乡下人在这种关系里沦为接受暴力的客体,惧怕可能的暴力无法进一步行动,从而无法迈入法的大门。
通往法的大门是敞开着的,是具有敞开性的,守门人有时还会走到一边去,乡下人甚至可以往里面张望。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自由人(可以自由思考并决定行动),他完全拥有选择自己行动的自由——他可以离开,可以抗议,也可以偷偷溜进去;但他选择了“遵守契约”,即遵守法律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的指导:“便打定主意,最好还是等到许可了再进去。”这便彰显了法的运行机制:它有时会得到镇压性机器的支援,但它主要还是通过法律-道德的非暴力的方式,让每个人成为法人,即遵守法律意识形态的规范,以法条为行为准则的人。小说描述的法的大门内层级的列数、守门人级别的空间和权力概念,象征着法的意识形态空间建构: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不敢被踏入的大门才能成为法的大门,它在整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里被摆在了一个崇高乃至于神圣的位置上。法的意识形态权威性也正是通过这种不可行的悖论得以运行:一旦法的大门可以被踏过,法的真身得以被窥见,那么法对于普通人来说就不再是一种神秘的运行机制,守门人也就没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威,作为系统的法的意识形态也就接近于崩溃从而无法运行。因此,这种欺瞒性和不可行性反而是法的系统得以在实践中运行的意识形态保障,正如同资本主义法条宣称自己保障公平,但对于保障谁的公平三缄其口一样。只有不包含任何实指的虚无的宣称,才能让系统顺利地运行。阿尔都塞认为,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之下来思考法这个名称实指的系统,就会把这个抽象的系统重新具体化,即法这个系统实际上包括:法典+法律与道德的意识形态+法院和法官+监狱,等等。“‘法’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行使一种完全特殊的功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②讲述故事的神甫在一开始就声明,这是一个关于欺骗的故事:守门人作为法这种特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最底层实践者,是无缘知晓最上层的景致的;在乡下人求见的岁月里,我们并未看见第二个守门人,我们也未曾知道在法的阶梯之上,除了法本身是否真的有更高级的意识形态实践者,如更高层守门人的存在。守门人自述面对第三层的守门人时已无法直视,主体沦为客体,沦为客体的主体却又能令他者化为客体,从而驱动意识形态下无所不包的科层体系,这加剧了作为意识形态实践客体的乡下人无能的恐惧与战栗。
二、真理,谎言与扯淡——意识形态运行机制与唤问
阿尔都塞批判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他尖锐地指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杜撰的产物,与之相反,“它是永恒的,也就是说,它无处不在,在整个历史中具有永远不变的形式”。阿尔都塞用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说法来阐释:“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恰好就像无意识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但我们又无时无刻不在呼吸着空气。空气这种介质的存在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意识不到它是支撑人类再生产的基础条件之一;意识形态遵循一种同样的逻辑,有一个人们根本不清楚作用机制的东西生成了人们自然以为的事物、主体性与独立的所思所想。“因为事实上,无意识的永恒性归根到底以意识形态一般的永恒性为基础。”这种结构主义式的理论向我们展示:意识形态是从来都存在的,而人们是被从虚空中抛掷到意识形态和被编造的意义之网当中的。事实上,所有意识都是意识形态的。
在《在法的门前》结尾的桥段里,我们能看见至少两层的反讽:随着岁月的流逝,乡下人变得衰老不堪而接近死亡,但守门人作为法的代言人及永恒的法的系统的一部分,却依然保持其青春永驻的姿态,时间并没有在他身上起到应有的削弱与衰老的作用。可以窥见,他或许已经对无数临终的乡下人说过无数句同样的:这扇门是专门为你打开的。意识形态有它的生产与运行机制,乡下人是这个生产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是意识形态机器流水线的最后成品。守门人不需要使用武力,他只需要在恰当的时间说出重复了无数遍的恰当的话语,观察无数个乡下人都会做的无数遍同样的行动。这种无穷无尽回环的西西弗斯般的故事,正是这套意识形态系统得以运行的关键要素。
第二层的反讽在于故事结尾守门人的话:这扇门是专为你打开的,而我现在要把它关上了。如果想要发扬自我的主体性,就必须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行为,前提是我们要且必须要有绝对自由的选择权。在超脱于意识形态的结构时,我们才是绝对自由的。但正像阿尔都塞所描述的,意识形态是具有实践性(物质性)的,主体在实践时,所信仰的那些观念是如物质般坚如磐石存在的。“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中,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所规定的——这个主体的各种观念(好像碰巧)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他作为主体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所自由选择的那些观念就‘依赖于’这个意识形态机器。”于是,每一个信仰自己意识的观念的主体,就会按照自己的观念来行动。守门人已经见过无数个乡下人,他们衣着举止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同样的特质:他是半透明的,是可以一眼被望到底的,守门人知道他会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说什么话,相信什么东西,做什么事,从而在这套法的系统中进行既有观念的再生产。守门人作为法的践行者和国家机器的代言人,乡下人作为一个陷入意识形态之网的注定不自由的追寻自由之人,各自践行了自己的角色而未曾越雷池一步。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思考一种话语:“人们之所以对自己做出了关于他们生存条件的异化的表述,是因为生存条件本身是使人异化的。”生活在意识形态之网中,人所践行的不是人与人之间实在的关系体系,而是作为其替代的某种编造的,被赋予意义的想象性体系;我们会给很多实际的问题提供想象性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真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商人会认为,他理应通过竞争获得更优越的生活;一个共产主义者会认为,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守门人会认为,他的职责就是守卫住虽然敞开,却绝对禁止入内的法的大门,不让任何人通过;最为吊诡的或许是乡下人,他被分配的想象性角色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这位公民想做的是一件不可能之事:去走入法的大门,探寻法的真身。意识形态是一种纯粹的幻象,梦想与空无,当你试图去理解它的运行机制,凝视它的真身(踏入法门,拜见法本身)的时候,意识形态就会崩溃,乡下人通过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机制也会随之土崩瓦解。那个大门竟然可以轻易地踏进去?终其一生所遵守的规则竟然是个谎言。为了维持自我意义的圆满,无意识让他拒绝进一步的行动,但自由意志又促使他采取行动,两者冲突之下,只有彳亍留存。乡下人注定踌躇不前,而守门人注定凝视着乡下人的踌躇,并给他足够的明示暗示,让他无法超脱于意识形态做出或战或逃的自由选择,从而进退维谷,心甘情愿地沉溺于这种悲剧的独角戏里。
《在法的门前》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阿尔都塞一再强调的意识形态唤问(interpelle)机制。阿尔都塞引用帕斯卡尔对跪拜这一宗教仪式的分析来阐释唤问:不是因为先信仰神灵才有跪下去这个行为,当你跪下去的时候,信仰就会随之而来。个体被权威的声音所占领,自觉地践行大主体(Subject,即大他者,具有权威的话语和命令产生者)所指派的位置,履行意识形态机器所指派的社会实践,主体借由命令沦落为没有主体性的他者。阿尔都塞运用这种拉康式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思路指出,意识形态的运行结构保障着把个人唤问为主体,使传唤者大主体和被传唤者小主体之间相互承认,从而在承认、臣服和保证的三重组合之下,“在法律意识形态中,镜像关系发生在(正义)这个大主体与(自由和平等的人)这些小主体之间”,意识形态机器就这样运转起来,从而让守门人—乡下人、正义(法)、自由人这个诸多角色参演的系统永续运行下去。在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的沉默(silence de la conscience)中,意识形态把显而易见的事强加于人,使人不得不承认事情的显而易见。
意识形态通过“宰制”(domination)不留痕迹地让人统治了那些想反对它的人③,进而不动声色成功地统摄了乡下人,让他颠覆了自己的认知。他“忘了还有其他守门人,而这第一个似乎成了他踏进法的门的惟一的障碍”。天长日久,他甚至忘却了求进法门的原因和求进法门这件事本身,而把生命的时光消耗在让(这个最低等)的守门人开口同意自己入内,消耗在自己和守门人的博弈与哀求中。在乡下人和守门人的博弈中(在其母篇《审判》中K 同神甫就这个故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此也可以看作是K凡人与神、主体与大他者、诸众与主权者的辩论),乡下人丧失了自己的绝对自由,他被意识形态唤问为主体,从一个可以自由选择面对法的大门和守门人态度的自由人,变成了一个围绕着法的大门打转,围绕着守门人乞怜,并认为这才是自我存在意义的他者。逃走,离开或者是反抗已经不再成为一种选项,而是一种可能性为零的、不可思议的生存方式。饶有趣味的是,尽管守门人一再暗示:“不妨不顾我的禁令,试试往里闯。”“我收下这礼物,只是使你不会觉得若有所失。”但乡下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关系的荒谬,反而认为他等待的选择是自主“自由”地做出的。主体的建构、身份的建立和运行的机制在这里建立并运行起来,他不想也不能够去怀疑结构的合理性,在终其一生的询问中维护了现有的系统和秩序,在法的门前消除了一切反抗的可能。而母篇《审判》中故事讲述者神甫的一句话更揭示了这种机制:“不必把他所讲的一切都看成是真的,只需把它看成是必然的。”真理,谎言与意识形态内涵,在这里昭然若揭了。
三、阿尔都塞美学与文学批评思路下的《在法的门前》
阿尔都塞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并依据法国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美学与文学批评见解,其中的某些看法与卡夫卡本篇小说的内涵不谋而合。
《审判》的德文(德语是卡夫卡的母语,同时也是作品出版的源语言)名为《Der Prozess》,意为“永不完结的过程”。作为《在法的门前》的母篇,两者所体现的思想有相当的共通之处。从前文分析中我们窥见,法门前纠缠的悲剧是永续的,是循环发生的。因为法的系统是永恒的,意识形态是没有既定的历史而永远存在的,守门人是永葆青春的。只有前赴后继的乡下人在求见那个根本不可能见到,或者可能不存在的至高的法。《在法的门前》(或是《审判》)不只是一个独立的悲剧故事,而是一组有相同特征的故事的典型代表。
阿尔都塞曾在《“小剧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The “Piccolo Teatro”:Betrolazzi and Brecht.Notes on a Materialist Theatre,1962)中提出对戏剧非高潮时刻,即所谓漫长无趣的戏剧空白时间的一个解释:“这是一个没有事件发生、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发展变化的时代(时间)。在这段空白的时间里只是固定不变地重复过去……总之,这是一个不发生任何堪称历史事件的、真空的、虚度的和停滞的时代……”④这与乡下人的际遇可谓不谋而合,除了那几句堪称得上故事发展推动的对话以外,乡下人令人玩味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这种空白时间中度过的。乡下人的命途是短暂的,这也就意味着乡下人主体的悲剧故事是短暂的,但最讽刺的是,这短暂且往往伴随着悲剧和戏剧张力的故事,在他们的生命里却是少有的充实的瞬间,也就是《在法的门前》主体所践行的“‘闪电般短暂’而又‘充实的’时间。”⑤
守门人和乡下人的博弈贯穿了全文,这种对峙是漫长幸福的人生的反面,它成功占据了作为普通人与意识形态实践者的乡下人的整个青春年华(甚至是生命)。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而无产者同样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可供书写的历史。无产者(乡下人中的“乡下”暗示了他的无产者属性)受制于意识形态,无法以自由意志主体做出日常生活的抵抗,甚至可以说无法察觉到意识形态幻觉。
而从形式上来说,《在法的门前》的文本与戏剧的呈现形式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在一个不变的场景中,不变的幕布之下,两个不变的人上演着情节与结构的变化(基于法和意识形态系统的代表——被意识形态宰制的两人之间的冲突)。阿尔都塞认为,我们进入剧院看戏这件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在我们所观看的戏剧中,我们可以“认出”自己,取得一种自我认同,看见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一种人。这就是上文所说到的负有传唤任务的大主体(Subject)任务的典范。“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是剧中的自我了。”在乡下人——守门人的二元关系独幕剧中,我们不仅能欣赏剧情本身,还能隐约看到一种主体与客体、意识同历史现实的虚幻关系,从而把观众代入一种历史情境和一种意识形态的思考里。
在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里,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是高度抽象的,而戏剧是这种抽象的具体化的一种呈现形式。“在人道主义美学中,人的面孔是灵魂,是主体中心的隐秘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中,剧中人的面孔必须有一种可以被认出来的独特的个性,可以被表现的、与世俗不同的独特灵魂。我们在文中可以窥见守门人的独特样貌、着装和神态,却没有关于乡下人任何的“优美的独特的灵魂”的描写,他似乎是没有面孔、没有外貌的透明的人,就像商场中机械复制的人体模特。没有对乡下人直接的相貌描写并不是一种忽视,而实际上是一种近乎刻意的暗示,是一种阿尔都塞主张的意识形态所着重提示的:要看清“人”,尤其是资本主义所号称的自由平等的人和现实存在的自然人之间的实际差距。读者是相对于文本不在场的他者,但正因这种不在场,我们才能采取超然的视角,看清乡下人空白的脸上叠加的无产者的悲剧的面容,其中或许也有自己的面孔。乡下人荒诞死亡的结局,或许能给沉溺于意识形态幻象的读者以一丝警醒。
阿尔都塞提醒我们,一切意识都是意识形态的,我们无法超脱出意识形态来进行自我理解,人们把自己想象建构成主体,并以主体的身份去思考,但如果我们在文章里没有(或不是全部)找到和我们相像的主体(无论是守门人还是乡下人);那么这反而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不能认出并代入角色,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代入“实际是对自我的误认(misrecognize)——那么我就能够开始‘认识’自己”。通过对既有角色代入的否定,来唤起读者对主体性的思考,唤起一种从古希腊延续到当代的“我是谁”的古老问题的深思,进而唤起对既有秩序的思考与质疑。阿尔都塞和卡夫卡,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四、结语
通过对卡夫卡《在法的门前》文本的阿尔都塞式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并阐发隐藏在卡夫卡法的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卡夫卡运用简单的幕布和背景,讲了一个某年某月日记式的故事;而利用阿尔都塞法、国家、意识形态相关理论作为穿刺的武器,对卡夫卡这篇小说进行一种形而上的冒险与解析,是笔者对这篇文本再解读的一个尝试。
阿尔都塞思考并战斗在20 世纪的法国,卡夫卡是旧世界的奥匈帝国公民,但不同的时代仍有共通的事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思索贯穿了这两位哲人的思想。我们可以从这个寓言般的故事中看到,资本主义通过法、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借助暴力和非暴力的形式,使用强制或“自愿”的言语,运行着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数量众多却难留姓名的无产者沦为没有面孔的乡下人,永远无法到达资产阶级号称自由与公平的法的面前,甚至无法踏入法的门内。整个故事揭示了一个往复循环的悲剧——乡下人在法的门前求,最终目的无非是在法的裁决下,意图他人遭到审判,以求得自由与公平;但自身却成为资本主义与法的意识形态的审判对象。并非报应不爽,命中注定,而是一个复杂的再生产机器的零件的必然下场罢了。
这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繁华之下的悲剧性,是一个极好的启示。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1》,韩瑞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 〔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杜章志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11页。
④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6页。
⑤ 〔澳〕卢克·费雷特:《导读阿尔都塞》,田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