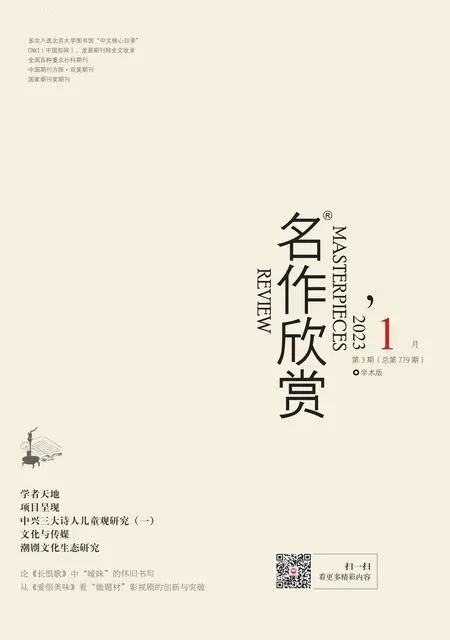技术文化里的人文呼唤
——《羚羊与秧鸡》的新卢德主义解读
⊙卫鹏羽[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6]
一、引言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是当代世界文坛最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锐利的笔触、冷峻的文风、深邃的洞察力为其赢得了诸多奖项和荣誉。《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是阿特伍德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疯癫亚当”(MaddAddam)系列的第一本。小说讲述了世上仅存的人类之一“雪人”带领一群基因创造物“秧鸡人”在疾病横行、受各种变异生物威胁的末世中艰难求生的故事。《羚羊与秧鸡》(以下简称《羚》)一经出版便在批评界掀起热议。国内外学者相继从生态主义、消费主义、后人类主义、后现代主义、空间批评等角度深入剖析了这本当代经典。尽管国内外讨论《羚》的视角多样,但对于其技术文化这一显著和重要的批评思想未进行系统阐释。而无论是技术统治下的背景设定、技术推动下的情节发展,还是技术猖獗致使的人文素养泯灭等因素都无限放大了“技术文化”这一批评思想,因此从这一角度解读《羚》十分必要。“技术文化”的内涵广泛,本文探讨的“技术文化”则属于新卢德主义范畴。
新卢德运动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技术批判思潮和社会运动,其主体是一批美国的知识分子。它的“新”是相对于英国19世纪兴起的卢德运动而言。尽管来自不同领域,关注焦点和学术诉求各不相同,绝大多数新卢德主义追随者认为,传统文化在技术的酶促下丧失多样性,转变为各个维度都与技术关联的技术文化霸权。阿特伍德在《羚》中表达的对未来世界滥用生物基因技术的关注和人文精神沦丧的担忧,正与新卢德主义分子对技术文化的批判不谋而合。本文借助新卢德主义技术文化相关批评探讨阿特伍德对技术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感受作品背后蕴藏的文化怀旧主义。阿特伍德尖锐地揭露了技术至上的时代,传统文化符号的意义失去活力,人类的交往方式狭隘化,文学艺术边缘化等种种异化现象,呼吁人类追寻人文精神,强化伦理道德观念,在技术文化的霸权下重塑本真。
二、技术重构文化符号的意义
在《羚》中,技术成为文化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传统文化符号在技术的笼罩下丧失所指而成为单一能指,其象征意义逐渐耗竭。这一现象最明显的表征就是阿特伍德所勾勒的媒体版图,在所有媒介中,阿特伍德着重刻画了工业文明的代表性成就——电视。
在阿特伍德笔下,电视及其人工环境干预并殖民了人的经验,全面侵袭并控制了人的身心。主人公吉米生活在一个各类设施一应俱全的大院,而大院外原先的都市,则变成了设施破败、治安混乱,供下层民众生活的无望之城。在物质富足但与世隔绝的大院里,电视成为居民开眼看世界最直接的窗口。人们在这种人工环境的包围下不自觉被吸引并自认为获取了有关“现实”的知识和信息,然而所有的这些知识和信息都是被加工的。在科技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环境的变化已远超个人经验的范围,知识依赖于各种所谓的专家、媒体。电视作为人造物扮演了人与宇宙之间“意识之墙”的角色,成为最好的传播载体。在小说中,吉米看到火会联想到电视中的爆炸画面,听到妈妈的温柔语调就想到电视里年轻女老师的声音,绚丽的广告牌和霓虹灯甚至在电视里也不常看见。讽刺的是,这些事物存在的意义却不在人类常识范围内:吉米一直期待一场炸毁所有道貌岸然的爆炸;母亲温柔的语调并不意味着愉悦的心情,而是她怒火中烧的前兆;“连绵不断的广告牌和霓虹灯信号”①曾是城市繁华的象征,如今却是城市破败混乱的标志。
电视的图像思维取代了语言符号思维,其带来的思维方式变化及相关反应是阿特伍德在字里行间中所探讨的。阿特伍德笔下的电视显然消耗了传统符号的意义。随着媒介技术大力发展,电视等新兴媒体无孔不入的渗透使声音、影像的复制、传播变得轻而易举,符号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不再指向更高等的世界观或超越性的源泉。这与新卢德主义代表人物尼尔·波茨曼(Neil Postman)的观点遥相呼应。在波茨曼看来,符号有其自身的规律:“符号可以无限重复,但并不是不可耗竭的,符号使用得越频密,其意义就越被削弱。”②在小说中,电视等媒体所制造的符号如政治鼓吹演说、被剪辑的新闻报道等并不是对现实事物的反映,而是一堆能指的随意堆砌。电视及其音像符号只是现代技术强势入侵的缩影。如果不思考其中利害,技术崇拜终将摧毁其他一切形式的崇拜,以至于服务其他存在的符号也相应失去立足的根基。如果现实果真是技术垄断一切,那么所有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都要让位给“无极限增长、无责任的权利和无代价的技术”③。技术失去道德基础后将无法塑造价值观。而从人文传统中获取意义的符号逐渐失去活力,其神圣和严肃的内涵将消失殆尽,社会终将呈现出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描绘的局面:人类生活在技术铸就的牢笼中,物质文明发达,但人文道德泯灭。
三、同化人类交往方式的网络空间
在《羚》中,技术成为主导文化,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将一切文化符号变为与技术相关的符号,此时技术文化显现了其最突出的一种存在形态——在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基础上形成的虚拟文化。虚拟文化以非现实的网络空间为依托,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
在虚拟空间基础上形成的虚拟文化,消除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多样性和他性。小说中,面谈、写信等传统交往方式被便捷的电子邮件、视频通话等取代,却减少了人们相互接触和交往的可能性,形成了单一疏离的社会空间。“雪人”和“秧鸡”同住在荷尔史威瑟大院时是亲密的伙伴,那时他们还起名为吉米和格伦。起初他们习惯于现实中的交际活动,未完全被虚拟文化所主宰,这一时间段内两人的关系也是最牢固和谐的。但电子信息技术无孔不入,异化了两人的正常交往。两人同处一室却用电脑下棋,因为格伦认为塑料棋子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棋在人的脑子里。格伦还对战争游戏情有独钟,因为他笃信科技理想,鄙视宗教、人文和自然,故而不懂得珍惜生命和尊严。与此相反,吉米非常在意艺术珍品,并担心它们会被毁灭,所以玩游戏后总是噩梦缠身。他们还时常在网上光顾自杀直播、虐杀动物、色情表演等各种刺激感官的网站,乏味的现实生活早已失去了吸引力,虚拟空间里展现的种种猎奇现象和扭曲价值观最终使他们渐行渐远。
阿特伍德暗讽了当下技术乐观主义者们的观点: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创造的新网络世界促进人的交往。琳达·哈拉西姆(Linda Harasim)曾热情洋溢地预测新虚拟世界带来的社会文化形式的改变:“网络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允诺社会话语和社区形式的新聚集场所。”④虚拟空间的确能消除现实世界的许多限制,提供人们相互认识的新途径,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性别、种族的人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基于共同的兴趣建立交往关系,共享经验。但这样的虚拟文化是一种基于共性的“关系聚合”,如果出现与自身的相异性,交往关系则会断裂。虚拟空间表面上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实际却通过控制差异和他性,抹除不同,建立统一。虚拟空间并没有开创人类聚合的新方式,也没有扩展人们交往的新形式,相反,它将人们原本多样的交往方式狭隘化和同一化。正如罗宾斯和韦伯斯特所说,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带来的并不是多样、宽容、亲密的社会空间,而“只是个一切均被知晓、熟悉且可以预测的狭隘的范围”⑤。在《羚》中,被虚拟文化框定的人类交往模式正是畸形技术化社会结成的恶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同化的就不只是交往方式了,唯技术思维形成的社会空间正在迅速侵蚀传统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模式。
四、技术时代的人文呼唤
阿特伍德剖析了虚拟文化消除人类交往方式多样性和他性的过程,跟随其批判性视角,读者同时也能感应作家自身所持有的文化立场——捍卫人文艺术。
《羚》中,科学技术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人文艺术则遭到鄙弃。秧鸡钟爱的游戏“血与玫瑰”,“‘血’的一方以大屠杀、种族灭绝等人类恶行作为筹码”⑥,“玫瑰”则代表诸如艺术品、科学突破、建筑杰作等人类成就。如果“玫瑰”方想要阻止“血”方的恶行,就要用本方旗下的各种人类历史瑰宝来兑换。玩“血”的一方通常都能取胜,意味着技术文化的人文道德沦丧,游戏的结果更象征着人文艺术的全面崩坏。秧鸡和吉米两人,一个是众星捧月的理科高材生,一个是微不足道的文科生。录取现场,顶尖科技院校轮番争抢秧鸡,最终他被沃特森·克里克大学高价挖走,而吉米则无人问津,还是靠父亲的关系才进了玛莎·格雷厄姆这所二流人文学院。两所大学校园环境和学术发展的强烈反差凸显了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备受重视和人文的衰退没落。克里克大学宛如一座高科技堆砌的宫殿,对比之下,格雷厄姆学院不仅环境破败不堪,学术领域的萎缩更为可悲——戏剧、文学、舞蹈等人文艺术的魅力全面消退。毕业后,秧鸡在最有势力的大院“雷吉文—埃森思”里平步青云,吉米却只是个随时面临失业的广告职员。科技的地位举足轻重,而文学艺术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只能依附于科学技术存在,成为一个卑微的附属品。
尽管阿特伍德创造了这个无限放大科学理性的技术世界,她却在行间字里不懈努力地捍卫人文艺术,比如塑造了文学、艺术、人性的化身——吉米。尽管在格雷厄姆学院死气沉沉的生活里备受煎熬,吉米还是认真投入学院生活,因为文学艺术是他的精神食粮。初遇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大放异彩的文学性词汇瞬间触及吉米的灵魂深处,让他深受震撼。文学的光辉与吉米的灵魂贴合在一起,让他在冰冷的科技世界里寻找到了精神家园。因此,当秧鸡肆无忌惮地抨击艺术的价值时,吉米愤怒而坚定地辩护道:“当所有文明灰飞烟灭后,艺术是唯一能幸存的东西。形象、文字、音乐、充满想象力的建筑,人类的意义就是由他们充当注脚的。”⑦新卢德主义分子罗斯扎克曾指出,当代学生“正被蓄意剥夺除逻辑推理外的其他感觉、常识判断以及审美趣味等能力……丧失了运用艺术媒介的技巧和自由地创造一幅图画的乐趣”⑧。摒弃了情感、审美、道德,盲从于科技理性崇拜后,理科尖子生秧鸡最终摧毁了人类;而钟爱艺术、碌碌无为的二流文科生吉米却成为仅有的人类幸存者。阿特伍德呼唤现代人类保留内心本真,铭记人文艺术对社会的价值,警惕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而忽略人性中最根本的感情诉求。
五、结语
阿特伍德通过《羚》表达对唯技术社会的担忧,借用生物基因等灾难警示并揭露技术文化对人文传统造就的恶果。她拒斥被技术重构的单一文化符号,暗讽被虚拟文化规约的交往方式。对人文艺术的留恋促使阿特伍德立足于传统文化人与人、与社会诗意和谐的关系,批判技术文化造成的实践方式去经验化和伦理观异化。阿特伍德通过小说警示读者:人类需要在追求科学理性的同时尊重传统文化、捍卫人文艺术。技术需要道德伦理的约束,否则会成为一种“理性之蚀”,最终导致人类未来的覆灭。
①⑥⑦ 〔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版,第29页,第80页,第172页。
②③ 〔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99页,第107页。
④ Harasim,Linda M.Networlds:Networks as Social Space.Global Networks:Computer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93:p 25-24.
⑤ 〔英〕凯文·罗宾斯、弗兰克·韦伯斯特:《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技术到虚拟社会》,何朝阳、王希华译,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版,第300页。
⑧ Roszak,Theodre.The Cult of Information.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