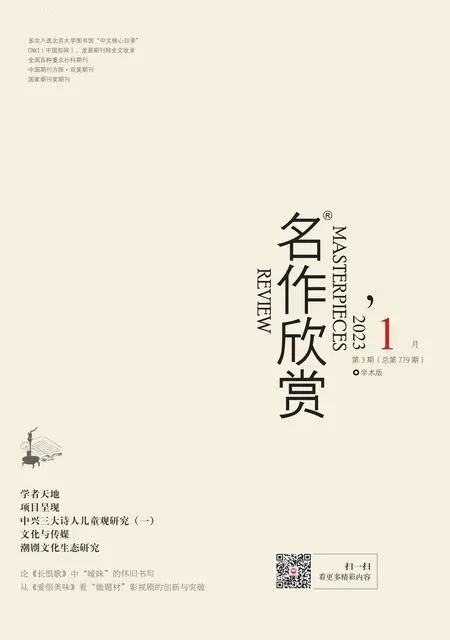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赎罪》爱情悲剧中的罪孽分析
⊙李春玲[湖南大学,长沙 410000]
西方文学创作中有一个永恒不灭的主题——忏悔与救赎。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于2001年提名布克奖,虽尚未获奖,但它别样的思考与叙述方式,仍使其受到关注。布里奥妮的姐姐塞西莉亚和家中仆人的儿子罗比彼此深爱,在他们好不容易明白对方心意,大胆相爱,即将共赴美好前程时,布里奥妮指证罗比为强奸表姐罗拉的凶手,二者被迫分离。后因战争爆发,他们虽有几次互诉衷肠的通信和短暂会面,却最终各自走向死亡,爱情成为悲剧。《赎罪》一名包含着浓厚的反思意味,那么如何认识文本当中的“罪”,作者又是如何通过书写主人公看似无望的赎罪,为人类和社会传达赎罪的现代意义?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一、布里奥妮幻想之罪
悲剧的源头直指布里奥妮的错误证言,它揭示出布里奥妮的本罪,仔细剖析这一行为,其背后展露出布里奥妮全然利己的自我虚构的幻想认知。
在布里奥妮遇见被侵犯的罗拉后,布里奥妮完全把握对话的主导权。她无视罗拉的犹疑,从疑问到肯定,在布里奥妮心中,“他”就不是模糊的、存疑的,而是一个肯定的、清晰的人物,由此将罪名稳稳安在罗比身上。同时,她不断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肯定自己已捕捉到“真相”,以绝对正义的姿态进行分析和命定,因为这“一切都很吻合”,“与最近发生的事一脉相承”。这两句话引出她判断凶手的逻辑链,即记忆。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回忆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不可靠的东西之一。此时此刻的情绪和动机是回忆和遗忘的看守者。它们决定了哪些回忆在当下对一个人来说是可以通达的,哪些是不能使用的。”①这显示出记忆具有强烈的建构性和主观性,对记忆的解读全然取决于主体的欲望动机。布里奥妮所选择的记忆事件,也全然为服务“罗比是凶手”这一命题被解读。
首先是发生于泉畔的花瓶事件。塞西莉亚和罗比自幼相识并且彼此爱慕,但出于阶级差异,他们总是以维系尊严的形式互相较劲,难以直视和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塞西莉亚拿着家中的古董花瓶来到喷泉旁边灌水,罗比本想伸出援手对其进行帮助,却在争抢中掰碎花瓶,碎片落入池中,塞西莉亚拒绝帮助,跳入水池,捡回碎片。出于视角局限,布里奥妮的记忆发生了丹尼尔·谢克特口中的“错源”现象:“记忆的主体将自己的幻想内容记成来自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从而走向理想的自我定位,逐渐获得内心的安宁。”②她看到罗比“高傲”地扬起手,姐姐“拗不过”他,罗比被解释成羞辱姐姐的恶魔。同样的场景,相对占上风的人物在不同的视角下被完全颠倒,她依据自己的想象对记忆进行符合逻辑的解释和梳理,将罗比理解为粗暴、自大、依据力量羞辱女性的人。这一描摹在后来的图书馆事件中更得以凸显,同样是双重视角描写,塞西莉亚和罗比在互相确认彼此的爱慕之情后,马上陷入浓情蜜意。但在布里奥妮眼里,姐姐深情的眼神变成惊恐的、被侵犯的眼神,面对罗比这个巨大而狂野的恶魔,她极度恐惧,努力“挣扎”“抗议”与“自卫”,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出自布里奥妮的主观幻想与解读。于是,布里奥妮的罪之根源深入记忆层面,作者将不可靠叙事和真实进行直面对撞,加深其假证之伤。
小说从一开头就凸显出布里奥妮乐于幻想并且沉醉于世界条理性、有序性的构建,她的认知建构于虚无缥缈的幻想、小说情节和叙事惯性中。她乐于用“自我虚构”的方式来发现身份和存在的意义。“自我虚构”最早流行于法国文学,瑞士作家保罗·尼松曾将自己的书写称为“对缺少的情节的弥补”,这种弥补是构建小说真实的手段,但布里奥妮将其运用于对生活的认知,造成许多偏误。她也曾意识到自己的偏误,有过回归现实的呼声,但她回归的意图是基于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渴望这一事件驱散她现实生活的卑微感。然而,日常的底色就是平淡与枯燥的循环往复,通过“重大事件”彰显自己的力量,也是一种幻想。作为少女的她对罗比心生情愫,因此跳进水中,等待罗比义无反顾地拯救她,从而用这种英雄救美的桥段展现自己在罗比心中的重要性。在她发现罗比会拯救她时,她确认了罗比对她的“爱意”,然而罗比的回应击碎了她的幻想,同时也对她“自我虚构”的认知方式构成威胁。
布里奥妮常常以自我欲望为中心,直接或间接性地构建他者,忽视事实与真相。
二、从个体到群体之罪
由于战事激烈,为重获自由之身,罗比加入英国远征军的队伍,去往法国参战。作者详细描述了罗比和塞西莉亚之间的通信,他们分享日常琐事,彼此鼓励慰藉、诉说爱意。塞西莉亚动情地表达:“我爱你。我完全信任你。你是我最宝贵的人,是我生存的理由。”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作为彼此活下去的动力,带给对方最恳切的温暖。给她写信成为枯燥乏味中的“喜剧”,为想念而措辞、沉溺于这种精神白日梦中,罗比才能暂时脱离现实的苦难和折磨。残酷的是,战争日益严重、通信受阻,最终造成他们的永久性别离。战争是造成二者爱情悲剧的二重罪孽,然而战争之罪远非如此。
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在“二战”爆发初期,由于德军绕过马其诺防线,四十余万援助军被迫困于法国的敦刻尔克小镇。因海水太浅,英国海军援救无门,英军只能与海峡对面的英国遥遥相望。在最危急之时,英国政府及时发动举国上下所有民众的力量,利用一切海运船只,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奇迹般地用民用小船营救出33.8万士兵,保住了战斗的主力军力量。然而,麦克尤恩父母对“二战”的体验,让他对战争有着独特的感受:“没能在场提供帮助带来的负罪感,或者与过去有这样一种活生生的联系但无法对之做出解释……作为后代我们理应向亲历战争的父辈们表示敬意。”他大胆颠覆民族叙事语境下敦刻尔克大撤退事件的英雄权威,解构这段历史记忆背后的战争暴力和创伤。
在大撤退的过程中,罗比常常看到路上、人行道中横七竖八堆满尸体,昔日或宁静或繁华的小镇也被轰炸成废墟,但是在对奇迹的歌颂下,“有谁会在意呢?”“谁又会持有说服力的论据去兴师问罪呢?”历史书写通过数据量化死亡人数,数据将个体聚拢与抽象起来,从而使得个体被纳入“死亡”“牺牲”的整体概念下。麦克尤恩在创作前阅读了大量老兵的日记、信函,以细节化地还原当时场景的细节,将战争残酷的本质直接撕开置于读者面前。作者还凸显出战争对人性的消弭,在“二战”背景下,英国士兵成为杀人工具。“树是刚长出叶子的悬铃木,腿,是条人腿……光秃秃的,从膝盖以下齐齐地斩断。”面对生的象征与死的震撼,士兵们却“发出轻蔑的声音”,因为“见得够多的了”。在正常的环境中,极端和暴力是少数,一旦出现就会迅速引发关注,但在“二战”背景下,杀戮成为日常,恐惧成为生活底色。除此之外,作者还描述了部分英国士兵在群体的癫狂状态下的理性丧失,他们因为不用承担任何道德责任,压抑在心中的挫折以对他人无端暴力的形式爆发。被定义为正义和荣耀的战争背后,包含着种种人性扭曲的血腥事实,它完全展露出人性冷漠和自私的一面。
战争的主体是人,战争之罪的背后就是人类罪恶,每一个人无论是否参与其中,是否被迫,都应当为此承担责任。1846 年,梭罗撰文批判服役士兵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批判公职人员宛如机器的例行办事,而不从道德良知的角度对抗政府的腐败,根据社会真实状况勇敢地做出选择。梭罗成为柏拉图洞穴神话中挣脱枷锁的第一人。对战争中的人们,麦克尤恩发出追问:“你今天没杀人?可是对多少人的死你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无论是在极端情况之下,还是在和平的现实社会当中,许多人仅仅只是专注于自身的利益,或为升迁求财,或为侥幸生存,而忽视道德与正义,在他们的逻辑中,如果不采取任何越界行为,只是被动地听从命令,就不用承担道德后果。由此,麦克尤恩通过战争环境,揭露出战争之罪,并进一步点明群体之罪孽,以及缺乏反思下人性本恶的原罪。
三、从赎罪意识到现实反思
小说以塞西莉亚和罗比的爱情悲剧,揭露背后的双重罪恶。随着布里奥妮的成长和成熟,她逐渐认识到自己曾经的错误选择,并从实际行动和写作行为两方面出发,开启赎罪的多重尝试。
布里奥妮自我虚构的认知惯性让她在多个再建构的叙事序列中确定身份,威廉·布洛姆提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③环境的突变会严重影响自我认知。罗比被强行定罪,这对他的人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间接摧毁了姐姐塞西莉亚与家庭的关系,这一系列事件直接影响了布里奥妮的生活与职业选择。自此,姐姐成为“支配”她人生选择的梦魇,她尝试用贴近姐姐的方式来弥补错误。于是,布里奥妮放弃去剑桥大学进修文学的机会,来到姐姐所在的医院,成为一名战地护士。游历于幻想之间,用笔和意识书写世界秩序的布里奥妮,终于在现实情况下被捆缚于一条条严明纪律和基本准则之中。同时,她也和姐姐一样选择与家人断了联系,意欲与姐姐贴近,与“他们”离远。家族各个成员常常不是站在道德的角度进行价值判断,而是站在阶层制的高点主观评价。逃脱法律制裁的真凶马歇尔为了湮没真相,维护自身利益,不惜迎娶受害者罗拉,阻止布里奥妮书籍的出版:“他们用活期存款就能轻而易举地使出版社身败名裂。”布里奥妮坚定地与其划清界限,即使“断裂”之后的生活给她带来浓郁的痛苦和回忆之伤。能够获得救赎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所犯之罪,拥有“罪感”,在此基础上,主体努力争取和追求赎罪愿望的实现。布里奥妮正视所犯错误之行,揭露真相的勇敢,以及生活中违逆内心、带来深刻痛苦的现实选择,都是她惩罚自己,为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的选择。
其次,布里奥妮用书写赎罪。她通过小说揭示真相,披露这一事件下自我和集体的罪恶,战地护士的身份让她直观地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病痛,通过书写凸显战争罪孽之深重,引导人们认识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残酷。作者描述了战争残酷而悲惨的画面,不仅仅是在揭露战争恶的本质,更是在披露群体性犯罪当中的人性之恶,以推动人们进行道德反思。
然而,老年布里奥妮的出现揭示出爱情的美好结局为虚构,现实情况是,罪孽已经造成,无法完全赎尽、完全弥补。一切都已经发生,那么这种看似“注定失败”的赎罪是否还有意义?人性当中的恶无法否认,即使罪恶无法消除,也不意味着赎罪失去价值。对西西弗斯而言,重复推石上山的行为本质上也能被解读为毫无意义,但是由于其存有这一欲望动机,对过程的体验就构成意义。布里奥妮无法让塞西莉亚和罗比死而复生,无法阻止战争爆发,但她尝试过,她用作家的仁慈给予他们一个美好结局,用自我揭露和揭露现实的方式书写自己的自我反思和忏悔意识,这就构成了赎罪的意义。直面并且深刻认识到人性之恶、人性之罪,将人性当中丑陋甚至矛盾的一面撕裂开来,才能够进行自我忏悔。这种忏悔立足于对人的深刻认识,是一种对自我心灵的忏悔,对道德的深刻认识和自我批判。麦克尤恩试图由此来唤醒人们对自我之恶的直视,从而推动人们净化灵魂,促进一个和谐、友善社会的发展。
麦克尤恩深刻认识到人性因素中的恶,揭示出人之恶、人之罪以及尝试赎罪背后的悲剧性,试图通过这一书写,让现代社会的人们拥有“罪感”,正确认识自我,面对所犯下的罪孽、错误,进行及时的道德审视、自我批判,勇于承担“无罪之罪”,从而推动人性向好的一面转变,推动社会稳定、健全、持续地发展。
①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② 邹涛:《叙事记忆与自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③ 乐黛云、张辉:《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