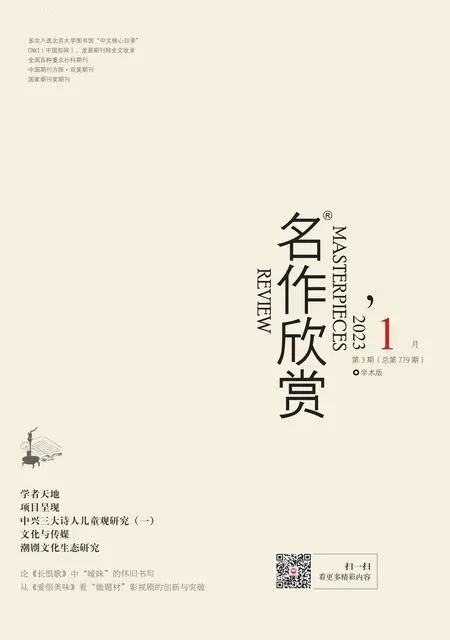浅论鲁迅所指老莱子之“雏”
⊙唐欣[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14]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后记中再谈《二十四孝图》时,提到了刻于同治十一年的一本《百孝图》。他摘出其中有关“老莱娱亲”的一段话:“莱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常弄雏于双亲之侧,欲亲之喜。”(原注:《高士传》)令鲁迅觉得特别的是其中的“雏”字,于是他对“雏”作以下猜测:“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Hina,写作‘雏’。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所以英语的Doll,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①
李圣华在《“弄雏”小考》中对“雏”的本意进行了考证。通过晋人徐广《孝子传》、唐《艺文类聚·人部四》所采《烈女传》《山东汉画像石汇篇》等图文资料,他证明“弄雏”之“雏”是“乌鸟”的意思。乌鸟即乌鸦,具有反哺的孝亲象征,因此鲁迅的猜测是错误的。②
鲁迅对于“老莱弄雏”中“雏”字的理解来自日文汉字“雏”,其平假名为“ひな”。日语“雏(ひな)”也有“小禽鸟”的释义,同汉语“雏”的意思基本相同。然而鲁迅明明知晓,却转而提出新思路,选择它的另一词义“人形玩偶”进行阐释。由于某些日语汉字词与汉语古语词的意思是相通的,鲁迅猜测“雏”可能属于这一类,得出汉语的“雏”也是某种人形玩偶,文字上写作“傀儡”。但实际上,如果无法追溯二者的词源、考证二者接触传播的关系,则无法证明日语“雏(ひな)”和汉语“雏”完全同义。因此,尽管存在可能性,鲁迅的推导不够合理,他自己也承认这不过是一时“臆测”,没有坚实的凭证。
鲁迅在猜测词义时,多次躲避“小禽鸟”的意思,偏向“傀儡”之意。这种偏向是有意为之,源于他对“老莱娱亲”的独自见解。本文通过研究鲁迅误解之“雏”,对其选择的缘由进行初探。
一、鲁迅所指“雏”之形
鲁迅对老莱之“雏”的解释是“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人形”可理解为“人的形貌”,后文“洋囡囡”“泥人儿”也表明“雏”确实像人。因此这种理解说得通,但并不正确。其实“人形”是一个日语汉字词。鲁迅作品中有多处相同用法,如《娜拉走后怎样》中“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译文《往访的心》中“是奈良人形似的并不细细斫削的人”③。这同样也可以在周作人的作品中找到,如“以雏与人形为其专门”④、“日本东北地方的一种木制人形的”等。这是因为在日语里早有词语“人形(にんぎょう)”存在,指的是一种日本人偶。二人都是直接用的日语汉字词。“雏(ひな)”的人偶词义就来自人形的一种——“雏人形”,通常译作“雏人偶”,是日本很有特色的一种手工艺品。又称“三月人偶”,是送给在三月三日满一周岁女孩的礼物,具有祈福消灾的功能。在日本平安时代,“人偶被称为‘雏’,玩人偶被称为‘玩雏’”⑤。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鲁迅对它并不陌生,自己还曾“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⑥,也有友人“内山君赠海婴五月人形金太郎一坐”,“山本夫人赠海婴以奈良人形一合”。因此,看到《百孝图》中的“弄雏”,鲁迅很可能联想到了“玩雏”,由此推测“雏”即人偶。
由于中国并没有雏玩偶,鲁迅最终“在文字上只好作‘傀儡’的”。“傀儡”源自“傀儡戏”,指“木偶戏中的木头人”,形貌接近真人。《列子》中就对傀儡有过夸张的描写:“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肢节、皮毛、齿发”,不过都是“革、木、胶、漆、白、黑、丹、青”所做,“皆假物也”。⑦鲁迅能够将“雏”当作“傀儡”,主要因为二者都似真人形貌。另外,傀儡也具有人偶之意。这在《玩偶之家》的另一译名《傀儡之家》中可见一斑。将本意为“娃娃”的“dukkhe”与“doll”译作“傀儡”,是因为它兼具“玩偶”与“受操控”的双层含义。不过,相对于巫术色彩更浓的傀儡,日本雏人偶更具有人文艺术内涵。它展现出仕女、儿童、艺妓等各种各样的群体,神态灵动,妆容、发型与服饰都十分精美,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艺术品。⑧
老莱子是春秋晚期人物,当时傀儡仍被用作“丧葬之乐”,未发展为吉庆娱乐的工具⑨,更不是玩具。而日本还处于绳文时代,过着部落氏族的原始生活。此时也没有中日交流的记载。因此,老莱拿的既不是“傀儡”,也不是日本人偶。不过,《百孝图》刻于同治年间,其作者是可能见过人偶类玩具的。
二、老莱弄“雏(ひな)”
汉语之“雏”和日语之“雏(ひな)”都有明显的“小禽鸟”的意思。而“人形玩偶”之意只有日语之“雏(ひな)”能够确定,且人形为日本特有的手工艺品。为什么鲁迅依旧说它“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偏偏选择“人形”的释义呢?这种带有主动性的猜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鲁迅的独特观点。
鲁迅认为人形玩具是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玩弄孩子的玩具比玩弄禽鸟更加“自然”。但对于现实中的老人,显然是把玩禽鸟比玩小孩子的人形玩具更加正常。因此此处鲁迅所说的“自然”,应当是放在“老莱娱亲”的故事语境当中的。“老莱娱亲”作为一个宣传孝道的榜样故事,其孝的重点落在“娱”字。老莱子故意安排滑稽搞笑的动作,博父母一笑,让老人家开心,消除寂寞。即故事本身的设计就是通过丑态达到喜剧效果,起到“娱”的功能,实现孝的目的。由此可知,老莱子手中拿着的东西越出格、越滑稽、越不可思议,反倒越能“娱亲”。对于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讲,小孩子的人形玩偶显然比小禽鸟更加稀奇,更能“娱亲”。所以,人形玩偶更加符合故事本身的语境,更“自然”地贴近了“娱”。
另一方面,鲁迅选择“人偶”释义,还能达到更强的讽刺效果。他在《二十四孝图》中明确表明对“老莱娱亲”的不解,甚至是反感。老莱子们或是拿着“摇咕咚”,或是“诈跌仆地,作婴儿啼”,把“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理,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七十多岁的老人偏要假装婴儿,惺惺作态,用极其不合身份、不合常理的方式逗笑,是令鲁迅讨厌的原因。基于这个理由,鲁迅还对郭居敬版本《二十四孝图》中的“摇咕咚”发出了攻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支拐杖。”可见,老莱子拿的东西越偏离于拐杖、越不接近常理,也就越肉麻、越能够成为鲁迅讽刺的对象。鲁迅把“雏”猜测为“人偶”,一方面因为他实在讨厌这种作态,于是愿意往更过分的方向去理解。另一方面,则可以看成是他故意理解为此,通过制造老莱与手中把玩之物的距离和陌生感,加强厌恶情绪和讽刺力度。
三、鲁迅之孝道观
鲁迅选用“雏”的人形意是为了增强“娱”的滑稽与讽刺意味。他真正反感的也是这种孝敬的方法,并不是对孝本身进行批判。首先,这种“娱”的方法是不适用于老人的。无论是把玩人形还是拨浪鼓,又或者是在双亲之侧挑逗小禽鸟,老莱子都摆脱不了一种“装佯”“诈”“作态”“假惺惺”的样态,都这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若要孝顺,老人自有老人的孝顺的方法。何必为求得一“孝”,忸怩作态,佯装小孩子呢?其次,这种通过丑态博得父母欢心的方法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孝的目的。形式主义的外皮下是浅薄的内涵,至多只不过赢得一时的笑意,给不了父母真正的精神慰藉。而放在现实中,两个百岁老人看到自己年迈的儿子如此作态,是否也会尴尬羞愧?在“老莱娱亲”的故事后,鲁迅还提及了“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故事,竟然要通过损毁身体甚至牺牲生命的方式来尽孝。鲁迅认为这种孝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更不能用来宣传。过度宣扬孝的方式而脱离孝本身,就会走向缺乏实质的形式主义的伪孝,最终变成统治者宣扬礼教的工具。把这样的《二十四孝图》给儿童看,不仅会引起孩童的反感,还可能成为毒害儿童思想的凶手。不但无益于父母,更是会对后代产生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
孝本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被统治者利用而走向畸形与僵化的情况。鲁迅反感变质了的孝的封建性、虚伪性与残酷性。他否认这种孝的方法以及对该种方法的宣传,不是要去破坏孝道,而是要进行重新建构——孝不在无聊的形式,而是要关注实质。那么如何形成正确的孝道呢?他也指出一个途径——“爱”。在父辈与子辈的关系里,父权不是一切,子女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年轻一代是未来的开拓者,不能让他们被封建的孝道残害,死气沉沉。觉醒的父母应当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要起到保存、延续和发展这些生命的作用,帮助孩子在身心上健康地成长。在爱的环境中,子女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形成正确的敬爱父母的意识。而只有这种健康的孝道,才能维护代际的和谐,使整个民族的生命延续下去。
四、结语
鲁迅本身就是一个孝子,始终赡养、关爱、敬重母亲。他在行动上竭尽所能,其孝顺出自本心的真诚。因此,鲁迅反感《百孝图》中老莱子的“佯装”之态,认为尽孝应自然,应当出自真爱。他的孝道观,不仅着眼于小家,更纵览历史,横观整个民族。他对封建孝道的虚伪与残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也为健康的孝道观指明了新路。因此,对于“老莱娱亲”这样的故事,鲁迅并不喜欢,自然会把老莱之“雏”猜测成幼稚的小孩子的玩具了。
①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34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李圣华:《“弄雏”小考》,《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第71—73页。
③ 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④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7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 杨敏悦、王妙文:《〈民俗之库〉之四·异国风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⑥ 鲁迅:《鲁迅日记》,中文在线2020年,第176章,日记十六,十一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⑦ 列御寇:《列子》,清嘉庆刊书名家江都秦氏石研斋刻本影印。
⑧ 陈学军:《日本人形艺术的发展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思考》,《书画世界》2015年第6期,第84页。
⑨ 张大新:《中国戏剧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