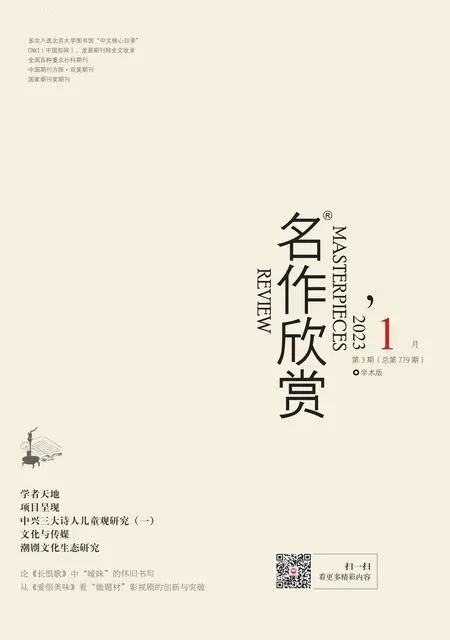抒情性意境下的还原与变形
——简论小说《萧萧》与改编电影《湘女萧萧》
⊙梁艺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1800]
沈从文以其抒情性小说享誉文坛,而轻冲突性的抒情性小说最特别之处就是在悠远而空灵的意境刻画之中蕴藏着独特的叙事功能。本文从整体色块的继承、移植与再调,明媚亮色的冰冷和压抑,以及自然物象全方位的变形和象征三个方面来阐述改编电影《湘女萧萧》对其原著在抒情性意境中整体环境的还原与变形。
一、整体色块的继承、移植与再调
(一)山水之境的继承与复演
毋庸置疑,整部影片做到了湘西山水之景一体风格的再现,还原了读者心中水江澄澈的清泠和郁郁葱葱树林下的宁静,再现了漫山遍野富有活力和生机的梯田以及依山而建、高低错落的吊脚小楼。其中,乡野自然的原始和活力一览无余,这无疑是对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整体性环境的继承。
(二)乡野习俗的“移花接木”
除此之外,导演谢飞将寥寥千字的《萧萧》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拓展出一幅真实而迂腐的封闭乡村的习俗画卷。在原汁原味地呈现湘西风光的同时,展现出边远湘西中的人情风光。
影片一开场就将《边城》中的地标型建筑“白塔”在碧波荡漾间呈现出来,渡船中载着即将嫁到春官家的新娘子萧萧,这是与《边城》一脉相承的:“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而在喧闹的拜堂仪式中,萧萧与一只鸡公,而非新郎春官,进行着一场可笑而愚昧的婚礼,这是来自《长河》中的习俗:“这些小女子年纪十二三岁,穿了件印花洋布裤子过门,用一只雄鸡陪伴拜过天地祖先后,就取得了童养媳的身份。”
而电影中因出轨被施以“沉潭”处罚的巧秀娘,衣服被剥得精光,被人捆缚成扭曲的模样,脖颈处缠绕着沉重的石磨,于河中央处被无情推下,直至发出一声凄厉的“啊”后就再无声响——这场触目惊心的“沉潭”,正是从沈从文另一部小说《巧秀和冬生》中移植而来:“那些年青无知好事者,即刻就把绳索和磨石找来……年青族中人,即在祠堂外把那小寡妇上下衣服剥个精光,两手缚定,背上负了面小石磨,并用藤葛紧紧把石磨扣在颈脖上……把小寡妇拥到溪口,上了一只小船,沉默着向溪口上游长潭划去……冷不防一下子把那小寡妇就掀下了水……颈背上悬系的那面石磨相当重,随即打着旋向下直沉。一阵子水泡向上翻,接着是水天平静。”可以说,导演谢飞遍览沈从文之书,才使得其电影无处不以湘西的风土人情为基础,呈现出瑰奇而独特的湘西风光,但不难发现,在风俗的背后,影片在迂腐保守的乡村气息的浸染下呈现出一股阴冷而诡谲的色彩。①
(三)整体色调的精神性变异
在高低错落的乡村小屋中,总有破败没落的残缺老旧之感;在喜庆欢快的婚娶之事外,还保留着扭曲人性的沉潭旧习、压抑生长的裹胸观念和愚昧落后、世代相袭的童养媳制度;再烂漫自然的山歌,再清丽迷蒙的山水也无法抹去老旧而压抑的情调。
除此之外,全片还采用以冷灰色为主的暗色调,在青山绿水间始终缺乏一股明媚之色,水碓石磨、黑漆漆的县城社戏甚至山林芦苇都有意蒙上晦暗的面纱。黑洞洞的祠堂、漆黑一片的河塘,总会在丝丝凉意中牵引着观众。尤其在沉潭戏的画面里,举目都是凝重的夜色,在水汽迷蒙中幽深与黑暗好像在隐隐蔓延。
在古朴优美的湘西地区风俗画卷中,嘹亮舒扬的山歌也有时而压抑晦涩的时候;迷蒙清冷的湘江山水也有着阴暗幽深的色调。再加之远多于小说《萧萧》的压抑禁欲的乡土习俗的铺陈,使得电影《湘女萧萧》在古朴中始终无法摆脱愚昧压抑的氛围,这与全片直指封建闭锁幽暗的文化习俗,大力批判封建禁欲主义的主题不无关系。而这无疑是对沈从文“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精神性颠覆。
二、明媚亮色的冰冷和压抑
整部影片最为明亮的两处便是婚礼时分迎接萧萧拜堂时的红色和巧秀娘沉潭时满山熊熊燃烧的火把的黄色光芒,可这两抹亮色并未带给观众以温暖柔软的色泽,而是在主色调——晦暗灰色的基调下,迸发出难以抗衡悲剧命运的悲哀与绝望。②
(一)冰冷不幸的鲜红色
婚礼本应是热闹欢喜的人生大喜之事,可每个观众都从影片中封闭愚昧的乡村童养媳制度中感受到萧萧所背负的悲哀懵懂的阴影。更不幸的是,因春官年纪过小,无法静站完成礼仪,婆家竟用公鸡代替新郎,隐隐暗示了萧萧的命运因童养媳制度而必然走向悲剧。在咿咿呀呀的唢呐声中,在时而欢喜高昂时而呜咽沉重的配乐中,借助红艳色泽的反衬,电影中压抑的氛围已经呼之欲出。
而在原著《萧萧》中,婚礼的描摹只是一笔带过的事端:“萧萧做媳妇就不哭……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笔端中只有单纯而稚嫩的少女,而全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和启蒙,色调是淡红色的,而非冰冷而压抑的鲜红色。
(二)明灿可怖的炽黄色
巧秀娘被沉潭时漫山遍野熊熊燃烧的火把,象征着腐朽和黑暗之光遮蔽了人性之光。当她被处死时,荫翳的天色中飘荡着的只有明灿的火把,这燃烧的是群体的愚昧,更是封建观念的残酷。在青黑色的天空之下,蓝白色的迷雾腾起,人影迷乱,只剩下或大或小摇曳的火光在闪烁,象征着一个人的站立,可无数的火把聚集在一起,群体无意识的狂热共同点起了最大的篝火,在这场篝火中,人性与人命尽数燃烧;直至火把最终熄灭,巧秀娘也消失不见。混乱杂繁的弦乐和哀戚的笛声相互交织,时而麻木时而恐惧的脸庞快速闪过,无一人想着去拯救巧秀娘。在炽热的黄色火团中,只偶尔窥得被绑缚石磨盘的巧秀娘一面,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暗夜里的悲哀与绝望。这样的光芒是恐怖的,更是沉痛压抑的。
而在原著《萧萧》之中,巧秀娘这位青年丧夫的小寡妇的故事是全然不存在的,电影中将其命运中“丧夫——干苦活——偷情——被捉奸——被沉潭”作为萧萧故事线中相对应的暗线表现出来,正是将女性群像在腐朽保守的湘西落后农村中的痛苦压抑集中展示出来,“鲁迅式”的批判意味不言而喻。
三、自然物象全方位的变形和象征
在以抒情性为主的电影世界里,自然物象往往挣脱事物本身,成为意象化的产物。在谢飞导演的《湘女萧萧》中,水碓、娇花和甘蔗林、石磨盘三者共同成为全片情节推进的象征,具有别样的叙事特质。这完全架空于原著的自然物象,表露出对小说《萧萧》的反叛式的表达和批判式的态度。
(一)水碓:时光流逝和轮回的见证者
作为南方农村代表性的农具之一水碓是劳动人民智慧的集中展现,而在时光和水流的共同作用下,上下不停舂米的碓杆正象征着萧萧的成长也如碓杆一般,无法扭转时光的流转,随着一下又一下的舂米,萧萧的身体也一点一点地发育起来了。
这个意象无疑是导演有意安排的,每逢时节的变迁、故事新情节的介入,形象化的水碓都会以时间分割者的意象被呈现出来,代表着时光的流转。全片四次出现的大水车将萧萧的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幼、青、孕、长。③首次是萧萧以童养媳的身份刚刚嫁入春官家,水碓旁的杂草丛生正预示着尚处于童年期的萧萧仍非常稚嫩,正要蓬勃地生长着。第二次是萧萧逐渐步入生理上的成熟期,在青年阶段,蓬勃的爱意与情欲以身体为载体催促着萧萧自由地寻找爱人,不断冲破封闭保守的乡间习俗,与花狗热烈地相爱。第三次是枯黄视野旁的水碓,碓杆依然在捶打米粒,但凋零的落叶带来了萧瑟的气息,也带来意外怀孕的萧萧的悲剧。最后是新草萌芽中的水碓,油菜花田烂漫开放,在欢快与阴郁并存的唢呐竹笛声中,既是萧萧作为长辈迎来新生,也是整个村落又一次踏入童养媳的悲剧之中,在时空的轮回里,不幸又再一次重演。完全脱胎于导演内心的水碓这一意象,正将时光不断流逝却始终是悲剧轮回的见证者这一意味传递出来。
(二)娇花与甘蔗林:蜕变与挣扎的必经之地
在萧萧与花狗正式相爱交欢之后,花朵与甘蔗林共同串联起二人情感“相爱——怀孕——分手”的全过程。
娇花正象征着美好情谊的表达,在赠予对象的不断转变中,女主人公萧萧的情感世界也在变化着:在起初调情时,花狗一面唱着调笑童养媳的荤歌,一面在进城后,映着夕阳晚波的余晖,送给萧萧象征着爱情的绣花。而在又一次的进城路上,又一次的轮回里,落叶纷飞,花狗也早已偷跑。这哑巴哥安抚不了春官而送出的落叶花,正赤裸裸地将萧萧爱人离去、人性重被压抑的苦闷透露出来。最后当萧萧逃亡失败后,春官在探望萧萧时又一次送出了花朵,这份单纯的善意,是一次美好与人性的传递,更是萧萧彻底摆脱与花狗的爱情的转折点,萧萧开始步入新的轮回。
而甘蔗林作为这个落后小乡村的隐秘之地,总是呈现着萧萧和花狗最真实的心意和想法:在夏季昂扬生长的甘蔗林里,二人一踏入这个隐蔽之地就开始热烈地拥抱和亲吻,这是自由与激情悄然蔓延的快乐。而当秋季再次相逢在甘蔗林时,二人被突如其来的怀孕的消息吓得惊慌无措,相互抱怨,这是二人无力抗争沉疴痼疾的逃避和无奈。而当萧萧再次来到甘蔗林时,就是得知花狗逃跑,在曾经相爱的玉米地里狂奔着找寻花狗。她寻找时的焦急、无奈,直至最后再也找不到的苦闷、懊恨,使劲地砸着荒草和大地的种种举动,和着狂风吹打着草叶,江流声、狂风声和哭嚎声交织的声浪,直白地将萧萧无力挽回而悲痛欲绝的心情表现出来,将满地愁绪的怒号和惆怅怒吼出来。毋庸置疑,甘蔗林这一场域正代表着生命力与爱情的勃发与消逝,在隐秘之中,不顾一切的爱情和自由生长的人性悄然地与保守压抑的习俗对抗,又悄然失败,埋葬在甘蔗林里。娇花与甘蔗林共同串联出全片萧萧与花狗情感蜕变与挣扎的全过程。
(三)石磨盘:自由天性与愚昧习俗的博弈
石磨与碾坊同样是劳动人民在不断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智慧成果的结晶,但又以其特殊的结构构造,成为《湘女萧萧》影片中最有批判力度、最别具一格的意象。
在全片中,石磨盘多次出现,不完全统计有六次之多。首次出现就是花狗和萧萧第一次在碾坊里偷情,磨坊里哗啦啦的水声和碾压声正是二人现实中交合的保护伞,而碾盘中同时有着阴阳两面不断啮合的石磨,在随着水流不断的轮转和紧密的咬合中,正象征着美好的性爱。④这一处随着水流肆意流淌,不断咬合的石磨盘正是自然人性与炽热爱情冲破陈规之后的最好象征。
而此后石磨更是频繁出现:巧秀娘偷情被抓后,就一直被束缚在石磨上;沉潭时,也同样是石磨使其难以挣脱,丧失生命;春官母亲在和老妈子谈论沉潭事件时也在推拉着石磨;花狗逃走后,怀孕的萧萧身处碾坊之中正是看着石磨,才回忆起当时既欢喜又不堪的时刻,开始疯狂捶打自己的肚子;在婆婆商量变卖萧萧时,萧萧就只能紧紧挨着石磨坐着。⑤以巧秀娘被沉潭一事为例,不难看出此时石磨早已成为愚昧习俗的帮凶和象征,隐喻着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碾压。巧秀娘脖颈上被缚着的磨盘,不仅是妇女出轨后被沉潭的惩罚,更是束缚在妇女头颅上的一份难以承受之重,是生命无法尽情追逐爱情、追逐自由的镣铐和枷锁。每一个女子被如石磨一般沉重而死板的落后习俗束缚后,都会发出沉潭窒息前濒死的一声呐喊,这是痛苦与绝望的号叫。
石磨的命运轮回在每一个女子身上,在纵享爱情的欢愉与保守习俗压抑的痛苦之间,每一位女子都在挣扎。毋庸置疑,石磨与碾坊这一意象是全片最具批判力度的意象。
四、结语
现代小说家在对乡土风俗描写时大凡持有两种态度:一是启蒙性的批判,二是诗意化的审美。⑥沈从文以普照的人性之光成为诗意化审美的代表。但谢飞导演在改编《湘女萧萧》时,虽在形似中描摹了湘西清丽舒扬的山水与习俗,但风俗、环境、色调和意象中处处都有主题性的暗示与隐喻。导演将一切悲剧的根源归结为旧社会封建礼教的罪恶,所以影片的整体环境意象和色调氛围都透露出一种压抑而晦暗的色彩。笔者认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启蒙意识复苏的产物。在电影中,愚昧、落后、苦痛、无助交织其中,将沈从文自身的湘西气息尽数挥散,这无疑是谢飞摆脱沈从文原著的自我意识的“再创造”,是将“希腊小庙”改造成闷死愚民的“铁屋子”的“鲁迅式”的故事的精神性的颠覆。
①④⑥ 胡斌:《一次精彩的“误读”——从沈从文的〈萧萧〉到谢飞的〈湘女萧萧〉》,《写作》2012年第23期,第23—25页。
②⑤ 杨浩:《沈从文小说电影改编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李天福、孔优优:《人生或若一盏沙漏——电影〈湘女萧萧〉的深度解读》,《电影文学》2015年第13期,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