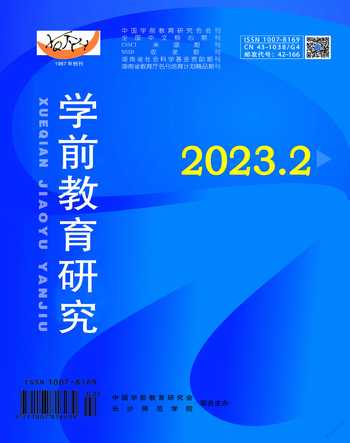培养儿童的“沉思之思”
孙蓉鑫 陈乐乐
[摘 要] 在当今的技术统治时代,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作为教育手段的技术表现出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然而,技术具有两重性,它虽然可以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但也会对儿童形成全面的束缚和控制。不过,人之为人的技术本质又决定了如果我们由此走向盲目抵抗的另一极,仍然是不对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對技术的工具论、计算主义或享用论的狭隘认识,借鉴海德格尔等人的技术哲学,通过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建构和解构,走向对技术的“沉思之思”。这本质上是让我们对技术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态度,使我们既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为何需要技术、应该如何发展与运用技术,又不会被技术奴役和控制。幼儿园教育可以通过丰富儿童对自然物的经验、支持儿童动手劳作、开展儿童哲学对话等方式,培植儿童对于“沉思之思”的心理意识萌芽。小学、中学和大学可以继续这种思维方式的培育,直至个体具备成熟的“沉思之思”,以此重建人类与技术出自本然需要的本质关系。
[关键词] 技术统治时代;技术的本质;技术哲学;“沉思之思”
今天的儿童正处于新的技术统治时代。技术统治时代以加速度的方式影响和变革着年幼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处于技术的“塑造”与技术文化的“襁褓”之中。技术的发明数量、更新速度以及传播方式以势不可当的姿态进入到年幼儿童的教育中,使得儿童教育与技术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儿童—技术—成长”之间的耦合。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所部署的十大战略任务中,第八条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现代技术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和评价等方面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撑与丰富,我们对作为教育手段的技术目前持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然而,从技术哲学角度来看,儿童及其教育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使技术对儿童生活的全面控制成为可能。年幼儿童的教育正在走向儿童与技术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教育者与技术物之间开启了一场对教育对象的争夺战。年幼儿童由于技术物的控制正在失去自身与世界的多样化联系,现代技术在儿童的发展和生活中表现出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技术可以促进年幼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为儿童教育提供一定的外部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年幼儿童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技术反过来又会控制儿童的生活。海德格尔等人的技术哲学思考从对物的追问开始,力图在技术的两重性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主要方法在于形成一种对技术的“沉思之思”的思维方式或认知态度,以此超越对技术的工具性或享用性认识。幼儿园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启蒙年幼儿童对技术生发出一种“沉思之思”的初步意识,进而帮助儿童在以后的成长中实现海德格尔所言的“沉思之思”。
一、技术统治时代与作为技术的生活
技术统治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的重要特征,我们不仅处于技术统治时代的背景之中,在此背景之下,现代技术正在逐步替代自然文明生活而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技术统治时代”从字面意思来看,现代人类生活已经从自然文明迈进了技术文明之中,我们已经把现代技术视为一种内在于人本身的生活方式传承了下来。技术统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新形式。地质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等众多学科都支持了这一观点。
地质学上把今天的人类社会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世”在这里表示的是地球的地质历史年代,人类出现在地质年代上的第四纪,因此将第四纪又称之为“人类纪”。在第四纪中又可细分为更新世(The Pleistocene)和全新世(The Holocene),全新世大约开始于11700年前。[1]2000年左右,生态学家尤金·斯托莫尔(Eugene Stoermer)和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全球变化通讯》上发表的论文中正式提出了“人类世”这个概念。[2]这就意味着从11700年前开始的全新世结束,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球年代——人类世。美国地质学家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认为人类世的最佳边界是20世纪中期。这就是说,按照扎拉斯维奇的推断,自20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就处于人类世了。由此而言,人类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变化唯一的重要因素,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自从大约40亿年前生命出现之后,没有任何单一物种可以独立改变全球生态,[3]但是人类做到了,各种生化武器和高科技等技术发明加剧了地球的气候与地质生态变化,人类技术逐步成为影响地球生态的决定性要素。
从社会学看,技术与人类社会历史共同发展,远古时期人类就学会利用自然制造工具,人类使用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技术统治时代,是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比之前任何的社会历史都要迅速,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4]现代技术对社会结构、生产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教育实践变革等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技术进步而发明和创造的新的生产工具被运用到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中,人类社会生产由此扩大,社会生活也得以丰富起来。[5]2014年8月,美国社会学界举办的“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首次提出了新计算社会学,主要依据在于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统治,人们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新方法获取和分析数据,为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范式。[6]在莫斯(Marcel Mauss)的“技术社会学”中,技术是社会的表征,技术最终将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危机中拯救出来。[7]这些论证已经超出了技术工具论的价值范畴。
就人类学而言,法国人类学家古尔汗(Audit Leroi?鄄Gourhan)发现工具和技术构成了作为生物的人与人类社会的关键中介。从东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不仅发生了大脑皮层的差异化发展,而且也发生了石器的差异化发展。但是从尼安德特人开始,大脑皮层系统几乎不再进化,相反,技术却以极快的速度进化着。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这种现象称为“人之所以为人”,其本质乃是一个生命技术外置化的过程,即人由此变成了技术而不仅仅是文化的产物。[8]波兹曼(Neil Postman)在《技术垄断》中将人类文明重新划分为三个阶段:工具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和技术垄断文明。他认为真正的技术统治文明的到来出现于18世纪,工业技术革命结束了早期的手工制造业。到了19世纪,技术垄断时代的出现又重新定义了人们的宗教、艺术、家庭、政治等。技术垄断时代即专制的技术统治文明已经到来。[9]
我们对关于人是工具制作的动物还是理性、精神的动物的思考,形成了哲学上工具论和理性论两大传统。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将人的本质重新定义为人并非天生的工具动物或理性动物,人的本质乃是非即成和被给予的,即它是专属于人的技术活动。人通过技术在建构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生活。[10]斯蒂格勒继续推进了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人是一种缺陷性存在,动物在出生时已经具备生存技能,而人从起源处就有无任何技能的缺陷,因此人的生存需要以技术来补救,即技术使人存在于世界之中成为可能。[11]换言之,人的存在需要依赖于技术。孙周兴把“人类世”看作是地质学和哲学双重概念,技术统治是其核心,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状态。[12]我们处于被“技术制造”的现代产品包围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技术而存在。这是今天技术哲学面临的新课题,同时现代技术也在渗透与变革着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
二、现代技术对教育的全面渗透与变革
新技术一方面推动着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新认识,另一方面,新技术也直接推动着作为人类事务中最为重要的教育实践的变革。借鉴媒介技术所构筑的社会传播图景来研究人类教育史,西方历史上经历了口传时代、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媒介技术变革。[13]借助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历史研究中的“时段论”,其长时段突出了历史事件的时间和结构特征,长时段所引发的稳定或变化缓慢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14]因此,在“时段论”理论框架下,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口传时代、手抄时代、印刷技术、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技术可以划分到长时段范畴。[15]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媒介技术环境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此,可以把从口耳相传到手工抄写、字母活字印刷机和互联网技术等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三次较为重大的教育技术革命。[16]现代技术对教育实践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和渗透,无论是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过程,还是教育手段和教育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技术转向。
在教育目的上,信息技术素养已经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和新的构成要素。现代社会生活以数字化方式呈现,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通过数据构建起来,其中包括声音、图像、图形、通信等皆由计算机语言0和1组成,这就需要从小培养年幼儿童对数字信息的关注、获取、加工、传递和处理等基本信息能力。此外,现代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构建一种虚拟社区或虚拟情境进行教育实践,教育目的中除了现实社会规范外,还需要注重虚拟社区中倫理规范和社会法则的培育。信息技术时代更新和拓宽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边界,在教育内容上,信息意识、数字思维和信息社会责任等成为教育内容中新的构成部分,信息科技成为一门专门课程。如2022年4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其中制定了《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学习的起始阶段提前至小学一年级,并提出要注重幼小衔接,注重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活动化、游戏化和生活化的学习设计,强调以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处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为课程逻辑主线。虚拟游戏、电子书包、在线作业、智能代理、交互式白板、触控桌等正在成为新的教育形式。在数字社会时代中,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诸多现代技术因素将使未来的学校和学生面临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17]
从教育过程和教育手段来看,现代技术对传统课堂教学活动提出了多重挑战。现代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教室的物理空间,每一个儿童都可以在虚拟的教室或网络空间成为教育过程的主导者。同时,虚拟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的集体教学,为儿童设计出适合于个体的个性化教育。在信息传递方式上,从单一的师生互动走向人、技术、世界之间的多元互动与虚拟环境体验,学习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学校教育并延伸至校外多层环境。在现代技术框架下,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始于课堂并扩展到其他情境的混合经验。[18]在教育手段上,由信息技术所引发的翻转课堂、微课堂、智慧课堂、智慧教育等,使得教学方式转变为由声音、图像、视频、虚拟体验、互联网操作等以儿童为主的信息化、智慧化教学。今天提出的智慧教育就是以机器智能与人类(教师)智慧相融合,同时指向学习者的高阶思维发展、创新能力培养、启迪学习者智慧的教育新生态。[19]人机对话正在成为新一轮教育技术改革的重点。从教育理念上看,从单纯的技术运用的工具性转向人文性探索。在教育关系上,在教书与育人的结构性分化上以学生为本。在学校形态上,富有韧性与弹性是未来学校对传统学校的升级迭代。[20]
从教育评价上来看,通过引入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数字化评价方式,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评价维度相比之前变得更加全面和容易获取。评价结果通过一种专门设计的评价系统自动生成,同时可以深入数据的背后形成评价结果原因的自动分析和输出。通过研究发现新近兴起的物联网技术可以为年幼儿童发展与学习评价方式提供强有力的潜在技术支撑,以期达到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的生态化。[21]再如美国早期教育正在普遍使用一种新的IT服务模式——软件运营系统和MCLASS:CIRCLE儿童发展综合监评系统,[22]以此来获取儿童早期发展的全面性指标数据。未来的教育评价将会更加依赖技术的全面监测和综合性指标。
现代技术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未来儿童教育的变革方向。除了前述谈及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的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外,从世界范围内看,全美幼教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NAEYC)与罗杰斯早期学习和儿童媒体中心(Rogers Center for Early Learning and Children’s Media)于2012年也发表声明,阐述了信息技术在0~8岁儿童早期教育中使用的优势:通过交互式课程可以促进儿童学习和自我表达;基于社交网络和信息媒介可以促进家园联系,提升家长的信息技术素养;网络专业发展项目可以提升教师的自我专业发展。[23]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要将信息化贯穿我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今天的孩子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已经处于现代技术控制之中,每一个儿童都可以十分便捷地接触到现代技术产品,如电子游戏、虚拟网络、智能技术等。从当前技术产品应用于年幼儿童及其教育生活来看,大多数家长对现代技术的应用持普遍的乐观态度。究其背后的原因,这与当前我们仍在一种教育手段意义上引入和运用技术密切相关。在教育实践中,现代技术在一种工具论意义上被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在家庭教育中,电子产品正在逐步成为父母陪伴孩子的替代物。当前引入教育领域的技术似乎还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现代技术尚未以其另一面成为控制人和教育的主宰。因此,我们并未深入思考和高度重视现代技术对儿童和学生日常生活的渗透与控制。然而,技术统治时代的哲学反思已经在提醒我们被技术全面反控制的可能和风险,特别是从“人类幼小的儿童能够无师自通、非常迅速且熟练地操作电子产品并陷于其所提供的虚拟世界之中”这一普遍现象(不仅中国的儿童是这样,其他国家的儿童也是这样)来看,这些哲学反思的提醒并不是杞人忧天。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年幼儿童和学生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技术控制,那么这样的儿童和学生来到幼儿园或学校,教育者所做的努力中就必然包含与控制他们的技术进行抗争和争夺儿童/学生的内容。换言之,当我们一方面热烈拥抱技术对儿童教育产生的积极的、好的影响之外,还需要及时反思技术对于儿童教育和儿童生活的反控制和消极的一面。年幼儿童作为“现代技术的土著人”,现代技术也同时触发了其与学校、教师之间对儿童/学生的竞争,即学校和教师是否因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而面临消亡的危险。[24]幼儿园或学校教育如何在一种更为复杂的技术统治之下保持存在的意义,这些都指向了技术哲学中对现代技术两重性的分析。
三、现代技术的两重性及其在儿童身上的表现
现代技术给儿童教育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在反制着儿童的教育生活。海德格尔在谈及现代技术的影响时说:“技术的发展在此期间将越来越快且势不可当。在此后的一切领域中,为技术设备和自动装置所迫,人的位置越来越狭窄。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的技术设备装置每时每地都在给人施加压力,种种强力束缚、困扰着人们——这些力量早就超过人的意志和决断能力,因为它们并非由人做成的。”[25]这说明现代技术对人的控制日益凸显,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沉思并不多。自古以来技术就被哲学遗忘在思维对象之外,哲学史上鲜有哲学家去认真对待或思考技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技术即无思”。[26]这就意味着技术本身无思,因为它本身的义肢性在场即是对原初的遗忘,①并且我们对无思的技术更加无思。[27]现代技术使人欢喜和担忧的两重性同时存在:既有对人的一种本质性奴役,同时人又只有通过对技术的沉思才能摆脱其奴役,进而实现技术解放之可能。因此,我们需要“洞察技术中的本质现身之物,而不是仅仅固执于技术性的东西。只消我们把技术表象为工具,我们便还系缚于那种控制技术的意志之中。我们便与技术之本质交臂而过了”。[28]
即便如此,海德格爾并不反对现代技术。他反对科学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也不赞成具有技术悲观主义倾向的人文主义,认为这两种姿态是在盲目地推动技术和无助地反抗技术以及把技术当作恶魔来加以诅咒。海德格尔试图走出二元对立,即走向一种中间道路的技术命运论。[29]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技术的本质乃是一种集—置,集—置也即真理的显现与无蔽。“在集—置中发生着无蔽状态,现代技术的工作依此无蔽状态而把现实事物揭示为持存物。因此之故,现代技术既不仅仅是一种人类行为,根本上也不只是这种人类行为范围内的一个单纯的手段。关于技术的单纯工具性的、单纯人类学的规定原则上就失效了;这种规定也不再能——如果它确实已经被认作不充分的规定——由一种仅仅在幕后控制的形而上学的或者宗教的说明来补充。”[30]我们要面向现代技术这个实事本身,②进而才能够完成对技术之物的本质追问,这种追问既不是把技术当成一种手段或工具,也并非把技术看成是人的毁灭物而加以抵抗。这集中表现为现代技术的两重性:技术一方面可以解放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过来束缚人和控制人。当我们去思考技术之本质,我们就把技术的本质经验为解蔽的方式。即当我们向技术之本质开启自身时,我们发现自己出乎意外地为一种开放性的要求占有了。[31]
从现代技术的两重性上看,一方面,技术进入儿童的生活,使得儿童在诸多方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学校教育的学习方式,儿童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发展出解决复杂问题以及交流的能力,[32]其中可以顾及每一个孩子的兴趣,同时依据儿童共同的兴趣而组建一个超越传统学校教育的学习交流平台,这种平台不受时间、空间等条件限制。如利用信息技术所开发的AR+图书有效地促进了儿童语言的习得与发展;[33]通过多媒体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的活动引入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儿童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儿童合理地使用计算机也有助于其自我意识的形成,交互媒介能有效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等。[34]现代信息技术也拓宽了儿童的智力空间,多种智能媒介的融合如人工智能技术、交互式电子白板和计算机编程工具等共同提升了儿童教育的上限。[35]从积极的方面而言,现代技术为解放和发展儿童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工具性支持。
另一方面,相对于年幼儿童而言,技术反过来又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束缚和控制方式。如智能技术作为一种强大的高级自动化特性,进一步拓展了对世界的“祛魅”范围,由于技术并不能穷尽任何一个具体的实在,因此儿童在真实情境中的丰富、独特、异质性的生命体验也恰恰反过来彰显了符号的空虚与干瘪,[36]技术对年幼儿童接触真实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生动性和活泼性而言又构成了一种新的束缚方式。同时,现代技术的过度依赖和使用也会对年幼儿童的身心造成伤害,全美幼教协会于1996年在《技术与年幼儿童》的声明立场中已有体现:以往的有些研究证明技术对儿童的学习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教育实践中,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设备代替不了高质量的传统儿童活动和材料,比如画笔、积木、水、图画书以及书写材料和戏剧表演。[37]现代技术在年幼儿童中的引入是限制性的或者是需要成人加以引导的。2016年,美国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其愿景在于所有幼儿在各个年龄段里都能在成人陪伴和指导下使用技术来促进学习,所有幼儿都有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使用技术方式)获得学习、探索、玩耍和交流的机会。[38]世界卫生组织于2019年颁布了《关于5岁以下儿童的身体活动、久坐行为和睡眠的新指南》,其中提及5岁以下幼儿必须减少坐下来观看屏幕的时间以及在婴儿车和坐骑上的时间,建议用更为积极的游戏取代长时间的受限或屏幕前的久坐不动。另外还详细地规定了每个年龄段儿童的屏幕时间,这些屏幕时间主要涉及看电视、视频或电脑游戏等现代技术产品。我国也于2021年1月以教育部办公厅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学生手机限制性带入校园,手机禁止带入课堂。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五个部门颁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其中要求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学校教育应本着按需原则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从现代技术的两重性在儿童身上的种种表现以及各个国家近年来连续出台的电子产品指南可以看出,由于受认知发展水平的限制,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儿童而言,年幼儿童更容易被现代电子产品或技术虚拟世界俘获和控制。这就导致在现代技术的两重性中,其控制和束缚人的一面在年幼儿童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现代技术与年幼儿童完全隔绝开来,完全禁止年幼儿童接触现代技术(如电子产品、人工智能产品等)。相反,这些恰恰表明年幼儿童在技术统治时代不仅需要更多国家和成人层面的保护,而且还需要尽早地培养年幼儿童对待技术的正确态度与基本认识。从积极的方面而言,只有将技术从工具主义的牢笼中挣脱出来,揭示技术本身所含的精神资源,技术教育才有可能彰显它的本体价值。[39]这就需要重建我们对待现代技术的思维方式,转向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中的“沉思之思”,克服现代技术对人的束缚和控制之消极意义。
四、重建对现代技术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从“人的控制”和“物的控制”的角度分析技术统治世界人的作用,明确指出我们之所以责备技术,恰恰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人的控制之首要作用,物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是人的不善自知或不健全导致了物的滥用。[40]这其实是一种技术中性论,即技术本身是一种人造物,应用的关键在人自身。另一种声音则是技术决定论,即技术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为社会成员确定了未来社会方向的全部可能性。[41]从西方技术哲学史的发展来看,以卡普(Ernst Kapp)和马克思(Karl Marx)等為代表的早期探索者,重点讨论了技术是如何将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有一种声音以海德格尔和埃吕尔(Jacques Ellul)等为代表,他们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反思,并呼吁人们关注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束缚方式。[42]消除对无思的技术之无思,我们需要面向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沉思之思”。海德格尔把思想分为两种,一种是计算性思维,一种是沉思之思。前者权衡利弊,投机取巧;后者则思考在一切存在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意义的那种思想。[43]这种“沉思之思”,乃是一种面向技术本质意义的现象学分析。“参与对意义的探讨,这是沉思的本质。沉思意味着比对某物的单纯意识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有意识,我们就还没有在沉思。沉思更丰富。沉思乃是对于值得追问的东西的泰然任之。”[44]面对现代技术对人的解放与新的束缚之两重性,这种“沉思之思”不是对现代技术权衡利弊,而是参与对其本质意义的讨论,并对追问的技术保持一种泰然任之的开放态度。
海德格尔早期并未把技术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他早期研究的是此在,是此在的生存论哲学。海德格尔并未把分析此在的生存论方法用于对用具的分析,早期只有此在的生存论而没有用具的生成论。[45]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方法对存在论作出分析的三个层次是在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出现:一是意识现象学还原,这个方法使海德格尔可以直接面对实事本身;二是现象学建构,即海德格尔对被分析对象的解释或生存论分析;三是现象学解构,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论或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46]从运用于技术分析来看,现象学还原即海德格尔面对的不再是此在,而是世界中的技术人造物。现象学建构展开为技术人造物的解释学即技术产生的生成论分析。现象学解构呈现为对传统工具性和人类学的技术本体论的批判性分析。[47]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形而上学或科技以工具性、对象性来对待物,只是单纯地关注物的明显可见的地方,把物视为一种有用性并占为己有,这些都是对物的干扰以及对物的消灭,必然会导致物的意义的全盘丧失,而不能让人体会到本然之物。[48]转向对技术物的沉思之思,其本质在于使我们超越对技术那种工具论的、计算主义和享用论的狭隘技术认识论,通过一种现象学哲学的还原、建构和解构,进而让技术物的本然状态显现出来。
基于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技术物首先需要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即不能用表象思维把技术物视为外在于人的世界之中的对象性存在,在海德格尔早期的实存论存在学考察中,他将“物”称为“器具”,器具对周围世界具有构成意义整体的作用。后期海德格尔则在“聚集”之意义上思考“物”。因此,传统哲学或科学对于物的认识都不能来把握物之物性,都是对物之本质认识的一种干扰。[49]在现象学的还原中,我们面对的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技术物,这就是面向存在者技术物之存在这一实事。其次,海德格尔在“沉思之思”中对技术物或人造物是如何产生的进行了生成论分析。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集—置,“集—置意味着那种摆置的聚集者,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置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50]现代技术的解蔽是一种对自然的促逼,这种促逼中显现出一种摆置的特征。因此物之物性乃是一种聚集。最后,在对技术物的还原和建构之基础上对传统工具性、对象性的技术本体论作出批判性考察。从对象性、工具性角度考察技术物,皆是对物之物性的遮蔽和干扰。从技术物自身来看,技术物乃是一种人造技术物,因此其本身显现着“天、地、人、神”四重整体世界。③由此再去考察技术物,我们就可以超越那种简单的乐观或悲观主义技术二元论。
如果保持对技术的无思,那年幼儿童会更容易受其控制和奴役。相对于自然文明而言,年幼儿童可以很快融入现代技术生活中去,按照斯蒂格勒的解释,人的本质恰恰是建立在技术之上的。“我们曾试图用后种系生成这个概念,来解释个体经验在遗忘过失中的积累。”[51]儿童从出生开始,其本性或技能是一种天生的缺陷,因此需要一种后种系生成,这种生成在其过程之中体现了人的技术本质,斯蒂格勒从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爱比米修斯(Epimetheus)的两次遗忘中重申人之为人的技术本质。“一切来自后自然状态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作技术,即作为操虑的超前意识,它存在于构成当即的现在、过去和将来的根本性分裂的偏离之中。这种向人为的时间性或时间的人为性的沉入,向脱离存在并使存在败坏的变化性的沉入,就是人的可完善性由潜在力量向现实行为偶然性的过渡。”[52]年幼儿童之所以不排斥或不反抗,除了其认知发展水平限制之外,还在于技术本身对于年幼儿童而言不是一种内在本质中的异物性存在,而是一种后种系生成,技术反过来使得儿童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状态成为可能。
就此方面而言,年幼儿童对现代技术物的需要是自然和合理的,儿童需要技术来弥补其本质性缺陷。当我们跳出传统技术工具论或技术享用论,这个时候技术物不再是海德格尔哲学早期中的“上手”“形塑”之器具,而是在其自身之内具有“天地人神”四重聚集之整体。技术于年幼儿童而言,并不会必然造成对其自然生活的破坏,反过来可以通过一种适当的引领与新的思维方式让儿童与技术物的本真世界遭遇,这种遭遇也是儿童逐步获得技术物的本质认识的必要方式。在儿童与现代技术遭遇的过程中,现代技术产品显现为一种解蔽的方式,体现为年幼儿童对真理之敞开的体验与感知。换言之,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沉思之思”,其目的就在于发展一种人对技术的新的思维方式与认识态度,让个体能够超越人与技术之间那种“物质”的、“功利”的、“享受”的关系,从而在对现代技术的生成历史和意义的沉思中,发现我们为何需要技术以及应该如何发展与运用技术,而不被技术所奴役,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人类与现代技术出自本然需要的本质关系。
“沉思之思”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思维方式,并不盲目地抵抗现代技术。对于儿童工作者或家长而言,重建这种对现代技术的“沉思之思”,超越我们对技术的盲目反抗或无思的乐观行为,可以在技术统治时代为年幼儿童的多方面发展提供智慧的支持与引导。今天的新技术已经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发明和创造出来,一方面我们需要警惕技术对年幼儿童生活的控制,另一方面,从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出发,我们对现代技术新的思维方式又可以帮助个体在强大的技术(特别是电子产品)面前形成具有自我抉择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从另一个维度而言,这实质上也为如何克服现代技术两重性中的消极属性与影响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路径。对于技术统治时代的年幼儿童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合适的途径和方法,尽早地培养他们对待现代技术(电子产品)的正确态度与基本认识,以及初步的“沉思之思”。
五、培植年幼儿童“沉思之思”意识萌芽的可能路径
经由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可以让技术物自身的本然状态显现出来,同时帮助个体克服对技术物的依赖,进而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技术物的世界。从培植年幼儿童“沉思之思”的心理意识萌芽来看,需要对海德格尔“沉思之思”的技术思维方式作出更具体的分析,而后根据其成熟样态尝试给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可能性教育建议。
具体来说,海德格尔“沉思之思”的成熟样态首先意味着对现代技术物应持一种泰然任之的态度,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之物的虚怀敞开是共属一体的。我们对技术物保持这样一种姿态,它们就会允诺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逗留于世界上。它们允诺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基础和根基,让我们能够不受技术世界的危害而赖以在技术世界范围内立身和持存。[53]其次,应保持对现代技术产品同时说“是”与“不”:“但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对技术对象同时说‘是’与‘不’,那么,我们与技术世界的关系不是分裂的、不可靠的吗?完全相反。我们对技术世界的关系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变得简单而安宁。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54]“是”与“不”的同时在场意味着我们既承认现代技术物自身的是其所是,又对这种承认保持一种沉思的态度。最后,“沉思之思”也意味着当我们对技术物敞开自身的同时,技术以一种解蔽的方式处于真理的显现之中。我们与现代技术打交道的同时,也从对它们的新的认识中获取了一种真理之敞开域——世界真理之涌现。
从教育建议上来看,对于认知尚未成熟的年幼儿童而言,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很可能无法实现。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基础性的、低层级的途径培植年幼儿童“沉思之思”的萌芽或心理意識,同时将这种培植活动延续至小学高年级、中学甚至大学阶段。如此既可防止年幼儿童被现代技术所俘虏,也可为他们将来成熟的“沉思之思”奠定根基。
首先,可以通过一种“返回的步伐”(返回的步伐意味着对技术物的“不要”以及相应减少观看屏幕时间),丰富儿童对自然物经验的机会。在海德格尔那里,物性体现着“天地神人”四重整体,引导年幼儿童实地触及自然物,他们在自然物中既可以体验和意识到技术物的初步生成历史,又可以形成对技术物本来面貌的基本心理认识。“技术物形成之前是什么样子?技术物产生的历史是什么?为什么今天需要这种技术物?”等等问题,可以展开自然物和技术物关系的多重分析与追问。此途径亦可引导儿童发现自然世界与技术世界的原初意义。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在《林间最后的小孩》中指出今天的儿童普遍地患有自然缺失症,这种缺失症是导致儿童多动症等产生的重要因素。[55]在自然缺失症的背后,是电视等媒体技术的发展替代了远古时期儿童生活的自然场景。通过重建儿童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儿童通过自身的意愿和视角探索自然,进而通过亲身体验发现自身和世界的意义。[56]
其次,引导年幼儿童经由动手劳作培植他们与世界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技术物中聚集着“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性,其实质在于通过对技术物的虚怀敞开而再次实现人类与世界之间的照料、关心等亲密关系。“农民从前耕作的田野则是另一个样子;那时候,‘耕作’还意味着关系和照料。农民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促逼耕地。”[57]动手劳作的目的不是让儿童变成一个农民,而是通过农民样态亲身的动手劳作,重新建立年幼儿童与大地之间的亲密关系,激发儿童内心天生对周围世界的照料与关心。
最后,允许儿童以“一百种语言”来开展与技术物之间的“对话”。“沉思之思”的实质也在于提倡一种哲学对话,通过教师与儿童、儿童与儿童以及儿童与自身的多重对话(包括儿童哲学活动、手工活动、绘画活动、游戏活动等),让技术物回归到它自身的存在样态中去,进而初步走向对技术物本质的艺术、哲学追问。成人需要鼓励儿童对技术的“追问”或自言自语,任何形式的“追问”或自言自语本身即是一种“沉思之思”的雏形和萌芽。儿童在心里好奇和追问了,成人借此可以展开与儿童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前提在于保持智性平等的观念,允许儿童打破成规或挑战权威。
在后續小学高年级、中学和大学教育阶段,如何使幼儿时期这种“沉思之思”的心理意识萌芽继续生长和成熟,是确保我们不被技术所奴役的必要教育行动。在小学高年级阶段,继续丰富儿童与自然物之间的操作与体验;专门开设手工制作、劳作、艺术类等课程,培植其内心与世界的亲密关系;展开更为系统的儿童哲学对话活动,丰富刺激物的选择。在中学阶段,可以开设一些基础类哲学课程,培育学生的哲学素养和逻辑推理能力;通过抽象的技术哲学话题讨论,引导学生形成对技术物的新思考;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通过艺术教育消解对现代技术的依赖与沉迷。在大学阶段,可以依照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的成熟样态,鼓励学生对现代技术保持一种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的态度,在面对技术物时可以同时说“是”与“不”,在对技术的经验之中实现对技术本质的把握和认识。
年幼一代已经站在了新的人类存在根基——技术文明之上,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当代成人的“老师”和未来成人的“父亲”。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后喻文化”在此亦可证明。由此而看,现代技术在儿童那里永远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而是一种内在于他们“本质”中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反思自然的东西和技术的东西在个体身上所占的比重到底多少是合适的,这也是我们对现代技术两重性所作出的哲学沉思与分析。在年幼儿童那里,他们确实比成人更容易受到技术物的吸引与俘获,这就会造成现代技术对年幼儿童生活世界的完全占领。海德格尔给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培育年幼儿童对技术物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态度,进而培植年幼儿童“沉思之思”的心理意识萌芽。总之,我们需要围绕儿童与技术的关系开展更多深入的讨论。
注释:
①“义肢”指的是一种人造的实体性器官。在技术哲学中,“义肢”指向的是工具,作为工具的义肢不是一种替代,而是一种生物肢体向外部存在的有机性延伸。“义肢”出自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第一卷中对于人的动作、工具、内在于动作中的超前技术操作过程的预见之论证。“义肢”也被翻译为“代具”。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我们不能把人的动作或工具的使用当作外在化的表现,因为在动作之中总是有一个超前的内在化的技术操作过程的相当程度的预见,因此“代具”并不取代任何东西,它并不代替某个先于它存在、而后又丧失的肌体器官,它的实质是加入,它构成了人类的“身体”,它不是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因此,这里的“义肢性在场”是一种技术作为“代具”的在场,我们通常会将这种“义肢性在场”理解为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进而把“义肢”理解为外在于人本身的东西或一种肌体器官的替代物,这样的一种思考即是对技术本身的一种原初性本质认识的遗忘,或存在论意义上的遗忘。(详见:张一兵.义肢性工具模板和符码记忆中的先行时间[J]. 社会科学辑刊,2017(06):60-65;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79)
②这里的“实事”借用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面向实事本身”。国内倪梁康曾对此做过深入分析,在胡塞尔或在现象学运动那里,所谓“面向实事本身”口号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摆脱以往传统与现存权威的束缚,试图像笛卡尔一样,在思想中再一次从头开始。套用海德格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实事概念的具体内容:在胡塞尔那里,实事本身是指意识及其对象性;在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中,它意味着在无蔽和遮蔽之中的存在者之存在。在此语境下,“实事”指的是处于工具论与作为新的存在根据的“现代技术”本身。之所以用“实事”,是为了强调我们对于技术的思考不能从外在的、“工具的”或“代具”的角度去考察,而应该直面“现代技术”这个实事本身,才能回到现代技术的本质或逻各斯中去。(详见:倪梁康.对现象学的误析[J].读书,2007(01):11-15)
③这里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源自海德格尔对物的追问以及对技术的沉思。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对《冬夜》这首诗的分析中阐明了其是如何召唤物、令物到来的:“它邀请物,使物之为物与人相关涉。落雪把人带入暮色苍茫的天空之下。晚祷钟声的鸣响把终有一死的人带到神面前。屋子和桌子把人与大地结合起来。这些被命名的物,也即被召唤的物,把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自身。这四方是一种原始统一的并存。物让四方之四重整体栖留于自身。”(详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从词源学上来考察,物的本质是“聚集”,物“聚集”什么或如何“聚集”呢?如果在历史性的表象思维或计算思维下,壶的本质就会被理解为被制造和被构成的质料,海德格尔认为这恰恰不是壶的本质。壶是一个物,那么作为物的壶如何聚集和聚集什么呢?如果说壶是被制造者的制造对象,这显然没有道出壶的本性。壶之本质乃在于它能够容纳什么,“能容纳”即是壶的物性,表象思维不能把握壶的这种物性。壶的本质是能容纳的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工匠制造了壶这个物,不如说是工匠制造了空洞。这一空洞或无是表象或计算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壶的空洞又以两种方式容纳,即承受和保持。承受和保持是为了倾泻,倾泻是一种馈赠,这种馈赠即是壶的容纳作用的本质。这种赠品是水和饮料,而这些又与天空大地相连,因此壶之壶性是赠品,总是栖居着天空与大地。与此同时,壶之赠品时也用于敬神献祭,即捐赠和牺牲,在一种饮料和一种奉神的祭品中,各自栖留着终有一死的人和永生的诸神,壶之为壶乃是“天地人神”四重聚集之整体。(详见:孙周兴.语言存在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61-265)
参考文献:
[1][12]孙周兴.未来艺术:几个基本概念[J].文化艺术研究,2021,14(12):1-7.
[2]CRUTZEN P J, STOERMER E F. The“Anthropocene”[J].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2000(41):17-18.
[3]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65-66.
[4][5]仓桥重史.技术社会学[M].王秋菊,陈凡,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8,71.
[6]罗玮,罗教讲.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5,30(3):222-241+246.
[7]夏保华.简论莫斯的技术社会学思想[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2):118-123.
[8]王程韡.“技术”哲学的人类学未来[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42(11):9-11.
[9]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M].蔡金栋,梁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9-44.
[10]敬狄.哲学人类学思考技术的第三条道路[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5):20-25.
[11]顧世春,文成伟.人—技术—世界: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源点[J].北方论丛,2013(03):115-118.
[13]郭文革.媒介技术:一种“长时段”的教育史研究框架[J].教育学术月刊,2018(09):3-15.
[14]孙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评价[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80-84.
[15]郭文革.教育变革的动因:媒介技术影响[J].教育研究,2018,39(4):32-39.
[16]郭文革.彼得·拉米斯与印刷技术时代的教育变革[J].教育学报,2022,18(3):184-195.
[17]孟繁华,蔡可.技术与教育精准融合,构建服务基础教育发展新模式[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S1):1-6.
[18][32]柯林斯,哈尔弗森.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M].陈家刚,程佳铭,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7,120-123.
[19]郭绍青.“互联网+教育”对教育理论发展的诉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7(4):25-37.
[20]王学男,杨颖东.技术力量与教育变革的作用机制及未来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21(11):1-7.
[21]郭力平,何婷,吕雪,等.物联网技术和儿童学习与发展[J].学前教育研究,2020(01):11-19.
[22]张晓梅.信息技术在美国儿童早期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与启示[J].早期教育(教育科研),2021(12):7-10.
[23]NAEYC. 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media as tools i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serving children from birth through age 8[EB/OL].(2019-10-02)[2022-10-10].https://www.naeyc.org/sites/default/files/globally-shared/downloads/PDFs/resources/topics/PS_technology_WEB.pdf.
[24]吕巾娇,刘美凤,康翠.技术对教育影响的系统性剖析框架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1,31(12):27-34.
[25][43][53][54]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M].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182,179,183,183.
[26][51][52]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5,226,144.
[27]张一兵.雅努斯神的双面: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构境基础——《技术与时间》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17(06):17-24.
[28][30][31][44][50][57]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6,22-23,28,69,22,15-16.
[29]孙周兴.海德格尔与技术命运论[J].世界哲学,2020(05):77-88.
[33]王璇,李磊.基于增强现实的儿童汉语学习图书设计与开发[J].中国编辑,2020(08):64-89.
[34]张炳林.信息技术在儿童教育中应用的逻辑审视与路径创新[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9):117-122+129.
[35]王戈.信息技术:拓宽儿童教育的必然选择[J].少年儿童研究,2019(09):4-8+14.
[36]石君齐.技术之于儿童教育:意涵与解构——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分析[J].开放教育研究,2021,27(6):44-52.
[37]朱书慧,汪基德.国外ICT应用于早期教育的项目实践及启示[J].学前教育研究,2014(06):21-29.
[38]张建欣,蒲远波.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对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启示[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9,35(9):34-38.
[39]陈向阳.技术教育的“立人”价值:技术哲学的审视[J].职教论坛,2014(04):8-13.
[40]吕文浩.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潘光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39-446.
[41]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42]米切姆.藏龙卧虎的预言,潜在的希望:技术哲学的过去与未来[J].王楠,译.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4,6(2):119-124.
[45][47]舒紅跃.技术与生活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2,82.
[46]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编者引论3.
[48][49]孙周兴.语言存在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66,258-260.
[55]洛夫.林间最后的小孩[M].自然之友,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79-82.
[56]赛利.儿童自然体验活动指南[M].肖凤秋,尚涵予,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7.
Cultivating Children’s “Contemplative Thinking”: the Possible Way to Beyond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SUN Rongxin,1 CHEN Lele2
(1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modern technology is shaping all areas of children’s education in an insidious way. Such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s an educational tool is mainly reflected in an optimistic and positive attitude. However,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is also achieving the restraint and total control over children. From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of Heidegger and others, it’s proposed that we need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that is, towards a contemplative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Kindergarten education can nurture the germ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wareness of contemplative thinking by enriching their experience with natural objects, supporting their hands?鄄on work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dialogue. The cultivation should continue at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lead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ntemplative thinking, which is the key to overcome the total control and enslave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on human beings.
Key words: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ontemplative thinking”
(责任编辑:刘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