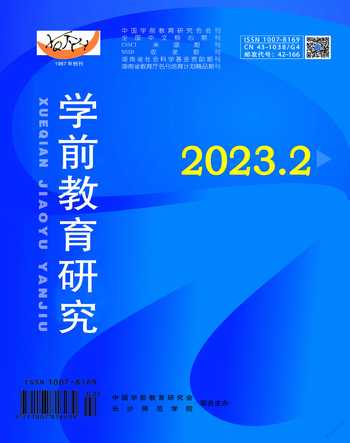儿童照顾中“新父职”的兴起、阻碍及其启示
王亮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扩张、父亲权利运动的崛起、教育溢价的提升、社会媒介的宣传共同推动了“新父职”理念的兴起。父亲被认为应该兼顾经济支持、身心照顾、情感融入等多元职责,这本质是对完美父亲的追求与想象,存在“霸权性”“阶级性”“对立性”等弊端。现实中,“新父职”理念也因其太过理想化而难以实践。尽管父亲参与育儿的时间与情感投入有所提升,但是呈现出“男性化照顾”与“选择性育儿”的特点,母亲仍然是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家庭友好政策的匮乏、性别文化的固化、经济生产的限制及社会再生产的不公使“新父职”实践成为一场“停滞的性别革命”。为增进儿童照顾中的父亲参与,政府应建立健全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应塑造包容平等的性别文化观念,用人单位应构建支持员工家庭角色的工作环境,家庭应破除“母职天赋”的迷思,支持父子形成“成长共同体”,通过相互陪伴和协助实现共同成长。
[关键词] “新父职”;父亲参与;儿童照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和北美国家开启了父职研究的新纪元,这改变了以往父职论题研究缺失的局面。此前,男性作为父亲的角色是鲜少被提及和重视的,此番父职研究的兴起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①所呼吁的家庭性别平等密切相关。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父职缺席的弊端,强调父亲参与(father involvement)对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要性,号召父亲主动为母亲分担家务与育儿责任。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们对父亲参与有了更为深刻且全面的认识,欧美国家普遍流行兼顾经济支持、身心照顾与情感融入的“新父职”(new fatherhood)理念,[1]并试图以此推动家庭性别革命的前进。在现行有关父亲参与的研究中,“新父职”已成为关键概念,被视为理解当代父职的有力工具。在国内儿童照顾的亲职讨论中,母职已成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并在近年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论是“教育拼妈”,[2]还是“母职的经纪人化”,[3]这些术语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中国母职照顾时间的密集化以及教育职责的密集化。[4]然而,对父职的讨论却显得稀少且零散。诚如学者王向贤所言,尽管成为人父是大部分男性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之一,是家庭生活、劳动力市场、人口生产、社会政策和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父職基本还未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独立范畴。[5]父亲与母亲共同构成家庭生活的基本角色,只有予以父亲同等的研究地位,方可全面理解我国在性别关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变化。
父职的缺席并非中国独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大多数国家也经历了从父职缺席到“新父职”的转向。尽管当前“新父职”在欧美国家还处于不均衡的发展阶段,但这些经验可为认识中国父职以及增进父亲参与儿童照顾提供思路与借鉴。父亲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积极的父亲参与对幼儿的情绪情感、身体动作、认知语言、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6]因此,有必要从学理层面理解父亲参与的现状与困境,为进一步探讨推进家庭友好政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对父职缺席的认识不应止于指责父亲的不作为,还应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结构性力量的形塑与限制,而社会学的洞察力有益于揭示父职缺席的社会性、结构性因素。有鉴于此,本研究聚焦社会学视野下讨论父亲参与的有关文献,分析“新父职”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现状及其面临的阻碍,以期为增进我国儿童照顾中的父亲参与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想。
一、“新父职”的兴起与争议
有历史学者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作场所与家庭生活的分离,父亲走进了城市、工厂,也走出了孩子们的视线,养家糊口成为绝大多数父亲的主要职责。[7]尤其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年轻父亲参军入伍,更是缺席了孩子的生活。这种缺席从美国、欧洲到第三世界,从大城市、小城市到乡村,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社会都很常见。[8]直至20世纪后半叶,父亲的缺席才开始受到学界与社会的重视。
(一)“新父职”兴起的社会背景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几乎同时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各个国家兴起,尤其在60年代末期,女性脱离了种族歧视,并随之开展了具有独创性的反对性别歧视运动,呼吁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为更多女性争取到了工作的权利,双薪家庭的数量开始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职场母亲(working mothers)人数的增加、女性职业地位和相对收入的提升动摇了传统的性别分工理念,[9]男性作为经济供给者(providers)和养家糊口者(breadwinners)的角色开始受到挑战,他们需要更充分地参与儿童照顾来适应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10]另外,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也带来了家庭友好政策的改变。父职假(paternity leave)首先在北欧国家实行,后来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逐渐增设父职假、育儿假(parental leave),实行育儿假配额制。以瑞典为例,作为最早于1974年实行父职假的国家,瑞典在2002年增设了为期16个月的育儿假,其中有2个月为父亲专享,不得转让,以鼓励两性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11]作为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男性运动——父亲权利运动(father’s rights movement),[12]离异的父亲要求在孩子的监护、抚养和探视方面获得公平待遇。在西方的文化脉络中,法官对男性的儿童照顾能力存在严重的刻板印象,常把孩子的监护权判给母亲,这迫使离异的男性不仅要承担高昂的抚养费用,同时也丧失了育儿的权利。[13]因此,参与父亲权利运动的男性声称家庭法和离婚法存在性别偏见,歧视男性,只对女性有利,他们开始以“好父亲”为使命,强调当前的法律基础设施阻碍他们成为“好父亲”。[14]这些团体组织的活动面向公众和社会宣传父亲的重要性,并推动了相关立法体系的完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社会不平等呈现加剧趋势。在英国和美国,教育溢价的上升拉大了收入差距,[15]很多父母越来越坚信孩子的成功取决于教育成就,父亲也开始花更多的心力投入孩子的教育。[16]尤其是中产家庭,拥有高学历的父亲期望孩子有所成就,倾向于调动他们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实现阶层继替。[17]
此外,为迎合女性主义运动所呼吁的性别平等与父亲权利运动的需求,社会媒介开始塑造“新父亲”形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书籍、文章、电影和漫画开始称颂那些花时间陪伴孩子、分担家务的男性属于“真男人”(real man);[18]另一方面,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父亲相比,80年代及以后的父亲在电视、电影、广告、杂志等媒介的报道中被塑造为更有情感、更具抚育能力以及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的形象。[19]甚至在一些国家,男明星也被塑造为照顾型父亲,用以吸引、鼓励男性参与儿童照顾。[20]
上述情境的变化促使父职话语在欧美国家出现了新转向,以往“养家糊口者”的父亲角色开始变得不受欢迎,“责任型父亲”(responsible father)、“新养育型父亲”(new nurturant father)、“融入式父亲”(involved father)、“亲密型父职”(intimate fatherhood)等“新父职”理念应运而生。尽管这些概念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扩展了“新父职”的意涵。例如,1996年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大卫·布兰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无父的美国》(Fatherless America)的出版触动了当时社会的神经,轰动一时。书中称,“今夜,大概有40%的美国孩子在家睡觉时,父亲没有同他们住在一起,‘无父’(fatherlessness)现象是当前美国社会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21]为缓解“无父”现象,美国学者詹姆斯·莱文(James Levine)在其作品《新期望:责任型父职的社区策略》(New Expectations: Community Strategies for Responsible Fatherhood)中提出“责任型父亲”理念,呼吁父亲:(1)做好情感与经济上的准备再考虑生孩子;(2)如果要了孩子,应给予孩子合法的名分(在法律上确定父亲身份);(3)从怀孕开始,主动为母亲分担孩子的身心照顾工作,主动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22]与“责任型父亲”类似,美国心理学家、父职研究权威学者迈克尔·兰姆(Michael Lamb)也提出了“新养育型父亲”的理念,强调父亲除了是经济供给者,还应该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身体照顾。[23]他还进一步明确了父亲参与的三个维度:互动性(engagement)、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和责任性(responsibility)。其中,“互动性”指花时间与孩子进行一对一的互动,如喂食、陪玩、辅助写作业等;“可接近性”指与孩子的间接互动,与前者相比,其特点是互动强度较低,如父母在厨房做饭,孩子在隔壁房间或在自己身边玩耍;至于“责任性”则不仅包括照顾,还涵盖了育儿实践中的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r),如知道孩子何时需要去医院并预约看诊时间,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衣服等。[24]随后,这类积极、广泛参与儿童照顾的父亲被大多数学者统称为“融入式父亲”。[25]作为上述概念的补充,英国社会学家埃丝特·德摩特(Esther Dermott)为“新父职”增加了情感维度。德摩特在关于南伦敦中产家庭白人父亲的育儿研究中发现,这些父亲将向孩子“表达情感”(performing emotion)视为实践“好父亲”的重要基础,不仅热衷于向孩子表达爱意,也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感。[26]为此,她提出“亲密型父职”,强调父亲在儿童照顾中的情感投入。
因此,与养家糊口的父亲相比,“新父职”提倡共同育儿(co?鄄parenting),鼓励父母在孩子的身心照顾与发展上付出与另一半同样的心力,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另外,这是一种全面型父职,父亲需要承担多元角色。理想的“新父职”既要提供经济支持,也要参与孩子的身心照顾,以及与孩子维持亲密的情感联系。但究其本质而言,“新父职”同以孩子为中心、听从专家指导、高情感投入、密集性参与且花费昂贵的“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类似,[27]都是对完美家长的追求与想象,它因太过理想化而难以实践。这也导致“新父职”开始遭受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新父职”的争议
“新父职”理念使父亲参与育儿的重要性获得社会大众的高度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父亲缺席的状况,其对育儿和家务的分担也将女性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并有助于男性习得一些女性特质进而模糊家庭分工中的性別界限,[28]以及为构建男性气质提供了情感基础,使那些在家庭领域展露情感的男性不会被视为过于女性化。[29]但也有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新父职”持批判态度,指出“新父职”存在“霸权性”“阶级性”与“对立性”。
首先,“新父职”并未正视男性的工作需求,甚至带有霸权意味,否定了其他可能的父职实践类型。艾米·舒弗尔顿(Amy Shuffelton)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新父职”将“密集母职”的育儿要求延伸到父亲身上,连职业女性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育儿,“新父职”却要求父亲不仅要实现养家糊口,还要承担令人满意且要求很高的育儿工作,以至于那些未能满足这些需求的男性备受指责。[30]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一些父亲也提到,高度参与、以孩子为中心的“新父职”形象,在某些方面使男性和孩子成为商业交易中的时尚商品,并剥夺了个别父亲选择符合其优势、劣势领域生活方式的权利。[31]亦即“新父职”为理想的父亲形象树立了唯一的标准,只有满足“新父职”的要求才能被称之为“好父亲”。但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亲来说,虽不能像“新父职”那样为孩子提供长时间的陪伴与情感的慰藉,但他们却在努力工作,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这也是他们理解“好父亲”的一种方式。
其次,带有浓重中产阶级意涵的“新父职”忽视了劳工父亲的现实处境。一方面,尽管所有的父母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但父母的育儿方式和偏好通常取决于父母在职业层级中所处的位置。劳工父亲很难达到“新父职”的高标准。[32]另一方面,中产父亲也只是借“新父职”之名享受育儿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对于无酬的家务劳动则避而远之,而母亲仍不仅需要工作,还得承担家务与育儿。[33]
最后,“新父职”术语进一步固化了对立的父亲形象。“新父职”中“新”(new)的标签,暗示了与现代和后现代/后工业时期相对应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父职模式。“新父职”被塑造为一种有爱的、融入的、非权威型的形象(loving, involved and non?鄄authoritarian),而“旧父职”则被视为情感疏远的、没有爱且权威的形象。[34]用“新”与“旧/传统”(old/traditional)来划分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标明这一转变所发生的时间点。[35]同时,“新”与“旧”的二分法过于简化,必然误导对“旧父职”的理解,使其成为“新父职”的对立面,即不仅权威、专制,而且对孩子也缺乏关爱。[36]
二、“新父职”实践:停滞的性别革命
从工业社会的养家糊口者,到当代社会“新父职”的转变,呈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对父亲角色的期待。尽管位于不同阶层的父亲普遍接受“新父职”的理念,[37]但美国学者拉尔夫·拉罗萨(Ralph Larossa)率先指出:“‘新父职’的理论构想先于行为。”[38]我们需谨慎对待观念与实践行动之间的差异,因为育儿实践往往是在特定情境下进行协商的,父亲实际做的并不总是与社会接受和期望的价值观念相一致。[39]当把“新父职”理念付诸实践进行检验时,许多量化研究结果都表明,父亲们的实践改变并未与认知同步。
与过去相比,父亲参与育儿的时间有所提升,但母亲仍是儿童的主要照顾者(primary caregivers)。一项对荷兰、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的父母每周花在育儿上的小时数都在逐年增加,但母亲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仍近乎父亲的2倍。[40]此外,自1993年以来,英国全职父亲的人数在十年间翻了一番,但如今只有不到23万名父亲在家照顾孩子,而全职母亲的数量则有205万。[41]育儿时间的差异还表现在育儿假的申请上。在英国,2011年至2012年只有0.6%的父亲申请了额外育儿假(additional paternity leave)与母亲共同照顾新生儿。[42]就连性别平等指数很高的瑞典,虽然绝大多数父亲都有权休假,政府也大力支持父亲更加积极地参与育儿,并为休假的父亲提供法律保护,保证他们休假以后能够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且提供80%的津贴补偿,但与母亲相比,父亲申请育儿假的比例仍相对较小。[43]例如,2000年,瑞典父亲休了所有育儿假天数的12%;到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5%,母亲所休的天数占所有育儿假天数的75%,仅有12.7%的瑞典父母平均共享了育儿假。[44]东亚国家亦如此。日本作为唯一一个为男性提供6个月以上带薪育儿假的国家,享有世界上最好的育儿假制度,但等级森严的企业文化、公领域以男性为主导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家庭主妇”成了影响父亲参与家庭育儿的三大阻碍,迫使日本父亲的育儿选择处于“挣扎”的困境中,雇主和保守的政客们仍然坚持“男性养家、女性照顾”的家庭分工。[45]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9年的报告显示,2017年只有5%的日本父亲使用了育儿假。[46]
在照顾内容方面,父职实践具有“男性化”与“选择性”的特征。挪威社会学家贝里特·布兰德斯(Berit Brandth)和埃琳·克万德(Elin Kvande)将挪威父亲的育儿实践概念化为“男性化照顾”(masculine care)。亦即父亲们倾向于选择那些看似男性化的育儿活动,如成为孩子的朋友、教导孩子学会独立自主,而那些具有女性特质的,如家务劳动,则不被认为是自己的事。[47]类似发现也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得到印证。纳吉斯·埃斯坎达里(Narges Eskandari)等学者基于伊朗的研究发现,虽然伊朗的父亲认为做家务是职责所在,但大多数父亲表示并不会过多地参与育儿。在他们看来,料理家务(housekeeping)和育儿工作是妻子的职责,而父亲的参与是干预妻子的职责。[48]其他学者还发现,这种“男性化照顾”现象也延伸至孩子的休闲活动中。例如,一些父亲会通过做家长会的负责人、组织社区活动等来继续扮演领导者、管理者等传统男性角色,而母亲往往成为“团队妈妈”(team moms),负责活动中的杂活。[49]除了明显的“男性化照顾”特征,父职实践还具有“选择性”的特点。专注于家庭研究的卡罗琳·盖特雷尔(Caroline Gatrell)对英国年轻父母的访谈发现,父亲们通常选择参与直接照顾孩子的活儿(如喂饭、洗澡)或有趣的活动(如陪玩),而那些间接性的育儿工作(如洗衣服、打包午餐盒),则被他们认为是乏味的且很少参与。[50]其他研究也表明,与母亲从事密集的、多重性的照顾工作相比(如给孩子穿衣服、接送孩子),父亲更愿意参与那些不规律、时间灵活的娱乐性活动或户外活动(如玩游戏、哄孩子睡觉、引导孩子挑战发展极限等)。[51][52]
在情感投入方面,中產父亲逐渐意识到情感之于亲子关系的重要性,开始实践亲密型父职。如果说传统的父爱是缄默的、严厉的,如今的欧洲父亲则将父爱视为一种行动,通过爱的实践来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53]来自对韩国中产阶层“野雁家庭”(wild geese families)②的研究也发现,除了定期为在国外的孩子和母亲汇款外,父亲还履行了负责任的情感角色,他们不仅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最先进的通讯平台与孩子通话或视频分享日常生活,还会抽时间飞到国外陪伴孩子,以实现“身体在场”的情感互动与身体照顾,从而弥补因长期跨国分居而留下的情感空白。[54]在与孩子分居之前,他们远没有以家庭为中心,其父职实践也不会超越性别界限。分居之后,许多父亲能够认识到以往被忽视的家庭价值,他们会亲力亲为地照顾孩子,甚至做一些他们以前回避的、视为母亲领域的照顾工作,如在探访期间积极参加孩子学校所组织的活动,为孩子做饭以及直接通过言语或行动向孩子表达爱意。[55]
当代父亲的育儿时间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父亲养家糊口的需求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男性养家、女性照顾”仍是主流的家庭分工模式,绝大多数的育儿假申请还是以母亲为主。在照顾内容与情感投入方面,尽管部分中产家庭的父亲可为子女提供一种关爱型照顾或亲密型互动,参与内容也比较多元,但“男性化照顾”与“选择性育儿”仍是父职实践的明显特质。尤其对劳工家庭的父亲而言,出于养家糊口的需要与文化程度偏低,他们很少向子女提供具身的照顾与亲密的互动。因此,在一些社会学者看来,“新父职”实践仍然是一场“停滞的性别革命”(stalled gender revolution)[56]或“不均衡的性别革命”(uneven gender revolution),[57]相对于女性走出家庭、步入职场的速度,男性选择投入家庭、承担育儿责任的速度更慢。
三、“新父职”实践的结构性阻碍
“不均衡的性别革命”意味着实现“新父职”还面临多重阻碍。从社会建构视角来看,虽然父亲参与是个人选择,但这类选择受制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要素的形塑。在此,本研究从家庭友好政策、性别文化、经济生产、社会再生产四个方面分析了“新父职”实践面临的主要阻碍。
(一)家庭友好政策的匮乏
家庭友好政策(family?鄄friendly policies)指那些有助于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并让他们从中受益的政策,如育儿假、父职假、育儿津贴、优质婴幼儿照护服务等,[58]这些政策通常为儿童照顾提供所需的时间、资金和服务三种基本资源。[59]从一些北欧国家的经验看,较为完善的家庭友好政策能够激发父亲参与儿童照顾的意愿。遗憾的是,全世界只有92个国家的男性享有法定的父职假,而且大多数父亲在孩子出生后照常上班仍是常态。[6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约三分之二的1岁以下儿童(近9 000万)生活在父亲没有带薪父职假的国家中。[61]甚至在连婴幼儿数量接近400万的美国,也尚未在全国层面制定任何法定的母职假或带薪父职假。[62]这也就意味着,带薪父职假的匮乏严重缩减了父亲与孩子相处的必要时间。
(二)性别文化的固化
依照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为充分发挥家庭的功能,男性通常扮演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以承担养家的责任,女性则扮演情感性角色(expressive role),是家庭的照顾者。[63]正是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养家、女性照顾”的性别分工长久以来被人们“化用”,进而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性别秩序、特定的性别配置和固定的性别结构。其导致的结果是,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的教育致力于让她们成为好母亲,因而难以卸下“母职守门”(maternal gatekeeping)的重担。[64]出于对母职身份的认同和育儿高标准的考虑,女性把自己视为儿童照顾的“守门人”(gatekeepers),不信任父亲的育儿能力,约束、限制、排斥父亲的参与。[65]这种母职“守门”的迷思不仅削弱了父亲参与的意愿,也降低了父亲参与的水平,进而合理化了父亲对育儿工作所保持的疏远感。[66]
另一方面,从男性气质视角看,父亲参与也是建构男性气质的过程,并在其中形成“男人”的身份认同。长久以来,支配型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最具社会权威,是父权制社会广为接受的。[67]其所强调的阳刚、理性、粗犷等特质通常被视为与情感化、精细化的儿童照顾相悖,以致大多数男性认为育儿不是“爷们的事儿”,是“女人的活儿”。刻板的性别印象通过不断的“自我预言”而弱化了男性参与儿童照顾的意愿与责任,强化了母亲“主要照顾者”的中心地位,这也是造成“男性化照顾”与“选择性育儿”的主要缘由。何况在这个母亲角色至高无上甚至神圣化的世界里,对父亲缺乏关注和支持,加上长期对父亲育儿无能的刻板印象,我们的社会总是希望他们能回到工作场域中去。[68]
(三)经济生产的限制
父亲养家角色的固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市场将传统的性别分工逻辑嵌入到工作结构与企业制度之中,从而将男性长时间禁锢在工作领域。出于经济考虑,男性必须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心力与时间,这不仅减少了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也增加了母亲轮换“第二班”(second shift)③的比重。[69]国际劳工组织201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调查涉及的100多个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就业男性(35.5%)每周工时超过48小时。[70]而这种“超时工作”(overwork)现象通常被视为默认的职业规范。[71]因此,对于大多数父亲来说,养家糊口的家庭角色和好员工的职业角色要求他们把时间投入工作。实现“新父职”需要他们花时间与孩子共度时光,并保证共处的质量,这种既要承担经济功能又要扮演融入式父亲的双重要求很难实现。[72]
经济理性主义认为,经济是决策的主要驱动力。既有研究发现,在考虑谁休育儿假时,夫妻会理性地决定工资较低的伴侣休更长的育儿假来照顾新生儿,以防减少家庭的经济损失。[73]事实上,正是因为工作领域刻板的性别印象而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与薪资不平等,那些被认为具备男性属性的行业(如建筑、金融、IT等)比女性属性的行业(如教育、服务业等)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导致育儿假的申请者总以母亲为主。同时,考虑到母亲与孩子天然的联系,即便是在母亲收入高于父亲的家庭,母亲的休假时间仍然长于父亲。[74]
(四)社会再生产的不公
与男性在公领域所从事的有酬经济生产相比,女性在私领域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通常在法律层面和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们被视为一种“以爱之名的劳动”(a labor of love),是不用支付报酬的无偿劳动。[75]这种关于劳动的分割,正是女性愿意走出家庭成为生产者,而男性却不愿回归家庭成为再生产者的症结。有时这种劳动还饱受歧视。对于那些全职母亲,虽然女性全身心投入琐碎的家务劳动和细腻的照顾劳动中,却被认为是“不用工作,靠丈夫养着”的“妈虫”。由于社会贬低了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的价值,从事这一类工作也被认为低人一等。当男性成为育儿的“主要照顾者”时,他们也体验到了来自社会的歧视与偏见,因而对育儿望而却步。良(Liong)对香港父亲的研究发现,当男性从工作领域回归家庭成为一名全职父亲时,他们感受到了“地位的下跌”。在工作领域,他们可以通过工作成就来获得声望与地位,但成为全职父亲后,他们为家庭所付出的心力并未得到认可,而是被视为“失败者”,从此丧失了尊严和价值,这使得很多父亲重返工作岗位。[76]
四、余论:对中国父亲参与儿童照顾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扩张、父亲权利运动的兴起、教育溢价的提升以及社会媒介的宣传推动了责任型父亲、融入式父亲、亲密型父亲等“新父職”理念的产生。同“密集母职”一样,“新父职”也强调密集性参与、高情感投入之于亲职实践的重要性,这本身是对“完美家长”的追求,为“新父职”的难以践行埋下根源。因此,“新父职”看似要打破“男性养家、女性照顾”的家庭范式,实则是一种残酷的性别平等主义。[77]一方面,“新父职”被塑造为传统父职的对立面,否定了传统父亲的价值及其情感基础;另一方面,带有浓重中产阶级意涵的“新父职”并未充分考虑劳工家庭的需求,以致那些未能满足“新父职”要求的父亲被排除在“好父亲”之外。
从“新父职”实践来看,虽然父亲们参与儿童照顾的时间有了大幅提升,中产家庭的父亲们开始把情感表达视为“好父亲”的基础,尝试用多种方式向子女表达爱意,但母亲仍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育儿假的申请也以母亲为主,父职实践倾向于“男性化照顾”与“选择性育儿”。需提及的是,尽管“男性化照顾”与“选择性育儿”再现了儿童照顾中的性别气质,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承认男性参与育儿的特质与优势,而不局限于对“男性化”的指责,这才有助于拓展对“新父职”的理解。因此,我们应充分考虑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同特质,实现符合彼此需要的分工与合作,并重塑对家庭友好政策、性别文化、经济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认识,从而推动“新父职”实践取得理想的成效。
“新父职”理念在中国社会并不陌生。儒家的为父之道强调“父慈子孝”,《韩诗外传》对“慈仁父爱”与“何谓父道”的界定也已近似“新父职”的标准,但由于汉代之后的孝道极力强调父亲对子女的绝对权威,使“慈仁父道”这一本土版的关爱型父职在此后的两千年间几乎未再现于儒家典籍。[78]费孝通先生最早从学理上提出共同育儿的理念,肯定育儿中双系抚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男女分工的体系中,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抚育的作用不能由一女一男单独负担,有了个母亲还得有个父亲”。[79]但双系抚育的理念与“新父职”也有所区别,费孝通先生更为强调社会性父职与抚育性母职,而非两者的混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少子化与亲子关系主轴化使孩子在家庭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心”与“唯一的希望”,[80]父母成为孩子的老师、玩伴或朋友,与西方“新父职”相似的“友好型”“慈爱型”父职理念也开始盛行,社会鼓励父亲更亲密地融入孩子的生活。[81]例如,基于对南京的研究发现,除了花时间照顾和陪伴孩子,中国城市家庭的父亲也呈现出温暖与体贴的特质,他们会通过口头表达、身体亲密等方式展现对孩子的关爱。[82]另有研究也指出,父亲倾向于选择倾听与讲道理的方式和孩子沟通,而不是一味地采取体罚的方式教育孩子。[83]
就亲职实践现状来看,虽然在一些城市家庭中也出现少量父亲深度参与育儿的迹象,[84]但密集的母职研究从侧面反映了父亲的缺席,父亲在儿童照顾中仍然保持着管教者和玩伴的核心角色。[85]2019年《中国年轻育儿家庭用户洞察报告》显示,约75%的母亲每天的育儿时间超过8小时,而过半数父亲(53.8%)的陪伴时长主要集中在每天1~4小时。[86]若如此发展,在当前我国“全面三孩”背景下,仅靠国家层面的号召难以提升生育意愿。儿童照顾不只是女性的责任,有必要重视男性的参与。基于“新父职”的有关实践经验,本研究从国家、文化、企业与家庭层面对增进我国儿童照顾中的父亲参与提出如下建议。
在国家层面,政府应加快父职假、育儿假以及在育儿假中设置父亲配额的立法建设,建立健全家庭友好政策。儿童照顾不应只被视为家庭的责任,国家应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持。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尚没有全国性的法定父职假(陪产假)与法定育儿假。虽然各个省份都在推进陪产假的制度建设,但除为数不多的几个省份规定父亲可休20~30天外,多数省份规定只能休7~15天,母亲则可休98天的母职假(产假)。由此可见,生育在制度层面被视为母亲的专责。从“陪产假”的名字也可看出,男性参与儿童照顾的责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父亲的职责只是“陪产”。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父职假以表示国家对父亲参与儿童照顾的重视,为实践父职提供政策保障。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8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补充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设立父母育儿假”,一些省份(如贵州、安徽、四川等)也相继出台政策规定父母每年各享有10天的假期。但从现实看,父母育儿假有可能只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员工有利,民营企业恐怕难以落实。因此,也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父母共享的育儿假,并在育儿假中设置父亲配额,完善配套措施,推动更多的父亲参与育儿。但需要注意的是,育儿假并不是越长越好。有研究显示,休假时间越长,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障碍就越多,母职工资惩罚的效应也会越强。[87]这也就意味着,建立健全亲职假政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多方参与,假期长度的设定和津贴补助的来源需要专门的论证以及多主体的支持。尤其针对假期长度的设定,一定要持性别平等的原则,避免因亲职假政策的实施而扩大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在文化层面,全社会要塑造平等的性别文化观念,鼓励刚柔并济的男性气质,消除父亲参与的心理之忧。父权制社会对男性的评价往往以经济充裕、事业成功为衡量指标,这不仅给男性制造了压力,也忽视了父亲在家庭中所需扮演的情感性角色。主张多元的男性评价标准、鼓励刚柔并济的男性气质不仅有助于打破性别气质之间僵化的区分,也能够为男性参与儿童照顾提供心理支撑,增强其育儿自信心。因此,有必要转变刻板的性别印象,接受多元的男性气质形象,鼓励父亲在亲子关系中的情感表达以及承认男性除经济供给之外的其他价值。另外,社会应该减少对从事全职育儿工作父母的歧视,给予全职父亲更多的包容、理解、尊重与认可。
在企业层面,用人单位要重塑“理想员工”形象,将员工的家庭需求纳入经济生产,构建支持员工家庭角色的工作环境。以往的“理想员工”理念过于强调男性的员工角色,要求男性全身心投入工作,并鼓励超时工作,从而巧妙地把男性的家庭責任隐藏起来。这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男性养家、女性照顾”的分工模式,导致男性未能有充裕的时间参与家务与育儿。因此,用人单位应适当考虑员工的家庭角色需求,重新定义“理想员工”标准,将其家庭角色纳入组织安排中。比如,引入弹性工作制,尽量减少为家有婴幼儿的员工安排超时工作或工作时间不确定的工作,杜绝盲目崇尚加班文化。对于有条件的用人单位,还应为员工履行父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适当延长带薪父职假期,落实父母共享育儿假。
在家庭层面,男性应深刻意识到亲子关系的重要性,明确为人父的责任,女性则应主动分享育儿经验,支持和鼓励丈夫的参与,破除“母职天赋”的迷思。育儿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女性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照顾技能,这是她们在持续的育儿工作中习得的。两性是否具有抚育能力,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在于想不想。在一些少数族群的文化中,幼儿的抚育责任就主要由男性承担。[88]在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看来,育儿这一项工作在本质上是去性别的,所有的父母都具备与孩子互动、建立亲密关系以及关心、照顾孩子的能力。[89]父亲的参与离不开母亲的“培力”,母亲应该向父亲敞开育儿之门,主动向丈夫分享育儿经验,传授育儿技能,辅助他们参与婴幼儿的生理性照顾工作,激发男性“成为父亲”的积极体验,强化父亲参与的意愿。与此同时,父亲也应主动发掘自身的儿童照顾价值,寻找育儿的成就感。
最后,“新父职”的未来发展应朝着“成长共同体”④的方向迈进。基于血缘的生物性关系,传统的父子关系被赋予某种伦理关系,其中关涉父亲的权威与文化的传承。现代社会已演进为风险社会或个体化社会,当面临风险与不确定性时,个体是无力的,因而父亲与孩子之间更应该构成一个“成长共同体”。个体在与外部建立联系时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先天的纽带可以让父子间天然地形成共同体,并通过相互陪伴和协助实现共同成长。“成长共同体”是一个个体进行终身社会化的场域,从最初的父亲教孩子学习,到相互学习,最后到父亲向孩子学习,理想的父子关系应该完整地把这个过程走完。在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中,父亲为孩子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持,与孩子建立绝对的信任,共同应对外部的挑战,其最終目的是让双方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注释:
①“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Second?鄄wave feminism)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最终波及整个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区,其主要内容包括争取性别平等、生育权、堕胎、避孕、离婚、女性的工作权利等。
②“野雁家庭”(Wild geese families)指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韩国中产阶级父母,通常是母亲带着孩子到英语系国家留学,而父亲则留在韩国继续工作,为她们提供经济来源。
③“第二班”(Second shift)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用以描述当今美国社会职场母亲现状的经典概念,意指职场母亲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下班后还得从事第二轮工作——家务与育儿。
④此处“成长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受益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伯清教授的启发,在此特别感谢。
参考文献:
[1]MCGILL B S. Navigating new norms of involved fatherhood: employment, fathering attitudes, and father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14,35(8):1089-1106.
[2][4]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南京社会科学,2015(02):61-67.
[3]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02):79-90.
[5][78]王向贤.为父之道:父职的社会构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1,27.
[6]马爽,高然,王义卿,等.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现状及其与幼儿发展的关系[J].学前教育研究,2019(05):51-61.
[7][8]ZOJA L.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M]. London: Routledge,2003:175-176,229.
[9]HOCHSCHILD A.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of fatherhood: the “daddy hierarchy” and beyond[Z]. Netherlands: WORC, Work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Centre,1994:3.
[10][13][69]JOHANSSON T, ANDREASSON J. Fatherhood in transition: masculinity,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M]. London: Springer Nature,2017:39,56,79.
[11]DUVANDER A Z, LAPPEG?魡RD T, ANDERSSON G.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fathers’ and mothers’ use of parental leave and continued childbearing in Norway and Sweden[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2010,20(1):45-57.
[12][14]CROWLEY J E. Fathers’ rights groups, domestic violence and political countermobilization[J]. Social Forces,2009,88(2):723-755.
[15][40]DOEPKE M, ZILIBOTTI F.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68-71,55.
[16][39]XU Q. Fatherhood, adolesce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families[M]. London: Springer Nature,2016:132,47.
[17][76]LIONG M. Chinese fatherhood, gender and family: father mission[M]. London: Springer Nature,2017:117,94.
[18][56]HOCHSCHILD A, MACHUNG A.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M]. New York City: Penguin,2003:32,12.
[19]WALL G, ARNOLD S. How involved is involved fathering?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fatherhood[J]. Gender & Society,2007,21(4):508-527.
[20]HOBSON B. Making men into fathers: men, masculinities and the social politics of fatherhood[M].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07.
[21]BLANKENHORN D. Fatherless America: confronting our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1996:1.
[22]EVINE J A, PITT E W. New expectations: community strategies for responsible fatherhood[M]. New York: Families and Work Institute,1995:5-6.
[23][24]LAMB M E.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 an overview[J]. Marriage & Family Review,2000,29(2-3):23-42.
[25][41][42][60][68]MACHIN A. The life of da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father[M]. London: Simon & Schuster UK,2018:34,86,86,185,181.
[26][34]35][36]DERMOTT E. Intimate fatherhood: a sociological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2008:130,44,45,45.
[27]HAYS 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97.
[28][29][32]COLTRANE S. Family man: fatherhood, housework, and gender equit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34,76,125.
[30][33][77] SHUFFELTON A. “New father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dependency[J].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2014,48(2):216-230.
[31]HENWOOD K, PROCTER J. The ‘good father’: reading men’s accounts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first?鄄time fatherhood[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3,42(3):337-355.
[37]ISHIZUKA P. Social class, gender, and contemporary parenting stand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J]. Social Forces,2019,98(1):31-58.
[38]LAROSSA R. Fatherhood and social change[J]. Family Relations,1988,37(4):451-457.
[43]HAAS L, ALLARD K, HWANG P.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n men’s use of parental leave in Sweden[J]. Community, Work & Family,2002,5(3):319-342.
[44]HAAS L, DUVANDER A Z, HWANG C P. Sweden country note[C]//KOSLOWSKI A, BLUM S, MOSS P.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eave policies and research 2016. Vienna: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Leave Policies and Research,2016:345.
[45]TAN T T. Literature review on shifting fatherhood[J]. A Journal of Identity and Culture,2016(06):53-78.
[46]NIPPON. Japan has the best paternity leave system, but who’s using it?[EB/OL](2019-10-28)[2021-11-27]. https://www.nippon.com/cn/japan-data/h00500/.
[47]BRANDTH B, KVANDE E. Masculinity and child ca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thering[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1998,46(2):293-313.
[48]ESKANDARI N, SIMBAR M, ABOU ALI VADADHIR A R B. Exploring the lived experience, meaning and imperatives of fatherhood: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J]. Global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2016,8(9):139-148.
[49]MESSNER M. It’s all for the kids: gender, families, and youth sport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249.
[50]GATRELL C. Whose child is it anyway? The negotiation of paternal entitlements within marriage[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2007,55(2):352-372.
[51]JOHANSSON T, KLINTH R. Caring fathers: the ideolog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masculine positions[J]. Men and Masculinities,2015,11(1):42-62.
[52]OFFER S, SCHNEIDER B. Revisiting the gender gap in time?鄄use patterns: multitasking and well?鄄being among mothers and fathers in dual?鄄earner famil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1,76(6):809-833.
[53]MACHT A. Fatherhood and lov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e emotions[M]. London: Springer Nature,2019:148.
[54][55]LEE S H. ‘I am still close to my child’: middle?鄄class Korean wild geese fathers’ responsible and intimate fatherhood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19,47(9):1-18.
[57]ENGLAND P.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J]. Gender & Society 2010,24(2):149-166.
[58][59][61] UNICEF. Family-friendly policies a policy brief redesigning the workplace of the future:a policy brief[EB/OL].(2019-07)[2021-11-27].https://www.unicef. 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7/UNICEF?鄄policy?鄄brief?鄄family?鄄friendly?鄄policies-2019.
[62]聯合国儿童基金会.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父亲无法享有带薪陪产假[EB/OL].(2018-06-14) [2022-04-11]. https://www.unicef.org.
[63]PARSONS T, BALES R F, OLDS M, et al.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M]. New York: Free Press,1955:151.
[64][65]ALLEN S M, HAWKINS A J. Maternal gatekeeping: mothers’ 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99,61(1):199-212.
[66]FAGAN J, BARNETT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gatekeeping, paternal competence, mothers’ attitudes about the father role, and father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3,24(8):1020-1043.
[67]CONNELL R W, MESSERSCHMIDT J W.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J]. Gender & Society,2005,19(6):829-859.
[70]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依然很大[EB/OL].(2016-03-08)[2020-11-20].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information/pressreleases/WCMS458129/lang--zh/index.htm.
[71]CHA Y. Overwork and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segregation in occupations[J]. Gender & Society,2013,27(2):158-184.
[72]KAUFMAN G, UHLENBERG P. The influence of parenthood on the work effort of married men and women[J]. Social Forces,2000,78(3):931-947.
[73][74]KAUFMAN G. Barriers to equality: why British fathers do not use parental leave[J]. Community, Work & Family,2018,21(3):310-325.
[75]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邹韵,薛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30-31.
[79]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7-68.
[80]FONG V L.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鄄child policy[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81]张亮,徐安琪.父亲参与研究:态度, 贡献与效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24.
[82]LI X. How do Chinese fathers express love? Viewing paternal warmth through the eyes of Chinese fathers,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J].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ies,2020,22(3):500-511.
[83][85]ABBOTT D A, MING Z F, MEREDITH W H. An evolving redefinition of the fatherhood ro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the family,1992,22(1):45-54.
[84]范譞.城市家庭中的父親深度育儿参与——兼论男性个体化家庭责任意识[J].宁夏社会科学,2021(04):182-192.
[86]亲宝宝&艾瑞咨询.中国年轻育儿家庭用户洞察报告[EB/OL].(2019-10-18)[2022-04-11].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1910/3457.shtml.
[87]MORGAN K J, ZIPPEL K. Paid to care: the origins and effects of care leave policies in Western Europe[J].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2003,10(1):49-85.
[88]PARKE R D. Fatherhood[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7.
[89]BIBLARZ T J, STACEY J. How does the gender of parents’ matter?[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0,72(1):3-22.
On the “New Fatherhood” in Childcare
WANG Li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second?鄄wave feminist movement and the father’s rights movement, the increase of the education premium,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media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new fatherhood” since the 1980s. Father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their children with financial support, physical care,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It’s a kind of illusion of“perfect fathers” and determines the practice impossible. Some social obstacles, such as the lack of family?鄄friendly policies, the entrenchment of gender stereotypes, the limitation of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the injustic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make it worse. Although fathers spend more time in parenting, mothers as the “primary caregivers” in childcare have not changed, which means the“new fatherhood” is a “stagnant gender revolution”. To promote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care, family?鄄friendly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s are needed. Fathers should also make their efforts to build “growth community” to develop with their children together in the process of parenting.
Key words: “new fatherhood”, father involvement, childcare
(责任编辑: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