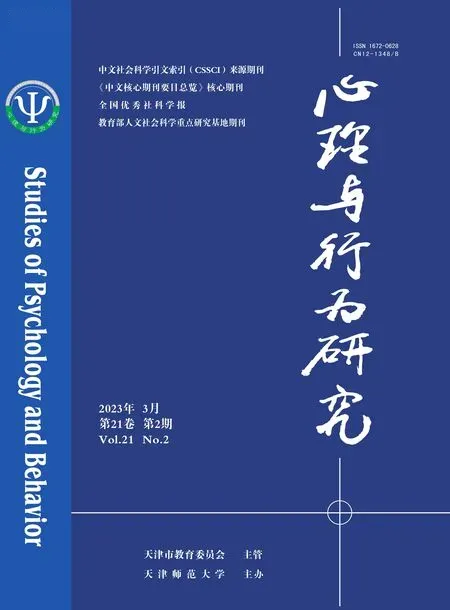群体认同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听障朋友支持的中介作用 *
马艺丹 薛威峰 刘 琴 徐 银
(1 乐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乐山 614000) (2 乐山师范学院人格与认知重点实验室,乐山 614000)(3 乐山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乐山 614000) (4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5)
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听力报告》中指出,听力损失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言语和认知发展,还会对其心理健康造成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WHO, 2021)。在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众多指标中,主观幸福感是重要指标之一(刘霞 等,2013)。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的认知和情感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Diener, 1984)。已有研究发现,社会适应行为、社会支持、感恩等是提升我国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因素(鲁玲, 2012; 田惠东 等,2022; 王玉, 2015)。然而,群体认同作为和个体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相关的重要变量(王勍, 俞国良,2016),其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却极少被探讨。听障人因听力损失和使用手语等特点形成了区别于健听人的听障群体,这一群体又因言语发展迟滞、与健听人沟通交流困难等问题易成为被污名和歧视的弱势群体(李美美, 杨柳, 2018;Ma et al., 2022)。那么,对听障群体的认同能否提升听障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该问题的探讨对促进听障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群体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个体对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与该群体成员身份相关的价值或情感意义(Tajfel, 1978)。社会认同模式(social identity approach)指出,当个体通过对特定群体的内化或认同来理解“我是谁”的时候,“我”便成为了“我们”,群体就有可能给个体生活注入安全、舒适、目标和意义,为个体提供面对和克服逆境的心理资源,因而群体认同能对个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Cruwys et al., 2014;Greenaway et al., 2015)。多项元分析结果支持了社会认同模式,显示了群体认同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组织背景下的群体认同与群体成员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Steffens et al., 2017);建立群体认同的干预手段能显著提升个体幸福感(Steffens et al.,2021)。基于社会认同模式视角并主要针对弱势群体的拒绝-认同模型(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进一步指出,对内群体的认同也能提升弱势群体成员的幸福感(Branscombe et al., 1999),并得到了部分研究的支持(Jetten et al., 2001)。但随着研究者对群体认同维度作用的深入探讨,群体认同的不同维度与不同群体成员幸福感关系的不一致性便逐渐凸显。在对群体认同维度的划分中,以认知成分(如中心性)、情感成分(如满意度)和行为成分(如团结性)的三维度划分最为常见(Scheepers &Ellermers, 2019),且最能涵盖Tajfel提出的群体认同结构(Feitosa et al., 2012)。其中,群体认同的中心性是指个体将内群体作为自我概念的中心成分;满意度是指个体对内群体以及群体成员身份产生的积极情感;团结性是指个体与内群体成员产生的心理联结以及对内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承诺(Leach et al., 2008)。Stronge等(2016)的研究发现毛利人的民族认同中心性与该群体成员的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Zitelny等(2022)的研究却发现性别的群体认同中心性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而满意度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也有研究发现心理疾病群体认同的中心性与心理疾病患者的幸福感显著负相关,而满意度和团结性则与幸福感无关(Cruwys & Gunaseelan, 2016)。由此可见基于群体认同不同维度来探讨群体认同与群体成员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必要性。但目前还鲜有探讨群体认同的中心性、满意度、团结性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厘清三者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相对关系,对于制定教育干预措施以提升听障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更进一步,社会支持是群体认同促进群体成员心理健康的重要路径(王勍, 俞国良, 2016)。社会认同模式认为,群体认同是群体对个体形成积极社会支持的基础:一方面,当个体通过群体认同将他人纳入自我意识后,就更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如向其他成员提供积极帮助);另一方面,当个体强烈认同某群体时,该群体成员身份便成为一种心理资源,使个体更相信自己能从群体成员中获取社会支持以及更愿意从中寻求支持(尤其在面对危及健康的挑战时),并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方式来解释因群体成员身份而收获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提升健康水平(Greenaway et al., 2015; Haslam et al., 2016; Haslam et al., 2005)。即使在弱势群体中,群体成员身份也是个体给予、接受和从社会支持中受益的基础(Branscombe et al., 1999)。根据上述观点,社会支持在群体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积极中介作用得到了不少研究的支持(包括针对弱势群体的研究),即群体认同能通过提高感知到的群体成员支持从而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Haslam et al., 2005)。然而,也有部分针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仅发现了群体认同与个体感知到的群体成员支持增加有关,但社会支持在群体认同与个体幸福感间无中介作用(McNamara et al., 2013)。以上不一致的结果可能反映了弱势群体中群体动力的复杂性(McNamara et al., 2013)。因此,听障青少年感知到的群体成员支持能否在群体认同和群体成员主观幸福感间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还有待考察。以往研究发现,同辈群体是个体在青少年阶段获取社会支持最主要的来源(林崇德, 李庆安, 2005; 马蓓蓓等, 2019),且朋友支持也被证实与青少年幸福感密切相关(Benner et al., 2017);同时,对于本研究中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生而言,听障朋友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交往最为密切的听障群体成员,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社会支持中的听障朋友支持与听障青少年群体认同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将考察群体认同三维度(中心性、满意度和团结性)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以及听障朋友支持的中介作用。基于以往研究中群体认同三维度与群体成员幸福感间关系的复杂性,本研究不做具体研究假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对四川省7所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366名10~12年级的听障生进行问卷调查,平均年龄为18.72±1.57岁。本研究的被试准入标准为:(1)无影响问卷理解和作答的残疾(如学习障碍);(2)懂手语或口语,能与问卷翻译人员交流。被试的基本构成为:男生165人(45.08%);全聋或极重度听力损失者(≥81 dB)167人(45.63%),重度听力损失者(61~80 dB)121人(33.06%),中度听力损失者(41~60 dB)45人(12.30%),轻度听力损失者(26~40 dB)33人(9.02%);72人(19.67%)使用了助听器,2人(0.55%)植入了人工耳蜗;2人(0.55%)报告有视力/肢体残疾。
2.2 研究工具
2.2.1 内群体认同问卷
采用Leach等(2008)编制的内群体认同问卷中的满意度、团结性和中心性三维度来测量听障青少年的群体认同度。满意度包含4个项目,如“作为听障群体的一员让我感觉很好”;团结性包含3个项目,如“我与听障群体团结一致”;根据前人研究(Nario-Redmond et al., 2013),中心性采用内群体认同问卷中的“ ‘我是听障群体的一员’对我来说很重要”和“ ‘我是听障群体的一员’是认识自我的重要部分”两个项目进行测量。该问卷9个项目均采用4点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分别计算满意度、团结性和中心性的总分,得分越高表明群体认同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的整体拟合指数为:χ2/df=1.47,p=0.063,RMSEA=0.04,90%CI=[0.00, 0.06],CFI=0.99,TLI=0.98,SRMR=0.03。
2.2.2 主观幸福感问卷
通过主观幸福感的三维结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Diener, 1984)来测量听障生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等(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4个项目,如“我的生活条件很好”,采用4点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的整体拟合指数为:χ2/df=4.50,p=0.011,RMSEA=0.09,90%CI=[0.04, 0.17],CFI=0.97,TLI=0.90,SRMR=0.03。积极情感参照前人研究(Goodman et al., 2018)采用1个题项(“最近两个星期,你快乐吗?”)进行测量,采用4点评分,从1“非常不快乐”到4“非常快乐”。消极情感采用包含3个消极情绪词的消极情绪量表(Goodman et al., 2018)进行测量,如“最近两个星期,你常感觉难过吗?”,采用4点评分,从1“从来没有感觉到”到4“总是感觉到”。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1。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量表和反向后的消极情感量表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2.2.3 听障朋友支持问卷
采用Zimet等(1988)编制的多维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含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在听障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王玉, 2015)。本研究仅采用其朋友支持维度,并将表述限定为听障朋友,共3个项目,如“我的听障朋友能真心帮助我”。问卷采用4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听障朋友支持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3 研究程序
基于听障高中生阅读理解能力滞后的特点(Bat-Chava, 1994),为提高问卷调查的有效性,本研究均在问卷现有译本的基础上,以不丢失原问卷信息为原则,根据预施测学生和特殊教育教师反馈,对所选用问卷的文字表达进行了修订,使题目表述符合听障高中生的阅读理解水平,且便于手语翻译(Bat-Chava, 1994)。其中两处项目数的改动为:(1)在Diener等(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中(共5题),由于“如果能再活一次,我基本上不会作任何改变”这一题项不符合听障中学生实际,且可能会对其造成伤害,因此在正式施测中将该题项删除,仅使用原问卷中的其余4题;(2)Zimet等(1988)编制的多维社会支持量表中朋友支持原本包含4个题项,其中“我能与朋友们讨论自己的难题”和“在发生困难时我可以依靠我的朋友们”两个题项的表达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和歧义,因此将其合并为“有困难的时候我能请我的听障朋友帮忙”,与原问卷的其余两题一起作为施测题项。为减轻听障生的认知负担,本研究将所有问卷统一为4点评分。采用8人小组施测,由两位经过统一培训的手语翻译为听障生讲解问卷调查的保密性和问卷题项,问卷当场回收。班主任老师根据问卷编号填写对应学生的人口学信息,包括听力损失情况、口语能力、书面表达能力、手语能力、是否使用听力设备和是否有其他残疾等。性别、年龄、父母听力状况等人口学信息由学生在填问卷时自行填写。
2.4 数据分析
采用Mplus7.4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主要步骤如下:(1)计算主观幸福感、听障朋友支持以及群体认同的满意度、团结性和中心性的Pearson相关;(2)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将性别、年龄、父母听力状况、听力损失情况、口语能力、书面表达能力、手语能力、是否使用助听器和是否有其他残疾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采用Bootstrap法来估计总效应、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设定公因子数为1,采用Mplus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如下:χ2/df=6.26,p<0.001,RMSEA=0.12,90%CI=[0.11, 0.13],CFI=0.67,TLI=0.63,SRMR=0.11,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主观幸福感、听障朋友支持以及群体认同的满意度、团结性和中心性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与群体认同的满意度(r=0.26,p<0.001)、团结性(r=0.11,p<0.05)、中心性 (r=0.11,p<0.05)显著正相关;主观幸福感与听障朋友支持显著正相关(r=0.26,p<0.001);听障朋友支持与群体认同的满意度(r=0.50,p<0.001)、团结性 (r=0.36,p<0.001)、中心性(r=0.34,p<0.001)显著正相关。
3.3 听障朋友支持在群体认同和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各变量的相关性以及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加入控制变量后对如图1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本研究数据的模型拟合良好,χ2/df=1.19,p=0.267,RMSEA=0.02,90%CI=[0.00,0.06],CFI=0.98,TLI=0.95,SRMR=0.03。在群体认同的三个维度中,仅满意度到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显著,表现为对听障群体的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直接效应为0.23,p<0.01,95%CI=[0.07, 0.38])。同时,群体满意度通过提升听障青少年感知到的听障朋友支持(β=0.45,p<0.001, 95%CI=[0.31, 0.58])进而提高群体成员主观幸福感 (β=0.19,p<0.01, 95%CI=[0.06, 0.30])的间接效应也显著(间接效应为0.09,p<0.01, 95%CI=[0.03,0.15]),见图1。群体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显著(总效应为0.32,p<0.001, 95%CI=[0.17,0.46]);听障朋友支持在群体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8.13%。

图1 听障朋友支持在群体认同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路径
4 讨论
4.1 群体认同各维度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社会认同模式指出群体认同能对个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Cruwys et al., 2014; Greenaway et al.,2015);本研究基于该理论,进一步探讨了群体认同中不同维度(满意度、团结性、中心性)与个体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Ma et al., 2022; Zitelny et al., 2022),群体认同中的满意度与弱势群体成员的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对内群体的积极情感(即满意度)有助于弱势群体成员摒弃歧视经历以缓冲其消极影响(Bombay et al., 2010),能促进弱势群体成员与他人的积极互动(Lee, 2005),有助于社会支持的获取(Branscombe et al., 1999; 本研究的中介作用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是弱势群体成员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仅群体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积极路径,而群体认同的中心性与团结性到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1)部分听障青少年会因自身不可逆的听力损失不得不将自己归类为“听障人”(中心性),也会因外群体歧视或不被优势群体接纳等因素与听障群体被动联系在一起(团结性),而只有群体满意度是弱势群体成员拥有积极社会身份、肯定群体积极价值最为明确而直接的反映(Leach et al., 2010),是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最可能的因素;(2)王小慧等(2008)在研究中指出,听障高中生的群体认同还属于幼稚型认同,因而他们可能还未深入思考听障群体对于“我是谁”的意义(中心性)以及自身对听障群体所肩负的责任(团结性),但对听障群体的情感(满意度)却是听障青少年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真实的感受,再加之本研究的对象是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的高中生,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听障群体中,体验着对群体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和情感,因而本研究结果提示群体满意度是群体认同三维度中与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关系最为密切的维度。
4.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与以往研究一致(Haslam et al., 2005),群体成员的社会支持在群体认同和个体心理健康间起中介作用;在本研究中表现为群体认同的满意度能通过提升对听障朋友支持的感知从而促进听障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群体满意度与听障朋友支持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本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朋友支持维度可以看出,听障青少年对听障群体的积极情感与个体对内群体友伴的信任感和求助行为的增加有关;根据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积极情感(如自豪、愉悦等)能为个体建构起重要的个人资源,其中就包括与他人积极关系的建立和社会支持的获取(Fredrickson et al., 2008)。另一方面,元分析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可能通过改变个体在交往中获得的满足感、自我价值感、归属感、安全感等方面来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宋佳萌, 范会勇,2013)。研究发现,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能促进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增强(王玉, 2015)。但目前还鲜有研究探讨社会支持中听障朋友支持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2008年,AI-Ballah的研究发现,对听障青少年而言,听障友伴关系至关重要,它在残疾和沟通模式等方面为个体提供了能有效交流和寻找共同经验的机会(Turkestani &Albash, 2022),能显著提升听障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Wolters et al., 2012)。因此,以友伴关系和友伴互动为基础的听障朋友支持,会因友伴的同质性、经验的相似性,使得支持更易产生信任、共情和互助,从而使支持更有效地发生(Heisler,2010);同时,本研究中的听障青少年均为特殊教育学校的高中生,听障朋友是在个体需要时能及时为其提供帮助、爱和关怀的重要来源,因而听障朋友支持与本研究样本中听障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积极相关。
4.3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结果为提升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教育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群体满意度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着重培养听障青少年对于听障群体的积极情感,譬如通过对优秀听障人事迹的学习促使听障青少年对听障群体产生自豪感;特殊教育学校可通过班级班风建设,让听障生感受到听障群体的爱和温暖等。同时,基于听障朋友支持与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学校和家庭教育应积极塑造听障青少年的亲社会品质,着重培养其沟通交流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提升听障青少年求助及助人的有效性。但由于本研究样本仅为四川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生,因此该结果是否适用于普校就读的听障青少年或是其他地区的听障青少年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5 结论
(1)群体认同的满意度、团结性、中心性与主观幸福感、听障朋友支持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2)听障朋友支持仅在群体满意度和听障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