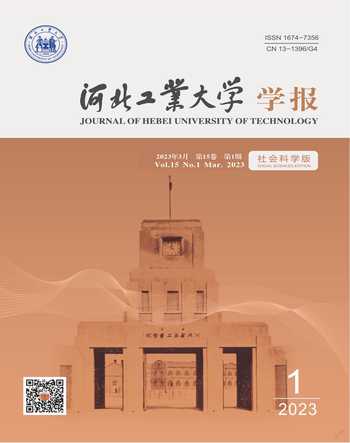辨析当前农民阶层分化的几个模糊认识
薛晴
摘 要: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当前农民阶层分化的几个模糊认识进行了辨析。认为:贫富分化在成因本质、运行机制等方面与农民阶层分化有着根本区别,以此说明农民阶层分化是偏执于一隅的错误推理演绎;不平等、不公平与农民阶层分化虽然在概念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交叉性,但因其所涵盖范围、侧重点差异较大,以此来说明农民阶层分化不但不会形成正确认识,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公众焦虑;以阶层固化来说明农民阶层分化的错误根源在于,既没有看到劳动方式对阶层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数据支撑,更没有看到持续增强的农民向上性阶层流动的制度性机会。
关键词:农民阶层分化;贫富分化;不平等;不公平;阶层固化
中图分类号:D422;D6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3)-01-0071-08
提到农民阶层分化,人们常常将之与“贫富分化” “不平等” “不公平”“阶层固化”等联系起来说明,且不说这种解读方式是否值得商榷,但由此而生的一些模糊认识及其可能的消极影响我们却不能坐视不理。农民阶层分化作为乡村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深入而日渐进入学术视野的。以“农民阶层分化”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可见,从1991年1月到2022年9月底共有326条结果,30多年来平均每年仅约11篇,且研究视角比较分散。如裴新伟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对农村社会整合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做出研究分析[1],严振书从宏观社会学角度归纳总结了社会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四方面特征[2],印子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对农村日常生活呈现的区隔化状态展开研究[3],许恒周从管理学角度对农民阶层分化产生的影响做出实证分析[4],杨华则从基层社会治理政治学角度关注了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影响[5],等等。多学科分散研究的现状,一方面说明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较强,能够以敏锐的视角去捕捉当前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发展变迁的焦点问题,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系统性研究尚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的较为分散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支撑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农民阶层分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亟待加强具有较强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支撑力的基础性理论研究,特别是亟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理性论证。“从主体认识活动的纵深发展来说”,农民阶层分化目前属于“在知客体”,即“正在被主体认识的客体”, “人类对在知客体的研究绝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事业”[6],因此其影响和作用也是普遍的。所以,辨析当前关于农民阶层分化的模糊认识,既是厘清农民阶层分化本质内涵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提高认识能力并早日掌握关于农民阶层分化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特殊规律的重要前提。
一、“贫富分化”为什么不能说明农民阶层分化?
(一)贫富分化在不同所有制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成因本质
贫富分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是人类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7]998。所以,贫富分化问题在不同所有制条件下,虽然有着相似的发展表象,但却有着不同的成因本质。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一种私有制形式,其本质特征是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和剥削,这就决定了其分配制度必然是以按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8]153。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9]428。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决定着劳动力的收益权。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是分离的,劳动者虽然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人身自由,但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资本雇佣劳动的结果只能是“劳动力所有权和收益权的分离”[10]。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无偿占有广大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全部社会财富,而广大劳动者仅能获得出售劳动力的补偿,不能参与其所创造的社会净财富的分配。“按资分配的收入远远大于出售劳动力的价值收入,因而会产生贫富分化”[11]。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资本有机构成呈不断提高的趋势,不具有生产资料控制权的劳动者,不仅无权参与社会净财富的分配,甚至还将得不到“他们允许”的劳动而走向贫困化。因此,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化,不可逆转。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常态化趋势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如今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全球新常态。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消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进而挖掉贫富分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既然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贫富分化的根源,那么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出现了有悖于共同富裕原则的贫富分化现象呢?唯物史观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收入分配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 “收入差距扩大的核心问题是贫富差距扩大”[12]。因此,对贫富分化成因本质的探讨,“离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离开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在经济中比重的增大去寻找根本原因,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13]。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顺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国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为补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演变历程。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最关键环节,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变迁必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资本收益增高、劳动报酬偏低尤为突出。虽然两者之间并不必然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也反映出我国初次收入分配领域尚存在亟须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这同时也是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根源所在。因此,目前我国所出现的一定程度上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不是改革开放的本质内容,而是由所有制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阶段性陣痛而已[14]。
(二)农民阶层分化是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
如前所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基础,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生产资料所有制必然对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意义。又因所有制结构是生产关系中的基础性经济制度,且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5]6,“人们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在一定制度范围内发生的,并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的影响是通过制度这一中介实现的。同时,人们按照经济制度的要求进行的行动,影响、改变着社会结构的表现形态”[16]。因此,所有制变革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之间是“一个有着逻辑关系的联动过程,所有制的变革必然促进阶层的分化,阶层的分化必然深化所有制的变革”[17]。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有制的变革集中体现为突破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形成了“以农户独立经营为基础,集体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股份制、个体、私营等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18]。结构调整的实质是调整利益关系,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利益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使社会阶层结构产生新变化。具体而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家庭承包经营成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的有效形式之一,农户根据家庭禀赋自主选择经营方式,进而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利益差别和利益落差驱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导致农民收入和经济地位分化,从而使农村社会突破了平均化的阶层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等特征。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不断改变着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农业产值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工业或非农业产值所替代,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主体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工、乡企管理者和工人等逐渐构成农村社会新的阶层。
如果说所有制变革是促进农民阶层分化的基础,那么市场经济运行则是农民阶层分化最重要的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依据土地占有状况和自我劳动占比,将农村居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不同身份。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农村土地所有制从农民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地主富农成为农民阶级的一员,严重的阶层对立已不再可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趋向简单化。作为对整个农民群体的政治定性,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共同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前“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通过政治嵌入方式实现的几乎无差别的社会阶层结构,再加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对农民社会流动的严格限制,彼时的农民基本上无法脱离农业生产去从事非农行业。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转型使得农村集体大一统时代的封闭结构转向开放,土地对劳动力的桎梏被打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经济发达地区,极大增强了社会流动性,释放出亿万农村劳动力潜在的经济效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频率得以提高,农村社会彻底摆脱了低效率的平均主义的负累,走向快速发展的分化中,异质性和差异化逐渐形成。而这种异质性和差异化主要受市场经济运行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中,支配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客观规律是价值规律。农民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自身所从事的职业及其所归属的行业以及所在区域和个人人力资本等诸多因素,都会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对劳动力价格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导致农民从市场中获得的经济收入和发展机会多寡不同,进而形成社会差别的客观存在,成为推动农民阶层分化的强大动能,农民阶层分化的静态状况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叠加,共同作用形塑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通过市场激发出来的农民效率的差别,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因而农民阶层分化也不会构成矛盾和冲突。
(三)把贫富分化错误演绎为农民阶层分化的关键在于前提错误
三段论推理是演绎推理中一种简单的推理判断,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结论是否正确,既取决于大前提,也取决于小前提,只有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正确,结论才能正确。“农民阶层分化就是贫富分化”,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推理,只不过隐藏了小前提,而且这个隐藏的小前提是有问题的。笔者梳理后发现,在这个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是“贫富分化的主要表现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小前提是“财富是阶层划分的依据”,于是得出结论“农民阶层分化就是贫富分化”。这个结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小前提是错误的,且其中隐藏着一个想当然的预设,那就是“农民阶层分化必然会形成贫富两极分化中贫者愈贫的一极”。显然,这个想当然的预设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或者一个被证实的客观规律,因此所得结论必然是错误的。诚然,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真正消失,相对贫困问题仍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而且相对贫困人口仍然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但是,这并不能必然证明小前提及其隐藏的想当然预设是正确的,因為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整体上是一场进步性的社会运动,期间得大于失的人远远多于失大于得的人”[19]。
小前提及其隐藏其中的想当然预设,实际上是对相对贫困问题过度紧张或焦虑的表现,尤其是这一问题还会因阶层分化的存在而长期存在[20],产生偏离农民阶层分化本义的错误解读也在所难免,无意为之可以理解,有意为之则贻害匪浅,必须正视。但是正视并不等于被动适应,更不等于抱怨和逃避,尊重客观事实、理清纠葛结点才是有所作为的重要前提。显而易见,关于“农民阶层分化就是贫富分化”的错误解读,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是农民阶层分化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不论是从本质属性角度解读其静态特征,还是从操作、方法或活动角度明了其动态特征,都离不开对“收入或财富差距”具体内容的解释。然而,仅偏于“收入或财富差距”一隅而不从农村社会结构转型角度分析农民阶层分化问题,难以真正建立起关于农民阶层分化这一概念的认知结构,尤其是社会转型面临新形势时如何保持这一认知结构的科学性。实际上,立足农村社会结构转型背景,辩证地、理性地看待收入或财富差距,勿将“贫富差距”演绎为人格化、人群化、阶层化的对立和矛盾[21],才是对农民阶层分化形成正确认识的焦点所在。
二、“不平等” “不公平”为什么不能说明农民阶层分化?
(一)辨析“分化”与“不平等”“不公平”概念,虽有相同点但不可替代
“分化”的基本释义是由同一性质变成不同性质的事物,或事物由整体变成分裂。通俗些讲,就是差别、差异的形成过程,关键词是“差别” “差异”。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差别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人类社会的差别或差异比自然界的差别或差异要复杂得多,原因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差别或差异除了受生理等自然属性的因素影響外,还会更多地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诸多具有社会属性的因素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对农民阶层分化做出通俗解读,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原先无差别同质性的农村社会成员或农民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诸多具有社会属性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有差别有差异的异质性社会成员或群体的过程,这种异质性还不意味着就是不平等。
“不平等”是一个极易引发争议的概念,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赋予其双重意义,即公平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平等。所谓公平的不平等是为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不平等,例如,纯务农者与农村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虽然是不均等的,但是这样的分配结果是遵循我国现行分配制度获得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相一致,所以这种客观数量上的不均等就能够为民众所认可并认为是公平的。相反,如果分配方式的正当性受到质疑,那么分配结果就不会为民众认可并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例如,腐败背离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必然为民众所不齿,由腐败获得的高收入当然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公平的不平等侧重于对客观差别或差异的描述,不公平的不平等并不是在完全客观意义上的使用,而是加上了主观评价。
“不公平”也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公平或不公平”概念时,包含着“合理或不合理” “公正或不公正” “平均或不平均”等多重含义,既有客观现象描述,也有主观价值评判。其中, “合理或不合理” “公正或不公正”表述的主要是主观价值评判, “平均或不平均”表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现象。农民阶层分化作为农村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存在于差别或差异的多元社会中,往往通过两种具体现象表现出来, “一种是纯粹客观的社会差异现象,另一种是对社会差异现象的主观评价”[22]4。所谓农民阶层分化研究也是围绕这两种现象的关系展开的,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合理不合理” “公正不公正”问题,而不是“平均不平均” “均等不均等”问题。
(二)“不平等” “不公平”背后是公众对农民阶层分化的焦虑和期盼
阶层分化是每个社会分层中的内部变化,这种变化有两个重要特征:功能专一化和地位多样化。其中功能专一化意味着人们社会职能的分化,一般来说由社会分工引起,表现为社会结构和功能的专门化和复杂化,没有高低等级或上下层次的区别,以水平分化的方式呈现;地位多样化则意味着人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差别或差异,一般由社会资源享有多寡不同而导致,以垂直分化的方式呈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社会不平等的特点。正是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具有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两种呈现方式,且垂直分化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不平等特点,很容易触碰到“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共振点,尤其对于尚未走出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的乡村社会而言,这一共振点极易遮蔽农民阶层分化的本真意蕴,从而出现关于“农民阶层分化就是不平等或不公平”的误读。
这种误读,一方面反映了公众的焦虑,当人们看到农民阶层分化这个词语时,本能地觉得这是一种以贫富论尊卑或等级的历史倒退。事实上,社会阶层分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途径,通过必要的社会阶层分化,包括分工意义上的水平分化和贫富程度意义上的垂直分化,能够激起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成员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推动性力量[23]15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在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矛盾、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事实说明,虽然农民阶层分化在一定意义上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阶层基础,但这是分层结构本身的差异造成的,试图通过消除分层结构、缩小地位差异来对待不平等问题,则会导致平均主义产生,改革开放前“大锅饭”所造成的平均贫困就是明证。显然,公众焦虑的并不是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本身的差异性问题,而是农民进入社会不同阶层的过程是否公平或公正。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误读背后的“焦虑期盼”,即公众对社会公平的热切期盼。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在追求效率中重建社会公平,在重建社会公平中提升效率”[24]。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在市场机制下开始了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经济分化,对此前形成的以身份划分为依据的世袭性阶层体系形成了冲击,但因制度性缺陷尤其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这一体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民的身份因素,尤其是户籍身份,限制了农民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权利。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是造成公众对农民阶层分化误读的原因之一。所以,对“不平等”或“不公平”的更好理解,不应该一般地反对农民阶层分化本身,而是应主张竞争型“地位准入”的平等观或公平观[22]10,所追求的应该是“机会公正、程序公正、结果公正三者的有机结合”[25],也可以说是公众对农民阶层分化的真正期盼。
(三)当前农民阶层分化所体现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资源在农民阶层中不平等分布的量化特征使农村社会产生了等级差异性,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农民阶层分化就是其主要表现之一。社会学认为, “社会不平等是指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对于相对稀缺的社会价值物在占有量、获取机会和满足需求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往往来源于人的特征差异”[26]295。而人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由人的特征差异表现出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从古至今也都是普遍存在的,且主要表现为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所以,在对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我们所认知的不平等应该是被应用于反映社会复杂结构的社会不平等,一般从特定的社会分层形式意义上理解和把握[27],更侧重的是一种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不平等,主要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冲突和失衡造成的,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体制改革或社会整合确保其在合理区间运行,以避免社会走向分裂和失序。
相对于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28]。“在农民收入不断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全面消除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之间收入不平等问题相对凸显”[29]。社会学意义上的收入不平等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结果不平等。通常,公众能够接受由努力带来的结果不平等,而很難接受因家庭背景、地域差异、性别等外在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且后者常常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当前,农村仍然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其内部收入不平等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反映。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表明经济成果并未成比例分配,这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势必影响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 “与不同农村地区的发展次序有关,先发展的地区有更多机会和潜力,资金、财富积累以及能力建设等差距会越来越大。”同时, “受各地政策、财政、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等因素叠加影响,最终体现为全方位的发展能力差距”[30]。所以,由农民阶层分化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不平等特点,更多地表现为结果不平等,而不是机会不平等。基于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理念,结果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机会平等是必须的。因此,对于农民阶层分化而言,其所体现出来的结果不平等特点,蕴含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农村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不能逃避也不能放弃,更不能步入歧途,与民粹主义“握手”,当平等、公平的价值祈望不能诉诸现实实践时,就将这一价值期望转变为对农村社会现存阶层秩序的猜忌、敌视和仇恨,进而衍生出民粹主义“毒瘤”,这是我们从事农民阶层分化研究必须警惕的陷阱。
三、“阶层固化”为什么不能说明农民阶层分化?
(一)阶层关系不取决于“出身”而取决于劳动方式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结构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而人的劳动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生产力,人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在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了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 “凡是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或方法,使社会结构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31]44。这说明,对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理解,不仅可以从生产力层面展开,也可以从生产关系层面展开。就生产关系层面而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承担着判别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中介职能。阶层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其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劳动方式为杠杆不失为一个积极的选择。劳动方式由生产技术条件和生产组织形式两个方面组成,农民阶层是否固化须从这两个方面考察。从生产技术条件方面考察,农业生产技术条件需要借助社会分工这一中介,才能对农民阶层分化起到推动作用。马克思指出: “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32]520。分工分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必然引起农业产业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择业就业的变化,而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职业又是划分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会通过社会分工这个中介对社会阶层结构产生重要影响[33]。也就是说,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就不会止步不前,日趋细化的社会分工也必然会引起传统职业变革和新兴职业兴起,职业类型的多元化又可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多层次性,那么由“大工业的本性”决定的“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34]560就不会消失,从而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就不会停下脚步,农民阶层也决不会从分化走向固化。当前,“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大的突破”[35],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已经并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将成为新时代重塑农村劳动力的引领力量,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从而推动农民阶层合理分化、良性分化。
从生产组织形式方面考察,不同于生产技术条件,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与农民阶层分化之间的联结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不需借助中介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家庭经营成为主导性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直接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部的最初分化。此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使农民的职业分化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等新的职业阶层,从农业劳动者这一母体阶层中分化出来。进入新世纪,农民专业合作社日渐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它从集中土地和组织农民两个方面进一步改变了农民就业结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农业工人、农村经纪人、农村信息员、全科农技员等新型职业农民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如今,随着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壮大, “合作社+”模式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发展已成为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必将深刻改变农村传统经济结构,进而深刻影响农村社会阶层关系。需要强调的是,随着农业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也会随之不断创新,二者紧密结合、共同作用,推动深化农民劳动方式变革,从而推动乡村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革乃至整个乡村社会结构变革。
(二)农村居民代际流动调查数据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观点
谈到农民阶层分化,就无法回避类似“寒门再难出贵子” “农二代”等公众热议话题,而这一话题往往被认为是阶层固化的体现。那么,如何界定并测量社会阶层是否固化呢?社会学认为,代际流动既是“辨别一个社会结构是否开放,即具体评判社会开放性程度的主要指标”[36],也是衡量一个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僵化、凝固、缺乏活力的主要依据[37]。所谓代际流动指的是时间维度上的一种社会流动,即“父代与子代之间,或是几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化”[26]312。就农民阶层分化而言,代际流动所要表达的主要是关于农民职业流动的动态分析。假设父母是农民的子女,通过努力最终成了企业家,从事了不同于父母的职业,那就表示其实现了代际流动,而且是实现了代际向上流动,即阶层跃迁。如果其没有获得除农民外的其他职业,而是和父母一样最终成了农民,那么其事实上则是继承了父母的职业,这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继承。只有在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社会纵向流动性明显弱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出现阶层固化现象。
那么,当今中国之乡村社会,农民的代际继承性果真在日渐增强吗?陆学艺及其课题组2004年调查数据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代际流动上升趋势明显,由改革开放前的32.4%提高至改革开放后的40.9%,而且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为调查对象,发现其父母为农民的占比高达46.2%[38]176,140。李强通过对比1990年代和21世纪有关子代与父辈的职业变化数据,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总体代际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且这种总体流动率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越是年轻的一代人”,其代际流动率上升趋势越明显,并呈“逐年攀升”态势。所以, “从全国的调查数据上并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说法”[39]。笔者同意上述陆学艺、李强等学者的分析,也同意陆学艺等学者关于农民和农民工基数大、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人群小、从概率上看前者子女进入管理阶层的概率低于后者子女的研究解释。问题是怎么理解调查数据与公众热议话题之间形成的差距或者矛盾?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调查数据代表的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事物,以数字符号形式呈现,具有信息载体功能。而公众热议话题多源于生活中的具体案例,比如“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个话题来自一位中学教师的帖子,具体案例是该校近两年中高考状元的家庭条件都不错,且当年中考上了重点线的学生中,有5人来自“开跑车、住别墅的家庭”。类似的案例可能在全国各地都有,当然也会有许多与此不同的案例,这些都可以为公众直接观察到。但是,直观感受的具体案例反映的并不是客观事物的全貌,那么据此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具有代表性,也经不起推敲。只有采用严格意义上的全国抽样调查法获取到的数据,才能得出最符合当代中国农民社会流动实际的结论。这也正是调查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三)农民向上性阶层流动的制度性机会在不断增加
不容否认,目前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阶层固化迹象,尤其是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虽然依然存在向上流动的特点,但其机会明显减少,中上层已出現固化态势[40]。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阶层的社会流动性已经或正在失去活力,也不意味着向上性阶层通道已经或正在变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制度对农民阶层社会流动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41],不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在不断畅通社会向上流动渠道和拓展社会向上流动思维方式。
从宏观上看,日趋健全的农地流转制度体系、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决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民生工程等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在促进农民市民化、农民职业化、农民现代化方面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选择。从微观上看,农民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之一,其市场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其向上阶层流动和地位实现。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市场能力强弱的主要表征,且这一表征指标的提升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为此,国家通过政策配置的手段使受教育机会向农村倾斜,从而降低了先赋性因素、同时增强了后致性因素对农民社会流动机会和社会地位实现的影响。如,时刻关注农村教育的“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国发〔2021〕25号),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 (农科教发〔2021〕13号),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 (人社部发〔2019〕5号),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印发的《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供给与政策安排,都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致力于解决农民受教育程度和生产综合技能水平总体偏低的问题,为改变农民在市场竞争体系中的劣势地位,为农民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获取更多、更有利的流动机会,从而实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 裴新伟. 新时代西部农村社会整合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背景的审思[J]. 农业经济,2022(1):70-72.
[2] 严振书.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J].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2):102-106.
[3] 印子.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2015(7):68-74.
[4] 许恒周.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偏好[J]. 中州学刊,2011(4):75-78.
[5] 杨华. 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新挑战[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6):40-45.
[6] 胡敏中. 认识客体存在和转化的四种形态[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62-64.
[7]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卫兴华,林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魏丽萍. 论贫富分化新常态的本质与根源——兼评“金岩石:劳动不能致富,财富的源头是货币”[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6):136-142.
[11] 卫兴华. 我国贫富分化的现实与成因评析[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29-133.
[12] 刘国光. 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贫富差距扩大[J]. 前线,2011(12):27-28.
[13] 衛兴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创新[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7):1-5,108.
[14] 程美东,靳建芳. 理性看待中国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4):75-81.
[15]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
[16] 董伟. 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基本关系的理论构建[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5.
[17] 齐卫平. 社会阶层分化是当代中国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J]. 探索与争鸣,2002(3):11-15.
[18] 肖万春. “入世”后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优化的迫切性和战略重点[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3):52-54.
[19] 裴新伟. 新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机遇与挑战[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2-79.
[20] 汪三贵,刘明月.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8-29+189.
[21] 《第一财经日报》评论员. 勿将“贫富差距”变成“阶层矛盾”[N]. 第一财经日报,2010-5-19(2).
[22] 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3] 惠中. 人类与社会[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4] 杨耕. 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N]. 光明日报,2016-12-7(13).
[25] 李强. 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2-9.
[26]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7] Н.Г.奥西波娃.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根源[J]. 李卓儒译.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4):112-123.
[28] 胡志军,谭中.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估计及城乡阶层效应——基于城镇、农村收入20分组数据的研究[J]. 南方经济,2016(6):38-50.
[29] 盛三化,李华. 家庭金融资产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一个倒U形关系[J]. 金融发展研究,2022(4):25-32.
[30] 两会大家谈:乡村振兴如何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N]. 南方都市报,2022-3-6(1).
[3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柯连君,司汉武. 技术进步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J]. 特区经济,2013(1):158-160.
[34]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5] 习近平.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J]. 求是(7):1-7.
[36] 李煜. 代际社会流动:分析框架与现实[J]. 浙江学刊,2019(1):32-37.
[37] 王春光. 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趋固化问题[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9):34-36.
[38]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9] 李强.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与趋势[J]. 河北学刊,2021(5):190-199.
[40] 王春光,赵玉峰,王玉琪. 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J]. 社会学研究,2018(1):63-88+243-244.
[41] 刘心红. 制度性机会与农民向上性社会流动[J]. 湖南社会科学,2007(5):72-74.
Analysis of Some Confusion over the Present Class Divide of
Chinese Farmers
Xue Qi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some confusion over the present class divide of Chinese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ivid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lass divide of farmers in terms of basic reason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thus demonstrating that the present class divide of farmers is a wrong notion. Secondly, although there is an overlap between the two conceptions, namely, the lack of equality and fairness and the class divide of farmers, the public worries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misunderstandings will be formed if the latter is explained by means of the former. This is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scope and focus within the the conception of inequality and unfairness. Accordingly, accounting for the class divide of farmers via social class rigidity not only ignores the decisive role of labor mode in class relations but also lacks the support of empirical data. Besides, this explanation neglects the increasing systematic opportunities with which farmers can work their way to the upper social ladder.
Key words: class divide of farmers; the divid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equality; unfairness; social class rigi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