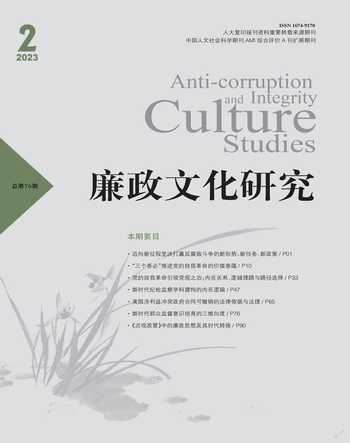《贞观政要》中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转换
徐瑾 邵哲夫
摘 要:《贞观政要》中的廉政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廉政建设的典型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官德修养为主体规范,以民本思想为价值导向,以监察监督等制度为践行保障。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廉政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要想充分发挥《贞观政要》中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时代转换,即在官德修养上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在价值导向上要从“民惟邦本”走向“人民至上”,在制度建设上要从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治”,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关键词:《贞观政要》;官德;民本;法治
中图分类号:D69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3)02-0090-07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廉政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最早的廉政思想大约起源于《周礼·天官冢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1]113。“六廉”体现了传统中国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在《贞观政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通过唐太宗及其属下大臣的从政实践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贞观之治”是传统社会少见的清明盛世,《贞观政要》中体现出的廉政思想时至如今仍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存在,我们对其也要进行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时代转换,这是充分发挥传统廉政思想积极作用的应有之义和必经之途。
一、廉政建设的主体规范:官德修养
“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2]454《贞观政要》中廉政思想的要旨大抵体现于这一句话中。对“明王圣主”的强调,意味着在传统中国社会,统治者的圣明是廉政建设的核心,这也意味着对整个统治阶级官德修养的强调。“节俭于身”是为官者加强自身修养以形成道德自律的核心,“恩加于人”是为官者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即施恩于万民。在传统官本位社会中,官员阶层是廉政建设的主体,主体规范的好坏直接影响世风民风,因此官德修养在历朝历代都被统治者所重视。
(一)官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及其合理性
《贞观政要》对官德的强调是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主旨,也是对西汉以来德主刑辅传统的继承。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特别明白统治者率先垂范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非常强调为官者的道德修养。
官德修养的目的是形成道德自律,這对于廉政建设尤其重要。因为廉政的对象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权力越大,受到的诱惑就越多,如果为官者不能做到道德自律,那么就必然走向贪污腐败。“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2]268对于修身律己来说,最可贵的在于有高尚的品德,这种高尚的品德能够起到榜样示范的巨大作用。唐太宗作为最高统治者,仍旧保持了清廉节俭的美德,这在传统社会殊为难得。太宗曾经一次性让后宫及掖庭内的三千宫女回家,其目的是为了节约皇宫开支,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太宗还说:“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2]101太宗深知用权的重要性,尤其对权重者更是如此,稍微不慎就可能产生恶劣影响,“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2]388。如太宗所说,如果自身品德不够,那么上位者的不良嗜好必定为下属所效仿,那么整个国家就可能陷入污秽混乱。在太宗身体力行的示范下,属下臣子多能做到基本的道德自律,由此才能形成政风廉洁的“贞观之治”。
官德修养还包括兼听则明,位高权重者尤其应当如此。太宗曾自谦地说:“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至天下太平。”[2]95正是因为上位者能够做到谦虚纳谏,属下臣子才敢犯颜直谏。贞观初年,殿中侍御史李乾祜直陈太宗之失:“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3]2853太宗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收回成命,免除了裴仁轨死罪。当时秘书少监虞世南、中书侍郎杜正伦、著作郎姚思廉、御史大夫韦挺等人经常进谏,甚至“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对他们敢行“逆鳞”之事大加赞赏:“为君不易,为臣极难。联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联岂虑宗社之倾败!”[2]102
为了促进官德养成,太宗还非常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贞观二年,太宗修建弘文馆,精选全国各地饱学之士担任学士,同时扩大国子学的办学和招生规模,并要求三品以上官员将自己的子孙入学接受教育。在经典整理上,太宗组织儒士对儒家流行的五部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进行了重新考证注释,编写了《五经正义》,从而将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进行了统一规范,也使得道德教化有了统一教材。
官德修养的核心是对廉政建设主体(官员阶层)的道德规范,具有深刻的内在合理性。传统社会历来有德治传统,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官德正则世风正、民风正。可见,《贞观政要》对官德的强调与正身为率、为政以德的传统是一致的。官德修养的过程就是摈弃私欲,从自私偏狭之心走向公正爱民之心的过程。自私好利是道德败坏的根源,《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一再强调,为官者不能追求一己私欲之满足而要清廉节俭,不能只考虑一己之得失而要敢于直言进谏。后世之所以称太宗为一代明君,属下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为一代名臣,根本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正己修身、行为表率;臣子敢于秉公执法、犯颜直谏,君主能够虚心纳谏、改过迁善。可以说,《贞观政要》对官德的强调深刻影响了后世,官德修养也成为后世廉政建设的核心内容。
(二)传统官德修养的历史局限性
就《貞观政要》官德修养的核心而言,约莫相当于“义”。“义”有适宜、合理、正当之意(意味着公平正义),还与“利”相对(意味着重义轻利、大公无私),由此《贞观政要》中的清廉、节俭、直谏等等官德就都包含其中了。“义”与“仁”“孝”“忠”等传统文化的主要德目紧密相连。“义”意味着为官者自身的道德自律,其基础是孔子首倡的“仁”,“仁”在中国传统血缘宗族社会中首先体现为“孝”,而后“移孝为忠”又表现为子民对君父的“忠”,譬如犯颜直谏既是为民之仁也是对君之忠。
由于传统社会是一个血缘宗族社会,所以忠、孝、仁、义等德目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历史烙印,从而使得其内涵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的实际需求。在血缘宗族制度下,对尊卑等级的强调使得传统官德的基础只能是官本位,由此缺乏对劳动人民大众的尊重。之所以唐太宗、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以及后世包拯、海瑞、于成龙、袁可立等被人认可,就在于他们真正爱民、为民;但是这种圣君贤相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究其根源,就在于官本位体系本身对尊卑等级的强调,使得劳动人民大众天然处于被统治地位,所以看起来对官德修养的强调是为“民”服务,但实际上仍旧是为“官”服务。如果不进行时代转换而僵化照搬忠、孝、仁、义等内容,那就很难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廉政建设的需要。
(三)传统官德修养的时代转换: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
在《贞观政要》中,官德修养是廉政建设的核心,而官德修养的内容由于与血缘宗族制度息息相关的原因,所以必然表现为忠、孝、仁、义等德目。忠孝仁义本身是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要想在当代中国发挥积极作用,还需要一个思想指引,即“为人民服务”。
表面上看,当代中国提倡的廉政思想和贞观时期颇有相似之处。如习总书记强调:“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做到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情。”[4]73这和太宗提倡的“节俭于身”很相似。习总书记还说:“选贤任能要‘近君子,远小人,坚持原则,严格标准,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引进人才要防止‘近亲繁殖,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5]256这和太宗主张的以德选才的观念也颇为相似。但是究其本质,两者的理论基础却完全不同。“忠孝仁义”所体现出的狭隘封建意识使得传统社会的廉政建设缺乏根本支撑和持续性,而“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却能为廉政建设提供永久动力。
在当代中国,以《贞观政要》为代表的传统忠、孝、仁、义等德目如果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就能发挥积极作用,而一旦背离了“为人民服务”,就只会沦为道德空谈。传统人治社会尽管非常强调道德修养的作用,但除了少数时期(如“贞观之治”)外,贪污腐败之风仍旧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其根本就在于官德修养缺乏一个“根”。这个“根”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也正如习近平所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6]。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固然要看待传统廉政思想的合理性之所在,但也要在客观看待其历史局限性的基础上进行时代转换。以官德修养而言,在“为人民服务”的指引下,忠、孝、仁、义及其具体表现出的清廉节俭、秉公直言、为民请命等品行才真正有了“根”,才能与时代相结合,才能在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廉政建设的价值导向:民本思想
《贞观政要》中的廉政建设有一个明确指向,就是“本固邦宁”,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民惟邦本”。民本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不过这一思想在发挥安邦定国等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即传统社会的“民”主要指“庶民”,“民本”的背后实际上是“君本”。只有在当代中国才真正实现了民本。
(一)民惟邦本的主要内容及其合理性
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典型表述。《贞观政要》秉承了这一思想,以民为本也成为廉政建设的价值导向。
民惟邦本首先在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唐太宗那里体现出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魏征曾以此来劝谏太宗,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初年京城附近发生蝗灾时,太宗手持蝗虫亲自向上天祈祷:“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2]522太宗随即将蝗虫吞了下去,希望将上天降下的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不危害百姓。正是皇帝的带头示范,所以才形成了重视民生、敢于为民请命的良好官风。唐朝建国之初,百姓生活仍旧比较贫苦,太宗在降低税赋的同时,也要求朝廷官员抑制私欲,不准铺张浪费。“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2]400在皇帝、大臣的带头实践下,太宗在位二十余年间衣无锦绣、风俗简朴,民无饥寒之弊。
政风清廉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由此实现国泰民安的和谐社会。注重农时是以民为本的重要体现:《贞观政要》记载,在皇太子举行加冠礼时,太宗认为与农事相冲突,于是将日期延后,太子本应二月加冠,“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2]522。太宗关注民生、注重农时、轻徭薄赋,且慎于征伐;对于边远纠纷常以和亲等方式和平解决,不轻易征用民力以做征伐之事。在太宗的带动下,治下官员多兢兢业业,勤政为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而且“米斗三四钱,行旅至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2]53,由此形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
在传统中国,造成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上位者的腐败。贪官污吏为了一己之私与民争食,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倘若君主昏庸无道,更会导致民不聊生甚至激发战乱。因此,爱民甚至畏民之心有利于上位者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如《左传·哀公元年》云:“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可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统治者应当信奉的真理。显然,一个能够清廉自持行为表率、秉承公心为民做主的执政者才能获得民众的爱戴和拥护,才能被百姓视为“父母官”“青天大老爷”。“贞观之治”正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太宗本人还是属下臣子多能做到爱民、护民,所以才能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清平盛世。
(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强调民惟邦本的确是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但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仍旧具有历史局限性,即“民本”并没有真正得以落实,因为传统社会中的“民”是“庶民”,“民本”实际上仍旧服务于“君本”。
民惟邦本中的“民”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而是“庶民”。《谷梁传·成公元年》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这也正如荀子所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众人者,工农商贾也”(《荀子·儒效》)。虽然统治者强调民惟邦本,但民(庶民)在社会上却毫无政治地位,是与“官”相对的被治者阶级。也正是如此,民(庶民)的生活好坏完全取决于“官”的清廉与否。之所以统治者强调民惟邦本,只是因为庶民是国家赋税(劳役、兵役)的重要来源;重视民生也有维护社会安定、防止民众暴动的理由在内。唐太宗也正是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才特别强调官员廉洁奉公、为民请命的重要性。
民惟邦本表面上是民本,实际上仍旧是君本,维护的是君主集权制。虽然传统社会强调了“民”的重要性,但在涉及“君民”关系的时候仍旧强调“君”的重要性。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十指》“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這里的“本”即“君”,“末”即臣民。朱熹在赞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同时,也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朱子语录》卷一〇八)。就《贞观政要》而言,尽管唐太宗本人特别重视民本,但贞观之治如果离开了唐太宗本人的清正廉明,恐怕根本不会实现。这从事实上也说明了,传统社会的“民本”只具有手段性价值,因为“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地位,“民本”背后的实质是“君本”。
(三)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转换:从“民惟邦本”走向“人民至上”
《贞观政要》体现出的民本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也要进行时代转换,即从“民惟邦本”到“人民至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民主”的本质。
产生于封建时代的“民惟邦本”不可能超越历史。马克思曾说:“私有制和阶级国家的产生让腐败现象产生,维护自身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为腐败提供了温床。”[7]154因此传统民本思想只是表象,内在仍旧是君本。所以尽管唐太宗在反腐倡廉上取得较好成效(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太宗自身的道德自律),但终归无法保证整个统治阶级的持续清廉(事实正是如此)。要想充分发挥“民惟邦本”的时代作用,就必须向当代中国秉持的“人民至上”转换。如习总书记所说:“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8]只有那些真正重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思想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在当代中国继续发挥作用。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9]55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人,在社会上拥有最高地位,传统社会的“庶民”则是毫无社会地位的被统治者。“人民”掌握自身的命运,而不是把命运寄托在少数统治者身上(即便这少数统治者是具有优良品德的圣君贤相),而“庶民”只能将命运寄托在“父母官”身上(父母官这一称呼本身就是官本位的体现)。正是因为庶民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明君清官,所以传统廉政建设始终缺乏扎实的群众基础。当社会上有唐太宗、魏征、包拯等人时,庶民尚能安居乐业,一旦君臣无德则民不聊生。因此传统民本思想需要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时代转换,即从“民惟邦本”走向“人民至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民本思想在廉政建设上的积极作用。
三、廉政建设的践行仪轨:制度保障
《贞观政要》中关于廉政建设的制度保障有甚多内容,这主要涉及官员选拔、奖赏惩戒、权力制衡等内容,这体现了唐初廉政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就,对于后世有着极大影响。不过,传统廉政制度仍旧带有明显的伦理法色彩,缺乏现代法治精神。
(一)廉政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合理性
《贞观政要》中有关廉政制度建设的内容很多,大致涉及选人用人、政绩考核、监督封驳、权力制衡等各个方面,看起来比较完备严密。
官员选拨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太宗非常重视人才,曾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2]95,又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2]479。在选拔人才上,太宗在注重才能的同时非常强调德行的重要性,“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2]189。太宗曾巡幸蒲州,刺史赵元楷阿谀奉承,是一个奸邪伪善的小人,太宗当面斥责说:“此乃亡隋邪佞,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2]440正是因为太宗亲君子、远小人,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所以清廉大臣多聚集于朝。对于已经任用的官员,朝廷还制定有专门考核制度以考绩黜陟,“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罪者戒俱”[2]189。只有赏罚分明,才能促使官员“竭心力以修职业”。增加官员的俸禄来防止腐败也是一项重要制度。太宗即位之后,针对官员俸禄普遍较低的情况实行“俸禄制”,俸禄包括工资、职分田和实物,以促进官员养成廉洁之风。
权力必须监督制衡,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廉政建设的顺利进行。《贞观政要》中的相关内容首先表现为监听制度的完善:朝廷制定、施行了京官值班制度,以了解京城和地方的世风民情;朝廷还坚持奏议制度,鼓励臣下发表意见,“若诏敕颁下有未隐便者,必须直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2]32;朝廷还实行谏官随朝制度,广开言路,由此得以了解民情、及时解决社会矛盾。其次表现为裁汰冗员、完善封驳制度。针对唐初官员冗余、鱼龙混杂的情况,太宗认为:“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2]183于是削减郡王数量,并让房玄龄裁定官员编制,精简冗官余吏。为了达到权力制衡、防止贪腐的目的,太宗强化门下省的封驳职权,由此使得中书、门下、尚书相互制约以防止一家独大和决策专断。最后表现为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立。贞观年间朝廷设立了御史台以专门掌管监察事务,同时派出监察御史等监察官员对全国各地进行定期、不定期巡视,其监察范围涵盖民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极大促进了地方吏治的改善。
在传统中国官本位人治模式下,加强廉政建设的制度保障尤为可贵。《贞观政要》反映了唐朝统治者“治吏不治民”的治理原则,其记载的诸多制度被后世王朝所继承,为反腐倡廉、保障民生、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廉政建设的核心是官德修养,但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能成为大公无私的圣贤,对于大多数普通官员来说,进行道德教化的同时强化制度约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惩罚,而且鉴于贪官污吏对社会的巨大危害,“不赦贪官”也成为一种常见做法。如唐太宗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包括死罪都可以被赦免,但是独独不赦免“枉法受财之赃官”。贪腐的根源在于权力,权力需要制衡。太宗时期实行的用人制度、封驳制度、监察制度等收到了很好效果,也成为后世制度建设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选材用人制度强调德才兼备(尤重德行),这有利于官德修养;封驳制度有利于兼听则明,防止权力专制;监察制度有利于世情通达,民意畅通,官场清明。自上而下,中央官吏受到监察御史、谏官、风闻访知等制度的监督,地方官吏受到巡察、弹劾、鞫狱等制度的监督,这些监督措施较为完整严谨,代表了传统廉政制度的较高水平。
(二)传统廉政制度建设的历史局限性
太宗时期制定的廉政制度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仍旧存在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突出体现为包括廉政制度在内的几乎所有制度都具有“伦理法”色彩,现代法治精神的缺乏是其必须克服的缺陷。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忠孝仁义等)实际上已经渗透到法律制度之中,因而传统法律表现为一种典型的“伦理法”特征。廉政制度也是如此,其各种条款都能够找到道德依据,“法”与“德”密不可分。由于在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实际上维护的是基于血缘宗族的等级尊卑关系(所以“孝”“忠”是最重要的德性),所以廉政建设的践行实际上非常依赖于上位者。下位者对上位者的监督很难实现,至于愚民政策下的“庶民”,除了喊冤之外更是不可能发挥监督作用。这样就使得传统社会的廉政制度实际上脱离了人民大众。
在传统社会中,君父处于最高地位,有制定、废除法律的至高权力,所以实际上廉政建设的对象不包括君父本身。对君父的约束只能付诸祖训、天降灾殃的警告以及臣子的谏言,这实际上给廉政制度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漏洞。因此,看似完善的制度执行最终不得不依赖统治者的德行。就唐太宗本人而言,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由此廉政制度能够在他治下得以完善落实。如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2]32由此大量选拔人才,并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引导臣下清廉为官。所以说,传统社会的廉政制度固然起到一定效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其缺乏现代法治精神。
(三)传统廉政制度的时代转换:从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治”
《贞观政要》中的廉政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是仍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腐倡廉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其徒有“法制”的外表,却没有内在“法治”的精神。
传统法制服务于君主集权,现代法治则服务于人民民主,因此即便是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中也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如习总书记强调:“巡视组要当好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抓住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勇于承担落实监督责任,敢于碰硬,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积极促进反腐败问题解决。”[4]108表面上看,巡视组与唐太宗时期的监察御史职责类似,但监察御史行使职责的目的是为了王朝(皇权)稳定,而巡视组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民权、促进人民幸福,所以两者最终起到的实际效果是不同的。显然,同样的制度在传统法制模式中难以起到重要作用,而在现代法治模式中则作用巨大。
传统法制没有现代民法(保障人民权益)的内容,而且法律制度的执行常常受到权力的干扰(君主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仍旧是一种人治模式。而现代法治制度的核心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没有任何人能够凌驾法律之上。如在权力监督上,习总书记充分认识到制度对公权力制约所起的关键作用,他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4]124相对于《贞观政要》中的权力监督和制衡,现代法治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民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的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4]126。正是因为传统社会无法发挥人民監督的作用,所以廉政制度最终成为官僚之间的博弈工具,即便有明君贤臣试图力挽狂澜,但终归无法阻止腐败之势。所以,《贞观政要》中的一些廉政理念及具体制度要想在当代中国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其根基就必然要进行从传统法制到现代法治的转换。
总体而言,以《贞观政要》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思想有其合理性,但是因为传统人治模式的局限,使得其始终无法避免封建专制本身固有的种种弊端。“我们不允许由一个人来治理,而赞成由法律来治理。因为,一个人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治理,最后成为一个僭主。”[10]148因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现代法治是廉政建设的根基。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廉政建设的重要目标是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廉政思想需要进行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时代转换,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以官德修养为例,以忠、孝、仁、义为主的传统道德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才能克服官本位的历史局限性,才能让这些德目在廉政建设的主体规范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民本思想也是如此,只有放在“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中,我们才能对“民惟邦本”加以正确的时代诠释。廉政制度建设也是这样,尽管《贞观政要》中的廉政制度建设时至如今仍有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法治精神的缺失。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下,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对我国廉政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也要进行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时代转换,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參考文献:
[1]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骈宇骞译注.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5]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 下好先手棋,开创发展新局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N].人民日报,2020-08-24(1).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7(2).
[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0]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校 王学青
Clean Governance Thoughts in Political Program During
Zhenguan Period and Its Contemporary Applicability
XU Jin,SHAO Zhefu(School of Philosophy,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Hubei,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clean governance in Political Program during ZhenGuan Period embodie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a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that is,the emphasis on the moral cultivation of officials,the emphasis on the people-oriented value orientation,and the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governance system. These ideas of clean governance also hav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f we wan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Political Program during ZhenGuan Period,we must give it contemporary modifications. In terms of official virtue cultivation,“serving the people” should be followed,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the people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should be transformed to “the people being at the supreme position”,and in terms of system construction,we should move from traditional rule of man to modern rule of law.
Key words: Political Program during ZhenGuan Period; official virtue; people basis; rule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