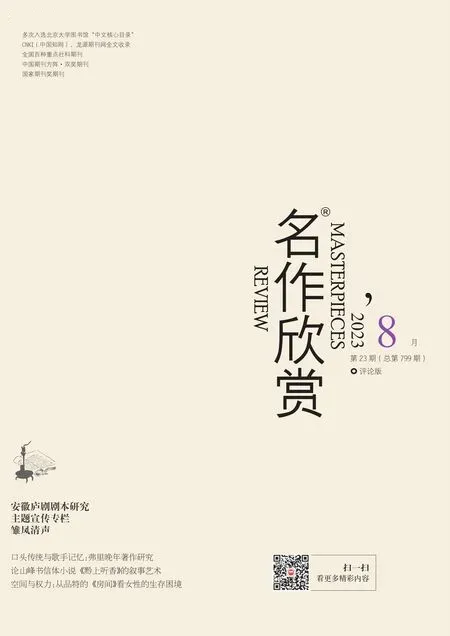论庐剧“打戏”的情节设置及其成因
⊙孙亚军 [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合肥 230061]
庐剧是安徽省主要的地方戏剧种之一,曾流行于安徽大部分地区,为当地人民所喜爱。在庐剧现存剧目中,地域特色明显的传统小戏更受民众喜爱。目前,传统小戏收录最完整是安徽省文化局在1958 年开始组织编写的《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庐剧》15 集(未能刊印的13 集,已遗失),总共收录了庐剧124 个,其中小戏有65 个(主要集中在汇编的第12 集、第14 集、第15 集)。在这些小戏中,以“打”字命名的小戏(为叙述方便,以下统一称作“打戏”)有12 部。具体是《打芦花》《打长工》《打窑》《打砂锅》《打桑》《打烟灯》《打围屏》《打补丁》《打五扇》《打灶》《打面缸》《打茶馆》(又叫《铁弓缘》)。占目前在录小戏的六分之一强。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庐剧“打戏”如此受欢迎,不仅源于其原汁原味的语言,庐剧艺人惟妙惟肖的表演,更离不开其富有特色的情节设置。情节设置是叙事性文学成功的关键,庐剧“打戏”的成功显然也离不开这个关键。
一、“打戏”的情节设置特点
讲好故事,是一切叙事性文学不断进行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庐剧“打戏”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地方戏曲来说,如何能吸引观众才是王道。除表演因素外,更需要剧作家在情节设置上下功夫。庐剧“打戏”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围绕“打”字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情节设置。
(一)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讲述“打”的故事
黑格尔对于故事如何创作曾有一段经典论述:“动作(情节)也罢,性格也罢,要成功地表现出来,必须经历一条无法避免的途径:纠纷和冲突。”就“打戏”来说,戏剧冲突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庐剧打戏中,《打灶》《打五扇》就是靠激烈的戏剧冲突来赢得观众的。
《打灶》主要讲述的是普通小民田三春想与大哥、二哥分家,要灶神托梦不灵,将灶神打倒。这部戏的开头就营造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戏剧冲突:“田三春来怒气生,忙把大棍手中拎。早奔东厨打灶神,将身流落东厨进……”最终灶神被其揍得遍体鳞伤,“恨声三春太不良,你不该半夜三更打灶王。打了我上牙犹小可,打落我下牙到二十三晚上不能吃祭灶糖……”后又因为分家不成再次迁怒于紫荆神,“忙把厨刀拿在手,早奔花园砍紫荆……”看紫荆不死又生一计。“田三春怒气生,要烧开水烫紫荆……”最后“一见神树不死……忙把铜钉拿在手,要到花园钉紫荆。”可以看出,由于庐剧早期创作者的视野和知识储备等原因,现存庐剧关于“打戏”方面的小戏本的冲突大多表现为外部的冲突上即语言上的冲突和肢体冲突,较为简单直接。而相对庐剧正本大戏的《秦雪梅》和《休丁香》 中细腻复杂的心理冲突来说,显得粗浅笨许多,难以表现戏曲艺术的婉约之美。
《打五扇》讲述的是浪子调戏卖唱人唱歌却不给钱,最后被卖唱人惩罚的故事。这部小戏围绕“钱”“给”还是“不给”展开了戏剧冲突,首先是两人语言上的对抗,你一言我一语吵起架来:旦:“喂,给钱吧!”丑:“怎么还要钱那?”旦:“人家唱了,怎么不给钱?”旦:“我一定问你要钱……”索钱不成,卖唱人气不过,狠狠打浪子五扇以示其愤怒。
像这样针尖对麦芒的冲突在“打戏”中其实并不多见,通过对于“打戏”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虽大多名为“打戏”,但这种以激烈的戏剧冲突来展开故事讲述的,在“打戏”中并不多见。实际上“打戏”中的“打”并非仅仅表现为这种简单粗暴的戏剧冲突。“打”字还有更为丰富的作用与内涵。
(二)以“打”为引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打桑》写的是母亲李氏命女儿去打桑,回来后母女互逗的场景,表现了真挚的母女情。但令人不解的是,剧本中涉及打桑的劳动场面的文字并不多,大多采用虚笔处理,更多的是放在打桑后母亲教女的情节上。女儿小毛打桑回来,衣冠不整,引起了母亲李氏的怀疑,生怕女孩吃亏上当,情急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又骂又打。“手指小毛一声恨,骂声小毛了不成!为娘在家交代你,你把我言语忘干净!你一头青丝怎么乱?脸上官粉怎掉干净?桑园因何裙带散?为什么擦烂绣鞋跟?越恨小毛越生气,要打小毛了不成!上去抓住青丝发,一把摔在地埃尘。”当得知事实真相(小毛说谎是因为害怕挨打)后,老母亲仍放心不下,非要教小毛十个月的《女儿经》。左叮咛右叮咛,真是爱之切才会恨之深。在《打桑》中,人们读到的更多是教女背后的母女真情。
《打补丁》写的是一个寡汉因为破衣去找干妹妹打补丁,干妹妹对他赌钱生气,互相埋怨到相互表述衷肠最后和好的故事。旦(干妹妹):“可记得你在我家害瘟疫,我为你东山西山去采药草……”丑(寡汉):“可记得你到荒春没得吃,大米灰面(面粉)向你家挑,不够去扛我家稻包;你家到夏天没得烧,大捆松柴向你家挑……”这哪里是打补丁呢?明明白白是情侣间的情感表达,处处写着只有“我”对你最好。
在上述两部戏中,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点:虽都以“打”字命名,但“打”在戏中并不占主导,它只是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以此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三)提供戏剧冲突的场所
由于小戏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主要人物设置一般在三到五位,表演的场景相对也比较集中。因此,场景的选择在剧本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场景能否表现人物生存的环境及相应的性格匹配;场景能否为故事的发展提供真实性的支撑;场景能否有效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等,均为早期的庐剧艺人们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因此,提供合适的场景,让情节发展有个较好的土壤,让表演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为观众打造一个更好的视觉效果。小戏《打茶馆》就是一个积极尝试。
《打茶馆》(又名《铁弓缘》)讲述的是开茶馆为生的将门之后严萧氏为女儿比武招亲了武将应广中,后当地恶霸戚继兴前来茶馆调戏严女,招致痛打的故事。严萧氏开场白即言:“新开店来久开店,久开店,不怕王侯来饮宴,老生找他要现钱。”从中我们便可看出,此人虽为妇人但也是个见多识广不怕事的主。自古以来,茶馆都会在集市上开设,南来北往的客商、儒雅风骚的文人、蛮横无理的地痞无赖、各色人等都有可能聚集于此,这就要求茶馆老板既要无所畏惧还要灵活多变。由于茶馆聚集人员较为复杂,各种信息汇聚于此,所以它也是一个社会信息交流的小平台。因为人多,才为严萧氏替女儿碧霞招亲提供可能;因为需要做生意招呼客人碧霞才会出头露面为人所知,竟而赢得“赛姜妃”的美誉;因为茶馆的特殊场景设置,才会有“父亲在朝官居大学士的戚继兴”听说碧霞貌美而前往茶馆强娶的暴行;才会有应广中揍打戚继兴的快事……
(四)设计关键细节,推动情节发展
在庐剧“打戏”中,剧作者常常设计一些关键细节。既能推动情节发展,又能起到特殊的戏剧效果,同时又能塑造人物性格。可谓一举几得。如“打戏”中的《打芦花》 《打砂锅》《打面缸》等均体现这一特点。尤其是金芝先生的《打芦花》对这一手法的使用堪称典范。
《打芦花》中的继母李氏,用芦花为絮为丈夫闵直公前妻之子闵损做棉衣。闵直公携子赴宴途中,因闵损叫冷遭到闵直公用马鞭抽打。马鞭抽过,芦花飞扬。闵直公才知闵损遭李氏虐待。于是引出了闵直公责骂李氏并写下休书。后因闵损跪求“堂前留母一子寒,堂前无母三子单”,深深打动了闵直公和李氏,一家人重归于好。
显然,在这部戏中,最重要也是最经典的细节就是:打芦花。闵损长期被继母虐待,但他顾全大局,为家庭和谐愿意忍辱负重。打芦花这一细节,让闵直公知晓了儿子挨冻的事实;因为这一细节直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加强了戏剧冲突,引出了闵直公和李氏的冲突;同时这一细节,对塑造闵损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没有这一细节,就无法塑造一个忍辱负重,宁愿牺牲自我成全一家人的闵损形象。
此外,打芦花这一细节中选择的道具芦花也具有特殊的戏剧效果。自古以来,芦花意象都带有悲情的意味。《诗经·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开辟了这种以芦花抒悲情传统。因此,这个道具选择可谓独具匠心。在这个小戏中,芦花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实物,它已经超越了实物层面,具有明显的悲情色彩。试想,马鞭抽处,芦花纷飞……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芦花吗?我们看到的是闵损的悲惨处境和忍辱负重顾大局的崇高品格。
与其情节设计类似的还有《打砂锅》《打烟灯》《打围屏》《打面缸》,就不再赘述。
(五)标签剧中人物,讲述主角的故事
在各类“打戏”中,《打长工》显然是个例外。它剧中人物的身份命名来设计与其相关的故事情节。
《打长工》也称“长年”。旧时整年受地主或富农雇用的贫苦农民。吃住都在地主家,习俗上农闲时要管他们一到两顿饭,农忙时得管两到三顿饭。由此可见,长工待遇不可能高,想养家糊口也是奢望。《水浒传》中李逵回家接母亲来享福的理由就是其兄长在别处打长工,无法侍奉老母。
庐剧小戏《打长工》讲述的就是一个长工的故事。长工被东家辞退生气,打钢刀报复被妻子劝退。长工为何如此怨恨东家呢?看看长工如何陈述的:“又叫长工去拉稻,又叫长工去舂米,又叫长工去搓绳子,又叫长工挤蓑衣,又叫长工去犁田,又叫长工去耙地。一人只长一双手,把我分到八下里!”如何辛劳还被克扣工钱,索性“打把大刀手中掂,心想望人要一百,不敢给我九十串”。这种情节设计不禁使人想起了汉乐府里的《东门行》。这是汉代乐府民歌中思想最激烈,斗争性最强的一篇作品。描写的是一个城市下层平民在无衣无食的绝境中为极端穷困所迫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的故事。其间也多为夫妻对话,长短不一,参差不齐,妻子的委曲哀怨,丈夫的急迫愤怒,活脱脱地反映了当时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及社会矛盾的激化,丈夫“拔剑东门去”的反抗。
通过贴签剧中主角,说明身份,能够让观众在第一时间把握基本剧情,产生联想,激发他们观看兴趣。
二、庐剧“打戏”情节设置的成因
(一)方言的丰富性
庐剧的主要流行区域在江淮之间,属江淮方言区,使用本地方言进行吟唱,乡气十足,深受百姓喜爱。
在某些时候,我们发现方言所具有的魅力是不能低估的。从方言类节目在本地吟唱时产生的幽默感及亲和力都是普通话远不能及的。究其含义来说,有时也远比普通话宽泛得多,使用场合相当灵活。翻阅现代汉语字典“打”的含义共计包括二十种之多,其中常用的含义为:敲击,还有振作,攻击,考虑、计划等意思。而在庐剧中“打”的含义得到延伸,赋有现代汉语中“打”所没有的更为丰富的表述。如《打桑》就是一种农事活动,为采桑之意。《打长工》的“打”和江淮地区的人们讲的“打小板凳”“打豆腐”的意思相近,就是做的意思。《打补丁》“补丁”的本意指的就是为了遮掩衣服或者被褥上面出现的破洞,使用小布块缝补上面的地方就被称为补丁。这是在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这里的“打”有缝补的含义。
由于“打”字本身含义丰富,在江淮地区使用范围广,因此,被早期艺人拿来为剧目命名并设计相关情节,观者也容易理解接受。虽然,在相似区域流行的地方剧种不乏以“打”字开头命名的剧目,如黄梅戏的《打猪草》《打豆腐》《打纸牌》等;皖南花鼓戏的《打红梅》 《打瓜园》 《打豆渣》 等;淮北梆子戏的《打金枝》等;综合比较庐剧中的“打”使用的场合更广泛,几乎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追求世俗的快乐
庐剧“打戏”从现存的剧本来看,反映的主要为广大农民的生活:农事劳动、情感纠纷、家长里短、阶级矛盾等。以极有生活情趣的故事情节打动人、感染人、吸引人。一部部“打戏”就像一幅幅画卷,惟妙惟肖地展示江淮儿女生存智慧。对普通百姓故事进行立体化的艺术表达,给人带来愉悦,让人无法忘怀。
安徽地处中国的中部地区,地貌以平原、丘陵和低山为主,土地虽然并不肥沃,经济也欠发达,但并不影响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辛劳而乏味单调中互相嬉笑打闹;对权贵的诙谐幽默的嘲弄;面对威压的反抗最终取得胜利的骄傲感和自豪感;在世俗享乐文化的影响下,人民较为满足于小安逸小快活,不求将相王侯一辈子荣华富贵,只求老婆孩子热炕头,顿顿小酒小肉伺候,一家人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如《打面缸》中妓女腊梅从良,县太爷等人对其垂涎三尺均想染指,而腊梅并不动心,最后嫁给和自己差不多的衙役张彩,只求恩爱一生;《打围屏》富翁马驿嫌贫爱富,打算退婚,要长工郭三游说张道洪,哪知两人为姑表亲,一同设计痛打马驿;《打烟灯》在嬉笑嘲讽中完成了对莫大寿的规劝,终于改邪归正,立志戒烟,好好和老婆一起过日子。
这种生活上的追求通过较为精准的情节设计得到真实的演绎,同时也获得了生活在这方水土上人民对于“打戏”的认可和追捧。
(三)文人参与编定的结果
庐剧最初为地方小戏,人们农闲或在农忙时,哼上几句,或解乏抑或助兴,即兴而歌自娱自乐。演员多为当地的农民,略懂音律且颇有资质加之唱戏努力,很快就能崭露头角。早期戏班没有设定专门的人员来负责编写剧本,演出较为随意,所以,剧本情节设计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但是随着庐剧的兴盛,人民欣赏口味的提高,加之班社间的竞争,情节设计的合理化、精彩性渐渐提上日程。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左右,随着民间班社的国营化,一大批文职干部充实到庐剧的创作中来,许多新文艺工作者加强了与老艺人的合作,对于庐剧小戏进行整理、改编,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小戏本,其中自然不乏“打戏”。“打戏”情节设计上的特色与新中国的庐剧人努力是分不开的。
庐剧“打戏”小本通过故事演绎以求农事丰收、风调雨顺、人丁兴旺、万事顺达;通过吟唱表达百姓的自然情感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简单朴素的情节设计,较为直白的语言间之于插科打诨营造的幽默,足以打动当时的观者,为他们贫瘠的精神生活带来一丝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