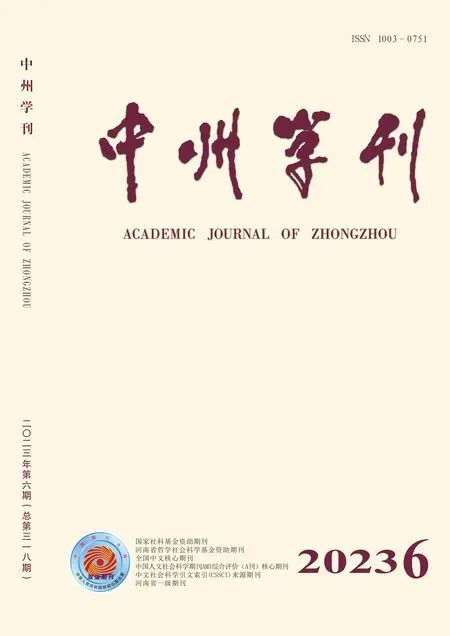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陆建华
世界是由道和道的生成物——天地、万物和人类所构成的,与道相比,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是道所生之“物”。道物之间由此而有着类似于母子的联系。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①,表达的即是此意。不过,这里的道是作为宇宙万物之本原的道。面对世界,道有道的原则,即道之道;物有物的原则,即物之道。这里,道之“道”和物之“道”中的“道”则是作为道和物之原则的“道”。这也意味着,从作为原则的“道”之主体来看,道有道之道和物之道,道之主体包括道和物。那么,道之道与物之道究竟是什么,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一、道之道
老子单独言道,有时指道自身,即作为本原的道;有时指道之道,即作为原则的道。比如,《老子·二十五章》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的“道大”中的道,就是指道自身,此句指道自身是“大”的;其中的“道法自然”中的道,则是指道之道,此句指道之道是“法自然”,即“无所取法”“以自己为法”[1],也即取法自己本来的样子。
“道法自然”,意味着道不以任何外在的原则为原则,不被任何外在的原则所限制,也意味着道之道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在需要,按照其本性而行动。这里,“道法自然”看似是针对道自身来说的,实则是针对道“物”关系来说的。即是说,道的原则是“法自然”,是取法自己,以自己的本性需求为原则,不以他物的规定为原则。
道之道之所以是“法自然”,原因在于道在宇宙中是最高的存在,不仅主宰其所生成的天地、万物和人类,是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至上者,而且还主宰人类信仰世界中的神灵,是宗教世界的至上者。《老子·三十九章》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表达的即是此意。在老子看来,天地、河谷、万物、侯王等道的生成物以及神灵,都接受道的主宰、遵守道的规定,才能够拥有自己的特质,并因而获得理想的生存机会;排斥道的主宰、违背道的规定,则必然会“失去存在的根据”[2],失去自己的特质,并因而毁灭自己。
关于道对于“物”也即天地、万物和人类的主宰,老子有多处的说明,比如《老子·五十一章》曰:“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谓道以生出、抚养、保护“物”的方式,使“物”得以生、得以长、得以成熟,其实,就是主宰“物”的生、死以及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关于道对于“神”的主宰,老子所言不多。《老子·六十章》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谓道主宰“神”之一种——“鬼”,“鬼和其他所有的神一样,其神性由道所规定,因而鬼在道面前不能发显其神性和威力,即使在遵从道的圣人面前也不能发显其神性和威力”[3]。《老子·四章》曰:“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谓道是最原初的存在,即便宗教世界中的最高存在“帝”也存在于道之后,也像是道所生,也在道的主宰和控制之下。
由以上也可以看出,道之所以能够主宰“物”和“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道是“物”的本原和制造者,道主宰“物”,主要以“生”和“养”的方式;道存在于“神”之先,好像是“神”的祖先,道主宰“神”,主要以决定其神性的方式。
在道“物”关系中,从道的角度看,道之道是“法自然”;从“物”的角度看,道之道又是什么呢?
从“道法自然”来看,道不受道之外的任何存在所制约。道又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按理说,道对于“物”是可以无所不为、为所欲为的,在此意义上,从“物”的角度来看道之道,应该是“无不为”。但是,《老子·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认为道之道是“无为而无不为”。
就道之“无为而无不为”来说,主要是指道对于“物”的主观上的“无为”与客观上的“无不为”。《老子·三十四章》曰:“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五十一章》曰:“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老子看来,道在主观上“不名有”“不为主”“不自为大”,对于“物”“不有”“不恃”“不宰”,也就是说,道没有欲望,不占有“物”,不为“物”之主,更不自以为强大,而是把“物”看作是“与自己对等的、独立自主的存在者”[4],任由“物”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发展。即是说,道对于“物”的存在与发展是放任自主、不加干涉的;道在客观上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生”万物、“衣养”万物、保护万物,赋予万物以生命和本性,以决定万物的生、死以及生命历程和本性样式的方式主宰万物,以主宰万物的方式实现其对于万物的“无不为”。
这么看,道之于“物”,“无为”是现象,“无不为”是本质。道既然赋予、决定了“物”的本性,还需要在“物”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为”吗?道既然赋予、决定了“物”的本性,不就意味着在“物”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无不为”吗?
二、物之道
道之道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物之道是什么呢?
由于老子认为“物”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包括道所生出的天、地、人以及道所生出的、生长在地上的自然万物,并且,“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在道所生出的“物”之中,天、地以及以“王”为代表的人为“物”之“大”者,天、地、人等又各不相同,所以,在老子看来,没有一个抽象的“物”之道,所谓“物”之道也就由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等所构成。
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看出,在天、地、人三者之间,天最“大”,仅次于道;由“天法道”可以看出,天取法道,天之道也就理所当然要取法道之道。
我们知道,道之道包括“道法自然”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但是,天之道是不可能像“道法自然”那样“法自然”的,因为天为道所制约,不可以放任自己、取法自己。这样,天之道所能取法的只能是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同理,地之道、人之道也只能取法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
天之道又叫天道。在老子看来,天之道是神秘的。《老子·四十七章》曰“不窥牖,见天道”,认为天之道不是透过窗户昂首看天就能看出来的,表述的就是此意。《老子·七十三章》论天之道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谓天之道一方面“不争”“不言”“不召”“繟然”,也即不争夺、不说话、不召唤、舒缓闲适,呈现出“无为”;另一方面却“善胜”“善应”“自来”“善谋”,也即善于取得胜利、善于回答问题、善于让他人自然来到、善于谋划,呈现出“无不为”。这表明天之道像道之道一样,也是“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由于天之“不争”“不言”“不召”“繟然”和“善胜”“善应”“自来”“善谋”都是客观的,天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就不是像道之道那样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而是客观上“无为”,也客观上“无不为”;这里,天之道的客观上的“无为而无不为”,以客观上的“无为”得到客观上的“无不为”,其中,“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是结果。
基于天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九章》又具体论述天之道的“无为”曰“功遂身退,天之道”,这是取法道之道的“无为”中的“功成不名有”(《老子·三十四章》)。
由于道之道“无为而无不为”,落实为“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三十四章》),“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在万物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犹如“守护神”,一直为万物的生存和发展贡献力量,并且至少在主观上没有任何私心和占有欲,体现出强烈的“利他”精神。《老子·八十一章》因而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认为天之道取法道之道,对他物有利无害,同样具有“利他”精神。
具体到天之道对于人的有利、天之道的“利人”,《老子·七十九章》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认为天之道是不亲近、不偏向任何人的,只帮助需要并值得帮助的人。
关于天之道的“利他”精神,《老子·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认为天之道是“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减少万物多余的东西,补充万物不足的东西,让万物处于既不在某一方面“有余”,又不在另一方面“不足”的恰到好处的状态,从而使万物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地之道
天作为“物”之一种,其道是“无为而无不为”。与天相对的“地”,其道又是什么呢?
《老子·七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认为天之道和地之道的共同特征是“不自生”,也就是生不为己而为他物,都具有“利他”精神。问题是,道之道、天之道的“利他”精神奠基于“无为而无不为”,地之道取法道之道和天之道而有“利他”精神,其道是不是也是“无为而无不为”呢?
关于地之道,老子没有明确说明;对于构成“地”的“万物”,老子也没有明确说明“万物”之道。相反,在老子那里,“万物”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动性的存在,只是作为道、天地和圣人等的陪衬者而出现,用以展示道、天地和圣人的特征。比如,《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用万物说明道的本原性;《老子·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用万物说明天地自然,没有道德属性;《老子·二章》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是用万物说明圣人之无为。
就“万物”中具体的“物”而言,老子也只提及飘风、骤雨、甘露、河谷、草木等少数的“物”。《老子·二十三章》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三十二章》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老子·三十九章》曰“谷得一以盈”“谷无以盈,将恐竭”;《老子·七十六章》曰“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由此也可以看出,老子只是从自然现象的层面论及飘风、骤雨、甘露、河谷、草木等,并没有从本质的层面论及飘风、骤雨、甘露、河谷、草木等,以及这些具体的“物”的“道”。
不过,相较于飘风、骤雨、甘露、河谷、草木等地的构成物,老子对于构成“地”的、“地”上最多的“物”——“水”最为关注,论述了水之道。关于水之道,《老子·八章》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认为水之道是“善利万物”“处众人之所恶”,具有“利他”精神;水之道是“不争”,具有“无为”特质;水之道的“利他”“无为”接近于道之道,是取法道之道的结果。这里,水之道是“无为”,而且其“无为”明显是客观的。
水之道具有“无为”的特质,是否还具有“无不为”的特质呢?《老子·七十八章》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这是说,柔弱之水最能够战胜坚强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它强、比它更合适。既然水最能够战胜坚强的东西,那么,水还有什么不可以战胜的呢?既然水能够战胜一切“他物”,水还有什么不可为的呢?这么看,水之道不仅是“无为”,也是“无不为”;不仅其“无为”是客观的,其“无不为”也是客观的;水之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并且,这种“无为而无不为”与天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一样,也是以“无为”为手段,达到“无不为”的结果。
老子论述水之道,而水又是构成地的所有具体之物中体量最大、数量最多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老子是以水为喻,或者说以水为例,论述地之道。这样的话,水之道是“无为而无不为”,地之道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四、圣人之道
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来看,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都是“无为而无不为”,人要取法道、天、地,人之道就应该取法道之道、天之道和地之道,就应该也是“无为而无不为”。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老子认为天之道是“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即“损有余而补不足”,具有“利他”精神,而人之道却与之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不但不具有“利他”精神,还对他物具有危害性。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减少万物不足的东西,用来供给万物多余的东西,让万物不能很好地发展,处于既在某一方面“有余”,又在另一方面“不足”的艰难状态。人之道既然不具有道之道、天之道和地之道基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利他”精神,当然也就不是“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不该有的贪欲。在贪欲的驱使下,人作为欲望的存在,违背了道,追求名利,贪图享乐,又有着攀比和嫉妒心理,什么都想拥有,即便有些东西对自己并无用处。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对待万物不会“无为”,只会“有为”,由于力量的有限,想因为“有为”而无所不为,又做不到。《老子·四十四章》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既是对人的贪欲以及为了贪欲而“有为”的控诉,也是提醒人们警惕贪欲、“有为”对人的危害,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危害。试想,健康没有了,还能享用财物吗?生命没有了,财物还是自己的吗?
为了拯救人类,老子抬出了“圣人”,也即人类中理想的人,希望通过圣人治理天下,管理人类,遏制人类的贪欲,制止人类的“有为”。那么,圣人之道又是怎样的呢?《老子·七十七章》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这是说,圣人作为“有道者”,是道的化身,取法道,服从道,圣人之道必然不同于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背叛,而是取法天之道,由天之道的“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损有余而补不足”,做到“有余以奉天下”,把多余的东西供给天下,以弥补天下之不足。这种圣人之道无疑也具有“利他”精神。《老子·二十七章》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还将圣人之道的“利他”精神落实为“救人”“救物”,不放弃任何人和物。
由于道之道、天之道和地之道的“利他”精神都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紧接着论述圣人之道,认为其是“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即是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这里,“不恃”“不处”“不欲见贤”“不争”,也即不依赖、占有对方,不显现贤能,不争夺,具有“无为”的特质;“为”“功成”,即有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具有“无不为”的特质。为此,老子总结出圣人之道是“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四十八章》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还论述了如何成就圣人之道“无为而无不为”,那就是通过学习道,减损自己的“有为”,随着对道理解的深入,减损的“有为”就越多;减损掉所有的“有为”,进入道的境界,就会成为圣人,就会“无为而无不为”。
关于圣人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有多处说明,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这是说,圣人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针对天地以外的自然万物和人类(民众)而言的,就其中的“无为”来说,包括外在的言行方面的“无为”“无事”“不言”,内在的心灵方面的“好静”“无欲”,以及态度方面的“不有”“不恃”“弗居”等;就其中的“无不为”来说,包括“生”“为”万物,使民“化”“正”“富”“朴”等。这里,圣人之道中的“无为”和“无不为”明显都是客观的,并且,其中的“无为”与“无不为”像天之道和地之道中的“无为”与“无不为”一样,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
关于圣人之道中“无为”的原因,老子有解释。《老子·四十二章》曰,“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是说,自然万物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而发展的,不会被人们所左右,比如,自然万物的“损”“益”即是如此。在此情形下,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任何“有为”都将是徒劳的,只能“无为”,也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这也表明,圣人对于自然万物的“无为”是不可以“为”而不得不“无为”,是被迫的。关于圣人对于民众的“无为”的原因,《老子·五十七章》曰:“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说,民众不需要圣人的“有为”,就“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实现圣人要求民众“化”“正”“富”“朴”等目标。这也表明,圣人对于民众的“无为”是可以“为”而“无为”,是主动的。
由以上可知,道因为至高无上而“法自然”,也因为至高无上而虽欲“无为”却又不得不“无不为”。道的至上性、主宰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道与“物”的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从常道引出天之道,从天之道引出圣人之道”[5],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无为”来说,“实际上包括了或代表了无欲、无争、无事、不居功、不恃强、不尚武、不轻浮、不炫耀等”[6];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由于人的贪欲,违背了道,造成人之道是“有为”而利己,这是有害的。
注释
①《老子·一章》。本文所引《老子》为王弼本《老子》,以《王弼集校释》为准,标点有改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