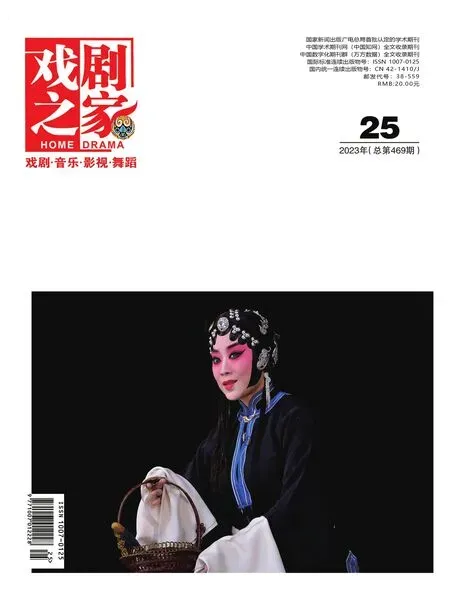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路学研究方法
——“路学”研究
赵 阳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8)
民族音乐学将音乐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将其置于文化中进行研究,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由于音乐文化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且差异性大,因此,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文化人类学者较早注意到道路所传达的社会文化意涵,受国际影响,国内学者围绕路学研究框架从2010 年开始就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种道路文明带来了人们在社会、文化、音乐、历史与当下多向空间的延伸与变化,从而形成‘路学’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新趋向”。
一、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道路研究
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开放性的跨界学科,非常注重与多样的方法论的结合,其开辟了“道路”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其他维度,并不断发展出相应的“路学”概念。人类学家的目标不再只是理解一个区域的文化,而是关注该区域的人口、货物和资源的流动。在区域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中,这一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既重要又可用于种族间文化变迁的研究。以《流动的地域,共生的民族,互惠的音乐》这本书为例,作者将研究对象——东路二人台、阿斯尔和雅托嘎三种音乐事象放在时空坐标下阐释文化通道中族际之间的交往流动与音乐事象的传播流动的互动关系。作者以“路学”为主线理论,将“路学”这一学术概念应用于研究过程,将宏观-微观、历时-共时等多方位的学术思想与当下人类学的各种研究文本相结合,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文空间中寻找合理的文化解释。从东口路以及东口文化下的文化通道开始研究东口路诸层面的音乐流动现象。作者以东口路通道为研究范围,从不同论域的学术脉络中厘清本书的探讨对象与研究范围。书中的“东口路”具体指“以中原地区的汉族人从张家口出关通往塞外,经坝上汉蒙交汇区、锡林郭勒盟蒙古族聚居区,延伸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地域路线。”
本书第一章通过走近历史现场并且与田野实践进行互照,对东口路通道以及通道内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进行整体叙事,探讨东口路的发展变迁过程。第二章对元代以来宫廷、王府、民间等不同社会层面东口路的音乐文化发展变迁以及人群流动带来的音乐文化交融现象进行探讨。第三章从族际互动的视野对坝上汉蒙交界地域流播的东路二人台这类民间艺术综合体从民间班社与国家艺术团等不同组织群体的视角进行多场域的考察与书写,并解析当下流传的表演文本的音乐表征与民族内涵。第四章对察哈尔—锡林郭勒盟地区独有的音乐品种——阿斯尔进行跨越古今的探访与记录,分析其音乐中承继的蒙古族文化传统及汉族音乐的渗透印记。第五章分别对中蒙雅托噶的田野现场与音乐表征展开叙述并进行对比分析,以跨境蒙古族音乐文化为轴线,境内外的音乐事象共同构成了雅托噶的音乐文化,粘连起中蒙雅托噶音乐文化版图。通过雅托噶音乐两个场域的对话,在文化回授视角中分析境内外雅托噶的音乐表征。第六章从族际视域切入东口路汉蒙音乐综合体,论证民族交往与音乐传播的互动关系,重新构建路学视域下的音乐文化多样性特质。总结第三章至第五章,其分别对东口路场域中的东路二人台、阿斯尔、雅托噶等音乐事象在当下的田野发展现状进行多点实地考察,对东口路汉蒙音乐文化进行整体串联。
作者的研究思路来源主要是她的导师杨红教授,杨红教授的三大项目提供了田野调查的基础以及理论实践的保障。在“路学”研究中,作者更加强调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等多向学术思路,并主张将历史学、图像学、人类学、社会学诸类文本以及视角转换的“多点叙事”方式纳入其中加以反思。“文化路线”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历史上在交通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道路提供了一个文化分析的视角,因为它们在连接个人与群体、地方与世界方面起着中介作用。在修建道路的同时,人们在创造着新的社会空间。伴随道路延伸而来的人口、物质、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塑造了文化路线沿线的社会空间。交流与流动是文化路线形成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众多的文化通道是维系各民族情感的纽带,在促进民族交往和交流的过程中,文化路线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二、通道文化研究
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现象,“路”在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的空间,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载体和呈现方式。它将历史浓缩,使空间与时间的联结从两个方面展现出来,即在形态上表现出历时性的变迁,另外,道路交通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时空压缩”,表现了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群体间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上的重新构造,使地方和空间的意义及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成为时代变迁的巨大驱动力。[1]通道研究可以跨越音乐事象,打破音乐种类间的藩篱,作者认为,东口路作为贸易通道,是不同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并且是人们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场域。不同的民族群体在通道内流动汇聚,频繁地交流互动,因而积淀出深厚的历史文化,生成了绚丽多姿的文化遗产。通过东口路通道的动态线路研究对音乐事象进行延伸和拓展,就可以连接起不同地区、不同形态的音乐事象,从而构建综合性的东口路汉蒙音乐文化整体现象,这是作者的研究思路主线。
赵书峰教授在文章《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关于音乐与“路”的研究主要针对由“流域”“通道”“走廊”构成的“路”的地理文化空间与音乐结构和象征意义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路”既是地理文化空间,也是一种意义空间,其强调从“路”的田野音乐民族志个案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考察走向“路”的地理文化空间中的传统乐舞形态构建与象征意义的关系性、流动性研究。尤其是思考音乐与“路”和时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辩证关系,以及“流域”“通道”“走廊”中音乐的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异地传播问题研究。同时,音乐与“路”地理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既是移动的、多点的、线索的田野民族志书写,又是对传统乐舞文化在跨区域、跨族群之间的异地传播问题展开的关系性比较分析研究。[2]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于2014 年举办了首届国际路学工作坊,此次的研究成果《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论文集反映出当前路学研究的领域范围和前沿进展,是“路学”研究系列的开山之作。周永明教授认为,“路学”是一门从跨学科的角度对道路的修建、使用和影响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其对道路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深入探讨。周永明发起的“路学”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研究,从生态和文化两个角度对“道路”对社会产生的综合影响进行探讨。道路学的研究视角显示,道路是一种充满文化意味的景观,可以从不同的背景去考察道路对社会的影响。对于文化线而言,历史性和流动性是其特殊属性,不同群体在文化线上的社会流动,如人口迁移、贸易、社会交换等事项,在空间上赋予了文化线以动态性特征,但在历史演进中,随着道路需求强度的变化,空间动态性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文化路线是以文化区与文明区之间多样化的沟通需求为驱动,并伴随着人员、物资、信息等的传递,构成空间走廊,进行文化沟通。作为历史上的道路,文化路线一直起着促进民族融合和区域交流的作用,是道路研究的重点。
在杨民康、赵书峰、萧梅等专家学者研究的跨地域的音乐文化中,研究者通过小传统间的比较,寻找彼此的文化特质,进而推动跨界民族间共同的音乐文化圈子和层次的建立,从而形成一个比较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与呈现大传统的互融图景。以点串线线成面,以板块连接通道,以通道构建生态,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分层一体的音乐文化研究学术格局。
三、田野考察研究
“田野考察是民族音乐学的立身之本,是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必修课。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必须重视田野考察实践,不做扶手椅式的学者,不空谈理论,不闭门造车。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与人类学专业一样必须以居住式、体验式的方式,通过至少半年或一年的实地调研,才能真正建立起与本地人的信任关系。”[3]田野考察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基础与资料来源,田野地点的选择非常重要,它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也反映着学科视域的变化。“去实地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理解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构成。”这是实地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的主要优势之一,即研究人员有潜力作为内部人员体验日常生活的世界,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人类生活并获得直接体验。
在20 世纪80 年代,民族音乐学者常将目光投向一个特定地点的音乐。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学者们发觉不能将自己的研究锁定在一个地方。东口路视域下的音乐文化实体由冀蒙交汇区的东路二人台、蒙古族聚居区的阿斯尔、跨国共享的雅托噶以及伴随晋商足迹流播的晋剧共同构成。在冀蒙相连地区,汉蒙民族共同拥有东路二人台这一音乐品种。对东路二人台的田野考察跨越冀蒙两省交界,构成汉蒙交汇区的整体视域。阿斯尔流播于东口路通道中的察哈尔右翼后旗、镶黄旗和苏尼特右旗等蒙古族聚居区,延续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音乐特征,但也有汉族音乐的融入和渗透,折射出汉蒙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互动关系。跨越中蒙的雅托噶音乐文化反映出蒙汉民族与中蒙两国在历史变迁中的互融与共生关系。而伴随晋商足迹流播于张家口和蒙古草原上的晋剧则呈现从起点的繁盛到终点逐渐消弭的离散过程。这些音乐实体在汉蒙人群的流动中生发出融合和共生的音乐文化,他们共同构建出东口路汉蒙音乐的综合性表征。
四、总结
“路学”研究是目前的学术热点,道路研究已成为综合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一门新学科。道路对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因而极具研究价值。但目前,道路科学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科学的道路社会文化研究框架。道路作为一种连接方式和路径,特别强调不同关系的构建。东口路是一个广阔的区域,所以,音乐学者必须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作者根据东口路空间的动态特征跟踪音乐活动的“流动”,动态地进行田野实践。在研究中运用多地点田野考察方法,采取多点串联的调查手段,从文化关联性入手,关注东口音乐文化体系中的东路二人台、阿斯尔和雅托噶等蒙汉交融音乐事象,分析汉蒙民族在族际交往中音乐文化间的互联与差异。《流动的地域,共生的民族,互惠的音乐》这本书将通道内的多个田野点进行系统整合,构建出东口路汉蒙音乐文化的多点系列民族志文本。
“通道”的边界也在不断的研究与实践、板块互动、渠道拓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以民族音乐学为基础,对“路学”历史地理音乐的研究综合考虑了音乐现象和共生的文化环境,这就决定了,从乡村、城镇到现代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都与现实有着深刻的关联。的确,面对现实,它更加强调实用性。通过深入研究、探索道路历史上的难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音乐中的焦点问题,这样的整体研究可以为区域音乐生态和文化保护与发展措施提供建设性的、现实的文化策略。重新审视道路音乐的价值地位仍需从“路学”的角度,从多元表达历史和地域音乐民族学的角度,对音乐新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