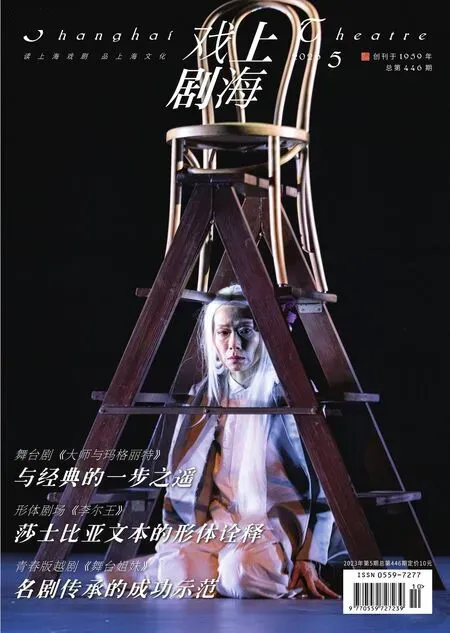消费逻辑视角下沉浸式演出的观演关系研究
□陈 敏

观众是舞台表演艺术存在的先决条件。这是因为,从浅层次意味上,舞台演出依赖观众经济上的支持,演员的激情也有赖于观众的捧场。从深层次意味来看,做戏本身如果没有观众的各种支持,戏本身可能就无法称之为戏。没有一种艺术体裁像表演艺术这样如此注重观众这一因素。观众是否在场,决定着舞台表演能否称之为演出这一事实。观众在传统表演艺术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演艺产业的语境中,观众的重要性更是被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以观众为中心的观演关系,成为当下的潮流。“当今表演学的一个趋势之一是观众在表演性元素的网络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性。当今的舞台,观众的地位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一些多媒体营造的虚拟的空间,产生了以观众为中心的观演关系,这种聚焦于观众的剧场组成了当下的潮流。”①
传统表演艺术的观演关系构建的是等级秩序,演员与观众是交集不多的两个独立部分,是纯粹创造者和欣赏者的关系,而且是以演员的叙述和阐释为主的。在传统的剧场结构中,舞台居于支配地位,观众处于旁观的状态,观众只需要观看故事如何展开,从而形成剧场主导的观演关系。进入消费社会,表演艺术内在的消费性催生的演艺产业迎合观众对娱乐消遣的需求,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介入到表演环境中的体验者和驱动者。贝内特(Susan Bennett)在Theatre Audiences中明确指出:“观众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不一定是受到戏剧研究理论的推动,也不一定受到我们戏剧创作的推动,而是受到文化产业的经济现实的推动。”②沉浸式演出聚焦于观众作为审美主体的体验性感受,是以观众为核心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主张。随着戏剧的发展,不断创新演出的样式,其中一个共同倾向就是缩短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观众参与”作为创作的起点,不仅考虑观众如何接受,而且考虑观众如何实质性地参与进演出之中。观众的欣赏方式由传统表演艺术中的静观,转向观众主动进入作品当中,动用所有感官参与艺术作品的完成。本研究从消费逻辑的视角,采用对比分析法,通过比较沉浸式演出《不眠之夜》与传统戏剧《麦克白》之间在观演关系上的差异性,揭示出沉浸式演出的开放性观演关系如何与消费互动,既能实现演出的艺术价值,又能实现其商业价值。
一、观众与表演的纯粹关系转化为观众与消费的关系
沉浸式剧场的典型特征是邀请观众直接进入演出场景当中,并成为有效的表演者。传统表演艺术是不需要观众深度地参与舞台表演,而沉浸式演出是需要观众与演员共同完成的戏剧“事件”。通过革新观众和表演者模式,加强观众参与,把观众放在一个具有相互性或互动性的情景之中,激活观众的参与感,并最终转化为消费。对比传统戏剧演出的《麦克白》和据此改编的沉浸式演出《不眠之夜》:前者是基于观众坐在台下,演员在台上的演出形式,在远处观看整出戏的表演,类似于欣赏者在博物馆欣赏绘画,远远地观赏表演。后者则是没有了传统舞台的限制,观众和演员同景、同台,观众随演员一起活动,而且还有互动,观众成为了表演的一部分,这是传统舞台艺术所难以实现的。
沉浸式演出与观众的消费行为紧密相关。观众作为行动者,他们的身体和“看”的过程被戏剧化地消费了。《不眠之夜》的演出过程包含完整的消费链:观众可以在酒吧点一杯饮料、和酒保聊天……这些消费的行为不仅隶属商业空间,同样也包含于戏剧空间之中,生活与戏剧空间的边界通过商业行为进一步模糊。沉浸式演出虽然故事内核选取经典文本,角色设计和主要情节遵循原著剧本,但观众的观看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联结,使得经典剧本中的叙事性在表演和消费过程中被折叠,观众不是去看懂故事,而是体验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因此,《不眠之夜》的先锋性被削减,消费性不断凸显,从而形成艺术和消费杂糅在一起的体系。一方面资本的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另一方面把原有的先锋艺术形式收编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消费景观。《不眠之夜》除票房收入外,围绕作品本身拓展产业链条,结合主题酒店、餐饮、购物等多种商业的业态,提升了演出的附加值。因此,《不眠之夜》的收入结构包括票房、租金、商务合作、酒吧及衍生产品等。如表1 所示,2019 年《不眠之夜》演出三周年之际,演出917 场,总收入达27 亿元,票房收入占2 亿元。

表1 《不眠之夜》上海版3 周年经营状况③
二、观众与表演性环境的互动产生消费
沉浸式演出空间在原先的物理属性之外,开始具有了表演性,乃至成为表演的主体。“21 世纪随着沉浸式剧场的兴起,区隔演员与观众空间的疆界进一步消失。这种剧场更极端的表现形式是观众被鼓励与演员互动,甚至与演员共同演出。模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出现于20世纪末。马塞尔·杜尚通过签名和展示把小便池转换成一件艺术品,同样地,艺术家通过邀请观众将真实的生活作为戏剧来观赏,从而把真实的生活场景呈现为戏剧。彼得·布鲁克声称,任何空的空间都有资格用作剧场。因此,戏剧表演再也不是限于某个特定建筑内,由某个特定人群按照某个特定风格表演的一种孤立的艺术形式。戏剧表演已经与人类社会活动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④《不眠之夜》的演出空间是把将废弃的烂尾楼改造为六层楼的非传统剧场,命名为“麦金侬酒店”,是专门为演出所打造的表演空间。
沉浸式演出缩小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观众参与成为沉浸式演出的亮点和魅力,强调作品与人的互动性,达到人、作品和表演环境的相互统一。《不眠之夜》表明表演与商品的绑定产生消费文化奇观。基于《不眠之夜》这样一种艺术特性非常明确的作品本身构成了一个商业矩阵,用一种好的文化体验调动各种商业消费的场景。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围绕《不眠之夜》打造了“尚演谷”这一文化综合商业体模式,以作品本身为核心,通过商品衍生授权和空间衍生授权,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带动周边酒店、餐厅和酒吧等商业设施。这种表演艺术新形态呈现出消费性意味,实现艺术与商业的紧密合作。
三、观众由固定视角转变为动态视角,吸引观众重复消费
沉浸式演出中,由于取消了固定的舞台和观众席,观众更是与演员近距离接触,自由选择剧情的走向,参与式进行观看,让演出的剧情走向和结局呈现为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版本中,创作是线性叙事结构贯穿其中,而沉浸式演出《不眠之夜》打破原剧《麦克白》的叙事脉络,剧中每个角色人物都有各自所讲述的故事线条,在各自的空间按照固定的表演路径演绎各自的故事,如此循环往复。演员散布在90 多个房间中各自演绎看似独立却相互关联的故事,观众可以自由走动,观赏到不同的场景,经历了由固定视角转变为动态视角的革新。《不眠之夜》采用多重的叙事结构,通过吸引观众“二刷”“三刷”,甚至形成“攻略”实现了重复消费。也正是出于这种戏剧设置,每一个观众跟随的演员、看到的故事和拥有的体验都完全不同;同样一个观众,每一次的观感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对于观众来讲,观看的已经不是完整的戏剧,而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西洋镜。因为没有座位、没有舞台,甚至连对白、旁白都一律没有,使得观众丧失了“上帝视角”。因为,没有任何两个故事相同。如图1 所展现的剧场内部空间和剧情关系,表明观众可以选择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进入剧场,也就选择不同的角色体验剧情。演出采用碎片式的多空间场景,观众以符号式身份直接参与演出,演出完整面貌需要好几次观看才能在想象中合成。所以,每位观众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获得传统演出那种首尾完整详尽的故事。但是,这种消费行为没有被附加文化再生产的能力,只是简单地、游戏式地重复消费主义的逻辑。
四、观众参与的有限性既实现了消费价值又保证了艺术价值
观众参与演出是有一定限度的,是建立在艺术而非生活的基础上的。观众与演员共享舞台,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隔绝关系,改变了观众消极观看的状态,是对传统剧场观演之间权力关系的解构。所谓参与是指,导演总是在想方设法打破横在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缩短乃至消灭二者之间的距离。但观众参与演出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种观演融合的演出在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看来:“寻求错觉,让人信以为真,以及剧场中的观众参与都可能导致戏剧不是艺术。”⑥所以,观众参与有两条原则:一、观众参与不能干扰大多数观众的正常欣赏;二、观众的参与必须是艺术的参与,而非生活的参与。苏联著名戏剧理论家泰伊·洛夫在《论观众》一文中“讨伐”了那些试图将观众纳入实际演出,使其实质性地参与进来的倡导者们。其理由为:“我认为共享性质作为显著特征,在戏剧存在中从未达到过这样重要的地步……在宗教中它的力量最为强大……那么,既然共享活动是一系列人类精神现象的毫无疑问的特征,它也就不成为其戏剧的特征了。相反,当它真的出现在戏剧中时,它常常是一种破坏的而非建设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要求20 世纪的戏剧回到共享行动,而且把戏剧的复兴之希望寄托在这个基础上,这只能意味着逆转戏剧艺术的车轮,意味着剥夺戏剧的独立价值,使其附庸于不论其为宗教的或社会的、这种或那种群众活动的思想。”⑦舞台与观众的分离标志着戏剧演出的成立,且二者之间的二元性是恒定,唯一的变化就是这种距离的缩短或增加。

艺术创作中观众参与必然是有限的,只能在局部对演出产生不同的作用,尤其是在演出的叙事层面,不可能完全由观众主导演出叙事、放任剧情随意发展,若果真如此,观众也未必能够获得观赏的愉悦和满足。正是,由于路径的不确定性和故事情节的随机性,观众遭遇各种互动性的表演。但是,观众与演员的互动(被王子送酒,国王耳语,护士检查,麦克白牵手等)并不会改变演员的演出和故事的走向。《不眠之夜》让观众从“旁观者”的身份转变为“参与者”,体验的升级激发了观众全新的消费兴趣。《不眠之夜》属于交互级别(级别0—无交互、级别1—可选交互、级别2—鼓励交互、级别3—要求交互)里面的级别1 可选交互,即有限的或最小限度的参与,参与者可以与道具互动,也可以与表演者交谈,没有硬性要求。“虽然大部分的体验过程并不涉及观众的任何互动,但是观众可以通过打开抽屉和橱柜来探索布景,同时阅读和检查其中的道具,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故事及其所呈现的世界。这些交互并不是必须的,但对于那些有兴趣的人来说确实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感。”⑧
作为一种规律,对于普通猪禽饲料而言,调质过程中,物料温度每升高10℃,水分增加0.6%~0.7%[9]。但对于水产饲料而言,因饲料吸水率较低,采用高压、低蒸汽量、长时间调质,温度每升高10℃,水分增加0.5%~0.6%。对反刍动物的精料补充料也有类似的情况。

结 论
兴起于20 世纪50 年代的接受美学,标志着观众作为剧场演出终端脱颖而出,成为剧场的重心,决定演出的最终价值。“当我们谈到参与文化时,积极的参与总是比被动的消费更受重视。通常这意味着对信息生产而非批判性消费的关注。”⑨传统剧场多为镜框式舞台,因此,观众的身份是确定的,观演关系是观众必须恪守常规,不允许在演出中与演员有直接交流。而沉浸式剧场颠覆了传统剧场的观看体验,观演关系由“观看”转变为“参与”。《不眠之夜》是在传统经典戏剧《麦克白》的基础上进行解构,形成新的叙事。从本质而言,《不眠之夜》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戏剧,而是重新定义《麦克白》中的“剧情”“表演”“观众”“观看”,决定了二者在观演关系方面的差异性。资本主导的剧场美学以利润最大化的标准来衡量、规定剧场艺术生产。作为演艺产品的消费者的观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忠实于受众的背后就是忠实于市场的经济逻辑。“各种艺术的成功,甚至是其生存,越来越依赖它们战胜剧场的能力。这一点也许没有比戏剧本身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在那里战胜我称之为剧场的东西的需要,主要体现在确立一种与观众之间的截然不同的关系的需要上。”⑩因此,沉浸式演出中开放性的观演关系与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同构,与消费主义契合。
注释:
①濮波:《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表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18 页。
②Bennett, Susan. Theatre Audiences: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J].London: Routledge, 1997:1.
③数据来源: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中国沉浸式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暨〈不眠之夜〉上海版3 周年总结报告》,数据截止2019 年12 月。
④[美]马文·卡尔森:《戏剧》,赵晓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9 年,第26-28 页。
⑤刘天博. 当代沉浸式剧场的空间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21。
⑥[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367 页。
⑦[苏]泰伊·洛夫:《论观众》引自[美]艾-威尔逊等:《论观众》,李醒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年,第126 页。
⑧《2020 全球沉浸式设计产业发展白皮书》。https://www.nextscene.us/
⑨[美]亨利·詹金斯,[日]伊藤瑞子,[美]丹娜·博伊德:《参与的胜利: 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13 页。
⑩[美]迈克尔·弗雷德:《艺术与物性》,张晓剑、沈语冰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1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