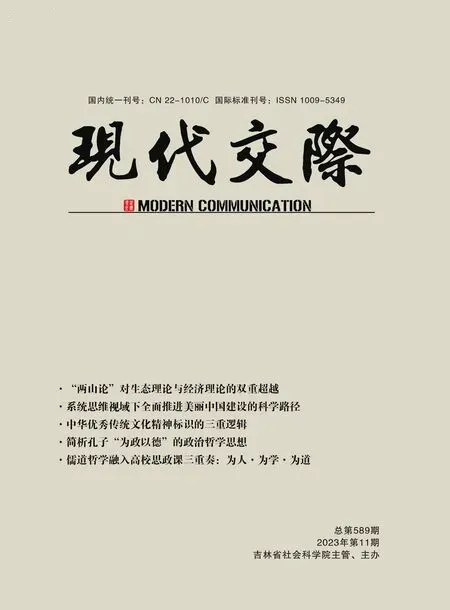简析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
□刘 洋 朱连增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00)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制度的建立与改革以及法律的地位与作用,试图通过外在的制度与法律规范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有关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也更倾向于“非道德的政治观”,其中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典型代表,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不仅没有把政治哲学思想的重点放在制度与法律之上,甚至主张一种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美德政治学”。《论语·为政》中开篇便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是指参与国家的政治管理与引导。“为政以德”的基本含义应是指为政者本身具有德行,然后用德行引导人民,用礼仪来规范人民,使人民也具有德行。而只有当为政者能够“为政以德”,他才能如“北极星”一般“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一、“以德配天”
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对西周时“以德配天”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展。而“以德配天”的思想又是从殷商时期“以祖配天”的思想演变而来的。“以祖配天”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以祖配帝”,因为“天命”一词是周人的说法,在殷人那里,与“天命”概念相等同的概念应是“帝命”。“帝”是殷人所信仰的最高神。殷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他们是以自然神为基础的多神教信仰。因此,作为他们至上神的“帝”也更多地具有自然神的色彩。“帝”可以像许多自然神一样掌控着风、雨、云、雪,能够决定是否降雨或者何时降雨;同时,作为至上神的他又可以掌管人间的祸福,既可以选择保佑人王,也可以选择降祸人间。由于“帝”对殷人来说更多只是一位自然神,故这个“帝”并不存在任何道德伦理属性,既不关心任何人,也不关心人间所发生的任何事,人所能做的只是祈求他的庇护。但人并不能直接和“帝”交流,只能通过祭祀祈求祖先传达人间的愿望。而祖先之所以能够直接与“帝”沟通,是因为在殷人看来,自己的祖先死后就会成为“帝”的臣子。因此,殷商时期会出现这样的卜辞:“贞,咸宾于帝。贞,咸不宾于帝。贞,大(甲)宾于帝。贞,大甲不宾于帝。”[1]“咸”“大甲”都是殷商先王的名字,而“宾于帝”即“配于帝”的意思。在殷人看来,他们的祖先神就是“帝”的臣子。但在殷商的祭祀活动中,只有人王才能祭天,而在人王祭天时又是以其祖先作为配祭的。在殷商的人王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治的统治权,乃是天命所归。故而,当纣王得知周人打败商的属国黎时,他会反问:“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因此,在政权获取的合理性上,殷商可以说是主张“以祖配天”。但西周用实际行为打破了殷商这种“以祖配天”的合理性。原本作为殷商附属小邦的西周在现实中却击败了作为大邦的殷商,且获得了原本属于殷商的政权。殷商灭亡后,周公在总结其灭亡的教训时,将“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作为殷商灭亡的原因。这与纣王所声称的“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不同,周公所主张的是“唯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在周公看来,天命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天命的改变是以“德”为标准的。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为政者是通过其“德”来获取天所赋予的政权,那么天又是如何来判定为政者是否有德呢?这个答案便是“民”。
伴随着“以祖配天”到“以德配天”思想的转变,有关“德”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德”在殷商时期是与“帝命”或“天命”相关联的。因为殷商时期的“德”多被理解为“得”,即所谓的“德者,得也”(《礼记·乐记》)。如《尚书·盘庚》中的“非予自荒兹德”,这里的“德”理解为“得”就明显比简单地理解为“道德”更为恰当,即并不是“我”荒废了先祖之所得。同时,“德”在殷商时期的卜辞中多被理解为“循”,即遵循祖先神或上帝神的旨意行事的意思,如“王德于止(此)若”“王德出”等。但无论是将“德”理解为“得”还是“循”都是直接与“帝命”或“天命”相关联的,即意味着对“帝命”或“天命”的一种获得与遵循。西周正是基于殷商对“德”的这种理解才提出了“以德配天”的主张,因为“德”本身就是与“天命”相关联的。而周人在对“德”的理解上仍然保留了殷商将“德”与“天命”相关联的思想。但不同的是,殷人觉得“天命”是不可变的,相对于“德”,他们更关注作为与上帝神和人相联系的“祖”;但周人认为“天命”是可变的,不仅要获得“天命”,还必须懂得保持“天命”,故而西周时期主张“敬天明德”与“敬德保民”。有关西周时期的“保民”思想,在周武王伐殷的誓词,即《泰誓》中有着更多的体现,如:“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意味着西周时期对“德”的理解已经不仅局限于“天命”,而是开始与“民”相关联了。正是基于这种对“民”与“德”的看法,周人在为政的具体措施上自然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即倡导彰显君主的德性,谨慎地使用刑罚。同时,在西周时期,“德”也开始正式直接与政治制度相关联了。“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分封制虽然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但是分封制正式的确立与大规模推行是从西周开始的。在这里,“德”直接与分封制相关联,且分封制的施行是为了彰显周公的明德。
二、“政者,正也”
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用“正”来阐释“政”的说法,如“政以正民”(《左传·桓公二年》)。但很明显,这种“政以正民”的说法是源于西周时期对于政治思想的理解,将“正”的对象仅仅指向的是“民”。而孔子的“正”不仅指向“民”还指向“君”,即为政者。孔子“政者,正也”的思想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由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状况,周天子、诸侯王与卿、大夫、士之间的权力与位置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混乱,为政者所获得的“为政”的权力就会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为政者大多不是依靠其德性与才能而获得其“为政”的资格,而是通过世袭获得。此时,为政者是否具有德性就成了一个问题。基于前者,孔子主张“正名”;基于后者,孔子主张“正身”。如果为政者所获得的“为政”之权并不正当,那么他就无法做到“为政以德”。因为“为政以德”的前提就是为政者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一个为政者在政权获取的合理性上都存在问题,又怎么会是一个具有道德的人呢?基于此,孔子主张“正名”。“名”这个字在春秋时代之前一般是指一种用于区分的文字符号,如“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帅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夜事”(《周礼·大司马》)。“名”这个字在这里就作区分辨别之用。也正是基于此,“名”字也多用于人名或物名,如“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礼记·檀弓》)。春秋以后,名的使用多了起来,其含义也丰富起来。此时的“名”更多是用于表示名声、名望,如:“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左传·昭公二十年》);“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名”在《论语》中出现过8次,除了“正名”一段中出现了3次,其余5处中有3处也都是用于表示名声、名望,如:“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但“名”作为名声、名望来使用有时也是与地位、身份相关联的,如“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左传·庄公十八年》)。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名位”的不同,所施的礼也应该有差别,因此“正名”即是指人的身份与地位的获得具有合理性。如果一个人所获得的身份与地位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那么这个人的名誉、名声自然也成问题。在孔子第二次居卫期间,蒯聩因得知灵公夫人南子与宋国公子朝通,于是计划与自己的家臣戏阳速杀死灵公夫人南子。但由于戏阳速临场反悔没有行动,此事不仅不成,还被南子所发现,告知灵公。灵公大怒,蒯聩因此逃往宋国。灵公死后,南子遵照卫灵公的意愿要立公子郢为太子,但公子郢借口自己一直伺候卫灵公到死都未曾听过此遗愿而拒绝了,因此其君位由蒯聩的儿子辄继承。九年后,蒯聩凭借晋国的保护得返卫国,辄派兵拒之。于是,子路与孔子之间就有了以下对话:“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悉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这段对话中,孔子特别强调“正名”在“为政”中的前提作用。同时,我们不难从这段话产生的背景中看出,卫君所获得的“为政”之权是存在问题的。孔子主张必先“正名”,即所获得的身份与地位本身不应存在问题。如果一个人所获得的身份与地位存在问题,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没有条理,其相应的行为也就无法施行,因此事情就不会成功;如果事情不成功,那么意味着礼乐没有发挥作用,故“礼乐不兴”;如果“礼乐不兴”,那么只能依靠刑法约束百姓,但原本用礼乐约束百姓的地方也用刑法进行约束,故“刑法不中”;如果“刑法不中”,则人民就会惶恐而不知所措。因此,君子在其名分之下,必然可以言语,但言语之后必然会依照所说的去做,君子对待自己所说的话必然不会苟且或马虎。
“正身”即是指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孔子如此强调“正身”,一方面是因为相较于君主的个人能力,孔子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君主自身的德行。“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虽然后羿与奡都有其独特的个人能力,如善于射箭或水战,但两人不仅没能称王还不得善终,亲自耕种田地的禹和稷却得了天下。南宫仅是提出了这一疑惑,便得到了孔子“尚德”的称赞,可见君主的德行在孔子为政思想的地位之重。另一方面是因为“正身”如“正名”一样是君主“为政以德”的前提。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如果统治者能规范好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那么管理政治事物还有什么困难的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怎么能去端正他人的行为呢?同时,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了,即便你不发号施令,人们也会遵从;相反,如果你连自己的行为都端正不了,即便你发号了施令,人们也不会遵从。“政者,正也”的完整表述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说明,孔子强调“政者,正也”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调统治者应规范其行为,使其行为符合道德,更在于通过统治者的道德行为去影响他人,使他人也能够根据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为一个具有道德的人。
由于孔子强调为政者应具有道德,因此孔子自然主张提拔有德行的贤人参与政治治理与引导。对此,孔子有着十分直接的表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而当季康子问及卫灵公如此昏庸无道为什么没有丧国时,孔子的回答是:“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卫灵公之所以昏庸无道但仍不丧国的原因在于有众多贤人帮他治理国家,如他有仲叔圉负责外交礼仪、接待宾客,祝鮀管治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如此,又怎么会丧国呢?由此可见有德的贤人参与政治管理的重要性。同时,选用有道德的贤人参与政治管理也是人民所希望的。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只有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人民就会服从了;若是把邪曲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人民则会不服从。而且,孔子还认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即把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曲的人之上,还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但如何知道谁是有德行的贤人并将其提拔出来呢?孔子的回答是:“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只要提拔你知道的贤人,你不知道的贤人自然会主动引荐。
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所追求的是人民具有道德。相较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孔子更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罚来规范人民,使他们的行为统一,那么人民只是为了免于刑罚而不去做有违道德的事,人民心中并不会因为做了违背道德的事而感到羞耻;但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仪来规范人民,使人民的行为得到统一,那么人民不仅会为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耻,而且会主动去端正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道德。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两者追求的都是引导和规范人民的行为,且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借助政令与刑罚从外部规范人的行为;而后者是通过追求使人民具有羞耻之心,即具有道德,主动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民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分别作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结果,两者的差异体现在前者的目的在于使人民的行为得到合理的约束,而后者在于使人民具有道德。
相较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孔子所主张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更为凸显的是为政者对于人民的关切与注重。因而,孔子在为政举措上必然反对暴政、苛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季康子认为通过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就能够使人民具有道德。而孔子很疑惑为什么要用杀戮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明明只要君主想要行善,百姓就会跟着行善。君子的品德就像草原上的风,而小人的品德就像草原上的草。只要草原上刮起君子的德风,小人的品德就会跟随其倾倒。孔子认为,“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而当被问及何为四种恶政时,孔子的回答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不经教化便加以杀戮便是“虐”;不加告诫便要求成功便是“暴”;起先懈怠,突然设置期限便是“贼”;同样是给予人财务,出手吝啬便是“小气”。
“礼”在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某种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礼”在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上扮演着一种道德教化的作用。西周时期,“礼”只是作为通往以天神或祖神为核心的精神支柱的途径,“礼”本身并不具有额外的意义。春秋时期,礼仪观念的兴起,“礼”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天神或祖神作为精神支柱的地位。这不仅是出于维系贵族身份地位和社会秩序的需要,更是因为此时的“礼”有了额外的象征意义。与西周时期仅仅作为祭祀文化的附属物不同,“礼”在春秋时期被视为古典文化教育的象征,一个人知“礼”,便意味着这个人具有成为国之干城、统率三军的能力。但无论是作为祭祀文化的附属品还是古典文化的象征,“礼”都是一种针对贵族的外在规范,与作为国家底层的平民无关。而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主张,便意味着孔子力求把“礼”的规范推向平民。且这种“礼”的规范与作为刑罚的外在约束有着本质的区别:“礼”所体现的是一种对古典文化教育的接受而产生对自我的约束,对自我品格的锻造;而刑罚仅仅是对自我的一种外在的暴力约束。其次,“礼”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与“智慧”的关系上甚至有着某种优先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智慧达到了足以知道的地步,但其“仁”德不能守护住它,即便得到了也会失去;智慧到达了足以知道的地步,其仁德也能守护住它,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人民,但不用“礼”来鼓舞人民,这也是不完善的。最后,孔子甚至认为“礼”的使用在国家治理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如果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么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的?如果不用礼让治理国家,只是空谈,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孔子的这一思想在春秋时期其实十分常见,《左传》中记载“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名”的产生必然包含“义”,且必然与“义”相符合。由于“礼”的产生是以“义”为根源的,因此“礼”是由“义”所产生的。而“礼”是为政的本体,是政治的骨干;政治是用来规范人民的。由此可见,《左传》中也强调“礼”在为政中的重要作用,且同样重视“名”在为政方面的影响。同时,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无论是西周时的“礼”还是春秋时代的“礼”都在彰显着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异,但孔子的这一主张表明,孔子所追求的是一种存在差异却井然有序的状态。
四、结语
孔子“为政以德”政治哲学思想的目的在于使人民具有道德,其实现方式在于君主本人具有德行,且用道德去教化人民。但使人民具有道德仍不是孔子“为政以德”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不仅是因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制”遭到瓦解,更是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原本的上层建筑已经不符合当时的经济生产状况。“礼崩乐坏”所体现的正是当时政治秩序的混乱。由于西周以“分封制”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是以人伦道德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么这种政治秩序的混乱也必然体现为人伦道德的混乱。孔子“为政以德”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以人伦道德为基础的稳定的政治秩序。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齐景公虽然在为政前期,勤于政事、虚心纳谏,使齐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在执政后期,他贪图享乐、厚赋重刑,不仅让大夫陈乞从国家中获取了大量财富与权力,还在自己多“内嬖”的情况下迟迟不立太子,这显然与孔子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左。孔子此时的主张并不包含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级思想,仅仅是表达处于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应该去做其相应身份和地位的事。因此,不难看出,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所追求的正是一种以人伦道德为基础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大家各司其职。也正是基于此,朱熹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2]。
——老子论官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