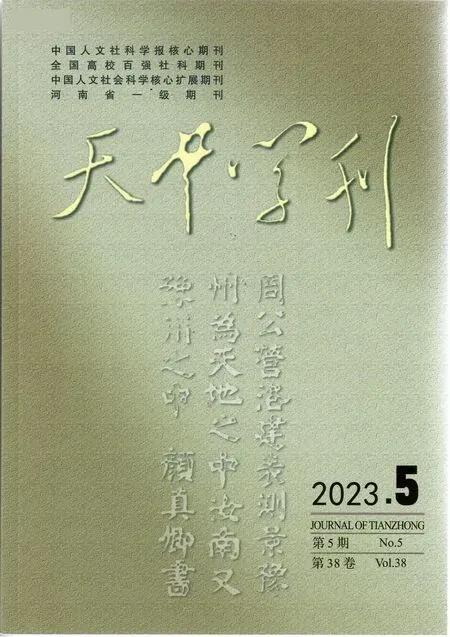试论微时代背景下的微交往模式
邹 珉
(黄淮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21 世纪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开始以“微”的方式和形态进入千家万户,中国社会逐渐跨入以移动互联网为中心的微时代。进入微时代,传播媒介开始逐渐由以文字为主转变为以视觉图像为主,人们用以表征、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微观化、图像化特征,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逐渐转向以形象特别是以类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形成了以图像为中心、综合其他媒介要素的微文化模式。有学者指出:今天的世界甚至可以用“图像先行”来定义[1]63。在以手机、互联网为中心的微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位移,以手机、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交往遮蔽了传统的身体交往,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单一模式,在实现信息交流互动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对话交往空间,生成了新的微交往模式,即“人们借助微博、微信、QQ 等移动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或虚拟空间,突破以往个人现实社会交往范围的局限性,而形成的人际间在‘线上’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互动的一种新的社会交往模式”[2]87。
目前,学者们对微交往的研究逐渐增多。唐晓勇、张建东认为微交往促进了人际互动类型的多样化,形成了多中心网状人际互动模式[2]。赵卫东考察了微时代的交往困境,认为微时代交往方式呈现出极端个人化、群体化、无序性等特点[3]。张丽丽通过调查发现微交往的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随意性、匿名性和平等性给高职学生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给教育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4]。李娜认为“微交往”对促进高校和谐师生关系具有重要意义[5]。总体来看,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微交往的意义、影响和困境等方面,对于微交往模式的具体内容和特征缺乏探讨。在微时代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微交往从交往主体、交往手段到交往内容、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由此改变了人们的思维特点、生活方式、政治参与乃至文化观念,进一步催生了微交往模式的新特征。因此,本文试图深入微交往系统内部,在详细分析微交往具体要素的基础上,思考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微交往的传播技术与符号载体
(一)微时代传播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传播从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媒介终端各个层面呈现出向“微”形态发展的趋势,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互联网为核心,以微博、微信、网站、3G 技术等为手段,以图像符号为主要信息载体,以手机为主要终端,以普通民众为主体受众的微时代。在微时代,随着技术条件的不断进步,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信息终端越来越灵活便捷,在时间和空间上极大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无障碍传播与交流。“与大众传媒的巨传播相反,微传播是由众多微小力量进行的微小信息的传播。其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传播媒介,而是信息的关键词的价值,价值越大,传播范围和深度越大。”[6]69微传播运用音频、视频、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符号,借助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通过微小便捷的收发终端,实现瞬时性、广泛性、互动性、高效性、扁平化传播。一两幅视觉图像或一两段微视频,再加上寥寥几行文字,便可以借助于微信、微博、博客等平台快速传播相关信息,看似短小精悍的篇幅却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微时代背景下微传播具有信息传播数量大,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迅捷,传播时效性强,空间开放,交流互动性强,参与者众多,个性化、群体化和大众化特点突出等特征。
微传播最早源自博客,它往往对突发性事件做出深刻尖锐的评论,具有及时性、大众化、尖锐化等优势,所以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随着微博、微信的加盟,不同媒介形态的边界被打破,媒介传播从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媒介终端各个层次呈现出向“微”形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微传播场域中,信息资源和传播方式不断向外位移、推延和播撒,实现了信息与媒介的分化、重组与转化,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微观化、情景化、动态化的微文化传播模式。微传播作为现代科技成果的延伸,正在潜移默化地重塑大众的思维方式,日益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感知经验,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传播媒介是我们人类意识的延伸,意识则是我们个人能量的“固定资产”,它塑造了我们每个人的认知经验[7]。
然而,现代科技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弘扬人文精神创造条件的同时,又在钝化着人们的感知和想象能力,消解着微传播的人文价值以及消费主体对现实世界的终极思考。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呈现着“微”的烙印,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现实性与虚拟性、个体性与群体化的界限已被打破,无聊与庸趣成为微时代青年人挥之不去的病态心理,谎言与谣传成为微交往难以克服的文化症结。以视觉图像为主导的信息模式日益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主动选择与理性反思,面对便利化、迅捷化、碎片化的海量信息,人们已经习惯于被动式、快餐式的咀嚼与消化。与此同时,人们的社会交往越来越依赖于现代传播技术带来的畸形、病态交往模式。“微传播完全改变了大众传播的传播方式,使得传播由‘教堂式’演变为了‘集市式’,虽然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但万千个聚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集聚效应,甚至可以影响主流媒体。”[6]69
(二)微交往的符号载体
“符号系统是人类交往的工具,人际交往过程实际上是借助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载体,进行传递信息和有效沟通的过程。”[8]198在微交往活动过程中,交往手段主要以微信、微博、微视频、微小说、微电影、微广告等为载体,由此构成了以“微”为特征的,包括图像、文字、声音、数码等形式在内的信息交往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图像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占据了信息交往的核心位置,并综合数字、文字、声音等多种元素,以达到表意、传情、交流思想、传播观念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文字、声音等要素本身不具有独立性,主要是对图像进行说明和阐释,因此,微交往的信息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信息交往为主的图像符号模式。现代语言学表明,包括图像在内的信息载体只不过是不同类型的物质语言符号,如图像符号、文字符号、声音符号、数字符号,等等。交往主体被信息符号以能指的形式带入意义世界,领会符号的指向和意义,从而实现信息传递和交流互动,推动人类交往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宗教等领域有序进行。因此,微交往活动的实质就是微时代背景下交往主体传递交流信息、实现彼此沟通的符号交往活动,交往内容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的意指世界,交往过程则是符号意义的实现过程。
由于交往形式以图像符号为主,图像符号在示意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由此推动了图像符号模式和图像文化观念在交往活动中的生成。但是,微交往的图像符号载体在带给人们便捷的同时,也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理性思考、联想能力与想象能力,以能指的形式把微交往活动的意义局限于浅层的文化消费层面。某微博上的一张摄影图片,描绘了一位面容姣好、青春美艳的少女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图像上方的标题文字为:一枝红杏出墙来。诗句的原意是春色满园,花儿竞相开放,但由于大门紧锁、高墙封闭,花儿难以展露风采,这时,一枝红杏不甘寂寞,探出墙外,于是引起了诗人对院内百花盛开的猜想。但是,由于图像的制约作用,诗歌的联想和想象机制已被打破,主要服务于信息交往的实用目的,“一枝红杏”不再是盛开的花朵,而是指这位衣着鲜艳、青春美貌的女子,“出墙来”也不再引发我们对春色满园的想象,而是传达出某种生活信息。“红杏出墙”与这位女子的生活轨迹有关,可能意指女子的追求超越了世俗层面,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也可能指女子性格叛逆,自甘堕落,最终造成了自己的婚姻出轨。这样,诗句和图像原有的艺术空间被大大缩小,功利性、工具性取代了艺术的想象性、自由性;同时,图像与文字领域的界限和规则被打破,信息符号的浅层示意功能则不断增强,微交往活动成为一个符号能指功能可以任意拼贴、组合、转换的示意过程,最终导致了表意过程的混乱。正如法国学者福柯所言:“语言符号把紊乱引进全部形象及其细腻的相似性中。紊乱实际就是仅仅属于语言符号的有序。”[9]
二、微交往空间的生成
(一)公共领域的私人化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行动发生在公共领域中,“公共领域的特征毋宁是在于一种交往结构……是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10]66。“哈贝马斯理解的‘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它处身政治权利之外,是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11]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早期的共和国,如罗马共和国,建立了代表参与制,由民主选举的代表根据民众意见,在公共领域提出治理国家的意见或方案,并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政务活动进行监督,因此,公共领域成为发表民主集体意见、参政议政、实现民主监督的社会渠道,集体性、参政性、监督性是公共领域的突出特征。但是,微交往空间中预设的公共领域却与哈贝马斯的阐释大相径庭,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性。由手机互联网技术和现代传媒技术创设的微交往空间,本应是由众多个体参与、互动的公共空间,然而这一空间正在遭受私人空间的挤兑,并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往行为和生活方式,改写了交往活动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微交往空间唤醒了交往主体的个体意识、个性风格,甚至赋予交往者更多个体化空间。在虚拟空间的遮蔽下,交往者在公共或私人空间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意见、传播信息,甚至谩骂发泄。这些个体化的空间往往成为山寨文化、平民文化、民间文化、草根文化的始基,逐步呈现群体化、无厘头、爆发式的特点。因此,微交往空间中预设的公共领域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交往活动更多体现个体特征,即便有群体活动,这种交往活动也往往是盲目的、自发的,不具有集体性质;交往活动更多侧重于日常生活的信息交往,信息活动基本上不服务于参政、议政;交往活动缺少必要的监督,至少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完全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公共领域的这种政治文化差异,表明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已经发生改变,公共领域正在被私人空间所侵占。
(二)微交往的网络生态空间
在以手机互联网为中心的微时代,微文化的形态转换引发了人类交往活动的变化,对于人们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交往模式和文化观念带来极大冲击,甚至改变了人们赖以存在的生活空间和交往格局。由手机互联网技术和现代传媒技术创设的微交往空间是存在于网络中的、不同于物理空间的虚拟空间。网络具有数字化、符号化、虚拟化等特点,以此构建的网络生态空间难免会对传统的社会规则、交往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造成强烈冲击。在微交往的网络空间中,微传播介质的相互指涉、相互拆解已经打破了空间中的真实与虚假、现实与幻觉界限,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信息现实失去其客观存在性,成为基于现代传媒技术的人为建构的符号世界。图像、文字、声音、色彩等信息符号的组合与调配显得支离破碎,本身并不蕴含任何深层的情感意蕴和文化内涵,而是以短暂、便捷的方式为人们提供速效的信息快餐。由于网络的虚拟性遮蔽了人们的真实面目,出于各种目的,一些人任意炮制虚假信息,导致谎言和谣传四处散播、色情与暴力泛滥,致使交往行为呈现虚妄、无稽、利益、无序的状态。一旦微交往活动中交往者之间充满着虚伪、怀疑和不信任感,社会公共秩序也会陷入混乱和无序的非道德状态。
网络生态空间中人们价值观念退化、交往秩序紊乱,究其原因,在于网络社交领域中缺少一种规约交往活动的公共理性,亦即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是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谈者共享的理性。与传统的标准理性不同,交往理性中不同言谈者之间是双向的、权力对等的对话关系。主体之于对象的知识范式是传统理性观的典型表达方式,而交往理性的表达则是主体之于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行为范式,交往主体处于对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的理解之中。交往理性适用于人类的语言领域,是体现人们认识、言语和行为的语言理性,能够推动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以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强调,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沟通或交往时,如果把语言当作工具,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或操纵,违背常人的语法规则或脱离原来的语境,变成不可理解的语言游戏[12]。为避免语言的工具化、保证交往行为中言说的有效性,哈贝马斯提出,应当建立言语行为规则体系,制定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领会性等规则,引导、规约交往各方共同遵守,保证交往行为的顺利有效。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行为理论对重构信息话语的存在维度有一定启发性,也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了理论假设和实践参照。
尽管在网络空间中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已经发生断裂,但仍然存在着修复可能,网络社交的生态格局亦有重构希望。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有着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的互文性关系,如果我们在技术层面放弃一种介质,如图像符号的垄断形式,倡导网络空间中信息介质的协调配合、互文共生,让文字的表达、图像的展示、声音的配置、色彩的调和共同构成一幅斑斓多彩的生活画卷,构成一曲美妙华丽的人生乐章。那么,信息交往模式的紊乱局面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扭转,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断裂就能在具体的言语情境中得到修复,主体可能不再被语言符号所控制,逐渐进入澄澈之境,一种开放性的、对话性的网络空间就有可能构建起来。为了避免信息技术的泛滥和网络舆论的误导,我们还可以借助于微信平台,建立基于交往理性的网络舆情评估机制和引导机制,通过公民的参与协商,确立一种公众广泛认可的信息标准和对话机制,进一步清除与我们交往活动无关的垃圾信息、病态信息,以真诚、包容的态度和谐相处、平等对话,摧毁话语言说的霸权机制与信息模式中的他者身份,改变网络空间中“我—他”共在的交往方式,将网络世界的关系改造为“我—你”的关系,改造为永恒的“我”与“你”相会。从这个意义来看,网络社交中语言存在维度和生态格局构建的关键不仅在于理论的预设和政策的匡扶,更重要的是人们用自己的有限感知和生命活动去践行这种“我—你”关系,最终达到“以自己的方式去为自己揭示生存的意义”[13]。
三、微交往活动方式与风格
(一)身体缺席下的微交往活动方式
微时代为我们提供的技术交往条件仅仅是当今社会交往活动得以合理化进行的基础条件,即先进的传媒手段和技术工具,而不是人际交往所必须依靠的必然条件——身体条件。现代传媒信息以“微”形式进入人类的交往活动,但又以其实用性和形而上学遮蔽了人类的实际存在,尤其遮蔽了人类的身体交往。在以图像符号为主导的信息交往中,人们的身体存在被遗忘,其感受、愿望、情感乃至表达的真实意图,也都被淹没在以技术为主导的滚滚信息洪流之中。微时代条件下,技术传播一开始便存在着形而上学问题。现代传媒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炮制超自然世界,以虚拟、泛化的能指符号传达意义,通过编码形式使自身服从于功利化、实用化要求。如果这种技术编码被视为话语言说,那么这种言说本身就丧失了身体经验的可能性,是不自由的,也不以追求自由为目标,因此不具有自由特征,也不可能向存在敞开。不同于传统交往意义上的话语言说,这种现代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言说舍弃了身体存在,是一种非本真言说。传统的身体交往被此符号编码拖向技术主义,遮蔽了身体存在,消除了语言经验存在的可能。微交往中的信息符号是一种概念符号,阻隔了信息传递时的感性经验,切断了身体语言与外物的关联,同时也阻断了身体交往敞开其存在意义的可能性。信息符号成为一种失去存在意义的空洞能指,扬弃或隐退了符号自身的存在,意指功能得以充分展现。
在微交往活动中,不仅身体存在会被遮蔽,交往主体也存在着被淹没的可能。哈贝马斯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病症时指出,后工业文化的逻辑链条已经阻塞了言路,工具理性压倒了人文理性,人类交往活动愈益呈现不合理的状态,而且现代艺术的主体性和交往模式也日益呈现出萎靡趋向[14]。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微时代条件下的微交往活动过程。在微交往过程中,信息符号将身体悬置起来,身体不能出场,身体对于现实的感受、体验、理解和评价,身体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幸福的追求,都需要借助于媒介符号的表意和传播来实现。然而,在微交往过程中,信息传播主要通过大量的类像、仿像、组合、拼贴的虚拟图像符号实现,这些符号的传播和影响已脱离了作为交往主体的人的行动逻辑,逐渐形成其自身逻辑,通过数字链接、程序设置、符号构筑等进行交往活动,交往主体则被悬置而不能出场。身体交往已经脱离了身体本身,演化成一种物化的符号献祭和仪式膜拜,在此过程中身体的感性存在被抽空,身体的存在感,如身体意识、身体想象、身体欲望、身体体验等,已经沦为文化消费的客体碎片和信息海洋,身体在媒介交往中失去了生命意义而变成虚空的东西。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作为人类文化产物和载体的符号,经历了一个从基本反映现实到逐渐脱离现实,再到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的演变过程,其中身体符号也经历了此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从约束性符号向解放性符号的转变。符号的解放表明微交往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作用基本丧失,微交往活动演变成主体名义掩盖下的随意性、扩张性的信息传播活动和充满娱乐性、虚拟性的符号游戏。
(二)个性化与群体性交织的交往风格
人类交往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和完成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只有摆脱阶级、种族、性别、制度等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才能进入无压迫的、自由的理想交往状态。德国当代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由此提出了人与人交往得以进行的可能性条件,即作为行为人,交往者要求承认他既是自律的意志,也是个体的存在,这是交往行为的普遍前提[15]。个体能自由自律,并能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社会秩序才能稳定运行。
面对面的身体交往是传统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在这种交往活动中,手势、表情、眼神等肢体语言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微交往的空间领域,微交往活动的主体虽然也是个体,但却是被信息符号淹没的个体,由于微交往活动旨在传播和交流信息,交往主体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肢体语言在交往中基本不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到个体主体性的发挥。此外,身体交往还要受到集体主义的塑造和纪律的规训。中国的政治文化领域受儒家思想影响,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基本是确定的、明晰的,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个体行为要以大局为重,个人意见和建议若与国家或集体观念相违背,则需要保留,不能一意孤行,社会集体观念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观念在政治、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在微交往的空间领域,这种关系往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所取代。一方面,个人的位置和个体化风格得到突出张扬,数字化的链接和程序化的设计培养的往往是个人的惯习意识,交往的整个过程也是通过个体来完成;另一方面,技术的同构性、信息的标准化唤起的往往是群体的、平民化的认同感,这种群体意识或认同感往往借助于舆论领袖在公共领域的振臂高呼产生狂欢化效应。
身处微时代,便利的现代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极具个性化、人性化的生活样态以及自在的交往风格,在微交往活动中,交往主体形成了以个体为主的个性化风格。尽管微交往也受到集体化观念的约束,私人化空间日益受到公共空间的侵占,但是集体主义观念和规章制度的影响相对淡薄。总之,微交往活动在信息交往中,同时具有圈层化、群体化特征与个体性、个人化特征,正体现出一种个性化与群体性交织的交往风格。
概而言之,微交往模式是以信息交往为主导形式、图像为主导符号、网络为交往空间、个体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当代信息交往机制。微时代场景下,微交往模式呈现出歧义和紊乱特征,究其原因是现代传播技术导致的交往异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产品成为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统治、奴役人,人的异化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随着科技的进步、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及其产物逐渐独立于人的本质和理性之外,成为相对的异己力量。在微交往空间中,工具理性的泛滥与价值理性的丧失导致人的理性迷失,人逐步偏离了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丧失了其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交往中,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主体性,提升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化解交往异化困境,促进人的自由健康发展的根本。因此,回归人本身,即人的身体自身,是解决微交往异化问题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微交往中,人们需要合理构建自我行为模式,加强自我约束、管理和规划,合理使用手机等传播工具,有意识增加真实场景下的身体交往,最终走出虚拟现实,实现身体的逍遥,并在真实世界诗意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