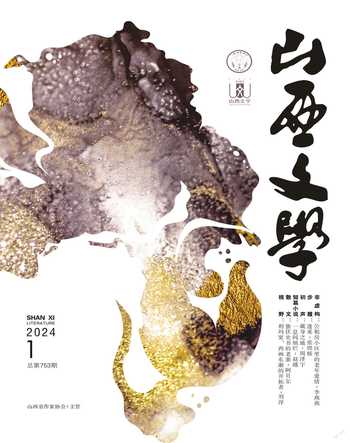关于书籍的杂记与随想
这个国庆假期有点长,没有出门给不堪重负的街衢“添堵”,窝在家里读了几本书和一篇文章。有英国作家汤姆·摩尔的《唯有书籍》、科克·斯塔基的《书虫杂记》《图书馆杂记》和汪家明撰写的范用传记《为书籍的一生》;一篇文章是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收录在郭老的《历史人物》一书中,是我前段时间在图书馆废弃的书籍里找到的。在这些废弃的书籍里我还找到《列宁印象记》和《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风》。我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要定期处理书籍?而且还是这么好的书籍。这本克·蔡特金撰写的《列宁印象记》,就是由范用先生一九七九年主持再版的,非常珍贵,却被图书馆遗弃堕入溷藩。
我“熟悉”范用先生,他写的书、他编辑出版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基本上都读过,厚厚的一册《为书籍的一生》还是令我感慨万端,范用先生永远是行业里的那座灯塔。有一年,一位远方的编辑书友赠我一枚范用先生自制的藏书票“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愈是金贵,愈是小心地保存,最终竟杳然不知去向,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后悔当初没尽快装池,以辉耀陋壁。读《书虫杂记》《唯有书籍》《图书馆杂记》,发现关于读书和书籍,大家的一些想法差别不大,但是所涉及的领域却千差万别,《书虫杂记》引用美国著名教育家、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的话说:
“书是人类最安静和最长久的朋友,也是最平易近人和最具智慧的顾问,还是最有耐心的良师。”一连五个“最”,把书的特质表述得深刻、到位。三层意思:一、书籍作为朋友——它永远在那里。二、书籍作为顾问——它是博大的,它不拒绝任何人,尽管这些伟大的书籍都是由伟大的人物创作的。三、书籍作为良师——它自性沉静,经得起任何读者的折腾。
交叉阅读这几本书的时候,我的大脑活跃着两个念头:
一是,完成一部与读书相关的摄影集——《阅读的姿势》;
二是,租一条旧船,搭建一座“船上图书馆”或者“船上书店”。
这是在阅读过程中,我“翩跹”的——遐想或曰瞎想!沉浸其中我愉快。
读什么书,始终是个问题。
现在“写作”的人多,读书的人少。关于读书,我认同的观点是:为热爱而读书。为自己读书。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在随笔《读书》里说:
“好书犹似良药,可以医治人们思想上的疾病;好书犹似亲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读书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服从自己的天性,因为凭着个人的兴趣去读,才是最佳的读书状态。” 爱默生建议读者:“第一,不要读当年出版的新书;第二,不要读名不见经传的书;第三,不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书。”
读书,当然要读经典。何谓经典?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常会碰到一些朋友问,读什么书好,我就问他:读过“红水西三”没有?他问:什么意思?我说就是《四大名著》。他说知道。我说我知道你知道,我问你读过没有。他说没读。我说那就从阅读四大名著开始。坊间有个笑话,说——经典就是人人都知道,但人人没有读过的书籍。其实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这是现实存在的真实状况。——因此,卡尔维诺又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大约藏有三万册书籍。有的书,我有若干不同的版本,重复购买的也不在少数。我藏读最多的书籍是古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大约有几十个版本,其中最珍贵的是随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大海的一个古老版本的覆刻本。还有鲁迅的书、孙犁的书、叶灵凤的书、高伯雨的书、赫拉巴尔的书、瓦莱里的书等等,版本别出,也有只有一个版本(三联书店版) 却令我爱不释手的,像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梅志的《往事如烟》、冯亦代的《听风楼读书记》……
或问,是怎么发现和找到那些好书的?
过去讯息不发达,采取的是笨办法,常年订阅报纸杂志,包括:《中华读书报》《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就是为读《笔会》副刊)《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羊城晚报》(花城副刊)《藏书报》;杂志有:《世界文学》《万象》《读书》《三联生活周刊》《书城》《文景》《译林书评》《新华文摘》《随笔》等等。从这些报刊里,获得一些好书的讯息。
再就是逛小书店,这些年每到一个地方逛小书店是我的第一选项。譬如说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重庆的刀锋书店、上海的思南书店、厦门的琥珀书店、昆明的麦田书店、成都的喜马拉雅书店、珠海的停云书房、大连的木文堂书店等等,最远的是希腊的亚特兰蒂斯书店,世界最美的书店;逛得最多的还是青岛的我们书店。现在,买书基本是在网上,但是看见书店,还是“拔不动腿”要进去巡阅一番。
阅读的过程,从一个作家到另外一个作家,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忽地眼前一亮,一本好書就被逮住了。其中就包括一些有关读书的书。记得十几年前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来青岛,我们聊到这方面的话题,他说他收藏的关于读书方面的书籍,大约有五百册。我自己所藏没有统计,但也不下几百册。好书尽在其中。有几个例子,可以一说——
我读戴望舒的诗歌和散文,没想到他还是一个翻译家,他翻译过西班牙随笔作家阿左林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就找来读,发现当年周作人、卞之琳、沈从文、林徽因、李健吾、汪曾祺等,都是阿左林的迷弟迷妹。当年周作人,读完阿左林的随笔叹气说道:要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 这样的好书岂能放过。薄薄一册,真是一字也不能错过。后来又购得林一安翻译的阿左林小品集《著名的衰落》,读到的却像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东西。先入为主的强大钳制力,也够可怕。文学的迻译,要做到“信达雅”,还真不是一般人所能驾驭的。尤其是诗歌,我觉得很难将其意蕴完全置换成另一种语言,因此,比较起来我藏读最少的就是迻译过来的诗歌集,我有时候仅仅是因为诗人的名头或者书籍的颜值而购读之,不过这样的书籍也不少。譬如我最新购买邹仲之翻译的惠特曼《草叶集》(译文精装版),里面藏书票上的一句话,还是激励我去亲近它——“现在我洞悉了造就完人的秘密,那就是在阳光里成长,和大地同餐共宿。”而我所藏《草叶集》的第一个版本,是楚图南和李野光翻译的两卷本,三十六年了,是我早期的藏书之一,因此格外“受宠”。而叙利亚大诗人阿多尼斯关于中国印象的长诗《桂花》,我是在外甥女乱糟糟的书架上发现的,拂去微尘,携归于我。
读苏珊·桑塔格的随笔,发现她对奥地利小说家彼得·汉德克赞誉有加,要知道苏珊·桑塔格,挑剔是出了名的。她在日记与笔记《重生》里列举的、十五岁的读书单即便是研究生,也难以俱全地读到。她能看上眼的,不会错,因为桑塔格我就开始搜集汉德克的作品(《缓慢的归乡》《痛苦的中国人》《骂观众》《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左撇子女人》等),果然还是桑塔格有眼力,二〇一九年汉德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我收获了先读为快的乐趣——“探索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彼得·汉德克先生曾来过中国,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做过“我们时代的焦虑”的读书分享会,远隔千里的我,嫉妒京沪两地有福的读者。
有一年重读作家、美学家高尔泰的隨笔《寻找家园》,他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小时候读过一本给他留下印象很深的外国小说,名字叫《石榴树》,他不记得作者是谁,但记得是语言学家吕叔湘翻译的。这勾起我一探究竟的欲望,好奇心害死猫,却是读书的正道,否则,有些好东西因麻木就错过了。我找出《吕叔湘全集》,果然在第十七卷找到,高尔泰读的是美国小说家威廉·萨洛扬的一篇短篇小说。我就手把这篇《石榴树》读了,从此爱上萨洛扬,他的《人间喜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与查尔斯·兰姆的随笔是我的枕边书。
一个理想的读者总要读几部别人不读的书。
我尊敬的一位诗人、学者西川说:读不懂的书,培养了他对文化的好奇。也就是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英语大词典》的编纂者)所说的:“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
经典伟大,因为它们是照耀人类文明存续下去的灯塔,没有那些经典书籍,我们就丧失了精神依皈的土壤。经典伟大,读者也不凡,因为读者是使经典“起死回生”的人。一本没有打开的书,是不存在的。
法国读书家夏尔·丹齐格说:“不读书的人是目光短浅之徒,读书的人是目光远大的人。”为什么说“读书的人目光远大”?普鲁斯特在《论阅读》里给出答案:书能将读者带往别处。譬如伊沃·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桥》,就把我带到他的故乡——塞尔维亚特拉夫尼克的一个小镇,我在那座小说“原型”的多孔石桥上走过,又在贝尔格莱德莫斯科大饭店安德里奇喝咖啡的地方,喝过一杯苦黑的土耳其咖啡;譬如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把我带到伊斯坦布尔,那天,去谒访那座因小说而打造的“纯真博物馆”未果,我委托当地导游择日再去,在我带去的中文版《纯真博物馆》书页内特为留出的空白处,盖上由女主人公芙颂的耳环打造的蝴蝶状印戳。
多年前,我读了一篇德国作家、探险家、植物学家沙米索的小说《出卖影子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说的是一个平民青年因为生活贫穷,向灰衣人(魔鬼)出卖了自己的影子而成为富豪,也因此赢得了爱情。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人们发现他没有影子都恐惧地躲避着他,因为只有鬼魂、魔鬼没有影子,因此他不敢在光天化日的白天和有月光的夜晚出行,他挚爱的人也离开了他。这时候,灰衣人也就是魔鬼建议他出卖自己的灵魂赎回他的影子,青年犹豫再三,到底还是良心未泯,断然拒绝,他把魔鬼给他的钱袋抛进深渊,自己隐居山洞,研究大自然,开笔写人生回忆录。读后我沉吟半晌,默祷,还好这大半辈子总算自己的影子(身份、名誉、尊严等),没有被魔鬼买去!
俄国作家沃洛申说:“我们的精神总是必须走与生活反方向的路。”
读书,是一生的事,它是一场缓慢的“时间旅行”。我想我们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活着,首先要生存,因此该赚钱还得赚钱,该拼命工作还得拼命工作,一个人决不能逃避生活,尤其不能以读书的名义!只要留心生活,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学问,处处都是可以打开的、好看的“书籍”。
几件亲历的小事可以拿来说说:
有一天,在书城参加一个读书活动,遇到一位拿着我的读书随笔集《我的文学地图》的书友,来找我签名,这套随笔集是我十年之前出版的,现在只有孔夫子旧书网上有售。我很感动,我感动的不是这位读者和书友买我的书,而是这位西海岸的书友日常的读书生活,充实而美好。过了一些日子,他给我寄来新出版的书籍《书话十二家》,简洁大方,一如他朴素无华的生活。
真正爱读书的人怕是都潜藏在民间。
南京《开卷》杂志曾经刊发过我的一篇读书随笔,是写与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交往的故事,这篇长文被北京的文化学者、作家、编辑家朱航满先生看到,选入了他编选的《2020中国随笔年选》(花城出版社)。去年他过访青岛我俩见面,我邀请他参观了我的部分藏书,回去后他在《中华读书报》写了一篇随笔《青岛书事》,记述我俩在读书、藏书等方面的交流,我总想着能在这份文化大报上发表文章,不承想却以这种“被动”的方式在《中华读书报》上露面。但心里还是挺高兴,这也是最暖心的书事。航满兄在我的书架上发现一册古希腊散文家卢奇安的《对话集》,他富藏文史哲,却没有这册书籍,回京后他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此书。卢奇安说:“灵魂的财富是惟一真正的财富,其他的财富都伴随着更大的烦恼。”读到这句话,心里得到莫大的安慰。或许,航满先生也感慨如我。
一位诗人与青年钢琴家,关于音乐与诗歌的对话,让我看到另一层——读书与生命的崇高境界。诗人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德国的诸多伟大作品,包括哲学、小说、绘画、音乐等等,构思的过程大多是在缓慢的散步中完成的。我就想“散步”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个什么概念?!人们生活的脚步太过匆忙,生活里好像没有散步这个充满哲学和诗意的概念。大家都像野地里的兔子一样被他人和自己驱赶着,疲于奔命。对于喧嚣的生活,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试图到“命运如雪的诗人”——罗伯特·瓦尔泽的书籍《散步》里寻找答案,果然打开第一页就见到黑塞说:“假如瓦尔泽拥有千百万个读者,这个世界就会和平得多……”而我想说的,至少我们可以“用散步抵御人生的落寞”。(《散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生存或者活着要做的事情不少,但我觉得值得为自己投资的,还是读书!
因为读过的书籍最终都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化为血和肉,成为自己往后日子里的库存。读书的最高境界,大约是在疲累之余,还有心情打开它!读书给我们带来智慧和快乐,所获的智慧和能量,慰藉着我们——读书的人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光,我说的是光而不是所谓的风景,当然看见光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内心有光。——人生的光,需要自己剔亮!
我喜歡现代作家孙犁,他是鲁迅先生的铁粉,只要鲁迅读过的书,他一定要想方设法买回来阅读。孙犁先生珍惜书籍,不管是旧书还是新书他都要端端正正包上书皮,且在书衣里面写下有关文字——谓之《书衣文录》,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笔文学遗产。孙犁先生晚年的文章,尤其他以小说白描手法撰写的一系列故乡人物,令我感动——什么时候我才能写出像孙犁先生这样的文章。孙犁先生,因秉性耿直和倔强,晚年退出文坛,销声匿迹,生活过得并不愉快。但他的文字,影响过当代一些著名作家,譬如贾平凹、莫言、铁凝等,尤其是对铁凝的影响,可谓抓铁留痕。铁凝在回忆孙犁先生的文章里谈到,当年他父亲的朋友、作家徐光耀(《小兵张嘎》的作者),对还在读初中的铁凝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铁凝说:“孙犁的书我都读过。”那一年,铁凝十六岁。铁凝说:引导她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铁凝特别提到孙犁的一篇小说《山地回忆》,尽管我读过孙犁先生的书籍不算少,但这篇《山地回忆》,我还是读过铁凝的文章后,找出《孙犁集》,才读的。
阅读为我们维系着一种超然于现实的姿态,因读书而获得的记忆和温暖,足以让我们沉着地应对人生乃至整个社会面临的“至暗时刻”。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崇拜鲁迅先生,他说他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他说没有鲁迅和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和作品,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4年)。大江受他母亲的影响很大,他获得诺奖那天,亲友都来恭贺这位母亲,这位母亲却说:他比鲁迅还差得远!大江健三郎最常阅读的是鲁迅的散文《希望》, 有一年,大江先生应邀来中国访问,他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去谒访鲁迅博物馆(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处住所,也是鲁迅写《希望》的地方),去了之后,他避开人群,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诵读,令人肃然起敬——“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纯粹的、高尚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只有人性的光芒!
善于读书的人,永远不会孤单
——因为远处的灯火,始终在那里发出温暖的邀请。
2023年10月17日
【作者简介】姚法臣,作家、藏书家、资深读书人。曾做过教师、公务员、电视台记者编导,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北方文学》《译林书评》《开卷》《散文·海外版》《厦门文学》《青岛文学》等,出版读书随笔《我的文学地图》上下卷,作品被收入《2020中国随笔年选》、问津文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