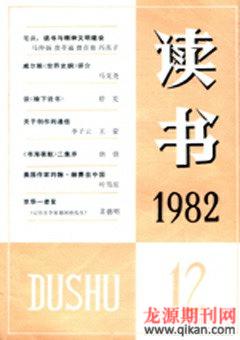对质疑的质疑
晋 崖
《人民日报》最近发表《评<谭嗣同传论>》一文,认为《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对谭嗣同研究中一些较流行的看法和史料,也依据史实提出质疑。”从我粗略的阅读中,觉得书中有的质疑尚难令人信服,还能对之提出质疑。
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初次相会,梁启超《谭嗣同传》本有明确的记载,谓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年末,“君(指谭嗣同)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指康有为),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在《饮冰室诗话》及《记亡友夏穗卿先生》、《与康有为书》、《与严幼陵书》等文中,也反复申言此事。这段史实的可靠性,多年来并未引起争议。《传论》对这一史实提出质疑说:
“按吴樵(即吴铁樵——引者)之认识梁启超,是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梁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梁启勋在梁启超年谱补充资料里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由京之沪,以强学会之余款二千四百元办时务报,识吴铁樵(见《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77)。又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原委》里说:‘丙申五月,季清先生(即吴德潇,吴铁樵父——引者)与其子亡友铁樵同到沪,即寓在报馆(见同上书页525)。可见梁启超与吴铁樵相识,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那么谭嗣同由于吴樵的称赞梁而去会见,当是这一年五月以后的事”(着重号引者加)。
上述梁启超的自述,其实只能说明他一八九六年在上海确实与吴铁樵见过面,并不能说明他们此时才相识。据此不能推断谭梁之初会不在一八九五年而在一八九六年,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至于梁启勋的说法,是第二手资料,不足为据,《传论》自身便并没有采用该书关于:“(梁启超)二十三岁乙未春入京……识谭复生”的说法。
实际上,梁启超早于乙未年间便在北京与吴铁樵相识了。周振甫注《谭嗣同文选》前言云:“查吴于乙未十月二十四日抵津,二十九日到京。十一月十二日吴樵《致汪康年书》:‘十二日,赴强学会议事之约,略坐即去,以无可言者。伯康(汪大燮)、卓如(梁)甚好。卓如以与诸人所论不合,拟辞职矣(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许多常见资料也曾指出此点。谭嗣同《吴铁樵传》云:“嗣同初不识铁樵,亦于京师偶遇之,片言即合,有若夙契。嗣同甚乐铁樵,又钦其父名,因铁樵请见……以长铁樵一岁,父事季清先生,而弟铁樵。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着重号引者加)。这记述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云正相符合:“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
谭梁初会关系到对他们二人尤其是对谭嗣同的历史评价。《传论》对这一史实的质疑似难以令人信服,所谓《谭嗣同传》“歪曲谭嗣同的形象”的看法也还可以讨论。
《传论》还有一处疏忽:谓谭嗣同“把三十岁以前所著集,定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实际上,《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是谭嗣同为自己三十以后所著集子起的总名,其三十以前所著集总名为《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
质疑和订正
晋崖《人民日报》最近发表《评<谭嗣同传论>》一文,认为《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对谭嗣同研究中一些较流行的看法和史料,也依据史实提出质疑。”从我粗略的阅读中,觉得书中有的质疑尚难令人信服,还能对之提出质疑。
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初次相会,梁启超《谭嗣同传》本有明确的记载,谓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年末,“君(指谭嗣同)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指康有为),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在《饮冰室诗话》及《记亡友夏穗卿先生》、《与康有为书》、《与严幼陵书》等文中,也反复申言此事。这段史实的可靠性,多年来并未引起争议。《传论》对这一史实提出质疑说:
“按吴樵(即吴铁樵——引者)之认识梁启超,是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梁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梁启勋在梁启超年谱补充资料里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由京之沪,以强学会之余款二千四百元办时务报,识吴铁樵(见《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77)。又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原委》里说:‘丙申五月,季清先生(即吴德潇,吴铁樵父——引者)与其子亡友铁樵同到沪,即寓在报馆(见同上书页525)。可见梁启超与吴铁樵相识,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那么谭嗣同由于吴樵的称赞梁而去会见,当是这一年五月以后的事”(着重号引者加)。
上述梁启超的自述,其实只能说明他一八九六年在上海确实与吴铁樵见过面,并不能说明他们此时才相识。据此不能推断谭梁之初会不在一八九五年而在一八九六年,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至于梁启勋的说法,是第二手资料,不足为据,《传论》自身便并没有采用该书关于:“(梁启超)二十三岁乙未春入京……识谭复生”的说法。
实际上,梁启超早于乙未年间便在北京与吴铁樵相识了。周振甫注《谭嗣同文选》前言云:“查吴于乙未十月二十四日抵津,二十九日到京。十一月十二日吴樵《致汪康年书》:‘十二日,赴强学会议事之约,略坐即去,以无可言者。伯康(汪大燮)、卓如(梁)甚好。卓如以与诸人所论不合,拟辞职矣(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许多常见资料也曾指出此点。谭嗣同《吴铁樵传》云:“嗣同初不识铁樵,亦于京师偶遇之,片言即合,有若夙契。嗣同甚乐铁樵,又钦其父名,因铁樵请见……以长铁樵一岁,父事季清先生,而弟铁樵。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着重号引者加)。这记述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云正相符合:“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
谭梁初会关系到对他们二人尤其是对谭嗣同的历史评价。《传论》对这一史实的质疑似难以令人信服,所谓《谭嗣同传》“歪曲谭嗣同的形象”的看法也还可以讨论。
《传论》还有一处疏忽:谓谭嗣同“把三十岁以前所著集,定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实际上,《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是谭嗣同为自己三十以后所著集子起的总名,其三十以前所著集总名为《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