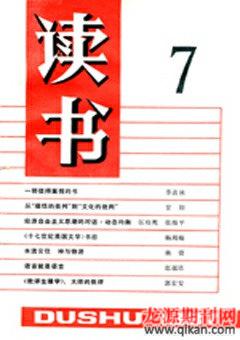订“扬州鹤”
韦明铧
据说在西方,鹤被视为一种淫鸟。然而在中国,鹤作为一种富有吉祥色彩、高雅韵致和神仙风度的嘉禽,却在文化史上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在历来的传说中,关于鹤的掌故轶事太多了,我们几乎随便就能举出诸如卫懿公好鹤、丁令威化鹤、林和靖子鹤等等一长串来。而“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也正是其中最著名的典故之一。
“扬州鹤”的魅力,在于它既意味着羽化登仙而脱离尘世,又表示着到人间最繁华处去纵情享乐。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事,被人们认为既是妙不可言的,又是求之不得的。故“扬州鹤”作为一个典故,大抵总是含有“不可能”的意思。如南宋刘过《沁园春·送人赴营道宰》云:“心期处,算世间真有,骑鹤扬州?”元夏永《丰乐楼图册·题记》云:“钱唐故地之豪奢,临安新府之雄壮。三千巷陌兮,丛花柳以兢妒;十万人家兮,列绮罗而夸尚。……玉女岩、金沙井,依依邺水之凫;烟霞洞、玛瑙坡,影影扬州之鹤。”明瞿佑《剪灯新话》卷一《华亭逢故人记》云:“苟慕富贵,危机岂能避?世间宁有扬州鹤耶?”清钱谦益《孙郎长筵劝酒》云:“燕山马角可怜生,扬州鹤背知谁在?”在他们的笔下,“扬州鹤”是怎样的神奇飘渺,可望而不可即!只是在被鲁迅先生称为“谈鬼物正象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的《何典》第八回中,作者张南庄倒是写道:
……忽听得半空中几声野鹤叫,一朵缸爿头云,从天顶里直落到地上;云端里立一只仙鹤,嘴里衔张有字纸。……(鬼谷)先生看了,点头会意。便……跨上鹤背,腾空而起,望扬州去了。
但这也只是“鬼话”罢了。
那么,“鹤”毕竟何以与“扬州”如此有缘呢?翻一翻扬州的野史笔记,访一访扬州的故旧耆老,便知扬州确有不少关于鹤的韵事——比如城里有寺,传为宋咸淳年间由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来扬州传教时创建,以寺门象鹤首、甬道象鹤颈、大殿象鹤身、左右二厅象鹤翅、厅旁二柏象鹤足、两侧水井象鹤目,故名“仙鹤寺”。又城外有冢,据说清代僧人星悟曾饲鹤一对,后雄鹤病死,雌鹤亦悲鸣不食而死,星悟感其义,遂将它们如仪合葬,故称“鹤冢”。又城南曾有“育鹤轩”,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二:“扬城中园林之美甲于南中,近多芜废,惟南河下包氏棣园为最完好。……园中有二鹤,适生一鹤雏,逾月遂大如老鹤,余为扁其前轩曰‘育鹤。”又城北曾有“仙鹤
“扬州鹤”一语来自“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而此说早在南朝已经出现了。南朝宋梁间人殷芸所作《小说》云: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殷芸的《小说》早已亡佚,但鲁迅、余嘉锡、周楞伽等先生都曾从各种故书杂记中辑录过这本书。据周楞伽先生说,关于“扬州鹤”的这一条,见《渊鉴类函》鸟部三鹤三,小题“上扬州”;又见《佩文韵府》鹤字“扬州鹤”条。这才是“扬州鹤”的真正出处。
“扬州鹤”之典一出,人们大抵都深信不疑这个扬州就是后来那个十里春风常在、二分明月独占的地方了。所以文天祥有《过邵伯镇》诗云:“今朝车马地,昔日战争场。我有扬州鹤,谁存邵伯棠……”按邵伯在扬州之北,因晋太傅谢安治水于此,人比于周之召伯,故地名“邵伯”(古召、邵通);又后人追思其德,立庙以祀之,故号为“甘棠”。文山先生因途经扬州城下,便想到“扬州鹤”、“邵伯棠”之典,他自然是把“扬州鹤”里的扬州当做宋时的扬州的。清乾隆间,李斗撰成《扬州画舫录》十八卷,备载扬州风物之盛,袁枚为其书作《序》曰:“嘻,余衰矣!以隔一衣带水,不能长至邗江登眺为憾。及得此书,卧而观之,方知闲居展卷,胜于骑鹤来游也。”随园老人因序《扬州画舫录》,而想到“骑鹤来游”之句,他当然也是把“骑鹤上扬州”里的扬州当成清代的扬州的。
但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中的扬州,原非指隋唐以后的扬州。在隋之前,今天叫做“扬州”的这个地方,乃被称作“广陵”或“江都”。正如南朝吴声西曲里的许多歌词所唱的“扬州”并非指今日之扬州一样,《懊
关于这一“历史的误会”,早已有人提出要订正了。如郑逸梅先生《艺林散叶》第4047条云: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此前人句也,诵者往往不求甚解,且以扬州即指今之扬州市而言。而李慈铭却谓扬州指建业,今之江宁府。六朝以扬州刺史,为宰相之职,故愿为扬州刺史,犹愿为宰相也。一欲贵,一欲富,一欲仙,皆指其极者而言。可知扬州,即今之南京市。
又,陈汝衡先生《“骑鹤上扬州”解》云:
经常在报刊上读到谈扬州园林的文章,认为扬州自古繁荣昌盛,并引用“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诗句,足见扬州早就为人所艳羡。……可是“骑鹤上扬州”里的扬州并非指现在的扬州市而言。“扬州”这一地名辖境,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变更。……三国时的吴国曾把扬州设在建业,即今之南京,而今天设在江都县境内的扬州乃是隋唐以来才确定下来的。……这些,我们还是搞清楚为好。
最近,曹道衡先生也有《漫话“骑鹤上扬州”》一文,说:
现在不少人引用这个故事,大抵用来说明扬州(指今江苏扬州市)是一个繁荣的好地方。其实这种说法包含着两种误解:首先,殷芸所说的“扬州”,并非现在的“扬州”,而是今南京市;其次,殷芸所谓“愿为扬州刺史”,主旨也不在说扬州繁华,而是指扬州刺史的地位尊贵。
就考证“扬州鹤”的本来意义而言,这几位先生的意见,的确非常之正确。南朝人之所谓“骑鹤上扬州”,自然只能是南朝时的扬州,而不能是隋唐以后的扬州。“上扬州”的“上”,也决不是“前往观光”的意思,而是“走马上任”的意思。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甫《解闷》:“商胡离别下扬州”——这里的“下扬州”,才真的是前往今日之扬州。“上扬州”与“下扬州”,一上一下之间,相差岂可以道里计!可惜多少年来,多少人们,,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将两个不同的“扬州”混成了一谈。凡欲研治中国文化者,难道不应该从这里汲取有益的教训吗?
不过我还想说的是,历史文化现象是复杂的,考据学大抵只能解释文化的“源”,而不能说明文化的“流”。“扶桑”一词的本义,有人考证是墨西哥,有人考证是新西兰,有人考证是苏北鲁南一带,但无法否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是指日本。“支那”一词的由.来,有人考证是秦,有人考证是荆,有人考证是丝或绮,但不能不承认在当今的世界上它就是指中国。鲁迅《送日本友人东渡回国》“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柳亚子《存殁口号》:“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原注:孙中山、毛润之。)如果依了考据家的意思去注解诗中的“扶桑”、“支那”,就一定会不知所云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我们最好在指出了它的谬误之后,还是采取承认现实的宽容态度。
对“扬州鹤”之说,亦应作如是观。象郁达夫在《扬州旧梦寄语堂》里说的:“写到这里,本来是可以搁笔了,……但我还想加上一个总结,以醒醒你的骑鹤上扬州的迷梦。”曹聚仁在《说扬州》里说的:“所谓‘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独照扬州,扬州是人间天堂。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是人生至乐。”还有象郭沫若为扬州史可法祠堂所写的楹联:“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林散之赠给扬州友人的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奇文与异气,美景不胜收。”——所有这里的“骑鹤”云云,都是指向今日的扬州哩!要说“考据”的话,似乎也应该把这些都“考据”一下才对。
以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再作一次如下的“订正”:“扬州鹤”中的扬州,最初固然是指江南的建业,但在后世的诗文里,在后人的心目中,它实际上是指江北的广陵。了解昨天的“故事”是必要的,明白今日的“时事”却更重要。
而且,我认为问题还不在于“扬州鹤”中的扬州是指什么地方,而在于这个广为人知的典故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就象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中谈到公孙龙的诡辞时所说的:“问题倒不在乎那些诡辞当作如何解释,而宁在乎那些诡辞究竟有怎样的社会意义。以何原因或用意而产生了那样的诡辞,倒是我们治历史的人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然面一般研究古代思想的朋友们,却偏偏不肯注意到这些上来。”
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无论“扬州鹤”里的“扬州”是指广陵还是金陵,它实际上是代表了想象中的人间最美妙的去处。所谓“腰缠”、“骑鹤”,不过是表达了人们对于一种理想中的极乐世界的渴望与追求罢了。——就这一点而言,“扬州鹤”中的“扬州”,确乎是指今日之扬州。
清褚人获《坚匏四集》卷一:
隋唐以后之扬州,秦汉以前之邯郸,皆大贾走集、笙歌粉黛繁华之地。古语云:“骑鹤上扬州”,以骑鹤为神仙事,而扬州又人间佳丽地也。
因此南明小朝廷的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诸藩,无不欲争夺扬州。“你占住繁华廿四桥,竹西明月夜吹箫;他也想隋堤柳下安营巢,不教你蕃厘观独夸琼花少。谁不羡扬州鹤背飘,妒杀你腰缠十万好,怕明日杀声咽断广陵涛。”(孔尚任《桃花扇》第十八出《争位》)扬州这“人间佳丽地”,竟使得南明重要支柱的江北四镇将领,置抗清的大业于不顾,而陷入自相残杀之中了。
“扬州鹤”的意义,从消极方面去理解是“贪得无餍”;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却是“不断追求”——追求富裕,追求长生,追求地位。难道金玉之宝只能供石崇、王恺们去斗富吗?难道不死之药只能让秦皇、汉武们去找寻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就不能给陈涉、吴广们也来做做吗?今《辞源》有“骑鹤上扬州”条,谓“形容一种妄想”,未免过于严肃;又《辞海》亦有“骑鹤上扬州”条,谓“比喻贪婪的妄想”,似乎更失之偏颇;曾见台湾《中文大辞典》里有“扬州之鹤”条,仅谓“喻欲多也”,庶几为持平之论。
然而奇怪的是,“骑鹤”的意思本是要成为天上的神仙,“腰缠”的意思却是要拥有人间的富贵;按理说,做了快活的神仙就不应该再迷恋红尘中的富贵了。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两句话,却偏偏把对于成仙的幻想和对于发财的渴望、对于当官的企求全部揉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社会心理的真实的一面。《红楼梦》里跛足道人唱的《好了歌》中有这样两句给人印象特别深的话:“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曹雪芹的这一创作思想,同“扬州鹤”的内涵恰好是相契合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总是希望人民奉行清心寡欲、安贫乐道、逆来顺受的人生哲学。“存天理,灭人欲”虽是宋代陋儒们的“发明”,但究其思想,却是纵贯了中国历史的古今的。孔夫子便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话(见《论语·述而》),还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见《论语·雍也》)。人的一切合理的欲望,似乎都是一种非份的奢求。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中,“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却以极富诱惑力的语言,大胆地宣称要上天入地,纵情享乐。这在那万马齐喑的社会里,也算得上是惊人的一声呐喊了——尽管它是以庸俗的面貌出现的。
正由于这个典故的感染力很强,所以人们不但在诗文中常常引用它,以委婉地表露内心的希求,它还被编成了戏曲。据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二载,清代三原双生曾撰《扬州鹤》传奇三卷四十出,原见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戏曲目》,今藏上海图书馆。又据《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八《快活三》条,云:
《快活三》,未知何人所作。所演蒋霆得妇事,见祝允明文,载在《纪录汇编》,因附会云霆作扬州太守,以票会银十万,其后与妇俱仙。盖采《太平广记》之说:有四人言志,一人欲贵,愿为扬州太守,一人欲富,愿腰缠十万贯;一人欲成仙,愿骑鹤升天;又一人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殆欲兼富贵神仙于一身也。作者因蒋霆得妇事,出于意外,遂缘饰成之,以快活之事凡三也。……既富且贵,又作神仙,故日《快活三》也。
关于《快活三》的本事,亦见明人凌
扬州既是一个人间的极乐世界,在民间也就流传了许多的口碑。如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谚(见洪迈《容斋随笔》卷九),意谓全国之盛数扬州第一,益州(今成都)第二。宋以后的扬州虽然大不如前了,但昨日的繁华记忆犹新,而且,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缘故吧,所以明代也有“扬州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俗语(见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八十回)。这与“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见施耐庵《水浒传》第六回)、“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见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十六回)可谓异曲同工了。要说扬州与梁园、长安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梁园为汉代梁孝王宴宾之所,长安为汉唐诸王朝立国之都——它们都充满了“王气”;唯独扬州,却完全是市井商民的天下。
扬州是这般的快活无比,故人皆向往之。以至张祜的一绝《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虽然全不避讳世人深忌的“死”字,却依然成了人人爱诵的名篇。扬州竟然不但是生的好地方,仿佛也成了死的好去处!于是,连“扬州死”也成了人生难得的幸事。《金瓶梅》第七十七回有一句话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黄金入柜,就是一场事了,哥的大阴骘。”这“黄金入柜”,便是说死了以后安葬在扬州的意思。《大明一统志》:“金柜山在扬州府南七里,山多葬地;谚云:‘葬于此者,如黄金入柜,故名。”
这一来,“扬州死”也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频频出现在诗人的笔下。明人黄周星《同诸子游上方寺》:“墓田虽好谁能死,桥上神仙不可寻。”清人卢见曾《留别扬州》:“为报先畴墓田在,人生未合死扬州。”近代思想家魏源的《扬州画舫曲》中,亦有“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只合死扬州”的句子。凡此,皆用“扬州死”之典。为了追求人生的快乐,宁愿以死为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敢。
然而扬州并不是真的天堂,象许多未曾到过扬州而只是遥遥地仰慕它的名声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好的。也有人穷死在扬州,如清代的伟大作家吴敬梓。吴敬梓是因穷愁所迫而从金陵来到扬州的,但他在扬州生活得并不快活。扬州慷慨赠送给他的礼物,只是“扬州死”。据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说,吴敬梓在扬州的最后日子里,最爱念诵的一句话便是“人生只合扬州死”,不料后来真的成了“诗衣食谶”。
近读清人诗,有吴嘉纪《过兵行》写道:“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椽屋。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里驰来如疾雨。东邻踏死三岁儿,西邻虏去双鬟女。……”写的是扬州屠城十年后的情况。又有张云
由此看来,对“扬州鹤”之说还需要再来一次“订正”:如同江南人爱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山东人爱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安徽人爱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广西人爱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四川人爱说“峨嵋天下秀,夔门天下险,剑阁天下雄,青城天下幽”一样,扬州人爱说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包含着很大的偏执、夸张、虚假、狂妄。
堂吉诃德在谈到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时说:
她头发是黄金,脑门子是极乐净土,眉毛是虹,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珍珠,脖子是雪花石膏,胸脯是大理石,手是象牙,皮肤是皎洁的白雪……(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十三章)
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姑娘,长得跟男人一样,“身子粗壮,胸口还长着毛呢。”
扬州好象是杜尔西内娅。面梦想着骑“扬州鹤”的人呢?对不起,真好象是那位爱白日做梦的骑士了。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扬州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