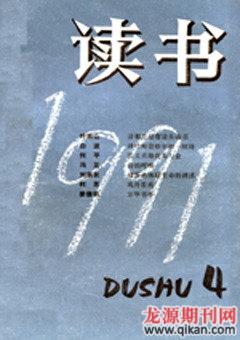1991年第4期,总第145期——编辑室日志
上月《编辑室日志》,提到《读书》的一个无可奈何的“特色”:无序。其实,杂志诚然可有“杂”而无序的一面,而作为一项事业,又应有“有序”的另一面。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王作进先生来信,加强了我们这个认识。
王先生信上说:“在十二期末尾读到读者购书不易之苦恼。岂只一位,我等皆然。为购三联版《美国山川风物四记》等书,几次托在京同事找寻,不得如愿。今见有郑州分销店可托,不禁喜出望外,即打电话0371—332127。尽管回话此书售缺,但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十分客气地表示歉意后,要下了我的地址,表示以后一定要寄书目订单来。我忙不迭地谢谢,他却说‘还得谢谢您!所有这些,犹如寒冬里的暖流。”
感谢郑州分销店我们未曾谋面的张先生,您的有条理的工作大大地弥补了我们的不足。
更有一件事提醒我们不可事事“无序”,这便是去年十一期吕叔湘先生的《剪不断,理还乱》一文,及其反响。
一二个月来,关于此文的来信不少,有不少是批评《读书》自己就是“剪不断,理还乱”,指出杂志上错字、病句连篇,证据凿凿。关于错字的来信,是每月来信中较多的,其次则是批评印刷质量下降。《读书》之错字,确已到了“理还乱”的地步。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首宪云先生来信说,读了吕先生的文章,“觉得是一把火,把我的脸烧得好烫;也像一根针,刺得我浑身发痛。一字一句直似冲我而来——也许是‘作贼心虚吧。”“说句心里话,吕老先生批评的是。”
这也是我们在编发吕文时的心情。
因受到批评而对吕叔湘先生表示谢忱的还有一位北京读者黄集伟先生。吕文中批评了“一本档次不低的刊物开卷第一面上”的一些病句,黄先生说:“我愿意告诉吕先生,那篇文章就是我写的,那些被吕先生客客气气归纳为‘不管妥贴与否,胡乱堆砌的病句,也一并都是我为汉字汉文那理不清的糊涂帐所作的‘奉献。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吕先生竟是除去我中学时代国文教师外认真指出我写字作文好堆砌毛病唯一的人。这一次我一点儿不悚然。这一次我开始明白‘空谷足音的另一层含义和它会给人以怎样的滋养。”
《读书》有幸,常常能发表一些前辈的文字,而受到读者的欢迎。甘肃读者周普生先生来信说,“当许多青年人因此或因被受了些挫折,以致竟至于
编辑部同仁这个月(九一年一月)太忙,没有举行例行的“服务日”活动,但也办了一件并非没意义的事情:为漫画界的前辈丁聪老人祝寿,向我们这个编辑大集体的七十八岁高寿的家长致意。一位美国批评家谈到《纽约客》杂志时说过:“欣赏《纽约客》杂志里的文章不能算聪明,但如能真正体会《纽约客》里所画卡通的意义,才是真正聪明过人的。《纽约客》不是我们的范本,我们也判定不了这句话的可靠性。但所说关于杂志中文与画的关系,却是我们竭力追求的。准此,我们理出一些中国的真正聪明过人的读者的来信,送给老丁留念。
编辑室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