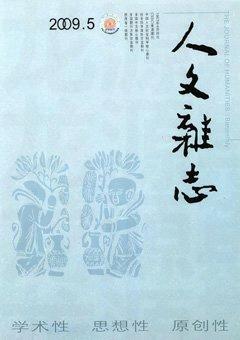法家对黄学的批判继承
赵小雷
内容提要 道家论政的主旨是因任自然的无为而治,法家论政的主旨则是以法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完善,采取的是循名责实的干涉主义;而黄学则是道、法之间的重要的过渡环节,正是黄学的“道生法”、“抱道执度”、“循名复一”以及上下有别的王术观念等,使法家实现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即上无为而下有为。黄学的一些理论命题及观念构成了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法家 黄学 道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4-0184-04
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法家的基本特征是“主刑名而本黄老”,指出了法家思想的理论来源。但是道家论政的主旨是因任自然的无为而治,而法家论政则试图以法为中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采取的是干涉主义的有为之治。这抽象之自然法如何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法,正是由于黄学的发现才补上了这一环节的空缺,陈鼓应认为:“在老子的‘无为与慎到以降的‘君无为而臣有为之间,必须有一个理论的中介,这就是《黄帝四经》”①。但是何为黄学则不甚明了,一则由于黄学之作不现于世,二则由于《庄子》的退尧舜而祖黄帝,后世遂以黄老指称道家,即老庄之学,三则由于汉初所谓的黄老之治,似更多的偏向于老学,因而以往所谓的黄学,多视为道家的老庄之学。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的发现,则为黄学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唐兰先生认为这附抄于帛书《老子》乙本之前的古佚书,即是 《汉志》首列的黄学著作《黄帝四经》②,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③。其成书年代大多数学者认同战国早中期之说④,此说正与《史记》所称慎到、申子、韩非等人归本于黄老的记载相印证。正是黄学以它的“道生法”、“抱道执度”、“循名复一”以及上下有别的王术观念等命题,从而使法家最终实现了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想,即上无为而下有为。
一、黄学对法家的影响
从《黄帝四经》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黄学正处于前期道家,即老子与法家的中间环节上,法家对道家的继承和发展正是经由黄学的过渡而最后完成的,呈现出老子→黄学→法家的发展轨迹。具体而言,黄学对法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道为法提供社会性合理依据
老子论政试图以天道来校正人道,但它的天道观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然法则,尚不能直接运用于社会。而他的后学——黄学则不但言道而且论法,从而使抽象的自然法则向具体的社会法则过渡,而所用的武器正是被老子所反对的规矩权衡。黄学在自然天道观上同老子是一致的,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最初规定,“恒先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大迥无名。天弗能复,地弗能载……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一度不变,通适蚑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四经•道原》)。可见黄学的道,仍然是先于万物,而生万物的独立实体,它无形,无名,是世界最初的和唯一的“一”,即宇宙的本源。因而黄学在论政治时,仍然主张要执道而治,把道视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终根据,以及评价社会治乱的唯一标准。所不同者,在于它将道转变成了法,明确提出了“道生法”的命题,“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称以权衡,参以天当……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己具,则治而制之矣”(《四经•经法•道法》)。道是一个独立的客体标准,它是公正无私的,圣人秉此而设之法亦具有道的这种性质,只要建立了这个独立公正的法制标准,社会就会得到规范。
* 陕西省教育厅2007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7JK126)
①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3页。
② 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③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④ 张增田:《<黄老帛书>研究综述》——载《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16页。
黄学用“理” 这个概念解决由道而法的转化过程。“物各合其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经法•论》)。道具体化为万物的理,理即道的具体显现。它一方面克服了道的抽象性,另一方面则保留了它的客观性。道既有本源性又有规律性,而理在此即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法则,掌握了这个规律来治理天下则万举不失理,此即谓之“有道”。
道与法的共性即在于它们的客观性,黄学因此主张圣人治理天下,就要以法为标准,而反对政由心出的人治主义,所谓规矩、绳墨、权衡、斗石即是道的显现,它们的共同特征即不因人而异的客观性、标准性。量即客观标准,即法,“治”即统治、治理,“制之”即制度化,故立法就能使社会的治理制度化。“世恒不可释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祸”(《四经•称》), “用我”则政由已出,政从已出即天下不一,天下不一,则“是以生祸”。后来法家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规矩、绳墨、权衡、斗石的重要性,就是为了以其来比喻法的客观标准性。这正是从黄老之学那里来的,因为老庄之学的道家是坚决反对规矩绳墨、权衡斗石的。因此,“抱道执度”不仅概括了黄学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而且对法家的影响亦正在于此,当然,正因为黄学是由道而法的过渡环节,它的客观的法制理论还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也讲德治、慈爱,主张刑德并用,另一方面它同时还主张“亲亲而兴贤”(《十六经•立命》), 提倡圣贤之治。由此,它也就没有以法为中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从而真正实现客观的法治,这些还要由法家去完成。法家必须再来一次否定,即扬弃,才能真正实现客观之治。
第二、循名究理”的刑名学说
黄学提出以循名究理的方法来治天下。道是抽象的独立实体,但它既然要化为万物,就必有一定的形,既有形就有名。名作为概念必然概括了某一类事物的本质规定,“道无始而有应……有物将来,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 (《四经•称》),亦即道的独特显现,圣人治国也一样,要确定社会的等级秩序,即赋之以形,然后授之以名,形名既已确定,则治理起来就方便了。只要按名的规定来监督管理就成,“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形名。形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经法•论约》)。这正是以自然界的秩序来规定社会秩序,以体现自然法则之名来解释社会秩序之名,形名相称,就是天下有道。形即人在社会上应处的实际地位,名即对此的称谓及有关规定。社会是复杂的,而法的标准则是划一的,其名也是划一的,执此之一,就能驭彼之多,并使之复归于一。“抱道执度”就是由道而法,“循名复一”就是以法治国,由此可见黄学的形名学说,正是其法治思想的方法论保证。不过黄学的形名学说还是一种治理社会的原则,还很不具体。后来法家则在此基础上将它发展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第三、“上下有等”、“尊主卑臣”的王术观念
老庄虽然也讲圣王之治,但由于其自然天道观的抽象性,故主张“天放”的无为而治,反对对臣民的人为控制。黄学在将其转化为法的同时,扩大了道的社会性,主张尊主卑臣的贵贱等级制,并且以父子关系来比拟君臣关系。黄学的等级制正是它以天道治人道的表现,天道有高低之别,人道有贵贱之分。故君臣和父子易位都是失道,如《四经》云:“为人主,南面而立,臣肃静,不敢蔽其主,下比顺,不敢蔽其上……天下无敌” (《经法•六分》)。不单是君臣,其他的社会成员之间也要有等级贵贱之分,君臣、父子、男女、妻妾、贤不肖等等都得有固定的位置。并且这种等级关系还是天道自然而成不可改变的,所谓“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经法•道法》)。在黄学看来贵贱失序即是亡征,对此法家是完全继承了这一思想,《慎子•德立》篇就讲 “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乱矣。失君必乱。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乱矣。失父必乱。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对此更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此外《四经》还明确提出了“王术”的概念,以为虽然有了完善的政治制度,但不能谨慎的推行它,仍然不能王天下,“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三者参用之,然后而有天下矣。为人主, 南面而立。臣肃敬,不敢蔽其主。下比顺,不敢蔽其上。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文德究於轻细,武刃於当罪,王之本也。然而不知王术,不王天下。知王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荒,饮食喜乐而不湎康,玩好嬛好而不惑心,俱与天下用兵,费少而有功,战胜而令行。……不知王术者,驱骋驰猎则禽荒,饮食喜乐而湎康,玩好嬛好则惑心,俱与天下用兵,费多而无功,战胜而令不行(《经法•六分》)。在此王术的内容只是勤政,不知王术即是耽于玩好享乐,即荒政,它与后来法家的术,即君主的统治计谋有所不同,在此也表明黄老之学对人治的肯定,而在法家看来只要建立起完整的制度,人主者尽可以“驱骋驰猎则禽荒,饮食喜乐而湎康”而天下大治,然而对人主的统治手段的重视还是给法家以重要的启示。在此,王术的概念加上尊主卑臣的内容,后来被法家改造成了一种完整的驭臣之术。
三、法家对黄学的批判继承
道法两家虽然一倡无为而治之说,一主循名责实之论,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试图建立一套客观的价值标准,以否定政由心出的人治主义政治。所不同者,在于道家否定现实而归于自然的天放;而法家则承认现状而归于社会的法制。法家对黄学的批判继承就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完成了由道而法的转化,以规矩权衡将自然的道改造成了社会的法
慎到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论命题,如“寄治乱于法术……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下,不伤情性……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慎子•佚文》),“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佚文》),在此道→权衡→法的演进轨迹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慎到就坚决反对“诛赏予夺,从君心出”(《慎子•君人》)的政治偶然性,认为圣人治国以法,正如称轻重以权衡一样,则万不失矣,亦即如万物归于道一样。
韩非则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指出世界万物都有它不得不然的法则,即道,人类社会也一样,即法,圣人治国以法,则正如万物秉道而生一样。如“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道是世界万物的根本规定,把握了道则万物无所隐其形,匿其迹,世界是无限的杂多,而道则是一,一生万物,万物体现着一。把握了道就能执一以驭多。同样,人类社会也是无限的杂多,然其中也必然隐含着一个本质的规定,这就是法,法即是一。人各异理,而道,即法则“尽稽”万人之理,亦即用一个客观的统一标准来规范社会,“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韩非子•解老》)。法即是道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一个规矩可以画出无数个方圆来,法即是人类社会的规矩,方圆即是理想的政治秩序。
第二、发展了黄学的刑名学说
法家将黄学的刑名学说改造成为一套完整的考察官吏及规范社会的政治制度,即循名责实。所谓循名责实就是以法律为准绳,根据个人所处的地位,即名,来考核其所应负的责任,即实。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韩非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因而任之,使自事之……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脩其形(顾广圻曰:“脩当作循”),形名参同,用其所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韩非子•扬权》)韩非此论充分概括了法家循名责实、无为而治的思想,由此也正显示出它同黄学的渊源。申不害对《四经》的抱道执度作了很好的发挥,“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当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大体》)概括地讲就是名正者治,名奇者乱,圣人治天下不亲躬于小事,而要抓纲,即以名责实。名为有限之形式,却包含者无限的内容,故要执一以驭多,就只有循名而责实了。
法家思想的中心就是强调对王权的加强,实际上即是对官吏的治理,圣君治国在于抓根本,如此则纲举目张,而“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只要官吏廉洁清明,则老百姓之善者自然奉公守法,其恶者亦不敢为非,而国家自然也就太平无事。但是君主只有一人,如何来实现对臣下的控制以达到上述目标呢?韩非认为“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韩非子•二柄》)人主好贤则臣下就会投君所好以获得高官厚禄,况且贤不贤人君又不得一一详考,无非是以誉听之,而臣下则比周结党以蔽其君,君蔽于上,则臣贪于下以渔民,国故不治。举能亦然,之所以是“妄举”就是由于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评判,无非是朝中有人好作官,韩非正是竭力要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其具体办法就是“循名而责实”,就是根据你的官职,即名来考核你所应负的责任,即事,以工作结果来评判你是否尽到了责任,即功,名、事、功相当则赏,反之则罚。此正是御臣之术,韩子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这里的名实即指官职和应负的责任,所谓“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周合刑名,民乃守职,”(《韩非子•扬权》)各人的职位及职责既已明确,则君自不必亲躬于具体的事务,即“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韩非子•扬权》)。
为此法家对黄学的抱道执度,循名复一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不但具体化了黄学的形名理论,而且给以了实施的保证,黄学的形名思想还有许多道家的自然法则性质,只是强调君主要以自然法则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它虽然也强调法的作用,但这两者还没有很好的统一起来。法家则使这两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的形名理论完全具体化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明确表明“名”即职位,“实”即其职责,以名责实,故能治官。在此由形名,到名实的发展正是法家对黄学的改造,在黄学那里形即事物本身,名即事物的称谓,因而它的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就缺乏一个实现的保证,法家则以社会效果使其具体化了,责实就是视其社会效果如何。黄学也知道名不正则乱,但它没有解决如何使其归于正的问题。法家则以法的标准,以赏罚为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君主实现了执一以驭多的无为而治。
第三、将王术概念系统化成了循名责实的驭臣之术
过去称韩非的驭臣之术是来源于申不害的,其实申子的术也是受黄学影响的结果。王术在黄学那里主要还只是君主勤政与否的个人操守,所谓有术之君,即不耽于玩乐而勤于政的君主,反之则为无术之君(《经法•六分》),在黄学那里尊主卑臣的实际内容与王术的概念还不相统一。申不害则将其统一了起来,认为君主要制御臣下,就得隐蔽自己的意图使其高深莫测,目的即在于专君权。但申子的术还只是君主个人的一些小伎俩,故韩非批判他,只知术而不知法,因而使韩国“托万剩之劲,十七年而不至于霸”(《韩非子•定法》)。韩
非吸取了申不害的教训,对其循名责实的君人之术,以法为中心进行了一番改造,从而形成一种客观的政治制度,由此韩非敢夸口:“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治理国家而单凭个人的小权术,是根本靠不住的。要之,黄学的王术概念加上尊主卑臣的内容,经过韩非的改造,遂成了一套完整的考核官吏的规章制度。
总而言之,法家敢于面对现实,一方面承认人对富贵的追求的合理性,从而解决了使在下者自为的动力问题;另一方面则以法制来规范社会,从而为在上者的无为而治提供了保证,至此,道家的上无为而下有为的政治理想才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法家的政治理论是道家的抽象原则的具体化。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