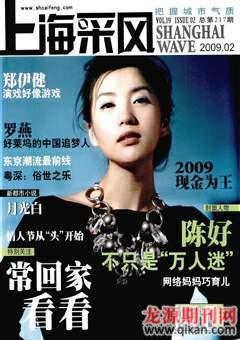孤独的启示
疯行水上
“一个人的电影”作为《收获》杂志的专栏,从2006年刊载伊始,迄今未止。现在结集付梓的这本小书囊括2006至2008两年的全部文章,只是专栏的阶段性总结。2008年之后,书写对象开始向香港影人转移。照此以往,若假以时日,华语电影的精英力量在专栏悉数登场,其所展现的全景与盛况,较今日将不可同日而语。
设立专栏的初衷我无从知晓,但专栏本身的出现的确是恰逢其时。电影作为大文学格局中的后起之秀,正在成为“后物欲时代”重要的文化消费。它不断挑战我们有限的视觉经验,丰富我们的表达习惯,甚至帮助消化我们“过剩”的能量与时间。正如同杨德昌的《一一》中讲的,“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我们从电影中得到的生活经验比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double就对了”。
我们是个有电影传统的民族,旧上海,即使是兵祸横行的年代,仍然有人拍出那么多的经典作品,为我们留下华语电影的第一笔遗产。从格非、李陀、毛尖等人的文章中,就能发现这种传统,发现在包含深情的文字下面曾被影像焐热的灵魂。虽然每个人电影记忆不尽相同,但传统从未中断。格非的“乡村电影”时代才怅然结束,李陀的“青春祭”才刚刚开始,随后,毛尖的“录像厅”时光又填满了忧郁的青春期。电影的世界是那么大,好像无论怎么成长,你都不能触及它的边界,看穿它的深邃。那些影像世界的后来者,会在他们的文字中看到自己的模样,基于对电影同样的热爱,甚至会理解一个你从未经历过的时代。
与膜拜者的情感书写相比,书中随后的导演访谈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严肃的话题,即电影的本质与现状。本质和现状,两者是关联性的,观众对电影本质的理解直接造成电影今日的现状,而今天的现状就是,好莱坞电影控制着绝大部分观众资源。我无意对电影的文艺和商业两种气质的对立老生常谈,但好莱坞电影的扩张的确在破坏着电影的多元化。观众在好莱坞电影中形成的单极认识,又反过来对华语电影进行苍白的解读,这一点,“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可谓深受其害。贾樟柯的《任逍遥》曾在戛纳被本国记者指责为“一个谎言”,张艺谋和娄烨也都表示,他们不在乎国内的评论,甚至连章子怡都露骨地说,不喜欢国内的影迷。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影人与影迷的隔阂,是什么让我们对诞生于身边的影像心怀陌生?作为影迷,我更想从自身寻找原因。
陈伟文对娄烨的那篇《全世界的导演都在解决时间问题》的访谈,之前就在《收获》上读过,拿到书之后又看了两遍。虽然我对文中的专业词汇一知半解,但它对我的吸引也正在于此。娄烨首先把电影还原成一个技术问题,作为国内最注重技巧问题的导演,他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并不是精通技术才可以解读电影,但观影者至少要具备基本的常识,娄烨说,“如果你的语言非常窄的话,它影响你对世界的理解”,常识就是观众的“语言”,它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电影。在不具备电影鉴赏训练的观众眼里,电影和文学一样,没有独立的艺术价值;或者还有人把电影看作是娱乐事件。当观众还在对《颐和园》的意识形态问题纠缠不清,徘徊在演员裸露尺度的下半身话题时,娄烨已经大大超越了观众赋予他的认识。不看访谈,我不会了解娄烨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图景,也就不会重头反思他的《苏州河》、《紫蝴蝶》。
中国的电影人是一个孤独的群体,他们在记录和反思我们的生活,却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和关注,他们在近乎绝望地坚持着,就像书的名字:“一个人的电影”。但他们站出来说话是对的,这些访谈在一定程度上廓清我们对电影似是而非的看法,哪怕是有限的;习惯的改变就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
《一个人的电影》:格非 贾樟柯等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定价: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