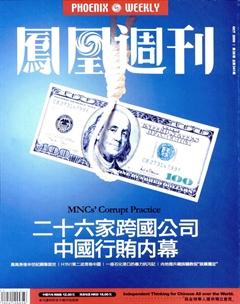爱德华·R·默罗反击麦卡锡的勇者
陈安
“Thls…is London.”——如今八九十岁的美国老人们,依然清楚记得这个电台呼号,其重音放在“This”上,然后稍作停顿,再接着说“is London”。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a R.Murrow)从伦敦发出的呼号。

从1937年至1946年,美国听众一直可以听到默罗发自伦敦的声音,听他及时报告欧洲大陆怎样一步步走向了战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怎样吞并了奥地利,《慕尼黑协定》怎样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德国,德寇如何狂轰滥炸伦敦……正是在那炮火连天的环境中,在严酷艰险的战争条件下,默罗发出了沉勇的呼号,“这——是伦敦”及其“大不列颠之战”系列广播报道,有力地震响在美国听众的耳畔,牵动了亿万人的心。
战后,默罗回国继续从事他的新闻广播工作,由于有了电视,他这个先前广播节目《现在就听》的播音员就成了电视节目《现在就看》的制作人和主持人。作为记者,默罗的文字简明、平实,喜用有力的积极动词。作为播音员,他的语调动人,能激起听众的热情。他把新闻工作视为神圣的职责,要求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准确无误,而且永远公正。
1954年3月的一个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节目轰动了整个美国,使那个名叫约瑟夫·R·麦卡锡的参议员声名狼藉,而默罗沉勇的声音又一次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今,那声音已经很久远了,却依然清晰可闻,甚至还出现在一部新电影中。那部影片的名字就是默罗留下的另一句像“这是伦敦”一样有魅力的广播结束语:《晚安,好运》
(Good Night,and Good Luck)。
成为麦卡锡之流的追查对象
爱德华·R·默罗1908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县一个贵格会教徒家庭,责格会这个基督教教派以信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注重心灵宁静著称。他是这家三兄弟中的老幺,他们的血统是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混合。他生下来时,他家住的是原木小木屋,没有电,没有抽水马桶.一家人靠种玉米和牧草,一年挣个几百美元维生。

爱德华·默罗(右)和杜鲁门,摄于1950年代初。
默罗6岁时,全家迁居华盛顿州离加拿大很近的布兰查德。他在中学里就显示了口才,是学校辩论队里的佼佼者。进华盛顿州立大学后,最终选的专业是“演说”。他在学校政治活动中颇为活跃,有一次在全美学生联合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敦促大学同学们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结果当选联合会主席。1930年从学校一毕业,他就到了他向往已久、政治和文化生活都很活跃的纽约。
在纽约,他有4年任职于国际教育研究院,协助安置从德国流亡来的著名学者(主要是犹太人),并参与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35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先在欧洲、后在美国的色彩斑斓的广播电视生涯。
战后从欧洲回国之后,默罗逐渐感受到了美国与苏联之间互相对峙、互相敌视的“冷战”气氛,尤其是从这气氛中冒出来的那个国会参议员麦卡锡,更叫他侧目而视。这个参议员是个地道的政治投机分子和骗子,他谎说自己在大战中参加过战斗,受了腿伤,其实他根本没有打过仗,腿伤是他酗酒后从梯子上摔下来造成的。他接受贿赂,为纳粹战犯辩护。他以诽谤别人为乐,总想置自己的政敌于死地。
就是这个麦卡锡在1950年的一次演讲中声称,他手中握有国务院内205名“已知的共产党员”名单。后来他又周游全国,发表许多次煽动性的反共演讲。他指称民主党等于共产党,谴责罗斯福把中国和波兰出卖给苏联,质疑前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是否忠于国家,指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是“最高级俄国间谍”,等等。恐怖的反共反民主的麦卡锡时期就此开始了。那是一种弥漫全国的“红色恐怖”,似乎到处是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到处是不穿军装的左翼游击队员,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万马齐喑。这场追查从事所谓“颠覆活动”的共产党人的政治运动,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起初针对政府部门,后来扩至军队,又遍及民主进步人士。其手段之一是立下所谓“交往罪”,给只是认识个别共产党人或同意共产党某些观点的人统统扣上“共产党”帽子。
当时杜鲁门政府对外的冷战政策、对内的反共宣传和对联邦雇员的忠诚调查,还有那场朝鲜战争,为麦卡锡主义的兴风作浪提供了政治气候,而杜鲁门总统最后也终于尝到了麦卡锡歇斯底里反其所造成的恶果,不得不感慨道: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和耻辱。”
默罗也是麦卡锡之流追查的对象,因为他曾敢于在电视节目中报道米罗·拉杜洛维奇上尉的冤案。拉杜洛维奇原是空军后备队一名普通的气象员,却只因他父亲和姐姐“持有激进政治观点”而被空军开除了。他被要挟说,如果他能公开声明断绝他与其父亲和姐姐的关系,他还可以恢复他的职务和军衔。但他回答说,这不是他所理解的“美国方式”,并明确表示拒绝“断绝血缘关系”。默罗对此案十分关注,怀着气愤心情制作并播出了以此案为中心、揭示美国政治黑暗面的电视节目。他说:“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整个领域内,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只会我行我素。这不能怪罪于马林科夫、毛泽东,甚或我们的盟国。”

1954年1月19日,爱德华·默罗(左)与电视节目资深编辑比尔·汤普森在一起。
在政治迫害面前坚守道德底线
麦卡锡他们寻求报复的机会到了。且看他们如何将欲加之罪加在默罗身上:1935年初赫斯特报系的某份报纸,在头版刊登一幅摄于莫斯科的照片,并发布了国际教育研究院出资主持美、苏教授之间暑期学术交流活动的消息。当时任职于该研究院的26岁的默罗刚开始崭露头角,赫斯特报纸在这则“揭露”研究院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研讨会的新闻中提到了爱德华·R·默罗的名字。
莫斯科!那还了得,对麦卡锡之流来说,这就够了。15年以前的一则新闻,对他们来说,显然是“铁证”。他们散布说:“默罗的名字列在苏联工资发送名单上。”何以见得?麦卡锡手下一名调查人员说:“国际教育研究院要通过苏联学生交流组织VOKS来安排活动,VOKS支付有关的经费,这就是说,国际教育研究院和默罗被放在了苏联工资发送名单上。”默罗的一个同事问那名调查人员,他是否可以把他说的这些情况告诉默罗本人,那名调查员答道:“我不是说默罗本人就是共产党。”接着他用当时盛行的追查共产党员之道——“鸭子考查法”说:“要是谁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他就是鸭子。”
当时大批美国人都成了“鸭子”。其中不少知识分子在被当成“鸭子”后显示了正直、无畏的品格。如著名戏剧家阿瑟·密勒,曾与文化界左派人士、共产党员有所接触,就给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盯上了,被他们传讯,要他交代他认识的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艺术家。密勒镇定自若,面无惧色,决不做告密者,没有提供任何人的名字,结果被判犯有藐视国会罪,还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其名作《推销员之死》由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拍成电影后,右翼分子扬言要冲击放映这部影片的电影院,哥伦比亚公司害怕事情闹大,就劝密勒在一份反共宣言上签字,他义正词严地说:“我拒绝作任何此类声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有辱人格。”他后来创作的剧本《坩埚》(亦译《塞勒姆女巫》)就是借古讽今,通过再现17世纪90年代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驱巫案来讽喻并控诉麦卡锡主义对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
当然,知识分子之中也有软骨头,有告密者。如好莱坞著名导演伊利亚·卡赞就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报了16名其产党员的名字,他们大多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事隔很久,人们依然不能原谅他的这种卑怯行为。当他在1999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接受终身成就奖时,许多人在场外举牌示威,抗议把这个奖授予一个曾经出卖朋友、出卖演艺界同事从而毁了他们一生的人。
爱德华·R·默罗则像密勒一样,在政治迫害面前坚守道德底线,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当他看到报上那幅“莫斯科研讨会”照片时,他确实也流露出紧张、恐惧神色,令其同事感觉到,麦卡锡主义危害整个国家灵魂的毒素也侵蚀到了默罗的灵魂。但是第二天,他脸上就再也没有因恐怖而浮现的苍白,他的同事们看到的是他似乎要张嘴大声咀嚼一头活熊的神态。他反复说着一句话:“现在的问题是我何时来反对这些家伙?”大家觉得,当时强忍着愤怒的默罗看起来真有点儿咄咄逼人。
默罗在严肃思考,思考着麦卡锡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思考着人们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他对同事们说:“我在想,我希望能教给我儿子的就是讲真话,不怕任何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民要有知晓、说话和思考的权利,还加上立法的神圣性。否则,这就不是美国。我们不应该把不同政见和不忠诚混为一谈。”
反击麦卡锡的电视节目进入了最后剪辑阶段。是否该播出了?究竟要不要播出?新闻报道小组成员们犹豫起来,明显地流露出了害怕情绪。就在此时,默罗说了两句令大伙儿惊醒的话:“这间屋子里可就有恐怖气氛啊。请注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恐吓整个国家,除非我们大家都是他的帮凶。”有人问他将在节目里说些什么,他答道:“假如我们中间谁也没有读过所谓‘危险的书,没有一个所谓‘持异议的朋友,从未参加过主张‘改变的组织,那我们就都是麦卡锡所需要的那种人。”
默罗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麦卡锡”节目播出前,他还对其同事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走路时将不再有一阵阵恐惧,我们将不再为恐惧所驱使进入一个非理性时代,如果我们能深挖我们的历史和教训,记住我们不是怯懦者的后裔,我们不是那种害怕写、说和交往,在人心惶惶时刻害怕维护正义事业的人的后代。我们可以否定我们的传统和历史,但我们不能逃脱对由此所造成的后果的责任。一个共和国公民不能摈弃他的责任。”
反击麦卡锡
1954年3月9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晚上,默罗终于把手中尖利的矛掷向了笼罩全国的恐怖气氛,掷向了麦卡锡,在电视节目中公开揭露和批判这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参议员。此节目的特色是用麦卡锡本人的讲话录音和图片来说话、来表演,让观众亲耳听一听他怎样对人威胁利诱,亲眼看一看他怎样上窜下跳。在每个片段前后,默罗都上镜头加以说明或评论。
其中比较长的一个片段是麦卡锡亲自对国务院雇员哈里斯的询问,不,准确地说,是审讯。哈里斯在20多年前当学生时写过一本政治观点比较激进的书,结果学校勒令他退学,为此美国公民自由权联盟曾委派一名律师为他辩护。麦卡锡从哈里斯的姓名、学校问起,一步一步追问到他写的书、他的辩护律师,然后对他狠狠地说了两遍:“你知道不知道公民自由权联盟是被列为共产党的前沿阵地,是为共产党办事的?!”就这样,哈里斯不得不马上向国务院递交了辞职书,麦卡锡得意地称之为“一大胜利”。其实,美国公民自由权联盟是一个旨在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超党派组织,尤其关心民意自由表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履行正当法律手续等重大问题,而麦卡锡所蔑视、所践踏的正是公民的自由权利。
默罗知道他的电视节目足以让观众看清麦卡锡的真面目,而同时他也想让观众知道,这场反共反民主活动究竟是谁之罪。他说,这不完全是麦卡锡的罪,麦卡锡并没有创造这个恐怖局面,而是利用这个恐怖局面并将之推向极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这两个总统都难辞其咎。在这个节目里,默罗编入了艾森豪威尔的谈话,这名正在竞选总统的五星上将说,他当选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清除行政部门里的颠覆分子和不忠诚分子,他说他“发誓”一定这样做。然后,默罗又编入了麦卡锡与艾森豪威尔晤面后的谈话,麦卡锡高喊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并将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事实上,若无有力的政治背景,麦卡锡能如此为所欲为、猖獗一时吗?
还应一提的是,这个“麦卡锡”专题节目的一大笔报纸广告费是默罗及《现在就看》另一个制作人弗兰德利自己掏的钱,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允许他们用公司的钱来做公开宣传,甚至不能用公司的标识做广告。
这个电视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更大的反麦卡锡主义声浪,并被视为美国电视广播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许多书信、电报和电话涌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在街上,卡车司机们把车开到默罗跟前,朝他喊道:“好节目啊,爱德!好节目啊,爱德!”
默罗给了麦卡锡也上《现在就看》节目来回应对他的批判的机会。三周后,麦卡锡上了电视,却只能为他已经狼藉的名声雪上加霜而已。
2005年,在默罗的“麦卡锡”节目播出整整50年之后,在默罗去世整整40年(他因吸烟太多罹患肺癌卒于1965年)之后,回顾默罗与麦卡锡之间这场斗争的电影《晚安,好运》问世了。原来拍摄的是彩色片,供放映时有意改成了黑白片,因为黑白片更有历史感和真实感,而这个民主与反民主、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决斗的故事也确实是真正的历史。影片由乔治·克鲁尼导演,获得奥斯卡6项最佳奖提名。
有一篇影评写道:“这部电影不仅是对麦卡锡的抨击,而且让我们学习默罗及其新闻报道小组,知道在历史重要关头记者们应如何表现自己。默罗在发布新闻过程中一贯的诚实和正直决定了他是美国新闻史,甚或世界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