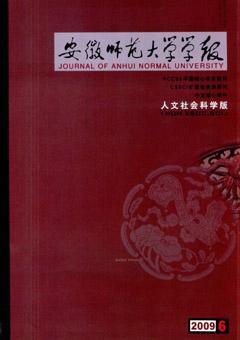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跨文化解读
吴越民 余 洁
关键词: 大众传媒;女性形象;文化内涵
摘 要: 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有其深沉的文化内涵。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象征反映了性别文化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及性别制度作用于时代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它们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图分类号: G206.2,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6072306
Intercultural Decoding of Female Images in Mass Media
WU Yuemin, YU J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China)
Key words: mass media; female image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mass media embodie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of female images in mass media reflect some typical features of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culture on social life and gender system on contemporary culture. Th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are indispensably related to different social lives and valu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在现代社会,报纸、广播、影视和网络等大众传媒对受众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从女性角度来看大众媒介,似乎也成为当今的一种新学术动向,它主要在于探讨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和角色,即女性在媒介中是否受歧视和压迫,媒介是怎样塑造女性形象的。
在今天,传媒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塑造已为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尽管今天的女性在家庭角色、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皆有跨时代的进步,唯独在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形象与角色,仍然处于被异化状况。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跨文化的角度分析和研究这种世界范围内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建构的深沉文化因素。
一、中西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媒介女性形象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用“阴阳”概念来解释男女两性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更多的是从宗教的角度来阐释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将女性视为男权社会的异己力量,导致男女之间深存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文明伊始,女性就被迫站在了与男性截然对立和“他者(the other)”的地位上[1]230。基督教文化对女性有两个重大的负面评价:第一是将女性视为万恶之源。在《圣经》的《创世纪》中,可以找到“厌女症”的根源,即认为人类最初的堕落是因为夏娃偷吃禁果所致,她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罪魁祸首。对女性的第二个负面评价是——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她存在的理由是给男人做伴,上帝创造女人,仅仅因为那个男人“独居不好”。[2]西方历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曾有过贬低女性的言辞。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毕达哥拉斯则说:“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你是我的法则。”尼采则将女人的一切归于生育:“我但愿男人和女人是如此:男人适于战争,女人适于生育。”他还说:“女人身上藏着一个奴隶与一个暴君。”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习惯将女人称作“我的爱兽”,“爱兽”符号指向的是文化秩序中的野人,未开化种族和所有异质群体。此外,卢梭、叔本华等人均对女性有贬抑甚至污辱性的言辞。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在媒介文本中再现时,有许多是明显涉及歧视的字眼,如以涉及不贞、淫荡的特定字眼骂人,以非人性的字眼、宠物、男性的附属品来形容女性。在美国的电视剧中,女性形象就存在类型化的问题。她们要么被塑造为带有落后性别意识的温良恭俭让逆来顺受的旧式女性;要么是做美容、逛商场、买首饰的所谓时尚女性;再有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和婚恋生活放荡不羁的另类女性。电视上的女性往往是年轻、漂亮、苗条、被动、软弱、没主见、依赖别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妆打扮上。例如,在很受欢迎的情景喜剧《甜心俏佳人》中,我们看到安妮主要是在法庭之外以一种十分传统的女人形象生活着,比如需要男人(“没有男人我觉得空虚”)、担心容貌(“如果不是我的脸,我将一无是处”)。实际上,这些电视剧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也就是说,电视剧的女性形象总是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出来并用男人的话语说出来的。在好莱坞影片中,女性在那个以男性为主体的世界里通常也总是个“局外人”,如女权主义评论家安妮特•库恩所指出的那样。女人没有可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所有形象都是由男人控制着的。一般地说,女人只被当作性的对象——她们的价值主要决定于她们的美貌和性吸引力。她们只是伺候她们的男人,而很少过一种她们自己的有意义的生活。婚姻和家庭是她们主要的生活目标,而很少有她们自己的重要事业。影片中女性的角色多半是一些边缘人物,很少处于事件的中心。女主角的职能就是在一旁喝彩,被动地等待男主角对她给以回报。智慧、雄心、性自信、独立性、职业技能这些品质,全被认为是天生属于男性的,所有这些品质往往被表现成对女性不适宜和不相称的东西[3]。
比起西方来,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更沉重、更漫长。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极为成熟和完备,极端强调等级、统治关系,没有给个性、自由、平等等观念留下空间[4]。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这一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戒》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妇者,伏也,伏于人也”。女性谈不上任何权利和地位,更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例如,在中国,媒体对普通女性和下岗女工的报道是双重的,既表现了性别平等,也有刻板印象在其中。一些女性努力工作,具有奉献精神,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但她们只是把自己完全融入家庭,在社会上没有独立性。她所做的一切,最主要的是为了丈夫,没有发展妇女权利的意识。因此,即便在今天,当一个妇女只为了个人的幸福或个人价值的实现而抛家弃子,必然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会感到良心不安。对于女人,个人的意愿必须服从于家庭,假如脱离了道德,幸福便无从谈起。
中国的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女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无疑根植于中西方巨大的民族文化差异。西方从根本上是以个性主义为主流的,中国则以集体主义、非个人主义为灵魂[5]93。
在西方,妇女解放就是为了妇女作为独特个体的人的权利和存在价值的实现,对于西方人来说,个人意愿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幸福,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个人的改变,妇女是目的和出发点。在西方,麦当娜教会年轻妇女具有充分的性感,同时又能完全控制她们的生活。她的音乐电视包括了新女权主张和性取向的多元化,强调人的天性的自然实现,而不是自我克制,从而培育出更加丰富与美好的人类情感,人能够创造新道德。在美国电影、杂志和流行小说中,“轻佻女郎”是一类无所畏惧、酷爱跳舞、为性发狂的女子,是正在经历一段不平凡时光的女性,青年文化所衍生的新道德和休闲产品使这类女性的存在成为可能。轻佻女郎成为了象征当代美国性问题、都市生活和现代主义最著名的符号之一。虽然轻佻女郎的符号仅能代表部分美国年轻人的真实生活经历,但是这个概念却飞快地在全国流行起来。轻佻女郎男孩气的外表和满不在乎的态度表达了一种自我憎恶而非自我满足,一种意图逃离自我、母亲,逃离任何将她标志为女性的事物的企图,她象征着西方女性个人意愿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6]。
在中国,对于男人来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弃家庭和个人生活则被视为美德。中国的女性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从革命、从国家、从男性这个群体中凸现出来,女性的自身价值从没有得到过肯定。国产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既是男性又是“首长”——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服从这个男性的性要求与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被人为地焊接在一起。投身革命事业的女性在面临革命和爱情的矛盾时,自然要把“革命”(政治)放在首位,而牺牲爱情这样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是革命话语强迫下的非个人行为),这样的叙事过程,其实是在革命话语中成功实现了女性从属地位和女性牺牲的合法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的妇女解放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
二、社会文化、传媒与女性形象建构
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意义和模式的功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映射,所以媒介中的性别偏见、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变得难以掩盖;媒介也不得不对不同性别有所区别对待,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性别上的权力关系。这无疑是社会角色的社会规范长期沉淀的结果,形成了坚如磐石的社会心理,是人们形成刻板印象的重要途径。人们通过观看媒介内容中对两性进行的角色定型化描述、媒体对女性群体的定位和形象的塑造,便在无意识状态下对社会知觉、价值判断以及态度和行为产生意义和价值认同,这一切在传媒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强大的父权阴影笼罩下,女性的精神触角长期处于萎缩状态,以婚姻为边界,以家庭为天地,养成了被动顺从的所谓女人“天性”。这种后天形成的被动状态,反过来又被父系文化拿来论证女性只配作为男人的附庸[7]。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迎合了男权文化的欲望,这种女性形象与角色仍然处于被异化的状态,它以其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维护着男权文化和男权观念。由于大众媒介是海量的、组织化的、以公众形式出现的制作、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机构,因此其所传递的内容对受众拥有潜在的大范围的社会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媒体没有如实和充分地反映女性生活和经验的各种面貌,却一直在将女性复制为性感尤物或“贤妻良母”、“女强人”等类型化女性形象,缺乏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传统角色。这些形象在各种媒体中反复被刻板印象化、琐细化、甚至边缘化,若干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流行偏见、神话与意识形态,也一直主导女性议题在媒体的呈现。
西方社会中尤其是当代女性政治精英在媒体再现上,一直承受着双重“他者化”压力,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中,由于男权社会对女性参政的敌意与疑虑,女性面临着长期历史所形成的被排挤、被边际化的待遇。因此,在新闻媒体报导中的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事件是以“男性”为中心来刻画的,而生活、消费方面的报导则是以妇女为主体,似乎只要和“家庭”、“私人”有关的内容,撰稿者都不自觉地以女性为对话的对象。女性形象主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艺术品。这些形象传达了关于妇女本性和角色的观念,但它们也象征着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在大众传媒诞生很久以前,这些妇女的面孔和形体已经服务于美国文化中的这个目的。在早期的公共艺术如雕塑、旗帜和硬币中,女性身体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加频繁地得到重视:男人们经常以他们自己、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但妇女的出现却是为了证明别人或其他事情的身份或价值[5]63。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被报纸和新闻节目进一步加强。两者都强调男人独立的行动,新闻实际上整个成了关于男人和女人被男人主宰的故事。关于男人的故事把重点放在他们的工作和成就上,一遍遍地重申男人必须行动、必须表现自我的文化信息。因而,女性通常很少在“重要”的新闻中出现,媒介的报导很少针对女性的工作、成就、情境或需要。另一方面在大众媒体中,媒体一直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女性政治精英的容貌、身材、表情、衣着化妆等,这种透过一连串观看视角、美学修辞所营造的意象,使她们同样承受被刻板印象化、被曲解塑造的看待。少数与女人有关的故事又倾向于强调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和主妇的职能。即使是关于因其成就和职业活动而成为新闻的女人的故事,一般也会提及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女人传统角色的其他方面。例如,当马格利特•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时,报纸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提到她是个“家庭主妇”,这是一个忽略了她活跃的政治角色的标签。网络中所体现和追求的女性形象也大多是:要么是漂亮的、具有性吸引力的时尚女性,要么是“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角色,或者是具有强烈消费欲望和购买能力的“购物狂”。而在政经新闻中,当女性进入一个完全以男性为主体的领域时,其身体、外貌还是最受注意的焦点,而且记者通常会以男性的观点来报导女性公众人物。男性公众人物可以在新闻媒体报导中以“公共身分”出现,而女性则在新闻报导中往往缺乏公共身分,她们的角色经常被简化为传统的女性。媒介灌输与传播女性传统的刻版印象,当女性涉及某种组织或行动而跨出其传统角色时,媒介通常予以扭曲及嘲笑;新闻报导的“事件取向”与新闻搜集的“路线结构”上,女性很少被报导,即便被报导,也被媒介以“琐碎化”或扭曲的方式报导。
20世纪以来,媒介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工业社会和商品社会的重要文化形式,媒介必须迎合大众趣味,而这种大众趣味则等于整个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
在市场杠杆的作用下,传媒的生存不得不依赖“大众”这个衣食父母。提高电视收视率、报刊发行量和电影票房收入的最好方式就是“迎合”大多数消费者的口味。大众文化说穿了就是一种消费性文化或文化工业,它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制造”。为了获得利润,传媒不断塑造和制造出被男性(也包括一部分女性)期待的女性形象,按照男权法则讲述和歪曲女性。消费社会把女人高度符号化,封面女郎、时装杂志、时装表演等在诠释着“做女人”的另一层含义,即,将苗条的身体、美丽的外貌以及拥有青春作为衡量女性美的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这种狭隘的审美标准几乎压到了其他各种对女性美的文化理解。使女性性别、女性形象已成为商业化时代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沦为客体、欲望的对象,沦为符码、空洞的能指。那些经过刻意包装过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美女”,不如说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欲望符号[1]26。广告更是体现父权意识形态的场域,透过符号的表意过程,不断复制出有助男性利益与权力的世界观和性别关系模式,并对不同的女人形象赋予男性价值社会判断。广告中隐含的男权意识形态常常会通过各种符号的巧妙和刻意安排,对女人产生“召唤”与“命名”的主体建构作用。男权观念作为我们社会的主流观念,一俟和已成为主流文化的大众文化相结合,便将女性逐出主流话语系统,真正的女性话语难以在传媒中拥有栖身之地。大众传媒中的思想意识早已成为社会的水泥,它们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观念与这种现存的社会结构,使这些本来由于天长日久早该风化和坍塌的东西更加牢固,更加持久,甚至有可能弥久弥坚。
三、中西传统文化象征与媒介女性形象的跨文化差异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象征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女性文化象征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线索中的一条,它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线索并行,并且以特定阶层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为发展基础。由于两性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不仅压抑了男女两性,尤其以对女性利益的牺牲最为突出,所以对中西方传统女性文化象征的溯源与反思,一定程度上也梳理出了性别文化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及性别制度作用于时代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
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是按宙斯的意志所造用来惩罚普罗米修斯的。在这个神话故事中,我们看到潘多拉的存在是由于男性权力争斗与复仇的中介作用。她的全部意义与构成要素,无不是男性制造与促成的结果。首先,由男性神为潘多拉命名,这就决定了作为象征符号的“潘多拉”,服从于她的男性制造者所同时订立的生存规范;其次,潘多拉的身上兼有女职和女色的所有优势,而这些优势是经过那些男性神所挑选和核定的素质,在将这些素质种植到潘多拉身上的同时,这些素质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复仇与毁灭功能。潘多拉的身份是“礼物”和“武器”,对于男性而言,她既可以成为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成为复仇者的最佳化身。无论怎样,潘多拉的存在,都是男性布局的棋盘中重要的一枚棋子。她纵然有无穷的破坏力,也需服从、服务于背后隐匿着的男性的游戏规则。
大众媒介塑造的各个类型女性形象中各有自己的“潘多拉特征”:女强人通常被认定是鲜有温柔和顺服的气质,这样的女性被刻画在情、爱、家庭上必然属于弱者。这种女性敢爱敢恨,性格强烈,比男性更为冷血、邪恶,媒体常常强调她们不能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或者刻意突显一些“女人间的战争”,似乎女人之间的吵闹争夺游戏比男人之间的争夺会更引人注意、更为有趣,在潜意识下标签了女人彼此间对身体、欲望、情爱的三角关系的争夺,这种行为甚至会被解释为是为“取悦男人”而争执。女明星通常被认定是依靠情色换取机遇的特殊工作者,女性主义者则往往与失婚、单亲、女同性恋等名词相联系。以潘多拉为原型的女性,无一不是令男性感到压力的对象,她们的优势往往被那些被认定的危险和威胁所抹杀,她们通常具有大众所公认的“致命吸引力”,由于这种吸引力总是伴随着观看个体或关注个体在其他方面的失误或失神,所以这类女性往往被当成“代价”、“损失”等概念的象征,而受到程度不同的隔离与误解。这类女性的吸引力在菲勒斯性别文化的调和作用下反而呈现出与大众相排斥的结果。由此可以证明,女性的性感或性别方面的吸引力,表面上看是由生理的性别所提供的,本质上依旧是社会习俗和性别文化传统所规约的产物。
飞蛾女神是中国古典文化中为爱奉献直至献身的象征原型之一,这种献身被视为中国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飞蛾女神为后羿提供了温暖的家庭生活,可口的饭菜并陪伴入寝,是后羿度过漫漫长夜的温柔寄托。但是当白天来临,后羿便感觉自己干一番事业的心思被这种温柔与温暖所消磨,飞蛾女神和她所营造的那些温情都被视为后羿向外部世界征服的阻碍。经历了这种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挣扎之后,后羿选择了射杀飞蛾女神。飞蛾女神的牺牲成全了后羿这个英雄,这个故事提供了“女性/男性=感性/理性”的刻板印象,飞蛾女神也成为不平等性别观念的其中一个牺牲者。飞蛾女神的困惑是许多女性共同面临的困惑--如何平衡自己在婚姻和自我价值方面的成长与被认同?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安守于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服务于丈夫的女人并不会得到传说中的幸福美满,她们会因各种理由而遭到遗弃,她们的辛苦努力并不会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因为问题所在不是女人应该奉献家庭还是奉献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女人应该取悦丈夫还是让丈夫取悦之间的矛盾,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无论外在形式是怎样的,男女双方是否都在个人的不断成长中收获人生经验与智慧,是否在与另一半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地完善自我。[8]为什么事业成功的女性往往要以形象异化、爱情背叛、家庭破裂为代价?为什么男性事业成功就是夫贵妻荣,而女性则必须做精神上的流浪汉、漂泊者呢?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几乎成为高学历、高智商的当代女性的婚姻定律呢?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仍然藏匿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文化观念,这张潜行的巨大网络依然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们的意识和思维。出走后的“娜拉”,当她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在社会上实现了自我价值,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想要重新品味家庭的温馨时,又遭遇了无法言说的困惑与烦恼[9]
女性文化象征是以女性为直接对象进行文化机制塑造与复制的一种表现,它的主体并非一定是女性的,传达的思想意识也并非完全是女性经验的总结。但是,作为社会精神财富的构成部分,作为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的构成部分,女性文化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反映出了女性普遍生存的环境与发展的困境。所以,作为一种间接吸收的意识资源,中西方不同的女性文化象征传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对中西方、尤其是中美两国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下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深层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理,男权意识仍然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深处,不仅制约着女性的主体行为,也制约着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和价值评价。然而,持有话语权的媒介生产者大多不可能脱离其生长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宗教、审美及风俗习惯的观念构建出不同的媒介女性形象。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中国的妇女观更多地隐匿于社会总的道德规范和革命运动之中。除了文化原因,与西方社会相比,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在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里,是相当匮乏的,中国社会对自由和责任的分裂认识还是很强烈[10]。同时大众传媒也是一种文化。一方面,它会利用观众非常熟悉的价值观念创造一种东西;另一方面,媒介对社会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的种种描述,常常内化为受众的一种期待,它所创造的文化强化了观众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对人形成一种影响,甚至是一种控制。由于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阶级性,同时还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因此,媒介如果不树立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就必然落入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传统文化和惟商业至上的文化巢臼当中[11]。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象征反映了性别文化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及性别制度作用于时代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它们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禹建湘. 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2] 贺璋容. 神光下的西方女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103-110.
[3] 贾内梯. 认识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272-273.
[4] 于东晔. 女性视域——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女性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9.
[5] 陈晓兰. 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
[6] 卡罗琳•凯奇. 杂志封面女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92203.
[7] 周力,丁月玲,张容. 女性与文学艺术[M].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76.
[8] 张敬婕. 性别与传播——文化研究的理路与视野[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233236.
[9] 李琳.刻板印象与性格平等形象——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C]∥荒林,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NO.2.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36.
[10] 张念. 持不同性见者[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232.
[11] 刘利群. 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162.
ぴ鹑伪嗉:王俊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