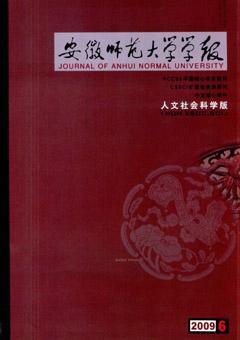朱熹在徽州本土遭遇的尴尬
徐道彬
关键词: 朱熹;徽州;遭遇;批判
摘 要: 朱熹的历史地位在元明时期至高无上,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宣传工具。事实上,他在徽州本土的形象和地位并不崇高。考察清代徽州民间文书和宗祠记载,以及徽州学者对于朱熹的批判,反映出徽州人对于朱子及其思想的怀疑甚至排斥的情绪。由此为进一步探讨清代朱子学衰落的原因提供佐证。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6067207
Embarrassment Zhu Xi Encountered in Huizhou
XU Daobin(Center for Hui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Key words: Zhu Xi; Huizhou; encounter; criticism
Abstract: Zhu Xi's historical position was suprem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as a propaganda tool of the ruling class' ideology. In fact, his image and status was not high in Huizhou by examining Huizhou folk documents and the ancestral halls' records in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Huizhou scholars' critique of Zhu Xi. People in Huizhou showed their doubts and even emotional rejection against the ideas of Zhu Xi. It provides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Zhu School.
元明以降,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其历史地位至高无上。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没落,程朱理学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商业资本主义已相当发达,朱熹的存理灭欲思想和三纲五常学说,已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贞节牌坊背后的血泪和“以理杀人”的呐喊,使得朱熹即使在徽州本土人们的心目中也逐渐失去了圣贤的光环,遭遇到猛烈的批判。本文通过考察清代徽州文书、宗祠记载和徽州学人文录,以及当地朱氏后裔的真实口述,可以发现:虽然朝廷为了政治目的将朱熹神圣化,但实际上平民百姓并没有对其顶礼膜拜;新安朱氏对朱熹的宗族认同并无特别的自豪与尊崇;而学者反对或攻击朱熹思想更是屡见不鲜;朱熹本人的形象及其影响在徽州本土遭遇到了异样的对待。
一、朱熹祖墓在徽州的尴尬遭遇
徽州人文荟萃,儒风昌盛,因历代战乱而不断迁移进来的中原世家大族,尤其注重族系和家世而竞相修谱传家,他们认为“礼莫大于尊祖,和必重乎睦族。夫问水者必寻其源,理木者必察其本,水源木本不可不慎重也”。[1]68但是,“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2]758修谱者遥托华胄,光耀门楣的做法,虽有不实,但也是人之常情。若按此常理推算,人们一定会认为新安大族朱氏所修宗谱,必以朱熹为荣,会把朱熹作为不迁之祖而推崇备至,朱氏族谱中也会将朱熹的形象大书而特书,极力地扩大和渲染他们与朱熹的血缘关系。但是,通过翻阅几部徽州的朱氏宗祠族谱,我们发现朱熹的影响在徽州社会民俗生活中并不凸显。譬如,在新近公布的《休宁首村派朱氏文书》中所附《新安朱氏宗祠记》中,我们没有看到朱氏有丝毫粘连朱熹,攀附名人的内容,对朱熹的文字也涉及很少。即使在今天,我们去休宁首村访问朱氏后裔,他们对同宗朱熹竟然较为冷漠,绝无半点引以为豪的意思。
据《新安朱氏宗祠记》[3]记载,朱氏自朱涔(原注:号师古,由苏迁歙,是为新安一世统宗始祖),于唐乾符五年迁入徽州,有四子,曰瓌公(原注:迁婺邑,乃文公之祖)、曰革公、曰珉公、曰璋公。在瓌公目下分载有:婺长田,瓌公领兵镇戍始迁;婺阙里,瓌公子廷俊公由长田迁,文公祖也;闽建阳,瓌公十代孙、文公第三子在公迁。朱熹(文公)属于朱瓌一脉,与首村朱氏共以朱涔为宗,因随父朱松为官而“流落闽中”,到朱熹的第三子朱在时,才确定其为迁闽建阳的一世祖。此后,婺源和首村的朱氏便成为留守徽州的大宗,但是无论在朱氏统宗谱或是支谱中,仍有各派的信息记录,如此谱中就有《新安朱氏四派五支图》和《新安朱氏篁墩统宗》等内容。关于这一点,除了《新安朱氏宗祠记》以外,在朱熹的《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中,以及保存至今的《新安月潭朱氏族谱》、《镇海虹桥朱氏族谱》、《铅山石岩朱氏族谱》中,也都有相同的说法。
朱熹作为新安的杰出人物,按理只要涉及有关他的事迹及其祖宗的内容,在徽州人的眼中本应该都是极其重要的遗迹,也理应会被朱氏宗族后人立祠树碑,以示慎终追远的纪念。然而,事实却出乎我们的意料。翻开这本清人所录的《新安朱氏宗祠记》,却有很多文字记录的是朱熹祖宗遗迹的风蚀凋敝,无人过问,甚或屡屡遭人破坏。如谱中记录了元代延佑时,婺源朱熹的祖业被邻人侵占,独存旧居,荒芜潦倒。朱熹五世侄孙朱光曾向浙江行省和福建督宪申诉,要求官府出面追回朱子祖业,官司打了近30年。直到至元二年,在婺源知州干文传的干涉下,又有邑中善人汪镐以自己的田地来置换被人侵占的田地,才恢复了朱熹的祖业之所。干文传又以颜子、孟子故宅立庙之例,奏请朝廷建立朱文公家庙,所需费用皆由汪镐捐献。汪镐另外又捐出30亩田地,以供祭祀之需。为了避免再出现疏于管理和邻人侵占的情况,干文传又特别移文于建阳朱熹后裔,请他们派人来婺源,亲自掌管朱氏宗祠之事。于是建阳的朱氏宗族按家族规矩,推选朱熹的五世孙朱曛回到祖居地,掌管朱氏的祭祀。由此可见,朱熹虽被元代朝廷尊为“学达性天”、“道脉薪传”的标准圣人,但这种尊崇仅仅只在于他的学问和思想,而对于朱熹本人并未得到实际的尊崇。相反,在朱熹的徽州故乡,祖先的遗迹竟然都会被人占为己有。可想而知,元代的朱熹在徽州故土的形象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该宗祠记又记载了有关朱熹祖先的另一件事,就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歙县人太学生赵滂到篁墩省亲,询问当地故老时,偶然得知朱熹祖墓所在地,但墓已毁坏,难以辨认。作为读书人,赵滂出于对朱子的景仰,于是与胡祖诒、潘允升等人清其税业,禀明知县刘伸,得立石碑,题曰“朱夫子祖墓”。然而,时过境迁,清初时,朱夫子祖墓“又为乡愚罩踞”,墓树遭到肆意砍伐,毁弃墓地于芜漫之中。谱中所附载吴廷彦的《呈为戕害先贤盗砍荫木事》曾载明此事,呈词曰:“徽国文公集前圣之大成,为万世之师表,上自天子,下及庶人,无不尊崇钦敬。乃有祖墓三穴,葬古歙之篁墩,地方因年远湮没,至万历壬子年,有太学生赵滂者,广搜博采,参订详确……得夫子祖冢一穴。鸣诸邑宰,播诸缙绅。邑宰刘公立有碑文阁,郡缙绅刊有志述。迄今两号三穴又为乡愚罩踞。延彦于康熙戊子春,偕友课文于篁墩,课毕访先贤遗迹,见刘家门前夫子祖冢没入土中,不忍湮没,偕朱氏后裔讳嘉惠者,率其族属大修旧冢,中立刘公伸名目大书‘朱夫子祖墓五字;左则邑宰邵公起凤碑记;右则刊五经博士朱坤碑记。是刘家门前二冢粲然复明,而朱家巷一冢,仍然未得近。”[3]吴廷彦考明朱子祖墓石碑,恻然心动,会同歙县朱氏族人大修旧墓。之后,朱子十七代嫡孙朱廷锡、十八代嫡孙朱澄等,先后致函吴廷彦致谢。不仅感激他使朱熹祖墓“粲然复明”,而且赞扬吴氏勇于向毁坏先贤的不良分子做斗争。
《休宁首村派朱氏文书》中又附《新安朱氏篁墩统宗》一文,也叙述了吴廷彦为保护朱熹祖墓而辛苦奔走的事迹,并将吴氏的呈词附于朱氏宗谱文末,以示珍重。词云:“篁墩地方,古称程朱阙里者,以三夫子祖墓在焉故也。今朱夫子祖墓有抱木四株,于四月廿三夜,遭土蠹程我嘉盗砍。廷彦一时性急,不暇遍告,星夜奔郡具呈。蒙府学储、姚两师尊印送县主蒋大父师准究在案理合刊呈布闻绅领先生,共彰公讨。”吴廷彦对同乡朱熹深怀尊崇钦敬之情,对地方豪绅盗占先贤墓地痛心疾首,“呈词遍告阖郡绅宪”,乞赐严究,云:“去年甲辰,获得万历壬子年刘公与缙绅之簿籍,于短字一千九百八十八号之内,细加详察访,果见号内有古冢一穴,古树四株,郁郁葱葱,圈围九尺,竟被土人当黄册,程我嘉罩占。本月二十二日将万历壬子簿籍,先贤古冢之由备述。我嘉此时允将坟地交出。岂至次日二十三夜,胆将古树四株尽行盗砍。先贤荫木、先贤祖冢,真乃神人共嫉,至法不容,为此备述前后情由,先叩宪案,随刊叩案,呈词遍告阖郡绅领宪大父师、科第世家理学名儒,伏乞恩赐严究,以崇先贤,以正国典,上呈。雍正三年四月。”由此材料可见,朱熹在徽州的历史地位并不象朝廷所宣传的那样,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他与常人没有任何不同。徽州本土的平民忘却了乡贤,抑或本不知道这样的圣贤。邹鲁之乡并非都能弘阐经学之精微,褒录诸贤之遗裔,他们把圣贤拉回到与己平等的地位。间或有读书人如朱光、汪镐、赵滂、吴廷彦等,对于朱熹或许怀有特殊的景仰,但并非所有同乡都能如此,尤其是深知朱熹家世的故人,正如俗言所谓“敬远而卑近”者。程我嘉之流的见利忘义,行径卑鄙,在此姑且不论,但此事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朱熹在徽州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所谓的“前圣之大成,万世之师表”只是贵族阶级举着朱熹“存理灭欲”的思想为幌子,借以压制民众的手段;“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也只是几个文人笔下的空泛的高调而已,而更现实的一面则是徽州人没有把朱熹神圣化,他们对于朱熹及其祖先的态度也是平常的。
二、徽州的文昌阁侵占了文公祠
朱熹祖宗在徽州的遭遇令人痛惜,而朱熹本人在徽州的形象也没能逃脱厄运。譬如,清代徽州府要建文昌阁,以求文运昌盛。其时,可建文昌阁的空余之地还有很多,但公众议论和官吏决定的结果,却是“夺文公之祠,以奉文昌,屈文公之尊,置之隘舍”。徽州人这样置乡贤于不堪,故而有大儒程瑶田起而抗之。程瑶田(1725——1814),号让堂,歙县人,一生之学在考古实证,思想上以朱子学为宗。他为此事极力向官府陈说得失,曾作有两篇《徽州府建文昌神祠议》,称:“朱子,我新安之所独尊,而以为斯文宗主者也。是故歙学宫之左,建紫阳书院,城阳山又建紫阳书院,皆崇奉朱子,以肄业多士。即浙江杭州,因接壤新安,其书院亦曰紫阳,苏州因与新安同为江南省,书院亦曰紫阳,皆崇奉朱子,冀私淑之以得其道德文章之绪余者也。新安会馆之最大者,在苏州、汉皋二处。皆崇奉朱子,无非藉以昌其文运。是新安人,无论家食、流寓,莫不崇奉朱子,以朱子为新安之所独尊,而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4]334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应受到朝廷的尊崇,朱子的道德文章也曾使徽州“昌其文运”。“自建文公祠以来,于今四十余年,即以吾歙本籍文运而论,解元二人,会元二人,状元一人,皆前此所未有。又如召试制科之殊恩,海内所艳羡者,此四十年中,吾歙共得十有一人,是岂未建文公祠前之所有者”?[5]334文公祠使“吾歙本籍文运”,令“海内所艳羡”,作用并不比文昌神祠差,为何要“夺文公之祠,以奉文昌”,相信神灵而置科举考试的祖师爷于不顾?其中深意,令人费解。
徽州人对于朱熹的漠视,甚至是排斥,程瑶田大为愤慨,曰:“文公祠何负于桑梓?而桑梓之宜敬恭朱子者,乃欲夺其居而跻之隘陋,无以对我文公。即非所以仰体圣朝累代有加无已之睿旨也。”[5]334文昌阁乃道教之所,以大儒文公之祠,以奉玄虚文昌之阁,“抚心自问”,恐贻笑四方。瑶田以为:“此议若行,大违累代圣皇之旨。新安文献之邦,举动如此,鲜有不传笑四方者也。紫阳山,故建紫阳观。昔人请去老子祠,改建文公书院,以其凭虚阁,改为韦斋祠。新安人之崇奉文公如此。老子祠,紫阳山之所故有者也,尚当归还文公。岂文公专祠,顾可移其肖像,改而新之,以为他用乎?文公人中之大贤,文昌天上之悬象,森列昭布,不生分别,固可分庭抗礼。要当耦俱无猜,别建一祠,以祀文昌,乃为允协。况文公之祠,在我徽郡,尤为乡后学之所独尊,非若他郡学者视之为众所同尊者也。孟子曰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同独之间,为乡后学者所宜忖度其轻重者也。生于文公之乡,至不能保守文公之祠,抚心自问,安乎不安?”[5]336337文公之祠在他郡皆为众人所同尊,而在我徽郡,却“欲夺其居而跻之隘陋”,令人痛心。《徽州府建文昌神祠议》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朱子地位衰落的悲哀,但又一面极力申述:“一旦漠视其所独尊,而以其专祠为可有可无,可大可小,若前之小者,本可不必大;而今之大者,何必不可复小?此心不可以对文公,此心亦可以对天下后世乎?况吾徽城中,择一建文昌祠庙之处,非必无其地也。两城之人,皆指谓武庙之东,现有大厦一所,其广其深,并与武庙同。今空在无用之地,不过为客馆不时之需,为到任、卸任官员暂憩之所。”[5]334本有空余之地可建文昌阁,却偏拣文公之祠为用地。人中大贤的文公之祠,竟然不及“到任、卸任官员”的休憩客馆。程瑶田严正指出:“今欲请朱子舍广厦,还归陋室,下乔木而入幽谷,此何心哉?朱子即随遇而安,而为朱子之乡人者,其何以立于天地之间乎?”[5]333在所谓儒风昌盛的徽州,朱文公祠的惨遭侵占,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朱子地位在徽州本土的消失,文公祠不及一道教文昌君,其诋毁朱子之意显而易见。程瑶田的两篇《徽州府建文昌神祠议》,与其说是对“斯文宗主”朱熹的极力维护,勿宁说是反映了朱熹本人及其学说在徽州本土的衰落。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能够从徽州学者的笔墨里窥出端倪。
三、朱子遭遇徽州学者的批判
朱熹祖先及其本人在徽州本土所遭遇的尴尬,也许只是徽州人自己的“家丑不可外扬”,朝廷对此不会知晓,仍赋予朱子“德高千古,万世师表”之称。以为“新安自朱子钟灵婺邑,绍统圣传,集诸儒之大成,而孔道赖之以不晦”,[5]卷21休宁县修学记,这只是官僚士大夫在行文时的得意表述。事实上,徽州人受到朱熹的影响,在明清时期应该是最为深刻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使徽州人深受其害。对于一般社会民众而言,“羽翼圣经”、“绍统圣传”都无关其事,故而朱熹在故土民众生活中与常人无异,绝无神秘之感。至戴震出,以乡邦后学身份和“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思想,猛烈批判朱子,在理论上否定了朱熹学说,使得人们都注目于他。但在戴震之前,就有许多人有所反对,而以徽州人姚际恒最为杰出。姚际恒(1647-约1715),字立方,休宁人。读书专事经史考证,经过十数年的潜心钻研,撰成《九经通论》和《古今伪书考》,开清代辨伪疑古风气,对近代“疑古派史学”也有重大影响。
作为朱熹的同乡,姚际恒对朱熹的质疑和批判是很有力度的,他对理学的空言心性、游谈无根,能够追根溯源,揭露无遗。如《仪礼通论》一书,就是针对朱熹《仪礼经传通释》而来的,在对历代礼学研究
的基础上,严正批评朱熹的注释缺失。曰:“朱仲晦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明是反见。朱之说本袭唐陆德明。其言曰,《礼记》记二礼之遗缺,如介遵宾主,《仪礼》特言其名,《礼记》兼述其事,意今之《礼记》,特《仪礼》之传耳。陆之说又本于臣瓒,以《仪礼》为经礼。可见缪学自有一种流传如此。今不举臣瓒与陆,而举朱者,以朱为近世所宗,且实有《仪礼经传》之书故也。”[6]卷首•仪礼论旨朱熹晚年治礼,著有《仪礼经传通释》,书未成,且舛误也多。姚际恒广为搜求散见于经传群书中有关礼乐制度的记载,对朱子沿袭前人的错误加以纠谬补失,阐明己见,且言词犀利,切中肯綮。并声称不以臣瓒和陆德明为批评对象,而紧扣朱熹来批判,是因为“朱为近世所宗,且实有《仪礼经传》之书故也”,姚氏此言是很有深意的。按照常理,姚际恒应该为乡贤者讳,而姚氏却弃他人于不顾,专对朱熹大加挞伐,一方面说明朱熹在徽州学人眼里并非如何神圣,其理学在徽州的不良影响已遭到民众和学者的极力反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徽州人反对因循守旧,而富于求变与创新的精神。学术发展,穷则变,变则通,“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物理之常,无足怪者。人之于学,既登堂而入室,复操戈以相伐。入而能出,此其所以大也。古今能自成一学派者,可屈指数,要其成功之由,莫不如此”。[7]378姚际恒专门挑拣同乡先贤来入室操戈,其做法与后来戴震的反对程朱理学,如出一辙。
在批判朱熹的力度上,姚际恒要比戴震猛烈得多。戴震重在对朱熹理欲思想的批判,而对其经解章句还多有依从;姚际恒则是从朱熹著述的文字根本上,加以批驳甚至推翻,措辞严厉,不留余地。指出:“《仪礼经传通解》一书,经传颠倒,前已言之。然吾实不解作者意指,以为尊《仪礼》耶?全录注、疏,毫无发明,一抄书吏可为也。尊之之义安在?以裁割《礼记》、《周礼》、史传等书附益之为能耶?检摘事迹可相类者,合于一处,不别是非同异,一粗识文字童子亦可为也。又何以为能?其于无可合者,则分家、乡、学、邦国、王朝等名,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此全属纂辑类书伎俩。使经义破碎支离,何益于学?何益于治?观其《乞修三礼札子》,欲招集学徒,大官给养,广拨书吏,迂妄至此,更有足哂者也?此书近世传本甚少,近有人重刊,然世究鲜传习,亦可见人心同然,但未能深知其非耳。至若黄勉斋之续编,吴草庐之考注,悉遵其指,又无讥焉?”[7]姚氏认为朱熹解经已将“经传颠倒”,甚至“凭臆变乱,牵强填塞”,裁割礼书史传以附益为能事,实为“毫无发明,一抄书吏”而已,甚至比之为“粗识文字童子”。如此揭露《仪礼经传通解》的迂妄和荒谬,对乡先贤的无情批判可谓无以复加,这与明清时期朝廷的“尊崇之义,未有伦比”相比,真可谓直率大胆,不留情面。姚际恒的做法未免有所偏激,但由此可见徽州平民的观点和心声,窥探出他们对待万世师表朱熹及其学说的反感。
朱子理学受到朝廷的大力提倡和理学家的弘扬,但却遭到同乡后学戴震的猛烈攻击,这又是学界至今仍然议论较多的话题。戴震(1724——1777),字东原,休宁人,出身徽州小商贾之家,其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书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思想大加挞伐,不遗余力。指出:“程子、朱子,其出入于老、释,皆以求道也。使见其道为是,虽人以为非而不顾。其初非背六经、孔、孟而信彼也,于此不得其解,而见彼之捐弃物欲,返观内照,近于切己体察,为之,亦能使思虑渐清,因而冀得之为衡鉴事物之本。然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远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足,无欠阙矣,实动辄差谬。在老庄、释氏,固不论差谬与否,而程子、朱子求道之心,久之知其不可恃以衡鉴事物,故终谓其非也。”[8]168戴震对朱熹的批判,是从理学的根本上寻求朱子出入于老、释的行迹,与姚际恒对朱子的批判可谓殊途同归。他揭示出朱子“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实为道家的“真宰”和佛家的“真空”,以出入于老、释而求道,“终谓其非”。并特别强调:“朱子《四书注》,《大学》开卷说‘虚灵不昧,便涉异学;云‘以具众理,应万事,尤非理宗之旨;《中庸》开卷‘性即理也,如何说性即是理?《论语》开卷言‘学可明善,以复其初。‘复其初出《庄子》,绝非《孟子》以扩充言学之意。”[9]713714戴震从朱熹《四书集注》的核心问题入手,指出他的“异学”性质,反对朱子“性即理”、“复其初”的道家面目,提出世界的本质是“气”,“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理”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也即是“治理”、“分理”、“条理”,绝不存在超自然的精神本体的所谓“理”。认为古人所谓理解者,寻其腠理而析之也;古圣贤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已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戴震与朱熹同出徽州,对学术与现实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他们思想的对立,也被后人过多地加以猜忌和渲染,认为戴震早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晚年转而攻击朱熹,是忘本。
实际上,戴震对朱熹的批判是基于学理层面的论争,仍是“承朱学之家法”,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的路数,主张“学问文章,互争不释”。但在后人看来,却别有一番意味和意想不到的结局。譬如,章学诚说:“戴君笔于书者,其于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于顾、阎诸君,则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或谓言出于口而无踪,其身既殁,书又无大抵牾,何为必欲摘之以伤厚道?不知诵戴遗书而兴起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向在维扬,曾进其说于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已,何如朱子,至于学问文章,互争不释,姑缓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实精,似浅而实深也。”[9]276章氏认为,凡是有悖于朱熹学说的言论,皆斥为“异端邪说”。于是便称东原“诽圣排贤”、“害义伤教”,言辞颇具情绪因素。并且声言“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则将戴震与朱熹置于水火不容的境地,实在有违东原本意。后世讨论朱熹与戴震的关系,多是带有某种观点的附会与曲解,致使戴震有“丑贬朱子”,“心术未醇”之罪。而事实上,戴震“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并不如那些毁坏文公祠者的“诽圣排贤,毫无顾忌”,也不如姚际恒的口诛笔伐,滔滔未已。
戴震生于贫寒,遭遇坎坷,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刻体验,痛恨“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对人民的残害。为了寻找“存理灭欲”的学理根源,东原用“以词通道”的方法,揭露宋儒糅合佛道,惑乱圣贤之意的虚伪本质。而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当然是在受批判之列。章太炎说:“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不可救。”[10]356戴震通过批判朱熹的理气理论,提出“理存于欲”的思想学说,以对抗“洛闽儒言”。戴震“知民生隐曲”,“为臣民诉上天”,敢于直面社会和人生,对社会政治问题批评,对唯心的性理之学做出合理的批判,摧毁“诏令谪人不以法律”的理学桎梏,使民众“死于理可救”。对于压在三纲五常和贞洁牌坊下的徽州人来说,这种做法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普遍赞同,所谓“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也是情理中的事。戴震虽然批判朱熹,但绝非个人攻击。他对自己一生的为人为学有一个鲜明的告白:“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免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9]743我们认为,戴震于朱子学术,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于程朱理学,纠正错误,追求真理,乃是从积极方面的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还是胡适说得好:“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11]1047学术思想的进步正是在不断的辩驳批判中进行的,戴震批判朱熹也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戴震只是徽州人反朱思想情绪的一个传声筒而已。
四、朱熹地位在清代社会的衰落
在徽州,无论是平民、官吏,还是学者,他们对待朱熹的态度与朝廷的政治宣传有着一定的距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身在本土,对朱子学的理解更为直接和现实;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和徽州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使得他们对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的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深恶痛绝。徽州人的这些思想和做法,清中叶时也逐渐与时代学风走向一致。
随着时代的发展,朱熹理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由《清实录》等史料可见,在乾隆帝举办的经筵讲论上,已经对朱熹《四书集注》提出了质疑,指出:“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起标榜门户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恶。”[12]卷128“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13]卷79皇帝的憎恶理学和提倡实学,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臣下立异朱子的行为,这在士林社会引起了巨大震动。清高宗以其举荐经学的重大举措,确立了崇奖经学的文化格局,对朱熹学说及其地位已有相当程度的否定。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所言,“清朝虽然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此时的朱子学只是作为统治的工具,而朱熹本身无论在官方或是在徽州本土,都不具备提倡和尊崇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