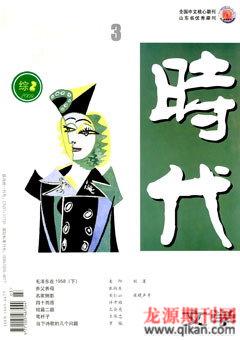短篇二题
火会亮
碎舅
小的时候,我常到碎舅家玩。我家和碎舅家只一河之隔。站在我家门前的台子上,能看见碎舅家门前活动着的人影。碎舅家门前有个园子,园子里有榆树、柳树、杏树,密密匝匝像片绿盖。麦子黄时,那种诱人的杏子的香味就会傍着河沿飘过来,这时节,你就会从那些盖住院墙的绿树问隐约看到一嘟噜一嘟噜的果子,仿佛一群很好的小孩在招手。
现在想来,碎舅家吸引我的,除了那一园玛瑙似的杏子外,就是窗台上放着的那本残破的《封神演义》了。那是一本黄旧的书,没有封面,繁体字,包在封皮外面牛皮纸上的书名已显得模模糊糊的了。第一次翻开那本书并且立即被它吸引住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个安静得可以听见苍蝇拍打翅膀的六月的午后。那时,大人们都下地割麦子去了,找摘了杏子就坐在碎舅家玩,玩着玩着,就看到了那本颜色黄旧的书。那本书立即吸引了我。晚上的时候,从地里回来的碎舅发觉我在看那本书,遂一边洗脸一边问,你才识几个字,能看得懂吗?我笑笑,又低下头去看书。碎舅颇感意外,于是又随口问道,你说说,谁托梦给的周文王?谁在渭河边上钓的鱼?我不屑地说出一个名字,碎舅便大惊。碎舅上上下看了我一遍,之后就格外小心地安顿道,不要人得太深。看看故事就行了。
在我们那里,能看得懂《封神演义》,已然就算个知识分子了。碎舅便格外器重我。偶尔地,碎舅还会给我找来一些更加难读的书,如《东周列国志》、《三国志》等,从那些书里,我隐约感到了书这种东西隐含的巨大幽秘,以及读书带给人的快乐与尊严。
渐渐地,我也能照猫画虎写点文章了。碎舅知道后并不显得怎样高兴,而是“心有戚戚焉”地说,还是想着干点实际工作吧,写书那个东西,说到底还是个虚的。
据母亲讲,碎舅年轻时很顽皮,因了几个哥哥的护佑,他便常跟着我外祖父走乡串户,玩纸牌。玩纸牌在我们那里叫做“抹金”。碎舅年轻时抹金的技艺十分了得。有关碎舅抹金的传奇,在我们那里是很有些说道的。据说,碎舅抹金可以抹三天三夜。抹牌之前,碎舅会吃饱喝足,在家静养一天,长长地睡上一个好觉,之后就到院里和庄稼地里转悠。转到天黑,他大声喊来我的舅母,以及他那几个儿子,细心地安排谁谁放羊,谁谁犁地,谁谁把园子里的韭菜拉到集上去卖。安顿停当,碎舅挥一挥手,他让舅母和我那几个姑舅各自领命而去,自已则像开“三干会”的干部一样,穿戴一新地去赶牌场去了。
一般来说,牌场设在一位可靠的亲戚或朋友家里的。四位高手在毡席上团团坐了,讲好输赢,说过规矩,这就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搏杀。关于抹金的规矩,我曾在一本记录民间棋牌技法的书中看过,那里面是隐藏着诸多的奥妙和机巧的,其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变化多端的象棋或桥牌。在我们那里,能抹得一手好金无疑会赢得人们的佩服与敬重,而碎舅,则已将其挤、碰、过、和(抹金术语)的过程演化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抹金之前,碎舅会像坐禅一样运气,搓搓手指,紧紧脸颊,然后才开始展头揭牌。碎舅已在事前安排好了家里的一应事务,因而心无旁鹜,一上场就进入了良好的竞技状态。碎舅在牌场上的表现,已不是简单的“高手”二字所能概括的。唯一的一个结果是,一场牌罢,其余的人都黑着脸悄悄打道回府,而碎舅则微微笑着,神态自若。他按按饱满的口袋,骑自行车来到附近的集上,买一些家用的零碎,吃一碗羊肉泡馍,然后打着饱嗝,一路摇着铃铛回到家中。
回家之后,碎舅并不急于休息,他像生产队长一样倒背双手,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谁都知道,他这是在检查自已临走时安顿过的事情和工作呢。果然,一会儿碎舅就走进了上房。他盘腿坐在炕头,一边往外掏东西,一边就像正式颁奖那样,开始论功行赏,一条背心,一顶帽子,几块糖果。总之,碎舅从牌场上回来的日子,就是大家的节日。大家轻轻欢呼以示庆贺,碎舅则满足地咂咂嘴,踅进上房,在无人打扰的安静中,美美睡上一天。
在我的十几个舅舅中,碎舅排行最末,俗称“老碎”。碎者,小也,既有排位最低之意,又含可爱顽皮昵称。根据辈分的不同,碎舅分别被人称为“老碎”、“他碎爷”、“碎爷”等等,总之,无论哪种称呼,无不包含了大家对他的尊敬和喜爱。在碎舅家那个只有李姓的庄子里,碎舅的地位显得那样特殊而耐人寻味。
“老碎,来捣两罐罐。”说这话的,必然是我的另一个,更加年长的舅舅,他一定是看见了在庄稼地边转着的碎舅。而想借着喝茶的机会,问一问今年的农事。喝着酽茶。就着干粮,碎舅便将自已的观察和思考一一道来。一般来说,这一庄子的农事安排,基本上就在这一早上的烟熏火燎中确定了。
“他碎爷,今晚上你到我家来。我给你宰个鸡。”一个年龄比他大点的侄子说。当晚,碎舅一定是坐在了那位侄子的炕头,一边吃鸡,一边听侄子讲他近来碰到的烦心琐事。如果是有关后代婚事的,他一定会说“不要嫌人家女子,老先人不是说了,丑妻薄田家中宝嘛”;而如果是夫妻吵架不和的,他一定会说“家和万事兴,这日子总归是平顺了才过得好嘛”。虽都是大实话,但让碎舅那么一说,却是那样的入耳入理,有滋有味。
还有些家事更为复杂的,那就得碎舅大动干戈了。每逢这个时候,碎舅必然是要动一动家族里的三老四少的。一家子,包括闹意见的双方,齐摆摆在地下的矮凳上坐了,等待碎舅和一干白胡子老者,_一像唱戏走场那样登堂入室。脱鞋上炕之后,碎舅便会虎着脸对闹意见的人说:“现在你们各摆各的道理,我看你们究竟有多少道理可讲。”大有不说彻底不罢休的架势。闹意见的双方,自然是要说一说,闹一闹的,说过闹过了,碎舅就会给他们讲一些与此相关联的早年故事,而这些故事无一例外都是春秋战国,或有出处的。听着这些故事,感受着这种氛围,老者拈须颔首,那闹意见的双方自然也冰释前嫌,早已沉浸在其中了。
我曾经多次见过碎舅为人说事的这种场面。我发现,碎舅为人们所讲的那些道理、故事,大都出自他那些颜色黯旧的书。那些故事简洁、单纯,却爱憎分明。那些堪称经典的故事,一经碎舅那样直白或控辩式的转述,竟产生了一种无可替代的、非常民间化的道德力量。
碎舅家的那个庄子,叫河东李家。在河东李家,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杂姓外,清一色都是本家李姓。李姓是个大姓。据碎舅讲,李姓在历史上就是旺族,贵族,根据老一辈人的追述,这河东李家极有可能就是李世民遗落在西北边地的一个后裔分支。河东李家的人听了,自然就高兴、自足,莫明其妙有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前几年电视台热播连续尉《杨贵妃》,河东李家的人看了,像过年过节一样高兴,晚上吃饭时,家家长面油饼,家家杀鸡炖肉。新闻联播过后,大家就像约好了似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来到碎舅家看连续剧。看着看着,大家就隐忍不住地要发发议论。
“这个女人,可是把咱老李家害苦了。”说这话的人正喝着茶,由于愤怒,他往下咽茶的时候喉结竟咕噜动了一下。
“就是,要不是这女人,咱河东李家说不定在西安城正占着一块地盘呢。”一个年纪大点的响应道。
“也别光怪人家,要怪就怪咱老先人,堂堂一个皇上,把个女人始终顶在头上,不倒霉不垮台才怪呢。”碎舅的儿子说。
昕了这话,碎舅终于忍不住而把烟锅猛吸了两口:“屁的个话,要是按你刚才说的,你就应该把你女人好好管一管。”
碎舅的儿子嘟囔道:“没办法,老先人把头安偏了嘛。”
大家一阵大笑。
看到最后,还是要碎舅出来总结总结的。碎舅倒一罐罐酽茶,说说唐朝,说说李世民,说到最后,自然又要追述一番李家的根基而使大家快活高兴。
河东李家的人就是这样简单而没有城府。
河东李家的人还爱耍钱。这自然还是与碎舅有些关系的。早些年,碎舅嗜好抹金,砍牛腿,河东李家的人便跟着抹金,砍牛腿;近几年,碎舅爱上了打麻将,砸金花,挖红四,河东李家的人就像着了魔一样开始研究学习。但无论哪种玩法,碎舅永远都领着风气之先。
碎舅说:“人一辈子连个钱都不会耍,那你就算是在这世上白活了。”
听了这话,你会觉得这河东李家的人或许跟赵匡胤也是有些关系的。
前些年,我因为拜年每年都要去舅家一次。去了也不怎么受人欢迎,烧了香,磕了头,偶尔地只几个姑舅忙里偷闲过来搭讪几句,其余时间我基本上是个食客、看客。因为过年过节时,其他庄子的人总要聚在一起,喝喝酒,或唱唱社火。而河东李家的人人老祖辈就只有一个爱好:耍钱。舅家的庄子几乎家家都设着耍钱的摊场。
后来,我也学会了偶尔耍点小钱,碎舅知道后异常高兴。
碎舅说:“这就对了,人其实还是有点毛病的好,人一点毛病都没那是最没意思的。”
碎舅还说:“你不要小看了这个简单的耍钱,啥人啥耍法,在赌场上,那是最能表现一个人人品和智商的高下的。”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去碎舅家,一去就成了碎舅家最受欢迎的座上宾。
得知我要来的那天,碎舅会特意让人组织组织,买两盒好烟,邀几个有头有脸的人,他本人也会推掉所有的赌局而整整陪我一天。碎舅坐在我旁边,一边打牌。一边不停地提醒关照我,生怕我因为赌技不精而输得太惨。我也因此躲过了好几年给舅舅舅母们磕头拜年的繁琐。
有一年大年初二,我一到舅家就被几个热情高涨的姑舅包围了。还没吃饭,他们就三下五除二摆好了摊场,邀我砸金花。
我故作为难地说:“我还没给几个舅舅磕头呢。”
碎舅说:“你耍你们的,磕头拜年嘛,那都是些虚套套。”
得了允许,我于是就放开了赌,结果一赌就赌到了大年初三。回到家不大一会儿,我的几个等我磕头的舅舅却不干了,他们联手纷纷找我母亲来兴师问罪。
舅舅们说:“你要把你儿子好好管教管教,还是个国家干部,过年连个头都不磕,一来就知道耍钱。”
母亲说:“还不都是你们河东李家的事,我儿子从来不耍钱,咋一到你们李家就耍钱?我还没找你们的麻烦呢,你们倒找我来了。”
我的几个舅舅无话可说,于是又转而去找我的几个姑舅们。
姑舅们说,“那是他碎爷的事,本来人家是要磕头的,可他碎爷挡着不让,说磕头拜年嘛,那都是些虚套套。”
我的几个舅舅昕了,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知道,在讲道理说事情方面,他们根本不具备跟我碎舅辩驳较量的能力。
在我的十几个舅舅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碎舅。碎舅瘦高个,黑脸,笑一笑,白白的牙齿间就会露出常年吸烟留下的斑渍。碎舅走路时不紧不慢。很悠闲的样子,鹅行鸭步的外八字,使他看上去永远都处在平静和安详的状态中。他喜欢在外衣外面再披一件外衣,出门时抖一抖,很有点脱产干部的味道。
碎舅是个农民,却不怎么下地干活。小时候,碎舅常跟着外祖父到处抹金,耍钱,成年后又当过多年生产队队长。队长自然是用不着下地出苦力的。后来,包产到户,这下该轮到他下地干活了吧,可他的几个儿子却已忽隆隆长大成人,他自然又不必下地干活,照例当他的甩手掌柜。一个农民,一辈子不怎么下地,而日子却过得不温不火,游刃有余,这也是需要一点透悟人生的玄机的。
碎舅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已娶妻生子,分家另过。由于都是农民,三个儿子均老实本分,不生一点事端。当初老大成家时,碎舅让另外两个儿子出门打工挣钱,安顿好了老大,再安顿老二,同样的办法,三个儿子很轻松地就成了家。这在河东李家也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前年五月,碎舅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病来得非常迅猛而蹊跷,事前没有一点征兆。等一家人不得不下决心住院治疗时,当地的乡镇医院已是毫无办法了。
一家人浩浩荡荡来到了市里。
三个儿子左呼右唤,就是住不进医院,医院需要许多手续,三个儿子没一个念书识字的。万般无奈,碎舅就托人给我打了电话。我和妻子闻讯赶到医院,托人找关系,总算安顿了下来,结果一检查,左肾坏死。也就是说,如不尽快做切除手术,那剩下的一个肾也要被感染坏掉。一家人一下子傻了眼。
碎舅说:“算了吧,不做了,我这人把生死二字看得很开,人活百岁也是个死嘛。”
三个儿放声痛哭,说:“你再不要胡说,我弟兄三个就是拉也要把你拉回来。”
接着弟兄三个分别拉住了我,说:“哥,我们不识字,跑路都跑不到地方,你只要把看病的人找对。我们就是拆房卖院也要把他老人家救活。”
其情其景,令人落泪。
我赶忙点头答应一定竭尽全力。
第二天,三个表弟左挪右借凑足了手术所需的两万元钱。
在等待住院手术的几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和碎舅在一起。碎舅显得很忐忑,一会儿在院里转转:一会儿又躺在床上长嘘短叹。他显然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开始考虑起了自已的生死大事。
碎舅说:“我这人说起来也没啥本事,就是勉勉强强完成了任务,老人抬埋了,儿子成家了,说起来也没个啥遗憾的。”
转了一圈儿又说:“要说遗憾嘛,还是有些,就是三个娃娃都把书没念下。”
折腾了几天,碎舅面黑如铁。
很快地,我和妻子托人找关系找到了一位专家。专家在看了所有检查的资料和亲自问诊后说:“这个手术嘛,暂时可以不做,那坏掉的一个肾,其实是几十年慢慢干掉的,留下并不会造成另一个肾的感染。”听了这话,我们就像犯人听到了赦免令一样群情振奋。
碎舅说:“回家吧,快点回家。”
三个儿子麻利地办好了出院手续。当天下午即打车回家。
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来探病问询的人络绎不绝,一拨连着一拨。碎舅一边给人们讲解病情,一边就畅谈在城里这几天的切身感受。
碎舅说:“城里啥都好,就是空气没咱河东李家好,人情也薄。”
碎舅还说:“人在生死面前都一样,就我这么刚强的人,一进医院还是七上八下,心里到底没有个着落。”
说了一会儿,碎舅忽然按住一个小孩子的头说:“狗儿,不要成天想着耍钱,还是要好好念书呢,耍钱那把戏,说到底也不是个啥好营生。”
现在,河东李家照例年年耍钱。碎舅也耍,但对后辈晚生们的耍钱。碎舅显然是没有以前那样喜爱和热衷了。
守岁
早晨起来,推开屋门,晃眼的白光把老杜刺得后退
了一下,但很快老杜就明白过来了,没错,昨晚又是落了整整一夜的雪。雪在静谧的清晨,就像覆在婴儿身上的棉被一样,似乎含着浅浅的呼吸。但这呼吸却是那样的清冽和寒凉。迈过门槛,走下台阶,老杜立即感受到了一种像冰水浇身那样的感觉。其实,从一人腊月开始,老杜就一直被这样彻骨彻肺的感觉包围着。
狗日的,竟然能下十几天的雪,人老祖辈都没见过啊。
老杜一边恶怒地骂,一边就又很快缩回屋子。这时女人已被吱呀作响的开门声吵醒了。女人一边缩在被窝里穿裤子一边催促他,快打开电视看看,看广州那边昨晚下雪了没有。
老杜说,看个屁,全中国都在下,广州哪有不下的道理。
尽管如此,老杜还是很快捅旺了炉子,打开电视。这时女儿花花也已散乱着头发下了炕,趿上鞋,像一只慎于走路的小猫一样坐到靠近炉子的电视前。电视里正在播放大年三十的早间新闻。说是新闻。其实内容与昨天的并没多大变化:照例是下雪,抗灾,说是湖北山区的一个什么村子,进山的道路都让大雪封住了。路面跟铺上了玻璃一样,人一走一滑,解放军正开着装甲车往进送米送面呢。
唉哟我的碎社呀。女人突然这样叹道。
因了这一声叹,老杜终于没能忍住盈于眼眶的一点泪水而吧嗒一声滴落下来。半年没见上大学的儿子,老杜这时竟扯心扯肺地思念起来。
都是你个老不死,儿子本来是要回家的,散学了,放假了嘛,可你非让他走个海南,见个广经(世面的意思),好嘛,这下娃可把百年不遇的广经都见了嘛。
听女人这样埋怨,老杜倒是有些心平气和了。老杜说,走海南没错,我也是念过两天书的,你没听老辈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走路和读书也是一样重要的。坏就坏在这大雪上,我知道的,这南方原本就是不见雪的,谁承想今年竟下个没完没了,竞下得都成了灾了。
争了一会儿,老杜和女人又坐下来看电视。这时电视画面一转,一阵祥和之音过后,主持人又开始播报全国各地喜迎春节的新闻了。老杜这时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地说,快洗脸梳头,今天是大年三十,咱们咋说也得把这个年过好。
得了鼓励,女人和女儿也开始动作起来。她们知道,一年之际在于春,年三十这天,怎么说也不能被忧情愁绪占了去。
洗漱一毕,老杜便哈着白气从屋子里出来。他出来的第一件事首先是扫院、铲雪,然后推了架子车将雪倒进门前的坡地里。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是热烈的,喜庆的。他在不停地指挥着女儿,把炉子架旺。水烧上,把那个艳红的灯笼用长竿挑了挂到高房的檐头上。之后,他便用热水和了一摊麦草泥,把包括牛槽、羊圈、粮囤、门楼,以及院墙里外凡是泥皮剥落的地方。都用一把圆头泥笔仔细地泥墁一遍。这是杨格庄每一个农民在大年三十这天早晨必做的一件事,寓人勤春早之意。做完这件事,村子里已嚷嚷而动,不知谁家的孩子,竟耐不住大雪封门的寂寞,跳上村头的崖畔上二话不说放了一个二踢脚,嗵地一响,年的味道便像溪水一样远远地从雪地那儿洇过来。
晌午过后,老杜又把院子扫了一遍,桌子抹了一遍,他还打算把供桌上的香炉灌上一些麦子或糜子,女人却喊他吃午饭了。大年三十这顿午饭也与平日有些不同,吃的是养面、地软和肉臊子做的杂和饭,名荞面搅团,取阖家团聚,增福添寿之意。这也是杨格庄人在大年三十这天减免不了的一个规矩。吃饭的时候,女人忽又重重叹息了一声。这一声叹,立即把老杜从年节的气氛中拉了出来。他这才想起远在广州的儿子今天竟还没有打电话来。
他捏着筷子对女儿说,花花,你哥昨晚咋说的,咋今天到现在还没打电话来。
女儿说,我哥说他在那边挺好的,让你们放心。
老杜说,好知道他好,但吃在哪里,住在哪里,年三十到底咋过的嘛。
女儿说,我哥说他已回到学校,学校让他们在广州过年,学校还给他们预订好了年夜饭呢。
这时女人又换了一副忧戚的神色,说,外面的年饭再好也不如家里的,我娃今年可是把罪受下了。
听完女人如此说,老杜陡地感觉鼻子一酸,一滴眼泪差点就夺眶而出掉到了碗里。
吃过饭后,女人忙着做肉做馍馍,老杜则把大小四个屋子的窗框卸下来贴窗花。本来,这件事放在往年都应该是女人干的,女人会像收拾嫁妆那样把所有的窗子收拾得蝶飞蜂舞,花开花放。女人是庄里有名的巧手,剪得一手好窗花,她剪下的“狮子滚绣球”“和“喜鹊登梅”曾经在县上举办的民间艺术展上得过头奖。但女人今年却没有了好心境。女人只把原来剩下的一些旧窗花拿出来让他贴。尽管如此,他还是贴得很慢,很仔细,他似乎要用这些踏实的举动来平抚年节时留给女人的浮躁和伤心。
贴了窗花,又贴对联。对联是村里一个退休教师给写的,字写得古旧难辨,意思却是村里最新也最见水平的。上房门上是:“奥运之年梅花放春回原上燕鸟归”;大门上是:“棠棣联根强中脉炎黄固本壮华魄”,既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也暗含了这一年在中国即将发生的几件大事情。除此之外,其余几个地方的春联也是各不相同,牛圈里是“槽头兴旺”,上房炕墙是“身卧福地”,当院粮囤上是“五谷丰登”,大门外柳树上是“出门见禧”,而灶房供牌上则是年年不变的一句“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贴好了对联之后。屋里屋外忽然就有了喜气洋洋的味道,白的雪,红的灯笼,而那苍劲的、横平竖直的方块汉字和汉字下的艳红对子则把年的气氛一下子就烘托得格外地道,格外浓烈。
下午的时候,老杜的大哥来串门。大哥身材不高,戴着一顶新蓝帽子,身上的显眼之处除脚上的一双黑亮皮鞋外,制服上还挂了一条围脖,身上披了一件黑呢大衣,进门后先跺跺脚上的雪,将两个肩头耸耸,其举止做派颇有些脱产干部的卖弄味道。
坐下之后,大哥便开始和他拉呱,拉世事、拉家常,拉着拉着就拉到晚上吃年夜饭的事上。
大哥说,今天晚上咱们到我家坐夜(守岁之意),我给咱们弄几个菜,弄几个蒸碗子,到时候你跟他二妈两个都来,咱们吃个团圆饭,弟兄们嘛,咋说咱们也是个一笔写不成两个的杜字嘛。说到这里,大哥便免不了要埋怨几句没有赶回家团聚的侄儿:这个娃。人家电视上都唱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你的事再紧总紧不过过年跟娘老子团圆的嘛。
如此一说,老杜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他赶忙端出儿子因去海南误了归期的事为远在南方的儿子辩解。
老杜说,娃本来是想回家的,娃老早就说想家得很,可我让娃去了一下海南,见了些广经,没想大雪把娃回家的路给堵了。
大哥说,你这个人啊,不是我说你,学生娃娃嘛,看的个啥广经。
说着说着,大哥就有些责怪的意思了。
这时老杜赶忙将话题岔开。老杜说,闲着呢,闲着呢。心里的愧悔却是比任何时候都重。
闲谝了一阵儿,老杜便叫女人给大哥装了些丸子,装了些油饼,打发出门之后就又返身走回来。这时候,中央电视台正播放春节联欢晚会特别节目,一个年轻的女主持人拿着个话筒正在不厌其烦地征求滞留旅客对晚会的意见。一场大雪竟把归期未卜的人们的情绪调动得那样浓烈,那样足。一个老太太说,爱看相声;一
个中年人说,还是赵本山的小品好;一个穿皮夹克留长发的小伙子则干脆说,无所谓,演什么都行。看着镜头慢慢移向人山人海的车站,移到校园,老杜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起来。这时候他最希望的就是他远在广州的儿子忽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哪怕不说话,不笑,只在电视上闪面一过也行啊。可这个不切实际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直到节目结束,电视屏幕上也没出现他的儿子碎社的影子,他不禁又伤心了一回。伤心了一会儿,又不伤心。广州那么大,人那么多,人家电视台咋就那么凑巧那么容易地碰到你家碎社呢。再说即使碰到,人家不采访你不拍你也是枉然。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的情绪又慢慢好起来。他想,年好过,月难过,年关以后的日子那才叫真正的日子呢。
黄昏到来以后,村子里的气氛更加热烈张扬,二脚踢的大炮不停地在空中炸响,远处的山脚下,则正有一阵阵喧天的锣鼓贴着雪地隐隐传来。敬过天地,进庙烧香的时辰就到了,这时候就有三三两两的庄户人从各家门里出来,弓着腰身,迈着碎步,在铺满白雪的土路上走着,身上的崭新衣服使他们的表情更加恭谨、谦和。他们笑着,互致问候,腋下则夹了用以向上苍神灵表达虔诚的香表与烛台。进庙以后,先敬土地,后拜方神。随后就按照排位的大小将供在庙里的二十四路诸神一一进行叩拜。击打钟磐的声音不绝于耳,庙前的槐树下,一群不大不小的孩子正在比赛着堆雪人,打雪仗,放花炮。
上了祖坟吃了晚饭后,就该到真正守岁坐夜的时候了,这时候老杜就感觉左右为难起来,因为女人不愿到别处去。女人是铁了心要坐在家里守这份孤清,而老杜的心里却有着更深一层的障碍和顾虑。
老杜说,这不去嘛,大哥叫哩;这去嘛,人总觉得别别扭扭的。
女人磕着瓜子说,坐个夜嘛,有啥别扭的。
老杜便对女人有些鬼崇地说出了埋在心里的几个别扭:你不知道,咱的娃今年不在,我看见人家儿孙满堂心里就难受,想咱的娃;再者,咱的娃今年考上了,到了广州,而哥的娃一个都没考上,这一提起娃娃念书哥脸上就不高兴。
听到这里,女人就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看你这人,狗肚鸡肠的,我咋就没看见他大爹不高兴,,咱的两个娃考上的时节他大爹不是还给过盘缠,给过一条床单哩嘛?
老杜便显得很有心机地说:那是两回事嘛,我哥心里咋想的我还不清楚?
女人便转回来安慰男人道:既然如此,你就少说两句,少喝两杯,弟兄们嘛。
正说话间,大哥的儿子一得就推门进来了。一得也是奉了父母之命来请他们吃饭坐夜的。一得说,我大说,让我二妈和花花都一块过去,一家子过年过节地凑到一起热闹。老杜便朝女人脸上瞅一瞅,然后转身对一得说,我过去,你二妈就算了,人常说坐夜守岁哩,这家里好坏得留个守的。花花说,我也不去,我还要等我哥的电话呢。老杜便在女儿的头上抚一抚,之后,又披了大衣装了些核桃糖果之类随一得出门了。
走在村道上,老杜的心里不由得一热,往日静静悄悄的杨格庄这一刻忽然间变得格外亮堂,格外喧闹,家家的门前或高房上都挂了红彤彤的灯笼,雪光一映。天地间忽然就布满了浓醇的祥和之气。雪忽忽悠悠下着。院子与树木顶上,则有星星点点的礼花当空炸放,仿佛天庭里忽然撒下来的异芳仙葩。雪地上走动着很多的人。很多人的影子被放大了投在路的另一侧。热闹而夸张地随着人的走动在不停地变换着各种形状。路还是原来的路,人也是原来的人,可是这一刻却变得陌生而新奇,被雪光和烟花点燃了的杨格庄似乎更像一个吉祥喜庆的幻境。
走进大哥家的时候,大哥正给孙子们散钱散核桃,大哥坐在中间,孙子们围坐两边。虽说世事变化很大。但杨格庄这种大年三十散糖散压岁钱的风俗却没变。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趁这个机会,老杜也将自己带来的一些干果之类散了,然后坐在炉边的一个小凳上等候烧香。一袋烟的功夫,厨房里的供品做好了,这时候大哥洗了手脸,挽起袖子,将那些鱼呀肉呀的供品摆好之后,便率领一家老小中的所有男人在祖宗牌位前焚香磕头。拜了先人,再拜活人,这时候大哥脸上洋溢出了一年四季少有的快乐与幸福。七八个儿孙呼啦一声跪倒,口里齐呼“给大拜年了”,“给爷拜年了”,遂双手触地像鸡啄米似地猛叩一气。拜完之后,大哥笑眯眯地指着老杜说,给你二大、二爷爷磕一个。这时儿孙们也像前次一样,演戏似地跪倒在地又拜一回。这一仪式过后,就该到吃肉喝酒的时候了,这也是杨格庄人在大年三十晚上守岁坐夜时减免不了的一个内容。一家人,包括女人和孩子,围着炕桌团团坐定之后,一盘刚出锅的肉块就端上来了,肉是真正大块的肉,酒却是用一个个如拇指蛋大小的杯子盛了的,同时旁边还放了四个如肝肺蹄筋之类调拌的凉菜。
吃肉之前,大哥让一得将酒杯一一斟满,男人喝白酒,女人孩子喝葡萄酒,举杯过顶后,大哥便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对大家进行祝福:大家每人喝一杯,要喝干。这就算我们一家人一年又到头了,除夕之夜,团圆的日子嘛,大家吃好喝好,也不要忘记给老先人敬供烧香。说完之后率先干了。之后大家一一干了。这时候屋里的气氛渐渐变得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将洗净的手伸向那个盛肉的大盘子,蒙古人一样大块大块吞咽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老杜的心里始终是翻腾着一些小小的波澜的,因为在大哥一家欢声笑语之时。他总是不由自主想起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他想,要是儿子在大年三十能赶回来,能一家团聚,他的屋里现在也该是如大哥家一般的温馨和热闹了。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的鼻子又陡然一酸,心里忽地就想到他此时略显冷清的屋子和正独守空屋的女人和女儿。
他端过一杯酒,也向大家祝福了几句,说,今天晚上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可我昨觉得头昏脑胀的,这样吧,这一杯一喝你们喝,我就回去了。
大哥却一把拉住他,显得有些生气地说,你看你这个人,我知道你的娃不在,把你叫过来就是要叫你高兴的,一家子嘛。
如此一说,大哥的几个儿子便蠢蠢欲动,他们高挽了袖子,执杯把盏地开始给两位长辈轮番敬酒。酒过数巡,老杜已有些热汗淋漓,大脑在酒精的作用下竟一点一点兴奋起来。他这才有兴致放眼对大哥的上房进行细致的观察。大哥家的上房果然与平日有些不同,雪白的墙壁,五彩的年画,用花花绿绿的商标纸拉成的顶棚闪闪有光,而靠墙的四周则用印着龙凤图案的花布齐齐围了一道墙裙。地上是本地杨郎农具厂生产的烤箱,靠墙则摆着两只漆成金黄颜色的大柜。电视机、VCD、洗衣机、座钟,凡是杨格庄殷实人家有的大哥家几乎都有了。大哥家还有一辆“金蛙”牌的三轮农用车和一台大型磨面机哩。
大哥说,这都是娃娃们的功劳,其实我屁事也不管。脸上竟笑出个圆圆的“几”字来。
老杜说,治家也要用脑子呢,光一个劲儿下苦力乱抓挖,往后还是出息不大。
话刚出口,老杜就有些后悔,他怕大哥怪他借此来有意炫耀自己的儿子,侧脸看时,却见大哥很坦然,一副欣然领命的样子。大哥说,书总还是要念一些的,比如我家一得,要不是念过几天书,不要说到深圳去打工
挣钱,恐怕到现在连咱们银川在哪搭都不知道呢。这样说着,便把目光投向一得。这时一得便颇有些神气活现的样子。他因为早几天回家而没被罕见的大雪隔在南方。他说他回家的那天深圳还热得能穿裤头。没想不几天,漫天大雪竟把大半个中国都覆盖了。这时电视上开始了向南方受灾地区的募捐活动。一得拿起电话也按照主持人的提示方式捐了款。捐完款,他就指着电视上一个唱歌的女明星说,这个人,我见过。见大家一副疑惑的样子,一得便益发得意。他一边往杯子里倒酒,一边就借此向一家人卖弄自己去深圳打工时见到这位歌星的一些经历。
人家一边唱,一边就把话筒举过来说,大家一起唱,大家就跟着一起唱。唱到高兴处,人家就走下来跟大家握着手唱,有时还拉着观众席里的人一起对唱呢。
一得媳妇说,那人家跟你唱了没有?
一得说,唱了,唱的《天仙配》。
一得媳妇脸上便悄悄一凉,鄙夷地说,嘁!
一得便有些忿忿然,说,怎么没有?我还过去摸了一下人家的手呢。
一得媳妇便在一得头上狠狠打了一巴掌。
酒喝到半酣时,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也渐近高潮。这时一位年轻的女主持人手握话筒,微笑着向大家宣布,再过几秒钟,新的奥运年就到了。大家立即欢呼雀跃。就像香港澳门回归的倒计时一样,还剩十秒钟时,大家齐呼阿拉伯数字,从“10”喊到“1”。“1”字刚落,新年的钟声就响了,随后屋子外面响声大作,弥天漫地的鞭炮声像爆豆一样从村庄上空隆隆滚过,紧跟着七彩的烟花便从各处的院子里飞出,哗哗剥剥照彻整个夜空。看到此景,大家再也坐不住了,一得和几个小孩率先冲出屋门,把摆在桌边的花呀炮呀悉数拿出,喊着叫着满地满院乱放起来。
老杜想,看来今年真的跟往年有些不同。这样想了一下后,他便立即想起儿子说过年夜打电话的事,抓起大衣不顾大哥的挽留冲出大门,直奔村北头。村北有个小卖部,紧傍小卖部的那座四方小院就是老杜的家。路过小卖部时,一群喝了酒的小伙子正在放花放鞭炮。七彩缤纷的光焰仿佛要涂染了雪地。千声万响中,老杜终于跌跌撞撞回到了家。一进家门,女儿花花立即将他搀扶到放电话的那个方桌旁,儿子的电话像安了电子眼一样适时而至。儿子大概也在一个什么地方聚会。人声嘈杂,儿子的声音像裹在万千浪花中的一滴水珠一样远远地飘来:大,我在学校礼堂里……之后就什么都听不清了。这时女人忽然指着电视机的屏幕说,快看,那不是咱们的碎社吗?只见电视荧屏上,果然就闪出了儿子碎社的身影,在一群欢呼雀跃的学生中间,他家碎社拿着个手机,也像其他人一样笑逐颜开,兴奋至极,电视里的声音和电话里的声音一下子合拍了。虽说只有一刹那,但老杜的心里却有了万钧雷霆,他在恍惚之间觉得世界变小变近了,他似乎还能看见所有的人在这一刻都神采飞扬,情绪不能自抑。之后,他像人定了一样举着那个话筒,直到呼声渐止,电视画面又转入其它的晚会节目之中。
走出屋子,老杜的脑子里金星闪烁,儿子的形象墙上的画张一样印在他心中。他想,他得赶快把这个消息说给大哥和几个侄子。正在此时,山脚下的那个村里忽地升起一团焰火,到空中后又嘭嘭几声炸响,几朵礼花在夜幕上渐次闪烁、放大,像幻境中盛开的一些九月菊花。
爆竹如豆。
杨格庄在这一刻正沉浸在无边的欢乐之中。
责任编辑房义经
- 时代文学·上半月的其它文章
- 毛泽东在1958(下)
- 天堂与炼狱之间
- 养父养母
- 四十而惑
- 笔杆子
- 西瓜、电鱼船和魔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