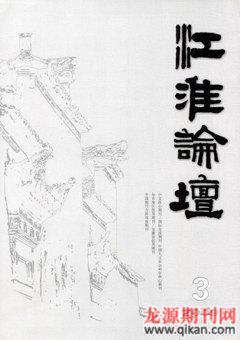巨赞论佛教徒人生观之改造
李华华
摘要:巨赞是中国现当代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之一。他认为广大佛教徒应树立“先立乎其大者”的人生观,为此,要实现三种改造:在理想境界上从执着到断执的改造,在信仰问题上从旧观念到大乘菩萨行的改造,在践行问题上从消极避世到弘扬爱国主义的改造。其人生佛教不仅及时引导了转型社会中的佛教徒,还促进佛教与社会、与人生的融合。
关键词:巨赞; “先立乎其大者”; 执着; 大乘菩萨行; 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巨赞是中国现当代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之一。从清末以至当代佛教,巨赞都经历其中。在社会主义时代,随着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何关注僧尼的人生,如何改善他们的精神面貌,以促进佛教与时代、社会的融合就成为这一时期佛教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巨赞法师提出“先立乎其大者”[5]246的人生观,认为广大佛教徒应以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的人生理想作为奋斗目标,来庄严佛教门庭。这是他人生佛教的宗旨。为此,佛教徒要实现三种改造:其一,在理想境界上从执着于求永生和福佑的迷信到无我、断执的改造;其二,在信仰问题上从返本还源论、因果轮回论等旧观念到大乘菩萨行的改造;其三,在践行问题上从消极避世到不离世俗、弘扬爱国主义的改造。
人生目标:“先立乎其大者”
“先立乎其大者”本是儒家格言,巨赞则从佛教的视角进行解读,将其视为佛教徒应该树立的人生目标,为他们人生观的改造及时指明了方向。
何者为“立”?自觉地献身正所谓“立”。巨赞认为,一个人的“立”,不能片面地依赖周围的客观环境,应该更为重视主观的努力,关键是佛教徒这一特殊群体在主观方面如何去“立”。他说:“尊重自己,不怕艰苦,不贪小利,才能立得稳,立得久,才能显得出肝胆、胸襟和担当来。”[3]882
只有尊重自己才能有所“立”,广大佛教徒只有懂得如何尊重自己,不为名声所羁绊,才能做一个有骨气的人,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同时,只有不怕艰苦,才能拥有“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4]的精神,这样,才会以实际行动熬过苦痛艰难的岁月,才会为了伟大理想而勇于牺牲。满足上述“立”的条件,自然就能显出肝胆、胸襟和担当来。巨赞认为,所谓肝胆照人,就是能以性命相见,所以一个人能以肝胆相照才会有气节、有魄力,从而情愿与众生共患难、为真理而牺牲。对于胸襟,则要开拓万古心胸。万古既包括无量无边之过去,也包括无量无边之未来。在巨赞看来,一个有胸襟的人,“要把整个生命投入全宇宙的滚滚洪流之中,以开发其无穷尽的宝藏,而争取自他物我的欣合无间”[3]883。至于担当,巨赞指出:后期禅宗提倡的“超佛越祖”就是一种,“佛”、“祖”本无可超越,但学人不能无此气概;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精神,也是从担当中来……历史上慧能、玄奘、鉴真等高僧大德的成功也绝非偶然,巨赞强调,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真精神光芒四射,这种真精神就是“血性”,这正是他们“立”的基础。
能“立”才能成其“大”,佛教徒还要明白“大”的含义。巨赞认为,孟子以“思则得之”[5]246为“大”,就是要我们利用思考的能力,确定一个崇高伟大的目标作为日常行为的依据。孔子说“天生德于予”[1]72,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98,耶稣说自己是“上帝之子”。这些伟大人物的自命不凡正表明他们“思”有所得:确立伟大的目标,才能够坚贞不拔地完成理想中的事业。所以,巨赞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先立乎其大者”,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的成功也是如此。
“大者”就是最伟大的理想,这在佛经中被认为是“一大事因缘”[6]。巨赞强调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作为“一大事因缘”的最好注脚,并认为这和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理想也并无冲突。可见,巨赞在当时对佛教徒人生观的改造,并非单单为了佛教,而是要佛教徒通过对佛教的确切认识和真实信仰,将上述最伟大的理想付诸实践,使佛教不离世俗。对此,李向平说:“其人生佛教的立意,也近似于太虚的人生佛教或人生佛学,关注宗教理念和社会政治理想的合一。”[7]
然而,过去佛教徒的表现往往是“先立乎其小者”[3]885。这种情形使唐宋以后佛教界的高僧大德越来越少。何以至此?巨赞模仿王安石的话答道:“佛门淡薄,收拾不住英雄,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里,英雄豪杰之士都走入共产党那方面去了。”[3]886释迦牟尼的真精神在佛教界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自然满足不了英雄豪杰的要求,所以出现佛门淡薄的现象。巨赞指出:一方面,佛教徒每况愈下,他们大都躲在角落里只顾个人修行,遇到困难就磕头求菩萨感应,而且越重视修行的佛教徒心量越狭小,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同情心;另一方面,那些不讲修行或乱讲修行的佛教徒肆无忌惮,甚至没有羞恶、是非之心,所以,佛教徒身上普遍缺少“血性”,也自然没有胸襟、肝胆和担当。随着佛教真精神的丧失,佛教徒落后的精神面貌大大降低了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吸引力,这种状况若得不到改善,佛教就会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巨赞强调,佛教徒要续佛慧命,就应该“先立乎其大者”,将佛教淡薄的门庭及时庄严起来。
巨赞认为,人生问题如果解决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积极的生活目标,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也能得到正常解决。然而,人生问题实在是复杂、严重而又值得毕生用力的。诚然,广大佛教徒树立“先立乎其大者”的佛教人生观并非平地起峰,在他们内心首先要经历理想境界的改造,这种改造能够引导他们不断向内追求,并激励他们的德性与善行。
理想境界:从执着到“断执”
佛教徒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在巨赞看来往往是陷溺于执着。执着会导致人的自私,而人们为了私欲的满足常常会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所以,巨赞强调,执着是导致世间争夺、纷乱、虐杀的真正原因,执着使人的心理处于不简单的状态。那么如何去破执着?人们应该在心理上做出调整,适当地控制欲望,顺理而行事,其行为必然会符合社会规范。何况,佛教的缘生之理受因果规律的支配:人们是享福报,还是遭报应,都是由人自身的善恶行为决定的。在这种报应论的约束下,人们除非自甘堕落,否则非要积极向上不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的道德行为被充分激发。
此外,执着与迷信的盛行有密切关系。由于求长生不死是古往今来人类情感上一种共同的强烈要求,所以不时出现各种神仙法术大兴的局面,许多人都把这种迷信的形成完全归罪于佛教。巨赞认为,这不合历史实情,因为各种形式的迷信活动在古今中外的宗教中总是很流行。他认为,迷信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是求灵性的永生,其二是求现世或来生的福佑。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若能常常体验宇宙无常的实相,就能够破这两种迷信,那么,在立身行事上就会有个人见解,在精神上也不会再受是非荣辱、得失苦乐等的干扰,从而慢慢达到孔子所谓“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87的境界,也就是佛教所谓的“断执”境界。在巨赞看来,人们一旦达到 “断执”境界,就可以获得崇高的人格与伟大的德性,那么,不管他们从事何种类型的职业,如治国、育人、经商、打仗等,都会很出色。
佛教徒要达到破除执着后的“断执”境界,就要对佛教缘生唯心、无我性空的“教理”有所认知。巨赞说:“佛家承认人为宇宙之中心,而心识又为吾人的中心,那末世间的一切问题,应该决之于吾心”[3]676、“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念念迁变,莫有一劫停留,自然没有一事一物能够常存不坏,所以无常是宇宙的实相。无常之故,由于缘生。”[3]676如上所言,佛教以一己之心为宇宙之心,缘生的枢纽操之于人们的心,而与神的旨意无关,这样,人们就走出了神的控制与威慑,具备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角色转换的可能性。由于人们一直生活在缘生的生灭起伏中,经历悲欢离合、兴废存亡,相当痛苦,实际上就是处在生死轮回之中,而人人都有避苦求乐的愿望,人人都渴望达到解脱的境地。巨赞强调:解脱与否的关键在于自我,在于“自家”如何去“改造环境”。由此,佛教徒才能在修行上、生活中彻底摆脱鬼神术数的迷惑,真正关注人心、人生、世间,以主体圆满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行为去追求“断执”境界。在这一意义上,“先立乎其大者”人生观中“大者”在现实中才有形成的可能,“立”的过程也会由于受到不断的激励而更加坚定和长久。
“断执”的境界也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自在、解脱。一切事物待缘而生,所以,万物没有自性,是性空无我,又是非常非断的,即一法不取、一法不舍。巨赞认为,《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8]、禅宗六祖慧能的一个有名的偈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9]都可用来诠释这种境界。真正的佛教徒在思想上应该具备这种在人世间追求超脱、圆融境界的立场和决心。
然而,广大佛教徒对于缘生无我等佛教基本“教理”一般存有重大误解,这使他们无法与封建思想彻底脱离关系,从而直接导致他们出现信仰问题,并在践行中一味自修自了,这些状况若得不到根本改善,“先立乎其大者”的人生观也只能是一个口号。
信仰问题:从旧观念到大乘菩萨行
佛教徒的信仰与他们人生观的树立有直接关系。在现、当代中国,人们大多将佛教的功能定位于祭祀、求福佑、做经忏等一些宗教仪式上;不少佛教徒也无法理解佛教的本旨,从而导致思想上愚昧无知,行动上畏缩退避,他们又不能像基督徒那样开展社会事业,往往被人们视为“赘疣”。如巨赞所忧,在解放后的三年内,佛教信仰已成为问题。在上述状况下,巨赞提倡的“先立乎其大者”的人生观容易令广大佛教徒费解而抵触。所以,解决佛教徒的信仰危机,实现从旧观念到大乘菩萨行的改造势在必行。
为阐扬正信,巨赞首先批判当时流行的返本还源论和因果轮回论。返本还源论认为:“‘真心本净,被客尘所染污故名为杂染,离烦恼时转成无漏,恢复本来清净的真心,称之为佛,或名正觉。”[3]917对此,巨赞进行否定,认为真心并非本净,并指出上述理论从唐末天台、贤首两宗合流以后就盛行起来,几乎成为佛教理论上的正统流派,尤其在禅宗盛行之后,佛教界一直忽视“教理”的研究,“致使佛教徒们为着返本还源而钻进牛角尖里去,和现实的社会与现实的人生完全脱离关系,当然也就无法体验社会与人生,进而改造社会与人生”[3]918。事实上,明清以来,中国佛教讲究遁隐山林、闭门静修,这种不问世事、漠视人生的倾向使佛教的发展逐渐背离了佛陀人生教化的本怀,最终脱离了整个社会的进程。
此外,一般佛教徒还把因果轮回视为佛教理论的宝藏。巨赞指出,一般人因为害怕死后或未来生命的堕落,又不理解因果轮回论是对佛教的宗旨——“无我”的注解,从而变成忠实的定命论者,丝毫不能发挥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主观能动的积极性,所以就消极退缩。可见,巨赞用佛教的“无我”宗旨来统筹因果轮回,佛教徒如果能够掌握现在,以现在或当前的一念为中心,就会实现“无我”;如果放弃当下的现实,只在意过去因及未来果,就会滑入定命论,使佛教生动活泼的局面丧失殆尽。
佛教徒如果在理论上被返本还源论与庸俗的因果轮回论所束缚,巨赞认为,那么,他们在修持上也必然产生两种偏向:其一,为逃避现实而求生西方。佛教徒往往只站在自身解脱的角度去追求理想的西方净土,根本抛弃了佛教救度众生的理念,也就是把方便当作真正目的;其二,为自私自利而了生脱死。一般佛教徒终日兢兢业业地忙于了生脱死,他们往往不明白:佛教从“无我”出发,以无得为归,头目髓脑都可以舍弃,生死大事也就彻底了了,所以有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庄严菩萨行。这两种偏向都违背并损害了佛教的真精神。广大佛教徒正是由于无法分清是非邪正而不重视自己的信仰,那么,在人民民主时代,如何使佛教徒发起信心,保持对佛教的真实信仰,从而发扬佛教本有的“无我”精神去为众生服务呢?
巨赞强调,要根除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封建迷信思想。在封建时代和民国时期,“佛教原来所具有的积极救世的精神湮没不彰,佛教徒的思想和行动也大都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革命的斗争生活,隔离得很远”[3]922。所以佛教徒要及时与旧观念绝缘,并坚信“大澈大悟,会心处不在远,肯死才是了生死,往生西方为的是改造东土,三业清净应从烦动恼乱中锻炼,现前荐取,不用他觅”[3]760。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佛教徒往往认为要先求得《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中说的“末尼宝珠”,再去充济有情。巨赞指出,这只是一种比喻,每个人身边都有一颗现成的、精光圆明的“末尼宝珠”,只要他们随时随地、毫无懈倦地做充济有情的工作,“末尼宝珠”就真正起了作用。总之,佛教徒的修行应是现实、具体、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的,而不是清闲自在、高高挂起、利己的;否则,佛教徒不但会在新生的社会制度下吃苦受累,甚至出现被人们鄙夷、淘汰的局面,还会妨碍革命与建设。这恰恰体现了巨赞对佛教徒深厚的人生关怀。
对佛教徒而言,一定要摆脱只追求个人解脱的狭隘观念,因为这是纯粹的自利。巨赞说:“现在我们根据教理要强调利他,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是‘新的道路,喧然如春。”[3]754大乘佛教强调自利利他,实际上,利他既是一个帮助众生解脱的过程,也是一个使佛教徒个人经受磨砺、锻炼本领的过程。巨赞认为,佛教徒要经常反省自己是否以大悲心在日常生活中去化引众生、是否真正地将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众生利益之后、是否真正在众生身上培养自己的福德,从而利他济世,以实际行动去获取人们的尊重。这种自利利他的精神正是巨赞所强调的大乘菩萨行的特质。“所谓大乘菩萨行,是在生死苦难中,烦恼纷扰中开展出来的。也就是把人家当作自己,从为人的工作中充实自己。所以大乘菩萨深入群众,随众生投入驴胎马腹都可以。”[3]730同时,巨赞认为,“一切艰难困苦都成为菩萨行人的炉锤或良药”[3]930。据此,大乘菩萨行与“先立乎其大者”的佛教人生观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佛教徒要真正地了生脱死,就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随时修行,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大乘菩萨行的真精神。
信仰问题一旦解决,广大佛教徒“先立乎其大者”人生观的树立就有了坚实的保障。那么,这种人生观的价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表现出来?这就离不开佛教徒积极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的践行。
践行问题:从消极避世到弘扬爱国主义
在巨赞当时,佛教徒的践行主要表现为自修自了的修行,这种消极避世的做法与“先立乎其大者”的人生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巨赞呼吁广大佛教徒在立身行事上关心时代,关心国家和民族。在巨赞看来,佛教徒的爱国主义有着从释迦牟尼到当时的历史传承;佛教徒坚持爱国主义,就是要积极参与支援抗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社会主义建设等活动。实际上,这些行为更深刻地体现了、并严峻考验着佛教徒“先立乎其大者”的人生观,也是他们将爱教、护教的观念投放到爱国大背景的具体表现。
不少人都强调佛教主张“戒杀”、“忍辱”、“慈悲”、“方便”、“出世”及“四大皆空”等,那么,佛教徒高扬爱国主义传统是否违背佛教的教义呢?巨赞指出,对于“戒杀”,出于口腹之欲或其它自私自利的冲动而杀害生命的行为是佛制戒律不允许的,可在现实中,如果为了救护众生,这种杀戒是可以开的;“忍辱”并非是对任何事情都逆来顺受或一味退缩,而是要人们在艰苦危难、被凌辱的境地始终保持可贵的坚持性,并在内心做到无怨无尤;对于“慈悲”,依照佛教“教理”,予乐名慈,拔苦为悲,因而,用来予乐拔苦的种种方法、种种工作就是方便;“‘出世一语,乃‘控制自我,主宰因果,把握生死,创造更高的生命之谓,并无逃避现实及其他消极的成分在内”[3]735;“四大皆空”并非意味着佛教就是虚无主义。所以,巨赞说:“我们佛教徒积极起来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侵略、爱祖国的阵营,非唯不违反教理,而且在教理以及戒律上认为是‘功德,是‘离苦得乐的必由之道,应该认真去做的。这就是佛教及佛教徒坚决主张爱国的理由。”[3]736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佛教在现代复兴过程中的重要背景。巨赞认为,国家民族的灾难直接延伸到佛教界,佛教徒就不能不问世事、只顾个人修行,而要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也就是说,新佛教运动一定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实际上,巨赞组织的佛教青年服务团就通过散发传单、募款、写巨型标语、举办超度阵亡将士法会等具体工作参与抗战。黄心川说:“这几个团体(主要指巨赞组织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引者注)在抗日战争紧要的关头,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组织和救难活动,受到了僧众两界的爱戴,这也表达了法师救世济人的志愿。”[10]实际上,佛教徒对抗战工作的积极参与,不但可以实现自救,还可以挽救更多人的性命、维护更多人的利益;不但有贡献于佛教界,还有贡献于国家和民族。总之,佛教爱国主义传统在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就是支援抗战。朝鲜被美国侵略、我国安全受到威胁时,巨赞认为,替朝鲜人民解除痛苦就是中国佛教徒的任务,正所谓“抗美正是方便,援朝乃是慈悲”[3]735;越南遭受美国侵略时,巨赞也主张我国佛教徒应及时给予精神支持和实际援助。可见,佛教徒的爱国主义与他们予乐拔苦的愿望与行为紧密相连,凸显了对人的尊重。
在社会主义时期,巨赞认为佛教徒爱国的主题是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培养爱祖国的情感。“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也就必须热爱我们的祖国。”[3]1095而且,广大佛教徒对佛教在新时代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巨赞强调,佛教徒有了对祖国的爱,其“聪明才智才会用之于人民群众,才会恢复释迦世尊积极救世的精神,庄严自己的法身慧命,而把超然世外逃避现实的方外思想洗涤净尽”[3]1096。这样,佛教徒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实现与世俗生活的完美统一。
巨赞认为,佛教徒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是认真参加劳动生产,主要方式有参与耕种、造林、制茶、园艺、手工业等,只有“从工作中吸收社会与人生的经验,才能正视现实,建立做人的基础”[3]920。这是巨赞“生产化”僧制改革目标在新时期的体现,也是佛教徒在新时代唯一的自救之道。广大佛教徒要深入群众,主动走上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这种情形有利于广大佛教徒改变懒散、懈怠的精神面貌,诚如巨赞所言:“‘生产化则求生活之自足自给,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之陋习,如此则佛教本身可以健全,然后才能谈得上对国家社会的贡献。”[11]625同时,巨赞强调,广大佛教徒并不能因为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活动而放弃自己的信仰,这就要求佛教徒要在劳动的过程中善于学习“佛理”,这是对“学术化”僧制改革目标的体现。如他所言:“‘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博学慎思,研入世出世间一切学问,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11]625 不论是“生产化”,还是“学术化”,都体现了巨赞对僧尼现实人生的关怀,能够引导他们直接投身社会实践,且不忘失佛法,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佛教徒,这正是根本意义上的护教、爱国。
尽管有些言论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巨赞法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前瞻性的眼光、踏实的践行,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徒及时树立了可供参考的人生观。1933年太虚在演讲时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12]诚然,巨赞的佛教人生观体现了太虚所言佛教的“究竟归趣”,可以引导广大佛教徒在新时期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遗害,真正立足于人生,着眼于当下,促进佛教与整个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朱熹.张子全书序[M]// 四库备要·张子全书[Z].子部056卷:1.
[3](释)巨赞撰,吴志云主编. 巨赞文集(下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4]徐仲雅.咏棕树//全唐诗(卷762-19)[Z]:2953.
[5]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妙法莲华经(卷一)第7页//《大正藏》第9卷.
[7]李向平.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革命走向”——兼论“人间佛教”思潮的现代性问题[J].世界宗教研究,2002,(3):42-56.
[8]黄夏年主编.精选佛经注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19.
[9]郭朋.《坛经》对勘[M].济南:齐鲁书社,1981:91.
[10](释)巨赞著,朱哲主编. 巨赞法师文集·序言(上编)[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3-4.
[11](释)巨赞撰,吴志云主编. 巨赞文集(上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2]太虚.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太虚法师全书(第47册)[M].431.
(责任编辑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