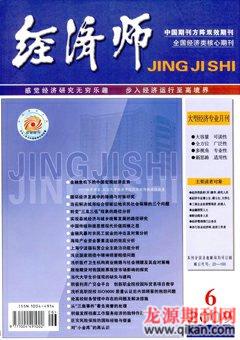杜甫人生最后岁月诗歌创作的审美特质
摘 要:杜甫人生的最后三年是在湖南长沙、衡阳等地的辗转、流离中度过的,这段时光既是他人生悲剧的高潮,也是他人生悲剧的结局。流寓长沙、衡阳期间,他创作了40多首诗篇。“但见性情气骨”、“不见语言文字”,构成了杜甫这些诗歌的审美特质;而这一审美特质的形成,又有赖于“缘事而发”的创作原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以及语言的朴素晓畅、白描手法的运用。
关键词:杜甫 诗歌创作 审美特质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6-102-02
杜甫作为光照诗史的一代诗圣,他的诗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真正好的素描,好的文体,就是那些我们想不到去赞美的素描与文体,因为我们完全为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所吸引”(《艺术论·素描与色彩》)。的确,当我们品位一幅名画时,大都有“身临其境”的美感,而不会仅仅瞩目于其中的色彩和线条。杜甫诗歌的美学成就,刘熙载在他的《艺概·诗概》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杜诗只‘有、‘无两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可谓一语中的。杜诗正是杜甫“性情”、“气骨”这些生命要素的集中体现,凝聚着诗人的生命精神,具有生气灌注的生命特征。“庾信文章老更成”,“但见性情气骨”、“不见语言文字”这一艺术形式美的规律,在杜甫晚年流寓长沙创作的40多首诗篇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请看他的《白马》诗:“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近时主将戮,中夜伤于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唐大历五年(770年)4月8日,湖南兵马使臧某杀死潭州(长沙)刺史兼湖南都团练观察史崔贯鹳,据潭州为乱。杜甫这时正流寓潭州,和无数百姓一起逃难,从城里逃回自己的船上后,便直奔衡州。这首诗就是写潭州至衡州途中所见情境。诗篇通过描写一匹从战乱中仓皇逃逸的白马,寄寓对死难将士的深沉哀悼和对乱臣贼子的无限愤慨。“丧乱死多门”,言简意丰,含蓄深厚,语句沉痛。仇注:“丧乱一语,极惨!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惟身历忧患,始知其情状。”结句“呜呼泪如霰”,“卒章显志”,正是诗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表现。杜甫诗歌字字句句渗透着这样一种爱国热诚,不管自己生活怎样艰苦,也不管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769年秋,杜甫在潭州遇到天宝年间的故交裴虬,裴虬将去道州任刺史。杜甫送行时殷殷劝勉:“上请减甲兵,下请安井田”(《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其实,此时的杜甫生活困顿到了极点:在湘江边搭起一间极为简陋的房子,名为“江阁”,在周围种一些草药蔬菜,并在渔市上摆设药摊,出售药材,以维持起码的生活。自顾不暇,却仍然时刻以苍生为念。即使是对自然现象,比方对“雨”的态度,也不忘从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定臧否”、“别善恶”。大雨滂沱,屋漏不止,他竟喜不自胜:“敢辞茅苇漏,已喜禾黍高”(《大雨》)。倘若久雨成灾,殃及庄稼,他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这就是诗人杜甫的“性情”和“气骨”。这种“性情”、“气骨”甚至在流连山河美景时,也会迸放出耀眼的火花:“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清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叶燮这样评论杜诗:“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原诗》外篇上)。可以说,杜甫每一首诗,特别是流寓湖南长沙的诗歌中,几乎都屹立着一位忧国忧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即诗人的自我形象),鲜明地展示着诗人的“性情”和“气骨”,显示出诗人独有的审美气质。而这种特有的“性情”、“气骨”的载体,是作为文学第一要素的语言。由于这些语言文字运用的准确自然,恰到好处,因而把“性情”“气骨”表现得出神入化,致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往往“但见性情气骨”而“不见语言文字”。那么,杜甫诗的这种审美特质是怎样形成的?
一、“缘事而发”的创作原则
刘勰总结了《诗经》和《汉赋》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归纳为两种情况:“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并且指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文心雕龙·情采》)。杜甫正是继承了《诗经》、《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以时事入诗,以“行”诗写时事,强化了诗歌反映现实的直接性、及时性,所以他的诗歌,都是有感而发,是真情实感的自然宣泄,是“为情而造文”。这种创作原则,在流寓长沙的诗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长沙是诗人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一个驿站,是他人生悲剧的“高潮”和“尾声”。他流泄在诗篇里的衷情悲慨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为深沉而真切。如大历五年逃臧某之乱中写的《逃难》:“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这是一幅多么伤心惨目的离乱图。“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即所谓“人寰难容身”,以乾坤之大,竟找不到一处安身之地,极写世乱,也表明诗人不为当道所容。“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自己虽然贫病交加,但仍然系念着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具有“民胞物与”的至仁至爱之心,这正是杜甫“性情”、“气骨”中最可宝贵之处。
“为人重晚节,行文看结穴”(林纾《春觉斋论文》),“结穴”是作品的“凝光点”,是一篇之中精神命脉之所在。《杜诗镜铨》说杜诗“结有远神”。因此,杜甫由“民胞物与”而升华的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在诗篇的结尾处往往“画龙点睛”,把他忧国爱民的思想,蘸着热泪凝成结句,使诗人的思想得到集中而强烈的表现。这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一脉相承的。《宿花石戍》的结句是:“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诗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一千余年前湘潭人民在战乱中的惨状,诗人自己也与无数难民一样流离飘零,却仍然在呐喊着“谁能叩君门(指官府之门),下令减征赋”。杜甫始终坚持“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的观点,就是在他的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呈奉湖南亲友》中,杜甫也仍然念念不忘尚在流血的黎民百姓:“血战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一种多么广阔的襟怀和高尚的思想!追根溯源,杜甫的思想基础乃是传统儒家“仁能爱民”的“民本”思想。战乱的时代,使他直接置身于黎民百姓的现实生活之中,有机会接触、了解人民的疾苦,与下层人民有相同的苦难、忧虑、欢乐、希冀。这种现实生活促使他的“仁能爱民”思想日益迸发出璀璨的光芒。最能体现诗人这种思想的作品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篇作品的结尾,杜甫饱含激情高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句句有泪,字字是血,见心见性,这是杜甫同情人民疾苦、关心人民生活思想的集中表现,杜甫这种“宁苦身以利人”的炽烈的忧国爱民情怀和迫切要求变革现实的愿望,千百年来一直扣响读者的心弦。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们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诗人正是通过自己的歌唱,抒人民之情,吐时代之声,这正是作为伟大诗人的杜甫留给后世的光辉的文学传统,也是构成杜甫诗歌审美特质的根本所在。
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
杜甫是一位具有清醒的语言意识且极为严肃严格的修辞家。他的语言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毫发无遗憾”,这些都说明他在语言运用上所下的功夫,表明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创作态度,也反映出他的审美思想,决定着他的诗歌创作的审美特质。这样锤炼出来的语言,精工、凝练,言简意丰,能更有力地表现和凸显作者的“性情”、“气骨”。例如,大历五年在长沙所作的《小寒食舟中作》的颈联:“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这一联描绘了舟中江上的景物,第一句“娟娟戏蝶”写舟中近景,故曰“过闲幔”。第二句“片片轻鸥”是舟外远景,故曰“下急湍”;这两句承上,写由舟中外望空中水面之所见。“闲幔”的“闲”字回应首联第二句的“萧条”,布幔闲卷,舟中寂寥,所以蝴蝶翩跹,穿空而过。“急湍”指江水中的急流,片片白鸥轻快地逐流飞翔,远远离去。画面的主角是“蝶”和“鸥”。蝶,色彩鲜艳、动作轻盈,以“娟娟”形容恰到好处,因“娟娟”表示“美好貌”;“轻鸥下急湍”,有迅疾如飞之感,所以在“轻鸥”前冠以“片片”,与飞驰气势相得益彰。如此闲适的景致,粗看,似乎感觉与结句“愁看直北是长安”中的“愁”字有悖;细品,方能体味到此联实是含蓄蕴藉,别具匠心。因为正是这样蝶鸥往来自如的景色,才易于对比引发出困居舟中的作者“直北”望长安的忧思,所谓“以乐境写哀境,以哀境写乐境,倍增其哀乐”(《船山遗书》),显示出鲜明的艺术辩证法,也由此向尾联作了十分自然的过渡。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引朱翰语云:“蝶鸥自在,而云山空望,所以对景生愁”,也是看出了第三联与尾联在景与情上的联系。可见,杜甫的锤字炼句,决不是孤立地对一字一句进行斟酌推敲,而是像条条血管都流向心脏一样,字字句句都向作品的题旨、情调、意境等整体构思汇聚。这样运笔,就使得诗作的语言更扎实、浑厚,简练有力,从而更充分地显示出作品的“性情”、“气骨”。
黑格尔说:“诗是心灵创造的新世界。”人们欣赏诗歌,不是单纯去了解客观事物,而是希望从中体验到某种感觉、某种情绪、某种只可意会而难于言传的领悟以及某种值得咀嚼的联想。杜诗的语言正符合这一审美机制。在《逃难》诗中杜甫发出这样的浩叹:“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乾坤万里,难容一身”,这种巨大的反差,显然不合事理,然而它却符合“心理”,即符合诗人特定的心理感受。这正好准确传神地表现了杜甫在战乱时期颠沛流离、走投无路中所产生的极度的抑郁和愤懑。雪莱说:“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诗句正是通过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段,真切地抒发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披文入情”,“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抒发的不仅是自我之情,也有家国之恨。因为接下来的句子是:“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他是为“故国”,为“邻里”,为苍生而一洒伤心泪!诗人在大历四年(768)春离开潭州赴衡州时所作的《发潭州》,描写启程时的情境:“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岸上风吹落花,樯桅春燕作语,这本是极普通的自然现象,但诗人以我观物,把落花、樯燕拟人化,托物寓意,感觉落花在送行,春燕似挽留;时局的动荡、诗人的寂寥、世情的淡薄,蕴含在飞花燕语中,情景妙合,表现出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
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在他晚年创作的诗歌系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苦心锤炼、雕琢,以其无论穷达都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的情怀和极为细致敏锐的现实感受力,借助恰切的修辞手段,吟哦咏叹中,激荡出杜甫式的“性情”、“气骨”。
三、语言朴素晓畅
诚然,在创作态度上,在追求诗歌语言表达的准确生动上,杜甫的确孜孜以求,力争做到“毫发无遗憾”。黄庭坚称他的诗为“无一字无来处”,这一看法虽然不免有些迂执,不过,在一字一句上,确实可以看出诗人的锤炼之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追求语言的深奥奇谲、冷僻怪诞,相反,他是非常注意行文的朴素晓畅的。在《戏为六绝句》中说“恐与齐梁作后尘”,就是诗人自己防止诗歌语言堕入“靡丽浮华”的自警。
杜甫诗歌语言的朴素主要表现在屡用口语俗字方面。宋人黄彻曰:“数物以‘个,谓食为‘喫,甚近鄙俗,独杜屡用:‘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栏添个个”(《溪诗话》卷七)。宋人孙奕亦曰:“子美善以方言里谚点化入诗句中,词人墨客口不绝谈”(《履斋示儿编》卷一○)。如:“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之六);“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兵车行》)。用语自然,通俗如口语,又极富表现力。在他人生最后岁月创作的诗歌中,依然保持了这一特点。请看下面几首诗,《逃难》:“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宿花石戌》:“午辞空灵岭,夕得花石戍”;《岁晏行》:“去年米贵缺军粮,今年米贱大伤农”……句句诗行,清新晓畅,明白如话,以它“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魅力,吸引读者进入诗人所营造的审美意境。特别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江南逢李龟年》,更是朴素感人:“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是杜甫晚年的代表作,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然用语却极平淡、浅近、素朴。仅仅二十八个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岐王宅里”、“崔九堂前”是“开元盛世”的真实写照;江南暮春、落花如雨则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败不堪的艺术写真;“落花时节又逢君”,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使人感到诗篇中字字蕴含着“民生多艰”、国运衰颓的慨叹,句句浸透了诗人身世落寞、黯然神伤的泪痕。清代黄生《杜诗说》评论:“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短小的体裁,明白浅切的语句,诗人却能举重若轻,浑然无迹,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抒写出丰富的人生体验。
四、善用“白描”手法
白描是中国国画传统的技法之一。其特点是用线条勾描,而不着颜色,不作任何渲染铺陈。它源于古代的“白画”。在文学创作上,“白描”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是指用简练的笔墨,不加任何修饰和烘托,直接描画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描写技巧。这也是中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描写技巧之一。杜甫长沙诗歌的创作中,绘景、叙事,状物、写人,都经常会有精妙的白描闪现。比如,“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南征》),十个字四个意象,把湘江两岸和春天的景色描绘得绚丽迷人;“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铜官渚守风》),寥寥十字,留下了潭州(长沙)先民生存耕作的状况;“水阔苍梧野,天高白帝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水阔天高,空旷渺远,透出举目非故乡之感;“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燕子来舟中作》),燕子娓娓絮语于船樯,穿花掠水,迟迟不肯离去,诗人见此情状,倍觉伤神,开始感悟到:人事冷漠,唯动物有情。“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白马》),“空鞍”暗示马的主人已于战乱中丧生。这是诗的起句,开门见山,破空而来,营造出一种悲壮氛围,它与结句“呜呼泪如霰”一呼一应,神完气足地宣泄了杜甫感时伤怀的爱国情怀。“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岁晏行》)。开头四句就把一个冰天雪地的潇湘与百姓正在为生计而打鱼捕鸟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眼前。白描最为动人的应为杜甫死那一年或之前一年,漂泊长沙时所作《楼上》(五律)的首联:“天地空搔首,频抽白玉簪。”苍茫天地间,一个贫病流离、满腔热血的老者,像电影中的蒙太奇,凸现于读者面前的只是一个频频抽动白玉簪挠头的动作,这一细节,把诗人那种忧国忧民的内心、倍受煎熬的苦痛揭示得十分真切、深刻!黄生说:“天地二字之下,却押一极细之事,读之失笑。然作者始吟出口,必定失声痛哭也。天地二字已奇,更奇在空搔首之下,仍接次句五字,其词愈缓,其意愈悲矣。”可谓知音。这个白描手法雕塑出来的“空搔首”的悲剧性的造型十分动人,千载而下,读之犹令人不得不“感叹亦歔欷”!杜甫的“性情”“气骨”由此也得到了鲜明和强烈的表现。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一般人无法想象和承受的政治挫折、贫穷、饥饿、疾病、逃亡,这些苦难与坎坷,铸就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造就了那一篇篇超越时空的动人诗篇,特别是他人生最后岁月创作的诗歌,以情感生命的起伏为起伏,极力追摹生命的节奏,“性情”、“气骨”这些生命要素,赋予了杜甫长沙诗特殊的审美意蕴。由于诗人情感力度的强大,人格魅力的动人,写景叙事的白描,更兼遣词造句的质朴,使读者在欣赏时这些诗歌时便自然“但见性情气骨”,“不见语言文字”,由此也构成了杜甫暮年诗歌的审美特质。
参考文献:
1.肖涤非.杜甫研究[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阮堂明.杜甫研究学刊[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肖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4.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刘春芳,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山东泰安 271021)
(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