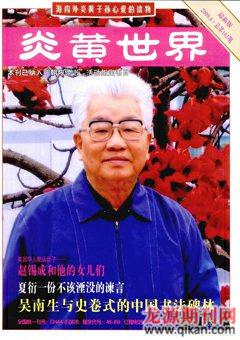鄂伦春族第一个女博士的生活与梦想
刘晓红
编者按:13年前,老《炎黄世界》杂志1996年第4期刊登了周传荣同志所写《鄂伦春猎人和他的“大秀才”女儿们》一文,文中介绍了一位鄂伦春著名猎手刘本占和他六个女儿的感人故事。这“六朵金花”在艰苦的环境中,个个奋发向上,学习用功,工作努力,一个接一个地考上大学、研究生。
现本刊再次发表这六姐妹中“老五”写其姐姐“老四”——鄂伦春族第一个女博士的生平事迹。文章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意境优美,鄂伦春族独特的生活情景与别致的习俗跃然纸上;整篇文章字句中缠绕着少数民族独有的幻影与色彩,给读者以极大的美的享受。敬请读者注意。
上个世纪80年代,如果你有幸是个大学生,那你绝对是一个展开金色翅膀的幸运天使,梦想如天际的白云翻滚升腾,激情似花朵般的热情拥抱太阳。青春常在,美妙醉人,仿佛《红莓花儿开》之中唱的那样: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我的姐姐刘晓春,正像从这诗画般的俄罗斯歌曲中走出来的娜达莎,艳丽动人,带着贝加尔湖祖先们凝神的双眸,带着鄂伦春人与生俱来的热情和虔诚,带着一个少女种种的好奇和幻想,开始多姿多彩如梦如幻的大学生活。然而,在愉快而紧张的学习之余,走在曲径通幽的小径上,或躲在大大的梧桐树下读书的悠闲里,姐姐的心头时常会跳出“思念”这只小鸟,它总是飞过万水千山,不知疲倦地飞回那个遥远的地方,借一株白桦树栖倦。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地方,正是遥不可及的故乡,那绵延的兴安岭、奔流的刺尔滨河,正是她梦幻开始的地方哦。
森林花仙子的童年
童年是什么?一些迷迷糊糊的往事,一些渴望的落空,一些新奇的发现,而背景则是一个山水环抱的小村庄,一个鄂伦春、汉、蒙、满杂居的地方,一个父母双全、兄弟姐妹众多,外加几十匹马、两条狗、八只鸭子和十六只鸡的大家庭。
姐姐是村里出名的小美人,宛如一块美玉,清纯、润白、沉静,后来乍看《城南旧事》,总疑心那个小英子是姐姐幻化的。上世纪70年代的小山村,人们过着艰苦而朴素的生活,但在春暖花开的初夏时节,刚上小学的姐姐却穿着妈妈为她缝制的奢华的碎花小旗袍,走在起伏不平的小路上,迈着小步,淑女似的走路。
等我上小学时,爸爸就把我们当小大人看了。秋天是榛子成熟的季节,爸爸会不定时地把我们带到大山里,留下我们在榛子稞里采集榛子,好比棕熊训练小熊一样,让我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学会自力更生、掌握种种技能和知识,可谓用心良苦。但那时,我们太小,姐姐12岁,我9岁,在运离小村十几里的深山坳里,心里害怕山里的野兽,又不敢说,所以总是抱怨爸爸心太狠。
记得那次,天高气爽,灌木丛里散发着秋天特有的香气,不知名的鸟间或唱着婉转的歌,我俩像勤奋的松鼠一样忙碌着。快到中午时,姐姐不见了。我钻出榛子丛,发现她正在给我们的坐骑——一匹漂亮的大白马驱赶蚊虫。过了一会儿,又说马渴了,要去小溪边饮马!
姐姐不仅细心、善良,并且总是对许多事物情有独钟。她把大山、河流、花朵、山雀、猎马都画在纸上,栩栩如生,可爱活泼;还把对故乡、父母、姐妹、教师的情感,写到作文中,时常受到老师的好评和同学的羡慕。姐姐生下来时,胸前有一小块淡红色的胎记,因此妈妈常说:“我的四女儿将来可是要戴大红花的。”姐姐的聪慧好学、富于爱心从小就显露出来,甚至对于我们家的“鸭先生”和“鸭太太们”也照顾得无微不至,以至于“鸭先生”长得肥壮高大,蓝绿色的头冠和羽毛总是闪闪发光,骄傲自大得“篡夺”了猎犬黑子的职务,为我们看家护院,姐姐也就得了“鸭官”的美称。
在我们家,母亲的角色举足轻重。我们的母亲有一个动听的鄂伦春名字——吴恰坎·戈儿巴,即洁白美丽的意思,汉名云花。其实,鄂伦春的语言非常丰富而富于诗意,它是流动而灵性的,浸泡了花草的气息、松涛山川的浑厚。吴恰坎·戈儿巴不仅描画了淡远白云,还有白云舒卷下的河流,甚至开放的花朵、白桦树下深眸浅笑的少女!然而如此美丽而贤淑的母亲,一个承载着七个儿女无限依赖的母亲,却在一次意外中生了一场大病,永远失去记忆。这对于我们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创伤,真希望灾难发生的那一瞬,将画面剪去,让时间静止。母亲的记忆停留在花好月圆的岁月,总是做些孩子气的恶作剧。失去母爱的感觉好像寒夜里穿着单衣在行走,孤独而清冷,尤其是看到因母亲的失忆而日渐沉默的父亲。我们想,也许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使父亲心慰;也许走出大山,才能请到名医为母亲恢复记忆。我们最初的努力,也许就是基于如此单纯的报孝双亲的愿望。山的那边,有希望、有梦想……
回首探寻时间的走廊里,在鸟鸣枝头或细雨纷飞中,在月色阑珊或红粉尘色里,姐妹们互相鼓励着,而姐姐的努力尤为突出。小学、初中,姐姐的老师都是黑河或上海来的知青,带来了各种新知识新信息。在他们的影响下,姐姐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欧阳海之歌》、《雷锋的故事》、《青春之歌》,加上每周一次的革命电影、春节和秋收时的大汇演,这一切都为姐姐的人生注入了新鲜而向上奔流的血液。就是到了黑河一中寄宿的日子里,姐姐也一直保持了刻苦、忘我、充满活力的学习精神。
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在三姐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的第二年,四姐晓春也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
大学的日子紧张而忙碌,读不完的好书,学不尽的知识,五花八门的演讲会,各种诗会、画展、甚至来一个小小的约会!在大学流光溢彩油画似的浓烈背景中,四姐穿着白底上飞着蓝蝴蝶的上衣,配着湖蓝色短裙,清纯可人,活泼中带着水色迷离的忧伤。所有关于人生遐想的轻飘,都最终回归于故乡那块温柔而少语的黑土地。是的,那个大山深处几乎与世隔绝的民族,那个神秘而浪漫的鄂伦春,那个与她血脉相连的兴安岭,她又如何能够忘记!责任就从关注开始吧!四姐在大学期间对鄂伦春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内容涉及狩猎文化、民族风格、宗教、鄂伦春人的现状及经济等诸多方面。鄂伦春,一个响亮的民族,一颗闪光的宝石,在它的光耀下翩翩起舞的是森林的仙女,在千年的荣耀里闪动着华美的光辉。
激情岁月
晓春姐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号称东方小巴黎,然而在它的旋转木马般的热闹中,四姐却是寂寞的。寂寞的精灵来自幽暗的丛林,闪着蓝色的翅膀。
四姐的生活虽然单调而沉寂,但她并不孤独,她有众多的学生。在讲台上四姐是生动渊博的讲师,她能把枯燥的经济学讲得娓娓动听,我把这也归结为“鄂伦春的才情”。鄂伦春人天生智慧而幽默,总是语出惊人,让人笑而感动。我想那是大山、河流、森林、动物们赐与我们的才能!姐姐的爱好既有鄂伦春人的天赋,也有其丰富人生的积累。
梦想是生活的原动力,为了有更大的发展,为了鄂伦春,为了忘不掉的北京城,四姐再一次显露了她惊人的努力,于1992年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重新走进了熟悉而温馨的大学校园。
研究生生活是四姐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四姐在三年的时间里,如一个修行者,坚定自信地钻研。在导师——知名的民族学家、经济学家施正一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思维方式、知识结构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她在读研究生期间发表了30多篇文章,有的还获了奖。“春风得意马蹄疾”,那时的姐姐充实忙碌而颇有建树,硕士毕业又连读博士。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仅有几千人的鄂伦春出了第一位博士,不禁令人刮目相看。
姐姐一时间成了名人,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采访、报道。母亲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四姐真的戴上了大红花,登上了荣誉的舞台。然而就在四姐即将攻读博士学业之时,母亲却离开了我们,她像一只大鸟,又似一朵轻盈的云飘远了。此后,只在斑驳的梦里与我们无语相对,用温柔的目光向她的孩子们传递着无限的希冀。
1997年的夏天,父亲来到北京与我们团聚,那时三姐、四姐(刘晓春)、我(老五)、小妹都在北京。1998年7月,四姐博士毕业,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为了父亲,四姐向单位申请了一个20余平方米的小平房,座落在民族大学西小院里。春天,父亲就带领我们把菜园的土挖松,然后种上花籽、菜籽。初夏时,爬山虎像一张绿网一样笼罩了围墙,牵牛花、土豆花开满庭院,青椒、大葱、小白菜长满菜园,我们悠闲地围坐在小院里,摆一碟瓜子,沏一壶浓茶,听父亲讲一些我们儿时的趣事。头上挂满了细长的丝瓜,还有青色的小葫芦,合着树上“知了娘娘”的叫声,幸福时光真如蜜糖一样浓得化不开!这都市中的乡村情趣、幽然的处所都是在四姐的努力下赢得的,使父亲的晚年在子女们的呵护下过得平安、快乐而满足!然而,那间温暖的小屋很快就被研究所收回去了,为此,姐姐伤心了很久。
家里有一张照片,是中央民族大学在为四姐和三姐颁发硕士证书,以及鄂伦春自治旗为姐姐们颁发奖学金时的照片:两个姐姐戴着硕士帽,笑逐颜开;老父亲呢,神色凝重,眼里还闪动着泪光。在姐妹们丰饶的收获里,包含着父亲一生的耕耘啊。如今老父亲已经不在了,隔着时光的距离遥望,依旧能感受到父爱的热度和辛酸!姐姐经常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老爸,尤其是住上新楼以后总是说“爸爸如果还健在该有多好”,然后就默默地流泪。
四姐在学术上的研究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生活中却好像大智若愚、智商不高。她爱美却不善于打扮,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上次去过的地方下次照样找不到,有时和小孩子也较真,有时又语出惊人,有时幽默搞笑。我们姐妹几个喝酒都是海量,老爸为六个千金豪饮的个性注解为——龙王爷的闺女会凫水,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每一次大家微醉时,四姐都会为我们跳起山寨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总是把大家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四姐、姐夫在最恰当的时候相识。虽然谈不上一见钟情,却也情深意浓。姐夫基本上具备了好男人的一切优点,并且也比较帅。姐夫本是纯粹的南方人——福建莆田人,但在四姐的影响下,姐夫也变成了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的鄂伦春式的男人。
这样琐碎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许最能显露出一个女人真实的一面。我佩服工作中勤劳如蚁的四姐,更喜欢生活中平和且温婉、妙语连珠的四姐。
收获的季节
一个人的奋斗,或者说一个女人的奋斗,最初也许只是儿时的一个小小的幻想,或者年少时的一些白日梦,但时间的河流从未停止过,它兼容并蓄,吸纳了山泉和雨水,也吸取着所流经土地的营养,她的执著也因此从来不是孤独的。母亲不离不弃的目光,照亮了她的童年;父亲坚实的臂膀,托起了她的欢乐;姐妹亲朋的关照增强了她的信念;师长睿智的教诲,为她开启了一扇扇奇异的窗口。为了身边每一双关注的眼神,为了那些贫穷的挣扎和坚强,甚至为了一抹依旧璀璨的彩霞,为了那颗启明星闪烁在永远清新的黎明里,这一切都可以是她努力的源泉,然而在一系列艰苦、严谨的,看似不夹杂感情因素的各种社会调查和考察中,都是由一些丰富又令人难忘的旅行构成的,那一次去新生鄂伦春族乡的社会调查,都给四姐很深的感触。
住在新生鄂伦春族乡村那间又旧又小的旅店里,四姐夜里被跳蚤咬醒,慢慢踱到户外,那漆黑的夜空里闪烁着硕大明亮的星星。乡里的鄂伦春人不足200,大部分仍旧怀念狩猎,不喜欢掌握汉民族沿袭了几千年的耕种方式,虽然国家一直实施各种优惠政策,但鄂伦春人的现状仍然令人担忧。民族语言迅速消失,狩猎活动早已被禁止,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以及乱砍乱伐等因素的干扰,兴安岭的自然环境已千疮百孔,人们的精神家园呈现衰落现象……每当想到和看到这一切,都会使四姐忧心忡忡,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旅店很简陋,门口有条小河,随洗随用,不必换水。那条河,正是我们小时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索尔其干河,但是,河水已没有从前透明了,小鱼也不见了。
离开新生村的那个夜里,雨下得很大,沼泽地和丛林里散发出幽湿的气息,如此浓烈地穿透越野车的窗子扑进四姐的鼻翼里。在浓密的黑夜里,松树在车灯的闪烁中忽明忽暗,飞舞的雨珠像一些挥别的眼泪,又像一些天上飞坠的星星,与故乡走出的四姐欲语还休。“鄂伦春”对于我们姐妹有时像妈妈缝制的狍皮褥子,温暖安详;有时又是一处伤口,深入骨髓,痛彻心扉。
在写博士论文时,最初四姐打算写一篇关于鄂伦春族经济发展方面的论著,因为对这个选题的熟悉及个人情感方面的偏重,姐姐很自信,但在导师那里却没有通过。导师说:“小题大做当然重要,但大题小作则非作不可。我不反对你写鄂伦春族经济问题,博士毕业以后完全可以写,但博士论文不仅要反映出博士生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拓宽你的思路、培养你的驾驭能力,并考虑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此,姐姐重新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即《俄罗斯的民族经济及其改革之路》,论文从民族的视角和文化的视角去研究俄罗斯这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的发展问题,洋洋洒洒,共7章、41个问题、27万字。四姐说,研究鄂伦春族问题固然能使我成为一个鄂伦春问题的专家,但如果以此下去的话,我的思路将永远不会走出鄂伦春族的圈子。正如一个日本学者所说的,作为一个人我们是无法看到自己的后背的,我们只有通过研究他人才能了解自己的另一面。四姐说:“地球是个家,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话。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祖国开始,扩大到爱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尊严的个体。唯有如此,你的爱才会更宽容、更无限、更有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朝这种善良、博爱、慈悲而智慧的方向努力,那么天空永远蔚蓝、森林永远昌盛、人类永远欢乐、动物们也不必睁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四处逃窜,一切都在纯净、明朗、平和、安宁里流转……”
说了四姐这么多,一定不能落下她身边的那个小精灵——四姐的女儿爱赫。
一个女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一个孩子来勾画她最艳丽的一笔才算圆满,四姐也不例外。没小孩子时,四姐一直把学问放在第一位,自己也永远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自从有了女儿,四姐忙碌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和乐趣,虽然更忙更累了,她反而觉得幸福。
一个鄂伦春女人,一个女博士,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在爱与责任的推动下,努力地尽自己的能力,改变着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事,甚至改变着鄂伦春。虽然这些改变在别人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那一抹光明,那一腔执著,那一份收获却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你望着一片成熟的麦田,金黄的麦浪轻轻起伏,它和你一起因为丰硕的收获而悸动。
我的四姐,就是这样一个童心未泯,朴实率真,事业成功,生活宁静的女人。她的人生,好像春天里冰雪消融的一条河,融化的冰互相拥挤着发出欢畅的撞击声,水面上漂浮旋转着一些去年的红红黄黄的叶子,鸭子柔软的羽毛、抽枝的红柳丝倒映在水中,还有白桦树俏丽的倩影,以及蓝天白云的写意,这条充满激情的河流不知疲倦一直流向远方。四姐的青春岁月也融入到她人生的激流中,就像她的名字“晓春”一样,常青常绿、鸟语花香、永不衰老、生生不息!
背景资料
刘晓春,女,1964年12月出生,鄂伦春族第一位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市第十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主要著作:《俄罗斯民族经济与改革》(专著)、《鄂伦春族风情录》(编著)、《鄂伦春历史的自白》(编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合著)、《鄂伦春乡村笔记》(专著)。文学作品:《走出白桦林》。《鄂伦春历史的自白》一书2005年荣获第三届内蒙古图书奖。主要论文:《论经济因素与民族因素的互动关系》、《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西部国有企业改革与亏损问题探析》、《青海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论西部地区如何实施名牌战略》、《西部开发与文化发展》、《狩猎文化与生态环境》、《鄂伦春族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鄂伦春族经济转型引发的思考》等。